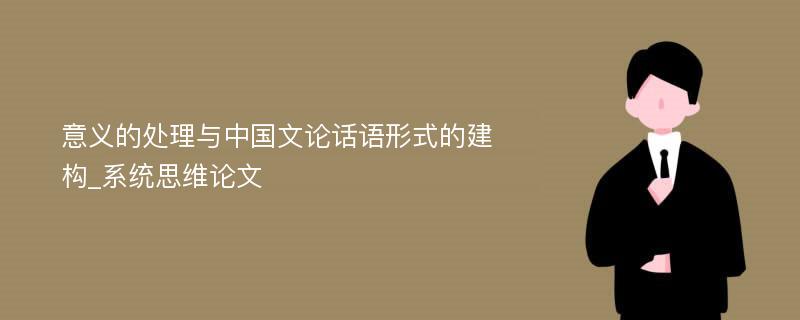
对待立义与中国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中国论文,形态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文论知识系统与阐释方法有着深厚的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基础,其理论思辨、致思方式与价值品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传统思维方式及其理论形态的沾溉,此一特质,尤其深刻地体现在文论范畴命题两两对举的构型及其所指述、所诠释对象的对待统一关系与规律上。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核心之一,对待立义广泛地闪现在古代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贯穿到古人对于天、地、人三界的理解中,成为古代知识体系中一个根本理念与致思方式乃至价值核心所在。探讨对待立义之源流统绪与质态特征,不仅能够使我们对中国古代艺术思想的话语形态、范畴特征以及审美价值追求有一个本源性的把握,而且有助于厘清古代思想史、观念史上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譬如作为对待立义思维最显在的观念对待,阴阳从直观的生命生活经验提升为一套圆融博厚人文理念的精神历程以及“两一观”所展示的古人在认识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所达致的思辨尺度等。本文拟从思想史和观念史的角度就对待立义的哲学基础与思辨特质进行一番知识学梳理,在此基础上,考察中国文论话语中对待立义所呈现的三大特质,即本体论意义上的对待型范畴群体、互动互释质态平衡的意义系统与对待立义求中和的审美价值追求,以及对于古代艺术精神及文论话语的培育与影响。
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体系特征,必然要追溯到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维特征、理论形态特点和价值取向以及建构文论范畴体系的方法论原则诸问题,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传统文论范畴的产生与中国古代文化哲学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不仅表现在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是从中国古代文化哲学范畴、命题导引而来,更显示在哲学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原则对文论范畴的形成及特征的潜移默化上。中国古代文论的对待立义思维源自传统哲学中以阴阳五行及“两一观”为核心的对待立义思想,并在随后的文学创作实践、批评鉴赏及理论建构中得以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所以探讨此一问题,我们不妨首先就对待立义所涵摄、所面对的哲学源流去了解,去分辨。
考察哲学意义上的对待立义思维①,大致思路有二:从思想史的路径考察,对待立义思维的渐次成熟是伴随着早期宇宙观的兴盛,并主要通过阴阳五行的发展演变而形成完整思想系络的。阴阳的起源,古今无有定论,无论从迄今发现的最早文字,如周原甲骨卜辞和西周金文中所见“阴阳”二字,还是《大雅·公刘》歌颂周人先祖择地而居的“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所指“阴阳”均是与天象、地理方位有关的知识概念。现代学者认为,阴阳作为范畴出现,肇端于《国语·周语上》中虢文公劝谏宣王不可废弛籍田仪节,以及伯阳父用阴阳失序来解释地震原因,从《周语》这两条材料来看,至少西周末年,人们已经开始用阴阳来解释自然界一些相互作用的现象。春秋战国以后,随着阴阳与五行合流,“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②,其思想精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汉儒董仲舒建构了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在“明阳阴、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的论断中③,阴阳五行遂成为了天地、四时、人事、性情乃至政治历史、道德伦理的关联性要素。宋儒周敦颐倡太极图说,太极依元气而立,化为阴阳,分而天地,变为四时,推而八卦,这种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的化生结构,完成了阴阳五行在哲学意义上的严谨结合。
从观念史的路径考察,对待立义思维是伴随着古人对于和同、物两与天人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而成熟的,原初形态在先秦业已确立,洎乎宋明精义全出,标示着古人认识客观世界和自身精神世界所能够达到的哲学尺度。从殷墟大量吉凶两端的卜辞来看,殷人已经习惯于一种两分的思维方式。在西周末年的“和同之辩”中,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晏婴“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史墨“物生有两”、“体有左右,各有妃耦”(《昭公三十二年》)等说法,已经是颇为清晰的“两一”观了。老子对于有无、动静问题的探讨,为对待立义建构了一个运动变化的思想体系,《老子》一书,对待立义概念近乎百对,所谓“反者道之动”相互转化的思想亦很饱满。易学总结了对待立义的三个核心命题:“生生之谓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构成了古代知识系统的基本框架。在理学家的形上建构中,对待立义业已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和系统的理论形态了,譬如张载围绕“一物两体”④的阐释,将对待立义相反相成、循环往复、物极必反的特质揭示得相当清楚。至此,对待立义在古代哲学思辨中的发展线索已然清晰,借助气之阴阳对待与循环化生的阐释路径也相当明确了。
在我们看来,所谓对待立义是认识天地人关系的一种方式。在古人的意义世界里,气被理解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作为气之两重性,阴与阳遂成为划分与贯穿所有生命体的对待项,并随着五行的程式化而成为象征宇宙力量的符号称谓。二元对举的方式普遍存在,阴阳的消长、五行的制约是宇宙生成、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总则,无论世界怎样变化,无论人事多么复杂,均可以纳入阴阳五行的解释框架与理论视域中,对古人而言,对阴阳五行的理解也就意味着对天地宇宙前生来世的理解了。以上所述旨在说明,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对待立义思想方法,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方法论原则,源自古人在长期自然、社会、人事观察中对天地人之间最一般联系和最深刻本质的探索,其思想精髓浸透到古代哲学、政治、宗教、艺术、医学、军事、地理诸领域。中国古代文学精神中,正因为包含此一思想基因与文化质素,所以才能既自成体系又独具民族特色。
对待立义思维方式的形成,是建立在天人学知识框架以及气化流行、循环恒变运行模式上的。考察其基本特质,大体有二:一而二的对待性、两归一的立义性。所谓对待性,即两两相对,缺一不可,这是天地人同生共在的结构,按照方以智的总结,“夫对待,即相反者也”,“有一必有二,二皆本于一”,“所谓一切对待之法,亦相对反因者也”⑤,也即一在二中,一参于二,阴阳对待,一气贯通,共同分享着天地人的一致性和类比性原则,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就是两两相对的对待型范畴群。
体系庞大的对待型范畴,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史上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这是古老的对待立义思维方式在话语形态与范型模式上的重要思想遗产。清人刘熙载《艺概》论及文学作品之内容、形式、风格、意境诸问题时,运用了一系列的对举范畴,如正与变、义与法、质与文、丑与美、疏与密、益与损、轻与重、实与虚、内与外、形与神、曲与直、断与续、深与浅、意与象、聚与散、真与伪、弛与严、幽与隽、淡与旨、平与奇、柔与刚、圆与方、细与阔、婉与直、逸与敛、是与异、含与露、皱与透、稳与超、徐与疾、僻与熟、隐与秀,以及结实与空灵、沈著与飘逸、复古与从时、出色与本色、人籁与天籁、俊致与狂逸、优柔与清深、醉厚与雄奇、迂徐与直捷、柔婉与硬直、沈著与飘逸、缠绵与超旷、幽淡与雄快、凝重与流动,等等,这是历代诗文评中所见数量最为庞大的对待立义范畴群。这些两两对举的范畴莫不因对待性的关系而提出,且于彼此串连结合中,形成另一层次或更高层次的立义性动态关系,其内涵和外延既独立又关联,于互动互释中展现出文本创作与审美鉴赏之浑然天成与韵味无穷,充分展示了刘氏所秉承“文之为物,必有对也”⑥的诗学主张,在他看来,这与《易传》“物相杂故曰文”,《国语》“物一无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目前所见的典籍来看,这种两两相对范畴的大量出现是很早的。上世纪70年代马王堆出土的《老子》乙本帛书《称》,提供了迄今最早的二元对举义项,其中涉及天、地、人的名目综合且庞杂,如云:
凡论必以阴阳□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重国阳,轻国阴。有事阳无事阴。信(伸)者阳屈者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取(娶)妇姓(生)子阳,有丧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客阳主人阴。师阳役阴。言阳黑(默)阴。予阳受阴。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过正曰诡□□□□祭乃反。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⑦
此一阴阳相应的语义系列,基本上囊括了早期对待立义思维的核心要素,虽然前者(主于阳)较之后者(主于阴)不乏具有在先与主导,但在本质上,天地、乾坤、男女、尊卑、内外、刚柔、君臣、高下这些相互对应的范畴,乃是以阴阳固有特质为基准,涵括规律、形式及缘由诸义,并透过此一特质来了解衍生系统中的对象,故而此一类对举范畴互为体用,缺少一方,另一方亦不复存在。
在古代中国,作为最普遍的思维方式,对待立义囊括了先民的宇宙经验、社会经验和生活经验,在社会各个阶层得以普及与运用,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这既是古代人文知识形成的运思方式与心理基础,又是古代社会知识产生的思维机制,因而也就自然渗透到古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并对传统时代的文化心态乃至人文理念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汉以后的经学传统中,阴阳五行对举的方法被经师们普遍采用,成为经学作用于现实政治和社会人生的一条有效路径。对于古老的对待立义思维方式,传统时代的学者大都心领神会,文论家们使用其诠释范畴之所生、之所变与哲学家使用其诠释天地万物之基始、之思理,如出一辙。对此,清人叶燮的论述颇为经典,《原诗·外篇》云:
对待之义,自太极生两仪以后,无事无物不然:日月、寒暑、昼夜,以及人事之万有:生死、贵贱、贫富、高卑、上下、长短、远近、新旧、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种种两端,不可枚举。大约对待之两端,各有美有恶,非美恶有所偏于一者也……推之诗,独不然乎!舒写胸襟,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叹,寻味不穷,转益见新,无适而不可也。
叶氏秉持“虚实相成,有无互立”的对待立义原则,将之熟练地运用于诗学诠释活动中,这是其文学理论建立的哲学基础。他反复强调万事万物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对立、相比较的,凡物必有对,有有必有无,有弃必有取,有美必有恶,“偏于一者”不可取。这种关于对待立义的理解,基本上代表了清代学者的一般看法。在中国古代以意会体悟为核心的知识生成模式与话语表达方式中,对待立义无疑是一种具有开放性,且蕴含多种可能性的方法论原则,故而广泛运用于诗文评以及骈文、对联等各种文学样式中。
作为一种有效的理论建构方法,对待立义所涵摄的两两相对、相反相成与循环往复、物极必反等理念亦内化为古代文论的理性品格与文化基因,运用于创设概念、范畴、命题、营构体系及品评鉴赏中。历史地看,自先秦以来的文论史,甚至就整个古代文论史的发展衍生来看,文学理论的诸多核心问题均趋向于对待立义结构或动态关系的把握与诠释⑧。从观念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史的中心范畴大都可以从对待立义结构或动态关系来考察,这是古人从思辨层面把握文学现象及其本质规律最直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考察大量成双作对范畴的构型特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并生互渗类,一是发生共构类。
前者如中和、教化、美善、诗乐、情志、形神、险僻、奇怪、直舒等,此类范畴两语素边界模糊,相蕴相含,互动相生,分殊而合,关照方位与指述对象在相互阐释与吸纳中呈现出开放的特征。以中和为例。中和范畴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三代以来“尚和”与“尚中”意识培育而成的⑨。在古人看来,有天地人之和,始有钟鸣鼎食之政和、人文之和,而达于“和”,必求于“中”,当触及对待面之转化时,“和”与“中”才相联系。对此,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认为:“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并进而断定:“中之所为,而必就于和。”董子认为天地之道“起于中而止于中”,“中”是规律、尺度,“和”是境界、目的,没有“和”的境界,“中”就失去意义,没有“中”的尺度,“和”亦无法达致。就对待立义思维而言,中和范畴的构型特征在于:和中有中,中中有和。
后者如文质、古今、虚实、巧拙、动静、奇正、浓淡、隐显、雅俗、真幻等,此类范畴两语素虽独立成体,但纯粹一极没有意义,须有所待,彼此点化,在相离中共存,在互补中共构,在相互牵制的共同结构中方能呈现出整体意义来。以文质为例。文质范畴是礼乐知识谱系下生成的元范畴,在古人看来,物之质文犹如人之内外,属于事物不可缺少的两个部分,宇宙万物乃至各种人文现象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质内文外的问题。古人习惯于在文质递变中寻求天地人之法则,如《春秋元命苞》:“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天质而地文。”《周书·苏绰传》载《大诰》:“天地之道,一阳一阴;礼俗之变,一文一质。”《太玄·文》:“阴敛其质,阳散其文,文质斑斑,万物粲然。”质是阴气内敛的结果,文是阳气外散的结果,文质结合而万物粲然,文质也因此具有了阴阳的普遍意义。就对待立义思维而言,文质范畴的构成特征在于:文不离质,质不离文。
正如老学以有无、一多的对举来理解本体,宋儒标举道、气、理、性、命、心阐释体用一样,在古代文学、哲学、美学的本体阐释范式中,常常采取的是范畴对举。具有本体阐释意义的对举范畴,譬如古人常用的中和、文质、动静、虚实、有无、心物、形神等,它们均能为现代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已发与未发诸问题提供一种理论形态的解答,均可视为古人基于不同的经验环境与认知方式,围绕文学、哲学、美学本体意义探讨而积淀的观念形态与思维模式,透过范畴的两两对举,在对待立义中促使两者的理解、融合,并通过两者相互限定、互为体用的思辨过程,既规范了问题,也提供了答案,从而获得整体与部分相互决定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结论。这种既规范问题亦提供答案从而获得整体意义的话语形态与范型模式,可以说在对待立义思维中已经充分具备了。因此,考察上述两类数量庞大的对待型范畴群,理解特定范畴的内在意蕴及其逻辑关系,对于中国文学观念史和哲学观念史的研究极具理论价值,不仅能够使我们理解范畴的思想意蕴,绎出概念所根植的相同话语形态,又易于明了其潜在的范型模式,而且可以察见范畴间的结构关联与逻辑意义延伸,这也更加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中国早期概念体系的发生特征以及尔后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渗透。
对待立义及互动化生的思辨品格与万物一体及整体和谐的审美旨趣,是讨论古代思想范畴形成的一个基本结构与意义框架,也是了解古代艺术思想的一个起点。体现在文学思想史领域,就是体用互为、互证互释,追求质态平衡文论意义系统的形成,这是建立在对待立义思维所具有的立义性特点之上的。所谓立义性,即两归一的特质,于相反相成中烘托出整体性,以万物相通、一气流行的方式呈现。王夫之归纳为:“两端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于一也。聚于此者散于彼,散于此者聚于彼,浊入清而体清,清入浊而妙浊,而后知其一也,非合两而以一为之纽也。”⑩此“一”,非两端之一,乃两端之间的关系,所谓“非有一,则无两也”(11),亦复此意,船山的理论兴趣偏于两归一,也即立义性所展示的关联结构与整体意义。从运思逻辑看,强调两归一的立义性,这既是两两相对、互动互释的对待型范畴的价值抉择,也是达成质态平衡意义系统在逻辑和审美上的必然要求。
此一意义系统的形成,乃根植于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逻辑理路,体现在天道、地道、人道与天文、地文、人文所具有的相似性与同一性上,这就自根源上决定了传统文学及哲学观念史在思想体系上的整体性追求,故而范畴两极之间也就自然形成一种整体关联的结构,如同水克火,金克木,土生木,火生土的动态结构一样,所显示的是两极之间的对待性与辩证关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决定,这与西学以抽象独立观念形成范畴的逻辑关系是不同的(12)。就阴阳本义而言,无论是日光所照为阳反之为阴,或是山南水北为阳反之为阴来看,均是就时令节气的时间迁移与地理位置的空间比照而论的,两者相对而言具有互换性,且正是在这种相对与互换中显示出对待立义的整体意义。所谓五行之“行”,亦不止于五种基本物象(属性)的描述,而是更为强调五者之间的内在法则与整体关联,这既是一个相生相克的变化过程,又有一个动态自足的运行结构。在此影响下,传统文论概念范畴两极之间往往交融互摄、旁通统观、相浃相洽、互为诠释,如情与志、心与物、趣与味、神与气等,虽然作为不同的概念,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形成过程以及内涵界定与理论向度,但文论家在使用这些范畴来诠释文学创作与鉴赏过程的审美体验,或指述作品内在的审美意蕴时,往往不加区分,在不同的批评语境使用不同的概念,所指述或诠释的对象却是相同的。以情志为例。情志同一,乃是儒学一贯的传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其中“六志”,即好、恶、喜、怒、哀、乐,是六种情感,孔疏:“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故以情为志气的观点,在古代的认识论传统中,乃是属于一种共享性知识,如《文心雕龙·附会》:“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所谓情志为一,是刘勰“才童学文”的四要素之一。又如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又如清人钱谦益《牧斋有学集·题燕市酒人篇》:“诗言志,志足而情生焉,情萌而气动焉。”在儒学一系知识系统的诸核心要素中,人的先天质素,如心、志、气、情、意等,并无明确分梳,往往融为一体,互为例证,互为支持,且常常处于圆融自足的平衡状态,故神化而不自知,外显在各种人文活动与审美创造之中。
源于对待立义、循环恒变的运思逻辑,在知识结构上,古代文论的范畴命题往往呈现出一体两面的特质,气(道)为体,阴阳、清浊、虚实、有无乃至境界、风骨、神韵等均为体之两面呈现。如清人李兆洛《骈体文钞序》云:“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园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园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凡阴阳、奇偶、方圆均呈现出一面两体、即体即用的关系,这既是天地之道,亦是文章之法。在文论家看来,一切事物均有对待面,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借助词语和句式上严格的两两相对,在形式和意义上体现出整齐均匀的美感,故《文心雕龙·丽辞》谓“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两个单独的范畴虽各有独特的艺术功能,但须相待而成,精义与韵味兼有,在互渗互涵中呈现出完整意义,在动态平衡中寻求适度和谐与丰富多样。譬如文质,《论语·颜渊》谓“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文赋》谓“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以结繁”,《文心雕龙·通变》谓“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均旨在说明作为对待之两端,文和质虽各具独立性,但纯粹的文和纯粹的质没有价值,只有在相反相成中相映成趣,才能达到文质并盛的理想状态。同时,体现在对待型范畴两极的关系上,亦呈现出一种相待相斥的理论张力,如言意、意象、形神诸范畴,既相待相须,又相斥相析,且正是借助于这种相斥相析,意、象、神方能超越言、意、形的层面,朝着更完善、更隐秘的方向发展,惟其如此,莹澈玲珑、不可凑泊之境方可诞生,从而完成对诗歌本质的一种整体性的艺术把握。诚如党圣元先生所言,这种理论观照空间的调整与拓展,使思理形式因素多样化而克服过于程式化之弊端,在指述和诠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增强理论之“解蔽”功能(13)。
更深一步考察,对待立义的两极间并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总是处于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之中,所谓“有盛则必有衰,有终则必有始”(14),保持着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动态结构,且在不断相摩相荡、竞长争高中达致新的平衡,如《艺概·词曲概》谓“词之章法,不外相摩相荡,如奇正、空实、抑扬、开合、工易、宽紧之类是已”。“相摩相荡”的说法源于易学,《周易·系辞》谓“刚柔相摩,八卦相荡”,是指阴阳两卦相生相济,由二而四而八而六十四的变化过程,而“一气之中,二端既肇,摩之荡之而变化无穷”(15),正体现出对待两极之间的动态结构关系。这种动态关系,又多呈现出循环往复的特征,按照司马迁《史记·平准书》的说法:“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按照明儒罗钦顺《困知记》卷上的说法:“盖通天地,亘古今……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按照清儒方宗诚《桐城文录序》的说法:“天地之气运,流行不能自已,蓄久则必盛,盛久则必靡,亦理之势然也。”一气流行往复,万物由此而生,由此而变,此乃天地间第一大循环,这有似于文学消长之道,在“一盛一衰”、“一文一质”、“一治一乱”、“一分一合”的循环往复中获得质态稳定性,极则反,反而因,万物皆然,故《艺概·书概》认为“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据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叶燮在《原诗》中,以源流本末之相续相禅、正变盛衰互为循环论及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明显也是承续对待立义的路子。
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传统中,以相反相成、即体即用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对待立义思维方式,在历代诠释者选择文化生存状态时,势必形成一种文化心理,并最终凝结为一股精神信仰与思维惯性,潜伏的、隐微的、暗示的存在着。在古人的宇宙观中,天地人之存在,不过是气之聚散与气之变化过程罢了,天地人之所以具有相似性和相通性,就在于气的大化流行,分阴分阳是对待,动静刚柔是流行,“三才之道”均可以统一于气。气既是宇宙人生的本体,也是文学艺术的本体,造艺的过程,乃是气化的过程,这是中国古代艺术创造和艺术生产的核心环节,在此一过程中,气之对待立义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造艺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审美趣味。见之于古代艺术理论,对待立义式的运思方式,屡屡可见,画论如动静结合、奇秀相称、形神兼备;书论如骨肉相称、肥瘦相和、燥润相济;诗论如以礼节情、中和之美、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化实为虚、意与境浑、思与境偕,等等,我们实在不难发现与对待立义方法论之间的蛛丝关联。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以“虚实相生”为例。气本无形,要表现气之形,需借助于“虚实相生”的手法,这种极具民族特质的艺术表现手法,广泛地闪现在各门艺术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领域。譬如书法艺术中所追求的墨气,就是在字体之大小相间、下笔之轻重缓急、笔画之勾勒顿挫、用墨之干湿枯润中,体现一虚一实、动静结合的品格,达致笔未到气已吞的理想效果。再如绘画技法中讲究线条之长短、粗细、曲直、刚柔,章法之开合、疏密、虚实、主客、呼应、入出,墨色之浓淡、深浅、干涩、苍润,色彩之冷暖、清浊,物象之大小、多少、高低、聚散、藏露,等等,均强调实景清而空景现,追求无画处皆成妙境的审美感受。作为传统艺术境界与审美理论的核心,“虚实相生”在诗学领域的运用也极为广泛。古人讲究虚与实之间的体用不二,所谓“虚”则神、“虚”则妙、“虚”则灵、“虚”则化、“虚”则纯一不杂,亦不滞于一(16),常以虚之无衬实之有,虚为体,实为用。在艺术思维中,通过感观而可观之外显,如言、形、秀、韵,与通过心灵而体悟之内蕴,如意、神、隐、味,相互衬托、相互关照,达致言与意、形与神、隐与秀、韵与味的浑然为一,文章家于虚实的回旋往复、联动会通中空纳万象,以虚无衬实存,于有限见无限,引发无尽想象,如范晞文《对床夜话》云:“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头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亦如吴雷发《说诗菅蒯》云:“真中有幻,动中有静,寂处有音,冷处有神,句中有句,味外有味,诗之绝类离群者也。”以实为虚,化有形之景为虚玄之思,这种虚实难明、情景交融的境界,如采采流水,蓬蓬远春,散发着浓郁的民族诗性智慧的韵味。凡古人论及意境、意象、韵味、兴趣、神韵、滋味诸问题时,均不离虚与实的理论视野,这对于古代思想文化的诗性智慧启发以及审美运思的逻辑延伸,有着内在而深远的影响。对此,宗白华先生认为:“我们宇宙既是一阴一阳、一虚一实的生命节奏,所以它根本上是虚灵的时空合一体,是流荡着的生动气韵。”(17)在他看来,中国人抚爱万物,与万物同节奏,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乃阴阳之道影响的结果。
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对待立义不仅仅具有经验描述性质,更具备了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导向性,其终极价值在于为主客相应的人文世界提供一种整体关联的解释模式。这是一个层级分明、圆融自足的解释系统,正所谓“凡是真实必有对待,凡有对待必有变化,凡有变化必有统一”(18),统摄了对待、变化、统一的多重关系。此一特性体现在古代哲学、文学观念史中,形成了以中庸之道为核心的哲学价值观,并延伸出以对待立义求中和为价值取向的文学审美观。
阴阳、刚柔、情性、清浊作为对待立义的两极,本无所谓高下、善恶、尊卑之分,而一旦被赋予褒贬之意,也就意味着隐藏在背后的哲学、文学价值观在发挥作用,对此,古代思想家有着高度的理论自觉。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从“性阳情阴”引申出“性善情恶”,并为纬书及《白虎通义》所阐扬,这种价值取向在中古文论中得以充分展示,如《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说法,已经意识到气之清浊对于造艺者文章风格的影响,后世论者很容易从中体悟出阳刚、阴柔之意。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才有庸隽,气有刚柔……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郭绍虞先生对照曹、刘之说后,认为刚近于清,柔近于浊,分别是指气之重浊柔顺和清新刚健(19)。刘勰《镕裁》谓“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定势》谓“文之任势,势有刚柔”,是将文章风格作刚柔之分,大体上分别指慷慨激昂之壮美与婉转柔和之优美。纵观《文心雕龙》全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与话语模式,对待立义业已内化在刘勰文学批评的各个方面。从历史文化语境看,随着有无、本末、动静、一多等命题在形上论辩的展开,玄学从认识论角度进一步阐发了物与物相反相成的关系,加之佛学中国化过程中对中国哲学固有命题的新诠释,大大增强了对待立义思维的形上思辨色彩,这与六朝时期丰富的文学创作实绩结合,促使文论家在理论层面认识的深入,代表人物就是刘勰。在文学批评总体性原则上,他提出宗经之“六义”,即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贞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宗经》)。评价不同文体,他取不同的标准,《书记》篇辨析笺和记两种文体,“既上窥乎表,亦下睨乎书,使敬而不慑,简而无傲”,恭敬谨慎但不惶恐畏惧,简易随便但不凭才傲慢,《铭箴》辨析箴、铭两种文体,“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选取事物要抓住要点且辨析清楚,使用文辞要简练而深刻。在文学史观上,他反对“竞今疏古”,认为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一部文学史的发展趋势就是“从质及讹,弥近弥澹”的过程。在具体作品点评上,他认为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序志》)。在刘勰看来,为文之精妙在于奇正相生、兼容并蓄、刚柔互济、应变适用,他所秉持的对待立义思想内涵丰富,层级分明,充溢着浓厚的中庸之道与中和之美色彩。在文章风格上,他提出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体性》)。在古人看来,文章风格的形成,与对待立义话语形态及其在结构上呈现出的动态气势,尤其是擒与纵、收与放、刚与柔、抑与扬、舒与促之间的行文张力,有着内在的关联。
就价值取向来看,虽然表现形态及其借以阐述的思想义理有别,但以阴阳之对待立义性、整体关联性作为理论思辨和认识论工具,却是文论家们共有的,无论偏于对待立义的哪一端,价值取向上仿佛相左,审美内涵上仿佛对立,但两者同源共生,常常相互为济,“尚中致和”乃是共同的审美价值理想,这是中国古代对待立义思维在价值取向上的基本特征。对待立义求中和的理念在传统时代艺术审美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譬如见于乐论,以中和论诗乐之缘起,乃是一以贯之的传统,在古人的文化视野中,乐乃阴阳之气相激而成,如《礼记·乐记》:“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阮籍《乐论》:“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无声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万物自乐。”嵇康《声无哀乐论》:“阴阳愤激,然后成风。气之相感,触地而发……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为用矣。”在他们看来,乐得天地之体,明万物之性,通乾坤之道,阴阳之和乃是乐和的基础,对于中和之境的追求,遂成为古代文学艺术起源的文化基因,以对待立义求中和的价值理想与尚中致和境界的追求,内在地影响到文学理论范畴的美学追求,并在价值取向上影响到对待立义思维所体现的普遍和谐品格。
从文学观念史的角度看,对待立义思维对于文论范畴、命题的影响表现在话语形态构成的相似性与审美价值追求的同一性上。古人认为,中和是一种遍布时空,充盈天地人的普遍存在方式,整个宇宙存在正是因为具有阴阳互补和五行相生的属性而处于一种中庸和谐的动态平衡之中,以对待立义求中求和,也就成为古代美学、文学思想史上众多命题的价值追求。体现在话语表达方式上,典型句式有二:“而不”句式、“阴中有阳”句式。
数量众多的“而不(无)”句式,是以两两相对的范畴构成的命题,自《尚书·尧典》“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记载后,我们从吴季札观乐,以及《论语·八佾》、《荀子·不苟篇》的诸多记载中,可以察见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而不”句式的广泛运用,从结构形态上先在地决定了中庸和谐的审美价值追求。在诗学鉴赏领域中,古人常常采用“而不”句式谈文论艺,究其根源,在于其用最简洁、最直观的方式表达了对待立义的理念。譬如《淮南子·泰族训》中,论物未尝有“张而不弛,成而不毁者”,惟圣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亏”,论圣人教化应该“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而非“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嵇康《琴赋》谓“曲而不屈,直而不倨”、“凌而不乱”、“离而不殊”。萧绎《内典碑铭集林序》认为,时势推移,“论文之理非一”,故赞赏“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雅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的“菁华”之文。《竹庄诗话》卷一引皎然《诗式》:“唯古诗之制,丽而不华,直而不野。如讽刺之作,雅得和平之资,深远精密,音律和缓,其象琴也。”这与《诗有四不》“气高而不怒”、“力劲而不露”、“情多而不暗”、“才赡而不疏”,以及《诗有六至》“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在价值取向上是相同的,均为相反相成、对待立义运思模式在诗歌理论中的具体运用和发挥。这种建立在“和而不同”、异而互补基础上的话语范式,培育了中国古代文论中正平和的价值追求以及开放流动的理论视域,构成整齐、对称、流动、平衡之美,整体上呈现出稳定和谐的精神气质。同时,我们或可以注意到,运用于文论领域的“而不”句式,在价值取向上业已发生了明显的转向,由早期强调外在的德行、伦常、心性转而关注内在的文采、文质、雅正、音律诸方面了。
所谓对待立义互为体用的特征,不仅体现在两两对举范畴的大量涌现,还体现为范畴的两极之间,既对等又统一,呈现出相生、相克、相推与互涵、互根、互补的关系,从而构成一种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话语表达方式,如《医贯·阴阳论》:“阴阳又互为其根,阳根于阴,阴根于阳;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这就将两极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相互依赖、资生、促进、助长的关系说得明白清楚了。又如《春秋繁露·保位权》:“声有顺逆,必有清浊。形有善恶,必有曲直……于浊之中,必见其清;于清之中,必知其浊;于曲之中,必见其直;于直之中,必见其曲。”在董学的文化视野中,事物对立面之间是互涵互为,相互印证的,这是表述其“天人感应”思想的典型话语形态。再如清人丁皋《写真秘诀·阴阳虚实》:“凡天下之事事物物,总不外阴阳……惟其有阴阳,故笔有虚有实;惟其有阴中之阳,阳中之阴,故笔有实中之虚,虚中之实。”丁氏以阴阳、虚实之道论及画法,每一对范畴,均由相反相成的两极构成,达致对立统一的整体。刘熙载《艺概》中,论述主客、物我之间的情景交融、形神兼备,也常常采用这样的话语表述方式,如幽中有隽、淡中有旨、浅中有深、平中有奇等,借以强调对立面之间相济相生的关系。古人诸如此类的说法颇多,如柔中见刚、平中见奇、薄中见厚、黑中见亮、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曲中有直、直中有曲、开中有合、合中有开、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等等。正因为得益于此一话语表述方式,传统时代的审美概念范畴往往能提供一种灵而动、虚而实、诗而画的理论思辨场景与诠释效果,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所言:“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借物引怀,意在言外,从思维机制的根底追究,大抵不离对待立义的理论视野。
源自对待立义思维方式,可以说,中国文论中的重要范畴均明显地对偶化了,而就整个文论范畴体系的构型而言,亦呈现出明显的对待性结构与立义性动态关系,透过此一结构与动态关系,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学中的理论问题更加趋向于以对待型范畴的方式提出,同时在此一对待型范畴的导引下,在价值追求与审美理想上,亦经历了思辨的发展历程并不断地趋向于立义性的合一境界。因而中国文论话语形态的基本质素与价值指向,亦由此在本原处得以规定。
注释:
①中国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的有:庞朴先生《对立与三分》中并生式、从生式、发生式的分类,见《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2期;吾敬东先生《古代中国思维对对立现象的关注与思考》中图形化、符号化和概念化的分期,见《中国哲学史》1997年2期。
②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本,第2344页。
③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天地阴阳》,中华书局1992年点校本,第467页。
④张载:《正蒙·参两篇》,《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0页。
⑤庞朴:《东西均注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8、89、94页。
⑥刘熙载:《艺概·经义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82页。
⑦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
⑧参考成中英《“本体与功夫”的现代哲学意义》,收入《创造和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
⑨参考拙著《礼乐文化与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9—262页。
⑩王夫之:《思问录·内篇》,《船山全书》十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11页。
(11)(15)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太和篇》,《船山全书》十二,第36页,第42页。
(12)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值得借鉴,如葛兰言(Marcel Granet)“中国思维模式”(structure of thought)、葛瑞汉(Graham)“关联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以及李约瑟(Joseph Needham)视阴阳为“自然主义”和“前”科学的看法。参见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陈立夫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3)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文学评论》1997年1期。
(14)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16)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394页。
(17)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5页。
(18)成中英:《阴阳思想的辩证法》,收入《创造和谐》,第55页。
(19)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