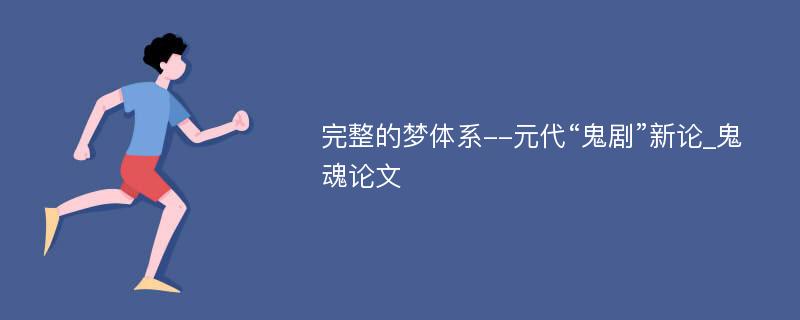
完整的梦幻系统——元代鬼魂戏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元代论文,鬼魂论文,完整论文,梦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代鬼魂戏大多取材于前代历史典籍、小说笔记,有原型可循。如《神奴儿》脱胎于《搜神记·苏娥诉冤》,《盆儿鬼》情节与《后汉书》注王忳事类似,《范张鸡黍》本事出于《后汉书·独行传》(据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但剧作家遵循抒发自我理想为主的创作原则,有意地进行挖掘、改造,赋于历史传说以现实的面貌和元代社会的基因,构造了一幅现实的环境,拓宽了反映社会的广度,抒发了时代的情感意绪,使其成为艺术家心灵世界的形象寄托,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下面我们将从内容上把鬼魂戏分为三类来论述,看它们表现了艺术家什么样的主观愿望和人生理想。
(一)历史剧:民族浩然正气的呼唤
不满现实,把眼光投向历史,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是历史作家选取历史题材的主要原因。元杂剧作家创作了大量历史剧,涉及鬼魂情节的有关汉卿的《西蜀梦》,宫天挺的《范张鸡黍》,杨梓的《霍光鬼谏》,孔文卿的《东窗事犯》和无名氏的《昊天塔》五种。
这些剧作选取的主人公都是历史上的忠臣义士如关羽、张飞、杨家将、岳飞这些名标史册流传千古的英雄豪杰。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汉族的浩然正气,在民族压迫空前深重的元代,作者缅怀他们,歌颂他们,正是为了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呼唤民族精神的高扬。
《范张鸡黍》中的范式与张劭,因痛恶朝政黑暗不屑仕进,共同的志趣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两人辞归闾里前,相约二年后在张劭的家乡汝阳备鸡黍相会。范式如期赴约后,两人又约好来年相会于荆州,不料临近约期,张劭因病而逝。远在荆州的范式得到张劭鬼魂托来的梦,不辞辛劳,千里迢迢亲自前往汝阳主丧下葬,并守墓百日。作者歌颂了两人的忠于友情、生死不渝的信义行为,并将他们的高行美德放在“宪台疏,乱滚滚当路豺狼;选法弊,絮叨叨请俸日月;禹门深,眼睁睁不辨龙蛇;纪纲败,缺炎炎的汉火看看灭”(二折[梁州第七])的社会背景中,与王仲略那种靠窃取别人劳动果实爬上仕途的卑鄙的小人相对照,其借古讽今、歌颂汉民族传统美德的用意不言自明。
杨梓在《霍光鬼谏》中着力刻划了一个忠臣形象。霍光生前对王室一片忠心,不但不徇私情,反而力阻宣帝加封二子、册立女儿。皇帝不从,他气恼成病,命归冥途。但他“为国家呵一灵儿不散”,在儿子谋反之前向皇帝托梦告密,真可谓:“生前出力保江山,命终尽节扶炎汉。”虽然有人认为此剧宣扬了愚忠思想,是杨梓对元朝统治者一片忠心的表白。但据说杨梓创作此剧在于“寓祖、父之意”(元·姚桐寿《乐郊私语》),而且我们不能否认忠于朝廷、死而不已的精神,正是儒家思想人格的体现。在岳飞、杨家将身上不都闪现着这种“忠”的传统美德么?
《东窗事犯》中的抗金英雄岳飞父子,屡建战功,却被奸人秦桧诬陷下大理寺,做了“负屈衔冤忠孝鬼”:
“想挟人捉将,相持厮杀数千场,则落得披枷带锁,枉了俺展土开疆,信着个挟天子令诸侯紫绶臣,待损俺守边塞破敌军铁衣郎,俺与你扫除妖气、洗荡妖氛,不能够名标簿上,刬地屈问厅前,想儿曹歹谋帝王前,不由英雄泪滴枷梢上,想着俺掌帅府将军一令,到不出的坐都堂约法三章。”(一折[混江龙])
我不合扶持的帝业兴,我不合保护的山河壮,我不合整顿的地老天荒……”。(一折[那吒令])
这声声悲诉与哀怨,表达了英雄壮志难酬的悲痛,负屈难伸的怨恨!
《西蜀梦》中关、张阴魂抚今忆昔,痛泪交流的凄怆,《昊天塔》中七郎之魂诉说被害之惨、骨殖之痛的冤情,都抒发了浓郁的激愤情怀,蕴含着惨烈、郁闷的悲剧气氛。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情状,追忆历史无疑勾起了人们对现实的沉痛反思。
然而,剧作家揭示民族悲剧并非只为了挑起人们伤悼、悲哀的心理,更主要是为了高扬民族正气,唤起人们反抗、复仇的意志。
历史英雄负屈而死但英魂不散,充满了复仇情绪。《东窗事犯》中,岳飞魂灵在托梦高宗时,抒发了自己的满腔怨愤:“想微臣志未酬,除秦桧一命休。陛下逼逐记在心头,将缘曲苦苦遗留;明明说透把那禽兽剐割肌肉,号令签字,豁不尽心上忧。”(三折[幺])表达了“这冤仇,这冤仇,怎肯干休”(三折[秃厮儿])的心志,希望高宗“用刀将秦桧市曹中诛,唤俺这屈死冤魂奠盏酒。”(三折[收尾])在《西蜀梦》中,关、张阴魂不散,来至宫廷向刘备诉说惨遭杀害的经过,临行再三叮咛为他们报仇雪恨。尤其是张飞之魂,嘱托刘备:“火速的驱军校戈矛,驻马向长江雪浪流,活拿住糜芳糜竺,阆州里张达槛车内囚,杆尖上排定四颗头,腔子内血向成都闹市里流,强如与俺一千小盏黄封头祭奠酒!”(四折[尾])表达了不杀仇敌死不瞑目的心愿,表现了强烈的复仇精神。而且此剧与关汉卿另一剧作《单刀会》相似,作者一再强调“汉家基业”、“汉家领土”,表现了特定时代下作者的民族思想情感。从《昊天塔》、《东窗事犯》等剧作所取的题材、情境都可以看出作者所强调的反抗异族、忠于汉室的思想倾向,这可以说是元代整个汉民族不满于异族统治、压迫,渴望复仇的共同的心理。作者请出古代英雄的亡灵,极力颂扬他们悲愤豪迈的英雄气概、誓报冤仇的大无畏精神,正是为了弘扬民族精神,呼唤豪杰辈以改变黑暗现实,完成民族复仇大业。虽然这些英魂都是托梦于生者得以完成复仇心愿,具有轮回冥报思想,但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力量。
(二)公案剧:惩恶扬善心理寄托。
在元代鬼魂戏中,较多是公案剧,有武汉臣的《生金阁》、郑庭玉的《后庭花》、关汉卿的《窦娥冤》、无名氏的《神奴儿》、《朱砂担》、《冯玉兰》、《盆儿鬼》七种。这些剧作基本上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剧中的主人公多是下层社会善良、无辜的小人物。有迂腐书生、贩夫走卒、贫民女子、天真小儿……他们与世无争,安分守已,本该平平安安地过活度日,然而他们做人不得,一个个被逼为负屈衔冤之鬼。是谁将他们推上悲剧的境地?我们看看这些悲剧所发生的时代背景吧。
《生金阁》中的庞衙内,“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嫌官小不做,马瘦不骑,打死人不偿命,打死一个人,如同捏杀一个苍蝇相似。”
类似的像什么鲁斋郎、杨衙内等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的“权豪势要”,在元代随处可见。此外,象盆罐赵(《盆儿鬼》)、铁旙竿白正(《朱砂担》)、张驴儿、赛卢医(《窦娥冤》)等打家截道、图财害命的泼皮无赖更是胆大妄为,肆意横行。在《元典章》中有这样的记载:“一等权富豪霸之家,内有充官吏者,亦有曾充军役杂职者,亦有泼皮凶顽者,皆非良善,以强凌弱,以众害寡,妄兴横事,罗织平民,骗其家私,夺占妻女,甚则害伤性命,不可胜言。交结官府,视同一家。小民既受其欺,有司亦为所侮,非理害民,纵其奸恶,亦由有司贪猥,驯致其然。”(《元典章》卷三十九《刑部》卷一《迁徙豪霸凶徒》)可见当时社会,蒙古贵族、上层色目人、地主豪商、流氓地痞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黑暗势力,使得整个社会处于混乱状态,杀人越货,伤天害理之事层出不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毫无保障。加上商业经济的发展,异族入主对传统道德伦理的冲击,见利忘义、谋财害命之事屡有发生,连家庭内部也出现了争夺财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在《神奴儿》一剧中,年幼的神奴儿便死在心狠手辣、欲独霸家私的婶子手下。
那么元代的吏治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楚州太守桃杌一上场便大言不惭地宣称:“我做官人甚殷勤,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来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窦娥冤》)贪赃受贿、卖官鬻爵、草菅人命,这便是当时官僚阶层的真实情景。他们不学无术,不懂律令,“自行威福,进退生杀,唯意之从”(《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有的甚至自行不法,危害别人,《冯玉兰》中那位屠世雄不就是身为巡江官却干着夺人妻子、害人性命的罪恶勾当么?如此腐败、黑暗之吏治必然会造成冤狱纵横、哀魂遍野的惨象。那一个个负屈衔冤的鬼魂正是现实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元杂剧作家身处其境,目睹丑恶现状,自然义愤满胸,他们将制造悲剧的种种因素一一展现在剧作中,正是为了对邪恶势力进行无情的揭露、鞭挞,以抒发内心之愤懑。
然而剧作家决不能容忍让无辜良善者任意遭受践踏,他定要让邪恶受到惩罚,正义得到伸张!于是,他们借助手中之笔设计出包公、窦天章、金御史等一些“清官”来审理案件,替民伸冤,并将一具具尸骨变为阴魂不散的形象,让他显示灵性,辅佐判案,有的还亲自出场,惩治仇人,以泄生前之恨。《盆儿鬼》中的杨国用,尸体被烧毁捏作盆子,仍然阴魂不散,一再显灵,陈述冤情。《生金阁》中的郭成,变为无头鬼,上元节大闹灯市,冲打庞衙内,使得满市骇然;大路上兴风马前,阻拦包公,法庭上大胆申诉,渴望报仇雪恨。这种大胆的、富有反抗性的举动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
鬼魂托梦、诉冤,通过清官或凭借神力报仇雪恨的结局有的杂有因果报应的宿命成份,但主导的方面则是表现了一种对恶势力不屈服、不妥协、敢于反抗、斗争的精神,这是作者出于对黑暗现实的痛恶,对光明未来的向往所发出的正义呼声。
(三)爱情剧:自由理想爱情的追求
郑光祖的《倩女离魂》与无名氏的《碧桃花》二剧都是爱情剧,曾瑞卿的《留鞋记》虽然后半部分涉及公案,但整个剧作始终以爱情居主导地位,故视作爱情剧。
《碧桃花》写知县千金碧桃被许配与县丞之子张道南,尚未完婚。一日,碧桃在园中游玩,恰遇入园追赶鹦鹉的张道南,两人相互问讯,不料正被归来的父母撞见,对其严加责骂。碧桃一气之下命归黄泉。三年之后,张生得官居于园中,碧桃阴魂不散,与之欢会。后张生染病,其父请道士萨真人勘问,得知碧桃阳寿未尽。不久,碧桃果然借妹之尸还魂,两人匹合夙缘。
《留鞋记》写落第书生郭华与胭脂铺小姐王月英彼此爱慕,互相思恋,后得丫环梅香大力相助,送帖传情,两人相约中秋之夜相会于相国寺。无奈相会之时,郭华醉眼不开,月英只得将香罗帕与绣鞋留下为证。酒醒之后的郭华懊悔万分,吞下罗帕为情而亡。此事构成人命案,月英因此被拘,有口难辩。不料七日后郭华死而复生,诉说原委,包公断其结为夫妻。
这两本剧都是写“还魂”之事的,关于“还魂”故事,过去小说中有许多,刘义庆《幽明录·卖胡粉女子》即是一例,也是《留鞋记》本事出处。但《幽明录》等释氏辅教之书,旨在发明神道之不诬,招徕善男信女,而这个剧本则重在表现男女主人公真挚的爱情与执着的追求。是生死不了情使人物得以死而复生,再续前缘。碧桃花与张生花园相见时并未回避,而是“擎着个笑脸儿将他厮问候”;受到父母责骂时心中却想着:“他须是我天缘配偶,常言道女大不中留”,渴望成就美满姻缘;碧桃鬼魂与张道南恋爱后,虽然担心张生做了“薄幸王魁”,但却仍然希望与之“日亲日近”,“相随相趁”。《留鞋记》虽然写男主人公“还魂”之事,但主要表现的也是女主人公月英的内心情感,尤其是第一折写她染病闺中,第三折写她公堂上坦露真情,维护爱情,表现了她的一片真情。郭秀才亦与一般读书人不同,他榜上无名,却不觉无颜,而一心恋着美丽的月英,为她羁留异地。在得到月英的允诺后,他喜不自禁;当错失良机后,他懊悔不已,吞帕而亡,充分显示了自己“苦为烧香断了头,姻缘到手却干休,拼向牡丹花下死,纵教做鬼也风流”的心迹。
以上两剧歌颂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充分表达了作者的主观情感,然而对人物的揭示不深,对人物反抗性格的塑造不足,且袭用姻缘前定的宿命论思想作为“还魂”情节的合理依据,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意义。相比之下,只有郑光祖的《倩女离魂》能够真正从人物情感出发,以“离魂”这独特的艺术构思,深刻地揭示人物真实的精神状态。
《倩女离魂》取材于唐传奇《离魂记》,但作者根据需要对它进行了大胆改造。首先,它将小说中所写的张王为表兄妹关系改为“指腹为婚”的关系;将《离魂记》中与倩女共同追求爱情的王宙改为满脑子理学思想,以“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之礼拒绝倩女的王文举;增加了张母赖婚,及要求王文举考取功名为结亲的先决条件等情节。这些改动,增强了对倩女的外在压力,符合元朝中后期的现实,突出了倩女的反抗精神。剧中“离魂”情节的设置也完全以人物的思想情感为依据,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叛逆性格。我们不妨作一具体分析:
剧本第一折,倩女一上场就道出了她“自从见了王生,神魂的驰荡”的心情,一曲[混江龙]又唱出了她对“落叶萧萧”之暮秋,满腹心事,百无聊赖,倍感压抑、苦闷之真情,她对王文举充满爱慕之意,然而不知母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让两人以兄妹相称,使他们虽咫尺之隔,却又似“地北天南”,只能在复杂、矛盾的心情中暗自伤叹、忧怨。当王文举辞行,倩女前往折柳亭送别时,作者更是细腻地刻划了她复杂的内心世界。母亲“三辈儿不招白衣秀士”的门第观念威胁着她的婚姻前途。除此而外,她有更深一层的忧虑,那便是担心王文举一旦高中便抛弃自己,另入“王侯宰相家”,所以临别她反复吟唱,一再嘱托,告诫心上人,“身去休教心去了”,并表达了“我这一点真情魂缥缈,他去后也不离了前后周遭”的愿望。这种“魂断梦劳”的心境为后面的离魂情节埋下了伏笔。
在男尊女卑、等级观念森严的封建时代,面临与情人的生死离别,倩女怎能不忧思重重。回到家中,他便在万般情思、种种忧虑的煎熬下,一病不起。然而,人的天性是无法扼杀的。倩女虽然无法冲破礼教的罗网,但内心深处却埋藏着对情人的一片深情,渴望着追求到幸福生活。这种情感的欲望是那样的强烈,犹如一盆熊熊燃烧的烈焰。于是灵魂便带着这种“和伊同走天涯”的深层次欲望升腾而起,不顾一切去追求心爱的人,构筑自由而理想的未来世界。
可见,魂离躯体是人物潜意识中执着追求的结果,倩女之魂实则是她内心真情的外化。作者抓住了倩女为情所扰,半痴迷、半清醒的特殊心态,联系传统的鬼魂说法,将她内心深处萌动、跳跃着的深层愿望和盘托出,借鬼魂形象使之具体化、直观化,深刻揭示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活动,表现了广大妇女对恋爱、婚姻自主的向往与追求,对封建礼教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从作者对离魂之后魂与体的对比描写中,我们看到闺阁中之躯体倍受相思之苦折磨,染病三年,如痴如醉,神思恍惚;而冲出躯壳之灵魂在大胆追求、顽强反抗中相随左右,获得幸福,这一方面反映了人物内心“情”与“理”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向我们昭示了反抗则终成眷属,屈从则奄奄待毙的真理,这是何等的鼓舞人心!
在元代,冲破封建礼教之束缚,追求自主幸福的爱情婚烟,成为剧作家的共同心声,“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便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郑光祖等适应了这一时代要求,利用“离魂”、“还魂”情节表现人情之奇,赋于人情以“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巨大能量,让魂灵冲破时空、生死之界限自由飞扬,这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挑战,对人生理想的充分展示,热情讴歌。
综观以上三类鬼魂戏,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剧作家的人生理想和美好追求,它们既是剧作家内心世界的形象寄托,又是剧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美好希望与梦想。鬼魂的出现,无论是作为惩恶扬善的使者,自由情爱的精灵,还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实则都是作家心灵世界的显现、展示,梦幻意识的变形、外化,剧作家运用这种与梦相似的象征符号,表现了“愿望的达成”,构筑了一座理想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