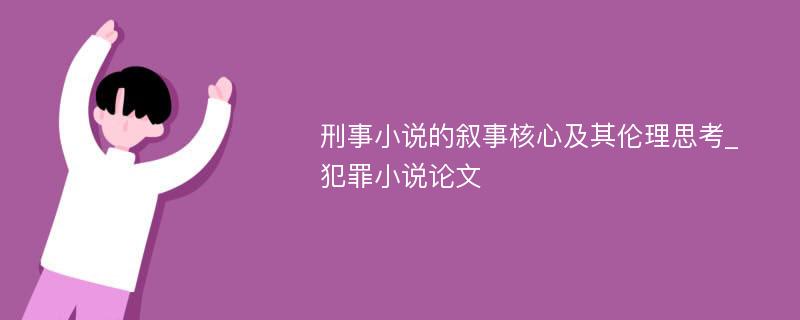
犯罪小说的叙事内核及其伦理考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核论文,伦理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社会中的犯罪现象久已有之,几乎所有的宗教典籍都包括对人们正确行为的指导,而人们对社会规范的逾越及其可能招致的惩罚,同样也是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的一个永恒母题。然而,包括罪行和侦破两个必要环节的、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犯罪小说(crime fiction)则是在19世纪中期以埃德加·爱伦·坡的相关短篇小说为雏形,经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等经典作家的创作,至20世纪中期演化出新的发展形式而逐渐确立的类型文学体裁。这种原本隶属于通俗文学的虚构叙事作品,在其后不到两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繁衍出多种形式和分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1970年代以前,西方学术界对犯罪小说的相关研究局限于侦探推理类和谜案类作品,自朱立安·西蒙斯的《血色谋杀——从侦探小说到犯罪小说》(1972)开始,这一现象已经发生了改变。在这本专著中,西蒙斯对主要关注犯罪心理和犯罪过程的纯粹犯罪小说进行了专门探讨,列举了它与侦探小说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在他看来,所谓“犯罪小说”,是指虚构情节涉及罪行及其侦破过程的小说作品总称,包括古典侦探(detective)、谜案(mystery)、悬疑惊悚(thriller)、硬汉派作品(hard-boiled)、纯粹犯罪小说(pure crime)等多种分支;而纯粹犯罪作品所关注的重点则是犯罪心理和犯罪过程,是前者在20世纪后半叶所发展出的新形式。①斯蒂芬·奈特则通过两本专著,分别探讨了犯罪小说与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语境之间的关系,②犯罪小说在其发展早期对悬疑推理的迷恋,其后对死亡主题的不断重视以及如今呈现的形式多样性。③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于世纪之交推出多部学术著作,不但考察了传统侦探小说,④也梳理了犯罪小说在后殖民、⑤后现代背景下⑥的新趋势和新动向。权威性的剑桥文学导读系列亦于2003年出版由马丁·普里斯特曼主编的《犯罪小说》分册,⑦该书不但包括对18世纪犯罪书写(crime writing)、⑧纽盖特小说(Newgate Novel)和奇情小说(Sensational novel)⑨以及对经典侦探推理作品的考察,⑩也探讨了犯罪小说在二战之后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指出黑人(11)和女性警探(12)等全新形象的出现。 发源于通俗文学的犯罪小说为什么能够在其享有的商业成功之外,受到评论界和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西蒙斯的看法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犯罪的年代,而犯罪小说这种以犯罪为核心的作品能够最好地体现这一点,它所展现的个别罪行有可能帮助我们了解身边的公共罪行,让我们对自己所处的世界和社会增添一些认知(289页)。普里斯特曼则认为,1960年代以来,“高雅文学”和“低俗文学”之间的壁垒被逐渐打破,在此背景下,鉴于犯罪小说本身的发展及它对大众电影和电视文化的重要影响力,对这种类型文学中所隐现的性别、种族和阶级问题进行深入考察显得非常必要。(13)从这些分析我们不难看到,正是由于犯罪小说紧密联系现实生活,能够反映特定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在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学术热潮之下,才越来越多地受到文化和文学研究学者的重视和注意。 然而,可能是由于学术界对犯罪小说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其社会指涉方面,犯罪小说叙事形式方面的研究明显缺乏。在犯罪小说的不同发展分支中,对叙事形式的分析集中于对古典侦探作品的形式探讨,其主要关注焦点在于为保证这种推理游戏的公平原则而必须遵守的一系列规范(如1920年代范·戴恩的二十条和罗纳德·诺克斯的侦探小说十诫),鲜有结合犯罪小说至今的发展考察其不同分支形式,并由此挖掘这种类型文学基本叙事模式的尝试。然而,为什么犯罪小说能够具有宽泛的社会纬度?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它体现了怎样的叙事模式和叙事常规,为何能够成为犯罪小说家探讨社会现象的文学工具,并能够承载文化和政治研究所赋予的重要社会功能?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娱乐功能之外的社会和政治含义,对它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和评价。本文试图结合犯罪小说的历史发展轨迹,参考爱伦·坡的小说创作思想和实践,阐明犯罪小说由犯罪和侦破两大环节组成的故事内核,并且讨论这一基本叙事结构在引入社会杂语、反映社会暗流方面的形式潜能以及相关伦理问题。 一、犯罪小说的故事构成 托多洛夫《侦探小说的类型》(1977)一文,可以说是从叙事理论角度对犯罪小说结构语法所进行的最早探讨。在这篇短文中,托多洛夫首先针对英国古典侦探小说,提出这类以“谁干的”(whodunit)为核心问题的作品包括由“犯罪故事”和“侦破故事”构成的双重结构,在其最为纯粹的形式中,后者发生之时前者已经结束,而后者中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行为内容——波洛这样的侦探们并不需要太多动作,他们需要的是掌握线索并作出理性分析,读者也不大会想象他们遭遇什么危险。这第二个故事由此享有某种特殊地位,它们时常由侦探的朋友或助手讲述,讲述者往往又公开承认自己在撰写某部作品,其功能实际在于解释这本书的完成过程。因此,在托多洛夫看来,前者,即犯罪的故事,涉及的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后者所涉及的则是读者(叙述者)获知这一犯罪故事的经过。在这一划分基础上,托多洛夫又借用了俄国形式主义者对故事(fabula)和话语(sjuzhet)的划分,认为侦探小说的双重结构对应的正是所有叙事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前者构成作品的故事(story),是自然中发生的事件,对应的是“那些被呼唤(evoke)的、与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事件”;后者则构成作品情节(plot),涉及作者将这些事件呈现给读者的方法和手段,对应的是“作品、叙事以及作者所采用的种种文学手段”。(14)这一讨论后来为评论界广泛接受,(15)叙事学者彼得·胡恩也从符号阐释和意义构建的角度,借用并发展了托氏对侦探小说所做的“故事”与“话语”之分,提出这类作品中包含两层故事和话语关系:首先,犯罪故事通过侦破故事的话语得以展现,而侦破故事则最终通过叙述者的话语得以展现。(16) 在托多洛夫看来,这两个概念所涉及的并非故事的两个组成部分,也不是两部作品,而是同一作品的两个不同方面,体现了关于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视角,而他所关心的问题实际在于二者在侦探小说中同时存在之时所产生的特殊效果(42-44页)。由此,托多洛夫提出,前者预示着一个不在场的故事,它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不能被直接呈现在作品之中——叙述者不能够呈现涉案人的对话,也不能直接描写他们的行为,必须通过推理故事中的人物来还原这些对话和行为;后者主要起到将第一个故事传递给读者的中介作用,因此它本身必须以最为简洁、清晰的形式被呈现给读者,由此,这个故事尽管是在场的,但其本身是无足轻重的。托多洛夫继而提出,与这种结构特色形成对比的,是20世纪中叶在美国演变出的、以雷蒙德和钱德勒作品为代表的惊悚小说。这种形式将两个故事糅合在了一起,或者说将重点放在了第二个故事之上:与古典探案作品相比,罪行故事不再构成侦破故事的前传,没有谜底和猜测推想,侦探探寻案件真相的过程与经历构成了作品的核心;其创作关键也不再是将谜底按特定形式所呈现的方法,而是这种追踪过程所烘托的紧张气氛,人物形象由此成为了这类作品的关键与重点(45-46页)。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正确指出了犯罪小说中罪行和推理/侦破过程这两大故事环节,托多洛夫所作的“故事”和“话语”之分却并不恰当(胡恩将其扩展为双层故事/话语结构的做法更易引起混淆),将俄国形式主义的术语“sjuzhet”等同于英文“情节”(plot)一词也容易引起混乱。(17)“情节”这一术语从亚理斯多德以来,一直被用来谈论某个特定行为(action)从其开头、中腰到其结尾的发展过程,涉及的是小说家在想象中构建的特定故事发展序列,由此应该被看作是叙事作品中“故事”层面的内容;(18)而托多洛夫所谈论的“情节”却是“作品、叙事以及作者所采用的种种文学手法”(43页),实际指的是小说家针对故事事件所采取的特定话语呈现策略。在推理/侦探小说之中,尽管读者的好奇心由案件真相勾起,然而,在其基本叙事范式中,如果犯罪的结果在作品一开头就被呈现给读者,直接参与故事发展的人物也不是罪犯而是侦破过程中所涉及的侦探、目击者和其他证人,作品情节构建的主线就仍然是侦破和推理过程,小说情节中隐含的罪行环节实际作为其侦破环节的“前故事”(prehistory)为后者发展提供原动力。所以,托多洛夫所持的“侦破故事无关轻重”这一观点也不尽准确:读者真正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谋杀本身,更是跟随侦探、利用已有线索逐步重构案件现场的推理过程。正因如此,作者才会通过对案件线索逐步呈现的特定情节安排,借助不同叙述和人物声音的设置,有步骤、有计划地向侦探和读者透露相关信息,在满足读者与侦探平等获得案件线索这一文类惯例的前提下,将真相隐藏到由侦探本人分析案情的文本最高潮,不但为文学史留下了杜宾、福尔摩斯、波洛等经典侦探形象,也使读者在与侦探所进行的公平竞赛中获得特殊的阅读愉悦。 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多洛夫所讨论的两类作品,其故事核心实际都是案件侦破的过程,区别在于前者重视的是根据已知线索进行逻辑推理的智性思考,而后者更加看重侦探在腥风血雨中探求事实真相的冒险经历。真正关注犯罪作品中的案件环节,考察罪行本身并凸显犯罪过程的,实际当属西蒙斯所定义的纯粹犯罪小说,即直接呈现犯罪心理和犯罪过程、并将其作为小说主要故事构成的相关作品。尽管西蒙斯认为这类作品出现于20世纪后半叶,然而,在爱伦·坡的相关短篇作品中已经可以窥见其雏形。 二、犯罪小说的雏形:爱伦·坡的狂想与理性 爱伦·坡之所以被视为侦探小说之父,主要取决于他于1841-1845年间所创作的《莫格街血案》(1841)、《玛丽·罗杰疑案》(1842-1843)、《金甲虫》(1843)、《凶手就是你》(1844)、《窃信案》(1845)等五部作品。通过神探杜宾这个人物形象,爱伦·坡不但首创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侦探及其助手”型人物模式,还突破性地引入了理性推理法(ratiocination),确立了推理小说黄金时期的基本叙述形式和风格。然而,如果我们考察爱伦·坡其他短篇小说创作,不难发现他的《黑猫》、《泄密的心》等名作,往往采取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自白或临终忏悔的形式,由这些罪犯本人在暗黑和诡异的气氛渲染中讲述他们犯下谋杀罪行前后的心路历程,实际预示了日后纯粹犯罪小说的发展方向。此处,我们不妨考察一下《黑猫》开头段落中的杀妻者独白: 明天就是我的死期,而今天我要为自己的灵魂解负。我的目的就是要直白简明地向世人讲述一系列家常琐事,不加任何评论。这些事儿吓坏了我,折磨着我,最终毁灭了我。然而这些我不想多说。对我而言,它们带来的唯有恐惧——或许不少人只会觉得它们古怪却并不可怕。以后也许能找到一些更为冷静、更有条理的头脑,能将我的幻呓归结为日常琐事——那些比我更为冷静、更有条理、也不那么容易激动的头脑,能够在我带着敬畏而详细讲述的具体情况中,探查到日常普通事件的自然因果逻辑。(19) 在这段独白中,叙述者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表明了自己的叙述意图,希望让读者了解令他备受折磨、为之犯下杀妻罪行直至自我毁灭的一系列恐怖事件,而同时他也对读者的理性逻辑提出了挑战,希望有“更为冷静”、“更有条理”的头脑,能在这一奇异惊悚的故事序列中寻找到因果联系。我们看到,不少评论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对此作出了回应,试图透过主人公貌似疯狂的呓语梳理其杀妻动机、挖掘案件真相。(20)在《莫格街凶杀案》、《凶手就是你》等推理作品中,坡笔下的侦探则圆满完成了凶手提出的类似挑战,依靠理性推理打碎了奇情案件的灵异表象,在看似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现象中“探查到日常普通事件的自然因果逻辑”。 现实生活中的爱伦·坡是个矛盾复杂的人物。在斯蒂芬·奈特看来,爱伦·坡身上融合了“19世纪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两大传奇”,这一点在他的侦探小说创作中,就表现为其笔下人物杜宾兼具诗意想象和理性推理的独特侦探过程。(21)文学史家海克拉夫特则提出,在早期作品中,爱伦·坡表现出极强的痛苦焦虑感和幻想,这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直到任费城《格雷汉坶》杂志编辑一职后,他才暂时用理性压抑并战胜了自己的黑暗狂想,过上了正常的宽裕生活,这种理性的胜利同时也体现在他这一时期的《莫格街谋杀案》等作品中。(22)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黑猫》(1844)、《泄密的心》(1843)等哥特式作品同样创作于这一时期,因此,海克拉夫特的说法并不令人信服。在笔者看来,与其说这一时期的爱伦·坡是用理性压抑住了自己的黑暗狂想,不如说他是将自己的奇情狂想和理性推理,或是通过对犯罪心理的生动塑造,或是通过丝丝入扣的侦破与推理过程,按照自己对短篇小说的一贯要求、作为特定的“单一效果”呈现于不同作品之中。在强调犯罪心理的部分作品中,他期望达到的效果是浪漫奇情,所以他借助非理性的哥特传统,挖掘人性中的种种黑暗欲望,并由此对理性推理提出了挑战;在推理小说中,他则用理性与逻辑战胜了奇情与狂想,将种种看似匪夷所思的事件还原成由因果关系串联的日常事件。这两类作品分别聚焦于犯罪小说“罪行”和“侦破”这两大情节内核,前者着重于对罪行及其环境的哥特式渲染以及通过罪犯自白所呈现的犯罪心理,而后者则重在凸显侦破过程所涉及的智性推理过程,将这种文体牢牢根植于19世纪小说主流的实证主义传统之中。(23)爱伦·坡所特有的写作手法则在黑暗浪漫主义非理性化趋势与实用主义的理性推理过程之间实现了奇妙的融合,不但为读者提供了特殊的阅读体验,也为后世犯罪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形式基础,预示了犯罪小说日后的浪漫奇情和经典推理这两派不同走向。 一方面,犯罪小说以犯罪作为小说情节的起点和核心之一,小说家艺术想象的内容本身就是对社会规范和理性准则的一种逾越,这种对于禁忌的逾越无论对艺术家或者读者而言都构成了某种诱惑,直接照应了人类意识或潜意识中的阴暗面。然而,与哥特小说神秘主义的超自然幻想不同,犯罪小说延续了《纽盖特纪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将这种逾越设置在19世纪日常生活的现实背景之下,展现了看似和谐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突然出现的断层和裂缝——平常的生活、平常的人物由于某个特定事件的突发而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点通过犯罪小说的发展分支——维基·柯林斯等人的奇情小说创作(代表作《白衣女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4)犯罪小说在对犯罪过程、案件现场及其犯罪心理的描写过程中,为读者提供了某种突破理性与法律桎梏的情感宣泄口,使之在恐惧、惊悚、怜悯等多重感官刺激中获得特殊的阅读感受。 然而,与一般通俗文学、绞刑架文学的区别在于,爱伦·坡作品所采用的典雅文体和精巧结构设计保证了其作品的文学属性,打破了通俗文学和高雅艺术之间的壁垒,通过暗黑主题和高雅文风的结合实现了特殊的审美效果。在这里,不得不提及的,是对爱伦·坡产生过重大影响(25)的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有关谋杀艺术的相关作品。在《作为一种高雅艺术的谋杀》(1827)中,他以虚构演讲作为载体,借一位“谋杀鉴赏者”在“谋杀鉴赏者协会”每月例会上所作的演讲,以讽刺幽默的语气建议读者,在对1811年托马斯·威廉姆斯在伦敦东区所犯下的七宗真实谋杀案作出恰当伦理评价之后,不妨尝试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出发,将这些精心设计的谋杀当作一种可以与“埃斯库罗斯或弥尔顿的诗句、米开朗琪罗的雕塑”相媲美、达到“壮美”效果的“高雅艺术”,进行赏析。 毫无疑问,这[谋杀]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但既然我们已无能为力,就让我们尽量利用这件坏事吧。反正我们也无法从这件事中得到任何道德裨益,那么让我们用审美的方式对待它,看我们是否能得到些什么。(26) 借用康德和席勒讨论的“壮美”与“审美”等概念,(27)德昆西提出,这里人们能够得到的是亚理斯多德悲剧理论中的宣泄效果,因为作为审美对象的谋杀,其“最终目的”同样在于“通过激发怜悯或恐惧,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28)在德昆西眼中,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对该隐弑弟场景形象而诗意的刻画、莎士比亚在其剧作中对死亡场景的描绘,都是这种审美效果的具体体现。(29)德昆西在他文中也提出,诗人在处理谋杀题材之时,必须要对谋杀者表现出同情,尽管此处的同情指的是理解而非怜悯或赞同意义上的同情,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入他的情感世界,才能够去了解他”;而这个谋杀者心中“必然翻滚着激烈的情感——嫉妒、野心、报复、仇恨,使他内心变成了地狱,这正是我们需要了解的”。(30)不难看出,德昆西已经开始关注罪犯的精神世界,而这种对犯罪心理的艺术想象则在深受其影响的爱伦·坡作品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并成为犯罪小说日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诚然,德昆西将文学作品中对谋杀的处理与现实生活中的谋杀相提并论,对威廉姆斯杀人“艺术”所表示出的审美欣赏在现实生活中确有教唆犯罪之嫌。然而,如袁洪庚所指出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脱离道德评价、仅从审美角度对作案手法进行评价的做法实际也暗示了另一种艺术的诞生:如果艺术和现实生活中的谋杀可以在审美眼光下被看作一件精心设计的艺术品,那么要对这一艺术品的组成要素进行解析和鉴赏,自然也需要另一种艺术——逻辑推理和理性演绎的艺术。(31)侦探们同样需要隔离道德评价,对案件涉及的各种蛛丝马迹进行去伪存真的理性推理,以求破解凶手所布下的谜团。叙事文本之中由此出现了两个性质不同但又紧密相关的故事时间和事件:发生在故事过去时间的犯罪行为以及发生在故事现在时间的侦破行为。犯罪行为打破了日常生活的常规和平衡,而侦探则必须通过证据收集、智性推理和诗性想象,还原凶手在过去时间的犯案动机和手段,揭露罪行并由此恢复一度被打乱的社会次序。爱伦·坡所确立的以理性推理为方向的侦破过程也成为其后百年间英国侦探小说的主要特色。 三、犯罪小说的社会纬度和伦理考量 推理小说以各种奇难疑案刺激读者的好奇心,通过侦破过程中逐渐透露的各种线索,邀请读者发挥理性推理的思考过程,与侦探一起完成这场解谜的智力游戏。然而,无法否认的是,这类以逻辑推演和名探魅力吸引读者的作品主要依赖以诡计为特色的情节内核,由此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忽视了人物性格刻画,无视造成犯罪的社会和政治原因,所展现的社会图景也十分狭隘。(32)尽管通过不同案件的设置,也通过侦探对众多嫌疑人的调查,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展现出当时社会公众的集体隐忧,揭开了中产阶级体面生活背后的秘密,从特定层面对社会核心阶层的虚伪表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然而,此类小说无意深究社会问题:试图打破既定社会次序的害群之马永远会被发现并得到应有惩罚,威胁社会稳定的破坏因素定会为强大理性所击溃;社会次序和主流价值观可能会暂时受到挑战和质疑,但最终将得到重塑与维护,而出身优越、智慧过人的男性侦探则被塑造为这种理性拯救力量的具体化身。正因如此,这一时期的侦探小说才被视为维护父系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其标志就是“男性侦探或男性叙述者那理性、高度逻辑化的冷静声音”。(33) 随着社会历史条件在20世纪40年代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如西蒙斯所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文化和宗教结构的变化打破了理性的统治地位,维多利亚时代和谐社会的假象无法得以继续保持,侦探/推理小说所努力维系的童话故事也显得可笑而幼稚(11-12页;161-162页),与此同时,传统侦探推理小说赖以生存的诡计内核在过度使用后开始呈现逐渐枯竭的趋势,这一切都推动了犯罪小说在形式和内容、尤其是其社会关联度这一层面的重大变革。因此,在美国战后发展出的硬汉派小说中,吸引读者的不再是迷宫般复杂精巧的疑案及其谜底,而是穿行于肮脏污秽的城市之中,饱经风霜、看破世间炎凉的独狼式美国侦探。罪犯在故事中的作用同样发生了改变,如钱德勒对哈迈特的著名评价所表现的那样:“哈迈特将谋杀交回给了他们手中,这些人有这么做的理由,而不仅仅是提供一具尸体而已。”(34)罪行和侦破这两大故事内核在犯罪小说的情节构建中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交叉进行、并列发展的互动关系。通过对犯罪心理的生动刻画,对不同城市场景“陌生化”的处理手法,(35)这类作品借助犯罪小说的黑色镜片呈现出了与传统文学作品截然不同的城市空间。而随着反映国家执法部门运作状况的警察程序小说在战后美国和北欧地区的出现和繁荣,随着全球化背景下罪案的国际化发展趋势,犯罪小说的社会维度和现实批判性更是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巴赫金在对复调小说和小说杂语的讨论中,曾着重指出了虚构小说以不同形式手法引入社会杂语并由此激发对话和思考的能力。犯罪小说通过罪行环节的故事建构,对犯罪地点、涉案人物、犯罪动机的艺术再现,实际上为各种激进观念提供了展示空间,引发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同时,借助侦探或警探在罪行侦破环节的所思所想所为,从特殊角度呈现了国家执法机关的运行机制,展现了对现行体制的相关批判。凭借自己对社会问题和各种社会潜流的敏感,犯罪小说家通过虚构小说的创作呈现不同的社会逾越行为,也通过罪行及其背后原因的挖掘引入不同社会杂语、揭示人性弱点和社会缺陷,正因如此,这种类型文学能够反映读者和公众的不同恐惧,能够从其特殊角度正视被大部分传统小说所忽略的社会阶层和相关问题。 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叙事小说的虚构性质容易让读者忽视相关社会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的紧迫性,将犯罪小说中所呈现的社会现象当作与现实隔离的东西;犯罪小说罪行环节所涉及的暴力场景不但向小说家提出了艺术手法和伦理考量的双重挑战,也容易使读者将其看作某种视觉奇观,从而忽视小说家通过不同罪案设置和不同艺术呈现手法对犯罪这一古老社会问题所进行的深入探讨;在犯罪小说这种目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类型文学中,不少作品也仅仅意在为读者提供感官娱乐。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都要求我们在阅读犯罪小说之时,需要仔细考察作者对“罪行-侦破”的总体情节建构,在反映社会现实、引入社会杂语过程中所采取的话语手段,审视相关文本策略背后的作者创作意图,并对之形成正确的伦理判断。 文中对坡、德昆西作品的引用由笔者在参考现有中译本后翻译,其余文献材料均为笔者自译。 ①Julian Symons,Bloody Murder:From the Detective Story to the Crime Novel(New York:Warner Books.1980),pp.1-6,pp.191-193.(下文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 ②Stephen Knight,Form and Ideology in Crime Fiction(Bloomington:Indiana UP,1980). ③Stephen Knight,Crime Fiction 1800-2000:Detection,Death,Diversity(Houndmills.Pasingstoke.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4). ④Warren Chernaik et al.eds.,The Art of Detective Fiction(Houndmills/Pasingstoke/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0). ⑤Ed Christian ed.,The Postcolonial Detective(Houndmills.Pasingstoke/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1). ⑥Bruce Murphy ed.,Encyclopedia of Murder and Mystery(Houndmills/Pasingstoke/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2); Hans Bertens and Theo D' Haen eds.,Contemporary American Crime Fiction(Houndmills/Pasingstoke/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1). ⑦Martin Priestman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rime Fi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P,2003). ⑧Ian A Bell,"Eighteenth-Century Crime Writing",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rime Fiction,pp.7-17. ⑨Lyn Pykett,"The Newgate Novel and Sensational Fiction,1830-1868",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rime Fiction,pp.19-39. ⑩Stephen Knight,"The Golden Age",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rime Fiction,pp.77-94. (11)Andrew Pepper,"Black Crime Fiction",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rime Fiction,pp.209-226. (12)Maureen T.Reddy,"Women Detective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rime Fiction,pp.191-207. (13)Martin Priestman,"Introduction:Crime Fiction and Detective Fiction",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rime Fiction,pp.1-2. (14)Tzvetan Todorov,"The Typology of Detective Fiction",Poetics of Prose(Ithaca,New York:Cornell UP,1977),p.43.(下文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 (15)道格拉斯·克尔:《英国小说与犯罪现场》,王理行译,载《外国文学》2000年第2期,66页。 (16)Peter Huhn,"The Detective as Reader:Narrativity and Reading Concepts in Detective Fiction",Modern Fiction Studies 33.3(1987),p.452. (17)对“情节”一词在学术界的不同理解和阐释,详见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0-35页。 (18)详见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42-43页。 (19)Edgar Allan Poe,"The Black Cat",Tales by Edgar Allan Poe(New York:Cornwall Press,1952),p.655. (20)Susan Amper,"Untold Story:The Lying Narrator in 'The Black Cat'",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29(1992),pp.475-476; Joseph Stark,"Motive and Meaning:The Mystery of the Will in Poe's 'The Black Cat'",Mississippi Quarterly 57.2(2004),pp.258-262. (21)Stephen Knight,Form and Ideology in Crime Fiction,pp.42-43. (22)Howard Haycraft,Murder for Pleasure: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Detective Story(New York:D.Appleton-Century Company,1941),pp.8-9. (23)爱伦·坡推理作品与19世纪实证主义的联系,参见道格拉斯·克尔:《英国小说与犯罪现场》,67页。 (24)这类作品关注的是社会核心阶层中所发生的绑架、通奸、谋杀、重婚、欺诈、伪造等罪行,犯罪嫌疑人也多为中产阶级、甚或是上流社会的成员。这无疑可以触动普通人的阅读神经,牵扯其潜意识中的隐含恐惧,正因如此奇情小说才会被批评借助感官刺激而鼓励低级趣味。参见Rebecca Martin,"On Crime and Detective Fiction:Perversities and Pleasure of the Texts",Critical Insights:Crime and Detective Fiction,ed.Rebecca Martin(Massachusetts:Grey House Publishing,2013),xvii页。 (25)R.Morrison,"Poe's De Quincey,Poe's Dupin",Essays in Criticism 51.4(2001),p.424. (26)Thomas De Quincey,"On Murder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ine Arts",On Murder(New York:Oxford UP,2006),pp.12-13. (27)See John Samuel Harpham,"Detective Fiction and the Aesthetic of Crime",Raritan 34.1(2014),p.127. (28)Thomas De Quincey,"On Murder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ine Arts",p.10. (29)Thomas De Quincey,"On Murder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ine Arts",p.10. (30)Thomas De Quincey,"On the Knocking at the Gate in Macbeth",On Murder.p.5. (31)袁洪庚:《现代英美侦探小说起源及演变研究》,载《国外文学》2005年第4期,64页。 (32)参见George Orwell,"Decline of the English Murder",Shooting an Elephant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52),156-160页. (33)John Scaggs,Crime Fiction(London:Routledge,2005),p.20. (34)Raymond Chandler,Raymond Chandler:Later Novles and Other Writings,ed.Frank MacShane(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1995),p.992. (35)Eva Erdmann,"Topographical Fiction:A World Map of International Crime Fiction",The Cartographic Journal 48.4(2011),p.279.标签:犯罪小说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侦探小说论文; 艺术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黑猫论文; 埃德加·爱伦·坡论文; 推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