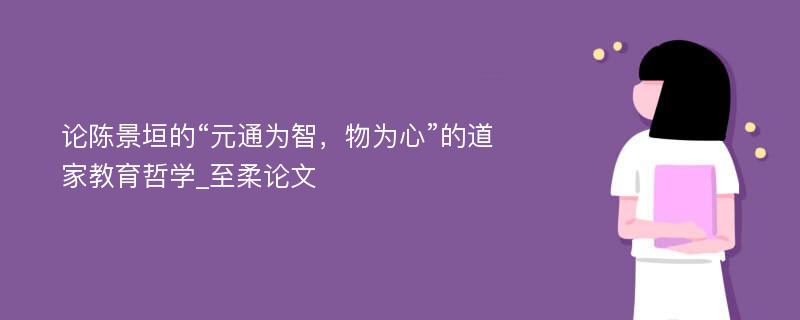
论陈景元“圆通为智,因物为心”的道家道教教育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圆通论文,道教论文,道家论文,哲学论文,陈景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景元,北宋著名道教学者,字太虚,师号真靖,自称碧虚子,建昌南城(今属江西)人。生平事迹主要见《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九、《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开题》和《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开题科文疏》卷一。“自幼读书,至老不倦”,尤其喜爱老庄思想,“凡道书皆自校写”,积日穷年[①],除著有《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十卷》、《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十四卷外,还集成《老子西升经》,“将示同学,使昭昭乎见古人之大体”[②]。宋神宗闻其名,特召对天章阁,累迁至右街副道录,赐号“真人”。从此,四方学者从游者众。后归庐山,卒于哲宗绍圣元年(1094)。陈景元在解注老庄中,提出了不少深刻的见解,且建构了一个承认差异、明辨真伪、倡导中正、力主兼容的颇具特色的道家道教教育哲学体系。
一、人从道生、禀气而别的资性差异论。
陈氏的教育哲学的建立是从对受道资性的考察开始的。他认为,一方面,道人同源——人及万物均是天地之母“道”的产物。从同类相感的角度,很自然就可以得出,人受道化,自然而然。因此,教化是可行的。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由世界的丰富多彩的特性所决定,人也会因先天之禀道气的清浊厚薄而形成学道、受教的“资性”上的差异:“气之相生,同资于道;随所禀受,名色有异”,“其心清者正而善,其识浊者邪而恶。立行既异,志性不同,故各自生意因”[③]。这种资性的差异正是陈氏建立其教育哲学体系的根据,也是他用以阐发其辩证的教育思想的前提。
为此,陈氏或把人分为至人、圣人、学人与俗人,或分为“为道学者”与“为俗学者”,或分为上士、中士、下士。认为,至人是自然得道者,圣人是教人学道者,学人是以学而入道者,俗人是因俗而离道者;上士能达道之妙而返朴归真,中下之士则只能行道之徼而迷途难返。
正是因为人的资性存在差异,因此学与教就应该坚持“合于自然涯分而无过溢之谈”的因材施教的原则,做到“量材授职,不伤性分”、“小大止足,各当其分”,以自然资性的多样性,去点缀人类世界的丰富性;在多样的差异中,创造一种教育效果上的和谐与均衡。
二、真与俗反,邪同正异的教学观。
陈氏立足资性存在差异,是为了强调要顺从自然,弗违其性,并由此把学、教之道明确划分为真学、正教,与假学、邪教,指出二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
1、是否做到“守自然之性,不越分外而学也”的“绝学”。
陈氏把真学又称作“绝学”,认为,所谓“绝学”,并非指绝而不学,而是指“守自然之性,不越分外而学也”,即按照大道之造化,服从大道之总体设计,保持自我的天真自然之“资质”,通过关注自我,发现自我,挖掘自我,达到回复本我。因此,“绝学”是指为回复本我而作出的与俗相反、与道合一的举措,具体是指:(1)善人之所不善:“常俗小人所好者有为,怀道君子所好者无为”;(2)喜人之所不喜:“人皆悦于声色,我独悦于无声”;(3)乐人之所不乐:“人皆爱于名利,我独忘于名利”;(4)为人之所不为:“人皆作憎爱,我独作不憎不爱”;(5)信人之所不信:“人皆信邪,我独信正”;(6)行人之所不行:“人皆行恶,我独行善。”[④]唯此,才可做到学而独立,在为学中找到个人恰当的位置和独特的方式,从而使本真的自我得到彰显和阐扬。
相反,假学之流以“务外学而失分内之真性”为特征,由于“心欲速达”,不惜“垂首刺股”,“映雪聚萤”、“跨步夹物”、“举踵而望”。虽“才力劣”,却“欲超略胜人”,其实质在于,“所趣不过虚名”,“所逐止存浮利”,其结果“有若延颈举踵,何能久立乎”[⑤]?
可见,在为学的态度、目标、方法上,真与俗反。
2、是否做到“因循无为,任物自然”的“不言之教”。
陈氏以“不言之教”概述了“正教”的基本特征,认为,所谓正教,就是教人以正,即“因循无为,任物自然”,“使长短广狭,大小多少,各尽其分而不损其自然之材器也”[⑥]。因此就需要立“不言之教”。
所谓“不言之教”,主要有三层含义:其一,指身教重于言教:“圣人圣天道之自然而谨身节,则伤容仪以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⑦]圣人的身体力行,就是一种无言的教化。其二,指简易、通俗、易知易行的教化。陈氏认为,“大道甚责……平易无往不达”[⑧]。“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⑨]所以,行不言之教,“并是无为、分内、简易之道。言则不繁,行则不劳,是易知易行也”[⑩]。其三,指“以道辅翼”,顺性而化。陈氏认为,清静无为是“不言之教”的精髓,无为而无不为则是“不言之教”的宗旨。虽为“不言”,却要达到“教化”的目的;虽为教化,却又自然而然,不见其迹痕。因此,一方面要做到“因人贤愚,就之职分,使人性全形完,各得其用”,从而“任其材器,使之圆曲直,不损天理”(11),无为而治;另一方面,则又应顺其自然以“辅”之:即顺善而辅之成善,迁恶以改之为善,“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也”。可见,“不言之教”既上承天道的清静无为,又顺应民情而因物化性,是“正教”也。
与此相反,所谓邪教,则以“失于自然,专任有为”(12)为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违背自然无为规律的“削足适履”。其二,以其迷迷,误人子弟。陈氏认为,“才辩始可传言,聪慧方能宣法”(13)。“而迷惑之徒谓道可以授人,自然可以与人,因相传授,岂不大惑哉?”(14)可见,“师既自迷,焉能解惑”(15)?其三,教人以邪,背道而驰。陈氏认为,人心既有顺逆之别,为行既有善恶之分,为教就必然有正邪之异:“坦荡君子,教人以正,故曰正言;嫉恶小人教人为邪,故曰邪教。”(16)
显然,真学与假学,正教与邪教,其根本的分歧就在于,是顺其自然,还是造作人为。因此,要改邪归正,超凡脱俗,就必须始终坚持“自然无为”的中正原则,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力求兼容融通;在追求均衡和谐的同时,倡导个性的发扬与升华。
三、“有无相资”、“中正无偏”的辩证教育观。
所谓“有无相资”、“中正无偏”的辩证教育观,是指在教育实践中,围绕着承认资性与强调教化、启蒙与自悟、常道与可道、守分与造极、博与专、坚与柔、真与俗等诸对矛盾,所采取的兼收并蓄、相辅相成的方法,与保持其均衡发展的态势,从而以正本清源、返朴归真为追求的最高理想而建构的辩证的教育哲学体系。其中,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1、“种根正者自然而正,种根邪者自然而邪”(17)的资性论,与“圣人运慈悲之意,开化导之方”的教化观。
如前所述,所谓资性,主要是指人学道、受教的素质、性分。由于先天禀受道气的不同,使人的资性出现了重大差异。就学道而论,既有不学而自化的“了达之人”(“了达之人无言无说,自契真常”);也有“非教不悟”的“世俗之徒”(“世俗之徒,无说无闻,不能悟道”(18));既有绝学而入道的“为道学者”,也有假学而离道的“为俗学者”。所谓“种根正者自然而正,种根邪者自然而邪”。这种资性的差异一经形成后,不仅不会轻易改变,而且还会直接引发出吉凶、祸福之结果。因此,人的资性是影响人能否学道,以及能否顺利地受道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唯有那些悟性高、德性好、且乐于接受道化的人,才可望收到施教之良效:“心能行道者,则道亦出而授之;心乐学经者,则经亦示而化之。”(19)而对那些“不知大道之自然而外物之所倾者”的“邪人”,和不“察道言之情实而大笑之”的“愚人”(20)来说,因其无受教之质,或曰“无根性”,则是“难可化谕”的。
另一方面,陈氏在肯定有不可教化的资性的同时,又十分强调教化的作用。认为,真与俗、正与邪,都是在“已然”的意义上而言的。事实上,“已然”之前存在着一个“未然”,从“未然”到“已然”,有一个由微至著的逐渐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客观存在,便是协调“不可教化”与“必须教化”的矛盾冲突的契机。为此,陈氏提出了“防微杜渐”与“依经法奉而行之”两种不同的教化理论,认为,在事物发展的“未然”阶段,应当采取前一教化方式,而在事物发展的“已然”阶段,则适于采用后一教化方式。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如是非、美丑、善恶、真假、正邪等,都是从微小累积而成的,因此,在其发展的“未然”状态,若能明察、预测,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扶植具有真善美意义的新生事物、抑制带有假丑恶基因的孽芽凶咎,则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夫是非美恶,怨怒恩德,皆生于微渐,无不始于易而终成难。”(21)“若予为之防,则未然之祸曷由而有?”(22)此谓“夫孽芽未成,凶咎未著,若救治在先,无巨恶之害矣”(23)。这种“不见其事,而见其功”的化导过程,体现的正是大道所倡导的“化导无方”,“因任自然”,“不言之教”的精神。
当事物的发展已进入“已然”状态时,则应采取“依经法奉而行之”的教化方式。因为,善恶、正邪一旦形成虽很难改变,但只要有悔过自新的愿望,教化较之前者难度虽要增大许多,但只要坚持不懈,就仍是奏效的。其具体的方法是“顺理而习,依教而行”:“但可依接经法奉而行之,先舍于恶,次忘于善;先破有欲,次灭无为;有为无为并忘,若善若恶皆泯。念念欲起,次次荡除。”(24)经过这样严格的“外去贪欲,自守无为”的层层清理、次次荡除的去尘除垢、修心修身之后,凡俗之流定然能改过自新,“反本归于真道”。
2、“道机妙不可言宣”的常道论,与“教化开不言之机缘”的可道观。
常道与可道的关系问题,是老庄以来道家道教思想家们讨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在继承前此学者的基本思想的前提下,陈氏从本末、体用、有无等矛盾关系的新的视角,对常道与可道关系作了一番深刻的阐发,试图揭示出二者之间的辩证性。
陈氏认为,由于常道之道,“杳然难言,非心口所能辩,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议”(25)。必须借可道之言即“经”而诠其理。这是因为,常道与可道,或道与经的关系,即为体与用、本与末、理与教的关系:“道为经之本体,经即道之迹用。”(26)“道,理也”;“经,教也”(27)。“本者,道也;经者,末也。”(28)因此二者“虽宗辙有殊,而体贯齐一”(29)。故尔“道非孤得,必自由经;故知人道之理,经为学先也”。
这种“经为学先”的意义就在于,“经”能对“道”进行诠释或转译或暗示,以启迪学人的悟性:“著经以宣理”,“借言以通达于理”。因此,人欲学道,就必须首先要接受圣人的教化,借圣人之经书之言,明常道之不言之理,此谓“教化开不言之机缘”。
当然,“可道”毕竟不等同于“常道”,充其量只是“常道”的一些方便说法。它在道与学人的沟通中增添“一致与共识”的同时,也会增添新的“歧异”。因为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与师说经文的文章字句,永远只能是本与末、体与用的主次关系,后者只是达到前者的桥梁。如果过分地执著甚至炫耀此“桥”此“筌”的话,很可能会因此而断送终极追求的远大前程。因此,“常道”应成为学人的“终极关怀”,“可道”则是实现这一“终极关怀”的工具,学人在经过“可道”的点化后,应通过自悟去把握大道之真义。
3、“夫人虽因师发蒙”的启悟式,与“至理出自天性”的“自得”论。
如前所述,“因师发蒙”的启悟式,是由“可道之道”完成的。没有大师的点教,学人将如盲人夜行,茫茫不知所向。因此,入道当须以“经”为学先。同时,受“道绝情虑,理超言象,隐显殊致”的“常道”之形而上特性的限制,圣人之教也常常只能采用譬喻、隐喻、转语等形式,作一些点到即止的暗示:“先圣之教如镜中之影,声中之响。随隐去来,镜自常静;随声大小,响自常无。”(30)一般在论证了要旨之后,往往不作进一步的解说:“著经处文,书其旨略而不具曲细。”(31)因此,“不易明究”,“固非浅识者所知也”。欲“寻其至理”,则须“出自天性”而“独化”。
“独化”又称作“自得”,即指在遵从大师教诲的前提下,尽可能调动自身潜意识的“能”,即出自天性的悟性,去“研寻大道,穷究幽微”。通过对师教承袭而后的超越,而达到与常道的契合。可见,在为学为教过程中,立其师资,与独化自得,是相得益彰,互相补充的,故曰:“夫圣人虽游心于自得之场,不可不立其师资也;虽立师资,复恐贵尚其师,怜爱其资,泥于陈迹,不至远达。故再举不贵其师,不爱其资也。夫人虽因师发蒙,寻其至理出自天性,是曰独化。”(32)一方面,为学必须“立其师资”,只有师授,才可望破惑开悟。而且,学有师承,才能学有根基,了解并能够遵守一些为社会认可、亦被前人证明行之有效的基本规则或学问之道,否则,纵有所得,绝难大成;另一方面,又要提倡不贵其师、不爱其资、独化自得。即在遵循师教的前提下,又要敢于超越师教。通过学人自己的刻苦钻研,以达到“文精言通,悟其旨耳”的目的。
4、“忘其企慕”的“绝学”,与“造至道之极”的“徐清徐生之道”。
人能否顺利受教、受教状况与否,与人的资性紧密相关。因此,“使人忘其企慕”而知足知止,是为学为教的宗旨。为学,则应提倡“守自然之性,不越分外而学也”的“绝学”;为教,则应倡导“明悟任物”的精神。
所谓“明悟任物”,用当今的教育学语言来表述即为“因材施教”,即顺其上智下愚的资性而有针对性的予以教化,使其各得其用,不损天理。因此,陈氏反对“拔苗助长”的做法,强调“伯乐不能御驽骀为骐骥,良匠不能伐樗栎为栋梁”(33)。即使是像伯乐那样的良师、鲁班那样的工匠,也不能训驽马为俊骑,使臭椿树成栋梁。因为,驽马不具备千里马的质性,臭椿树只是一般的木材。与其勉为其难,非分“企慕”,不始置驽马和臭椿树在适当的位置上,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进而言之,陈氏指出,在“使人忘其企慕”的同时,切不可让人丧失了“造至道之极”的追求。二者之间的辩证法在于,只有“忘其企慕”,服从自然的限定,才可能安于本分,从而在适合自我的这一范围内将自己的才情和学识发挥得淋漓尽致,以实现自我肯定性的超越和发展,从而“造至道之极”。当然,这种“造至道之极”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遵循着“徐清徐生之道”的规律。
所谓“徐清徐生之道”,是一种循序渐进的修行方式,指的是人在“忘其企慕”、做好分内之事的同时,又要防止“久而不迁,住于诸境”,因此要不断求取上进,通过“复境上善,“不住小成”的积微成渐,使境界日益更新,直至达到“至道之极”(34)。
与“拔苗助长”的外力强为方法根本不同的是,“徐清徐生之道”强调的是将内在的智慧、德性与潜力逐渐发扬光大,乃至最大极限,以达到对“道”的领悟与契合的最佳状态。因此,人首先要有自知之明,尽可能地了解自己的资性,探寻自己的思想,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在此意义上,人自然应当“忘其企慕”,力戒左顾右盼而失掉了自己独到的个性和最佳位置。其次,则应该为自己的特长的最好发挥创造一个最佳环境,去其企慕,专心致志,保持不断进取的态势,不断冲破自身的局限,以追求个性发展的尽善尽美,“造至道之极”。可见,这种注重挖掘内在资性潜力的“徐清徐生之道”,充满着辩证法的机智,可以看作是陈氏教育哲学体系中最具特色的思想。
5、“为行之道多方,修身之途非一”(35),与“专精味道,抱一守玄”(36)。
所谓“一”与“多”、博与专,实际上是指大道的基本精神的绝对性(专、一),与达道之诸多环节的相对性(博、多)之间的关系,因此,“为行之道多方,修身之途非一”,貌似博多,实则归一,此“一”即为清静无为的大道精神。前者的博、多是相对的,为一中之多;后者的一、专是绝对的,为多中之一。“一者,道之子,谓太极也。太极即混元,亦太和纯一之气也,又无为也。”(37)“抱一无为可以兼包之,故为天下式。”无论是师授、为学,还是炼己、悟真,都只是以形式上的差异之不同侧面展示着大道的统一之无为精神。所谓“得一万事毕”也。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为行之道多方,修身之途非一”,与“专精味道,抱一守玄”的辩证法在于,一分为多,从而以多求一;多统于一,从而守住“多”中之“一”。
6、“真与俗反”,与“和光同尘”。
陈氏认为,有道之士应该是,外与凡俗无异,内与大道同体的通达至士:“外示混浊,不异凡流;内本澄清,同乎道体。”(38)“内心清静,外毁波流。”(39)因此,既能“和光”,又能“同尘”:“在光则能和与光而不别,在尘则能同与尘而不异。”(40)“显则与万物共其本,晦则与虚无混其根。”(41)虽又达至道之境界,却依旧是凡俗之模样。以出世之虚心,做入世之实事。“泛然无著,若云之无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随方随圆,不滞于常。”
前面已言真与俗反,正与邪对,二者如冰炭之不可共存;此处又言“和光同尘”统于一身,前后是否构成了思维的矛盾?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前者是以分别智的态度进入道的初级境界的,后者则是以超越的精神去追求道的妙湛圆明之理想境界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
一般来说,从俗返真、改邪归正,变有为为无为,这只是修行的初始功夫。修行的至高境界则在于:“有为无为并忘,若善若恶皆泯”(42),从而,“应物则混于光尘,归根则湛然不染”(43)。与道合一,与俗无异,如赤子,如婴孩。因此,从“真与俗反”,到“和光同尘”,可以看作是认识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境界中的一次大的升华。
7、“学道者当知婴儿之貌”的至柔,与“心直如矢,志端如弦”的至坚。
婴孩之“至柔”,一向是道家道教学者们推崇且追求的理想人格。陈氏有所发展的是,他把至柔与至坚联系了起来,认为,学人的“心直如矢,志端如弦”的至坚精神,是实现至柔人格理想的重要保证。至坚与至柔在这里达到了辩证的统一。
所谓至柔,实际上是用来形容至人精神的。陈氏认为,“学道者当知婴儿之貌,所贵养其醇朴之性”(44)。这种“醇朴之性”,表现如婴儿般真性专一、虚心无情、气运自动、诸欲莫干的全真纯和之性:“夫至人纯粹,怀德深厚,情复于性,澹泊无欲,状貌兀然,比于赤子。赤子者,取其纯和之至也。”(45)这种“纯和之至”的实现,标志着归根复命、返朴归真的“造至道之极”之事业的终极完成。
而要真正实现这一至柔的终极理想,则又必须要具备至坚的最大意志、信念与精神,如金石一般,坚不可摧。因为,至柔的婴儿期在人的一生中是十分短暂的,仅是生命的一个起点。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欲念、情思的膨胀,人便逐渐会背离本然的人性而流为凡俗,沦为邪恶:“有欲之人贪遂境物,亡其坦夷之道,但见边小之缴迷而不返,丧失真原。”(46)因此,欲回复人性的本初,以返“坦夷大道”,就必须要做到“心如金石,形如枯木”。“行之以深,信之以笃”,否则,散漫疑虚、三心二意,或“有始而无卒,先勤而后惰,功业近成不能戒慎”的话,则会前功尽弃,“复亡败也”。可见,至坚而后才能至柔。至柔的实现凝聚了至坚的艰辛与奋斗。可以说,至坚是人性为找回失去的自我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代价,这个代价的价值则可以由至柔的实现而充分证明。至坚与至柔的辩证统一,为人性的起点与终点的逻辑统一找到了结合点,从而为陈氏教育哲学体系的最终完成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不难看出,陈景元的道家道教教育哲学体系尽管是以解老注老的形式而建构起来的,但形式的平淡却无法遮掩其辩证思维的灿烂的光芒。那种对历史上一直传为佳话的“垂首刺股”、“映雪聚萤”的中肯的批判,表现了超乎寻常的远见卓识。而在常道与可道、启蒙与自得、忘其企慕与造其至极,博与多、坚与柔等矛盾的两极寻找使之均衡的“张力”的思想,更是对传统的中庸境界的超越,充分展示了陈景元作为道家道教学者的“智者气象”。
注释:
①《道藏》第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下同。
② ③ ④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4)(27) (28) (30) (31) (35) (36) (42) (44)《道藏》第14册。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11) (12) (21) (22) (23) (25) (32)(33) (34) (37) (38) (39) (40) (41) (43) (45) (46)《道藏》第13册。
(26) (29)《道藏》第2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