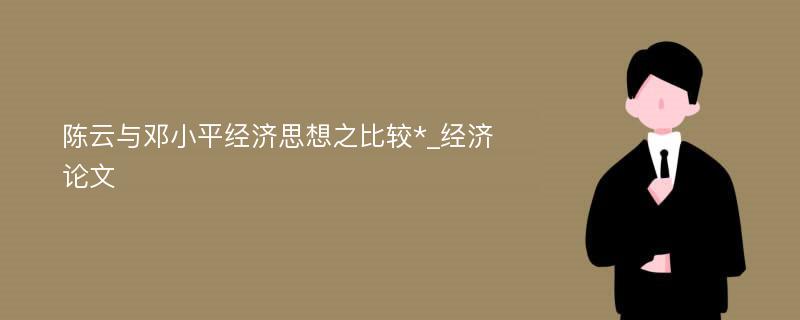
陈云和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经济论文,陈云和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爱云译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邓小平等人成为负责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政策的领导人。面临着变幻、严峻的经济形势,他们都试图设计、发展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本文主要论述70年代末、80年代初陈邓二人对中国经济变革、经济政策的主张,并分析其异同。
陈云
70年代末、80年代初,陈云最主要的经济思想是把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即计划经济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市场调节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须的。虽然他没有明确指出市场应发挥多大作用,但他坚持认为供与求是决定许多商品生产量必不可少的因素。陈云所指的市场是西方经济学家可以理解的,即它是“盲目的”、“无政府的”,反映了价值规律(商品按等量价值交换)。在1979年,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是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3月,陈云就计划与市场问题写了一份提纲,认为“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①]
1981年下半年到1982年,陈云更关注计划经济问题。他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比作“小鸟与鸟笼”。计划是鸟笼,市场是小鸟,如果鸟笼太小,小鸟就会窒息;如果没有鸟笼,小鸟就会飞走。他强调许多经济部门必须由计划支配,例如农业。企业也应该有计划,产品有没有销路,原料从哪里来,都要计算好了,才经营得好。陈云指出,实际上资本主义企业也相当有计划。他建议改进中国原有的特别强调总产量的计划体制,使计划制定程序合理化。然而,他没有明确说明如何改进计划工作。
经济调整是陈云的另一个主要思想。他被看作是“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建议者。陈云并不是首次提倡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他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调整思想与1956—1957年、1961—1962年调整期间的思想是一致的。在他看来,调整包括一系列综合措施,如扩大财政对计划的支配作用,降低计划指标,减少基本建设、尤其是重工业的投资等等。历次调整总是通过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来监督计划、财政,陈云是历届财经委的主任。
陈云提出,经济要合理运行,就必须做到“三大平衡”,即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物资平衡(1979年后又加上外汇平衡)。这三大平衡加强了财政、贸易系统的职能,削弱了计划机关在经济决策中的霸权和重工业在计划中的优先权。陈云还为在“文革”中遭受严厉指责的财贸金融系统恢复名誉,指出财政、金融、商业部门“消息灵通、反映灵敏”,“在这些部门中可以看出大局”。[②]陈云还反对财政赤字,要求严格的财政集权,这就批评了1980年初确定的财政分权。
陈云调整思想的另一主要观点是削减基本建设、尤其是重工业建设规模。1979年初他指出,华国锋1978年初提出的1985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方案是不可能做到的。1985年根本达不到生产6000万吨钢,那时能生产4500万吨、2000年生产8000万吨就不错了。到2000年实现华国锋所制定的1985年目标是比较实际的。至于冶金工业部迅速提高中国钢铁生产量的设想,陈云说:“冶金部提出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设想,我都看了。他们是好心,想要多搞,可以理解。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现在的情况是:冶金部一是把问题看简单了,二是看孤立了。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③]陈云认为迅速提高钢铁生产量是没有绝对可靠的基础的。
陈云提出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即生产必须首先保证最低的生活水平,只有保证有饭吃之后,国家才能进行新的建设。这意味着消费品比重工业更重要。对陈云来说,工业现代化是以引进技术、而不是以新建设为基础的。他倡议在每个五年计划期间只建设一个像宝钢那样大的工程。但他没有详细阐述引进工业技术方面的具体经济政策。
陈云还坚持整体利益是第一位的,换句话说,中央利益高于地方利益。1981年12月,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发表了“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的讲话,在最后要求以中央为中心,并说:“我讲的这些话,都是‘北京话’。地方的同志说北京人讲‘北京话’,我是上海人,但话属于‘北京话’。有的同志讲,赵紫阳同志到了北京以后,讲‘北京话’了。我看这是确实的,因为赵紫阳同志是管全国的”。[④]
1978年以后,陈云还多次谈到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的问题,这也是陈云主要经济思想之一。他不反对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国门,但他认为应严格控制中国的外债,应慎重评价经济特区的经验。他一再警告,借外债前一定要考虑到如何偿付债务,考虑还本付息问题;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借给中国钱,是为了能挣钱。他宣称,他不反对利用外资,但干部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外债,外国资本家并不是为了给中国做好事,而是尽可能从中国获取最大利润。他希望国家全面控制中国与国际企业、国际银行的经济往来。他赞成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低利自由外汇贷款,而不愿向其他外国银行贷款。陈云还指出,有的外债是重工业部门为逃避经济调整而借钱继续其建设项目的一种手段。
陈云也很关心经济特区,他多次强调慎重估价经济特区的经验。1981年12月,他指出虽然各省都希望办经济特区,但特区不能再增多了,尤其是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经济特区。从总体上说,陈云对中国向国际经济开放的路线方针,尤其是对经济特区,是有点矛盾心理的。
综上所述,70年代末、80年代初陈云主要经济思想可归纳如下:首先,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市场调节范围可以变化。但他没有指出市场发挥作用时,价格的波动范围。其次,必须严格调整经济,严格控制基本建设、尤其是重工业建设规模。要以三大平衡机制衡量国家计划,以确保首先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确保适当的建设规模。他强调财政预算平衡,认为财政集权是关键。最后,陈云在中国对外开放问题上有矛盾心理。他认为外债和经济特区试验都可实行,但领导必须警惕不能失去对国际政治经济交往的控制。总之,与改革相比,陈云更着重调整。
邓小平
与陈云相比,邓小平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较为灵活。确切地说,邓小平很少具体地谈论经济问题,他对经济事务所做的一些评论十分抽象。由于邓的经济思想比较散,所以作者是按时间顺序进行论述的。
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邓小平就提出整顿工业领导班子,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迅速发展经济等主张。1977年恢复工作后,他着手贯彻1975年制定的一系列方案,并亲自抓科学与教育工作。1978年3月,他支持工资改革,赞成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赞成调工资、涨工资、恢复奖金制度。但他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改善工资制度,如何制定奖金。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吉林省领导人时提出,中国应对外开放。他解释说:“国际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中国“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⑤]在他的鼓励下,1978年底,中国与许多外国公司签署了协议。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总结性发言,着重讲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要求向基层单位下放决策权,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要求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加强经济管理,加强责任制等。
此后不久,到1979年3月,邓小平就完全改变了下放权力的主张,要求在陈云和财经委的领导下,以“强有力的集中领导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进行经济调整工作。他降低了从西方国家增加进口的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领导地位。换句话说,邓小平似乎远离了三个月前所讲的话。
直到第二年,邓小平才又深入讨论经济事务。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讲话中,他表示要继续进行调整与改革,继续发挥并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更快、更好地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原则。他还首次提出市场对计划生产起补充作用。但他没有谈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没有涉及1979年发生的最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至于改革与调整,邓小平比陈云更强调改革,指出尽管“改革的步骤需要放慢一些,……(但)已经从各方面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要继续实行,不能走回头路”。[⑥]邓小平最希望继续进行的改革措施是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政策。看起来虽然邓小平承认需要调整,但他只是把调整期视为改革再次成为重点之前的一段短暂间歇。甚至说,他可能只是勉强支持严格的调整。
可以看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在不同的时期支持过发展中国经济的两条政策路线(改革、调整)。相对来讲,他比别人更看重活跃经济,他首倡通过外债、技术引进和经济特区向国际经济开放,并大力支持下放权力、推行按劳分配原则和奖金制度。他还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改革中的主导地位,要求党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目前中国最“毛泽东主义’的领导人。
陈云、邓小平经济思想之异同
陈云、邓小平都主张中国经济必须现代化,实现现代化主要依靠提高已建成企业的技术水平,而不是新建设。必须改进强调总产量的计划体制,运用市场补充计划。他们一致认为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实行生产责任制和厂长负责制。也认为必须平衡国家预算,降低通贷膨胀,优先发展轻工业、农业,控制基本建设尤其是重工业建设规模。还要求中国向国际经济开放,并进一步发挥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专家在实现现代化中的作用。他们也都同意对中国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然而,具体到如何贯彻其中的一些措施,陈、邓二人却存在某些差异。如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陈云比邓小平谨慎。与市场相比,陈云更强调计划;与微观经济问题相比,陈云更关注宏观经济问题。总之,与改革相比,陈云更着重调整。
邓小平比陈云更明确主张中国对外开放。与调整相比,邓小平更倾向于改革。陈云依靠三大平衡机制来到引导经济,邓小平则认为党在中国经济变革中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邓小平还把现代化与建立新的、大型的现代企业相联系。总的来说,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比陈云更灵活。
虽然陈云、邓小平在一些重要经济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这些分歧是互补性的,甚至是分工性的,不会影响他们合作进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注释:
[①] 《陈云文选》第3卷,第24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陈云文选》第3卷第279页。
[③] 《陈云文选》第3卷第251—252页。
[④] 《陈云文选》第3卷第307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2页。
* 本文编译自《陈云与中国政治体制》一书,加利福尼亚大学1985年出版。著者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