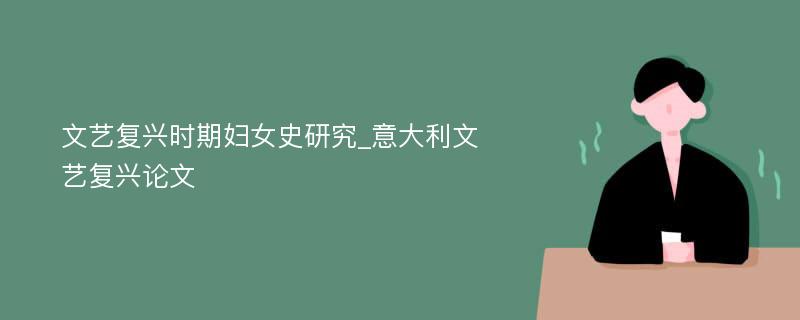
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妇女论文,文艺复兴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以来,妇女史日益成为西方文艺复兴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学者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新的研究成果对旧的文艺复兴解释体系提出了严重挑战。中国学者王挺之先生很早就注意到西方文艺复兴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并做了简要的介绍。(注:王挺之:《文艺复兴研究的新趋势》,《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78页。)本文则打算进一步评述欧美学界对文艺复兴妇女研究的成就和最新动态,希望能对国内读者有所裨益。
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单独列出一章探讨妇女的地位问题。他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上层妇女经历了与贵族男子一样的重大变化,她们接受了相同的文学和语言学教育,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并在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总之,她们处于和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注: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87—393页。)如同布克哈特的宏大文艺复兴观,他对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的论断也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
自布克哈特到20世纪60年代,妇女研究在文艺复兴学界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注:美国学者华莱斯·佛格森在他那本论述文艺复兴学术史的经典著作《历史思想中的文艺复兴》(Wallace Ferguson,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48)中未提及任何研究文艺复兴妇女的著作即是佐证。)对文艺复兴时期妇女问题有所关注的学者寥寥无几,仅有朱利亚·卡特莱特、马丽·坎农、伊西多罗·德尔·伦格、埃马努埃尔·罗多卡纳基等。(注:例如,Julia Cartwright,Isabella d'Este,Marchioness of Mantua,1474—1539,New York,1903;Mary Cannon,The Education of Women during the Renaissance,Washington,D.C.,1916;Isidoro del Lungo,La donna fiorentina,Florence,1906;Emmanuel Rodocanachi,La femme italienne al'epoque de la Renaissance,Paris,1907.以上所举著作转引自Margaret King,“The Renaissance of the Renaissance Women,”in Paul Clogan (ed.),Medievalia et Humanistica,New Jersey:Rowan & littlefield,1988,p.165.)如同布克哈特,这些学者的视野也主要集中于少数精英女性,尤其是显赫的贵妇和知识女性,而他们对文艺复兴妇女的乐观描述也与布克哈特的论断基本一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注:例如,伊西多罗·德尔·伦格宣称, 但丁对碧亚特丽丝的理想化描绘揭示了中世纪晚期妇女的地位及人们对她们的尊重,他的这一观点转引自Samuel Kohn Jr.,Women on the Streets:Essays on Sex and Power in Renaissance Italy,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19.另外,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西方文艺复兴学者对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夸大其词的描述,可参考Lisa Jardine,“The Myth of the Learned Lady in the Renaissance,”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28(1985),no.4,pp.799—819.)这些学者的论述进一步扩大了布克哈特文艺复兴妇女观的影响,如20世纪早期被列入“家庭大学丛书”(Home University Library)并在英语世界流传甚广的《文艺复兴》一书对文艺复兴妇女的描述即为布氏文艺复兴妇女观的翻版:“文艺复兴时期是妇女的时代,它给妇女提供了新的领域,并赋予其新的重要性……她们充满活力和好奇心,展示了一种本真的成熟,她们的艺术和本能矛盾地混合在一起,她们自由自在、快乐、妩媚动人,她们乐观地看待自己和他人,在她们看来,一切似乎都是有价值的。她们跳舞、歌唱、统领军队,她们读维吉尔、西塞罗和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她们操持庞大的家庭、撰写著作、设计服装并治理国家。”(注:Edith Sichel,The Renaissance,London:Williams & Norgate Ltd.,1914,pp.129—130.)这段热情洋溢的文字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妇女的黄金时代,这种浪漫色彩十足的布克哈特式文艺复兴妇女观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直盛行不衰。(注: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里亦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它有利于强者的暴露,对性别则漠不关心。女人成为权倾一时的君主、战士与将领、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这些著名女人大多数都是高级妓女;她们在精神、生活方式和财源上都是自由的,她们的罪过和放荡都有传奇色彩。”)
从20世纪60年代起,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影响日益扩大,妇女史作为“新社会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开始受到史学家的重视。另外,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欧美女权主义运动也对西方学术界造成猛烈的冲击。(注:关于女权主义运动对妇女史研究的推动,可参考Joan Scot,“Women's History,”in Peter Burke (ed.),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University Park: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pp.43—64.Merry Wiesner,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1—3.)正是在“新史学”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双重影响下,欧美文艺复兴学界日益重视对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的研究。
70年代早期,西方学界出现了一些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的论文,它们多从家庭史的角度探讨文艺复兴时期上层妇女的处境。经济—社会史家理查德·戈德斯维特认为,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兴建私人宫殿的热潮,致使贵族的家庭结构从传统的联合家庭(大家庭)逐渐向以一对夫妇和孩子为中心的核心家庭转变,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贵族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获得提高,成为真正的一家之主。(注:Richard Goldthwaite,“The Florentine Palace as Domestic Architectur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7(1972),no.4,p.1009.)社会史家劳洛·马丁认为,虽然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道德规范要求妇女留在家里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但有些妇女,尤其是一些商人和官员的妻子也从事家务以外的工作,她们的世界并未局限于家庭。(注:Lauro Martines,“A Way of Looking at Women in Renaissance Florence,”The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vol.4(1974),no.1,pp.15—17.)斯坦利·乔伊纳基认为贵族妇女是影响显贵家族之间关系的重要力量,她们在威尼斯政治和社会网的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注:Stanley Chojnacki,“Patrician Women in Early Renaissance Venice,”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vol.21(1974),pp.176—203.该文后收入其论文集:Women and Men in Renaissance Venice,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p.115—131.本文引用的是后者。)可以发现,上述学者虽不一定同意布克哈特关于文艺复兴妇女的论断,但仍强调了文艺复兴对妇女的积极影响,从这个意义讲,他们仍未跳出布克哈特文艺复兴妇女观的范畴。
真正的突破发生在1977年。这一年,美国妇女史家和女性主义者琼·凯莉—加多尔发表了《妇女有一个文艺复兴吗?》一文,(注:Joan Kelly-Gadol,“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in Renate Bridental (ed.),Becoming Visible: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7,pp.139—164.)矛头直指布克哈特的文艺复兴妇女观。她认为,从男人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确是一个进步时代,因为这一时期的所有进步,包括资本主义经济、近代国家和人文主义文化,都为男人提供了种种机会,男人发现了他们的个性和尊严,并追求世俗生活的幸福。但对妇女来说,文艺复兴却是一个倒退的时代,“国家、早期资本主义以及由它们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文艺复兴时期各阶层妇女的生活,但一个惊人的事实是,妇女作为一个群体,特别是意大利城市里的贵族妇女,她们的社会和个人选择面却逐步缩减。”(注:Joan Kelly-Gadol,op.cit.p.139,140,147—148,161,139,140.)凯莉—加多尔特别借助典雅爱情(courtly love)文学中两性关系的变化来支持其观点。她发现,在中世纪的典雅爱情文学中女性受男子尊重,两性关系基本平等,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典雅爱情文学却日益强调女性的贞洁,并把两性关系塑造成男尊女卑的形式。(注:Joan Kelly-Gadol,op.cit.p.139,140,147—148,161,139,140.)她认为文学作品中两性关系的变化正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里,贵族妇女拥有较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她们可以通过赞助艺术和典雅爱情文学有意识地塑造有利于女性的理想爱情并使之广为流传。(注:Joan Kelly-Gadol,op.cit.p.139,140,147—148,161,139,140.)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贵族妇女却丧失了支持文化活动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事实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进步——她的原始资本主义经济、国家和人文主义文化——一起把妇女塑造成一种美丽的摆设:端庄、贞洁、对丈夫和君主双重依赖。”(注:Joan Kelly-Gadol,op.cit.p.139,140,147—148,161,139,140.)由此,凯莉—加多尔指出:“妇女没有经历自己的文艺复兴,至少在文艺复兴时期是这样。”(注:Joan Kelly-Gadol,op.cit.p.139,140,147—148,161,139,140.)凯莉—加多尔的这篇论文震撼了欧美文艺复兴学界,可以说,这是掀起文艺复兴妇女研究高潮的一篇纲领性论文,此后关于文艺复兴妇女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她所提出的问题而展开的。
妇女在俗世
凯莉—加多尔指出,研究社会的象征产品,如文学、艺术和哲学里的妇女意识形态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们不仅直接反映了社会主导阶层的妇女观,也暗示了妇女的性、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等信息。(注:Joan Kelly-Gadol,op.cit.p.139,140,147—148,161,139,140.)但完全借助文学资料却使其论述显得有些单薄。伊安·麦克林的研究弥补了凯莉—加多尔的不足。他发现,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医学、伦理—政治学和法学著作中所体现的妇女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世纪晚期经院主义妇女观的延续,它们都宣扬了这样一些观念:女人在身体和精神方面天生不及男人,呆在家里、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和服从男人对她们而言是天经地义的事。(注:Ian Maclean,The Renaissance Notion of Wom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麦克林的研究表明,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受到男权意识形态的压制。
在男权意识形态的压制之下,妇女在各个领域的实际处境如何?妇女史家沙龙·詹森首先探讨了妇女在政治领域的活动机会与空间问题,这正是传统的文艺复兴政治史著作、尤其是普及性著作所缺失的,它们往往只涉及男性统治者及其治国术,女统治者基本上被排除在外。正如詹森抱怨的,“历史”‘故事’仅限于一连串我们所建构的著名男子”。(注:Sharon Jansen,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Female Rulers in Early Modern Europ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p.6.)为弥补传统政治史的不足,发现“被湮没”的女统治者的历史,她详细论述了15世纪后期法国、英格兰和苏格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一些著名女统治者的事迹,努力重建女统治者主政的模式。不仅如此,詹森还特别注重性别因素,即从女统治者的视角看近代早期欧洲的政治史,并由此提出与传统政治叙事不同的“叙事”,比如她的研究就向近代早期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叙事认为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疆界划分,但从女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疆界仍互相交叉”。(注:Sharon Jansen,op.cit.pp.223—228.)如果说詹森勾勒了妇女对政治的直接参与,那么纳塔利·托马斯则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了上层妇女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情况。她一反19世纪以来借助为某位宫廷贵妇立传塑造具有传奇色彩的文艺复兴妇女形象的惯常做法,深入探讨了甚少为学者注意的佛罗伦萨美迪奇家族的女性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注:Natalie Tomas,The Medici Women:Gender and Power in Renaissance Florence,Aldershot:Ashgate,2003.)对精英妇女参政经历的“发现”有助于纠正男性中心主义的文艺复兴政治史的不足,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尤其是普通城市妇女是否获得了和男子一样的参政机会呢?路易·哈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妇女的公民权是不完善的,或者说,她们只享有除参与政治生活之外的“消极公民权”。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艺复兴时期对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严格区分(前者属于男子,后者属于女性)及文艺复兴城市的军事性质,(注:Louis Haas,“Women and Politics in the Urban Milieu,”in Linda Mitchell (ed.),Women in Medieval Western European Culture,New York:Garland,1999,pp.221—235.)这一现象也反映了男女的不平等。
文艺复兴是欧洲文化发展的高峰之一,因此,妇女参与文化生活的情况自然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学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该时期的知识女性(女诗人、女作家、女人文主义者等)身上,为使更多人了解这些知识女性的精神世界,他们大力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她们的著作,这些基础工作大大推动了关于文艺复兴妇女的研究。(注:例如,Margaret King & Albert Rabil,Jr,(ed.),Her Immaculate Hand:Selected Works by and about Women Humanists of Quattrocento Italy,New York:Medieval & Renaissance Texts & Studies,1983.目前,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正陆续出版“近代早期欧洲的异声丛书”(The Other Voi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这套丛书汇编、翻译、整理出版一些知识女性的著作,许多女人文主义者和女作家的著作首次有了英译本。)在知识女性中,最受关注的是女人文主义者,因为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文化运动,所以妇女对这场文化运动的参与自然备受重视。马格丽特·金深入考察了伊索塔·诺加罗拉(Isotta Nogarola,1418—1466)、卡桑德拉·费代莱(Cassandra Fedele,c.1465—1558)、劳拉·切蕾塔(Laura Cereta,1469—1499)和亚里桑德拉·斯卡拉(Alessandra Scala,1475—1506)等杰出女人文主义者的求知生涯,她发现,女人文主义者从事学术研究的道路荆棘密布,常使她们无法实现其学术抱负。障碍之一是婚姻与学术研究的矛盾,许多女性的求知生涯婚后就停止了。更大的障碍是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她们一方面受到大多数女同胞的误解甚至敌视,另一方面,大多数男子根据“女人有才便无德”的传统观念把她们视为不男不女的怪物(或变性人),他们甚至还给那些追求学术研究的女性冠以不贞的帽子。在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女人文主义者被迫或放弃学术,或进入修女院,或孤身独居,默默地生活在书本构建的牢狱之中。(注:Margaret King,“Book-Lined Cells:Women and Humanism in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in Albert Rabil,Jr.(ed.),Renaissance Humanism,vol.1,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8,pp.434—453.)李萨·佳尔丁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她认为男子可凭借其人文主义训练成为教师、顾问和公职人员,但女人文主义者即使在学术领域达到相当造诣,也无法凭此获得体面的职业,她们所接受的人文主义教育及其在人文主义学术上的成就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高雅的装饰。(注:Lisa Jardine,“Women Humanists:Education for What?”in Lorna Hutson (ed.),Feminism and Renaissance Stud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68—69;Lisa Jardine,“The Myth of the Learned Lady in the Renaissance,”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28(1985),no.4,pp.815—819.)马格丽特·金和李萨·佳尔丁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冷酷的事实:人文主义运动带给妇女的好处是十分有限的,妇女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其人文主义教育而改变,妇女与男子的平等根本无从谈起。
女艺术家是文艺复兴时期另一个引人瞩目的女性群体,但传统的文艺复兴艺术史著作对她们鲜有记载。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论述文艺复兴女艺术家的论文和专著相继问世,这些著作展示了普罗佩尔齐亚·德·罗西(Properzia de'Rossi,c.1490—1530)、索芙尼斯巴·安圭索拉(Sofonisba Anguissola,1532—1625)、拉维尼亚·丰塔娜(Lavinia Fontana,1552—1614)等著名女艺术家的成就。(注:例如,Whitney Chadwick,Women,Art,and Society,London:Thames & Hudson,1990,pp.59—103;M.D.Garrard,“Here's Looking at Me:Sofonisba Anguissola and the Renaissance Women Artist,”Renaissance Quarterly,vol.47(1994),no.3,pp.556—662;Caroline Murphy,Lavinia Fontana:A Painter and Her Patrons in Sixteenth-Century Bolog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F.Jacobs,Defining the Renaissance Virtuos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对这些女艺术家的研究促进了人们对文艺复兴妇女的了解,也弥补了传统文艺复兴艺术史的不足。
如果说,女人文主义者和女艺术家通过直接参与文艺复兴文化促进了其发展,那么也有些女性借助另一种方式——文化赞助——对文艺复兴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对妇女从事艺术赞助的研究最充分,而对她们在其他文化领域的赞助涉及不多。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研究文艺复兴艺术史的学者对曼图亚公爵夫人伊莎贝拉·代斯特(Isabellad'Este,1474—1539)的艺术赞助、艺术趣味和艺术收藏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其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给予高度评价。(注:Rose San Juan,“The Court Lady's Dilemma:Isabella and Art Collecting in the Renaissance,”in Paula Findlen (ed.),The Italian Renaissance:The Essential Readings,Oxford:Blackwell,2002,pp.317—340;Clifford Brown,“A Ferrarese Lady and A Mantuan Marchesa:The Art and Antiquities Collections of Isabella d'Este Gonzaga(1474—1539),”in Cynthia Lawrence (ed.),Women and Art in Early Modern Europe,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pp.53—71;Molly Bourne,“Renaissance Husbands and Wives as Patrons of Art:The Camerini of Isabella d'Este and Francesco II Gonzaga”,in Sheryl Reiss (ed.),Beyond Isabella:Secular Women Patrons of Art in Renaissance Italy,Missouri: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pp.93—111.)埃芙林·维尔希探讨了15世纪米兰、曼图亚和莫德纳等地宫廷妇女的艺术赞助与宫廷政治生活的密切联系,她指出,宫廷妇女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即增强其丈夫和儿子的政治影响力的框架内进行艺术赞助的。(注:Evelyn Welch,“Women as Patrons and Clients in the Courts of Quattrocento Italy”,in Letizia Panizza (ed.),Women in Italian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Society,Oxford:Legenda,2000,pp.18—29.)由此可见,宫廷妇女的艺术赞助和艺术收藏并不完全取决于艺术趣味,也是维护其家族声誉和统治的重要手段。与上述学者相比,凯瑟林·金的视野要广阔得多,她不但讨论了文艺复兴时期贵族妇女的艺术赞助,也考察了宗教妇女和艺妓的艺术赞助情况及其特点,凯瑟林·金曾直言不讳地说,她的研究本质上是一项女性主义的事业,即重建女赞助人的历史。(注:Catherine King,Renaissance Women Patrons,Manchester &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pp.5,201—210,247—253.)事实上,对妇女艺术赞助的研究热情一直持续下来。(注:例如,Sheryl Reiss (ed.),Beyond Isabella:Secular Women Patrons of Art in Renaissance Italy.)对妇女从事艺术赞助情况的研究一方面揭示了女赞助人在塑造文艺复兴文化,尤其是视觉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以艺术大师和艺术风格演变为中心的传统艺术史,向注重艺术与社会互动的新艺术社会史的转变。
然而,参与政治、从事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仅仅是少数精英妇女,那么在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群体中占多数的普通劳动妇女的生活处境又如何呢?一些学者考察了城市资本主义对普通妇女生活的影响。朱迪斯·布朗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佛罗伦萨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结构的变化,托斯卡纳地区的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她们参与户外工作,赚取工资,成为工薪妇女。这些拥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自然比纯粹的家庭主妇高,从这个意义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有一个文艺复兴”。(注:Judith Brown,“A Women's Place was in the Home”,in M.Ferguson (ed.),Rewriting the Renaissance,Chicago &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pp.206—224.)科恩也认为,1346年至1600年期间,托斯卡纳地区的妇女在佛罗伦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她们不仅广泛从事各种职业,而且也能加入小行会,甚至是一些大行会,她们在一些重要行业(如纺织业)内的地位也并非最低。总之,这一时期妇女的经济独立性和经济地位都有所提高。(注:Samuel Cohn Jr.,“Women and Work in Renaissance”,in Judith Brown (ed.),Gende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London & New York:Longman,1998,pp.107—126,especially,pp.115—126.)乔伊纳卡对威尼斯普通妇女的研究进一步增强了布朗和科恩的结论,她指出虽然威尼斯的普通妇女受到父权制社会的种种限制,但她们的生活空间并不囿于家庭,甚至享有比贵族妇女更大的“能动性”(agency)或“社会权力”:她们能走出家庭,通过工作养家糊口,在城市里自由经商,在宗教和世俗法庭中捍卫自己的权益,构筑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等,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既属于男人,也属于妇女。(注:Monica Chojnacka,Working Women of Early Modern Venice,Baltimore & London: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pp.xiii—xxii,138—139.)这些研究表明,文艺复兴时期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如凯莉—加多尔所说加重了妇女对男子的依附,相反,它提高了妇女的自主权,并拓宽了妇女的生活空间。
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婚姻状况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早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一些美国学者仍遵循布克哈特传统强调文艺复兴对妇女的积极影响时,法国女学者克拉皮什一祖伯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她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剖析了佛罗伦萨上层妇女在家庭谱系里的地位及其财产权。她指出,佛罗伦萨家庭由男人确立,亲属网由男子决定,财产继承也依据男性,妻子在家中完全是一个过客。(注:C.Klapisch—Zuber,Women,Family,and Ritual in Renaissance Italy,translated by Lydia Cochrane,Chicago &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p.117—118.)此外,佛罗伦萨的法律也规定了不利于妇女的嫁妆制度和财产继承权,(注:Ibid.,p.216.)这都表明父权制对妇女的压制依然很重。法制史家托马斯·库恩对克拉皮什—祖伯的观点提出修正意见,他指出,“在佛罗伦萨的财产继承制度中妇女并未被完全排除在外,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如娘家没有儿子或兄弟时,女儿也可以享有继承权。”(注:Thomas Kuehn,Law,Family and Women:Toward a Legal Anthropology of Renaissance Italy,Chicago & London: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4,pp.238—257,especially,pp.254—257.)斯坦利·乔伊纳基有关威尼斯贵族妇女嫁妆的研究表明,贵族妇女具有对嫁妆的支配权,因而大多数贵族妇女在丈夫死后不寻求再嫁,而是留在丈夫家中抚育子女。(注:Stanley Chojnacki,“Getting Back the Dowry:Venice,c.1360—1530”,in Anne Schutte (ed.),Time,Space,Women's Liv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Missouri: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pp.77—96.)可见,克拉皮什—祖伯说妇女是家庭“过客”,显然太绝对了。对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婚姻状况的研究也表明了男女的不平等。首先,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很少有婚姻自主权。大量研究表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尤其是北部和中部地区)盛行的嫁妆制度使中下层家庭的女子在婚嫁问题上基本无自主权可言。即使对上流社会的女性来说,以情爱和个人自主为基础的婚姻也十分罕见,她们被父亲当成通过联姻维护家族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筹码,(注:J.Kirshner & A.Molho,“The Dowry Fund and the Marriage Market in Early Quattrocento Florence,”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50(1978),no.3,p.436.)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注:包办婚姻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主导婚姻模式,这一点基本上得到公认,此外还可以参考Anthony Molho,Marriage Alliance in Late Medieval Florence,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Trevor Dean (ed.),Marriage in Italy,1300—16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3—16.)其次,在嫁妆上涨造成家庭财政困难时,家长往往采取有利于男嗣的婚姻策略,迫使“多余的”女儿进入修女院,以避免因支付嫁妆而导致家庭经济危机。(注:请参阅本文后面评述西方学术界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修女研究的部分。)
上述研究表明,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在俗世的生活状况是复杂多面的,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们并没有摆脱父权制的压制和束缚,更没有处于“和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当然也不应过分夸大父权制的压迫,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并未一味消极屈从,而是表现出了相当大的能动性,因此,断言妇女没有一个文艺复兴也欠妥当。只有将父权制的压迫与女性的积极能动结合在一起,才能描绘出一幅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世俗妇女生活经历和处境的完整画面。
妇女与宗教
多数学者认为,妇女在12世纪至16世纪中期的宗教生活和宗教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妇女开创了体验和表达宗教虔诚的新方式。许多无法进入修道院的贫苦少女和寡妇自发组织了一些非正式的宗教团体,她们一起祈祷、相互扶助,过着平等友爱的生活。如15世纪荷兰出现的“共同生活姐妹会”,该会成员无须立下宗教誓言,只靠自己的努力维持生计。在同一时期的一些意大利城市也出现了一些开放式修女院,它们接纳寡妇、未婚女子,甚至包括从良的风尘女子。(注:Merry Wiesner,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183—184.)这些女性宗教社团在城市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甚至一些上层妇女也被吸引加入其中。在特伦特宗教会议之前,这些准宗教妇女(介于专职修女和世俗妇女之间)组成的宗教社团在宗教生活和宗教文化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注:Patricia Raneft,Women and the Religious Life in Pre-modern Europe,London:Macmillan,1998,pp.79—112;George Duby (ed.),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vol.3,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37—166.)其次,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许多“卡里斯玛妇女”(charismatic women),即那些具有“超凡魅力”的女圣徒、女神秘主义者和女预言家等,她们对当时的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赫尔利在其《妇女有一个文艺复兴吗:我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虽然妇女在很多领域日益丧失其地位、权力和知名度,但许多女性仍以其超凡魅力获得了社会影响力。1348年到1500年间就出现了因个人宗教虔诚而赢得众多追随者的卡里斯玛妇女,如锡耶纳的圣·凯瑟琳(St.Catherine of Siena,1347—1380)、圣女贞德(St.Joan of Arc,1412—1431)、热那亚的圣·凯瑟琳(St.Catherine of Genoa,1447—1510)等,赫尔利认为这些妇女“都是最充分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坚信自己的力量,抨击男子占支配地位的机构及其领导社会的方式。这些卡里斯玛妇女极频繁地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社会,并对社会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妇女有一个文艺复兴。”(注:David Herlihy,Women,Family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Oxford:Berghahn Books,1995,pp.33—56 especially,p.56.)意大利女学者加布里埃拉·扎里亦指出,在16世纪早期(1530年之前),意大利各个城市卡里斯玛妇女的数量急剧增加,她们在世时就被世俗大众视为“活圣徒”(living saints)而备受崇敬,她们成为意大利各地宫廷的座上宾,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即使去世后,她们依然在很长时间内受到人们的缅怀和敬仰。(注:Gabriella Zarri,“A Typology of Female Sanctity in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in D.Bornstein (ed.),Women and Religion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Italy,Chicago &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p.219—240.)赫尔利和扎里的研究揭示了妇女在宗教领域获取权力和社会知名度的特定方式:由于罗马教会的中级和高级教职皆由男性垄断,妇女要在宗教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显然不能通过罗马教会,但她们却可以唤起普通大众的宗教情感并产生共鸣来获取影响力。这些卡里斯玛妇女的巨大感召力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虔诚的信众对罗马教会世俗化和腐败的失望、不满和情感疏离,这恰恰是正统的罗马教会陷入深刻危机的表现,这或许能为我们认识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提供新的视角。
在过去几十年里,欧美学界对文艺复兴时期修女的研究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注:关于西方学术界对文艺复兴时期修女院和修女研究的最新动态,还可参考S.Evangelisti,“Wives,Widows and Brides of Christ,”Historical Journal,vol.43(2000),no.1,pp.239—245.)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呈现如下特点。一是研究区域相对集中,尤其以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修女的研究成果居多,近年来关于威尼斯修女的论著逐渐增多,但研究对象的区域不平衡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二是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元化,如理查德·特雷斯克勒和朱塔·斯伯林就独辟蹊径,分析了修女院与城市社会之间的关联。理查德·特雷斯克勒认为文艺复兴时期修女院和修女数量的持续增长(至16世纪后期达到顶峰)是由于嫁妆飞涨,迫使许多家庭不得不把“多余的”女儿送至修女院,这样,修女院客观上充当了佛罗伦萨的国家福利机构。(注:Richard Trexler,“Celibacy in the Renaissance:The Nuns of Florence,”in Richard Trexler,Dependence in Context in Renaissance Florence,Binghamton,New York:Medieval & Renaissance Texts & Studies,1994,pp.343—372.)朱塔·斯伯林指出,在文艺复兴晚期,约有50%—60%的威尼斯贵族妇女进入修女院,但真正自愿当修女的女性并不多。她认为嫁妆飞涨只是迫使威尼斯贵族妇女进入修女院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威尼斯贵族的价值观,由于贵族家庭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不允许自己的女儿下嫁给比自己门第低的家庭,这样就导致许多女子不能出嫁,被迫进入修女院。(注:Jutta Sperling,Convents and the Body Politic in Late Renaissance Venice,Chicago &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斯伯林的研究对于深入认识威尼斯的贵族文化也是颇有助益的。上述研究表明,文艺复兴时期的修女院绝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世界,相反,它一直与城市社会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朱迪斯·布朗则以16世纪晚期托斯卡纳的一个修女院为个案,阐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女同性恋现象和性观念。(注:朱迪斯·布朗:《不轨之举: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修女》, 王挺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她的著作是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叙事史复兴”的“微观史学”(micro—history)的佳作之一。
另外,学者对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修女院的文化生活进行了深入探讨。沙龙·斯特罗基亚考察了佛罗伦萨的拉波修女院和圣尼科罗修女院附属学校给世俗女子提供教育的情况,指出修女院学校不仅是世俗女孩获取读写基本技能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塑造、表达和传播15世纪佛罗伦萨女性文化的一些重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注:Sharon Strocchia,“Learning the Virtues:Convent Schools and Female Cultur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in B.Whitehead (ed.),Women's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New York:Garland,1999,p.36.)埃丽莎·魏沃尔着重考察了1450年至1650年间托斯卡纳地区修女院内部的文化生活,她指出,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修女多来自中上层家庭,受教育程度较高,她们不仅阅读《圣经》、祈祷,也从事著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她们还编写剧本和上演戏剧,这些戏剧不仅能提供娱乐,也是妇女接受教育的重要途径。这些戏剧对修女院以外的世俗社会也有影响,是世俗大众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注:E.Weaver,“Spiritual Fun:A Study of 16[th]Century Tuscan Convent Theatre,”in M.B.Rose (ed.),Women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6,pp.173—197.)在她看来,修女院的文化生活构成了主流文化之外的一个女性亚文化传统(feminine subculture)。(注:E.Weaver,Convent Theatre in Early Modern Ita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2—3.)凯特·罗芙剖析了修女撰写的历史著作并归纳了其特点:风格多样,注重个人经历和口述材料,虽以修女生活为主,但兼顾世俗世界。另外,修女还开创了以修女院院长为中心的历史纪年法,这意味着修女院的历史是以女权为中心的历史。(注:Kate Lowe,“Historical Writing from within the Convent in Cinquecento Italy,”in Letizia Panizza (ed.),Women in Italian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Society,Oxford:Legenda,2000,pp.105—118.)还有些学者探讨了修女的艺术创作、艺术赞助以及修女院的音乐文化。(注:有关修女艺术赞助研究成果甚丰,其中比较重要的专著有J.M.Wood,Women,Art,and Spirituality:The Poor Clares of Early Modern Ita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A.Thomas,Art and Piety in the Female Religious Communities of Renaissance Ita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此外还包括大量论文J.M.Wood,“Breaking the Silence:the Poor Clares and Visual Arts in Fifteenth Italy,”Renaissance Quarterly,vol.48(1995),no.2,pp.262—286;Kate Lowe,“Nuns and Choice:Artistic Decision-Making in Medici Florence,”in E.Marchand & Alison Wright (ed.),With and Without Medici:Studies in Tuscan Art and Patronage,1434—1530,Aldershot:Ashgate,1998,pp.129—153;M.Winkelmes,“Taking Part:Benedictine Nuns as Patrons of Art and Architecture,”in G.A.Johnson (ed.),Picturing Women in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Ita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91—110;关于修女的音乐文化,可参考C.Monson,Disembodied Voice:Music and Culture in an Early Modern Italian Covent,Berkeley &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研究修女院的相关著作的不断涌现反映了近年来西方文艺复兴学界的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各种“小社会”,并孜孜不倦地发掘这些“小社会”代表的亚文化传统(包括女性亚文化传统)。对各种亚文化传统的发掘不仅可以丰富文艺复兴时期的大众文化,也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文艺复兴时期的精英文化。
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主义”
在关注文艺复兴妇女在教俗两界实际处境的同时,学者也注意到文艺复兴时期妇女自我意识的变化。中世纪的消极妇女观在文艺复兴时期仍大有市场,但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出现了敢于挑战男权妇女观的女性,她们为自己的性别辩护,宣扬妇女的美德。这种现象引起学者的浓厚兴趣,他们称此为“文艺复兴女性主义”。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并不存在“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学者主要用这个词指文艺复兴时期妇女捍卫自己性别的思想意识和抗争精神。
凯莉—加多尔在《早期女性主义理论与妇女之争》中对现代女性主义之前的女性主义思想做了一个长时段的考察。她指出,早期西方女性主义起源于中世纪晚期法国的“妇女之争”(querelle des femmes),它在反击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厌女(misogyny)传统的斗争中诞生并不断发展,所以,1400年至1800年之间关于妇女的争论具有积极意义,若没有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18世纪末期现代女性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像的。此外,她还敏锐地指出了早期女性主义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或者说不足):“早期女性主义者的斗争没有体现为政治行动,仅局限于笔战。”(注:Joan Kelly-Gadol,“Early Feminist Theory and Querelle des Femmes,1400—1789,”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vol.8(1982),no.1,pp.4—28,especially p.28.)这一洞见为后来学者认识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主义确定了基调。
康斯坦丝·乔丹主要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著作中的“女性主义言论”。她把这些言论界定为“为妇女辩护的言论”,(注:Constance Jordan,Renaissance Feminism,Ithaca &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2.)并将其分成两类:一是肯定家庭生活胜过教会提倡的独身生活的,二是为妇女争取与男子平等地位的。(注:Ibid.,p.11.)乔丹在肯定这些辩护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文艺复兴时期为妇女的辩护并没有成为社会革命的前提,这些著作中所提出的种种改革建议,如教育、婚姻法和公共生活方面的改革建议,从未变成行动纲领;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要求变革,也没有一个场所可以接纳这些特定的不满。而且,这些作家对这些信念的忠诚度也不尽一致。”(注:Ibid.,p.309.)
碧亚特丽丝·戈特利布通过分析法国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san,c.1364—c.1430)和纳瓦尔的马格丽特(Margaret of Navarre,1492—1549)的女权思想,总结了15世纪女性主义的特点。(注: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代表作《妇女城》已有中译本(李霞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戈特利布指出,虽然两位女作家犀利地批评了男权专制,并捍卫自己的性别,但她们的思想与当时社会的主导爱情观和宗教观有颇多吻合之处,例如,她们给妇女指的出路就是争取过一个好基督徒的生活,妇女比男人更容易得到上帝的宠爱,表现了其女权思想的浓厚基督教渊源。因此,戈特利布认为不能夸大她们的女性主义思想,它只是“认真反思妇女的处境并主张妇女在现实世界应受到更好对待的思想。”(注:Beatrice Gottlieb,“The Problem of Feminism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in Julius Kirshner (ed.),Women of the Medieval World,Oxford:Basil Blackwell,1987,pp.337—364,especially p.359.)另外,戈特利布还通过对15世纪女性主义和近代女性主义的比较揭示了早期女性主义的局限。她指出,从19世纪开始的近代女性主义强调“男女能力平等的信念,女性受教育和职业训练的平等机会,女性团结起来争取她们所渴望的东西等一整套纲领”,(注:Ibid.,pp.359—360.)而这些都是15世纪女性主义所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戈特利布提醒人们在把现代的“女性主义”一词用于文艺复兴时期时应有足够的警惕性,否则就可能产生时序倒错(anachronism)。
维吉尼亚·考克斯和萨提亚·达塔考察了以莫德拉塔·冯特(Moderata Fonte,1555—1592)、鲁克雷西亚·马里内拉(Lucrezia Marinella,1571—1653)和阿坎杰拉·塔拉波提(Arcangela Tarabotti,1604—1652)等为代表的威尼斯女性主义思想。(注:他们分析的对象主要是莫德拉塔·冯特的《妇女的美德》(Il merito delle donne,1587)、鲁克雷西亚·马里内拉的《妇女的高贵与优秀》(La nobiltà et eccelenza delle donne,1600)和阿坎杰拉·塔拉波提的《父权专制》(Tirannia paterna,1654)。)他们与戈特利布一样,也注重从当时的语境解读女性主义,因而得出的结论也相似:首先,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上半期的威尼斯女性主义是“妇女之争”传统的一部分;其次,威尼斯女性主义思想的出现与当时威尼斯社会和文化环境息息相关。考克斯认为,16世纪威尼斯女性主义诞生的社会根源是贵族妇女处境的变化,那时,由于嫁妆上涨,贵族家庭采取了保护家族财政的婚姻策略,强迫“多余的”女儿进入修女院,如此不公平的命运安排激发了一些贵族妇女反抗男权专制的女权思想。(注:Virginia Cox,“The Single Self:Feminist Thought and the Marriage Market in Early Modern Venice”,Renaissance Quarterly,vol.48(1995),no.3.pp.513—581,especially,p.521.)达塔则分析了威尼斯女性主义产生的文化原因:比如识字率的提高,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及威尼斯作为文化出版中心的地位等,这些都是促发威尼斯女性主义思想的有利条件。(注:Satya Datta,Women and Men in Early Modern Venice,Aldershot:Ashgate,2003,pp.155—182.)
上述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女性主义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们廓清了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源流和谱系。过去不少学者在追溯西方女性主义的思想传统时,往往以18世纪末期为起点,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显然欠妥,(注:约瑟芬·多诺万的《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过作者在序言里坦承,19世纪的女权主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现在她倾向于认为“西方社会早期的女权主义浪潮发生在15、16、17世纪”。顺便提一下,该书书名或许译作《女性主义的思想传统》更为妥当。)事实上,在现代“行动女性主义”之前还应加上一个“空想女性主义”阶段。其次,它们对认识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的生活经历和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两性关系开辟了一条新路。虽然文艺复兴时期女性主义确如某些学者所言未能转化成社会运动,但这不免有苛责古人之嫌。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主义更应得到积极评价,它是文艺复兴妇女身上最耀眼的部分,也是妇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解放,正如16世纪威尼斯女性主义者鲁克雷西亚·马里内拉所说:“如果妇女从压迫她们的漫长梦魇中觉醒过来,那么,傲慢和忘恩负义的男人们将变得何其温顺和谦卑。”(注:Merry Wiesner,“Gender”,in Guido Ruggiero (ed.),A Companion to the Worlds of the Renaissance,Oxford:Blackwell,2002,pp.188—204,especially,p.199.)我们不得不赞同妇女史家曼瑞·魏斯娜的观点:皮桑等女性主义者的存在表明“妇女有一个文艺复兴”。(注:Ibid.,pp.188—204,especially,p.204.)
余论
由于几十年来学者的不懈努力,文艺复兴妇女研究从昔日的边缘课题变成今日文艺复兴学界的显学,并从社会史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领域。丰富的研究成果使人们对文艺复兴妇女的生活和处境的了解比以前更深入和全面。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从事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研究的学者与布克哈特一样,主要依靠文学著作考察文艺复兴妇女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且常常集中于少数精英妇女,视她们为文艺复兴时期所有妇女的缩影,结果不免失之偏颇。20世纪60年代之后,学者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展,他们广泛利用公私档案、婚约、遗嘱、私人日记或札记、税收记录、审判记录等第一手材料,采用跨学科方法来考察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他们的研究对象也不再局限于精英妇女,而是放眼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妇女,包括下层妇女,展现了一幅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生活的真实、完整的画面。
丰硕的研究成果使“重写文艺复兴”成为必要。妇女在传统的文艺复兴研究中不受重视,在各类关于文艺复兴的著作中所占比例都很小,但最近几十年来关于妇女的研究使人们对文艺复兴时期不同阶层妇女的生活有了更多了解,这就要求修改传统的文艺复兴史学框架,补充更多有关妇女的内容,使她们从“看不见的”和“无声音的”的群体变成“看得见的”和“有声音的”群体。必要时,甚至要彻底抛弃旧的史学框架,撰写以文艺复兴妇女为主体的各种“历史”(her-story)。(注:事实上,一些学者已经做了积极的尝试, 马格丽特·金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Margaret King,Women of the Renaissance,Chicago,1991)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做了总体描绘,强调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受到的结构性压制。该书尚无中译本,不过新近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加林主编,李玉成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收录了她论述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的一章,可供参考。最新出版的“朗曼欧洲妇女史”(Longman History of European Women)系列中的第二卷《中世纪欧洲的妇女:1200—1500》(Jennifer Ward,Women in Medieval Europe,1200—1500,London:Longman,2002)在大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翔实地描述了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生活。该书描述多过分析,思想深度上不及马格丽特·金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此外,曼瑞·魏斯娜的《早期近代欧洲的妇女和社会性别》(Merry Wiesner,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3)也是一部优秀的妇女史,不过该书侧重于1500—1750年间的欧洲妇女。)
但也有学者开始意识到,只“发掘”或“复原”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的经历是不够的,他们发现妇女的实际处境与两性关系的社会—文化建构(性别)存在密切关联。因此,他们研究的兴趣逐渐从纯粹的妇女史转向性别分析。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琼·斯科特就呼吁用社会性别(gender)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注:Joan Scott,“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1(1986),no.5,pp.1053—1075.这篇文章的中译文刊登在李银河主编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51—175页。)她的倡议得到一些文艺复兴学者的响应。(注: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代表性别研究取向的著作包括Judith Brown (ed.),Gende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London & New York:Longman,1998;Natalie Tomas,The Medici Women:Gender and Power in Renaissance Florence,Aldershot:Ashgate,2003;Satya Datta,Women and Men in Early Modern Venice,Aldershot:Ashgate,2003.)一位文艺复兴女学者解释说:“妇女史充其量帮助人们发现了隐藏在历史背后的妇女的生活,但是,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把妇女史隔绝为一个孤零零的领域,有可能使妇女的过去非历史化,形成一个永恒不变的受害图景。这样一来,无历史性的和无阶级性的‘妇女’就可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客体而非主体。然而,历史学家想要了解的是作为妇女和男子如何解释男性和女性的意义,以及过去的男人和女人所赋予‘女人属性’和‘男人属性’的特征,而且这些属性如何被时间和空间改变,男女双方如何为了不同的目的运用这些属性。”(注:Judith Brown (ed.),Gende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London & New York:Longman,1998,pp.3—4.)这段文字表达了这些学者对纯粹“发现式”或“填补式”妇女史的不满,阐述了他们从事性别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目标。性别理论的引入将在文艺复兴妇女研究方面开辟一个新天地,它将产生另一个学术研究的高峰,并形成新的研究范式。
本文得到北美基督教联合董事会亚洲高教基金会的资助,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