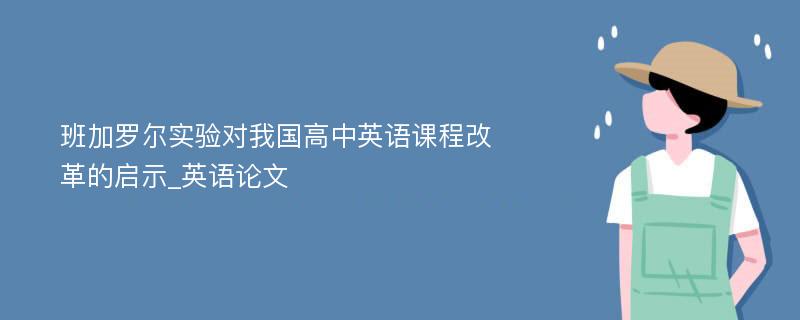
论班加罗尔实验对我国高中英语课改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课改论文,启示论文,高中英语论文,我国论文,论班加罗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部2001年和2003年制订和颁发的两个英语课程标准都倡导在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中使用任务型语言教学途径。在没有二语习得环境的条件下,任务型语言教学要在中国外语教育这块土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只有依照我们的国情、教情和学情的实际对其加以改造,使之本土化、多元化,才能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1]。然而,在改造利用某种方法之前,我们一定要追根溯源,在深入了解其来龙去脉并充分理解其内涵实质的基础上,才能取其精华并加以借鉴。本着这种认识,笔者根据任务型语言教学实验的先导者之一印度语言学家N.S.Prabhu《第二语言教育》一书对班加罗尔实验进行简述,并结合我国高中英语教学的现状,通过比较班加罗尔实验背景、原则和方法,梳理出该实验对我国高中英语课改的一些启示。
一、班加罗尔实验的内容与特点
国内许多研究者在论述任务型语言教学时,都提到Prabhu的班加罗尔实验(Bangalore Project),但很多介绍均引自Howatt 1984年对该实验的简短描述和把其归类于强势交际观产物的论述[2]288,对班加罗尔实验的具体介绍、分析和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却为数甚少。Prabhu的《第二语言教育》一书主要内容是他对该实验的介绍、分析和总结,其中大量包含他对以“任务”为形式的交际英语教学的理念、目标、教学方法、大纲和教材等方面的论述。
班加罗尔实验第一学年教学采用的几种主要方法是完成故事(教师在讲述到某一故事最有趣之处时停下,邀请学生给出可能的结局)、模仿(包括角色扮演和戏剧改编)、各种智力游戏以及“真实生活会话”(教师和学生就课堂之外有关他们自己、他们的看法或经历的话题相互交谈)。但由于活动难度、趣味性、教师与学生间期望值的差异、缺乏稳定的不同课文教学模式等原因,这个时期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实验组经过反思和师生间的协商,决定采用“任务”形式,即“需要学生对所给信息经过思维处理后取得结果,教师对其过程进行控制和管理的活动”[3]24进行教学。每节课分为“前任务”、“任务”和“结果”三个部分。“前任务”为教师控制和指导下全班活动(通常为师生间的问答或对话,占半个至三分之二课时时间);“任务”则是由每个学生独立完成(或有时两个学生自愿合作)并需要教师在特定处给予帮助的活动;“结果”指对个体学生完成“任务”的书面陈述的快速评价,这种评价重在内容而非语言,它既能为学生提供成功水平方面的建议,同时也为教师对任务难度的反思和优化下一步课程设计提供了机会[3]24。为区别于S-O-S的活动形式,实验组采用“聚焦意义活动”,在活动中,学生进行理解、扩展(例如通过推理)或传送意义,同时解决任务中遇到的语言形式问题。因此,对语言形式不是故意关注,而是附带在感知、组织和表达意义中。任务包括三大类活动信息差距活动、逻辑推理活动和观点表述活动。信息差距活动中学生的任务是传递信息,即把信息转为语言陈述,或把语言陈述转为信息;这种活动较为简单,往往一步到位,与逻辑思维关联甚少,常会影响学生保持兴趣。逻辑推理活动要求学生从给定的信息中,通过推断、演绎、实际推理或根据对关系或模式的感性认识,推导出新的信息。观点表述活动要求学生在给出的情景中识别和阐明个人爱好和情感态度;但因难于提供客观统一的对错标准而对学生的安全感有所影响。逻辑推理活动既为满足感,又为安全感提供了保证,所以最为理想。此外,实验中还使用了任务序列,即由形式相同的任务组成的若干节课,后来的任务是先前任务的总结或是先前任务中推理的扩展。
由于“聚焦形式的描写语法教育只能提高学生的语言显性知识而非发展他们的内化系统;预先计划好的、有选择性的聚焦形式的‘课堂后的’常规教学①同样如此”[3]73,Prabhu提出,“一种更好的方法是由聚焦意义活动一个需要理解或获取意义所需要的过程组成的课堂任务型互动”[3]16,28,这是班加罗尔实验“程序教学大纲”的内核。“在这种教学大纲中,语言教学不是从语法或词汇出发,而是围绕任务进行组织。其目的是使用和学习语言,而不仅仅是学习语言项目”。实验使用的任务类型都是贴近学生生活的功能项目,包括认时间、识地图、做课程表、制定活动计划、查询列车时刻表、填写表格信息等任务的适合度按照实验大纲提供的五个参数,即(1)信息提供程度,(2)推理需要程度,(3)准确需要程度,(4)对制约因素的熟悉程度,(5)抽象化程度来设计[3]87-88,其顺序则按照“对意义复杂性增加的常识判断”[3]39来决定实验的教学资源主要包括教学材料和教具两个部分Prabhu认为,任务课堂教学不是课本行为或语言呈现,而是话语创造的环境;教学材料只是语言学习的可借用助手,是构建课堂教学的实用话语项目,任何任务型教学的材料来源只能是教师收集的教学资料而非教科书;任务教学资料选择取决于其认知复杂度和语言可行度,即对学生既有挑战性,又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实验组没有使用国家大纲和指定教材[3]93-94。实验中使用的教具与当时印度大多数学校的实际相符,只用了黑板、粉笔、纸和铅笔
二、对我国高中英语课改的启示和借鉴
在讨论班加罗尔实验对我国高中英语课改的参考和借鉴性之前,首先应当分析两个问题(1)中印两国在英语教学环境和学生英语学习动力方面的异同从英语环境方面来看,当时在印度英语作为“准官方语言”使用,使用英语的印度人大约占总人口的5%;在很大部分领导阶层中和大城市里将其作为一种通用语言使用[3]5。目前印度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大力推行英语教学,部分学校采用英语讲授各门功课;在大学阶段,除个别文科外,全部采用英语教学[5]。而在我国,尤其在西部地区不存在这种目的语环境从学生学习动力方面来看,由于英语在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是一种影响择业和晋升的重要因素,学习者的工具性学习动机很强但中国学生很少会有对外语学习有更大促进作用的综合性动机,而且就整体而言,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的工具性也不十分明确[6]。但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后经济与国际接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资和合资企业的开办对基础英语和高等英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情况在上海、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凸显出来,使相当部分高中学生因升学和就业目的而驱动的工具性动机大大增强尽管存在上述不同,但“当时在印度南部,孩子们未必需要功能语言教学法所强调的那种英语的社会和个人语境。如果他们将来需要英语,很可能在一种偏向知识而非情感的、需要充分母语帮助的教育环境中学习”[7]347,表明我们在教学环境和学生动力方面与班加罗尔实验开始时的情况多少存在相似之处。(2)英语教学中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二者间关系处理问题。班加罗尔实验采用的是强势交际观的理念,Prabhu一再强调,由于“语言能力主要由自动遵守语法规范的能力和理解、获取或传送意义的交际能力组成”,因此,“教学只关注在课堂上创设对付意义的环境,而非任何发展语法能力或单纯的语言行为情景的预设规则”[3]1-2。这种观点显然过于极端,它可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针对情景听说法弊病的一种“矫枉过正”。班加罗尔交际教学实验是在1979年开始的,而那时我们刚刚才把听说法引进中学英语教学,我国初中和高中英语大规模引进和提倡采用交际法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使我们能够通过比较,不走极端,尽可能科学实效地处理好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的关系。比如,我国1992、1993年提出的“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7]252和“初步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8]304,以及章兼中提出的“交际的能力”[9],就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学英语教学目标。又如,我国1992年引入交际法时,人教社推出的“五步教学法”也是结合我国教学实际,整合形式与意义优势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再如,近年来我国基础英语教材所采用的“功能-结构-话题-任务”[10]274相结合的设计途径,也是融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为一体,符合我国学生学习实际的教学途径。
班加罗尔实验之后,“TBL成了当代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产生了各种任务型语言学习大纲和指导原则,有的相互之间差异很大,有的相互之间渗透重叠。但是各种大纲和指导原则都坚持一条主要原则:强调完成课堂活动/任务的自然学习过程”[11]。遵循这一原则,笔者认为,它主要有以下几处值得我们在高中英语课改中参考借鉴。
任务要源自真实生活,要生活化。班加罗尔实验强调紧贴真实生活的任务,强调任务活动要贴近学生学校内外的真实生活,强调使用学生生活语言。在班加罗尔实验中,语言活动不仅用于课堂活动,而且用于考试。当然,我们在教学时不可能像Prabhu那样丢弃大纲和课本去设计和使用真实生活任务,但可以通过填补信息差距来逐步实现真实语言教学的目的。为此,教师可以根据所教的功能话题,尽可能使用信息差距来设计各种不同形式的听、说、读、写活动。这些活动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模拟真实或相对真实的(笔者认为,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我国教学实际),“只要任务型活动可以填补一个‘gap’,只要不照搬虽贴近外国学生生活却不贴近我国学生生活的‘任务’,就能够成功地进行任务型教学”[12]168。教师在设计任务时,可以参考Prabhu[3]138提供的和Richards、Rodgers[13]232-233推荐的真实生活任务。需要强调的是,高中英语的任务设计不仅要考虑任务的生活化,还应当紧贴学生的未来学业、职业的真实要求来选择任务的形式、语言和内容。
任务过程要简单化、易操作,适用于大班教学。Prabhu提供的两个“前任务”课堂实录[3]123-137均是大班问答活动。与PPT不同的是,教师没有把呈现、练习、表达分离开来,而是使用问题和教具,把学生引入具有信息差距的真实语言情景里,让他们经过思维和判断后回答问题,对于语言结构(如词汇、拼写、短语等),则通过个别/全班学生在语境中重复的方式进行掌握。教师不时使用自己重复和用yes肯定等方法帮助学生理解或学习。笔者认为,这种方法既容易操作,又与意义和思维紧密联系,非常利于大班教学中的教师控制和学生学习,值得西部农村和民族地区高中教大班的教师试用。需要指出的是,班加罗尔实验的对象是8-13岁学生,而高中学生具有“成人学习者运用抽象思维和自身生活经历进行学习,对学习过程怀有期望并已有自己的学习模式,纪律性较强和学习动机比较稳固等特点”[14]40。因此,高中英语大班式“任务”教学应针对学生生理、心理特点和语言、思维水平,可采用问答、复述、讨论、讲演、辩论、表演、集体/独立/分角色阅读、合作/独立写作等多种活动方式进行。教师在设计各种“任务”时,应参照Stevick所描述的不同类型外语学习者的特点②,在“有的放矢”和“因材施教”的原则下,充分考虑“有意识学习”和“语境中习得”的关系、机械性练习和思维性应用的比例、语言结构学习和信息内容活动的方式、问题和“任务”的难易程度等相关因素,确保学生能通过课堂活动,在学习语言知识和掌握语言技能的同时,逐步形成初步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注重非物质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非物质教学资源“包括教学环境、师生群体及其互动模式、教师的智能结构和教师的教学艺术等”[15],在语言教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Prabhu在此方面提供了很多见解,如教师的教学语言要确保与课堂任务的关联性及可理解性;在教学中要让学生进行独立的思维努力,使任务具有合理的挑战性;教学中要使用其他非目的语资源,如推测、手势、习俗和识数知识以及母语等;教师要与学生进行协商,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调整和修订任务的难度和方式。此外,他还就如何进行“非故意纠错”,如何解决“任务疲劳”问题,以及如何促进语言教学专门化和发展教师的应变意识等进行了论述。这些经验对我国高中英语教学改革,尤其是西部农村高中和民族高中的英语课改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针对这些学校因英语物质教学资源的相对落后而极大地影响了教学效果的现状,我们可以通过加大开发和利用非物质资源来提高教学质量。一方面,要善于利用学生自身方面的资源,如通过调查和协商,根据班级和个体学生的语言水平和兴趣取向把任务或活动设计得丰富有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按照班级中学生的人际关系和学习水平等排座或分组,使课堂氛围始终保持和谐融洽;让学习较好的学生发挥“小老师”的作用,在学生中开展互帮互学和合作学习的活动;改变传统的作业评改方式,采用“自我纠错—同伴纠错—教师纠错”的方法和D.Byrne的纠错符号③来消除教师“见错就纠”的现象,给学生提供更多自我发展的机会;改进评价方式,大量采用过程性评价,制定有利于学生发展的评价和测试标准等。另一方面,教师要自觉提高自身的教学理念和专业素质,如多搞科研多读书,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和语言水平;每天坚持收听英语广播,优化自己的语音语调;建立集体备课制度,提倡同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关爱学生,走进学生中间,经常与他们交流协商,关注他们的情感发展等。
尽管Prabhu的交际观是激进和超前的,但他承认客观上交际路子的多元化[16]199,早在1990年他就指出,“教学环境方面存在的大量差异影响了最佳方法的选择。因此,世上没有一种可被视为人人适用的最佳方法”,“不同的最佳方法只适用于不同的教学环境;每种方法或数种不同方法——甚至可能在概念上矛盾的方法,都有一定道理(价值或有效性)”[17]。班加罗尔实验已经过去30年,在此期间任务型语言教学从理论到实践也从雏形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尽管此后国内外许多专家已从多方面探讨了它的价值和缺陷,有人甚至认为“班加罗尔实验呈现对交际语言教学的根本背离”[18],但“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该实验是战后最富创新的实验之一,它在促进语言教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使其在我们整个专业领域内始终占有重要一席”[7]349。它的价值还不仅表现在学术方面,“今天印度在信息技术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03年仅在班加罗尔地区电脑软件的出口总值就超过两亿五千万美元。很凑巧,班加罗尔也是著名语言学家N.S.Prabhu上世纪80年代在当地中小学进行交际法英语教学试验取得出色成绩的地方”[19]。这也是我们应当回视班加罗尔实验并研讨其可借鉴之处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按照Prabhu的分类,前者是指“规则操练活动”和“形式操练活动”,后者则指“意义操练活动”。
②Stevick把外语学习者分为7类,即直觉型学习者(intuitive learner),正式型学习者(formal learner),非正式型学习者(informal learner),想象型学习者(imaginative learner),主动型学习者(active learner),思维型学习者(deliberate learner),自省型学习者(selfaware learner)。引自E.W.Stevick.Success with Foreign Languages:Seven Who Achieved It and What Worked for Them.Hertfordshire:Prentice Hall,1989.pp.1-127.
③转引自J.Harmer.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3rd edition),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