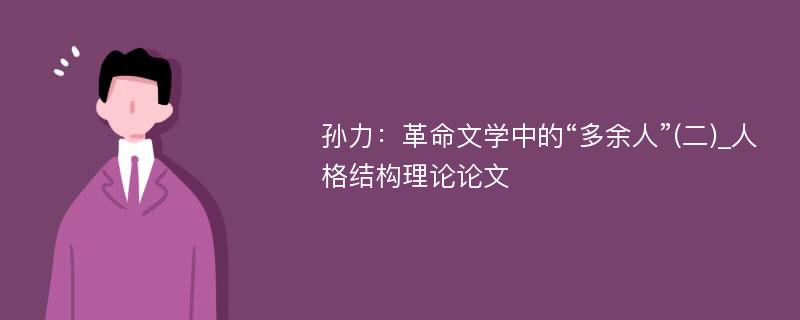
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多余论文,孙犁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道德二元:“多余”的根源
孙犁大半生身在革命文化中,可他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主要受到的却不是主流革命文化的影响。孙犁人格心理与价值系统的形成,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鲁迅及五四启蒙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一是传统的儒家文化精神。人道主义和儒家文化这两种在新文化运动中被作为对立关系的文化精神,以一种特殊的形态相互整合、共同建构了孙犁的人格与价值系统,这使孙犁具有一种现代个性意识与传统儒者中庸气质相混合的精神特征,也使孙犁人格心理长期处于相互矛盾的紧张与焦虑之中。
儒家文化精神构成了孙犁道德至上、谦以自牧、人格完善以及伏膺权威正统的人格心理,而人道主义则构成他以人为本、尊崇个性的价值尺度。儒家追求道德完善的人格取向与人文主义的泛爱生命、个性独立价值观这两种因素构成的精神范式,应当说在现代文化史上具有某种代表性,它以一种现代性与传统兼容(具体来说是现代的人文思想与原始儒家的“仁”相互兼容)的形态,通常存在于一些追求道德自我完善而又不以入世为目标、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有独立人格却又显得温和的知识分子身上。孙犁的不幸在于:他所默认的权威文化,即以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为方式的当代革命文化,是一种既不符合儒家道德之“仁”、又相悖于人道主义之博爱及个性自由的革命道德,而孙犁忠于“正统”的儒家人格又使他几乎是无条件地服从于革命道德。这样,人道与革命的调和与它们事实上的难以调和,就成为孙犁一生精神焦虑的根源,也使孙犁精神形式显出一种独特——一种既“旧”又“新”、正统与偏至共存、保守与激进兼有的充满矛盾的独特存在。
他始终不肯因为政治上的“正确”而放弃对人的理解和怜悯。而他缺乏反叛、顺任自然、服膺正统的性格、心理,又使他在明确感受到他道德系统中两种观念的冲突后,不能毅然地作出选择,而努力以自我检束的方式达到二者的调和。在抗战时期,统一战线政策使孙犁的调和成为可能,但调和带给作家的毕竟是痛苦。孙犁在晚年的文章中才放言倾诉自己的忧郁和苦闷,说这些忧郁和苦闷几乎在他进入革命队伍开始创作时就已滋生(注:《耕堂杂录·接受遗产问题》,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及《老荒集·爱书续谈》等。),尽管那时他写作的基调是“欢乐”。一般人将单纯或单薄当成孙犁艺术的某种本质,却难以体察孙犁既不单薄也不单纯的内心。“我的一生,残破印象太多了,残破意识太浓了。大的如‘九一八’以后的国土山河的残破,战争年代的城市村庄的残破。‘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残破,道德残破。个人的故园残破,亲情残破,爱情残破…”(注:《曲终集·残瓷人》。)这么深重的悲剧意识,当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曾经有批评家认为,如果现实的政治氛围稍微宽松的话,孙犁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肖洛霍夫(注:胡河清:《重论孙犁》,《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这个判断应当说是对孙犁的深刻理解。孙犁五十年代初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其情绪的沉静、叙事的生动和结构上的诗史脉动,都显示出一种大家气派,预示了孙犁创作上的巨大潜能。这部小说本应是孙犁创作步入成熟的开端,不幸却成了封顶之作。孙犁前期的创作,实际是在人道与革命之间踩高跷,是小心翼翼的打擦边球。建国以后,政治的统一使淡化政治的言说越来越不可能,孙犁的“中间地带”也就越来越狭窄。五十年代初批胡适、批胡风,主流政治从文化的外部和内部否定了五四的人文精神,孙犁的侥幸心理也失去依托,多年的精神忧虑加上对政治风暴的惊惧(注:孙犁在《老荒集·王婉》中说,1953年他的一个同事被打成胡风分子,孙犁当即坦言不满,不久该同事被公安机关逮捕,孙犁“受了很大刺激,不久,就得了神经衰弱症”。),他终于精神崩溃,大病几近死亡。对于他1956年的这场突发的大病,研究者往往语焉不详,而孙犁后来屡次提及此事,语调十分严重:“我当时处境,已近于身心交瘁,有些病态”(注:《孙犁书话·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进城初期,已近于身心交瘁状态”(注:《孙犁书话·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这个看来蹊跷的持续十年的大病,连他的妻子都不能理解,倒是他的母亲一语中的:“你别看他不说不道,这些年,什么事情不打他心里过?”(注:《孙犁书话·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可见孙犁的病实是一种精神危机的总爆发,而这个危机的加剧,是从土地改革开始的。孙犁父亲一生勤谨,从学徒到掌柜,几十年辛苦操劳挣下一个小康家业,土改被分“浮财”;当时孙犁有不同意见,便“陷重围”,并被“搬石头”(隔离)(注:孙犁《陋巷集·〈善闇室纪年〉摘抄》,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几乎同时,孙犁被《冀中导报》作为“客里空”典型批判,消息传到家乡,他的家庭遭到当地更厉害的批斗;也就在这种恐惧中,孙犁的妻子为避祸将他的许多书籍付之一炬。土改孙犁下乡时,曾见农民用骡子在田里拖拉地主,说是执行上级关于对地主实行“一打一拉”政策。全国解放孙犁随大军进城以后,其所见所感皆与理想不合;他挚爱着的那些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重大牺牲的人民,在解放以后好像被忘却。现实与他的理想仿佛越来越远,他看见历来被人们珍视的文明、被人们认同的道德,都处于被轻贱的地步。他内向怯懦的性格,使其郁闷得不到疏解,加剧了内心的郁结。建国伊始就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使知识分子心灵严重受挫,如孙犁描述的,每次运动下来,往往哀鸿遍野;在这样的文化专政下,他虽然并未受批判,却也噤若寒蝉。由于孙犁的谨慎性格和一向的“边缘”姿态,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都没有直接冲击到他,而他却在这个时候开始了最初的退隐。当他同时代的作家大都被卷入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时,孙犁却如“优游林下的高人”(注:胡河清:《重论孙犁》,《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先是在小汤山、青岛、西湖等地疗养,然后是大量搜求古书字画,闭门读书。“远离尘世,既不可能,把心沉到渺不可寻的残碑断碣之中,如同徜徉在荒山野寺,求得一时的解脱与安宁”(注:《孙犁书话·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
自四十年代解放区确立了党对文艺的绝对领导以后,主流知识分子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中,大致经历着两种命运:一种以理性坚持真理,最终刚强而折,例如胡风;另一种则在虔诚的理想崇拜中由怀疑自我、而最终泯灭自我,如丁玲。孙犁命运的许多偶然性,都使他在主流文化中成了一个“例外”。一方面他没有积极地介入政治、因而政治相对来说也没有过多地介入他。丁玲等是在一直不被信任的政治压力下为争得信任而逐渐放弃个性主义的,而孙犁虽然受过冲击,可一直是被当作“自己人”优待的,绝对没有直接承受过丁玲那样的严峻的政治压力。这就为他寻求一种既不直接对抗、又不放弃自我的“中间道路”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孙犁人格心理中浓厚的“传统性”,使他在理想和现实发生严重冲突时,在不可解决的精神矛盾中,十分自然地像历来的文人一样,选择了退而独善的道路。
孙犁身上的“传统”性,最明显不过的是他对家庭、人伦、感情的眷顾。他不大容易轻易抛弃既有的感情关系,哪怕这种关系有违“阶级立场”。土改开始后他与“剥削阶级”家庭并不划清界限,还对别人好心的提醒不屑一顾(注:孙犁《陋巷集·〈善闇室纪年〉摘抄》,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他受到批判的《一别十年同口镇》也是因念“朋友交情”而“忘”了对方的阶级成分。他自称有许多“旧观念”,对父母孝、对妻子“忠”。父亲在土改期间去世,他怀着愧疚想为父亲立碑,并以“弦歌不断,卒以成名”的碑文相告慰(注:孙犁《陋巷集·〈善闇室纪年〉摘抄》,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碑当然是没有立成,但孙犁对父母的孝心及尽孝的方式,却不那么革命。孙犁在婚姻和爱情上有过浪漫激情的荡漾,但最终还是“不逾矩”。1945年孙犁由冀中到了延安,当时革命阵营中流行婚姻革命,上自党的高级领导,下至普通干部,都纷纷在投身政治革命的同时,重新择偶。正值青春年华并富于浪漫诗情的孙犁此时也曾萌生爱情,可终于“发乎情”而“止乎礼仪”。孙犁一生有过几次爱情悸动,最终都被掐灭在萌芽状态中,而他为此长久地对结发之妻深怀“惭德”(注:《书衣文录·陈老莲水浒叶子》。),与周围环境相比,孙犁显得“保守”;而事实上,在他优柔的行为中,人道主义思想支持了他在人际关系上的“保守”。儒家的“仁”与人道的爱,在孙犁身上统一成了他对人间感情的珍视。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主流文化几十年来主演着的为表现政治忠诚而“划清界限”的夫妻离异、子女反叛、朋友出卖、情人反目的种种悲喜剧,就会感受到孙犁这种对感情的珍惜,正是我们这个支离破碎的当代文化所最缺乏的人本精神。
孙犁人格中有一个核心的东西,那就是道德中心主义,这是他身上儒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道德上的“唯善”追求使孙犁的人格与人生姿态有一种独立性与坚定性,这在普遍的知识分子主体人格伴随政治气候沉浮的当代主流文化中显得十分突出。而由于他道德观念上的二元性,孙犁的独立性和坚定性,又常常伴随着对十分尖锐的矛盾的解决与无法解决的焦虑。他一生追求的是艺术与现实、作家的内在与外在生活的统一,即修身养性、人格完善与写作为文的统一,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理想的生存状态与人格模式。他早期作品对人性之善的崇敬,他文革期间反求诸己的道德深思(注:《书衣文录·陈老莲水浒叶子》。),都体现出这个特征。“文章写法,其道则一。心地光明,便有灵感,入情入理,就成艺术”(注:《秀露集·文学和生活道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这种典型的“道德文章”论,最体现他身上的“传统”色彩;而他对文学艺术的理解与与阐释,也无处不体现道德中心的意识。譬如,他认为“风格是一种道德品质”(注:《孙犁文集(四)·论风格》,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艺术的高潮应该是情节的发展最后达到的道德力量”(注:《孙犁文集(四)·论情节》。)。他自称其文学追求真、善、美,而“真、善、美”的概念在孙犁的话语系统中,其意义实际就是善。他的“真”,是排斥了“伪”的“真之善”,他概念中的“美”,也是排斥了“丑”的“美之善”。他自称现实主义,一生崇尚的也是现实主义;但他的“现实主义”,已经不是美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即不是创作方法,而仅仅是一种关怀现实的道德姿态,也就是作家对待现实的伦理态度。我们很容易看到,孙犁的“现实主义”所表现的,常常是那些趋于理想的美的、善的现实,而美学概念上的“现实主义”的特征,恰好是热衷于表现那些非理想的、充满缺陷的现实。因此人们从不怀疑丁玲、赵树理是现实主义,却常常将孙犁划归到浪漫主义一派。由于是一种道德论的思维方式,所以孙犁有时也将“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视为一种因果范畴:“只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才能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而一旦成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就成为伟大的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形态,对于人类固有的天良之心,是无往而不通的。 ”(注:《秀露集·文学和生活道路》,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当然,最典型地体现孙犁传统人格的,还是他对主流文化的“正统”态度。
孙犁无论是价值观念还是个性气质,都是不属于现实中的这个革命文化的,然而他却至少在理性上将主流革命文化视为“道统”。我们从孙犁文革中与文革后的随笔杂记中很容易辨认出他那体认正统的传统儒者心理。“三四跳梁,觊觎神器,国家板荡,群效狂愚。”(注:孙犁:《澹定集·幻华室藏书记序》。)孙犁对文革灾难的归因,在道理上符合主流文化的“林、江反党集团说”,而在语言上,则体现出儒家的正统忠诚。文革结束、新时期之初,当他感到“盛世”又现而再度“入世”时,他那正统的道德义务感使他居然不能接受丛维熙的“伤痕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的悲剧结局(注:《秀露集·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的通信》。)。正是这种儒文化心态,使孙犁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心灵磨难而终于“红尘意远”之后,呈现出的状态既不是顿悟,也不是反叛,而是中国传统文人千古不变的退隐、独善的老路,只不过,孙犁不是隐于山林皋壤或故里园田(没有这种条件了),而是隐于书斋,隐于黄卷青灯、残碑断碣的幽古世界中。他文革后期以来的相当部分随笔杂著,读书论道、谈古说今,常表现出万事参透、平淡旷达的超然之状,看似道的虚静,实际还是儒的退守——“忽闻精神文明决议,正在播出,心情激动。过去从未如此关心政治,晚年多虑,心情复杂,非一言可尽,概然良久”(注:孙犁:《无为集·书衣文录》。),“近日友人送前后出师表字帖一本,翻到:‘亲贤人,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亲小人,远贤人,此后汉之所以颓败’一节,掩卷唏嘘,儿至流涕”(注:《孙犁书话·我的集部书》,北京出版社1996年。),这将孙犁传统的儒家人格活脱脱展现出来。所以孙犁于无奈中到底找到了医治心灵创伤的妙法——“中国人的行为和心理,也只有借助中国的书来解释和解决。”(注:《孙犁书话·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
孙犁的儒家人格心理的形成,相当程度上来自家庭的教养。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儒雅、谦逊、严于律己的小商人,当时他在县城经商,每从城里回家,路过村庄必下车步行,言行颇有古风。孙犁从父亲那儿承传了“儒雅”、“里仁”一类儒者风范;而孙犁母亲对儿子的启蒙教导“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则将一种刚毅与驯顺、骨气与奴性兼具的合于儒家理想道德规范的性格与原则传给了孙犁。孙犁“一直记着这两句话”,对于自己与主流文化的牴牾以及自己在这个文化中经受的心灵痛苦,他的感受是一种在下的委屈:“自己一生,就是目前,也不能说没有冤苦,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告状、打官司。”(注:《陋巷集·芸斋琐谈·诗外功夫》。)如果说在早期,孙犁人格心理中“儒”的因素还处于潜在的心理状态,那么文革大劫则使这种潜在心理转化成理性的复苏,他文革后期用文言陆续写下的《书衣文录》就记载了其“伤心悟道”而回归传统的心路历程。回归传统的结果,是对中国历史循环式演进有了睿智的洞见的同时,对人生产生无限悲凉的宿命感。孙犁晚年的随笔杂论,一方面对现实痼弊往往一针见血,显出几分狷介,另一方面又因“忠顺”正统而心理矛盾不得解决,最终只好舐伤自怜,追怀永逝的故情、故旧与故园,陷入不能自拔的感伤中。
“从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新理论转到旧理论;从文学转到历史”(注:《孙犁书话·我的读书生活》。),从理想抒情到历史言说再到不言说,孙犁用远离当下、退隐静默的方式保全了他独立的人格与个性。在当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人格沦落的悲剧人生形式中,这似乎是一种“正剧”式的结尾;而在孙犁个人的人生理式上,它又仿佛是悲剧性的结局。因为孙犁一生追求理想,最终却只能在现实中祭奠理想。他终其一生,都没有体验到曾痴心追求的圆满——文化的圆满、道德的圆满、言说的圆满、家园的圆满、爱情的圆满……自然,十足的圆满是没有的。然而对于孙犁这样一个善良而谨慎、刚正而自律的诗人,生命中似乎本该是少一些“残破”的。
1997年元月——1998后6月于无为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