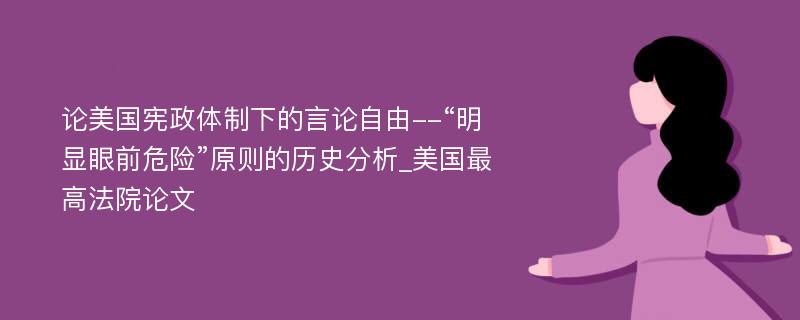
谈美国宪政下的言论自由——“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的历史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政论文,言论自由论文,美国论文,危险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向来以自由的社会自居。然而,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现实中,美国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权利。本文试图通过对盛行一时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原则的探析,揭示出言论自由与美国宪政体制的关系,并提升到自由的普遍性层面作一般性思考。
一、原则的创始
“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肇始于1919年的申克诉合众国(Schenck V.U.S.)一案。申克是社会党总书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散发抨击美国征兵违宪的传单并煽动应召男子抵制征召以维护权利,被联邦区法院判决违反1917年的侦察法(Espionage Act of 1917,又称反间谍法)。侦察法是美国国会继1798年的危害治安法(The Sedition Act of 1798)以后制定的第2个管制言论的法律,经1918年的修正,规定了12项对言论的管制情况,其中第2项和第3项涉及到征召兵员和煽动反叛的言论管制。[①a]申克认为侦察法违背了第1条宪法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认定申克构成犯罪。首席法官霍姆斯(Holmes)在判决意见中写道:“我们承认,被告传单所说的一切,若在平时的许多场合,都属宪法所保障的权利。但一切行为的性质应由行为时的环境来确定。对言论自由作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容忍一个人在戏院中妄呼起火,引起恐慌。禁令所禁止的一切可造成暴力后果的言论也不受保护。一切有关言论的案件,其问题在于所发表的言论在当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性质下,是否能造成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产生实际祸害。如果有这种危险,国会就有权阻止。这是一个是否迫近和程度的问题。当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下,许多和平时可容许的言论,因其妨碍战事而变得不能容许了,法院也不认为它们是宪法所保障的权利。”[②a]
“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开创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设定言论自由之司法标准的先河。在此之前,国会曾制定了一个管制言论自由的法律——1798年的危害治安法,也引起了一些讼案,但都没有上诉到最高法院,也就不可能产生对它的合宪性进行司法审查的问题。但公众舆论对该法的抨击却自始就非常激烈,肯塔基州甚至还通过了一个谴责该法的决议。1798年的危害治安法至1801年3月3日效期届满。自此以后一个多世纪国会未制定管制言论自由的立法。1917年侦察法的出台始为联邦最高法院设定言论自由的司法标准提供了契机。
从申克诉合众国案对“明显而即刻的危险”表述的上下文分析,联邦最高法院对言论自由的立场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一是第1条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权利,国会得制定关于言论自由的法律;二是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可作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之分,而不是不分背景、场合、时间概无差别;三是对言论自由以保护为原则,以限制为例外;四是确定一项绝对的标准是困难的,在涉及到言论自由的讼案时,言论是否要承担责任得视发表言论的性质和当时的环境而定。
“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不独难于成为万验的标准,就是作为一项原则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和培育时期。大致说来,从提出至1940年属于培育时期,1940年以后则日渐风行。
二、原则的培育和发展
“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的培育和普遍适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霍姆斯和布兰代斯(Brandeis)。在培育时期,联邦最高法院对言论自由的讼案适用多个原则。弗洛维克诉合众国(Frohwerk V.U.S 1919)案适用了“可能的影响”(probable effect)原则,德伯斯诉合众国(Debs V.U.S)案适用了“自然倾向”(natural tendency)原则,在1920年的舍弗诉合众国(Schaefer V.U.S)案和皮期诉合众国(Pierce schaefer V.U.S)案适用的是“恶劣倾向”(bad tendency)原则。而霍姆斯和布兰代斯从阿布拉姆斯诉合众国(Adrams V.U.S)案起,坚持不懈地强调以“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来衡断言论讼案。在舍弗诉合众国案中,霍姆斯和布兰代斯一致认为:“有罪的判决,必须能证明被告的言论,确有导致实际祸害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仅仅认为它是有‘恶劣倾向’是不够的”。[①b]在1925年的吉特洛诉纽约州(Gitlow V.New York)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意见中主张对言论自由得作事前的限制,所谓“潜隐的革命火种一经点燃,可以酿成有席卷之势和毁灭性的火灾。因是之故,政府基于保护公共和平和安全的必要考量之判断,不待其燎原而及时扑灭火花,就不能说是专断或无理的行动。”[②b]与判决意见相左,霍姆斯认为:“申克诉合众国案全体法官一致认可的标准适用该案。显而易见,大家公认与被告持相同的观点的人是少数,没有蓄意以暴力推翻政府的明显的危险。”[③b]1927年的惠特尼诉加利弗尼亚(Whitney V.California)案中,布兰代斯又不失时机地阐明了“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虽然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是基本的权利,但它们在性质上不是绝对的。政府为保护政治、经济或道德免遭破坏成重大损失,对于将造成或意图造成某种实际祸害的明显而迫切的危险得根据宪法予以限制”。[④b]
正是由于霍姆斯和布兰代斯坚持不懈的努力,“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才不致于因长期未得到适用而昙花一现。到了本世纪40年代,“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终于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普遍认同,成为适用煽动性言论的基本原则。1937年的亨敦诉洛利(herndon V.Lowry.)案可以说是联邦最高法院重新适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的伊始。自此以后至1950年,可以说是适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的黄金时期。荆知仁把该项原则在这段时期适用的范围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罢工纠察哨案,二是传教自由案,三是强迫向国旗敬礼案,四是蔑视法庭案,五是公共集会演说案。[⑤b]到了50年代,“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始呈衰颓,但也不是销声匿迹。大体的情势是在不同程度的修改下间或适用,例如在1969年的布兰登堡诉俄亥俄州(Brandenbwrg V.Ohio.)案中,法官布兰克(Black)和道格拉斯(Douglas)一致认为不能以“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来阐释宪法第1条修正案。1978年首席法官史蒂文斯强烈主张对一切试图控制言论自由的立法,根据严格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进行审查。
三、原则的历史分析
以“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为视角透视美国宪政容含的自由的量度,不可避免地要把对该项原则的分析投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提到人文理念的层面上来。本文选择该原则成就的宪制背景、司法解释的权威性和原则变迁的历史内涵进行分析。
前面已指出“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是联邦最高法院确定言论自由的界线的首次尝试,距美国宪法的制定已逾一个多世纪。为什么在这么漫长的时期联邦最高法院在这方面未能有所作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理解美国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款以及这些条款所蕴含的历史背景。
美国宪法正文并没有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已公认是制宪者故意的安排而非一时的疏忽。汉密尔顿直言不讳地承认:“人权法案,从目前争论的意义与范围而论,列入拟议中的宪法,不仅无此必要,甚至可以造成危害。人权法案条款中包括若干未曾授予政府的权力限制;而正因如此,将为政府要求多于已授权力的借口。”[①c]其实,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无法与保存奴隶制度维持政治思想的逻辑性。而奴隶制度的保存对于宪法的批准又至关重要,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已公开声称如果宪法废止奴隶买卖就退出合众国。饶有兴味的是,制定者为求得宪法的批准而处心积虑所作的安排成了反对宪法者抨击的目标。杰佛逊在1788年7月给麦迪逊的一封信中对此明确地表示不满,他把宪法比成一幅需要作修描的精美油画,而列入人权法案就是不可省略的一笔。批评的力量产生的现实效果是“如果不是答应新国会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通过一项权利法案,宪法也许就得不到批准。”[②c]于是乎就有了1791年10条宪法修正案的出台,称为“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权利法案”第1条就规定了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即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的法律。美国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这种规定以及隐藏在这种规定的历史背景决定了联邦最高法院对言论问题的介入要以国会制定了管制言论自由的立法为前提,而国会又基于在这方面的立法权范围的限制和鲜遇就管制言论进行立法的必要情势(主要是战争),在美国建国一个多世纪也只于1798年出于与法国的战争有如箭在弦之势制定了短命的危害治安法。故联邦最高法院一直都对言论问题无从入手,直至国会1917年制定了侦察法,才寻觅到机会。
美国的“权利法案”关于言论自由的表述显而易见是非常简要的。惟其简要,适用时就需要阐释,同时也能张开自如地吞放社会千变万化的量度。毫无疑问,联邦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的权威性是美国宪法能以强劲的历史穿渗力浸润美国生活的一个泉眼。这也可以说是美国以自由社会自居的一份本钱。那么,为什么会确立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解释的权威性呢?这对分析“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有什么意义?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希尔斯曼认为联邦最高法院解释宪法的权威性权力是“窃取”的,但把这种“窃取”完全归结为联邦最高法院窃贼般的狡滑奸诈,未免过于夸张。[①d]美国宪法确实没有授予联邦最高法院解释宪法的权力,遑论这种解释的权威性。不过,从美国宪法所构建的分权制衡政制看,联邦最高法院的“窃取”也正合制宪者的本意。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的一段话道出了个中真味:“宪法除其他原因外,有意使法院成为人民与立法机关的中间机构,以监督后者局限于其权力范围内行事。解释法律乃是法院的正当与特有的职责。而宪法事实上是,亦应被法官看作根本大法。所以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如果两者间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自以效力及作用较大之法为准”。[②d]
从英美法系的固有传统看,法官解释法律甚至法官造法可谓源远流长。联邦最高法院的“窃取”也系祖传,于历史的传统和当时的体制并无太多的龃龉,也就易于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所认同。另外一层意思是,美国不奉行议会至上,认为多数的专制一如少数的暴政皆属应避免的灾祸,由法院执掌解释宪法之权威性权力正是避免代议机关蜕化为多数专制的掣肘。这一层较诸英国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显然又是新开的一枝。
应该说明的是,联邦最高法院解释宪法的权威性地位既不等同于联邦最高法院享有至高的地位,也不意味着联邦最高法院解释宪法就绝对不受其他机关和社会力量的影响。联邦最高法院曾明确指出:“任何一条法律的通过,都要靠立法机关的智慧、正直和爱国精神,除非这条法律违反宪法昭然若揭,使人没有合理怀疑的余地,否则,承认这条法律的有效性,无非就是对立法机关的这些品质表示应有的尊重罢了。”[③d]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同样要受到政治力量、利益集团和公众舆论的影响,只不过影响的方式和程度与国会和总统不同。同时它也倾向于对与作出决定利害攸关的各种力量作综合考量,这又正是它能保持其宪法解释的权威性的秘密。如其一味恣意孤行或生搬硬套宪法条款或死守抽象的政治法律原则,而不放眼资产阶级的现实利益和保护这些利益的社会秩序,它将无以自保——资产阶级是不会供养自己无法驾驭的机构的。
至于联邦最高法院宪法解释的权威性对“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三方面。首先,它决定了原则的地位,赋予了原则的宪法性质。更确切地说,在它的适用期间它就构成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关于言论自由与煽动叛乱的界线之宪法原则。正由于原则被赋予了宪法性,它才能“不仅成为证据的标准,也成为判断法律有效性的检验方法,即便立法机关已经断定有关言论是属于危险性的。”[④d]其次,联邦最高法院宪法解释的权威性决定了该项原则应具有一定的弹性以适应情势的变迁。权威性要求一定的连续性和相对的一致性为外部支撑要件,如果解释出现经常性反复和前后冲突是说不上权威性的。而过于详尽的硬性原则也往往就缺少回旋的余地。故霍姆斯慎重地使用了“明显的”和“即刻的”这种意义含混的词,以便面临新问题时又可在对词的含义的理解上做文章。第三,联邦最高法院宪法解释的权威性影响了“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适用的范围和方式。由于1925年的吉特洛诉纽约州案的判决把言论自由纳入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保护范围内,联邦最高法院对言论问题的裁判就由对国会立法的合宪性审查扩大到包括州的议会立法,相应地“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的适用范围也就覆盖了全国上下的言论自由与煽动性问题之诉案。不仅法院得根据该项原则进行裁决,当事人也可根据该项原则主张自己的权利。就原则适用的方式而论,必须以发生了言论诉案为前提被动地适用,而不主动就未引起争诉的立法作出判断。
1925年吉特洛诉纽约州案是一个转捩点,联邦最高法院由19世纪对言论问题的垂拱而治转而变为纷乱忙碌了。言论自由的历史内涵因而也能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历程中有所折射,具体到“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就是该项原则的变化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美国历史的变迁。1919年的申克诉合众国案对“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的内涵的界定主要是把责任与言论的性质和环境联系起来,而未对何谓“明显的”、“即刻的”作解释,这项工作由布兰代斯在1927年的惠特尼诉加利弗尼亚一案中完成了。布兰代斯是这样理解的:“除非言论所能引起的明白的祸患是如此紧迫以致来不及充分讨论就会发生,否则言论所导致的危险就不应是明显而即刻的。倘若还有时间通过讨论揭穿谎言和谬误,得以教育的方式避免祸患,那么补救的办法就是更多的言论,而非强制沉默。”[①e]顺便说明一点,国内学者对该项原则流行翻译为“明显而现实的危险”,从布兰代斯这段话分析,“present”理解为时间性的限定“即刻的”应更为贴切。另外,布兰代斯还对该项原则补充了一点,认为该项原则与紧急情况(emergency)联系起来适用才是合理的。到了50年代,该项原则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在1951年的丹尼斯诉合众国(Dennis V.United.states)一案中,首席法官文森明确指出适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但对该原则又作了新的解释:一是言论的责任并不绝对要求言论造成的祸害是现实的,还可以是潜在的;二是排除了言论与言论所能造成的祸害的时间考虑,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言论责任的“即刻的”限制;三是不考虑言论的环境,只要言论是法律所禁止的就予以惩罚,显然纯粹以言论的性质来论定言论的责任。
促使“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内涵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直接也最重要的因素主要是两个:战争和共产主义运动。本世纪以来,美国向世界各地到处伸手,频频参战。为争取战争胜利的立法也就层出不穷,当然少不了对言论的管制。1917年的侦察法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1917年4月6日美国国会对德宣战,6月15日就制定该法,遂有“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面世。根据战时立法确立的原则到了和平时期适用的角度由限制让位于保护,故布兰代斯在惠特尼诉加利弗尼亚一案中采取了较为大度的立场阐扬该项原则。这表明在不触及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美国统治者尚颇有几分沽自由之名的兴趣。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勃兴,到二战后大有席卷全球之势,这几分兴趣便烟消云散了。共产主义学说坦然宣称要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确实“有理由”感到恐惧。如果说美国的统治者在共产主义运动之初(美国1919年成立共产党)还能粉饰一下自由民主的门面,那么到了本世纪40年代以后,外表的粉饰就渐渐被内心的恐惧撕破了,1940年制定史密斯法(Smith Act-Alien Registration,又称外侨登记法),1947年制定塔夫托—哈特莱法(Taft-hartley Act,又称劳工管理关系法——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s Act),1950年制定国内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亦称颠覆活动管制法——Subversive Activities Control Act),1954年制定了共产党管制法(communist Control Act),其间又有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位总统迭次推行的“忠诚计划”(Loyalty Program),凡此种种无一不针对共产主义运动而作。1951年,丹尼斯诉合众国一案对“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的修补正是二战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互相敌对的反映,当然也是联邦最高法院务统治者利益之实的表现。
四、思考与启示
对“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的批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原则过于简单,而适用又过于宽泛,不便于操作;二是何谓“明显的”、“即刻的”难于界说,留给法官自由阐发的余地太大,难免有违宪法第1条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的目的;三是“没有对至关重要的政府利益提供充分的保护”。[①f]也许这些批评都有一定的根由,不过正如比尔德所指出的:“在表达对有秩序的进步确实有害的见解与表达即便属于极端但是还在宪法保证的自由范围之内的见解之间划一条准确的界线,是很不容易的。”[②f]无论如何,该项原则至少为考察美国的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视角,而该原则作为司法上的标准,对它的解读应是能真切地把握隐藏于其后的宪政文化的精神的。《牛津法律大辞典》在“公民权或公民自由权”这个条目中的一段话甚是公允:“公民在特定的政府和法律制度下享有什么公民权或自由权问题,部分取决于宪法、法律和判例赋予了哪些公民权或自由权,但也取决于,并且经常更重要地是取决于这些权利或自由在实际中怎样被解释,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被获得和实行。”[③f]
“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是美国的宪政文化培育出来的果实,是甜是苦只能由美国人去品尝。但是,该项原则解答的是人类生活普遍的、永恒的主题,故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所蕴含的启示应是全人类都可共享的财富。
“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给人什么启示呢?这就是能打开自身困惑切口的东西。以前面对该原则的分析看,最使人惊叹的莫过于美国社会自由力量的深厚根底了。它深植于美国人对自由的理解和信仰,这种理解和信仰就是“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的自觉自醒。故能为宪法未列入“权利法案”而主动鸣不平,对国会的法律和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甚至进行抨击,根据个人对宪法和法律的理解而行动,但又勇于承担责任,足见美国人洋溢着倾注国家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情怀,这种情怀不仅是不断地对美国政制注入新鲜血液的源泉,也是使社会深层矛盾得以通过浅层的公开争议和零散的冲突而达到一定程度的消弥。可见人民自由情怀的培育和舒展实为自由社会的奥秘所在。我国“民不可虑始”的传统观念与之相比也就不是程度到范围上的差别问题,而是价值取向的对立了。
丰盈的自由情怀陶铸了自由的制度,两者的交互作用融会出自由的生活。无论“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的本质如何、适用和操作上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和不足,它毕竟表明了言论问题可诉诸司法公断,应该说这种制度是与法治吻合的。对言论问题的司法裁决,不是对言论的真理性有时还包括言论的真实性作出决断,而是在维护发表言论的权利与社会秩序之间作利弊权衡。只有言论——不管是谬见还是谎言能表达出来,权衡才有前提,因此对言论自由事前限制的一般应受到排除。
联邦最高法院在适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时探求的是崇尚自由的理想与务实的步骤相结合的路径。既不囿于抽象的原理原则,也不盲目附合现存法律对言论的管制。联邦最高法院仿佛是美国这只船的压舱物,使得美国社会的行进于动荡中还有稳健。
注释:
[①a] 参见荆知仁:《美国宪法与宪政》,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62页。
[②a] Geoffery R.Stone and others:Constitutional Law,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6,P.944.
[①b] 参见荆知仁:《美国宪法与宪政》,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68页。
[②b] Geoffery R.Stone and others:Constitutional Law,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6,P.957.
[③b] Ronald P.Rotunda and ofhers:Modern Constitutional Law,WestPublishing,Co.,1989,P.728.
[④b] Geoffery R.Stone and others:Constitutional Law,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6,P.962.
[⑤b] 荆知仁:《美国宪法与宪政》,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72~187页。
[①c]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29页。
[②c] 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曹大鹏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31页。
[①d] 参见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曹大鹏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9页。
[②d]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92~393页。
[③d] 转引自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3~64页。
[④d] 卡乐威因、帕尔德森:《美国宪法释义》,徐卫东、吴新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①e] Geoffery R.Stone and others:Constitutional Law,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6,P.963.
[①f] [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页。
[②f] 转引自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7页。
[③f] 《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页。
标签:美国最高法院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法律论文; 美国史论文; 宪法的基本原则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即刻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宪法监督论文; 美国法院论文; 美国宪法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