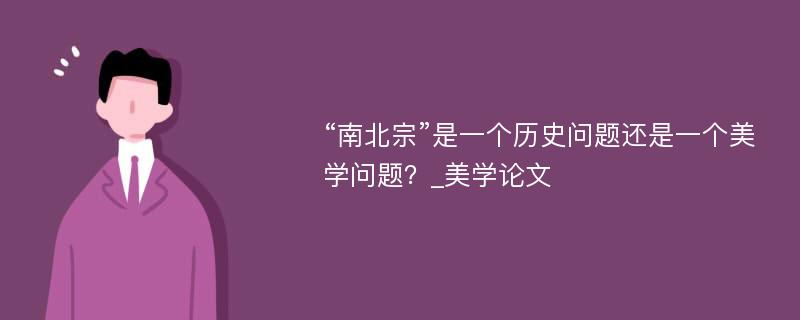
“南北宗”是一个史学问题,还是一个美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是一个论文,史学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明董其昌等人提出的“南北宗”论在民国时期是重要的画学研究课题之一。20世纪初思想界受到致用观念的影响对之进行政治学术批判,继而史学界在整理国故和“疑古”思潮下从文献考辨角度对之进行史学辨伪,否定了它的客观性。之后随着社会语境的变迁,这个画学问题被不断赋予新的学术含义。如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意识形态上对学术研究的参与,通过“南北宗”研究达到对古代社会体制和地主阶级的批判,使之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学问题;80年代,“释古”思潮出于对民国学术“疑古”风气过重的反思和对古代文化发展过程的重建心理,促使“南北宗”研究向美学阐释转向,因而“南北宗”自身包蕴的美学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提倡,导致其研究性质在史学问题与美学问题上纠缠不清。实质上,“南北宗”对晚明之前山水画史的构建所体现出来的史实性与美学价值双重特征,是任何一个具备风格实践意义的画学命题得以产生历史影响的普遍前提,也是其多重学术研究性质存在的潜在内因。而对其学术性质的阶段性选择,却与外在的时代观念、研究方法及重要学术思潮息息相关。“南北宗”研究后期之所以会出现对美学和风格学价值的大力提倡,主要源自对山水画“信史”重建困境的回应。毕竟经过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学界对山水画史发展脉络的了解和把握,无论从文献记载、作品例证还是考古发现上,都显示出在真“破”与实“立”之间仍然存在不小的障碍。所以,笔者认为厘清“南北宗”学术研究性质几经变化的潜在原因,不仅有助于对这条画论双重结构的认知,同时亦有学术史和文化学意义。
晚明董其昌等人提出“南北宗”之说①: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幹、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躁、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一作“色”),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②董其昌提出的另一条与之辉映的画论即“文人画”之说: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一作“易”)学也。③这两条画论所区分的“南宗”与“北宗”、“文人”与“院体”、“着色”与“渲淡”之别,在晚明至民初三百余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大部分画家作为古代山水画史两种风格并存发展的事实来接受。即便有些画家在创作上并不遵从或认同它所列出的传承脉络,但对它基本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态度。那么,这个原本与绘画实践相伴生的宗派性画学理论,为何在民国初年成为史学辨伪研究的批判对象,而20世纪末又因对其风格价值的推崇,受到美学阐释理论的关注,这是值得从学术史角度认真反思的一个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学术思潮对研究性质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画学命题本身蕴含着多义性和复杂性。笔者对“南北宗”学术研究性质变化的关注,最初导源于阮璞的观点,他在《对董其昌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之再认识》一文中申明:“不应把‘画分南北宗’说仅仅看成是个史学问题,即不应该仅仅从历史事实上去看是否真的存在过两个并行发展的、代代承传不绝的画派世系,而应把‘画分南北宗’说主要看成是个美学问题,即主要应从绘画美学的角度去看是否可能同时并存着可以相对划分的两种不同画风、不同画法、不同审美追求和不同的作画态度”;“我们有理由认为:董其昌倡‘画分南北宗’说,与其说它的实质在于从绘画史上捏造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两个代代承传的绘画宗派分道扬镳、一盛一衰的历史事迹,倒不如说它的实质在于从绘画美学上阐发实际上是存在的两种各有千秋、相映成趣的由不同画风、画法、审美追求和作画态度所显示出来的美学现象”④。同时期与阮璞类似的观点不在少数,他们共同推动了“南北宗”问题向美学研究转向。其中侗廔《论董其昌的“南北分宗”说》一文更加推崇此说的美学立意:“作为董其昌美学核心的‘南北分宗’说,事实上却是启发和帮助了后人在绘画美学上分清两种不同笔墨效果和不同审美情趣,从理论上分清了文人画和非文人画的不同内涵意蕴。……总的看来,董其昌的‘南北分宗’说和‘文人画’说,不是中国绘画史上一般的微枝末叶的分宗列派,其高明处在于寓精辟而又深邃的美学见解。”⑤在学术渊源上颇有意趣的是,阮、侗二人分别是民国时期“南北宗”史实批判学者滕固和童书业的学生。20世纪末,他们分别通过提倡“南北宗”美学价值而对其师的观点有所辨讹和补充,使“南北宗”的史学研究和美学理解双重学术特征因传承关系而前后呼应。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研究性质前后分化现象,笔者认为可以从外在的学术思潮和“南北宗”内在的构建方式两方面来寻求原因。
首先,民国学术体系以“求因”、“明变”和“述学”为范式,以扩充史料范围(包含传统画学在内)、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推进史学理论学科化为目标。20年代初期,围绕整理国故运动出现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开启了学术研究中的古史辨伪思潮。他们提倡大胆疑古辨伪,决心以科学理性的标准审查以往的文献典籍记载。1923年初,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他推翻伪造的古史体系的系统观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这对民国史学界造成了强烈的刺激。批判和质疑精神使其将学术研究“求是”观念放在首位,“疑古”思潮带动了多个学科的辨伪潮流。经过顾颉刚弟子童书业的引介,将这种研究特征逐渐导向绘画史研究领域,致使一些画学问题进入现代学术辨伪研究视野,“南北宗”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顾颉刚的研究方法对“南北宗”辨伪特别适用,如南宗绘画的真正开端不始于唐,王维的画史地位的变迁具有“层累性”等。最终,通过对唐宋到晚明多部画学文献内容的排比和考辨,证明了“南北宗”所罗列的画人师资体系明显是董其昌等人虚构出来的。“南北宗”文献的确凿性受到批判和质疑,最终多数学者否定了其历史客观性。然而,本质上属于史学研究范畴的辨伪研究结果,却导致了中国古代山水画史脉络的空缺,否定了晚明以来三百余年存在于画学观念上的一段备受推崇的“信史”。即便是持辨伪观的民国学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欲求借助文献追溯、作品例证和考古材料来重新找回真实的山水画史脉络,但囿于多方面资源的缺乏,当时他们的具体做法多以文献的替代方式来弥补“疑古”的破坏性。如滕固、童书业等人,分别在不同时期通过推崇与董其昌同时期的王世贞提出的山水画史“五变说”,来填补“南北宗”辨讹之后的空位。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中记载:“山水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⑥滕固1931年在《关于院体画和文人画之史的考察》一文中认为:“论唐宋以来山水画的发展,我觉得明王世贞的寥寥数语,比较得当。”⑦童书业1936年在《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一文中也肯定王世贞“五变说”是“明代中世人很精到的议论”⑧。我们暂且不论“五变说”对山水画史发展实质上过于依赖朝代更迭,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绘画风格延续的自律性之不足,仅从民国学者肯定它的时间段落而言,“五变说”受推崇与“南北宗”的辨伪批判之间的关联是直接性的,尤其王世贞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重要先导人物,其史学思想中的实学精神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国学者的“疑古”趣味。所以从批判一个学说到肯定另一个学说,在客观条件无法满足学术需求的时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最终仍无法真正实现对山水画史“信史”的学术诉求。因此,实证主义无法解决的史学问题给将来的学术研究留下了转向的机会。
那么80年代之后,学术界又遭遇了怎样的一种学术思潮,进而使“南北宗”研究在阮璞等人的倡导下开始重视其蕴含的美学价值呢?首先,这一思潮缘起于考古学界对民国“疑古”思潮的反思和对上古史的重建愿望。1986年,李学勤发表《对古书的反思》⑨一文,提出“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的想法,欲用新的眼光审查古籍文献。阮璞提出“南北宗”研究性质向美学阐释转向的观点,就是受到了当时“释古”思潮的影响。一方面,“释古”思潮对“疑古”时期一味地在典籍文献系统中寻求反证,进而忽视这些说法产生的深刻现实根源和存在合理价值做法,起到了纠偏的作用。这对于我们理解“南北宗”是针对于绘画创作而产生的画学主张也有所帮助;另一方面,针对考古学界对古史佐证的成功,尤其是以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为基础,殷墟出土文物与上古史文献记载的吻合或言为巧合,无疑促成了部分考古学界学者重新提出“释古”观念,试图加强中国古史可信史的时段范围。但自民国建立考古学以来,无论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以及今天一些学者的研究方式,都没有走出文献证史的范畴。而关于唐宋以后的山水画史研究,毕竟与上古史研究存在一定的区别,也远没有古史研究和考古学界在材料获取上所想象的乐观,反而随着真伪鉴定的推进,前期可信赖的很多作品通过研究都成为了问题作品,尤其是董其昌借助“以想心取之”的鉴定方式构筑的一份古画体系,为当前的鉴定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另外各个时代的伪作、仿作和代笔等现象,都干扰了目前研究对实物作品的取证。因此,虽然山水画史研究中的美学阐释受到古史研究的“释古”思潮影响,但其研究内涵却是对作品风格类型的趣味化阐释,而非实证性的。我们还需要认真审视的一个问题是,当时阮璞等人对“南北宗”的美学阐释,借助的主要手段依然是文献性质的,这在方法论上还是没有突破民国学术体系的拘束。所以“南北宗”的美学阐释研究,也只能是学术史的一个片段而已。
综上所述,30年代“南北宗”的史学研究,是在“疑古”思潮和科学实证主义史学方法指导下,对古代画学文献史实阐述客观性的质疑;80年代中期的美学研究,是在“释古”思潮波及下,对山水画风格、画法及文人趣味累积发展至晚明时期既成事实的理解和阐释。
其次,“南北宗”自身就蕴含着史学与美学双重价值,这是导致其研究性质变化的内在因素。从实证主义历史观出发,“南北宗”对之前山水画史发展历程和画人师资传承体系的排列极为失实;从画学主张和创作角度看,它建立在美学意蕴和风格学之上的归纳与创作导向价值,又有着明确的致用目的。这些都本于立论者根据创作需要对史实的主观采集和褒贬,是命题本身历史性和风格价值论并存的前提。
就一般史学研究而论,对“南北宗”研究性质的界定,似乎不应存在过多分歧,毕竟命题内容与众多历史文献记载和部分作品风格之间的确存在抵牾之处。而从绘画史研究的特殊性出发,“南北宗”在史实考证辨伪之外,又涉及美学风格理解,这是绘画史研究的一个特殊现象。阮璞即已认识到从“南北宗”双重内涵到学术研究的实质,都暗含着两个不同结构:其一,史学考证所关心的真实性、客观性;其二,绘画发展的自律性、美学风格价值。就艺术史的叙述依据而论,大致可分为两种主要形态:以艺术家为线索的人物传记式和以作品意蕴为主体的风格演变式。这两种写作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内在准则,即画家主体趣味和作品美学意蕴的前后关联,是真正能够使艺术之史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性因素。所以,由于艺术史是建立在个体画家作品风格和意蕴“历时性”演变之上,就会不断地使艺术发展的历史性掺杂于美学风格的演变当中。这样一来,我们在区分“南北宗”到底是一个史学问题还是一个美学问题时,就会左顾右盼。笔者认为,由于创作风格和审美取向积累延续的独立性,往往使我们忽视甚至漠视,艺术史的所有构造形态都是建立在实存画家和作品基础之上的历史撰述,导致某些重要的艺术史命题的史实逻辑或史学意义会以现实致用为前提而被主观截取。先就艺术史的陈述者来说,从审美角度完成对个体画家思想和作品风格的描述,再过渡到对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安排,是其述史的主要目的。在艺术史家的讲述当中,如何使自己所关注和重视的艺术风格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审美趣味,尤其在缺乏客观实存艺术作品和文献证据的情况之下,那只有通过建立必要的“叙述学”意识,才能树立这种风格趣味的历史合理性。再从作品角度出发,艺术史的撰述意义在于通过对现存发展过程有意识的梳理,进而使作品进入一种既定风格发展的历史框架,成就其历史性存在而不仅仅是孤立的个体性风格。众多艺术个体凭借着有限的史实依据,被合理或成功地安排进一个人为的风格结构或序列当中,就有可能形成一幅由史实和风格二元结构所构筑的连贯性图景。虽然艺术史实原本是客观存在的,但对风格趣味的领悟和叙述始终没有一个客观给定的标准,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艺术史先前本应存在的客观性史实状态转而人为化或风格化了。最后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艺术史研究的确存在史实考辨与美学风格阐释的不同选择。一方面,艺术史在梳理其自身发展脉络时,必须借助于一般史学的科学实证方法,因此由于实证史学的影响而去追究某种艺术发展历程的客观性;另一方面,由于作品坚持某种风格样式的艺术理论或宗派性特征,强调超越客观历史的审美独立价值,在史实考证辨伪之外,又有着一套顺应风格趣味的选择性发展标准。相对于一般史学来说,艺术史并非完全把对史实的复原作为主要目的,而是较为重视对已有视觉经验和风格趣味的回顾与“分类”,寻求人类审美思维发展历程,探求其内在规律并做出利于当前风格演变与拓展的选择。“南北宗”就是这样一个蕴含史学与美学双重结构的绘画史命题,因此对于它的研究也就因而有了前后不同的学术性质。
对于晚明时期所产生的这一重要画学思想,在20世纪逐步经历了史学辨伪研究和美学阐释研究过程,当下学者在理解其双重含义时也逐渐达成了部分共识。如针对中国古代画史建构模式及晚明论者创建画史言论的心理动机,美国学者高居翰都有所论述,他认为晚明时期的绘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关心过去的传统,所以“无论是高古或近古皆然,对于高古传统敬重的态度,可由当时鉴赏与收藏之风见出;对于近古传统的关注,则可从画家依附地区传统,或是地域流派间的党同伐异现象看出”⑩。对其内在原因他分析说:“到了明代,一些画论家开始采取较为广袤的视野,回顾过去一段绵长的画史。他们的见解阐释往往不过短短的数行,从未发展为长篇大论或写成专书,而且诸如此类的简短记述,总也是别有意图,而非单纯表达有关画史的讯息。画论家在追溯某一画风的缘起及发展的同时,他们对于自己同时代的种种绘画流风,一般也免不了各持立场,择善固执,他们会建议同时代画家应当遵循那些正确的传统,同时,也会议论并希望影响当时收藏家与鉴赏家对高古绘画的评价。可想而知,‘真正客观的艺术史’乃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的观念,因为在重新建构过去的历史时,必然会牵涉到何者较为重要、何者较有价值等判断,此中难免会掺杂个人好恶。尽管如此,客观仍然可以是一种理想,只不过明代的画论几乎无此意图,画论家可能可以据实以述,就事论事,但是,他们却往往借题发挥,为的是发表个人的议论。明代的画论家似乎偏爱派系争论,不愿意将‘史实’和派系争执区分开来,或是撇清个人立场,对所争执的议题展开讨论。这种偏见或争辩不休的艺术史发展模式,决定了晚明以及以后讨论画史的基调。”(11)高居翰的高明之处在于将晚明画学思想产生的美学风格价值影响与史学意义结合起来,相较而言,“‘南北宗’不过是在与对手的角逐中打出的一面旗号,它所虚构的历史线索只具有批评意义,而不具备历史学意义”(12)的论断就显得过于片面了,它没有将“南北宗”自身不可分割的史实论与价值论结合起来,也没有认识到艺术批评学存在的切实基础究竟源于何处。所以“南北宗”之说隐含的批评意图,是董其昌等人立足松江画派对晚明山水画坛现实创作的一种规约,而我们今天对其画理的批评学的价值定位,需要一个较为完整的艺术史发展过程为依托作整体性把握。因为任何一种新的艺术风格主张的独立意义和文化功能,只有将其放置在一个能够联系过去与现在的艺术史经验的情景中加以讨论,才能具备真实的学术价值。通贯地反思绘画史研究,特定时代的风格批评学价值也会在一个特定阶段完成最终的史学定位。画学批评所追求的现实意义和派系风格价值,最后依然要依赖其理论内涵在将来被接受或拒绝的历史事实为判断标准,这也会使命题的史学品质逐渐丰厚起来。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石守谦从文化史学角度关注过古代画史之“变”的各种形式。《文化史范畴中的画史之变》一文着眼于从画史文献著述者(画史主体)的角度把握绘画历史的变化,而不仅仅局限于绘画美学风格的单线演进,毕竟美学风格变化在没有更多可靠作品例证的情况下,后人往往借助于现有的画史文献记载采取判断。他首先以张彦远和王世贞两人对画史变化的描述言论为代表,建立起从唐代甚至更早时期到明清以来一以贯之的论述思想。他认为即使是个人对“变”的推动人物、“变”的数量等具体内容在认识上有所差别,但基本上对画风改变的历史意义的肯定,可以说长期以来都保持着相当一致的共识。但是“在这个基本的共识底下,却可以看到互相之间颇有意味的差异”(13)。石守谦将张彦远和王世贞对画史变化的描述,看做是中国古代较为有代表性的两个范本:“纵使唐、明之间对画史之变的了解,在本质上有如许的差异,但它们却都可以视为对画史之变所进行的某种解释工作。他们虽然不足以称为某种体系,但隐然形成两种模式,前者侧重外部结构的形塑力量,后者则以内部结构自生之力量为画风变革最紧要之动力。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基本上也规范了后代学者对中国画史,尤其是山水画史之变的解释途径。”(14)在论述唐代和明代的绘画作品与文献互证关系上,作者肯定了这两个时代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的重要转捩地位,也体现出张彦远、王世贞和董其昌的论述贡献与现实环境保持着一定的互动关系。正是由于述史者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堆固定的史料,更是一个由经济、文化、思想、宗派及个体等共同构筑的复杂结构。所以,严格区分命题性质归属是一件为难的工作,因为在某些艺术史命题中美学价值与史学内涵具有异质同构的特征。从绘画实践角度所提倡的美学风格,只有借助一定的既有史实才能成就其合理化地位,而它们也只有在不同时期、不同观念及不同方法的研究框架下,才有可能被分离为不同的学术目的。
经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南北宗”研究性质的论断,必须建立在以下几点认识之上:
(一)任何画史结构和画学问题,都以一个最为基础的历史性存在为前提。通过阐明具备影响的历史意义,来促成具有某种共识性的审美心理认知和风格认同。在相当程度上,过去的艺术历程会转化成语言形式的历史叙述行为,但不是任何叙述行为都具备深刻和有深远影响的画学史价值,只有与当前绘画风格的审美趣味追求发生关联,并且延伸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历史意识时,它才会具有立论于美学风格的历史性或史学价值。
(二)艺术史价值判断倾向是一种重要的内在发展力量。从今天我们对艺术史研究和写作的状态分析,几乎所有的艺术史建构都充满着这样的色彩。换言之,艺术史研究在看似追求客观真实的外表之下,也带有很强的风格美学价值判断与批评倾向。我们可以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米芾《画史》、瓦萨利《名人传》、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等经典艺术史文献中窥得一斑。同时,所有美学风格的对立也是一种人为性价值追求的结果,如院体画与文人画风格的对峙、古典主义与巴洛克的不同等等。
(三)美学风格和创作思想在一定阶段会成为艺术史研究和写作的理论基础,使某些原初的美学观念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化并固定为一种历史结构,从而完成从美学风格向艺术史观念的转化,美学观念最终成为历史观念,史学内涵与美学风格难舍难分。董其昌建立的“南北宗”论,一方面通过以禅喻画建立了新的创作和审美方式,另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对绘画历史或师古传统的重视,而是将两者结合为一体,构成画史命题所具备的两个层面。而导致学术研究性质出现分歧的外部原因,主要源自后期方法论投射的问题,同样的材料,研究观念和方法不同,成绩和结论也就不同。本质上,学术范畴的史学研究与特定时代的文化语境是一种明确而具体的动态关系,民国时期的“疑古”思潮促生了“南北宗”的史学研究,而80年代中期的“释古”思潮又推动了其美学研究。
(四)从寻根溯源的宗派意识出发,任何一个艺术史命题只有将其美学主张与历史渊源结合,才能具有合理的历史身份。当以往的绘画史是在人为性选择基础上对当前创作风格具有了批评学价值时,才是真正具备史学价值的前提,而不仅仅是编年的或史料性凭证。尤其古代绘画发展至元明之后,出于对传统的“临鉴”心理所导致的历史述变意识,使明代多位学者和画人纷纷着鞭对之前山水画史脉络和变迁过程进行论述,这在整个画史发展中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15)。这些画论不仅与之前的画史典籍记载构成了史实方面的冲突,同时也成就了自身对山水画史把握的文献性价值。换言之,一旦绘画史实发展中的有利因素与当前美学风格主张达成一致,进而就会消弭历史的确凿性和其有用性之间的距离。所以晚明时期对山水画史述变意识的存在,可以说是中国画史自张彦远以来,在写作模式上的一次集体性突破。这一时期关于山水画史述变行为的背后,显示了这样一个史实:山水画从魏晋发展到晚明,是一个逐渐从思想到技法,从个体趣味到派系风格发展、积淀、衍化和选择的过程。对其历史脉络的关怀,既显示了对山水画史发展的整体性把握,同时在绘画风格的发展趋势上也注重其影响力,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疏通知远”的心理意识。
“南北宗”已经成为一个多元性的画史问题,尤其是在绘画历史脉络—美学风格批评—绘画创作实践—学术研究旨趣之间构筑了一份自足结构。研究者在选择同一艺术史问题时,可以根据不同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构筑起与众不同的史学构想和解释模式。所以,从整个研究史分析,“南北宗”不在于命题本身和其论述的内容客观与否,而在于从其产生之后,它对于山水画史自然逻辑的改变,这使“南北宗”从一个简单的个人性或地区宗派性画史理解,转变成引发一连串画史问题的史学结构。在研究中,我们更应该注意其具有选择性的历史脉络与美学风格之间的相互砥砺,明了“议论”与“实旨”确然一事。“南北宗”史学辨伪研究,本质上体现了实证主义史观对史实脉络和文献材料的阶段性苛求。就文献的史学价值而言,晚明之前的很多画学记录是否能够真正地从“趣味性”品评转化为客观的文献史料,并用来核校“南北宗”所涉的史实内容,极大程度地取决于时代思潮和研究者主观态度的选择。因为过分注重艺术史研究的客观性,本质上是一种实证主义历史观的折射,最终也并不能真正为山水画发展提供一个真实合理的风格逻辑。当然,阮璞等人提出的美学风格理解,对山水画史脉络结构的建设意义究竟又有多大,也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从美学风格入手,强调和突出晚明时期“南北宗”出现和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并不能代替晚明之前山水画史的实际发展逻辑和脉络,也不能以对既成风格的美学趣味理解来代替实证史家视野中的“信史”诉求。借助风格趣味进行的美学阐释,只能让我们进一步理解“南北宗”一说在晚明画坛起到了支撑松江派创作的理论价值,这种应现实需求而产生的宗派性画学理论,不能成为此前历时性山水画风格演变过程的全部证据。由此我们也深刻认识到,古代山水画史经过近百年的研究,仍然没有一些更为确凿的史实材料或合理的风格结构填补批判“南北宗”后所留下的空缺。我们更不能因为“南北宗”虚构了文人画史,就期望将来能够在线性矢量的时间流程中重建或找回历史的真实性,这不仅在文献材料和实物作品方面是不可为的,而且就算还有更多的方法论可供选择,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方法论本身并不足以让我们做到:只要按它的研究程序进行,就可以使许多画史问题得出完全确凿的结论来。所以,合理看待史学辨伪所渴求的真实性和绘画美学风格阐释之间有效的互助关系,不仅是“南北宗”研究,也是整个山水画史研究的重要思考方向。
注释:
①“南北宗”论的作者和提出时间存在争议,作者有董其昌和莫是龙两说;提出时间有1595年、1613年和1621年三说。
②③董其昌:《画旨》,于安澜编《画论丛刊》,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版,第75页,第76页。
④阮璞:《对董其昌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之再认识》,《中国画史论辩》,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195、196页。
⑤侗廔:《论董其昌的“南北分宗”说》,《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⑥王世贞:《艺苑卮言》,俞剑华编《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⑦《滕固艺术文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⑧《童书业绘画史论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98页。
⑨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文化传统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1986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⑩(11)高居翰:《山外山——晚明绘画(1570—1644)》,王嘉骥译,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第6页。
(12)黄专、严善錞:《文人画的趣味、图式与价值》,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13)(14)石守谦:《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第3页。
(15)这些论述除“南北宗”外,大致还有:宋濂“是故顾、陆以来,是一变也”条;杜琼“山水金碧到二李,水墨高古归王维”条;王世贞“山水至大小李一变也”条;何良俊“画山水亦有数家:荆浩、关仝其一家也”条;陈继儒“山水画自唐始变,盖有两宗:李思训,王维是也”条;王肯堂“自六朝以来,一变而为王维、张璪、郑虔”条;詹景凤“山水有二派:一为逸家,一为作家”条;沈颢“禅与画俱有南北宗”条,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