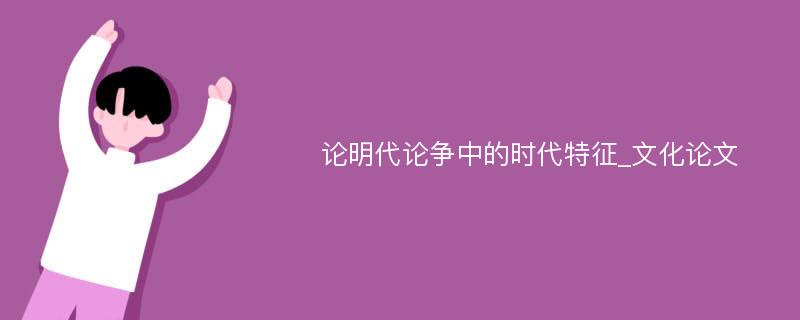
论明代论辨文的时代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时代特征论文,论辨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0)03-0011-10
论辨文作为一种文类,可以包括论、说、辨(辩)、原、解、释、驳(驳议)、考、评、问、对等文体。在古人的文体观念和写作实践中,这些文体无疑各有特征,但它们大都旨在说明某种道理,所以自有相通之处。到了明代,这些文体之间的差异渐趋模糊。如吴讷(1372-1457)认为:“若夫解者,亦以讲释解剥为义,其与说亦无大相远焉。”①徐师曾(1517-1580)指出:说,“傅于经义,而更出己见,纵横抑扬,以详赡为上而已,与论无大异也”;原,“虽非古体,然其溯原于本始,致用于当今,则诚有不可少者。至其曲折抑扬,亦与论、说相为表里,无甚异也”;解,“以辩释疑惑、解剥纷难为主,与论、说、议、辩,盖相通焉”;而“文既有解,又复为释,则释者,解之别名也”②。正因为这些文体原本就有相通的特征,所以姚鼐(1731-1815)《古文辞类纂序目》概称为“论辨类”③。本文即据此统称这些文体为论辨文。
那么,历代论辨文有哪些共同的文体特征呢?刘勰(466?-539?)《文心雕龙·论说》指出:
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④
大要而言,论辨文的内容指向是明辨是非,辩释疑惑,自出己意,申述道理,做到“理明义精”⑤;论辨文的论证方式是仔细观察客观事物,全面概括各种言论,深入思考,融会贯通,做到“审时度势”⑥;论辨文的表达方法是论点鲜明,说理通达,文心细密,逻辑严谨,文辞简要,顺理成章,做到“精微而朗畅”⑦。
除了具有论辨文共同的文体特征以外,明代论辨文与唐、宋、清各代论辨文相比较,还特别表现出三方面的时代特征,即:在内容指向上,强调自创新意,翻新出奇,表达与众不同的见解,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在论证方式上,偏重执一而论,明辨是非,发挥势如破竹的气势,具有深刻的思辨性;在表达方法上,喜好引古证今,“横说竖说,以抑扬详赡为上”⑧,具有强烈的感染性。以下分别加以论述。
主体性:研精一理而师心独见
毋庸置辩,论辨文必须以“理”为本,而文之“理”则本于人之“心”。早在东汉时,王充(27-约97)《论衡·超奇》就指出:“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论以文墨验奇。奇巧发于心,其实一也。”⑨刘勰《文心雕龙》也认为,论辨文的内容指向无非是“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而最高妙的论辨文作家则大都“师心独见,锋颖精密”,为“人伦之英”⑩。明代论辨文作家尤其强调“师心独见”的主体性,明清之际魏禧(1624-1681)认为“作论有三不必”:“前人所已言,众人所易知,摘拾小事无关系处,此三不必作也。”(11)论辨文原本是为己立言,自应强调作家的主体性,发前人所未发,言众人所未言。
从明代论辨文探究道理的内容指向来看,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原本经术,粹然一出于正;一派奇气坌涌,戛然自成一家。这两种内容指向殊途同归地表现出研精一理而师心独见的主体性特征。
宋濂(1310-1381)的论辨文就大多“贯穿四库之书而粹然一本于《六经》”(12)。如《文说赠王生黼》,开篇即提出“文”不是一般文学之“文”,而是“圣贤之道”:
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斯文也,果谁之文也?圣贤之文也。非圣贤之文也,圣贤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
因此,欲求为文,必须“参之于气而致其平,推之为道而验其恒,蓄之为德而俟其成”,这才是培本探源之法。这是因为文者“发乎心也”,心者“主乎身也”,圣贤“道德仁义积,而气因以充;气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13)。全文以“圣贤之文”作为立论根据,一以贯之,颇富说服力。宋濂的《六经论》,本乎理学正宗,论述“《六经》皆心学”的道理,也颇有雄辩之气。文章起首即说:“《六经》皆心学也,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因此,圣人之所以要传《六经》之学,“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则众事无不正”(14)。以“心中之理”作为《六经》的本旨和作文的本源,宋濂的文学观念开启了明人对论辨文主体性的鲜明认识。
由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之学,明代文章家大都精通经术,因此有明一代始终有一派论辨文作家,以“议论纯粹,不愧儒者之言”为尚(15),在坚持“经术”为本的基础上,阐发自身的一己之见。如明中期邵宝(1464-1527)的论辨文,“原本经术,粹然一出于正”(16)。其《对问性者》云:
性犹水也。水,未出山为云,出山而成形,始命曰水。论水者,其于是,斯得水之实矣。前乎是者,是以云论水也;后乎是者,是以涧溪江河海论水也。涧溪江河海独非水乎?杂于泥沙而非水之本也。以云论水则迂,以涧溪江河海论水则陋。由君子观之,宁迂无陋。知此,可以论性矣。(17)
全文虽为谈性之文,却既无嚼蜡之辞,亦无拘执之理,独出己见,言简而意赅。归有光(1506-1571)的论辨文也“原本经术”(18),但他对纲常伦理的理解,则时有越出宋元腐儒之处。如《贞女论》的总论点是:“女未嫁人,而或为其夫死,又有终身不改适者,非礼也。”以下展开两个分论点:第一,“夫女子未有以身许人之道也。未嫁而为其夫死,且不改适者,是以身许人也”,“女未嫁而为其夫死且不改适,是六礼不具,婿不亲迎,无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礼也”;第二,“天下未有生而无偶者,终身不适,是乖阴阳之气,而伤天地之和也”。因此归有光认为:“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适,为其夫死者之无谓也。或曰:‘以励世,可也。’夫先王之礼不足以励世,必是而后可以励世也乎?”(19)归有光秉持先王之常礼,驳斥后儒之苛论,可谓一语破的,百发百中。全文或据理申论,或引经据典,无一费辞,见解鲜明,行文明快。
明后期沈一贯(1531-1615)的论辨文亦以儒学为宗,大抵“辩而大”(20),多圆通达明的见解。如《喙鸣文集》卷7中,《卜论》申发柳宗元《非国语》之论,详引诸家之说,以张文定之说为反论,以陈君举之说为正论,复申以己说:“凡卜者,必大疑而作止者也。吾明知其可,而百姓不与知,故卜也。”因此卜虽不可尽信,但又不得不行。《乐论二》列举唐太宗、魏征、司马光之言,申论“凡治之降不由乐,而治之替未尝不由乐”。《正统论》认为刘备非正统,因其“正则正矣,而不统者也”。凡此皆有根有据,不温不火,执正以御奇。黄道周(1585-1646)的论辨文,“源本六经,取裁《左》《国》秦汉,不乞灵唐宋,奥博渊通,奇峭高古,自为一家”(21)。作于天启初年的《本治论》三章,上章论:“夫妇、兄弟、朋友,此三者之伦,自天子博,不自天子薄也。”中章论:“为天下有序,则条而贯之;有数,言之则以为常言,不言则购天下无言之者。”下章论:“为天下者,慎无讳而已。讳在内,则贼在于内;讳在外,则贼在于外。”(22)这些见解源自儒家传统,但在明季乱世,却自有针砭时势的独特效用。而行文步骤井然,论述层层深入,不急不徐,有论有据,犹见儒者本色。
明代另有一派论辨文作家,讲求奇气坌涌,戛然自成一家。如明前期徐有贞(1407-1472)的论辨文,如《君师论》、《文武论》、《宽猛辨》、《言行说》、《玉山说》、《制纵论》、《谏说》、《汉元功与唐凌烟功臣优劣论》、《周礼在鲁论》等,“多杂纵横之说。学术之不醇,于是可见;才气之不可及,亦于是可见”(23)。《文武论》(前)开篇即云:
世常以文武为二事,予甚病之;非予之病之,为天下病之也。为天下病之者何?文武为二事,则天下无全才;天下无全才,则吾道之用阙;吾道之用阙,而天下之事不治。夫文武皆吾道之用,固儒者之事也。为儒而不备文武者,不足以为儒。
以下首论“古之圣贤皆儒也”,继论“古之所谓文,非今之所谓文也;古之所谓武,非今之所谓武也”,复论“儒者之事失”而天下之治不可得,倘若“儒者而知事其事,文武之才萃于厥躬”,则天下可治(24)。在明代政治萎弱之时,徐有贞呼唤文武兼备的“真儒”,这显然是有为而发的。
明中期程敏政(1445-1499)尤以史论见长,见解独特,往往足以“成一家言”(25)。如《篁墩文集》卷11《陈平论》申论“西汉之士,其策事率以利而不以义”;《伍员论》倡言“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一也,不幸而处其变,则如之何?曰:君臣之合以人,父子之合以天,以人者可绝,而以天者不可绝。”凡此,大都戛戛独造,不同凡响。祝允明(1460-1526)的论辨文更是“肆口横议,略无忌惮”(26)。如《怀星堂集》卷10中(27),《治乱论》提出“治不可绝也,乱亦不可绝也”;《古今论》称“谈者类判古今为岐途,吾恒患之。大校君子多是古而非今,细人多狃今而病古,吾以为悉缪也”;《学坏于宋论》指责宋儒“谋深而力悍,能令学者尽弃祖宗,随其步趋,迄数百年不寤不疑而愈固”;皆敢于直言己见,无所忌惮。
在前后“七子”中,以王世贞(1526-1590)的论辨文最有特色。王世贞的史论文章,往往于细微处着眼,发人所未发,辨人所未辨。如《弇州四部稿》卷110“史论”中(28),《太公》篇言“为管仲难,为太公易”,又说:“凡太公之所为,多阴谋秘术见于《金匮》、《六韬》诸篇者”。《季札》篇论:“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关羽》篇论道:“关羽之失荆州,以为羽之失,余以为非羽之失,而昭烈之失也。”凡此,皆洞微知著,别出心裁,有理有据。王世贞的政论文章,也多有痛心疾首之辞。如《正士风议》一文(29),以“唐虞之世”为典范,总结历史经验道:“人孰不为其贵,而顾为其贱者,则是有以使之贱也。其所以使之贱者,则是在上而不在下也。探本计委,殆未可责之士也。”这的确道出了士风不正的根源。
李贽(1527-1602)“为文不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30),这一文风以论辨文最为鲜明。如《童心说》云: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
李贽倡言“童心”,旨在提倡“真情”,反对假道学,所以他说:“《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31)这样的论断,真有摧枯拉朽之势。
钟惺(1574-1624)的论史之文有《史怀》一书(32),“发左氏、班、马之未竟,钩其隐深而出之”,“冷眼颖心,直具史之才识”(33)。如《史怀》卷5《平准书》篇旗帜鲜明地提出论点:
平准之法,是武帝理财尽头之想,最后之着,所以代一切兴利之事,而救告缗之祸,所谓穷而变、变而通,其道不得不出于此者也。
以下就此展开论述,并深刻地指出,司马迁之写《平准书》,“盖有深悲焉,非悲平准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于平准之故也”,隐然批评武帝“喜功生事”以致与民争利。在卷9《货殖列传》中钟惺认为,司马迁之写《货殖列传》,是“借以写胸中实用,又以补《平准书》之所未备耳”,大要言之:“《平准》言利,渐向剥削;《货殖》言利,渐向条理。”此论颇有独见。钟惺《隐秀轩集》卷23另有史论38篇,亦多精思卓见,而且要言不烦。
大要而言,无论是原本经术而粹然一出于正,还是奇气坌涌而戛然自成一家,明代论辨文都表现出研精一理而师心独见的主体性特征。明中后期作家对这一主体性追求更有明确的表述,如唐顺之(1507-1560)《答蔡可泉》云:“自古文人虽其立脚浅浅,然各自有一段精光不可磨灭,开口道得几句千古说不出的说话,是以能与世长久。”(34)李贽《又与从吾》云:“苏长公片言只字与金玉同声,虽千古未见其比,则以其胸中绝无俗气,下笔不作寻常语,不步有脚跟故耳。”(35)焦竑(1541-1620)《刻苏长公集序》云:“古之立言者,皆卓然有所自见,不苟同于人,而惟道之合,故能成一家言而有所托以不朽。”(36)袁宏道(1568-1610)《与冯琢庵师》其二云:“独谬谓古人诗文,各出己见,决不肯从人脚跟转。”(37)袁中道(1570-1623)《李温陵传》认为:“昔马迁、班固,各以意见为史……岂非以独见之处,即其精光之不可磨灭者?”(38)因“师心独见”而“研精一理”,这赋予明代论辨文独特的思想文化价值。
思辨性:锋颖精密而是非明辨
论辨文是说理之文,东晋李充(约323年前后在世)《翰林论》指出:“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39)萧统《文选序》提出:“论则析理精微”(40)。刘勰也主张“论”体文应做到“锋颖精密”,“论如析薪,贵能破理”(41)。在论证方式上,明代论辨文往往偏重执一而论,明辨是非,发挥势如破竹的气势,具有深刻的思辨性特征。
论辨文是明代科举考试的程式文体,因此以八股文的章法写作论辨文成为一时风气。明前期李时勉(1374-1450)称道:“今之所谓时文者,特掇科求仕者假是以进焉,虽其文体轻浮疏浅,而于道则未尝戾也。道在是而不戾,则由是而进于古也,不难矣。”(42)他的《师友说》,以韩愈(768-826)《师说》所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为基本论点,从正反两方面论述“师弟子之所以为教与学,有成与否”:
夫所以为教者,必由于是而后其教行;其所以为学者,必由于是而后其学进。是故为师者,道既充矣,而必为人传之;业既广矣,而必为人授之;惑既释矣,而必为人解之。彼不吾求也,不吾受也,不吾问也,是自弃自暴者也,绝之可也。为弟子者,道不足于己,必于师而求之;业未成于己,必于师而就之;惑未释于己,必于师而辨之。彼不吾传也,不吾授也,不吾解也,是为己而非为人者也,去之可也。夫如是,则为教者诚,而为学者笃,其能相与以有成也必矣。
若夫为师者靳恡闭固,非有重资厚币足以动人者,未肯一轻示之,而辄绝之。为弟子者,怠惰玩愒,非有诵习可以速成者,未肯一轻从之,而辄去之。是则为师者不知所以为教,为弟子者不知所以为学,其能相与以有成者鲜矣。(43)
全文隐然有八股气息,但却出自情衷,“平易通达,不露圭角,多蔼然仁义之言”(44)。以八股之道、八股之格贯穿于文章之中,而以浅显平实的语言加以表达,这是李时勉论辨文的风格,也是明前期占主导地位的论辨文风格。
黄凤翔(1545-?)的论辨文,“辨古法真,似不爽锱铢”(45),也表现出鲜明的“八股文法”。如《田亭草》卷20《救时名实论》指出:“乃今郡邑政治,有浮慕其名而实不副者,则重积储、饬乡约是也;有其名可喜,其实可行,而未及措意者,则嬉遨当禁、僭侈当惩是也。”以下详加分疏,是典型的八股文作法。他尤以驳论见长,善于列举大量史实,有理有据,步步紧逼地辨驳传闻之讹误与旧说之非当。如同卷《裁欧阳子本论》辨驳欧阳修《本论》之说,认为:
世儒之尧言禹趋,颂法周孔,而耽嗜势利,肆行不顾,以乱天下国家者,其人何可胜数?顾谓持礼义可以胜佛教,只见为迂阔,而远于事情也。
文章主张用釜底抽薪之法,使遁入佛门者无利可图,斯可为治本之论,论世隐含愤慨,行文颇有气势。
当然,“八股文法”仅仅为明代论辨文作家提供了一种论证方式,还有许多论辨文作家能够超越“八股文法”,以广征博引、论证透辟见长。如明前期方孝孺(1357-1402)的论辨文纵横豪放,议论恢宏,辞锋奇峻,大有纵横家的气势。他撰有《深虑论》十篇(46),其一云: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与?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所不及者,天道也。
这无疑是从正确的前提下引申出错误的论点。但是他却引证大量史实,申论这一论点,如秦之变封建为郡县,汉之大建庶孽为诸侯,以及“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又引证唐太宗与宋太祖开国初的一些措施,往往是“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于乱亡”。最后得出结论:“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并提出方略:“惟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如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不忍遽亡之。”他认为,这就是“虑之远者”。文章思虑周密,气势汹涌。
明中期杨慎(1488-1559)的《封建》一文,申论唐柳宗元、宋苏轼“封建”之说,博引史实,文气强盛:
封建始于黄帝,不得其利,已受其害矣。……至周,则其事又可睹矣。大封同姓以及异姓,谓之万国。其初建之意,亦曰藩屏京师也,夹辅王室也,使民亲于诸侯而诸侯自相亲也。成、康继世,未百年间,昭王南巡而胶舟溺死矣,穆王西巡而徐偃煽乱矣,藩屏焉在乎?夹辅焉在乎?至于春秋战国,干戈日寻,迄无宁岁,肝脑涂地,民如草菅,乌在其为亲也?
其立之政典,防其僭窃,为述职之制曰: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为建国之典曰:负固不服则伐之,内外乱、鸟兽行则灭之。其法似严矣。周之世,诸侯之不朝多矣,贬谁之爵乎?削谁之地乎?矧敢曰六师移之乎?负固不服,先莫如秦楚,后莫如吴越,天王方且迁避之不暇,敢言伐之一字乎?内外乱,鸟兽行,莫如晋之齐姜,卫之宣姜,鲁之文姜、哀姜,二嬖之子,非类之孽,方为太子而世其君,天王册命之不暇,敢言灭之一字乎?三朝之制殆为虚设,九伐之典亦是弥文,则封建非圣人意明矣。(47)
全文议论,多设疑破惑,虽不以识见称擅,却能以博辩称雄。
黄省曾(1490-1540)的论辨文,风格略近东汉王充,有“反复诘难,颇伤辞费”的特点(48)。如《难柳宗元封建论》开篇立论:
王天下者,计乎生民而已,非可仅曰子孙利也。计在子孙,未有能利其生民者也。不能生民利,而能终庇其子孙者,鲜矣。
以此为据,他认为:“宗元《封建论》,大抵为子孙也,卑乎浅矣!”以下列举大量历史事实,逐一驳斥《封建论》中的观点(49)。《难墓有吉凶论》、《难术家以八字射决论》二文(50),以自然现象和社会常识为据,批斥“堪舆风水之说”和“珞琭三命之说”,破除世俗之见,鞭辟入里。后文假设与术士沈生辩难,层层递进,洋洋洒洒,若江河决口,势如破竹,最能体现黄省曾论辨文的风格。
李贽《与友人论文》说:“凡人作文,皆从外边攻进里去;我为文章,只就里面攻打出来,就他城池,食他粮草,统率他兵马,直冲横撞,搅得他粉碎,故不费一毫气力而自然有余也。”(51)收录在《焚书》中的论辨文大都具有这一特征。如《何心隐论》以“世之论心隐者,高之者有三,不满之者亦有三”发端,先详引他人之论,畅言何心隐(1517-1576)之高为“不畏死”、“任之而已”、“为道而死”,是为正论;而对不满何心隐“偏枯不可以为训”、“明哲不可以保身”、“亡固自取”三端,仅以简短的文字轻轻拨去,是为反论。最后,文章“就里面攻打出来”,下一转语曰:
独所谓高心隐者,似亦近之,而尚不能无过焉。然余未尝亲睹其仪容,面听其绪论,而窥所学之详,而遽以为过,抑亦未可。吾且以意论之,以俟世之万一有如公者,可乎?吾谓公以见龙自居者也,终日见而不知潜,则其势心至于亢矣。其及也,宜也。然亢亦龙也,非他物比也。龙而不亢,则上九为虚位;位不可虚,则龙不容于不亢。公宜独当此一爻者,则谓公为上九之大人可也。是又余之所以论心隐也。(52)
李贽如此申论,虽为“以意论之”,却具有鞭辟入里的雄辩之气。
清人极力倡导论辨文的“自然深厚”,如李光地(1642-1718)说:“学古文须先学作论。盖判断事理如审官司,必四面八方都析到,方可定案。如此则周围折折都要想到,有一处不到便成罅漏。久之,不知不觉意思层叠,不求深厚,自然深厚。”(53)与此不同,明代的论辨文作家更自觉地追求“锋颖精密”,这不仅表现为论证的精密,更表现为思维的精密,而思维的精密实有赖于思想与言论的自由。明中期以后文人标榜之风大盛,在政治、学术和文学领域流派蜂起,门户角立,出奴入主,党同伐异,形成独特的时代风气。史可法(1601-1645)《请饬禁门户疏》描述明末党争局面时说:“从门户生畛域,从畛域生恩怨,从恩怨生攻击,而线索渊源之计愈巧,而君子小人之辨愈淆,先儒谓‘纤丝翳胸,万物倒置’者矣。”(54)《明史》卷282《儒林传序》描述明中期学术分裂的情形说:“宗(王)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靖)、隆(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55)范景文(1587-1644)《葛震甫诗序》描述当时的文坛风气说:“往者代生数人,相继以起,其议如波。如吴下之正用修,近代之翻王、李,后必非先,沿用故事。今则各在户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拟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吴右楚,我法坚持。彼此纷嚣,莫辨谁是。”(56)正是这种时代风气,孕育了明代论辨文的独特风貌,即擅长于论说辩难,明辨是非,“虽厉声色,虽露锋芒,然气力雄健,光滔长远,读之令人意强而神爽”(57)。
感染性:理与气偕而辞共意并
当然,明代论辨文之所以“读之令人意强而神爽”,还得益于其理与气偕而辞共意并的感染性特征。
以理与气偕、辞共意并作为论辨文独特的审美风貌,唐李翱(772-836)《答朱载言书》已先发其论:“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词盛则文工。”(58)明代文章家对此更多有精解。如刘基(1311-1375)认为:“文以理为主,而气以摅之。理不明为虚文,气不足则理无所驾。”(59)苏伯衡(约1360年前后在世)评孔子升文章:“理到矣,气昌矣,意精矣,辞达矣。”(60)方孝孺《与舒君》云:“盖文与道相表里,不可勉而为。道者气之君,气者文之帅也。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文者,辞达而已矣。”(61)陈敬宗(1377-1459)《题米芾遗墨》云:“夫文以理为主,必气以充之,然后振励而不薾。”(62)周忱(1381-1453)《高太史凫藻集序》云:“文以理为主,而气以发之。理明矣,而气或不充,则意虽精,辞虽达,而萎薾不振之病有所不免。”(63)陈洪谟(约1506年前后在世)云:“文莫先于辨体,体正而后意以经之,气以贯之,辞以饰之。体者,文之干也;意者,文之帅也;气者,文之翼也;辞者,文之华也。体弗慎则文庞,意弗立则文舛,气弗昌则文萎,辞弗修则文芜。四者,文之病也。是故四病去,而文斯工矣。”(64)
善于设喻举譬,侃侃而论,这是明代论辨文的突出特征,无论是文章家、学问家还是政治家,大都如此。这一点最能体现出明代论辨文理与气偕而辞共意并的感染性特征。
文章家如明前期方孝孺的《严光论》开篇立论:
君子之处世,必乎仕则忘其身,必乎不仕则忘其民。忘身,不智也,忘民,不仁也,皆非君子之事也。譬之水之在川,通则流,障则止,随其所遇,而水不与力焉。故隐不求名,仕不规利,各当其宜而已。
全文即以“各当其宜”论仕隐之选择,以为严子陵决非“为名高而隐者”,其所以不仕而隐,是因为他“量其主而后入,察其幾而后动”,对光武帝的“志趣德量之浅深审矣”,深知光武决非“推诚善任”之君,所以“与其用而使人主有疏薄故旧之嫌,则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义哉?”(65)全文理正意深,剖析入微,气盛辞达,简洁明快。朱元璋曾作《严光论》,指责严光为“罪人大者”,其意盖在于威慑蒙元遗民。方孝孺当读过朱文,此文恰可作为驳论(66)。知徒莫如师,宋濂曾称道方孝孺:“精敏绝伦,每粗发其端,即能逆推而抵于极,本末兼举,细大弗遗。见于论著,文义森蔚,千变万态,不主故常,而辞意濯然常新,滚滚滔滔,未始有竭也。”(67)方孝孺史论之文,最能见出这一特点。
明中期李东阳(1447-1516)的《弈说》云:
吾尝观于弈矣。弈之初本无情也,卒然而合之,疆分类别,击取攘劫,若有得失乎其间者。及其地交意偪,主于必胜,其势莫肯先却焉。故或役心命志,如蛛游蜩化,而不自知。其胜者施施然,若辟土地而朝秦楚;不胜则赪面戟指,无所不至。
今之言奕者必以适,以适而反自劳,则不若缩手而旁观者之为适也。劳与适相遭,非智者不能卒辨。至于覆图敛奁,则其所谓胜负者,始茫乎其不可揽,然后劳亡而逸见,其甚者犹或以夸之乎人,或者怅怏郁结,愈不可释。呜呼!此又何哉?
古之不善弈者曰苏子瞻,其言曰:“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则是知不工于弈者,乃得奕之乐,为深人之达于是者,可与言弈也。世之善喻世者,必以弈。以弈观世,鲜有不合者也。(68)
文章由博弈者之心态发论,倡导以“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超然态度处世,可谓善喻世者。何景明(1484-1521)的《说琴》一文,也饶有情致。文章用制琴的取材,比喻对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行文略显堆垛,用语时或晦涩,但条分缕析,朗朗可读。如:
凡攻琴者,首选材,审制器。其器有四:弦、轸、徽、越。弦以被音,轸以机弦,徽以比度,越以亮节。被音则清浊见,机弦则高下张,比度则细大弗逾,亮节则声应不伏。故弦取其韧密也,轸取其栝圆也,徽取其数次也,越取其中疏也。今是琴,弦之韧疏,轸之栝滞,徽之数失钧,越之中浅以隘。疏,故清浊弗能具;滞,故高下弗能通;失钧,故细大相逾;浅以隘,故声应沉伏。是以宫商不诚职,而律吕叛度。虽使伶伦钧弦而柱指,伯牙按节而临操,亦未知其所谐也。……
吾观天下之不罪材者寡矣。如常以求固执,缚柱以求张弛,自混而欲别物,自褊而欲求多。直木轮,屈木辐,巨木节,细木欐,几何不为材之病也?是故君子慎焉,操之以劲,动之以时,明之以序,藏之以虚。劲则能弗挠也,时则能应变也,序则能辨方也,虚则能受益也。劲者,信也;时者,知也;序者,义也;虚者,谦也。信以居之,知以行之,义以制之,谦以保之。朴其中,文其外,见则用世,不见则用身。故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材何罪焉?(69)
这两段文字,皆用辗转递进之法,句法、语气,实得《左传》行文之神,可谓善学古者。
明后期徐渭(1521-1593)的《论中》七篇,最能代表其论辨文风格。如《论中一》论述“不为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的道理,设喻云:
鱼得水而饮水,清浊不同,悉饮也,鱼之情也,故曰为中似犹易也。而不饮水者,非鱼之情也,故曰不为中,难而难者也。二氏之所以自为异者,其于不饮水不异也,求为鱼与不求为鱼者异也。不求为鱼者,求无失其所以为鱼者而已矣,不求为鱼也。重曰为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长人,量悉视其人也。夫人未有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为过中;衣长人以侏儒,是为不及于中,圣人不如此其量也。若夫释也者,则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量何施?故曰不为中。(70)
此文析理精辟,譬喻恰当,真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特点。黄汝亨称其“文崛发无媚骨”(71),王思任称其“文似厌薄王侯之鲭,独存蔬笋之味;又如著短后衣,缒险一路,杀讫而罢”(72),于此可见一斑。
明代学问家的论辨文也多以善喻著称。如王守仁(1472-1528)的论辨文,擅长运用生动具体的比喻,以一组或几组排列对比的偶句,形象地阐明他的观点,深入浅出,因小见大。如《示弟立志说》中云:
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正目而视之,无他见也;倾耳而听之,无他闻也。如猫捕鼠,如鸡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结,而不复知有其他,然后此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觉,自然容住不得矣。……盖无一息而非立志责志之时,无一事而非立志责志之地。故责志之功,其于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阳一出,而魍魉潜消也。(73)
这篇文章所说的“志”,无非是“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但剥去这层内核,仅作抽象的“立志”之说,我们不难看出,王守仁谈论立志之法,还是确乎可行的。杨慎的论辨文,大率既含博综之学,又挟凌厉之气,尊古而不忽近,模拟而能变化,格高气盛,“明白俊伟,能道其意之所欲言”(74)。如《性情说》征引《易》、《庄子》、许慎、李善、班固、《钩命决》、《礼运记》为据,指出:
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犹水也,情波也。波兴则水垫,情炽则性乱。波生于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观于浊水,迷于清渊,小人也;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举性而遗情何如?曰“死灰”。触情而忘性何如?曰“禽兽”。(75)
全文显然是针对宋儒主张割裂性、情,进而存性灭情的观点,有为而发的。文章以水、波喻性、情,贬斥“举性而遗情”与“触情而忘性”,主张“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言简而气盛。
明代政治家的论辨文,可以张居正(1514-1587)为代表。张居正的论辨文言辞相当激切,风格颇为凌厉,与他的性格为人相近。如《辛未会试程策》之二提出:
法不可以轻变也,亦不可以苟因也。苟因则承敝袭舛,有颓靡不振之虞,此不事事之过也;轻变则厌故喜新,有更张无序之患,此太多事之过也。二者法之所禁也,而且犯之,又何暇责其能行法哉!去二者之过,而一求诸法,斯行矣。
对于孟轲主法先王,荀卿主法后王,张居正赞成后者。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因此,衡量法之得当与否,应以“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为准则。议者认为,明初所定的法制,已历两百余年,“科条虽具而美意渐荒,申令虽勤而实效罔获”,故必有所更张,以新天下之耳目。张居正则不以为然。他设譬道:
车之不前也,马不力也;不策马而策车,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下流壅则上溢,上源窒则下枯。决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76)
因此,他主张整饬吏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严肃法纪。此篇虽属应制之文,而议论恢宏,笔锋犀利,显示出张居正有志改革朝政的怀抱与识见。史称张居正“勇敢任事,豪杰自许”,“慨然以天下为己任”(77),从其文章,可见其风采。
从文体风格来看,论辨文无疑应以理明意高为体,以气盛辞达为用。宋人陈亮(1143-1194)《书作论法后》说:“大凡论不必作好语言,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故大手之文,不为诡异之体而自然宏富,不为险怪之辞而自然典丽,奇寓于纯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内。不善学文者,不求高于理与意,而务求于文采辞句之间,则亦陋矣。”(78)清刘熙载(1813-1881)甚至主张:“论不可使辞胜于理,辞胜理则以反人为实,以胜人为名,弊且不可胜言也。”(79)
然而,论辨文固然以理为本,如宋濂《莆田四如先生黄公后集序》说:“其为文词,务以理胜,不暇如它文士驰骋葩藻以为工”(80);但论辨文要做到说理透辟,文章家就不能不讲究一气贯通,气势磅礴。而行文之气,实出自于文章家之性格,所以黄宗羲(1610-1695)《论文管见》说:“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81)同样的,论辨文固然以意为主,如宋人田锡(940-1003)云:“文以意为主,主明则气胜,气胜则锵洋精彩从之而生”(82),宋人陈骙(1128-1203)《文则》也说:“辞以意为主,故辞有缓有急,有轻有重,皆生乎意也”(83);但论辨文要做到雄辩有力,文章家就不能不讲究结构精巧,辞采丰茂。如曹植(192-232)说:“辩言之艳,能使穷泽生流,枯木发荣。庶感灵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84)刘勰也说:“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85)明代论辨文体现出理与气偕而辞共意并的感染性特征,正是其不朽的审美魅力所在。
综上所述,明代论辨文的时代特征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研精一理而师心独见的主体性、锋颖精密而是非明辨的思辨性和理与气偕而辞共意并的感染性。
在这三方面时代特征中,研精一理而师心独见的主体性最能体现明代论辨文作家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崇尚和张扬。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86)。无论是研寻哲理,是讽议朝政,是探求经术,是指摘历史,是衡论宗教,是品藻人物,是箴贬风俗,是讨论礼制,还是品评艺文,明代论辨文所表现的研精一理而师心独见的主体性,实际上都指向大道的弘扬与生命的永恒。桓范(?-249)《世要论·序作》曾指出:“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论俶傥之人,为不朽耳。”(87)明代的论辨文往往与“大道”的弘扬、“圣教”的阐发、“事义”的推论、情感的抒写等密切相关,可以为当代和后代开启智慧的法门,推进历史的进展,这就使论辨文作家得以实现人生的文化价值,从而长存不朽。
与“诗言志”、“诗缘情”不尽相同,论辨文以理为本,以理为主,以理为魂,更讲究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章炳麟(1869-1936)在解释陆机《文赋》“精微而朗畅”的论断时指出:“论者,平抑臧否之作,人之思想,愈演愈深,非论不足以发表其思想,故贵乎精微朗畅也。”(88)论辨文旨在论道说理,明辨是非,要求作家运用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方式,深入发掘事物的内在联系、本质和功能,因此论辨文是最适宜表达思想的文体,渗透着人们深刻的理性思维、情感旨趣和生命意识。明代论辨文作家往往极力在畅所欲言的议论之中,表达自身独特的思想,从而使论辨文发挥弘扬大道、针砭时世、教化群伦、坚持志向、张扬典范的特殊功能,这也赋予明代论辨文以深刻的思想价值和丰厚的文化价值。
注释:
①⑤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3页。
②⑥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32-134、133页。
③姚鼐:《古文辞类纂》,北京:中国书店影印世界书局,1935年版,1986年版,第1页。
④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27-328页。
⑦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⑧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第43页。
⑨王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通津草堂刻本,1990年版,第137页。
⑩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327-328页。
(11)魏禧著、张潮辑:《日录论文》,《昭代丛书》乙集卷31,台湾《丛书集成续编》第204册影印本,第679页。
(12)邵长蘅:《邵青门全集·青门簏稿》,卷11《书宋学士集后》,清盛宣怀辑:《常州先哲遗书》第一集,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武进盛氏刊本。
(13)宋濂:《宋学士文集》,卷66,《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正德间刊本。
(14)宋濂:《文宪集》,卷2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24册。
(15)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9朱同《覆瓿集》提要,第1467页。
(16)张廷玉等:《明史》,卷282《邵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247页。
(17)邵宝:《容春堂集·续集》,卷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58册。
(18)张廷玉等:《明史》,卷287,第7384页。
(19)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8-59页。
(20)张邦纪:《沈文恭公集序》,沈一贯:《喙鸣文集》,卷首,《四库禁毁书辑刊·集部》第176册影印明刊本。
(21)郑玫:《序》,黄道周:《黄石斋先生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84册影印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郑玫刻本。
(22)黄道周:《黄石斋先生文集》,卷6,第129-135页。
(23)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70《武功集》提要,第1487页。
(24)徐有贞:《武功集》,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45册。
(25)李东阳:《篁墩文集序》,程敏政:《篁墩文集》,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52册。
(26)王士礼教禛著、湛之点校:《香祖笔记》,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27)祝允明:《怀星堂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60册。
(28)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收入《明代论著丛刊》,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影印明万历间刻本,1976年版。
(29)王世贞:《凤洲笔记》,卷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4册影印明黄美中刻本,第537-539页。
(30)(38)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卷17《李温陵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21、723页。
(31)李贽:《焚书》,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8页。
(32)钟惺著,蒋励志、蒋励修辑:《史怀》,《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287册影印明刻本。
(33)陆云龙:《钟伯敬先生合集序》,钟惺著、李先耕等标校:《隐秀轩集》,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04-605页。
(34)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7,《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
(35)李贽:《焚书》,卷4,第223页。
(36)焦竑:《焦氏澹园集》,卷14,收入《明代论著丛刊》第三集,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影印明万历间欣赏斋刻本,1977年版,第537页。
(37)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81—782页。
(39)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60页。
(40)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页。
(4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328页。
(42)(43)李时勉:《古廉文集》,卷7《文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42册。
(44)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70《古廉文集》提要,第1485页。
(45)甘雨:《田亭草序》,黄凤翔:《田亭草》,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4册影印明万历三十九年甘雨刻本。
(46)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辛酉王可大台州刊本。
(47)杨慎:《升庵集》,卷4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
(48)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20《论衡》提要,第1032页。
(49)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28,《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94册影印明嘉靖间刻本,第761—763页。
(50)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29,第769-778页。
(51)李贽:《续焚书》,卷1,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页。
(52)李贽:《焚书》,卷3,第88-90页。
(53)梁章钜:《退庵论文》,周钟游辑:《文学津梁》,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本,1916年版。
(54)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1,《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87册影印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史开纯刻本,第190页。
(55)张廷玉等:《明史》,第7223页。
(56)范景文:《范文忠公文集》,卷6,台湾《丛书集成新编》第76册影印《畿辅丛书》本,第99页。
(57)谢枋得:《文章轨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59册。
(58)李翱:《李文公集》,卷6,《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成化十一年(1475)刊本。
(59)刘基:《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卷5《苏平仲文集序》,《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刊本。
(60)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5,《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正统七年(1442)刊本。
(61)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1《洁庵集序》。
(62)程敏政:《皇明文衡》,卷49,《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间卢焕刊本。
(63)高启:《高太史凫藻集》,卷首,《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正统九年(1444)周忱刊本。
(64)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第80页。
(65)方孝孺:《逊志斋集》,卷5。
(66)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67)宋濂:《宋学士文集》,卷70《送方生还宁海(并序)》。
(68)李东阳:《怀麓堂集》,卷3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0册。
(69)何景明著、李淑毅等点校:《何大復集》,卷33,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89-590页。
(70)徐渭:《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8页。
(71)黄汝亨:《徐文长集序》,徐渭:《徐渭集》,附录,第1355页。
(72)王思任:《徐文长先生佚稿序》,徐渭:《徐渭集》,附录,第1351页。
(73)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页。
(74)陈邦瞻:《杨用修太史集序》,杨慎:《升庵集》,卷首。
(75)杨慎:《升庵集》,卷5。
(76)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卷16,《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13册影印明万历四十年(1612)唐国达刻本。
(77)张廷玉等:《明史》,卷213《张居正传》,第5644-5646页。
(78)陈亮:《陈亮集》,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3页。
(79)刘熙载:《艺概·文概》,刘熙载著、徐中玉等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44页。
(80)宋濂:《宋学士文集》,卷30。
(81)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0册《南雷诗文集》(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页。
(82)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引,第92页。
(83)陈骙著、王利器校点:《文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84)曹植著、刘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页。
(8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7页。
(86)曹植著、刘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196页。
(87)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89页。
(88)章炳麟:《国学讲学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