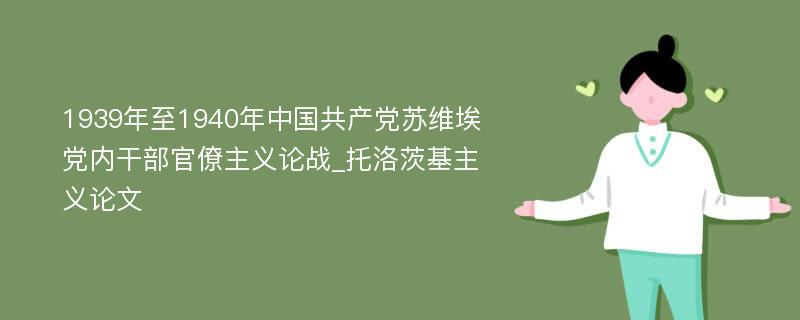
1939-1940年托派关于苏共党内干部官僚化现象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派论文,党内论文,官僚论文,现象论文,干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已经证明,苏东国家政治发展曲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一个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重损害广大民众利益的官僚集团。所谓官僚集团,指的是通过权力垄断,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自己又享受特殊待遇的一群人。在取得政权、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布尔什维克党由于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很快就出现了领导干部的官僚化现象,在20—30年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集团。①其标志有三点;一是官僚集团的地位已经稳固,党外的反对党不再存在,党内的反对派也遭到禁止,它牢固地控制了党和国家机关,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二是官僚集团的触角延伸到了整个社会,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决策权和执行权都集中到掌握行政大权的少数干部的手中;三是官僚集团在物质生活上享受着极大的特权,在精神上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工资收入和生活方式都与普通人民群众出现了很大差别。
对苏共②党内干部官僚化现象和官僚集团形成关注比较早的人之一是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及其党内的支持者,他们从20世纪20年代就把批判苏共党内干部官僚化现象和官僚特权阶层当作同斯大林争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武器。1929年,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后,在国外又获得了不少拥戴者,形成了托洛茨基派(Trotskyist,以下简称托派)。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由于苏联接连不断的政治大清洗,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苏联对波兰、芬兰的领土侵占,托派内部在苏联还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进而在1939-1940年围绕苏共党内的官僚集团的性质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的直接后果是托派的分裂,而更深远的影响是他们提出的官僚集团是“特权阶层”(Caste)还是“新阶级”(New Class),苏联是一个“异化的工人国家”还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社会等问题,成为后来持不同政见者和学者反复研究和争论的焦点。
一、托派对苏共党内干部官僚化问题上的看法与分歧
1939年前,托洛茨基关于苏共党内的干部官僚化现象的看法在托派内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最早使托洛茨基注意到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内的领导干部可能会成为一个“统治阶级”的人是考茨基。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考茨基最早使用“新阶级”③这一概念批评俄共(布)党干部官僚化现象。在1919年发表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中,考茨基认为俄国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社会,“这一社会打算废除阶级差别。它从侮辱和摧毁上层阶级开始,以形成一种新的阶级社会告终”。苏俄存在三个阶级:首先是资产阶级,包括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这个阶级处于社会的最低层,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财产;位于资产阶级之上的是工人阶级,他们在法律上是统治阶级;上述两个阶级在现实生活中都处于一个“新阶级”的统治之下,“从工人苏维埃的独占统治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官僚阶级的独占统治,这个阶级一部分是从工人苏维埃产生的,一部分是由他们任命的,一部分是强加给他们的。这是三个阶级中的最高的一个,是新的统治阶级,是在老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家和战士的领导下组成的。”④
1920年,托洛茨基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对考茨基的答复》中尖锐地回击了考茨基。他指出,考茨基的批评是对俄国的恶毒的攻击,在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成为社会新的统治阶级,俄国共产党人正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存在考茨基所说的产生了一个新的官僚阶级的问题。⑤
然而,到了1920年代中期,当托派批评俄共(布)党内的官僚化现象时,使用了“特权阶层”这个特定的术语。1923年10月,在《四十六人声明》中,支持托洛茨基的46名领导干部明确指出:“广大党员群众都不能提名选举俄共的省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相反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都是由党内的书记特权阶层来挑选的,而这些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正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变为这个特权阶层的高级官员协商会。”⑥此后,“特权阶层”就成为托派对官僚集团的一个标志性术语。
到了1936年,托洛茨基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苏共党内的官僚化现象的观点。
托洛茨基认为,苏共党内的干部官僚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形成的是一个“特权阶层”而非一个“统治阶级”。所有权是划分阶级的基础,“各个阶级是由它们在社会经济制度中所占的地位来划分的,并且首先是从它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的。在文明社会中,财产关系是得到法律的确认的”⑦。尽管官僚集团通过垄断国家政权可以任意管理和分配国有化财产,但是,苏联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性质并没有改变;尽管官僚集团从政治上剥夺了无产阶级,但是,“他们不得不保卫作为自己的权力和收入源泉的国有财产”,“依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武器。”同时,官僚集团没有股票,也没有公债,也不能把官位传给下一代。这与传统的阶级有着根本的不同。总之,官僚是一个“特权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苏联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关系”:生产资料属于国家,而国家“属于”官僚集团。⑨
关于官僚集团统治产生的根源,托洛茨基认为,这是社会的现实需要。十月革命发生在落后的俄国,不仅广大无产阶级文化水平低不能直接参加社会管理,而且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资料。因此,要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或者避免人民群众因匮乏产生的“你争我夺”,需要“指派一个警察来维持秩序”,官僚的权力由此产生。掌握了权力的革命者,越来越认识到权力带来的好处,便不断地试图巩固和扩大手中的权力,成为嗜权者,从而背叛了社会主义。⑨
基于以上分析,托洛茨基断定,根据统治阶级的性质决定了国家的性质这个原则。由于官僚集团不是一个阶级,苏联的社会性质因而并没有改变,只是一个“异化的工人国家”。官僚化现象只是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现象,至于将来朝何种方向发展还有待历史证明。托洛茨基认为,苏联的社会性质有三种可能:无产阶级推翻官僚的统治,建立起真正的无产阶级国家;苏维埃的统治阶层被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官僚继续统治着苏联,可这又必将转向前两种可能。⑩
托洛茨基讲这些都是为了发动世界革命,其中,在苏联就是推翻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的统治,建立他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一个具有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党将代替官僚集团成为领导者,恢复工会中和苏维埃中的民主制度,恢复苏维埃中各党各派的自由;在经济上,保持和发展计划经济,废除特权,“使劳动报酬上的不平等只限于经济方面和国家机关方面的生活必需部分”(11)。
然而,到了1938年,由于认为苏联在控制社会、打压反对派、实行经济政策等方面与德意法西斯有相似性(12),意大利的托派分子布鲁诺·里齐(Bruno Rizzi)开始怀疑托洛茨基的观点,进而在1939年4月完成的《官僚化的世界》一书中系统地批判托洛茨基。
里齐认为,苏联的官僚集团并不像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个“特权阶层”。虽然苏联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但官僚集团在法律形式上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只是在实际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可以通过拥有国家权力而实际地占有、享用和分配国有化的生产资料。在里齐看来,苏联的所有制形式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单个资本家拥有个人的所有权;在苏联,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国有化所有权。“在苏联存在着一个剥削阶级,它如同所有者一样控制着生产方式,这个阶级的成员不愿把财产拿出来分享,而是他们自身作为一个集团,以一个阶级的整体形式作为所有国有财产的真正所有者。”(13)因此,国家所有权不但不是官僚集团没有成为一个新阶级的证据,恰恰相反,是这个“新阶级”的新的所有权形式。这样一来,苏联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不是什么“异化的工人阶级国家”,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官僚集体主义”(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里齐反驳托洛茨基说,官僚化现象不是一种暂时的异化,而是代表着一个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一个新的社会形态。
至于官僚集团产生的根源,里齐认为,托洛茨基所说的官僚化现象产生于苏联社会的需要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不高是站不住脚的。官僚集团的产生根源并不在于革命者背叛了无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自身根本不能像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所说的那样担当起社会管理的职能。无产阶级本来就是社会中的一批没有知识的人,他们能力如此之弱,以至于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之后,也只能把社会的管理权交给一个新的社会管理者——官僚集团。(14)也正因如此,里齐断言,取代资本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集体主义”。它不仅存在于苏联,也存在于像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和罗斯福统治的美国这样的采取国有化和计划方式的国家。(15)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里齐进一步指出,“官僚集体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有效地组织生产,因此,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不是一种历史反动。“官僚集体主义”只要还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就有其存在的历史意义。(16)
里齐的观点在托派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部分托派的支持,也引起了托洛茨基的注意。1939年9月25日,托洛茨基发表《大战中的苏联》一文,批驳里齐的观点。除了重复先前的观点外,托洛茨基还针锋相对地指出,不存在“官僚集体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代替问题,“官僚集体主义”也不是历史的进步。苏联的国有化政策与法西斯主义、罗斯福新政有着本质的不同:苏联的国有化政策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基础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变革;美国和德国的国有化政策只是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局部调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因此,尽管官僚集团的统治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范围内都会存在,“官僚集体主义”即使是一种新的制度的话,那也只适用于苏联。在苏联,“官僚集体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代替并不是历史的进步。苏联的真正的进步性在于它的集体主义,而不是官僚主义。党员干部的官僚化正是苏联一切罪恶的根源,是无产阶级革命被背叛了的结果,是生长在无产阶级国家上的一个“毒瘤”,而不是一个“新的器官”。(17)
然而,托洛茨基的论断并不能说服托派内里齐的支持者,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表现更加坚定了他们的看法,他们于是纷纷加入到与托洛茨基的论战当中。
二、托派对苏共党内干部官僚化问题争论的深化
1939年9—10月,苏联通过苏波战争,侵占波兰东部领土即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1939年11月—1940年3月,通过苏芬“冬战”,占领了芬兰东南部包括维堡在内的卡累利阿地峡、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岛屿。在这种情况下,托派内部的一些人尤其是非苏联的托派分子不断发出疑问:苏联这么做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有什么区别?这样的国家真的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
由于托洛茨基并没有否认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一些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于是转向了里齐,美国的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和马克斯·沙赫曼(Max Shachtman)就是其主要代表。最终,托派内部形成了支持托洛茨基的正统派和支持里齐的少数派。少数派反对托洛茨基提出的苏联是一个异化的工人国家的观点,谴责苏联对波兰和芬兰领土的侵占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提出“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能再认为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了”。在战争中,形成了以英美帝国主义为一方,以野心勃勃的德国及专注于“权力、特权和国家收入的斯大林官僚主义”的苏联为另一方的对立阵营。托洛茨基将苏联与斯大林政权区分开是一种抽象的作法,实质是为斯大林政权辩护。最初,反对派只是借用里齐的理论来反对托洛茨基,但后来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
伯纳姆重复了里齐关于“官僚集体主义”的看法,认为一个由“管理者”发起的革命正在苏联、美国和德国兴起,他们通过控制国家的管理权和掌握国有化的生产资料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管理者”阶级包括企业的主管、技术人员、官僚主义者和军人。他们虽然没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可以使用和分配生产资料。“官僚集体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是历史的必然。同时,由于采用“集体主义”的所有权方式,“官僚集体主义”将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最终的准备。与里齐不同的是,伯纳姆认为:苏联的“官僚集体主义”并不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动,是一种独裁制度。国有化政策和计划经济正是官僚独裁的基础。正是因为官僚的反动统治不得人心,“官僚集体主义”才会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18)
沙赫曼认为,就像在20年前说“工人的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一样,现在说“异化的工人国家”也是一种抽象。要弄清楚苏联的社会性质,必须具体分析在苏联发生了什么,“(苏联)政权的异化程度不能依据抽象的国有化的所有权为依据,而应当关注活生生的现实”(19)。沙赫曼从里齐对所有权的定义方式获得启示,确立了他批判托洛茨基的理论基础。他提出,“所有权关系”而不是“所有权形式”才是判定阶级的真正依据。在苏联只是建立了“所有权形式”上的国家所有权,而没有建立“所有权关系”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所有权形式”上的国家所有权与苏联社会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已经毫无意义。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官僚集团可以通过垄断国家权力而控制、分配和享有国有化的生产资料,并以此来剥削其他的社会各个阶级,占有他们的劳动,这才是苏联的真正的“所有权关系”。托洛茨基的错误就在于把“所有权关系”和“所有权形式”混为一谈。
然而,沙赫曼并不完全认同里齐提出的“官僚集体主义”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新社会制度的说法。他认为,苏联的官僚集团与美国、德国的官僚集团有所不同:前者服务于一种新的所有权关系,是一个“新阶级”;后两者只是服务于资本主义所有权,而且这些国家的所有权基础仍旧是私有制。因此,官僚集团只是一个官僚阶层,“官僚集体主义”只存在于苏联。(20)
伯纳姆和沙赫曼等人抛出自己的观点后,托洛茨基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反驳伯纳姆和沙赫曼,如《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给国家委员会多数派的四封信》、《小资产阶级道德主义者与无产阶级政党》,等等。在这些文章中,托洛茨基在重申自己以前观点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尽管侵占波兰和芬兰是一种侵略行为,但苏联的做法从战略上增强了抵御希特勒进攻的能力,为了工人国家的战略利益牺牲芬兰是值得的,斯大林在波兰和芬兰占领区采取的国有化政策更具有进步意义。托洛茨基还进一步指出,伯纳姆和沙赫曼等人毫不区分地将苏联等同于斯大林的政府的做法违背了辩证法;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官僚集体主义”这一新的社会制度的观点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伯纳姆犯了“实用主义”的错误,而沙赫曼则成了“折衷主义”者,他们都是托派内的小资产阶级。(21)
托洛茨基的回击加剧了托派内的分裂趋势,伯纳姆和沙赫曼及其支持者继续与托洛茨基争论。他们争论说:“财产国有化并不是抽象的,它自身没有好坏之分……(它的价值)必须根据政治和社会背景来判断……(苏联)在被侵占的国家实行财产国有化,不再能证明在大战中支持红军的观点的合理性。首先,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所有权关系并没有改变,苏联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即它控制了三个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其次,乌克兰西部和芬兰南部的国有化仅仅意味着占领这些领土的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推翻斯大林政权,建立令人他们满意的、真正进步的、具有社会主义价值的财产关系,就像他们在苏联所做的那样。然而,这种情况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成为现实。”(22)伯纳姆等人还指责托洛茨基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辩证法式的诡辩:一方面承认苏联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而国家政权掌握在官僚集团手中;另一方面,又说工人阶级仍旧是苏联的统治阶级。这种做法是为了转移争论的焦点,是毫无意义的,辩证法虽是政治的基础但不是政治的全部,托洛茨基已经背叛了托洛茨基主义。(23)与此同时,他们还决定脱离托派。1940年4月,沙赫曼及其支持者宣布脱离美国的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跟随他退党的人大约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五分之二。不久,沙赫曼宣布自己放弃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加入了诺尔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领导的美国社会党。1940年5月21日,伯纳姆公开发表了《詹姆斯·伯纳姆致工人党的辞职信》,与托派决裂。1940年8月,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遇害。这次场争论最终结束。托洛茨基传记作者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对此评价说:“托洛茨基在晚年最后一次目睹了他滚上险峻高山的巨石重新滚回了山下。”(24)
三、托派在对苏共党内干部官僚化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原因
为什么托洛茨基和里齐等人在判定苏联是“异化的工人国家”还是“官僚集体主义”,苏共内部的官僚集团是“特权阶层”还是“新阶级”上,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分歧,以至造成托派的分裂呢?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因素。
首先,这些问题关系到托派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托派存在的理论依据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有三部曲: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的“不断性”。根据托洛茨基的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没有中间的社会形态,帝国主义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前夜,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在短期内就会发生。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后,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象。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可以首先在一国爆发,但它的胜利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胜利后,如果得不到国际上无产阶级的援助和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便处于孤立的状态——在国外将面临国际资产阶级的颠覆和包围,在国内各种社会矛盾随着孤立状态的持续将逐渐增加,并最终失去政权。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就是依靠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取得胜利后,应当立即扩展到西方发达国家,进而扩展到整个世界。托派的历史使命就是促成这一事件的到来。(25)对托洛茨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证明了帝国主义的垂死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新的契机。他写道,“我们对此坚信,如果这场战争唤起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苏联官僚的垮台、苏维埃民主在远远高于1918年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复兴。到那时,关于斯大林官僚是‘新阶级’还是工人国家身上的毒瘤的问题就会解决了……每个人都会明白,在国际革命的广阔进程上,苏联官僚的出现仅仅是偶然的倒退。”(26)因此,对托派来说,如果十月革命建立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那么世界革命的前途又在何处呢?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世界革命的最好时机,那么他们还要等多久呢?
里齐等人把官僚集团看作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把“官僚集体主义”作为一种代替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实际上就是对“不断革命论”的根本颠覆。从这一理论出发,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引发了世界革命,推翻了“特权阶层”和资本家的政权,“不断革命论”的结果仍旧是另一个剥削阶级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这样一来,“不断革命论”完全失去了意义。托洛茨基认为,里齐等人“公开地或默默地承认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潜能已经消耗殆尽,社会主义运动已经破产,旧的资本主义正在向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的‘官僚集体主义’转变”(27)。正因如此,他不遗余力地与里齐等人论战。
其次,托洛茨基与里齐等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民族情感和国家利益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观点。托洛茨基是苏联人,更与苏共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与列宁等人一起发动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之后,托洛茨基又与布尔什维克党一起领导红军击败了白军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他在与斯大林的权力斗争中失败并被驱逐出苏联,但仍认为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性质并没有变,无产阶级仍是苏联的统治阶级,在大战中应当保卫苏联。与此相对,里齐、伯纳姆和沙赫曼等人的背景却不同。里齐出生在意大利,1921年加入意共,是一个鞋子零售商;伯纳姆出生在美国,在1930年代初加入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美国工人党,直到1935年才与托派开始交往;沙赫曼出生在波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05年移民到美国,曾经加入美国共产党,但在1928年被共产国际开除。因此,他们不仅对苏联和苏共没有亲近感,甚至是由于对斯大林政权的不满才加入托派的,他们的批判也就更容易比托洛茨基尖锐。
然而,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里齐及其支持者对苏共党内干部官僚化现象的批判都存在不足之处。
托洛茨基和里齐都是按照马克思主张的方法把所有权作为判定官僚集团是不是“阶级”的标准。前者认为,苏联法律上规定的国家和集体的所有权,是官僚集团不是“阶级”标志;后者则认为国家和集体的所有权正是“新阶级”的所有权形式,因为国家“属于”官僚集团。然而,所有权并不能作为划分阶级的永恒标准。任何概念都是历史中的概念,脱离了其背后的历史现实来空谈概念,概念就没有了任何意义,反倒会成为人类思想发展的束缚。所有权这个概念也是如此。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家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是合一的。一个人拥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就意味着他可以占有、享用并控制生产资料,从而形成不同的集团在生产和分配领域的不同地位,“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28)。也就是说,法律上的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即所有权)是生产过程的主导的因素。因而,马克思把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作为划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标准。然而,通过法律上的所有权只是马克思划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的一个特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马克思将生产关系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把财产关系(所有权关系)当成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29),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更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30)他指出,把所有权单纯理解为法律关系是形而上学的、主观的,也是不切实际的,“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31)所以,后来的列宁就把阶级定义为:“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32)所有权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列宁上述阶级特征的一个直接原因,而真正重要的它所反映的生产关系。如果法律上的所有权不能反映客观的生产关系,那么它也就不能成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了。
后来的学者,尤其是苏联学者,为了强调苏联国有的和集体的所有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不同,往往简单地把法律层面的所有权作为划分阶级的根据,而忽略所有权背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托·鲍威尔早就对此提出批评,“只有对社会主义持一种难以形容的肤浅观念的人才认为,实现财产的社会化即实现剥夺和没收的法律行动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任务。其实,财产社会化不过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形式;它的最重要的内容是生产社会化,即改组生产的经济任务、在生产部门中重新分配人员和劳动力、生产和分配的合理化。财产的社会化用暴力一下子就可以强行实现。生产社会化只能是数十年之久有计划进行的工作的结果。”(33)在苏联,除了法律的所有权发生改变外,在实际的生产体系中,仍旧存在着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关系不同、在劳动组织中的所起的作用不同、对社会财富的取得方式和多少不同的集团。至于官僚集团能否称其为一个“新阶级”,应当从苏联的现实生产关系中考虑,也不应当根据是否拥有法律上的所有权。托洛茨基和里齐等人在最终判定官僚集团是否是一个阶级时,最终都要回到所有权的概念,这是教条的。
托派对官僚集团的评价也是有历史局限的。托洛茨基的观点侧重于道德方面,通过苏联的社会现实与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比,用“异化”这个词来评价官僚集团的所作所为与共产党人的不同。然而,从俄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上看,官僚集团的产生又是和俄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需求密切相关的,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作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生产力远远落后于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现代化成为俄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客观需要。尽管革命者打算通过政权的力量,在革命胜利后建立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生产关系,但在后来的实践中,俄国现实的生产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客观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带有落后生产力的特征,执行的是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客观使命。官僚集团尽管背叛了革命,但是它通过野蛮的方式加速了俄国的工业化进程,成为东方国家进行工业化的一种方式。(34)
里齐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犯了历史客观主义的错误。他虽然提到了苏联社会存在的官僚集团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大清洗等现象,但却不做道德评价,而是更强调客观的生产方式的演进,把“官僚集体主义”看作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一种历史进步。里齐的历史客观主义给他的理论带来了两方面的缺陷:其一,“官僚集体主义”的逻辑前提是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已经是一个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这实际上忽略了俄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其二,由于忽略掉官僚集团统治的不正义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深远的负面影响,他看不到由此所带来苏联后期的整个社会的停滞和倒退。
托派对苏共党内干部官僚化现象的评价方面存在的问题,除上述他们自身认识上的缺陷外,还与当时苏联的历史现实有关。在20世纪30年代,苏共党内官僚集团的统治才刚刚确立,更多的弊端还未充分显现。然而,站在今天的高度回过头看,托派争论触及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严重弊端。正是一个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控制和享受着国有化和集体化的财产的官僚集团的存在,才导致了苏联东欧国家政治发展曲折并最终失败。不仅如此,对于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摆脱苏联模式、探索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中,如何避免一个拥有特权、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集团的产生,也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注释:
①学术界对官僚集团形成时间,看法也不一致。有人认为它形成于列宁时期,有人认为是斯大林时期,还有人认为是赫鲁晓夫时期,还有人认为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参见黄宗良:《官僚特权阶层问题与社会主义命运》,《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
②前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8年3月成立,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成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1918年3月改名俄共(布),1925年12月改名联共(布),1952年改名苏联共产党。
③最早提出共产主义革命者中的部分人在革命胜利后会变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是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他认为,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层“只能意味着少数特权者统治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所谓的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由真正的或者冒牌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人数很少的新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治理人民群众”。然而,巴枯宁的主张只是代表了一种无政府主义者的担忧。参见[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马骧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3页。
④中央编译局资料室编:《考茨基言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中文版,第336—337页。
⑤Leon Trotsky,Terrorism and Communism:A Reply to Karl Kautsky,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6.
⑥E.H.Carr,The Interregnum,1923-1924,Lond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54,pp.367-373.
⑦[苏]列夫·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柴金如译,北京: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版,第181页。
⑧同上,第182页。
⑨[苏]列夫·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83—101页。
⑩同上,第184—187页。
(11)同上,第184页。
(12)Adam Westoby,"Introduction," in Bruno Rizz,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World—The USSR: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London,New York:Adam Westoby Tran.,Tavistock Publications Ltd.,1985,pp.14-15.
(13)Bruno Rizzi,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World—The USSR: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p.63.
(14)Bruno Rizzi,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World—The USSR: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p.54.
(15)Ibid.,pp.64-65.
(16)Ibid.,pp.62-69.
(17)Leon Trotsky,In Defense of Marxism: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I,New York:Pathfinder,1995,pp.41-64.
(18)James Burnham,"The Politics of Desperation," New International,Vol.6,No.3,January 1940.
(19)Max Shachtman,"The Crisis in the American Party," New International,Vol.6,No.2,March 1940,pp.43-51.
(20)Ibid.
(21)Leon Trotsky,In Defense of Marxism: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I,pp.89-242.
(22)Max Shachtman,"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orld War," New International,Vol.6,No.2,March 1940.
(23)James Burnham,"Science and Style:A Reply to Comrade Trotsky," In Defense of Marxism: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I,Pathfinder,1995,pp.283-313.
(24)[波]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施用勤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514页。
(25)[苏]列夫·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蔡汉敖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中文版,第87—88页。
(26)Leon Trotsky,In Defendence of Marxism: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I,pp.48-49.
(27)Ibid.,p.40.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1页。
(31)同上,第178页。
(32)《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33)[奥]奥托·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史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中文版,第117页。
(34)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5—168页。
标签:托洛茨基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生产资料所有制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斯大林论文; 经济论文; 法律论文; 集体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