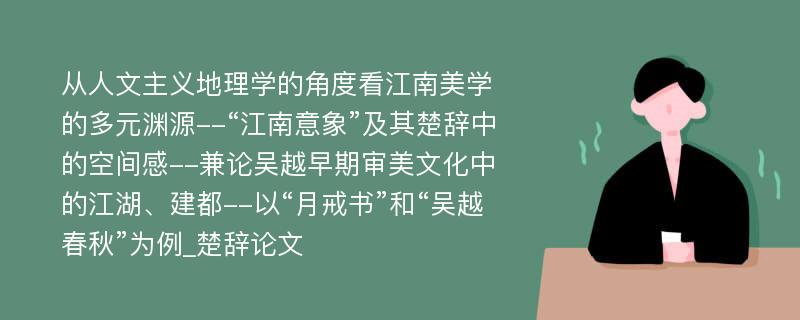
江南美学的多元源头(笔谈)——楚辞中的“江南想象”及其空间感——从人文主义地理学观念来看——论早期吴越审美文化中的江湖与剑道——以《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为例——良渚审美文化中的玉陶、徽饰、墓葬及其江南特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剑道论文,人文主义论文,笔谈论文,楚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4-0115-10
楚辞中的“江南想象”及其空间感
——从人文主义地理学观念来看
刘彦顺
刘彦顺,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本文所论及的楚辞中的“空间感”,不是在真实物理空间中生成,而是通过语言描述而形成,是一种诗性的江南空间想象。虽然此空间感来自语言描绘,但是一旦形成,就会对真实物理地域造成影响,使得物理空间主观化。当然,就楚辞的空间感而言,只是针对那些受到楚辞中相应作品影响的读者而言的,即通过阅读作品而获得深刻的记忆,这一记忆会与真实的空间相联系或发生联想,从而实现一种人文主义地理学所称的“地方想象”。同时,我认为,作品中所描述的空间绝对不能与真实的空间或者地方史做等同或者比对,也不能幼稚地认为,处在某一特定空间或地域的文学家在其作品中必定机械地、被动地传达其地域文化,甚至文学作品比如楚辞对于楚地的描绘,会赋予该地域以文化意义和想象。
一、楚辞中的“恋地情结”
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段义孚曾经使用“恋地情结”来指称对一个地方的依恋,他说:“‘恋地情结’是一个新词,可被宽广地定义为包含了所有人类与物质环境的情感纽带。……这种反应也许是触觉上的,感觉到空气、流水、土地时的乐趣。更持久却不容易表达的感情是一个人对某地的感情,因为这里是家乡,是记忆中的场所,是谋生方式的所在。”[1](P196)这标示着一种新的地理学的产生,即超越于实证主义的地理学所进行的客观、微观的研究方法,人文主义地理学侧重研讨的是现象学式的地域空间感,它往往体现为对某一地域的感受经验或者想象、描述。这一恋地情结同样适用于楚辞中对江南故地那种不离不弃的情愫。
《楚辞》中所言地域及其名物在数量上极为繁复,历来有不同的见解。宋代黄伯思在《东观余论·校定楚辞序》中曾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游国恩先生也认为,《楚辞》中所述地理,以《九章》之《涉江》《哀郢》为最详,如《离骚》之济沅、湘,《湘君》之沅、湘无波,邅之道洞庭,遗佩之澧浦,《湘夫人》之洞庭波、木叶下、有芷之沅、有兰之澧,《涉江》之济江、湘、上沅水,《哀郢》之上洞庭而下江,《怀沙》之沅、湘分流,《惜往日》之临沅、湘之玄渊,《渔父》之赴湘流等等,皆属于江南之地,称为江南之水。游国恩先生针对钱穆曾撰《楚辞地名考》一文认为屈原之放未尝至江南提出异议,并做了大量考证,认为“屈子所欲济之沅湘,断在今之湖南明矣”[2](P43)。
在《楚辞》中,“恋地情结”指向的当然是“楚国”,甚至指向整个楚文化的历史文化传统。比如就屈原而言,他的“恋地情结”来自于被家国除名,背井离乡,因而,在楚辞中的“游”就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主题。此“游”或是被迫的流放,或是诗人自发的旅行,而且这两种“游”的方式往往缠绕在一起,不分表里。就前者而言,抒情主人公往往意欲回到故土,在作品中以繁复交错的楚地符号抒发故土的空间感;就后者而言,抒情主人公又往往意图建立一个想象中的故土,以便在那里安然栖居。
以《哀郢》为例,屈原在作品中描绘了郢都的水陆路线,以此为核心来抒写所恋故土的空间感。其中大量出现的就是“家门”意象。在这里,作为“建筑意象”的家门完全转化为“地理意象”。诗人写到被迫离开郢都,沿着都城的水门与水道离开,他说:“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出国门而轸怀兮”、“发郢都而去闾兮”等,就一再地以“门”为界线。作为“建筑意象”与“地理意象”交织的“门”,除了标示纪南城水路交通便利、门户众多与诗人必须穿门而过之外,“顾龙门而不见”还分明预示着“家门”再不可入的深意。在临近离去时不断回望,最后的一个画面就定格在因为距离渐远而再也看不见的“宫门”。除了“家门意象”之外,还有与家园相反的“荒原意象”。如“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在王逸的阐释中,就以夏为“大殿”、丘为“废墟”,即诗人预感郢都即将化为荒原,“家门”也即将荒芜。
在《哀郢》中,最为典型的“江南地理意象”还是耐人寻味的“水道”。就其抒情的方式而言,作品采用了在“回忆”中追溯并建立“空间感”。作为故土的郢都越来越远,致使原来那些流畅贯通、联系四面八方的水路系统,都因为遥遥相距而变得不相通了;同时,也使用这一“水道”的变化作为喻体,来表现自己心绪的杂乱与郁结。诗人巧妙地将郢都发达的水路与自己的心境相对照,先描述心情,再以都城内的水路作对照。《哀郢》首句即言:“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正因为如此,诗人离去时总是徘徊不忍,即便“去终古之所居兮”,行船时仍“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乃至于“出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还说“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这一切都体现了极为繁复的江南水乡的“水道”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其他意象。除了在水道中的游历之外,《哀郢》中还使用了“登高”意象,“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来表达细腻的“恋地情结”,可谓极为典型的体现。
二、屋宇之感
“恋地情结”在空间感上还较为宏观,尽管真切,却还不能免于泛泛,而对故地的“屋宇之感”则将这种“恋地情结”落实得踏实而强烈。段义孚曾经指出,对农村的屋宇与城市建筑的空间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比如:“聚集的村落在景观上显得非常引人注目。当我们走进村落时,会看到房子的轮廓以及在农田上矗立的树木。比较起来,都市地区缺乏较显眼的可见物,每一社区只占整个建筑区域的一小部分,分不清哪一区是尾端,哪一区是开头。”[3](P175)虽然在楚辞中的屋宇不仅限于村落,但是其空间感却极具“地方性”。
据今天的考古研究,当时的楚人对于居室极为重视,徐文武在《楚国宗教概论》中提到:“在楚简中,室神又称宫室,分别有称为宫、室。楚人对宫室的安全十分关注,占祷卜辞中经常出现宫室是否平安。”[4](P209-210)这都能反映出,“恋地情结”往往实现在空间感最强的地方,即自己的“居室”及其相关的所在。比如“宗庙”在《天问》中就充当了重要的角色。王逸曾经指出,《天问》是诗人见到楚国宗庙、面对宗庙中的壁画有感而发形成的作品。其《天问章句序》说:“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
而在《九歌·湘夫人》之中,所抒发的空间感就十分浪漫超拔。如果说楚辞中的很多作品带有浓郁的江南美学因子,是取自于现实的话,此篇中的空间感则是完全自由地利用了江南风物,把它们作为一种可供自己驱使的符号,构筑了一个梦幻中的屋宇:“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由于“筑室兮水中”,因而就有了“荷盖”、“紫坛”、“芳椒”、“兰橑”、“薜荔”等散发着醉人气息的花草,除了描述视觉上的酣畅之外,更把屋宇空间感的重点落脚在丰富的嗅觉之上。通过这一浪漫构思的屋宇,所传达的就不再是作为现实人文地理的楚地美学,而是《湘夫人》赋予了楚地湘水以芳香诗学,赋予了“恋地情结”以亲切想象。
除了以“芳香诗学”为著的《湘夫人》之外,《招魂》更是在招魂仪式中以富丽堂皇甚至奢靡无止的屋宇来实现神灵的附体:
魂兮归来!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贼奸些。像设君室,静闲安些。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渡些。光风转蕙,泛崇兰些。经堂入奥,朱尘筵些。砥室翠翘,挂曲琼些。翡翠珠被,烂齐光些。蒻阿拂壁,罗帱张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室中之观,多珍怪些。兰膏明烛,华容备些。二八侍宿,射递代些。九侯淑女,多迅众些。盛鬋不同制,实满宫些。容态好比,顺弥代些。
从以上段落可以看出,《招魂》以七百字之多来描写宫室的豪华、奢靡,笔墨极为铺张,意象极为繁复多变,辞藻华丽,繁类成艳。在《大招》中,对于招魂所利用的屋宇描写,也同样集中在“美屋”、“美色”与“美味”之上,而且“美色”与“美味”都杂陈于“美屋”之中:“易中利心,以动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泽只。长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归来!以娱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媔只。靥辅奇牙,宜笑嘕只。丰肉微骨,体便娟只。魂乎归来!恣所便只。夏屋广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坛,观绝霤只。”从《招魂》与《大招》来看,所描绘的“屋宇之感”可谓视觉、触觉、嗅觉、肤觉、味觉乃至于全身感觉的纠结与杂糅,与上述《湘夫人》一脉相承,都通过想象赋予了楚地以诗性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想象。
当然,楚辞对“屋宇之感”的抒发是多样的,除了直接抒发之外,还有很多取“屋宇”作为比喻的作品,如《离骚》的“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与“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三、芳香诗学
除了楚辞在“恋地情结”与“屋宇之感”所建构的江南想象之外,“芳香诗学”也是很典型的,即在楚辞中不仅出现了大量的花草植物名称,而且在其中凝聚了感官的欢愉与记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江南的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因而,这是一种充满“地理个性”的“芳香诗学”或者满目芳菲的环境生存经验,尤其是与北方文化相比就更加突出。
从自然地理来看,所属江南的楚地处在长江与汉水之间,这里气候温润,雨水充沛,汀渚沼泽遍布,土质肥沃,易生各种植物,尤其是其中的美丽花草,更加得到人们的钟爱。散见于屈原的《离骚》、《九歌》中的植物就有一百多种。花草在楚辞中极为典型的体现就是“香草”的使用,对此,学界已有公认。诸如,其一,以植物为佩物,“扈江蓠与僻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户服艾以盈要兮”(《楚辞·离骚》)。其二,以花叶为衣裳,“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楚辞·离骚》)。其三,以植物济饮食,“朝饮木兰之堕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楚辞·离骚》)、“惠肴蒸兮兰藉”(《九歌·东皇太一》)。其四,以香草沐浴,“浴兰汤兮沐芳”(《九歌·云中君》)。其五,以香草和香木为建材,“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檫,辛夷楣兮药房”(《九歌·湘夫人》)。其六,以香草之名直呼神灵,乃至成为神灵的代称。王国璎认为:“诗人登山涉水采摘草木时,所重视的不是草木的珍贵和芳香的品质,强调的是草木禀赋的象征意味。”[5](P26)也可以说,在楚辞的很多作品中,往往是把草木的珍贵、芬芳与丰富的象征凝聚在一起来呈现的,诸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竣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在此,既表达了抒情主人公作为园丁的情怀,又把土地的旺盛繁殖力毫不含糊地倾吐出来。另外,屈原使用香草的主要意图也在于——在遭遇挫折之后,意欲回归芰荷、芙蓉等初服所象征的“自然”,期望再度经由身体与自然物的接触,才能自然地与故地的母体融为一体。
在《少司命》一篇中,同样很典型地集合了多种香草意象的运用方式:“秋兰兮糜芜,罗生兮堂下。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谏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此篇的第一句到第四句先是直接从神堂景物的“芳香诗学”写起,其中的“荪”就是作为一种香草直接称呼“少司命”的,而且,最后两句更是以“荪”直呼神灵并乞求神灵来守护儿童。在第二节文字中,为了迎接湘夫人的到来,祭神者也同样使用了各种佳木香草来装饰她的殿堂。除了作为祭神或者作为人神交接的神秘巫术的作用之外,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更是一种以来自于“花草”或者“香草”的浓烈“嗅觉”与“味觉”在空间感上的体现。
尽管是在以语言作为材料的文学作品当中描述此类空间感,但是由于大量、繁复而且交织使用“花草”、“香草”意象,就使得楚辞的芳香诗学显得尤其强烈或者浓烈,以至于弥漫于全篇,导致在时间绵延上的强势,因而,感官的刺激加强就更加强化了内在的空间感。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曾对这种嗅觉导致的空间体验做过细微的描述:“我一个人,在我对另一个年代的回忆中,可以打开心底的橱,那里面只为我自己保存着一种独一无二的香气,那是暴晒在柳条筐里的葡萄香气。葡萄的香气!它是淡淡的香气,必须用很多想象才能感受到它。”[6](P13)而在楚辞中的“芳香诗学”,不仅在江南空间想象的维度贡献极大,而且在美学的维度上,也拓宽了审美感官不仅仅局限于视觉、听觉,而且来自于复杂、立体的身体诸觉,“芳香诗学”同样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