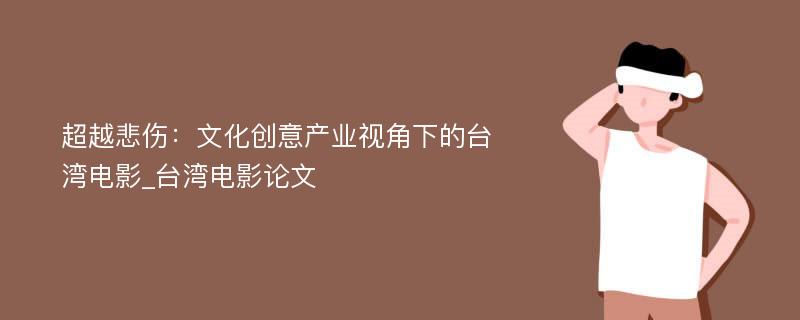
超越悲情:文化创意产业视野中的台湾电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意论文,悲情论文,视野论文,台湾电影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序言:从悲情到温情的台湾电影
在华语电影史中,台湾电影常常和“悲情”二字相连。一方面,《悲情城市》(侯孝贤,1989)为华语电影首次获得威尼斯金狮奖;另一方面,鲜为人知的“台语片”早就推出过同名的《悲情城市》(林福地,1964)。①因此,“悲情”不仅涵盖了20世纪80至90年代台湾新电影代表性的叙事风格,“悲情”还塑造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期闽南片典型的情感结构和商业品牌。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台湾新世代导演通过其代表作《海角七号》(魏德圣,2008)的票房成功,开始完成台湾电影“从悲情到温情”的过渡,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中力求重建台湾电影新的文化创意产业结构。本文首先介绍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理论,然后回顾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闽南片和作为作者个人风格的台湾新电影,最后分析台湾新世代导演超越悲情的电影追求及其面对全球化的温情叙事和跨地实践。
媒体资本:文化创意产业理论的视野
文化创意产业最近开始得到媒体和文化研究的重视。柯廷认为,在跨国媒体研究中我们必须关注地点的问题,比如“在这个世界中,文化产品来自什么地方?流通到哪里去?这种流通又对我们展现了不同群体和社会之间什么样的权力关系?②柯廷突出“媒体资本/都市”(media capital)这一概念,以理解跨国的华语文化经济的空间动力。英文中一语双关的capital同时涉指“资本”和“都市”,指一个将几个地方相互联系起来的地理中心,一个集中了资源、名声和人力的枢纽。因此,“媒体都市”是中介的场所,是复杂的力量和流通的互动地点,其典型的例子是好莱坞、伦敦、东京和孟买。某个城市是否能成为“媒体都市”是经过不断协商、争论和竞争来决定的。在华语世界,我们看到这个过程中几个大都市的竞争起伏: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上海,繁荣至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以及新世纪以来崛起的北京。这样看来,“媒体都市”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在历史上不确定的现象,其特征也随着这些大都市的地理位置而有所不同:譬如亚洲青年文化的中心是东京、首尔,而不是资本更加雄厚的纽约、好莱坞。
按柯廷分析,世界影视产业中存在这么三个结构性原则:(1)资本积累的逻辑;(2)创意迁移的线索;(3)社会文化变更的形态。一方面,资本必须高度集中,以便将生产的场地集中起来;另一方面,资本又必须加快发行销售的速度。正如马克思指出,工业革命时期资本所同时具备的向心的和离心的倾向,哈维斯(David Harvey)也强调在后工业社会中资本“压缩”时空的特征。在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通过“管理革命”将其重点从生产转向发行销售,吸引和管理人才因此成为电影制片厂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关键。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资本必须为专业的劳工群体提供合适的工作条件,为什么新好莱坞不再扩展控制严密的流水线影视生产,而开拓可以让各类媒体公司更为灵活合作的集中地。好莱坞因此转化为以地方为基地的各种社群的聚集地,这里所聚集的不仅仅是大制片厂,也是技能各异的文化劳力,以及能够保持文化劳力进行社会再生产的空间。
当然,媒体产业的发展一方面依靠商业实践,另一方面也依靠政府和媒体机构的管理,包括文化政策(如本土的、民族的)、媒体批评(如类型趣味的培养)、贸易战争(如海外进口的配额限制)等等。这里,媒体经营中民族自豪感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政府的支持还表现在媒体产业可能在远离本土的地方开辟小众市场的可能,形成一种新的中心和边陲的空间辩证关系。
柯廷强调,“媒体资本/都市”的概念必须同时承认以下四个要素中的“空间逻辑”:(1)资本;(2)创意;(3)文化;(4)政体(polity),而要求在四个要素中不仅专注某一要素。这个要求说来简单,但不容易操作。在注重资本和政体的产业研究中,主导研究方法是政治经济学的数据分析,更多地罗列出发生了什么事,但不一定探究为什么发生这些事;相反,在注重文化和创意的文化研究中,主导方法是意识形态批评,根据某种理论解释为什么发生了某些事,但却无法解释与这种理论相异或相反的其他事。柯廷强调“空间逻辑”,希望通过探索以上四个要素之间的互动,更深刻地认知媒体资本/都市的运行逻辑。以下是我参考了柯廷的四个要素,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视野中重新反思台湾电影。
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悲情:闽南片的兴衰
我认为,在闽南片时代,“悲情”既是一种创意的定位,也是一种文化的诉求,而两者在特定的政体中调动了本土的资本。闽南片兴起的直接原因是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品的“厦语片”在台湾放映时以“正宗‘台语片’”做广告,结果一开始就深受台湾观众的喜好。为了夺回“正宗‘台语片’”的称号,台湾电影人开始遵循厦语片的制作方针,吸取闽南方言文化提供的民间文化创意,推出台湾自己的闽南语戏曲电影《六才子西厢记》(叶福盛,1955)和《薛平贵与王宝钏》(何基明,1956)。这两部闽南片说明,台湾的歌仔戏为闽南片提供了最早的创意,而这类回归本土戏曲传统的创意其实早就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如天一公司的制作)和20世纪30年代的香港(如粤剧戏曲片)。随着闽南片的产量从1956年的12部激增到1958年的62部,厦语片在台湾的放映也从1956年的37部降至1958年的13部,在1960年放映1部之后便在台湾市场上销声匿迹。③
除了歌仔戏(这本来也是海峡对岸闽南文化的传统戏剧),闽南片的创意来源还包括台湾歌谣和流行歌曲,而且创意上的本土立场也同样体现在影片放映的草根文化策略,因为闽南片充分动用了台湾乡间的戏台、戏院和喜好传统戏曲和民间故事的观众。到了较为现代化制作的20世纪60年代,闽南片创意上的本土立场仍然表现在梁哲夫的《高雄发的尾班车》(1963)和《台北发的早车》(1964)这两部影片中:不仅片名指涉了台湾的两个大都市,而且片中的歌曲也为观众所熟悉。同时期的其他影片,如《旧情绵绵》(邵罗辉,1962年),也推出观众喜爱的歌手和歌曲。从厦语片的“哭调子”到歌仔戏的苦情剧,闽南片的创意来源决定悲情成为其主要情感结构和叙事策略。④闽南片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民间,其悲情宣泄可以看作是特殊创意品牌的塑造,而以下数据则表明当年闽南片悲情品牌的流行程度:从1955到1969年,闽南片共生产1052部,而同期的国语片只有373部,后者包括带有香港资金背景的台湾民营片厂(如李翰祥的“国联”和制作胡金铨电影的“联邦”)的大量出品。⑤
悲情并不是闽南片的独创,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电影和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粤语电影都渲染过悲情,甚至苦情。但是,广泛吸取本土的文化创意资源(戏剧、歌曲、唱片、广播音乐、民间故事、时事新闻等)的确使闽南片的悲情成为一个品牌鲜明的文化产品,⑥不仅在台湾地区拥有可观的票房,在东南亚也有固定的观众。悲情的创意由此既是本土的,又是跨地的。其实,从厦语片在台湾的展映开始,闽南片的发展本身就包含了多层次的跨地因素:争夺“正宗‘台语片’”的地位不过是一个开端,因为许多闽南片的导演本身就有明显的跨地乃至跨语言的经验:如何基明曾在日本东宝公司导演过教育片,梁哲夫曾在香港导演过粤语片,而白克曾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上海当过袁牧之的助理。⑦
作为创意产业,闽南片还为许多日后出名的台湾“国语”导演及时提供了训练的机会。标志李行出道的是闽南片《王哥柳哥游台湾》(1958),而李行自组的民营“自立公司”所导演的“国语”片《街头巷尾》(1963)更是处处可见悲情,其中小人物的生活拮据,比起上海早年的《十字街头》(沈西苓,1937)来说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不难理解,闽南片所尽力渲染的悲情在不同层面上也影响了台湾“国语”片的情感结构,在李行为“中影公司”导演的“健康写实”的经典影片《蚵女》(1963)和《养鸭人家》(1964)中,悲情时隐时现,不过按照新的“健康写实”的要求,这时的悲情必须升华到新的现代化语境之中。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闽南片在现代化语境中也呈现出相应开阔的国际视野。比如《地狱新娘》(辛奇,1965)就改编自由《呼啸山庄》改写的畅销小说《米兰夫人》。⑧而类似梁哲夫1966年导演的《间谍红玫瑰》和《真假红玫瑰》等间谍片,虽然背景是内地的抗日战争,但灵感却来自国际谍战片007。
进入20世纪70年代,闽南片从高峰跌入低谷,1969年生产84部,1972年减到21部,1974年只有1部,1975年后基本绝迹。台湾本土电影市场同时期由“国语片”垄断,“国语片”从1969年的89部,飙升到1971年的101部。⑨有关闽南片衰落的原因,电影史学家经常提到粗制滥造、题材重复、内容模仿、创意人才流失以及电视娱乐的兴起等,但除了这些创意和媒体方面的原因外,政体和资本也直接介入。比如20世纪60年代后东南亚“台湾当局”进入后殖民时期,开始控制非本土的方言文化的流通,使得闽南片的海外市场迅速失落。⑩此外,由于“政府”推广“国语教育政策”,新一代的台湾地区观众开始掌握双语能力,对闽南片所展示的悲情情感结构的认同逐渐淡化。与此同时,类似《西施》(李翰祥,上集1965年,下集1966年)等“大片”也改变了资本所营造的影像欣赏趣味,以及民营和国家资本新的合作模式。最后,闽南片本来就依靠戏院的预付投资,东南亚市场的失落和本土观众趣味的变化导致闽南片的大量积压,资金无法周转,生产只好停顿,行销达15年的闽南片由此在20世纪70年代初消失于历史之中。
作为作者个人风格的悲情:新电影的功过
虽然闽南片在20世纪70年代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但其建立的悲情情感结构却在台湾新电影中意外地保留下痕迹。这里说“意外”,其原因是电影史经常忽视作为草根文化的闽南片和作为精英文化的新电影之间不难发现的联系,如二者对闽南语的使用、对乡村的眷恋、对本土文化的认同等。其实,悲情的延续充分表现在早期台湾新电影中对台湾“乡土文学”的大量改编,以及侯孝贤在《童年往事》(1986年)等一系列影片中对个人和家族记忆的追求,这种“童年”的记忆一方面上升到新电影导演群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却与早年台湾拍摄的影片所宣扬的“国族记忆”相去甚远。从文化角度看,新电影和闽南片都强调本地的乡土资源,但在创意方面,新电影更多地从新兴的国际电影中吸取跨地的灵感,创造了一种符合当年台湾地区中产阶级价值品位的作者风格。(11)
台湾新电影成功的背后不乏台湾当局资本的支持。“中影公司”推出杨德昌参与导演的四段式的《光阴的故事》(1982)及其独立导演的《恐怖分子》(1986)等,间接地肯定了作为先锋影像的作者风格在文化创意上的成就。不难看出,在类似的新电影作品中,新兴的中产阶级挥之不去的忧愁也以悲情来呈现,但表达这种悲情和忧愁的不再是以往情节剧大起大伏的宣泄模式,而是欲言又止的现代派的实验模式。其实,从提倡“健康写实”开始,“中影公司”从来没有放弃过悲情叙事,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选用李行拍摄《蚵女》时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支持李行导演《汪洋中的一条船》(1978年)时亦然。
台湾新电影与“中影公司”之间微妙的关系证明,文化、创意、资本和政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根据不同的空间逻辑进行不同的组合,而作者风格并不一定与主流政治完全背道而驰。时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的保守派和激进派都批评新电影:前者谴责新电影脱离本土观众的欣赏水平,曲高和寡,因此导致台湾电影市场的大幅滑坡;后者则指责新电影接受台湾当局的招安,因为侯孝贤等人为政府拍摄过宣传片。(12)卢非易列举的数据令人沮丧:1985年1月,台湾400余家电影院中有50家停业;1986年12月,台湾地区主管部门撤销600家久未制片的空头公司;1989年7月,相继倒闭的电影院增加到199家。当然,新电影在台湾电影产量中的比例本来就很小,不可能成为市场滑坡的主要原因。更直接的原因之一是1986年8月台湾地区宣布取消外片配额制,好莱坞影片从此长驱直入,送审的外片从1986年的462部激增至1988年的791部,迅速占领台湾地区市场。(13)
台湾新电影并不像卢非易所说的那样在1987年后结束,而是继续艰难地发展。从1989年起,新电影就一直面临两难的窘境。一方面,每年都有台湾地区电影在海外主要的电影节上获奖,台湾的作者电影从侯孝贤、杨德昌到其后的“新新电影”,创作人数不断增加,台湾地区电影的国际知名度也大幅提升。(14)另一方面,华语电影占据台湾放映市场的份额也从1992年的50%(其中台湾电影15%、香港电影35%)跌落至2000年的2%,而好莱坞电影却从1992年不到50%的市场份额,一路飙升到2000年的98%。(15)进入21世纪初,不仅是台湾电影,甚至香港电影在台湾地区市场上也是一蹶不振。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可以依赖台湾地区的政体和资本,新电影可以忽视台湾地区的市场,不在乎没有本土票房。台湾地区主管部门“电影辅导金”的设立,间接地鼓励许多“新新电影”导演追求类似侯孝贤的作者风格,因为只要在海外获奖,导演就不必退还辅导金的奖额,没有经济责任。换言之,台湾地区主管部门关心的是台湾地区电影在海外的声誉(以其文化资本兑换政治资本),而不是本土票房的表现(经济资本)。台湾地区新电影因此也就可以继续生产在海外成为标志的“台湾风格”(长镜头、慢节奏、远景构图、非职业演员等),而侯孝贤本来独具风格的电影悲情也渐渐在不断重复和演绎之后失去创意。创意淡化最明显地表现在蔡明亮近年在主题建构和影像营造方面的不停重复。
更讽刺的是,正当“新新电影”为迎合海外电影节的期待而努力“再生产”侯孝贤式的悲情影像时,侯孝贤本人却在新世纪里开始追寻新的创意。《千禧曼波》(2001)力图超越以往的悲情模式,以快节奏表现出侯孝贤对都市青年文化的关注。《最好的时光》(2005)以三段式的模式,在风格上重新甄别不同历史时期悲情的社会文化的含义和艺术风格的再现。在《咖啡时光》(2003)和《红气球》(2007)中,侯孝贤更显示出超越本土的视野,在创意上靠近日本和法国的电影文化。不妨再考虑杨德昌:当《一一》(2000)在欧美、日本等艺术院线放映并得到海外媒体的高度评价时,杨德昌本人却拒绝让该片进入台湾地区市场。总之,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台湾地区新电影创造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个人作者风格,但其艺术创意却与本土产业脱节,其产品的流向逐渐以海外为主,基本上与本土资本绝缘。在本土创意文化资源和资本的整合上,新电影因此就远不如闽南片成功。
超越悲情:全球化语境中的跨地实践
回到《海角七号》,2008年以其意外的5亿新台币的票房新纪录,显示台湾电影在新世代的青年导演的创作中,已经突破新电影的模式,创出一条新路,完成了“从乡土到本土”的过渡。“乡土”本为台湾新电影早期作品中所承接的台湾“乡土文学”的创意,但这个创意到了新世纪初的台湾地区电影中几乎荡然无存。以《一一》和《咖啡时光》为例,制片资金基本上来自日本,台湾地区新电影老将们的叙事策略已经国际化,因此与台湾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概念相去甚远,甚至与新世纪的台湾电影市场也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戴乐为指出,如果说台湾新电影早期所体现的“乡土”在当时还是一种“反霸权的意识形态”(即质疑西方文化价值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以“辅导金”为主导的政策指导下,“新电影成了台湾电影:一种在众目睽睽下由台湾当局支持的运动,不断有人批评它的高标准、精英化和商业缺陷,以及它与流行模式的格格不入”。(16)戴乐为将《海角七号》视为一个“和解”的作品,从中既看到台湾新世代导演对“后新电影的余留作品”(即“新新电影”)中的现代主义的“灰暗色调”的抵制,也看到一种新的“本土”风格的巨大潜力,可以在多样化的混合过程中容纳边缘的乡村、少数族群和族裔、异同的语言以及外来的人口。(17)
在我看来,台湾地区电影中新的“本土”概念已超越以往“乡土”的所谓“在地性”,而更多地强调全球化语境中“地点”本身的跨地性和多地性,即某一地点与其他诸多地点的联系和包容。(18)《海角七号》中恒春这个地点,相对于让影片的男主角长期失望的大都市台北来说是“乡土”,但对恒春人来说却是“本土”,而且这个“本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跨地特征,既融合了客家人、台湾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喜怒哀乐,又挑战了强势的日本流行文化,而且还通过一包无处投递的日文情书引起了对台湾日据后期一段未了的爱情的眷恋。不同于以往闽南片和新电影中的乡土悲情,《海角七号》在关注小人物的台湾电影传统中,创意地制造出了一个本土男性赢得异国女性恋情的神话,用温情包装了一个在性别和族裔层面上反向思维的文化更新。好莱坞色彩浓烈的结局因此完成了银幕内外的庆典仪式,宣告了新的温情影像时代在台湾的来临。
在新世代导演的作品中,不同程度的悲情仍然存在,但温情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情感结构和叙事策略。其实,温情作为一个文化创意,在焦雄屏新世纪初制片的华语都市电影中早已出现,比如《蓝色大门》(易智言,2002)。近年的《一页台北》(陈骏霖,2010)以法国的温馨想象为开端,讲述了一个近似荒唐的黑帮追尾下初显的爱情故事,最后推出不必远涉重洋就能在台北寻找到的属于本土的浪漫。《第36个故事》(萧雅全,2010)更具小资情调,以两位年轻姐妹创办咖啡馆的简单情节,用奇特的“以物易物”的经营方式,让顾客带来各自多余的物品及其背后的个人记忆和文化符码,在狭小的都市空间中展开跨时空的叙事想象,以雅致的温情衬托出在台北都市一隅悄悄展开的既具本土特点又含异国风情的色香味俱全的故事。
新世代导演“超越悲情”的创意努力将“本土”重新构建在变化中的跨地、跨语言、跨文化的全球化语境中。《台北星期天》(何蔚庭,2009)主要使用菲律宾语,让菲律宾演员出演在台北工作的菲律宾外劳,而台湾地区本土观众则需要依靠中文字幕跟踪故事的发展。当两位菲律宾外劳在星期天搬运一个似乎被遗弃的红沙发穿越台北的都市街道的努力最终成为泡影时,温情的叙事最终让他们意识到新的人生价值,也让银幕外的本土观众从外国人的眼光中重新认识台北,意识到台北已经成为一个多语言、多种族、多文化的国际大都市。同样大量使用中文字幕的是《不能没有你》(戴立忍,2009)。虽然这部像纪录片一样展现单亲的客家父亲拒绝放弃对到了就学年龄的女儿的抚养权的故事充满了悲情,但是父女之间深厚的细腻情感使得该片洋溢着感人的温情,而这种温情又随着故事在客家语、台语和国语的多声部的交叉对话的进展中,让本土观众重新反思台湾地区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现状。
《台北星期天》和《不能没有你》等新世代电影证明,“从悲情到温情”的过渡不必只关注个人情感和记忆;相反,温情作为叙事策略同样可以展现变化中的跨地民生风景,甚至可能调和或淡化社会文化冲突。戴乐为将《海角七号》视为一个“和解”的作品,这说明他看到电影的温情可以跨越时间、空间、语言、族裔、文化等疆界的特殊潜力。我也认为,温情不仅是台湾地区新世代的青年影像风格,也是一种创意性的跨地实践,对吸引年轻的台湾地区观众重返电影院、复苏长期萧条的台湾地区电影市场有着积极的意义。
结语:重整电影文化创意产业
纵观台湾地区电影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电影发行、放映大于电影制作的传统。从日据时期开始,台湾地区的几任政体都严格控制发行、放映,而制片不过是政治宣传中的一小部分,到目前为止几乎很少看到将制片长期纳入产业发展考虑的例子,其部分原因是对主持电影部门的官员来说,他们主要对政治,而不是商业负责任。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以来的民营电影产业情况基本沿袭了发行、放映大于制作的这一模式,三者之间的资金并不完全流通,这也部分导致李翰祥的“国联”在轰轰烈烈的大片制作后,由于资金拮据,5年内便悄然隐退。历史上,台湾本土电影投资的力度相比香港显然不足。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闽南片的繁荣算是台湾电影史中的例外,而这个整合了当时台湾文化创意和民间资本的成功例子也促进了台湾电影本身的发展,包括“政府”投资的“健康写实”制作。
台湾电影发行、放映大于制片的传统在台湾电影市场20世纪90年代陷入低谷以后还引发出另一个奇特的现象:从1995年到2007年间,台湾地区电影制作能够进入发行的数字一直徘徊于每年11至23部左右,(19)在这样萧条的情况下,台湾地区各级主管部门支持的电影节及其力度却明显增加,从传统的金马奖电影节到近来的台北电影节、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台湾女性电影节、高雄电影节等等。这些台湾当局资助的电影节表明,如今看电影在台湾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商业行为,而更多的是一个文化行为。其结果是电影文化与商业的两极分化:台湾地区电影文化越来越国际化,但是电影却离市场化越来越远。在众多的电影节中,政体的指导行为多于资本的市场运作。一年一度的台湾当局拨款投资明显地缺乏电影节的一贯性,承办单位不停替换,选片质量难以保证,新的品牌也就难以创建。
鉴于台湾地区在国际政治文化关系上依附美国,台湾当局要恢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片”“进口”配额政策,在电影市场上抵抗好莱坞、保护本土电影放映的可能性极小。台湾当局在全球化时代关心的不是保护和拓展本土市场,培养本土良性资本循环的产业,而是通过本土的电影文化创意,营造一定的“台湾电影”的影响。当然,台北和高雄等城市投资电影节,目的也是想通过影像文化的传播提高城市的国际知名度,但是二者与“媒体都市”的距离还相当遥远。如何有效地在国际化和本土化(后者包括立足本土的跨地实践)的层面上有效地整合政体、资本、文化和创意的资源,这仍然是台湾地区电影目前最大的挑战。
2008年以来台湾新世代导演超越悲情的突破——本土电影发行的数量从2008年的26部、2009年的28部增加到2010年的38部。可以说是台湾电影人在更大规模地重整台湾电影文化创意产业的探求。借助《海角七号》的成功,魏德圣经过几年的融资、创意和宣传的努力,终于推出众人瞩目已久的《赛德克·巴莱》(上下集,2011),备受媒体和观众的青睐。有趣的是,这部再现台湾少数民族抗日题材的史诗电影回应了闽南片的先例,无论影片的基调温情与否,《赛德克·巴莱》以其高投资、高概念的制作和长期的跟踪宣传,创造台湾地区新的票房纪录已成定局。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由《海角七号》到《赛德克·巴莱》所开创的超越悲情的台湾地区电影文化创意产业模式是否可能持续,是否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闽南片、健康写实和新电影的道路,在台湾地区电影史乃至华语电影史上留下了一个绚丽的新篇章。
注释:
①黄仁:《悲情“台语片”》(台北:万象,1994年),213-214页。闽南片指在台湾生产的以闽南语发音的影片,以此区别在香港生产的以闽南语发音的“厦语片”。
②Michael Curtin,"Chinese Media Capital in Global Context," in Yingjin Zhang,cd.,A Companion to Chinese Cinema(London:Wiley-Blackwell,2012),pp.179-196.
③叶龙彦:《春花梦露:正宗“台语”电影兴衰录》(台北:博雅,1999年),81-83.
④Jeremy E.Taylor,"From Transnationalism to Nativism The Rise,Decline and Reinvention of a Regional Hokkien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ter-Asia.Cultural Studies 9.1(2008):72-73.
⑤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北:远流,1998年),表格11.a.
⑥参见廖金凤.《消失的影像:闽南片的电影再现与文化认同》(台北:远流,2001年),73-90.
⑦黄仁《悲情“台语片”》.406-407、424-426;黄仁编:《白克导演纪念文集及遗作选辑》(台北:亚太,2003年),第92-94、135页.
⑧参见黄仁编:《优秀台语篇评论精选集》(台北:亚太,2006年),197-199.
⑨卢非易.《台湾电影》,表格11.a.
⑩Jeremy E.Taylor."'Our Native Place—Our Cinema':Nation,State and Colony in the Amoy-Dialect Film Industry of the 1950s,"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5(2009):235-256.
(11)参见焦雄屏编:《台湾新电影》(台北:时报,1988年)。
(12)有关台湾影评界此时的分野,参见卢非易:《台湾电影》,309-320.
(13)卢非易.《台湾电影》,321-322.
(14)“新新电影”一词来自焦雄屏编:《台湾电影90新新浪潮》(台北:麦田,2002年)。
(15)Yingjin Zhang,Chinese National Cinema(London:Routledge,2004),272-273.
(16)Darrell William Davis,"Second Coming:The Legacy of Taiwan New Cinema," in Yingjin Zhang,ed.,A Companion to Chinese Cinema(London:Wiley-Blackwell,2012),p.134.
(17)Davis,"Second Coming," pp.145-147.
(18)有关跨地性和多地性的阐释,见张英进《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空间》,《文艺研究》,2010,(7):85-93.
(19)Davis,"Second Coming," p.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