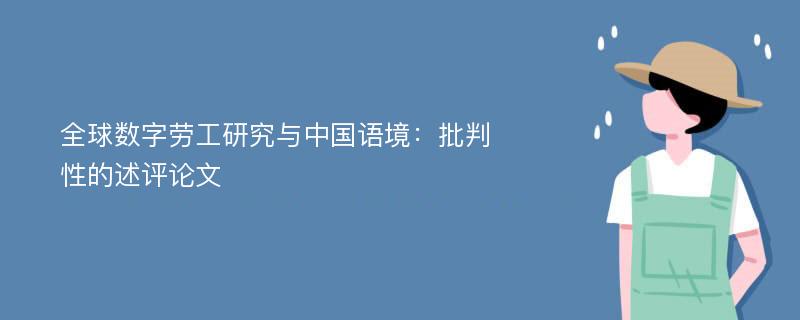
全球数字劳工研究与中国语境:批判性的述评
姚建华,徐偲骕
摘 要: 随着传播研究的理论、对象、方法和价值取向的日趋多元化,一些曾被遮蔽的重要议题开始进入传播学者的视野,其中有的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传播劳动研究。在传播新科技突飞猛进将劳动数字化、数字技术使用者“劳工化”的趋势下,数字劳工作为最新的分析范畴,逐渐成为传播劳动研究领域的前沿。笔者梳理了全球数字劳工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进路和最新成果,即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产消合一者和玩工,以及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并从中国语境出发,呈现本土学者对该议题的思考与贡献。最后,批判性地检视了上述研究存在的局限和盲点,这同时也是数字劳工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理论创新可能的源泉。
关键词: 传播劳动;数字劳工;传播政治经济学;信息与通信技术
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方式,以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重新配置了各种生产要素与资源,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带动政治经济向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转型[1]。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随着越来越多从事信息生产、传播、监控的劳动者以数字技术为生产和加工工具,且人类的知识本身不断以数字的形态存在,数字劳工日益成为传播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研究议题涉及他们的劳动过程、劳动价值、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商品化和控制方式,以及自身特征与主体意识等。
电磁发射技术可以方便地为实验室提供超高的速度,以便对目前比不可能达到的速度进行研究。可以进行高压、冲击物理实验、研究材料的状态方程等。
一、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型劳工议题
马里索尔·桑多瓦尔(Marisol Sandoval)将数字劳工定义为:将ICTs和数字技术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包括生产者和使用者。在她看来,资本对ICTs和数字技术的吸纳加速了资本主义的主要积累空间从“工厂车间”到以大都市写字楼为主的“社会工厂”的转变过程[2]。
根据桑多瓦尔的定义,数字劳工研究不仅聚焦于对工程师、设计师或者媒体从业者工作和日常生活的研究,而且强调对工厂内外生产科技产品的产业工人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今天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都需要面对新的ICTs、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不稳定的工作环境,甚至是随时可能被取代的命运。因此,扩大数字劳工的内涵和外延,而非使用来自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ur)概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劳动形式之间的联系[3]。虽然“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在构建新型政治主体方面颇有建树,但它却过于偏重产品的最终形式,而忽略了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环节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强化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
数字资本主义同样是资本主义,是后者在新技术环境中的延伸,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判断,且业已被大量实证研究结果所证实——资本主义并没有随着传播新科技的发展而改变其通过剥削劳动力实现自我增殖的基本逻辑。特雷伯尔·肖尔茨(Trebor Scholz)指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劳动的剥削以一种更加隐蔽的形式围绕新型的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而展开[4]。资本家通过将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控制的工具,加强了全球范围内有关生产活动的传播与协作,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与离境外包[5],从而将后福特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工作被传播新科技进一步切割、细分,知识与技能持续并加速贬值,资本完成了对数字劳工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与弹性雇佣,并通过各种通信工具实现对劳动力在劳动场所内外的无差别监视与控制,这些都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型劳工议题。
二、政治经济学进路的全球数字劳工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传播领域的应用和延伸,始终秉持着其母体学科的基本理论出发点之一,即将劳动视为价值的源头,并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解建立在资本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剥削之上,这种理解脱胎于传统生产劳动,延伸到知识劳动,继而扩展至数字劳动,在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看来,“数字领域的大部分工人都在昔日产业工人似曾相识的条件下辛苦工作。”[6] 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尖锐地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直指该制度中的核心矛盾——劳资关系的矛盾。”[7]他强调,任何回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忽视劳动价值论的新媒体和数字技术研究将无法触及真正的问题。本部分将从四个方面梳理全球数字劳工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进路和最新成果,它们分别是: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产消合一者和玩工以及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
1.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
对于离境外包的审视让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到世界政治图景的复杂性和流变性,而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的仍是资本的扩张和劳动力的商品化[14]。存在于离境外包这一制度性安排背后的权力不平等,使苹果公司能够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外包消费性电子产品的生产来获得超额利润[15]。这也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笔下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症候,体现着核心国家对半边陲与边陲国家经济的宰制与剥夺,而是否为已开发的经济地区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则是判断该地区是否是边陲经济的重要依据[16]。但核心与边陲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互联网与科技进步的势头此消彼长,如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既可以成为一时的核心国家,也可能在下一波科技浪潮中沦为边陲国家;此外,中国和印度正在从边陲国家转变为核心国家。基于这一视角,当前各国间频繁发生的尖端科技领域的纷争与摩擦就不难理解了。
在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格外关注全球劳动者中因信息技术应用的不平衡而导致的新型的“数字鸿沟”[8]。在米歇尔·罗迪诺-克劳希罗(Michelle Rodino-Colocino)看来,它主要表现为:特权精英启动并控制数字创新过程;中间阶层负责在现有协议的基础上设计出新的应用程序;大量的数字劳工被安排从事日常的装配和服务工作——数字鸿沟的存在更加固化而非挑战了现有的阶级结构[9]。这种将概念与执行、创意与生产分开的做法恰好是19世纪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思想的延伸,他主张把工作的执行分解为不同的过程,这些过程要求不同种类和熟练程度的技能。企业主可以更精确地根据特定的流程来匹配工资率,绝不支付超过必要的部分,而将劳动过程分解为最基础的重复性操作,又恰恰是“工作降格”(work degradation)和资本将工人“去技能化”的最佳体现[10]。
从表3看出:乳熟期(5月16日)6个处理病情指数依次为处理3(玉米茬秸秆还田)>处理4(玉米茬秸秆还田加药剂拌种)>处理5(玉米茬秸秆清除)>处理6(玉米茬秸秆清除加药剂拌种)>处理1(清除西瓜茬)>处理2(清除西瓜茬加药剂拌种)。由此可见,小麦乳熟期以处理2(清除西瓜茬加药剂拌种处理)的茎基腐病感病最轻,病情指数为19.1;其次为处理1(清除西瓜茬处理),病情指数为20.6;处理3(玉米秸秆茬还田)感病最重,病情指数为28.1;处理4(玉米茬秸秆还田加药剂拌种)和处理5(玉米茬秸秆清除处理)的感病也较重,病情指数分别为25.3和24.7。
与此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致力于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对数字劳工进行考量,即将数字劳工的分析置于全球体系进入以数字媒体为基础的积累阶段的背景之下,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只是全球数字生产与劳动分工的一环。也就是说,从全球资本积累和价值链的角度切入,制造业中的数字劳工研究能够折射出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结构性的不平等——安妮贝儿·费鲁斯-科米罗(Anbiel Ferus-Comelo)在她的研究中发现,跨国公司已经纷纷涌入印度,在各邦政府的默许下,将这个国家训练有素的工人迅速纳入资本化的轨道。这些年轻人被锻造成“唾手可得”的廉价劳动力,为“如饥似渴”的消费者市场生产廉价的手机,而这些手机给跨国公司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但同时,他们深陷工作无保障、弹性雇佣、收入极低、缺乏安全保护、没有发展与晋升机会、女工与童工泛滥等困境。不过,年轻的产业工人并非全无能动性,在印度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开始跨越既有的边界,尝试团结其他贫民、草根与社区组织,并将国内外的手机生产者和消费者团结起来,从而为公民政治教育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11]。
首先,ICTs的发展加速了媒介产业中数字劳工的商品化进程,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这一过程是通过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和“再技能化”(re-skilling)实现的。何塞·阿尔贝托·加西亚-阿维莱斯(José Alberto García-Avilés)等学者在对英国和西班牙六家数字化新闻编辑室进行观察和访谈研究的基础上,强调随着数字化新闻运作方式的普及,新闻工作者需要不断生产大量新闻节目以满足24小时播报新闻节目的要求,因此他们所具有的包括调查能力在内的诸多“创造性”能力被“操作性”能力所取代。这一取代在导致新闻产品质量持续下降的同时,使新闻工作者彻底沦为高度依附于计算机的“鼠标猴”(mouse monkey)[17]。在这种“去技能化”和“再技能化”同时发生的过程中,不只是职业技能与技术角色的界限被模糊了,工作与闲暇、办公室与家庭之间的界限也被消解了。
研究对象为对旋轴流地面主要通风机,在风机或风硐上选择面积不同的断面Ⅰ—Ⅰ和断面Ⅱ—Ⅱ,断面Ⅱ—Ⅱ位于对旋轴流式主要通风机的一级电动机前,该位置处机壳上均匀布置有若干个静压孔和全压孔,断面Ⅰ—Ⅰ位于一级电动机之前,该位置处机壳上均匀布置有若干个静压孔,如图1所示。
传播政治经济学指向的劳动研究并不天然带有脑体之分,即“劳心”与“劳力”之间并不截然对立,这同样适用于对数字劳动的分析过程。有鉴于此,将包括制造苹果设备的富士康流水线工人在内的制造业中的产业工人纳入数字劳工的研究视野,正是将人类劳动作为一种整体来思考的有益实践,因为数字产品并不是脱离“生产后端”而单独存在的“技术前端”。同样地,新兴经济体在数字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日常装配智能手机部件到开发新的操作软件和应用系统。
选取2014年5月~2017年5月与我院接受尿道肉阜手术治疗的患者62例作为研究对象,均为女性患者,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31例,年龄25~75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
随着传播新科技的突飞猛进与媒介生态的变迁,大量媒体从业者积极或被动地卷入数字化进程,数字技术渗透到他们劳动过程、日常生活甚至抗争运动等方方面面。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的媒介数字劳工也无法摆脱资本的影响。
现任/北京和睦家医院骨科医生。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2004年经北京市卫生局认定为骨外科专科医生,于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对骨科学、包括脊柱外科学有着深入的研究。
产消合一者和玩工的原子化状态使其很难形成集体身份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劳动”,并为资本创造价值,更遑论组织起来成为自为状态下的劳动阶级[30]。新形式的用工关系往往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而富有活力,但这也导致了劳动者就业身份的模糊化,让他们通常被排除在与雇佣关系相连的保护范围之外[31]。因此,传统劳工组织与工会组织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形成团结(unionization)成为了它们亟待解决的难题。数字经济的产生一方面促使传统雇佣关系开始松动,另一方面建立在以往社会化大生产与标准雇佣关系之上的一整套劳工保护制度因为灵活而富有弹性的用工条件和劳动过程而变得支离破碎,与劳动相关的各类法律在面对数字技术发展而产生的这些新现象时已显得滞后且力不从心。
最后,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愈发呈现出不稳定的特征。约翰·兰特(John Lent)通过对美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电影业和图书出版业中的动漫创作者经年累月的民族志研究揭示出:跨国集团和财团推进的全球漫画产业的集中化和商业化一味追逐利润,并不强调漫画的艺术价值。为追求劳动力成本最小化,这些巨头采取了外包的策略,挑动全球劳动分工的变化,不仅使得美国很多漫画创作者失去了工作机会,而且使接受外包的漫画创作者面临诸多困境,导致劳动者“双输”的局面[19]。这些困境具体包括:动漫创作者对于自己创作的作品不享有所有权、酬劳微薄、工作紧张等。此外,他们因为政府的管制而不得不时刻进行自我审查,这使他们长期处于不安全和孤立的工作环境之中。
3.产消合一者和玩工
冯建三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由“计算机、互联网与手机等新技术条件所复苏、扩大或催生的参与、合作与分享的生产模式,固然蓬勃进行,唯这种有偿、无偿、志愿与非志愿的劳动,究竟是一种偏向让人产生赋权经验的‘参与’之旅,还是滑向资本增值的航道,从而遭到资本剥削的成分会浓厚些”[20]?实际情况是,新媒体平台的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的增长点,包括用户有意识地上传图片和视频,义务为网站进行宣传、翻译,甚至参加有偿或无偿的众包任务,这些都被用于生产新的可以被商品化的内容,或者成为商品化内容(如广告)的载体。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边界因数字技术而变得不再清晰。一方面,资本将个人的生活方式、欲望和知识等统统裹挟进工作之中[21];另一方面,工作与闲暇之间边界的消融恰恰对应了马克思笔下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转化为“实际吸纳”(real subsumption)的过程[8]。
资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资本对于文化和媒体的控制,即对传播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产品的控制,(使得)受众劳动的‘个体性’被不断整合到资本流通和积累的过程之中”[22]。从本质上来说,这个过程是对受众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夺,诚如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和纳森·尤根森(Nathan Jurgenson)所言,作为生产者的用户虽然被赋予使用生产性资源的权力,但他们所产生的利润和价值,或潜在的利润和价值都归属公司[23]。瑞泽尔对亚马逊(Amazon)的研究则更清晰地证明了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还承担了生产者的角色,因为他们自己在网上完成了从选购商品到取货的所有工作,但原本这些工作应该由亚马逊员工来完成,用户的能动性并未换来任何报酬,而他们留下的购买信息却成为大数据,继续进入生产循环[24]。可见,除了用户主动生成的内容,其“数字痕迹”同样也被“吸纳”到商品化过程之中,作为大数据挖掘的对象与算法推送的依据,包括网民的浏览和购买习惯、社交圈子、消费品位,以及其他人口学信息——使企业能够在掌握个人“信息地图”的基础上,更精准地进行研发、更有效地预测和引导市场消费,进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齐齐·帕帕科瑞希(Zizi Papacharissi)认为,“隐私已经成为奢侈品。”[25]以脸书(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极力推广信息“公开”与“分享”的理念,用户以牺牲自己隐私为代价换取基于社交媒体的社会交往与资源,他们为数字资本主义注入源源不断的“数据燃料”[26]。
尤里安·库克里奇(Julian Kuücklich)较早提出了“玩工”(playbour)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通过玩耍的形式,在其闲暇时间内创造价值的用户[27]。他通过对游戏模组爱好者的研究发现:他们除了每日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游戏中,还通过使用游戏开发者提供的或自己开发的各种编辑工具来打造专属自己的游戏。首先,“玩工”(即游戏模组爱好者)是游戏公司重要的创造力来源。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为游戏平台吸引了更多的用户,创造了更多的内容,甚至修改游戏中的漏洞以优化用户的体验。他们自发修改和创作的游戏内容成为了游戏产业价值和创新的重要源泉,他们的创造性极大降低了公司在研发和营销上的人力成本和其他费用。其次,“玩工”是无酬劳动力。一来游戏公司的现有制度并没有将模组爱好者纳入有保障的、稳定的劳动关系之中,其本质是对他们劳动的免费占有;二来游戏模组作为一种“无酬劳动”形式的事实往往被休闲娱乐的意识形态和修辞所遮蔽;三来模组游戏的知识产权牢牢控制在游戏公司而非玩家的手中,同时游戏模组爱好者承担着其活动可能引发的一切经济和法律风险。在现实生活中,游戏公司悄无声息地成为了最大的赢家。最后,将休闲活动“劳动化”的普遍实践标志着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即弹性积累模式,“玩工”的普遍化与之高度匹配[28]。游戏模组爱好者为资本积累贡献了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经远远超越了兴趣爱好的范畴,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游戏产业的生命线。这一模式正在全球不断扩张和蔓延[29]。
其次,媒介数字劳工成为“无酬劳工”(free labour)的趋势日益明显,他们被排除在有保障的、稳定的劳动关系之外。大量民族志研究发现,“无酬劳动”是目前资本主义数字经济中创造价值的关键,但在卡琳·法斯特(Karin Fast)看来,它却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脱胎于网络化的数字时代,而是受到包括奴隶、学徒、兴趣爱好者和志愿者等在内的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七种不同“无酬劳工”类型的影响[18]。“无酬劳工”正是迎合了资本降低生产成本,同时让劳动者而非企业承担风险的诉求。因此,“无酬劳动”剩余价值的积累过程也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相互建构和交织的复杂的历史的产物。
停工吹扫期间,轻油线的吹扫基本在4月11日至4月12日完成,为了在安全的前提下完成吹扫任务,采取以下较好的措施:
而在服务业中,知识性的生产因其不需要长距离的物质性迁徙,加速了离境外包(outsourcing)的普遍化,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大规模出现的呼叫中心就是其中的一例。这个过程与全球通信系统的使用密切相关,其运作成本也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降低。在贝弗里·西尔弗(Beverly Silver)等学者看来,这就是资本在面对强大工人运动时做出的普遍反应之一,“将生产转移到具有更为廉价和驯服劳动力的地点”,即资本的“空间调整”[12]。这种调整对于产品原生产地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而言,意味着工作岗位的骤减;同时,对于接受离境外包的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而言,也并非是一个好消息。恩达·布罗菲(Enda Brophy)发现,接受离境外包的呼叫中心的劳动者饱受低薪、高强度工作压力、不稳定的雇佣关系、僵化的管理体制、冷漠的工作环境以及无处不在的电子监控等问题的“折磨”。呼叫中心的劳动者是信息社会中关于工作的、更广阔的社会转型的缩影,这些转型包括大型企业的重组、外包的普遍化、工作中传播形式的强化,以及弹性雇佣实践的深化。他进一步强调,呼叫中心作为传播生产的隐蔽场所,完美地体现了20世纪最后十年间资本在追逐利润时所做的策略调整和风险转嫁。离开了这种传播劳动,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也就不复存在了[13]。虽然这些信息“灰领”的劳动工具是电脑和电话,其直接工作对象是内容、符号和信息,但他们在低工资、低福利状态下从事重复性劳动这一点上和制造业中的“蓝领”别无二致。
4.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
邱林川认为:“互联网是资本的场域、剥削劳工的场域,也是社会的场域、阶级形成和抵抗的场域。”[32] 那么,数字劳工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以集体组织的方式改变其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现状呢?在这个过程中,工会组织和政府可以发挥哪些积极的作用?例如,加拿大的新闻记者不断面临着大量不稳定的因素,包括因全职岗位减少而导致的自雇从业者规模的急速扩张、薪酬水平的停滞不前甚至持续下降,以及逐渐失去对新闻生产过程的控制等。为改变上述状况,尼科尔·科恩(Nichole Cohen)呼吁加拿大职业作家协会(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PWAC)和加拿大自由工作者工会(Canadian Freelance Union,CFU)在改善新闻记者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为他们提供交流平台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33]。与此同时,科恩本人也积极投身于加拿大作家组织(Canadian Writers Group,CWG)。该组织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家建立在代理机构—工会组织合作关系之上、代表自由雇佣的新闻记者权益的代理机构。它努力在加拿大出版商和作者之间建立连接和对话的机制,尤其是在合同与薪酬的协商等问题上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费鲁斯-科米罗以电子制造行业为例,通过对劳动者集体行动机遇和困境的讨论来探究劳工工会化的可能性。她发现,在全球电子制造行业中,工会化的程度非常低,且工会组织的运作缺乏制度性保障。因此,如果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希望有效地组织和代表工人,他们就必须与其他行动组织或社会运动建立广泛的联系,后者可能是非营利性、基于社区的实体组织(如高科技企业中的工会组织致力于联合学校、医院和政府机构中的每一位高科技电子产品消费者),也可能是应对某项具体议题的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环保运动等。此外,马奎拉团结网络(Maquila Solidarity Network)和IMB公司劳工抗争的经验表明,工人之间的个体联系和信息交换有益于冲破资方的信息封锁与掩盖真相的行为,同时更好地向劳动者展示行业内的一般工作条件,以便加速劳工联合的形成[34]。在迎接国际劳工组织100周年纪念日的全球对话论坛上,来自工会组织的代表充分肯定了工会组织是适应20世纪传统雇佣关系的、有效组织劳动者的工具,但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21世纪,因为工作和劳动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以往工会组织保护工人的方式已经略显过时,因此他们主张组织新的团体来保障不同行业中劳动者的权益,包括全球产业链上的工人、个体经营者,以及在数字经济(如媒介产业)中的从业者等。
以上四个领域的研究基本囊括了全球数字劳工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进路和最新成果。这些研究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厘清媒介组织与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力之间的勾连关系,深刻地揭示出数字资本积累和增殖的实质,考察劳动是如何在信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剥夺与异化,以及国家保护、社会福利和工作稳定性被解构与瓦解的过程。在方法论上,这些研究大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如民族志等,依托大量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微观的、切实可感的体察,探讨数字劳动领域的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阶级意识等一系列经典“老问题”究竟发生了何种“新变化”。将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不仅开拓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和方法,使它不囿于宏观层面的批判与宏大理论的生产,而且极大地弥补了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学研究的盲点。
三、中国语境:本土学者的思考与贡献
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的协同作用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同样面临数字劳工大量涌现的现状。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等所言,中国经历的是“压缩的现代化”,面临着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双重强制”的共时性困境[35]。也就是说,与西方社会所谓第三产业在吸纳就业方面已经超越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不同,中国仍有大量劳动力处于传统的农业和工业部门,从事体力劳动和物质生产。但与此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受过中、高等教育,集中在城市就业的青年人开始全面转向从事非物质的办公室知识劳动,而如前文所述,当代大部分知识劳动已经必须经由数字技术所中介才能实现,因此,即使不能说数字劳动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主要的劳动形式,劳动的“数字化”所带来的影响仍然是结构性的。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随着ICTs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这直接导致在信息产业部门或其他部门中从事信息处理与传播工作人员数量的上升,劳动的数字化与数字劳工规模的扩大,某种程度上已经追赶甚至超越了大部分发达国家。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推进,中国的数字产业已经与全球其他国家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如德温·温赛克(Dwayne Winseck)等发现,三大中国互联网公司(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在资本结构、所有权和控制权方面已经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三家总部位于美国的风投基金持有百度公司初始资本的近30%,其中最多的为德丰杰全球创业投资基金(Draper Fisher Jurvetson ePlanet)的15.6%,腾讯40%的股权由外国机构投资者持有,这个数字在阿里巴巴则高达47.4%[36]。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从数字劳工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语境出发,思考和探索中国的数字劳工问题是极其必要的。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传播劳动一直不是中国传播学界的主要议题,学术耕耘不足,规制劳资关系的现有法律也远远落后于数字劳动领域的实践,使中国数字劳工与传统体力劳动者面临着同样的,甚至更为恶劣的系统性风险,如劳动力商品化;技术变迁对工作场所的宰制;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如鼓励主动超常加班、知识技能迅速贬值、自我监督与残酷竞争、计件工资与淘汰制度);工作的不稳定性(如劳务派遣和弹性雇佣);社会福利的瓦解(如住房、医疗和教育的商品化所导致的脆弱的抗风险能力);以及孱弱的应对和抗争(与传统工人和农民颇为不同的是,知识劳工遇到劳动纠纷时往往采取辞职、换工作等个体化策略而非集体行动来解决问题,当然也有极少的例外)。在与网络平台的力量对比之间,数字劳工处于明显的劣势。此外,大量产生实际价值的“观看”和“玩乐”劳动尚未被视为劳动。
一部分中国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回应,为中国的数字劳工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如邱林川[37]、潘毅[38]、洪宇[39]等对ICTs制造业中数字劳工的研究,孙萍等对中国小型互联网公司IT程序员身份认同与传播实践的研究[40],曹晋[41]、姚建华[42][43]对中国出版产业中编辑人员的研究,刘昌德对中国台湾地区报业记者“去技能化”的研究[44],曹晋、张楠华[45]、胡绮珍[46]等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网络字幕组成员的研究,吴鼎铭对于本土网络视频众包生产的研究[47][48],张志华等对网络直播平台主播的研究[49],梁萌对平台经济中家政人员的研究[50],陈玉洁对滴滴司机的劳动与行动主义的研究[51],胡慧等对网络文学平台上网络作家群体的研究[52],贾文娟等对中国娱乐资本盘剥实习生的研究[53],以及赵月枝团队对缙云淘宝村的研究[54]。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他们的本土劳工研究根植于中国独有的丰富且充满活力的日常实践土壤之中,帮助劳动者发声,增加他们的曝光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术品格。另一方面,作为互联网大国,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是否应该为全球最大的网民群体支付红利?国家是否应该介入监管,改革数字生产资料(如数据、平台)的所有制,使其在一些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公有和“传播工地”的特色?这些问题都亟待本土学者进一步地探讨和研究。
逻辑推理能力是一种迅速掌握问题核心的能力,而鼓励学生自主归纳就是要锻炼学生独立的思维,使学生有意识进行自主学习、独立思考。所以,在小学数学基本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鼓励学生对教材所学的内容进行自主归纳,继而为学生形成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打好基础。
四、理论反思与未来研究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不难看到,中西方数字劳工研究者在劳动过程、劳动控制、抵制剥削和异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学理探索和对数字劳工进行理论化的进程却是永无止境的。当前研究仍存在局限和盲点,这些部分既是未来研究值得关注的,也是数字劳工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理论创新之可能的源泉。
首先,通过借鉴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的理论,未来数字劳工研究可以考虑转向政治—经济—文化联合分析的理论框架,将意识形态问题纳入研究视野,关注在数字劳工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生产同意是如何形成的,即“数字劳动版本”的“制造甘愿”(manufacturing consent)是如何运作的[55],不仅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出发,而且在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前提下展开政治经济分析,聚焦于数字劳工的“劳动”与生产政体(production regime)之间的互动关系[56]。这一思考路径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联合分析的理论框架尤其适用于创造性地阐释产消合一者与玩工是如何“心甘情愿”地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为新媒体产业贡献劳动成果的。其核心是召唤劳动者的主体性,关注他们的个人体验,以及探讨他们如何参与自我剥削和异化的过程[57]。
其次,未来数字劳工研究,特别是本土的研究还应尝试将考察范围扩大至生产场所之外的领域,将劳动者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过程作为整体来分析,如他们的地缘特征、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社会保障、后代哺育、老人赡养、社会关系,甚至情感生活等各种面向,即从“生产的政治”迈向“生产的政治”与“生活的政治”并重的理念。在工作场景之外,数字劳工并不直接受到资本和国家的控制,学校教育、同乡支持、社区生活都使他们得以突破狭隘的生产政体,意识到自身受到压迫的不合理性,进而“锻炼组织能力、建构团结网络”[58]。
山西省小浪底引黄工程土洞段施工Ⅶ标,盾构隧洞全长5.516 km,桩号为47+350—52+866,采用海瑞克制造的泥水平衡盾构,自大桩号向小桩号进行掘进,为国内最长泥水平衡盾构独头掘进施工隧道。本段隧洞多位于地下水位以下,自大桩号向小桩号逐渐升高,最大水头高度约105 m,最大埋深120 m,穿越地层为低液限粘土夹卵石混合土、级配不良砾(砂)层,地质条件对施工存在不利因素。
最后,未来数字劳工研究应注意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主体多样性,也就是说笼统的“劳工”一词很难精准描述实际上十分复杂的劳动者群体,男工/女工、移民/本地人、全职工/临时工/派遣工之间的差异非常巨大。在劳资关系与生产政治中,也并不只有阶级抗争和工人运动这一种抵制模式。保罗·约翰斯顿(Paul Johnston)提出,全球化时代的劳工运动强调劳动者在阶级立场以外的多元化的利益和身份,与公民权运动、性别平等运动等其他诉求的社会运动汇聚与合流,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改造社会的潜能,共同追求社会公共福利与公正的劳动和生活环境[59]。
参考文献:
[1]Schiller D. Digital Capitalism[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2]Sandoval M. Foxconned Labour as the Dark Side of the Information Age: Working Conditions at Apple’s Contract Manufacturers in China[J]. TripleC, 2015, 20(2): 1383-1399.
[3]Haralt M, Negri A.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M]. New York: Penguin, 2004.
[4]Scholz T.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M].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5]陈世华. 信息政治经济学批判[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47(3): 91-97.
[6]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 [M].胡春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179.
[7]格雷厄姆·默多克.导言[M]//姚建华,主编.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9.
[8]Manzerolle V. Mobilizing the Audience Commodity: Digital Labour in a Wireless World[J]. Ephemera, 2010, 10(4): 455-469.
[9]Rodino-Colocino M. Laboring under the Digital Divide[J]. New Media and Society, 2006, 8(3): 487-511.
[10]Braverman H.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11]Ferus-Comelo, A. “Free Bird: The New Precariat in India’s Mobile Manufacturing,” in Maxwell R.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ur and Media[M], London: Routledge, 2015: 119-129.
[12]贝弗里·西尔弗.劳工的力量 [M].张璐,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4.
[13]Brophy E. The Subterranean Stream: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Call Centre Labour[J]. Ephemera, 2010, 10(3/4): 470-483.
[14]Mosco V. Here Today, Outsourced Tomorrow: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J]. Javnost/The Public, 2005, 12(2): 39-55.
[15]Chan J, Pun N, Selden M. The Politics of Global Production: Apple, Foxconn and China’s New Working Class[J].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2013, 28(2): 100-115.
[1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M].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7]García-Avilés J, León B, Sanders K, et al. Journalists at Digital Television Newsrooms in Britain and Spain: Workflow and Multi-Skilling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J]. Journalism Studies, 2004, 5(1): 87-100.
[18]Fast K, Örnebring H, Karlsson M. Metaphors of Free Labor: A Typology of Unpaid Work in the Media Sector[J].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016, 38(7): 963-978.
[19]Lent J. The Global Cartooning Labour Force, Its Problems and Coping Mechanisms: The Travails of the Marginalised Cartoonist[J].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and Globalisation, 2010, 4(2): 160-172.
[20]冯建三. 从《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看文化与劳动的关系[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4(4): 56-63.
[21]Read J. The Micro-Politics of Capital: Marx and the Prehistory of the Present[M].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22]Nixon B.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Audience Labour’ in the Digital Era”[J]. TripleC, 2014, 12(2): 713-734.
[23]Ritzer G, Jurgenson N. Production, Consumption, Prosumption: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he Digital Prosumer[J].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2010, 10(1): 13-36.
[24]乔治·瑞泽尔.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消费圣殿的传承与变迁[M].罗建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25]Papacharissi Z. Privacy as a Luxury Commodity[J]. First Monday, 2010, 15(8). doi: http://dx.doi.org/10.5210/fm.v15i8.3075.
[26]Murdock G. “Political Economies as Moral Economies: Commodities, Gifts, and Public Goods,” in Wasko J, Murdock G and Sousa H (Eds.), The Handbook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M]. Oxford, UK: Wiley Blackwell, 2011: 13-40.
[27]Kücklich J. Precarious 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J]. Fibreculture, 2005, 5(1). http://five.fibreculturejournal.org/fcj-025-precarious-playbour-modders-and-the-digital-games-industry/.
[28]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38.
[29]Taylor N, Bergstrom K, Jenson J, et al. Alienated Playbour: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EVE Online[J]. Games and Culture, 2015, 10(4): 365-388.
[30]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The Future of Work We Want: A Global Dialogue”[EB/OL], April 6-7, 2017, http://www.ilo.org/global/topics/future-of-work/dialogue/lang--en/index.htm.
[31]袁文全, 徐新鹏. 共享经济视阈下隐蔽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制[J]. 政法论坛, 2018(1): 119-130.
[32]邱林川. 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J]. 社会, 2014, 34(4): 119-137.
[33]Cohen N. Negotiating Writers’ Rights: Freelance Cultural Labour and the Challenge of Organizing[J]. Just Labour, 2014(17/18): 119-138.
[34]Ferus-Comelo A. Paving the Path Toward the Unionization of High-Tech Sweatshops[J]. Trade Union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A Review by the Global Union Research Network,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07: 51-62.
[35]贝克, 邓正来, 沈国麟. 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J]. 社会学研究, 2010(5): 208-231.
[36]Jia L, Winseck 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Internet Companies: Financialization, Concentration, and Capitalization[J].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18, 80(1): 30-59.
[37]邱林川. 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J]. 开放时代, 2009(12): 128-139.
[38]Pun N, Chen J. Global Capital, the State, and Chinese Workers: The Foxconn Experience[J]. Modern China, 2012, 38(4): 383-410.
[39]Hong Y. Labor, Class Formation and China’s Informationized Poli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1.
[40]Sun P, Magasic M. Knowledge Workers, Identities, and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Understanding Code Farmers in China[J]. TripleC, 2016, 14(1): 312-332.
[41]曹晋. 知识女工与中国大陆出版集团的弹性雇佣制度改革[J]. 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 2012(4): 11-40.
[42]Yao J. Knowledge Work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M],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4.
[43]Yao J. Precarious Knowledge Workers in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A Study of Editors in the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J].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 2017, 3(1): 63-81.
[44]Liu C. Deskilling Effects on Journalists: ICTs and the Labour Process of Taiwanese Newspaper Reporters[J].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6, 31(3): 695-714.
[45]曹晋, 张楠华. 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2(5): 39-47.
[46]胡绮珍. 中国字幕组与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J]. 新闻学研究(中国台湾), 2009(101): 177-214.
[47]吴鼎铭. 网络“受众”的劳工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网络“受众”的产业地位研究[J]. 国际新闻界, 2017(6): 126-139.
[48]吴鼎铭. 作为劳动的传播:网络视频众包生产与传播的实证研究——以“PPS爱频道”为例[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8, 40(3): 56-63.
[49]张志华, 董欣佳. 劳动力商品化视角下的网络直播[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8(1): 121-129.
[50]梁萌. 强控制与弱契约: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17(5): 47-59.
[51]Chen J. Thrown under the Bus and Outrunning It! The Logic of Didi and Taxi Drivers’ Labour and Activism in the On-Demand Economy[J]. New Media and Society, 2017(6): 1-21.
[52]胡慧, 任焰. 制造梦想:平台经济下众包生产体制与大众知识劳工的弹性化劳动实践——以网络作家为例[J]. 开放时代, 2018(6): 178-195.
[53]贾文娟, 钟恺鸥. 另一种娱乐至死?——体验、幻象与综艺娱乐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劳动控制[J]. 社会学研究, 2018, 33(6):163-189+249.
[54]赵月枝. 中国与全球传播:新地球村的想象[J]. 国际传播, 2017(3): 28-37.
[55]Burawoy M.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56]田海舰,黄逸超.关于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论争[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60-64.
[57]Burawoy M.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M]. London: Verso Books, 1985: 10.
[58]汪建华. 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3.
[59]Johnston P. The Resurgence of Labor as Citizenship Movement in the New Labor Relations Environment[J]. Critical Sociology, 2000, 26(1/2): 139-160.
Global Digital Labour Studies and the Chinese Context :A Critical Review
YAO Jianhua, XU Sisu
Abstract : As the theories, research objects, methods and value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there are a few under-researched issues that have gradually emerged, to the attention of communication scholars. Among these issues, that of communication labour studies, for instance, has become a fertile area for academic research. With rapi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 trend readily distinguishable has been as much a digitalization of labour as technology users being turned into “labour”, and as a consequence, the digital labour has become the digital labour has become a latest analytic category, gradually serving the frontier of communication labour studies. In this context, the authors examine the four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gital labour studies: digital labour in th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industries, digital labour in the media industries, prosumers and playbours, and worker organization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y seek to facilitate the dialogue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scholars, who have likewise contributed to digital labour studies from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Finally, the authors critically examine possible weaknesses and blind spots of these scholarship, which would also be the source of academic growth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in digital labour research.
Key words :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digital labou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DOI: 10.19503/j.cnki. 1000-2529. 2019. 05. 017
基金项目: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校共建新媒体系列项目
作者简介: 姚建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上海 200433)
徐偲骕,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加拿大卡尔顿大学访问学者(上海 200433)
(责任编校:文晶)
标签:传播劳动论文; 数字劳工论文; 传播政治经济学论文; 信息与通信技术论文;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