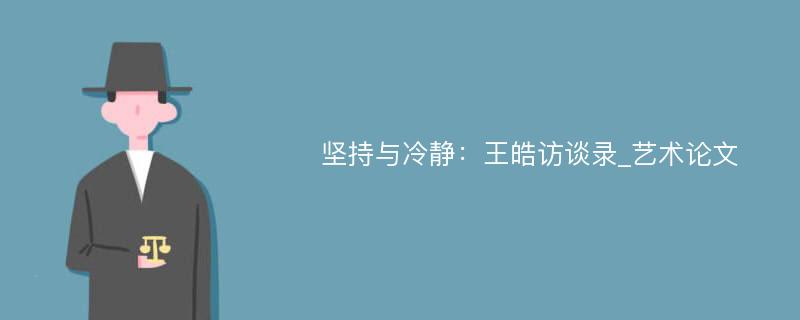
坚守与淡定——王好为导演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访谈录论文,导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杨远婴(以下简称杨):好为导演,在女导演中,也可以说在第四代导演中,你的创作时间是最长的了,从20世纪60年代初进摄制组,到现在还在拍片。
王好为(以下简称王):我最近拍了电视连续剧《徐悲鸿》,38集,自己写的,这是我多年以来的愿望。
杨:剧本是你自己写的?
王:原先还不是我弄的。1982年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写了本回忆录,当时我就看上了,想拍它,先后约了两个作家写剧本,一个是李準,一个是柯岩。我跑去跟廖静文先生说。可是我们厂另外一个导演也想拍它,她觉得很为难,最后谁都没给。退休后,我又想起这事来,开头还真找到一个人,写了个电影剧本提纲交给中影集团领导史东明,史东明觉得不理想,说能否改一改,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于是搁置下来。我无法向廖先生交代,就自己写了一稿。
杨:通过了吗?
王:经电影局认真审读并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可以筹拍。上面通过了,但投资很大、很难回收,当时电影形势很严峻。虽然有个剧本,还是没法弄成电影。由于素材非常多,我看了三百多万字,除了她的回忆录,还有前夫人蒋碧薇的回忆录,很多徐悲鸿学生、朋友的回忆录,所涉及的中外画家齐白石、张大千、吴作人、蒋兆和等人的传记,以及他的恩师康有为、蔡元培的传记。我就跟廖静文先生说,还是弄个电视剧吧,否则材料用不完,太可惜了。
杨:电影的篇幅只能选取人生的片段,选裁不好,人物就可能立不起来。
王:廖先生同意。我动手写了初稿28集后,就开始学打字,从拼音开始学起。
杨:专为《徐悲鸿》这部剧学习了电脑打字?
王:我的字写得很乱,请别人打我还要抄,打完我还得校两遍,想了想还是自己来吧。我以前不会打字,不会拼音,过去学的是国音字母,拨(音)、坡(音)、摸(音)、佛(音),于是我重新学了拼音。愣在那打字,结果打出了肩周炎、腱鞘炎。这个剧本我写了11稿。廖静文、李准、仲呈祥是顾问。
杨:从徐悲鸿的哪一段经历写起?
王:从青年时代——1915年他流落上海滩开始,一直写到解放后他逝世,但解放后这块写得比较虚了。
杨: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的故事也就接近尾声了。
王:也没那么尖锐的矛盾了。刚开始时是28集,我找投资找了一年半,谈了16家,台湾的、香港的、国内房地产的、证券公司的、省电视台的、民营的,刚开始都认可,后来都说不行,说商业性不强、娱乐性不够。最后河北省委宣传部想投资,他们的常务副部长想做文化名人系列,说他们可以投,我很高兴。可是还没投产,他又调到承德当书记去了,他一走这事就搁下了。他底下一民营公司接手,可是民营公司资金又不够,后来又吸收了别的公司的资金。
杨:那后来你又去找了其他投资?
王:后来不是我去的,资方去的。但是拍摄中间出现几次资金链断裂,没有按合同分期付组内人员酬金,全摄制组罢过一次工,所有道具都收了。几位主角罢演过几次。幸好最后拍完了,我和李晨声的酬金到现在还没付。
杨:你的演员是怎么选的?
王:吴刚演徐悲鸿,我看完《光荣的愤怒》就决定用他了,他是一位难得的性格演员。廖静文对他演的徐悲鸿非常认可,对薛白演的廖静文也非常满意。刘晓庆演蒋碧薇,演得真好,有深度。杨立新演的张道藩,葛存壮演的齐白石,薛中锐演的康有为,他们都很出色。
杨:这台演员还是很不错的。
王:选演员,最大的困难出在吴刚这里。我们想用他,他也非常愿意出演,但资方坚决不同意,说他知名度不够,影响销售和收视率。那时候吴刚演的《铁人》还正在拍,还没得“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呢。资方指定从六位当红的大腕明星中选,也不管演徐悲鸿合适不合适。我和资方一直较劲,最后他们只得听从我。拍完后,资方现在也服气了。
杨:你们的拍摄过程顺利吗?
王:还算顺利,2009年5月开始到年底就拍完了,我们把法国、德国的戏份都拍完了,还去了卢浮宫拍,拍完之后资金链又断裂,没法做后期。
杨:你们还去了卢浮宫?给了多长的时间?
王:在卢浮宫拍了整整一天。我们给文化部打报告,中国驻法使馆跟法方反复协商,法方说每星期二休馆,休馆那天就让我们去了。
杨:付钱了吗?
王:付钱。谈判时对方说,要是故事片就很昂贵,纪录片可以便宜些,这段戏没有任何情节和语言,就是徐悲鸿在卢浮宫巨大的艺术圣殿里屏息静气举目四望,无数大师的杰作使他目眩、惊异、折服得落泪。于是按纪录片收费,但是拍摄时每个馆都有法方的工作人员跟着我们。
杨:演员在卢浮宫时穿什么款式的服装?
王:这是他当年刚到法国求学时来卢浮宫参观,是1919年,穿的是西装,整整一天拍他观赏几十幅世界名画。后来在徐悲鸿的母校——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和柏林动物园等处又拍了不少他学习艺术的独特场面。这些也都是中国驻法、驻德使馆出面联系的。
杨:你自己对《徐悲鸿》这部剧如何评价?
王:比较满意。它真实地表现了徐悲鸿作为一代宗师的艺术道路、爱国情怀和感情生活的波折。
杨:从整体创作生涯看,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几部片子?
王:我比较喜欢的是《夕照街》、《哦,香雪》和《生死擂》,这几部影片在体裁上有点创新。《生死擂》比较成功地运用电影手法表现戏曲的诗、情、美,在戏曲电影的虚实结合上有新的突破。《夕照街》是个散文体的群戏,没有贯串的矛盾冲突,全凭生活的细节和真切的人物关系吸引观众,因此驾驭起来比较难。
杨:《夕照街》的线条和情调在当年很受赞扬。
王:汪洋厂长跟我说,你要是能拍好这个戏,你会长进一大截。它极难拍,人物众多、台词太多、几条矛盾线,又没有总的悬念。所以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锻炼。
杨:这部影片奠定了你的职业地位。
王:还有《哦,香雪》,太散文化了,太淡了,是清丽、自然、富有生活情趣的散文诗。
杨:《村路带我回家》也很散淡。
王:我觉得更散文化的是《哦,香雪》。《哦,香雪》比《村路带我回家》更难拍。因为《村路带我回家》毕竟还有几个人物的纠葛,《哦,香雪》就什么故事也没有,只是香雪们的生活片断,像一幅幅素描。
杨:选择诗意题材,要拍清雅的东西,那你是怎么解决“淡”处理的问题?
王:我刚开始时满腔热情,剧本铁凝给了我五年,我年年向厂里申请,北影厂都没让我拍,担心票房不行。整天在家摩拳擦掌。可当转到儿影厂真正要拍的时候,我心里又惶恐起来,因为很难把握它,并且剧本确实太短了。我当时请谢铁骊导演看,他说就能拍50分钟吧,问题是影片怎么着也得凑够90分钟。后来我给陈怀皑导演看,他觉得可以,还有水华导演,这三个人都是我的恩师,我经常请他们帮我把握剧本。我还找过李準,他一口认定这个本子好。铁凝跟我说,你要是觉得剧本篇幅不够,可以下去看看。由于美工一时来不了,我就跟李晨声在北京市远郊区跑了40天,开着车一个村一个村地筛,找山村、找山洞、找铁路隧道,那时候北京郊区已经很多红砖瓦房,找石头盖的房子很难。到深山里去,脱离了公路,进去之后才能找着,结果在十渡山里找着了我们要的场景,这个过程发现了很多的素材。
杨:什么样的素材?
王:是生活细节。比方说碰到他们晒花椒,山村都是石头房子,拿席子晒花椒,一张席子晒着黑的花椒籽,一张席子晒着红的花椒皮,像图案,非常入画,我们在影片中就安排凤娇和爹晒花椒。后来我看到老乡擀毡,大家都知道农村的炕上铺着大毡子,还有毡鞋垫,可是怎么弄成毡子我不知道。一看老乡擀毡简直是一出优美的舞蹈,把羊毛像弹棉花一样弹松,铺在苇箔的席子上,像棉絮做的被子一样铺匀了,接着洒上烧得很烫的水,把它卷起来,两个人坐那用绳子一勒一踹,踹结实了,愣把松散的羊毛压成那样,一人勒一人踹,很有舞蹈性,太好看了!我们就把这全套动作安排给剧中人去做。还看到老乡们窗外挂着一捆捆短的高粱秆,我问干什么的,他们说做擀面条、包饺子用的盖帘,还现场给我们演示。后来还看见村民家晾着许多杏核,原来是熬油用的,怎么弄的呢,把山里的苦杏仁核用石碾碾碎,然后放在柴锅里煮,油就浮出来了,最后拿勺子把上面一层油撇出来,这就是他们吃的油。这些素材都用上了。此外,还增加了许多细节。
杨:全是乡村生活的技巧,还有动作的美感。
王:表现山民自给自足的生活情状。
杨:这是在八几年啊?
王:1989年,深山仍是这种生活形态,我们在那里亲眼所见。这些细节不是点到为止的环境描写,而是本片重要的展开部分。影片就是要表现这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生存状态,火车一分钟的停车给山村投下工业文明的曙光。
杨:记得当时很多人称赞片子里铅笔盒的构思。
王:做铅笔盒是香雪爹自己刨啊、锯啊、画啊,一切都自己动手。这部影片的声画构成也追求田园诗的韵致。我在深山里,有时候从这个山坡望着那个山坡,突然哪家母鸡下蛋,全村的鸡都跟着叫起来,特别好听,真有一种礼赞的感觉。山里的声音非常丰富,小溪的流水声、牛叫啊、鸡叫啊、打石头啊、叫谁回家吃饭啊,特别有韵味。我们把这些都用到影片里,影片就是这样一步步发展过来的。表现如画的江山和几个天真纯洁的少女。
杨:《村路带我回家》和《哦,香雪》在当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王:但是有些人觉得《村路带我回家》里的那个女主角怎么就那么没有出息。
杨:生活中不常有这样的人吗?!
王:对啊,我就认识这样的人啊。
杨:和那种阳光、向上、积极的主旋律人物相比,这是一个灰色地带里的形象,但她是生活的大多数。许多评论都认为这个人物非常好,突破了常规,因为当时电影里缺少这样的形象。
王:在一群大有作为的知青中,就她一点作为都没有。慵懒、散淡、与世无争,但她善良、恬静、坦诚。她的美德,尤其她的弱点,构成独特的魅力,使人同情、怜爱、无可奈何。
杨:作为艺术形象,这个人物能留下来的,是人群中的这一个。
王:这个我也喜欢。《村路带我回家》我还追求一种忧郁的诗情。
杨:你拍过若干农村片,在当时很受赞扬。《迷人的乐队》表现农村的变革、写农民的精神状态,被看作是积极的主旋律电影;《村路带我回家》有知识分子的感怀;《哦,香雪》是抒情诗;还有《失信的村庄》、《能人于四》等。有一阵子,大家觉得你几乎是一个主旋律电影导演。
王:其实最主旋律的就《迷人的乐队》,后来的也就不太主旋律了。
杨:《迷人的乐队》好像中央还下过表彰文件?
王:对,他们很推崇这个。
杨:认为你反映了变革后农村和农民的新面貌。
王:这部影片虽然清新,充满欢乐,但比较浅。
杨:除了农村题材系列,你还有《瞧这一家子》、《潜网》、《夕照街》、《离婚》等都市题材系列,风格和农村片很不一样。我觉得你在每一部片子里都想尝试新的东西。你还拍过一个西部类型片《寻找魔鬼》。
王:当时你还批评我,我记得很清楚,你说仪式性不够。我跟李晨声说,远婴提的这个意见很重要。后来拍《生死擂》场面展示时我就特别注重仪式性。不过《寻找魔鬼》资金不够,该发挥的没发挥。那时我真实的动机除了尝试70毫米彩色宽银幕立体声的表现力,还有就是想沿着丝绸之路走一趟。
杨:真走了一趟?
王:真走了,对我来说那真是最大的审美享受。古丝绸之路的苍凉、肃杀、壮美常使我感动得落泪。
杨:80年代,你是不是一年拍一部影片?
王:几乎就是一年一部,而且《村路带我回家》和《金匾背后》是套拍的,当时厂里要求我套拍,因为等季节的时候,全班人马除了主演李羚没有参加,其他人又都在山西运城拍老作家西戎写的《金匾背后》了,拍完这个,又回到河北拍《村路带我回家》。
杨:你好像不追求风格的稳定性,并不专门拍某类题材或某种类型。这是你个人的选择还是当时实际条件的限定——碰到什么就拍什么?
王:有什么吃什么啊!但终归还得自己选择,我选择真正能打动我的,哪怕别人对它有些微词。我真正喜欢的,就一定会有一部分观众喜欢。
杨:《瞧这一家子》和《夕照街》之后,大伙觉得你能拍喜剧,可是你接下来又不拍喜剧了。
王:幽默的作品我喜欢,淡雅的抒情的,我同样喜欢。我愿意在样式、风格上做多方面尝试,只要本子确实能够打动我,与我天性接近的,使我有一种非拍不可的冲动的。
杨:你还拍过几部戏曲片?
王:《生死擂》和电视连续剧《武生泰斗》。
杨:“文革”结束后,电影界有个口号叫“和戏剧离婚”,你认不认同这种观念?
王:我觉得那得看题材,有的东西戏剧性很强的,那就不能失掉冲突和矛盾,戏剧那套创作方法不能丢掉。但是有些东西,我举个例子,比如《夕照街》,它就没有巨大的强烈的冲突,只是平凡的生活,但中间也透视出一些矛盾和变化。像《哦,香雪》更没有什么戏剧性,是散文诗。所以得根据题材而论。从某个意义上说,那时候有的电影舞台腔很重,表演、叙事上有很多人为的、夸张的东西,这在电影上是不太适合的。包括长镜头、短镜头的讨论,我就从来不爱参加,需要长就长,需要短就短。
杨:所以你很少参加那些纯理论的研讨会。
王:我不太感兴趣,我觉得要从实际出发,遇到什么样的题材用什么样的手法,把自己框到某一个流派反而作茧自缚。
杨:你是不喜欢标榜理论派别。
王:比如《村路带我回家》的镜头数就很少,镜头就比较长,因为它的舒缓长镜头和人物性格及忧郁的情调是契合的,要是乱切就不对了。《瞧这一家子》镜头就短,镜头数就多,因为它是喜剧的需要。形式技巧一定要和内容结合在一块。
二
杨:你们这一代学院派导演是否大都是贵族子弟?当年能进电影学院学习的名额很少。
王:也有很多平民子弟,很多复转军人,张华勋就是海军出身,我们班长原来是志愿军,我们班有几人来自工厂,我也不算是贵族子弟。
杨:你觉得当时的学校教育对片场实际操作有用吗?
王:不能说一点用都没有,也还是有用的。
杨:是不是当年的很多教师也未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
王:好多老师没有拍过电影。
杨:当时的课堂主要讲授什么内容?
王:从苏联莫斯科电影大学照搬,在我们上学的五六年苏联导演专家、表演专家、摄影专家在电影学院办过班,谢添、于洋、陈强、李文化等都在这儿学过。我们的老师也跟着听,或当过助教,把那一套都学过来了。
杨:当时的导演系主要有哪些课程?
王:课挺多的,导演课、表演课学三年,这是主课。小品得自己编,单人、多人、独幕剧,排这个我当导演你当演员,下次你排我当演员,互相帮忙。再就是写剧本,从短的到长的,一直到毕业实习剧本。还有就是语言技巧课。
杨:写台词还是念台词?
王:念台词,这也很重要,将来做导演要有这方面的能力去指导演员。形体动作课,虽然我平时形体动作不好,分还挺高,到课上我就正规地做动作,什么转身啊、起身、站啊、坐啊,各种各样的吧,是戏剧学院的形体课老师教我们。美术欣赏,中央美院的老师教美术史,名画分析。音乐欣赏、名曲欣赏,是音乐学院老师讲。王树薇老师教我们画速写,许之乔老师、余倩老师教文学作品分析,还有文学概论、语法修辞、政治经济学、哲学、俄语。
杨:还有外语课?
王:是个白俄老师。课程不少,压力最大的是导演课。
杨:导演专业课上学什么?
王:从表演到导演,得自己构思自己演。还有影片分析课。
杨:当时的影片分析课偏重技巧还是注重内容?
王:都有,从技巧讲的多点,看普多夫金的《母亲》、《成吉思汗的后代》、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罗马11时》等,这些都拿来分析。每次让同学们先谈观感,各抒己见,老师最后再点拨、总结。我们还有戏剧观摩,至今不忘的是裘盛戎演的京剧《姚期》、秦腔《火焰驹》和话剧《降龙伏虎》。有时还有名演员、名导演来讲座,白杨、陈怀皑、谢晋。谢晋、白杨在全校讲,陈怀皑在我们班上讲《青春之歌》。听这些名家的创作经验,对我们真是如聆佛音。还有体育课,我们倒没有声乐课,不像表演系。
杨:这些课程也还是有专业性的。
王:我觉得对于我们分析文学剧本、判断演员、指导演员还是有用的。还学新闻纪录片,韩建文老师讲的。纪录片实习,自报主题,拍了以后打分。剪辑也学,还让我们把《英雄虎胆》拆分开来,重新剪辑成一个个小主题。
杨:剪辑课还是挺有用的。
王:还学了照相摄影课,在室内打灯光拍,也拍外景照片。蒙太奇也教。中国电影史是全院上大课,程季华讲,还配合看电影。学的东西挺多,对以后的导演工作还是有用的,最欠缺的是老师的电影拍摄实践经验很少,除了个别老师有。学校教育只是打了些基础,提高了我们的艺术修养和鉴赏水平。
杨:老师没有片场实践?
王:没有,我们也没有实践,毕业作业班上就拍了两个短片,有一个短片是我写的,改编王汶石的《春节前后》,还有一个是张暖忻改的《白大姐》,全班18个人就分成两摊。
杨:就你们两个女将写了?
王:每个人都写。
杨:但只有你们俩的被选中了。
王:全班一半人在我这组,一半人在暖忻那组,这短片也就半个钟头吧。我那儿是李苒苒、程汉焜演的,徐孝先老师领着我们实习,他在北影厂做过副摄影,那就算有实践经验了。也就是你拍几个镜头我拍几个镜头。摄影系跟我们一块,也跟我们一样分成两拨。
杨:那就是说你们俩的本子统领全校的各个专业。
王:我们“58届”就招了导演系和摄影系,没有表演系,没有美术系,那时候文学系还没建。毕业作业的短片,美工由1959年建系的美术系老师担任,还在摄影棚搭了景。实践这部分完全是毕业后从厂里学的。在学院时没有条件,胶片很少,怎么把文学剧本最后变成电影,这个过程反而很缺乏。
杨:缺少导演工作整体过程的把握。
王:而且学的有些东西在创作上用处也不大,什么蒙太奇的前进式、后退式……后来我一分镜头,完全不是按这句式、句法来处理,得根据剧情啊,学校教育也有些教条的东西吧。
杨:老师没有实践经验就只能照本宣科。
王:只能照搬苏联教科书,那时候苏联库里肖夫的《电影导演基础》一大本,每人都拿着看。
杨:你毕业分配到北影厂后跟过哪几位前辈?
王:我开始是跟凌子风导演,1962年我毕业后就在第三创作集体,凌子风领导的,我就在他手下做场记。他正在拍《杨乃武与小白菜》,北京曲剧,我去正好赶上后期配对白,负责盯演员的口形准不准。唱腔是现场放声,事先录好的。还让我写宣传材料,说明书、介绍等等。后来又跟他的《阿里玛斯之歌》,描写蒙古族摔跤手的故事,台词少、注重画面造型。他当时看了新浪潮电影之后非常激动,要弄个创新的东西,看上了内蒙古作家敖德斯尔的作品,为此我还跟他们去内蒙古体验生活,分了镜头,选了演员。后因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夏衍要求改为抗日战争背景,这个民间传说将弄得不伦不类,凌导演只得罢手。然后又搞《詹天佑》,我从詹天佑的亲友那搜集了很多材料,包括相片、文章、书籍,当时想让孙道临演。
杨:孙道临也拍了个《詹天佑》。
王:那是多年后的事,他自己导演的。他当时正在北影厂拍《早春二月》,我们就去找他,他看了这些资料很高兴。但是后来上头说《詹天佑》怎么能搞呢?那是实业救国,咱得革命啊,光实业救国中国能有出路吗?结果《詹天佑》就半截夭折。这时又赶上1964年为国庆十五周年献礼,厂里叫凌导演去弄当代题材,与董克娜联合导演。
杨:《昆仑山上一棵草》?
王:是《远方青年》,领导说要加强力量,把它变成重点片,叫凌子风导演去当第一导演。我就跟着凌导演、董克娜导演在新疆拍了八个月,非常艰苦,那是我第一次完整地跟下来一部片子。这之后毛主席批示,文艺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批判了一些电影,比如《早春二月》等。北影厂搞了整风运动,创作集体就解散了。然后我又做了故事片《龙马精神》的副导演,李準编剧的。到了“文革”中期又调我去《海霞》剧组。
杨:于是你又跟了谢铁骊?
王:是。他主要是《海霞》编剧,他应该是导演,但他一直抽不出身来,他又拍样板戏,又是厂里第一把手。开头让凌子风导,凌导演弄了个“黑线回潮”,下马了。1974年又让钱江、陈怀皑加上我做导演,钱江还领着王兆麟和李晨声做摄影师,重组了《海霞》摄制组。《海霞》女主角戏实在不行,谢铁骊就自己从北京赶到福建执导。他排戏,我很注意看,他对演员也是启发式的,不做示范。结果他去了后也还是不行。拍女主角就只能多用背身和画外了。
杨:当年的样板戏到底谁拍得更好?“北谢”还是“南谢”?
王:《海港》谢晋拍过,后来谢铁骊重拍了。
杨:据说第一版的《海港》江青很看不上。
王:说来话长,江青看的双片在珠影厂放映,珠影厂多年都不生产了。“文革”中间,这放映机黑乎乎的,全是灰尘,放出来的画面就非常黯淡,江青很不满意,于是命令重拍《海港》。其实,影片在北影厂审查时,大家全鼓了掌的,很漂亮。如果真正到好的放映室不至于这样,毕竟是李文化拍的,不会太差,而且李文化也拍过《红色娘子军》。但是谁也不敢跟江青说,于是只好报废重拍。
杨:你没有参加样板戏电影的拍摄?
王:没有。
杨:为什么不让你们这些年轻的电影人去啊?当时不是倡导培养新生力量吗?
王:那不行,拍样板戏政治审查很严,我们这些修正主义苗子,一大堆把柄怎么会让我们去呢。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厂一个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交代听我说了江青什么,于是我被怀疑多年。
杨:你不知道自己被怀疑?
王:不知道。党组织生活我恢复得很晚,我很奇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军宣队就叫我交代,说那个人攻击江青的材料是听我讲的,我真不知道交代什么。我估计那人也是为了保护谁才咬我。
杨:你们这些社会主义学校培养出来的新人,没有旧社会痕迹,根正苗红,也逃不脱怀疑和整肃。
王:修正主义更严重啊,反“封资修”啊。
杨:“文革”标榜培养新人,可创作中又不用青年。
王:江青拍样板戏用的全是名导演,绝不让年轻人染指,比如谢铁骊、成荫等,都是老革命,业务上也独立当过导演多年。后来扩大了,用的又是崔嵬、谢晋、陈怀皑、武兆堤等。
杨:后来你去了《海霞》剧组?
王:我的嫌疑案可能他们也弄不下去,虽然她一口咬定我,我一直不承认,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交代不出来,所以后来也就让我恢复党组织生活。谢铁骊就把我调回来了,开始搞故事片。谢铁骊、钱江和我到浙江、福建、广东一带为《海霞》选景,体验生活。起初让我做《海霞》副导演,负责选演员,谢芳也回来了,让谢芳演。
杨:那太难为谢芳了。
王:对啊,谢芳岁数太大了,我们就选了蔡明演小海霞,吴海燕演大海霞。
杨:当年蔡明一出来大家就觉得好,灵气十足。
王:那时她小学四年级。凌子风来导演时,我还是副导演,到南澳岛拍的,当时已经1973年底了,海水都变黄了,而且照明灯也不够,样片很不理想,于是批凌导演“黑线回潮”,就停下来了。第二次拍《海霞》时跟陈怀皑导演倒是学得比较完整,从选景、选演员、分镜头、化妆、做计划,一直到现场拍摄、后期剪接、录音完成,陈怀皑老师那一套方法我都学过,这对我太重要了,他这方面经验丰富,修养比较深,很正规。我后来导演的所有片子,从剧本到分镜头再到样片直至剪辑,我都请他看,问他怎么样,哪儿好哪儿不好,怎么改进。
杨:而他也不厌其烦地赐教?
王:他对我特别好,他说年纪大了,拍不了多少片子了,就给你们做场外指导吧。我觉得我受他影响非常大。我自己并没有真正跟过水华导演,可是后来跟他关系也很好,我也请他看,他是我们厂的艺委会主任,像《村路带我回家》他就极喜欢。他建议我追求《走出非洲》那种情调,《哦,香雪》他当时不赞成我拍,片子拍完后他还说“好为给我上了一课,我没想到能拍出这样的效果”。
杨:他原来是否定的?
王:他觉得剧本太短、太淡了,影片他很喜欢,以至于他后来一直扶持我拍《荷花淀》,这也是我一直没有完成的夙愿。
杨:就是孙犁风格的东西。
王:我们请了几个编剧写这个东西,都不是那个味道,那种散文化的诗意出不来。
杨:看来这是你最心仪的格调。
王:我一直想弄这个,最后我就想到汪曾祺先生,我也不认识人家,愣到他家去,自报姓名,请汪先生帮我改编《荷花淀》。他说他没写过电影,我说你看过电影啊。他说他是南方人,我说这语言本来就不多,问题不大。谈的还比较投机,临别他送了我本书,我觉得有点谱了,他说那我还得看看,我就赶快把孙犁的短篇给他送去,他看完后选了七篇,《荷花淀》、《芦苇荡》等等,把几个人物考虑进去。改编期间,他生病,就常常电话联系,问我有什么想法。这时水华老师让我把孙犁的短篇、中篇、长篇全找来,他都看了一遍,他治学特严谨,我弄一个孙犁的短篇,他结果把中篇长篇都看了。他看完后,我告诉他选了哪些哪些,他说可以。他说在延安的时候,《解放日报》登了《荷花淀》,他看了就极其兴奋,才知道抗日战争可以这么写,不一定要正面来写。
杨:《荷花淀》在当时标志了风格化的表达方法。
王:剧本完稿后,我第一个就交给水华老师看,他看完当夜就给我打电话,说“太好了太好了”,他说“你拍出来是诗!是散文!是电影!”我当时也特别高兴。正赶上庆祝抗日战争胜利45周年,北影厂、河北厂、电影局、中宣部都同意拍,中宣部文艺局长李准来牵头。
杨:老李準?
王:不是,是小李准。河北省委宣传部长也来了,由河北厂出资来运作这个事,就差一百万,不够。因为它虽然很单纯,但是十多年前我就跟李晨声去白洋淀看过,那时船也不对了,桨也不对了,网也不对了,房子也不对了,全都不对了,所有都得重弄,跟《小兵张嘎》时还不一样,而且又牵涉到从荷花开到降大雪,拍摄周期太长。
杨:需要一年四季的景致。
王:就这,成本很高。但是要不把这些都表现出来,就没有那个味道。后来河北省委宣传部长非常着急,他说我给中宣部打报告,让他们资助一下。原来中宣部每年都有一部分资金,赞助他们认定的剧本,可那一年刚好丁关根部长改主意了,说不赞助了,你们拍好了我们再发奖金。
杨:那就是说不给拍摄投资。
王:后来河北省委宣传部长说“我们就缺这点钱,你能不能先给我们,如果我们得不了奖,我再退给你,成不成?”“不成。”又搁到那儿,一直搁到现在。我一个《徐悲鸿》搁了多少年,一个《荷花淀》搁了多少年。
杨:不能做电视剧吗?
王:电视剧不行,效果出不来。
杨:电影和电视剧在题材、形式、质感上都不同。
王:绝对不一样,尤其是宽银幕立体声电影,怎么能跟电视小屏幕单声道比呢,它的造型表现力、声音表现力绝对不一样,感觉完全不同。这个要不拍成宽银幕立体声电影就糟蹋了,电视小屏幕根本没法弄,味道全没了。到现在我庆幸《徐悲鸿》好歹弄出来了。
杨:是不是可以说对你有过专业提携的是四位第三代导演:凌子风、谢铁骊、陈怀皑、水华,其中陈怀皑的影响最大。
王:陈怀皑导演是制作方面,水华导演是另外方面在提升我。
杨:真正让你成才还是这些片场实践,学校教育只是给了你一个初步的电影概念?
王:对,知道了今后自学的方向。
杨:上学时你们看片子多吗?
王:多,每星期都看几次。
杨:都看到了哪些片子?
王:主要是苏联片、国产片,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有些片子也借来放。
杨:青年时代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些电影?
王:苏联片,还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片。我现在依然认为苏联片很好,苏联好多片子的美学价值绝对超过美国商业片。俄罗斯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的传统很深厚。意大利的文化也辉煌灿烂、博大精深。
杨:这也影响了你的创作,我看你的作品很讲究文学性,特别注意吸收文学里面的营养。
王:是,所以我觉得学那些电影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现在好多的好莱坞大片的价值高得多。
杨: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职业偶像,你的榜样是谁?
王:我倒没有专门瞄着哪个导演,我上学时比较喜欢苏联导演莱兹曼和贝利耶夫。
杨:那就是说你当时的电影模板是苏联片?
王:对。山田洋次的《远山的呼唤》我也很喜欢。山田洋次和山本萨夫访问中国时,“影协”给他们看了两部片子,一个是《归心似箭》,一个是《瞧这一家子》,在民族宫举行座谈。山田洋次拍过《寅次郎》,是位喜剧大师。当时我刚好看了他的《远山的呼唤》,看完后我激动得一夜没睡。座谈会上,山田洋次在肯定《瞧这一家子》之余,指出了不足,对我教益很大。第一,他说这片子里的照相师是个相声演员,应该换一个更老实的形象,效果会更好。第二,化妆不够自然,他认为现代戏甚至可以不化妆。影片中的女婿装了个假睫毛。我后来自己都觉得恶心,我当时怎么会这样。
杨:专注于社会写实的山田洋次对男性戴假睫毛肯定非常敏感。
王:老胡家的宿舍也搭大了,工人宿舍哪有那么大啊。山田洋次说:拍室内戏,即使搭景,也不必拆第四面墙,以免把房间拍大,镜头可以从门窗外打进来。
杨:他是强调空间真实感的重要性。
王:这几个方面他提醒了我。我在后来拍《夕照街》时基本不化妆,除了眉毛、胡子、发型做了些处理、有点变化,根本就不打底彩、不化妆,千万不能把千人千面弄成千人一面。在《夕照街》中,要求演员换上服装后,混在人群中要跳不出来,结果还比较真实、生动。我记得评论家钟惦棐说过,电影学院最难认的是表演系的,都长得浓眉、大眼、高鼻梁,太标准了。像其他系、像我们导演系,都长得并不漂亮,但各有特点。
杨:有特点才容易记住。
王:你看北京人艺的演员也没有特别漂亮的,可各有特点。《夕照街》选演员时,我就要求在身材上、面孔上、气质上一定要人各有貌,要不然二十多个人物全混为一谈了。后来我就很注意这些方面的问题。倒不是说永远都不打底彩不化妆,即使化也要很自然,有的人就根本不用化妆。
杨:这个原则现在你还保持着?
王:对一部分人保持着,有些演员有的人物需要化妆就化。
三
杨:这么多年的片场历练之后,你如何定义电影?在影像格调、情节结构、人物形象等方面你更注重哪个?
王:我觉得恐怕单是影像不行,应该是情节结构加影像,但中心还是人物。自《海霞》之后,我认为影片中,一切的关注点最后都落在人物上,演员要是不行一切全完。
杨:那就是说建组后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演员,演员选坏了就全完了。
王:现在很多明星我不认为是出色的演员,更不是表演艺术家,但是就被捧成了红星。拍片要找真正的好演员,而且要适合这个角色,倒不一定是明星。电影不像话剧,一个话剧剧本全国都可以上演。而拍电影只有一次机会,所以要力争找到最佳人选。所谓最佳人选,第一得是好演员,第二外形得合适,第三气质得相符。关于气质,我认为一般来说,演员的某些气质与人物相近才好。当然也有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是“千面人”。开拍后演员不能更换,导演不好厂长都可以把他撤了,包括摄影、美术所有工作人员都可以换,唯独演员没法替。
杨:中途换演员成本太高。
王:所以每次选演员我都跟押宝一样,特别紧张,都有如履薄冰的感觉,选对了就对了,选错了,你就是急死,再给他启发、示范也没用。
杨:好莱坞的明星制首先基于商业利益考虑。
王:它是观众买账啊,主要从受众的欢迎度来考虑,我是从创作者角度来说。
杨:所以贝拉·巴拉兹在电影诞生的初期就说电影是肖像学,演员那张脸错了影片的表意也就错了。
王:所有的创作,编、导、摄、录、美、化、服、道,最后都主要通过演员作用到观众的感受上,观众通过人物来认识这部影片。关于演员,我还有个看法,我觉得演员主要靠天赋。
杨:后天学不来的。
王:后天的方法也是需要的,但是首先必须是块璞才能琢成玉。像蔡明,当时只是个十岁的孩子,她能知道什么啊?她就这块料,她就行。后来我拍电视连续剧《第三军团》,剧中的中学生们我从全市高中和清华大学选出来的,也都没有任何表演训练,有这个素质就可以。我认为好演员能够比较深入地揣摩不同人物的心理、情感,通过自己的形体、表情、声音,可以很细腻、很生动、很准确地当众传达出来。有没有这种表达能力,区别就太大了。很多人能够体会得非常深,比他深刻得多,比他能说能写,但是不能成为演员。这种表现力,我认为主要靠天赋。我跟电影学院表演系老师说过多次,我说你们最大的功力在于能发现人才,然后再教他方法,方法也是要紧的,但要不是这块料绝对是白搭。这跟别的行当不一样,不是建立在知识上的,而是一种天赋。导演啊、摄影啊都有些知识素养来培育他。
杨:好演员看着就活灵活现。
王:我给你举个例子,《离婚》里面老李的孩子演得挺生动。刚开始副导演给我找了两个孩子,是培训班培训出来的,一拍,我就傻了,根本就不行。后来换了两个小孩,根本没上过训练班,很灵,演得很好。人家就是这块料。
杨:你当年怎么看上刘晓庆的,几部重要影片都找了她来演。
王:她当时正在厂里拍《小花》和《婚礼》,我在北影厂院里碰见她,觉得她形象挺好的,她过去拍过《同志感谢你》,演个街道清洁女工,我调了几本看了看,《小花》正在拍,我还没法看样片。我觉得她还行,就把剧本给她了,她也不知道让她演哪个,就跟我说,导演,我可不演那大正面,我说你指谁呀,她说就是戏里的姐姐嘉英,我说我没想让你演这个,我想让你演张岚,她说那我愿意。
杨:在专业上她是有个人诉求的。
王:她挺聪明,而且想拓宽戏路,她演《小花》、《婚礼》都是正面角色,何必再演个大正面呢。可是我对她了解就这么点儿。第一场戏就是她戴着发卷接待老胡他们,给她送裤子,敲门后她照照镜子,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她分寸感、节奏感、幽默感全有。关于喜剧演员,我也跟陈强老师认真请教过,除了其他一般演员的素质之外,第一要有幽默感。第二特别要有分寸感,喜剧的分寸比正剧的分寸还要难,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要不然这彩就出不来。第三,节奏感,节奏把握得准很重要。第四,就是形体的控制能力,这是陈强老师传给我的真经,我一直记着。我觉得晓庆这宝算押对了,我很惊喜。她确实非常用功,一共就那么几场戏,每个镜头她都十分珍惜,想法非常多,不满足于一般性地完成。
杨:她做事不怕吃苦,演戏用心。
王:她要是认真对待的角色,一定非常努力。她绝不满足于一般化地把台词念出来,跟对手做一般的交流,她一定要找到独特的表达。她为什么对我的戏念念不忘呢,她说得奖是一回事,李翰祥看上她演慈禧也是因为看了她演《瞧这一家子》,觉得她戏路很宽。
杨:这个演员的生命力是很强的。
王:她每天都打羽毛球,锻炼身体,吃东西都很注意。
杨:身体健康就会有好的工作状态。
王:能持之以恒不容易,这是她工作的本钱。而且她极其守时,出了名的。我们要到哪儿,她永远早于我到。她说我当然应该比导演早到啊,所有的片场她从来都只有早到,没有迟到。
杨:不迟到是很好的品质,不耽误集体的事。
王:还有一点,你看那《徐悲鸿》38集,台词那么多,我说晓庆你怎么背的啊,几乎一字不错。她说我还是分析它的逻辑啊,逻辑通我就很容易记住。
杨:但她的台词也常被批评。
王:台词原来不是她的强项,现在也有很大进步,传达出来的东西比较丰富、深刻。
四
杨:从1962年进摄制组到此刻的2013年,你经历了中国电影的数个重大变化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意识形态钳制、80年代的思想解放、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
王:市场化我倒没有经历太多,我退休了。
杨:但到处磕头要钱的拍片体验也有吧?对此你个人有什么感觉?
王:从导演的角度,我跟张暖忻交流过,她说还不如厂里掏钱给我们拍片,哪怕片酬低,生活差些。我感触最深的就是1985年到日本访问时,那时咱们国家还很穷,日本艺术家生活富有,但我从日本电影人言谈之中感觉到他们总为筹资操心、担忧。而我们在创作中是优越的。
杨:你是说80年代跟日本电影人相比?
王:站在我背后给予经济支持的是祖国。
杨:当时导演还无需商业考量,只需埋头创作。
王:我们都不用为集资、发行操心,我只需要想我的创作。我觉得“文革”之后,有一段时间状态还好,思想禁锢也打开了。
杨:你是指80年代?
王:就是80年代,也没有市场化之后在金钱方面的巨大压力。
杨:那时大家都憋着股劲,一心想出活,而且社会氛围也比较简单。
王:也让你想,也不限制你拍,在那个状态国产片有一批很好的作品,至今看来也是很好。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赶上完全市场化,2000年我满60岁退休了。
杨:可你又干了十来年,一直也没闲着。
王:那是业余的,比如《生死擂》是人家找我们拍。
杨:你退休以后活儿也没断。
王:《生死擂》就是退休后人家找我们的,然后是李晨声自己导演了几部片子。再后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徐悲鸿》。《徐悲鸿》也让我体会到市场化的制约,对我们来说挺严酷的。
杨:记得90年代电影厂企业化,创作条件很严酷,你们要给厂里交租子吧?
王:那个我觉得不难完成。我们要交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四百,包括工资、补贴,都得给厂里,它再发给你工资。但是只要我在外拍片我能交上这钱,这个压力不是很大。过去是政治上、思想上的制约,后来是金钱上的制约。金钱上的制约也很头疼,有很多想法就很难实现,好在我们早就退出江湖洗手不干了。我也不用为这些着那么大急,发那么大愁。
杨:你认为80年代制片厂时的创作状态最好?
王:对,思想又没那么多禁锢的时候。
杨:那是一个大家都热衷思想的年代。
王:对,而且倡导各种各样的流派和风格,那时候有这种空气,而且空气比较浓。
杨:大家喜欢凑在一起探讨新思潮,侃前卫艺术。
王:不管你是谈理论、谈创作,大家都挺钻研的,学术空气比较浓。
杨:大家的心思很单纯,没有经济概念,就是捉摸艺术那点事,想着怎么干得好干得有趣。
王:反正我是体会到思想禁锢和金钱对我们的压力,在这些压力下,创作自由谈不上。
杨:这个过程你是很完整地体验了。
王:是。
杨:你的个人特点是特别专注、特别顽强,不追赶时髦,但始终坚持创作,只要能拍片就马上去干活。
王:就干我自己喜欢干的事。
杨:那你最喜欢做的是什么事?
王:拍电影,看书,到处走走、看看。
杨:好多女导演都抱怨剧组里的性别歧视,觉得比男导演的工作难度更大,有些工种的师傅会欺负女导演。你对此有何感想?
王: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李晨声在身边。首先摄影不跟我捣乱,不仅不捣乱,他还从文学剧本就开始介入,想法都交流得很充分,都说摄影与导演就是夫妻关系。
杨:恰好你们就是夫妻关系。
王:这两者太密切了,如果摄影与导演打起来,拍摄就难以进行,我这点没有后顾之忧,他不仅介入非常早,而且不受时间限制,下了班回家继续讨论。我们俩美学趣味也比较接近,这个矛盾首先就没有了。而且我这个人也还比较严肃。
杨:不苟言笑,也不婆婆妈妈。
王:摄制组有好多人都说有点怕我。我今天跟你说话太多了,平时我话没那么多。
杨:我知道你平常话很少,这是否也有好处,太啰嗦会没有威严?
王:在剧组里我要求比较严。自己也还以身作则。虽然性格急躁,但对工作从来没有无理要求。
杨:你说话比较干脆,这是性格特点还是职业养成?
王:我就这样,从小就这个急脾气。但我从来不侮辱人格,组里最普通的人员我都很尊重。摄制组真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我虽然不太多说,但我跟底下这些人,挺哥们儿的话我也能说。
杨:关键时刻你也有点江湖气?
王:嗯。与大家关系还不错,我平时说话也不咬文嚼字,都直截了当。对他们,第一个还得尊重人家,严格要求。第二个我也不是什么大家,也不跟人摆架子。拍片这个事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多少行当在弄啊,而且行行出状元,想把片子拍好,脱离了谁都不行。
杨:现场发过火吗?
王:有的时候急了也嚷嚷几句,有时候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是某一部门出了问题,耽误了,很致命、很着急,那也就是急吧,但我从不侮辱人。
杨:今天我们谈了很多,一起吃个便饭?
王:不了,我还得回家做饭,我是我们家的钟点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