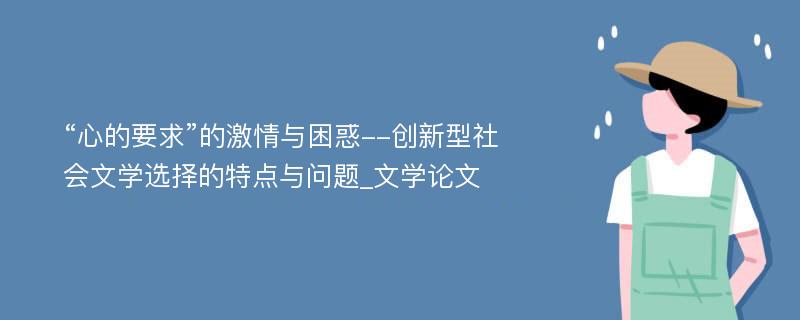
“本着内心的要求”的激情与困扰——创造社文学选择的特点与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扰论文,内心论文,激情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异军突起”于中国新文坛开始,创造社作家的文学姿态就给人留下躁动不安、甚至含混矛盾的印象,与此前的中国新文学作家尤其是同样有着留日经历的鲁迅一代产生了鲜明的反差,应该怎样来认识和理解这样的文学姿态呢?我认为必须从这些创造社同人自己的文学经验与思想逻辑中去寻找解释。
过去的文学研究总是笼统地将新文学运动前后的留日作家群体概括为放弃实业、转向“文学救国”的同一过程,殊不知在创造社作家的留日生涯中,文学之于他们的实际意义已经较鲁迅一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众所周知,鲁迅对文学的选择经历了一个“弃医从文”的理性的转折:“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①鲁迅这里所回顾的思想转变过程不仅充满了理性思考的深度,而且连表述本身也体现出了清晰的思想逻辑性。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开始于读书所激发出来的翻译的冲动,正如钱理群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周作人由读书的兴趣,进而激发起创造的冲动。”②这种不问世事、埋首书案的人生旨趣决定了他通过知识性阅读进入文学的基本方式,这一方式同样是理智的,虽然与鲁迅的思想苦索有所不同。
但是,到了创造社青年特别是更年轻一些的青年那里,留学的专业已经开始发生了改变,这就是由前一代的清一色的“实学”转向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或外语等文科,有的直接就选读了文学。如学英文的田汉,学哲学的郑伯奇,学社会学的朱镜我,学法国文学的穆木天,学德国文学的李初梨,冯乃超先后学过哲学、社会学、美学与美术史学,虽然创造社青年中的一些人依然与鲁迅一代人一样,都经过了一个由“实学”转向“文学”的过程,但是,对于许多创造社青年来说,这种转向更像是顺应自身本性要求的“感性的回归”。
郭沫若回忆说,“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被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这一个“逼”字道出了他内心的无奈与不甘。“自己本是爱好文学的人,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到日本去学习医科。日本人的教育方针是灌注主义,生拉活扯地把一些学识灌进学生的脑里。这在我又是一番苦痛。”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学医以后的外国语言学习,再一次唤醒了他压抑的文学热情:“这些语用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③
在东京帝国大学学经济的郁达夫对文学最初是业余爱好:“《沉沦》里的三篇小说,完全是游戏笔墨”,④不过,在“受了社会的许多暗箭明创,觉得自己所走的出路,只有这一条了”。⑤
在东京高等师范学英文的田汉早就明确了自己的文学方向,他告诉郭沫若:“我此后的生涯,或者属于多方面,但不出文艺批评家,剧曲家,画家,诗人几方面,我自小就有做画家的手腕,可是此调久不弹了,恐怕只能应用向文艺的描写方面去。”⑥
郑伯奇在东京学文科,在郭沫若、田汉的影响下,他的兴趣“却全被文学牵去了”,他自己也顺水推舟:“我想,我有这种倾向,不妨用几分力去做做。”⑦
创造社成立,有了“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之说,对此,郑伯奇说得好:“创造社也自称‘没有划一的主义’,并且说:‘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但是接着就表明:‘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这,‘内心的要求’一语,固然不必强作穿凿的解释;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完全忽视。这淡淡的一句话中,多少透露了这一群作家对于创作的态度。”⑧准确地说,这里“内心的要求”并不是指理性的思想探索,而是来自本能、裹挟着欲望、饱蘸着激情的追求倾向。
本着“内心的要求”,创造社青年满怀感情地拥抱着文学,伊藤虎丸借用日本社会的代际分类,将他们比作大正时期的“文学青年”群体,可以说是比较准确的概括。
此外,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创造社这一代之前,虽然梁启超、鲁迅等几代中国学人都深受了日本文学与日本的西方文学的影响,不过,他们在总体上与日本文学本身乃至世界文学潮流本身关系却不明确,特别是就鲁迅这样“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⑨的人来说,其文学世界的建构似乎始终是按照自己内在的社会文化理想模式进行,文学是被纳入其中的,无论是梁启超关注的“政治小说”还是鲁迅、周作人关心的“弱小民族文学”,这都是他们更为宏大的社会文化关怀的组成部分。外来的文学现象似乎并不能撼动他们各自的“人生”追索的整体计划。
就如同青春的郭沫若、郁达夫们在自己的人生欲望萌发期就陷入了资本主义蒸腾上升的种种诱惑一样,这些中国的“文学青年”也恰逢其时地遭遇了日本近代文学蓬勃发展的高潮期,“日本社会近代转型期的开始在明治维新,但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真正成熟却是到了明治末年至郭沫若他们留学的大正时期。这是日本近代文学突飞猛进,甚至让人眼花缭乱的发展时期。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流派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又登场,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欧洲文坛百多年的历史演绎了一遍。”⑩到他们倾情投入文学的浪潮时候,我们可以相当容易地在他们各自的身上辨认出日本文学密切相关的文学精神与具体的师法对象。从总体上,创造社青年从留日体验中获得的文学起步也是相当清晰的,这就是以融合了日本式自然主义与新浪漫主义艺术的自我表现与情绪抒发的文学。有别于法国自然主义的客观、冷静,所谓日本式的自然主义就是包含了明显的主观色彩与自我精神写照,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等人的自传性小说,就与源于日本自然主义的“私小说”颇多一致;在“新浪漫主义”(唯美主义)方面,则可以找到郁达夫、郭沫若、陶晶孙、田汉等人之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的袭取。关于中日文学这方面的联系,历来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作了相当丰富的揭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们不妨可以观察比较两代中国留学生对厨川白村的不同接受。
厨川白村(1880~1923)是日本大正年间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文艺理论家。虽然,“作为一个理论家,他的文艺理论著作的价值也没有得到日本文学理论批评史家的普遍认可”(11),但无疑是对现代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重要的外国文艺理论家之一,更是鲁迅、周作人与郭沫若几代(到后来还有胡风)留日学生崇拜的对象,构成了中国新文学作家“日本体验”的重要内容。
厨川白村代表作《苦闷的象征》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立普斯的移情说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整合起来,作为对包括文学在内的创造活动的解释。文艺的本质被他认为是生命力在绝对自由心境上的创造活动;而苦闷是文艺创作的心理动力;文艺的表现法则是广义的象征主义。这些言说对中国青年来说不仅别开生面,而且其中的关键词如“生命”、“自由”、“苦闷”更是与他们留日时期的人生体验与求索不谋而合。这是厨川白村进入几代留日中国作家精神需要的基本原因。
中国文学界对厨川白村的注意是比较早的。早在“五四”时期,厨川白村的文章就被翻译了过来。朱希祖所译的《文艺的进化》发表于1919年11月《新青年》6卷6号,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关于厨川白村文艺理论的最早译文。文章译自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第九讲。接着,罗迪先译《近代文学十讲》由上海学术研究会于1921年2月出版,这是厨川白村专著的最早中译本。另一部著作《文艺思潮论》最早由汪馥泉全文翻译,连载于1922年2月至3月的《民国旧报·觉悟》,樊仲云的译文也连载于1923年12月至1924年5月的《文学周报》,后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1924年12月出版。
《苦闷的象征》是厨川白村罹难后的1924年2月才由日本改造社正式出版的,不过在厨川白村生前,该书前两部分就由《改造》杂志刊出。中国早在1921年就有明权译出过其中的《创作论》、《鉴赏论》两章,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1924年又有樊仲云翻译的部分章节分别发表在《文学周报》及《东方杂志》上,接着便先后出版了鲁迅与丰子恺的全译本。
鲁迅、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就读到过厨川白村的著作,鲁迅日记记载,鲁迅早在1913年8月8日即已邮购到了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在1917年11月2日还得到了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潮论》。周作人的日记表明,他至少在1917年就接触了厨川白村的著作。同样,早在留学期间,创造社一代在留日期间就阅读了厨川白村,甚至还有过直接的交往。郁达夫、田汉、郑伯奇、曾于1920年拜访过厨川白村,并与之讨论文学问题,郭沫若1922年8月直接宣称“文艺是苦闷的象征”,(12)1923年又如此告白:“我郭沫若所信奉的文学定义是:‘文学是苦闷的象征。'”(13)郑伯奇1923年指出“文学,是太平的精华”的思想已经过时了,苦闷才是现代文学的原动力。(14)“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这是现代文学的标语。郁达夫则称自己的创作“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15)
两代中国留日学生对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体验”都离不开他们主体的基本情况。鲁迅、周作人的人生阅历决定了他们对厨川白村的理解往往与他们其他的人生经验与思想经验联系在一起。在周作人的温和稳定的中年心态中,厨川白村思想主要价值体现在他对一些文艺问题的具体观点与论述上,是作为在日本的周作人广泛的知识吸纳的一个部分发挥自身影响的。例如厨川白村对小品文essay的界说,“灵肉一致”的理想人性说,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契合说等等,都成为了周作人形成自己“人的文学”主张的思想资源,不过,对于整个中国文学界影响甚巨的“苦闷的象征”理论,周作人却有意无意地加以了改造和简化,他仅仅从中抽取了文艺表现人的情感这一当然的意向,而回避了“苦闷”这一表述的核心。(16)与性格平和软弱的周作人不同,从来都敢于直面人生的鲁迅自然不会将厨川白村这样的外来思想资源仅仅当作冷静的“知识”,他的忧患意识也使他主要为其中关于生命“苦闷”的阐发所打动,并自觉融化为自身创作的一些因素。鲁迅《野草》创作于1924至1926年间。一般认为明显体现了鲁迅内部精神世界,反映了厨川白村生命的苦闷观与文学的象征观,不过,严格说来,鲁迅无意在自己的作品中刻意倾诉他所遭遇种种的“苦闷”本身,而是透过苦闷引发的关于生命奥秘的更深的思考,这似乎刚好与“自我表现”的创造社文学有着重大的差别。
郭沫若曾经有过一首诗歌《死的诱惑》:
我有一把小刀
依在窗边向我笑。
她向我笑道:
沫若,你别用心焦!
你快来亲我的嘴儿,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
这是表现自我的生的苦闷,据说,此诗还得到了厨川白村本人的赞赏。(17)不过,久久沉浸于苦闷中的鲁迅似乎就不止于这样的倾诉了。他力图要在不断的追问中告诉我们,即便死亡又怎么样?苦闷与烦恼真的会因为死亡的降临而烟消云散了吗?在鲁迅式的逼问中,我们发现,死后的世界依然如此的糟糕,毫无解脱可言。什么“自从踏遍涅槃路,了知生死本来空”、“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死后原知万事空”之类都不过是人们的幻想而已。鲁迅写道:
但是,大约是一个蚂蚁,在我的脊梁上爬着,痒痒的。我一点也不能动,已经没有除去他的能力了;倘在平时,只将身子一扭,就能使他退避。而且,大腿上又爬着一个哩!你们是做什么的?虫豸!?
事情可更坏了:嗡的一声,就有一个青蝇停在我的颧骨上,走了几步,又一飞,开口便舐我的鼻尖。我懊恼地想:足下,我不是什么伟人,你无须到我身上来寻做论的材料……。但是不能说出来。他却从鼻尖跑下,又用冷舌头来舐我的嘴唇了,不知道可是表示亲爱。还有几个则聚在眉毛上,跨一步,我的毛根就一摇。实在使我烦厌得不堪,——不堪之至。(18)
生命不仅没有获得梦寐以求的解脱与自由,恰恰相反,倒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无力和尴尬了!“死后”的世界也并不是我们幻想中的极乐世界,它依然是现实人生的继续,这里依然有麻木的看客,有现实秩序的捍卫者,有蝇营狗苟却故作高雅的人们,也有贪得无厌的势利之徒,它不过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铁屋子的一种延续。在这里,死亡根本就无法起到阻断两个世界的作用,我们现实世界所建立的秩序是这样的强大,它一直延伸到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与每一种形式当中,而且更为糟糕的是我们自己却完全丧失了起码的自卫能力!
鲁迅以“死”观“生”的彻底足以让每一个能够诉说青春期苦闷的人感到惊叹。
在鲁迅这里,我们读到的是意志性的精神力对生命多层次意义的穿透,是自我的思想的力量。鲁迅思想世界中形成已久的意志性力量参与了厨川白村的理解和接受,后来,鲁迅又翻译了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继续推介厨川白村进行文明批评的战斗精神,并引为自己的文学追求的助力。相应地,我们在创造社文学中,主要读到的是其对苦闷的多方位的描写和展现,和由此获得的能够表现苦闷的勇气与自由。如果说鲁迅更看重厨川白村对“生命”的重视和文学的可能的“象征”意义,那么创造社则更多领悟了他的“苦闷”、颓废与自由。
从梁启超到鲁迅、周作人,对外来文学领悟和借鉴的问题常常是表现为一个“思想启蒙”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学的内容与意义是主要关心的对象。到了创造社青年这里,日本式的自然主义与新浪漫主义除了内容上的吸引外,常常都涉及其意象、情调、语言、风格等等所谓的“艺术”问题,尤其是像新浪漫主义,更将艺术独立的问题提到了一个至高点上,这都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于“艺术”的期许和对自我的评价。郭沫若断然宣布:“我对于艺术上的功利主义的动机说,是不承认他有成立的可能性的。”(19)郑伯奇提出:“在艺术的王国,我们应该是艺术至上主义的信徒。就艺术的王国的市民看来,艺术是绝对的,超越一切的。把艺术看做一种工具,这明明是艺术王国的叛徒。”(20)成仿吾表示:“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Beauty)与美(Perfection),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21)
比起鲁迅等前一代的文学追求来说,这些才华横溢的青年人更愿意突出自己的艺术修养与艺术趣味,不愿再将自己简单蜷缩在什么“人生”的陈旧话题当中,以至在后来与文学研究会的抗衡中,“为艺术”竟有意无意地成了“为人生”之外的重要表述。
这里涉及到一个有意思的分类,即“为人生”与“为艺术”。应该说,一定要在“为人生”与“为艺术”之间做出一个分别,肯定是一种极其简单的归类原则。因为,虽然对艺术本身如此钟情,但是创造社青年的作品无一不是他们人生生动的写照,所谓“为艺术”从来就没有成为“为了艺术而艺术”。郁达夫的留日系列小说就是他孤独无助的日本生活的自传,郭沫若的早期小说基本也是其生存状态的生动描写,其男女主人公从形象、性格到生活故事都直接取材于他与安娜的实际。《鼠灾》里写方平甫家庭关系:“平甫的女人和他是一个绝妙的对照。平甫的擅长是‘燕瘦’,他女人的却是‘环肥’。他女人全体印象是男性的,大陆的,女丈夫的。”《残春》、《漂流三部曲》、《行路难》与《圣者》中爱牟的身世是:四川人,有日本夫人,家住博多湾,医科大学生,十一年没有回家看望父母,心中满怀惭愧,其中对“笔立山”的描写更与诗人自己诗歌一般,也曾经暂回上海艰难度日,《未央》中主人公“的两耳,自从十七岁时患过一场重症伤寒以来,便得下了慢性中耳加答儿,常常为耳鸣重听所苦,如今将近十年,更觉得有将要成为聋聩的倾向了。”甚至也有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五岁,小的名“佛儿”。《喀尔美萝姑娘》中那位“工科大学生”的妻子瑞华“是那样一位能够耐苦的女性,她没有我也尽能开出一条血路把儿女养成,有我恐怕反转是她的赘累呢。我对于她是只有礼赞的念头,就如象我礼赞圣母玛丽亚一样。”这分明就是郭沫若现实人生的“实写”!
同样,鲁迅一代依然对文学艺术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那种以“功利主义”论述之的观点显然是过于简单了。《摩罗诗力说》早就指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22)人永远无法完全杜绝目标性的考虑,但是,是不是一切带有目标性的选择都可以被称作是“功利主义”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现代文化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一样,由于我们始终缺少一个“思想的平台”,因而在一系列的基本概念的使用上形成了纠缠不清的缠绕,以至往往让我们的学术讨论难以有效地进行下去,一些学术意见的分歧也变得似是而非,暧昧不清了,最终失去了“分歧”本身所带有的思想的力量。今天的学术研究要真正有所推进,就有必要从学理上进行新的考源、辨析,重新清理各自真正的立场与含义。在学理上,“功利主义”系与“伦理学说”区别而言,前者只关心效果,而后者只关心“动机”。(23)或者说,“功利主义”是指没有自己的对正在实施的对象的独立意义的认同,而只是将这一对象用作其他目的的过程和手段。对文学艺术的功利主义指的就是并没有对于文学本身的关怀和兴趣,而只是利用文学的力量达到其他的目的;但是,这与一个人是否也认为文学具有某些现实功能,对文学的追求中有助于其他现实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混淆这两者的差异,我们就无法真正鉴别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艺术追求的差异,也无法知道一个处于人生涡流中的个体究竟有着怎样不同的文学的趣味。
创造社青年与鲁迅一代同样都存在“为人生”与“为艺术”的需求,在我看来,关键在他们各自的心目中,人生——艺术的“结构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在鲁迅一代,“人生”意义的郑重提出便在于现实中国的人生模式与它背后的社会模式一样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需要改造和重建。因而“为人生”实质便是“重建新的人生”,文学本身就是整体的人生现象之一,它也自然要被纳入这一整体结构中来加以重新的认识;又因为整体的人生都在重建当中,所以我们需要的文学也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也应该随着我们对人生的重建而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不断再阐释和再结构,——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一种既有的文学现象,无论是中国古典的还是西方最流行最时尚的,都不可能“原样”进入到我们正在重建的人生需要当中,西方文学的优势不是天然的和绝对的,只有它们切合了中国新的人生建设的旋律才有价值。
对于创造社青年而言,“人生”当然同样是最不能回避的现实,不过,与鲁迅一代的不同在于,他们的“人生”首先不是等待“改造”与“重建”的对象,而是他们自我实现的一个场所或程序,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需要调动许多的力量,其中文学艺术的力量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郑伯奇说过:“‘自我完成’是一个人一生最终的目的,譬如人类最终的目的是‘至善’一样。”(24)郁达夫提出:“我本来原自知不能在艺术的王国里,留恋须臾,然而恶人的世界,塞尽了我的去路,有名的伟人,有钱的富者,和美貌的女郎,结了三角同盟,摈我弃我,使我不得不在空想的楼阁里寄我的残生。”(25)张资平直截了当:“在青年期的声誉欲,智识欲,和情欲的混合点上面的产物,即是我们的文学创作。”(26)
在这种需要下,文学艺术也就不存在一个“被重建”、“再结构”的问题了,一切中外的文学艺术追求都可以成为“自我实现”的助力,而文学领悟的迅捷与高效往往也被认为是“自我”超越他人与凡俗的重要表现,因此对于文学潮流特别是外来文学新潮的追随也时常能够显示出一种特别的意义。这里似乎还出现了一个别有意味的悖论:就创造社青年的力图超越凡俗的意愿来说,他们不屑与充满功利主义的世俗为伍,他们需要竭力突出自己在文学艺术上的纯正性,(27)在艺术的才华方面,也的确常常体现出自己足以傲人的一面,然而,当所有这些“为艺术”都最终被纳入到“自我实现”的坚定目标当中的时候,我们却一点也不能忽视其中所存在的功利性的因素,而且有意思的还在于,与鲁迅一代比较,这种功利性因素似乎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创造社从前期到后期,从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到无产阶级文学,如此巨大转折的内在逻辑性恐怕也就在此了。
从“艺术至上”的理想到现实目标的功利,在创造社文学这里形成了值得注意的强烈反差。这种情形的出现在一方面说可以认为正是中国学人在接受外来影响之时依然保持自我“主体性”的例证,是留日作家不是被动“模仿”西方文学而是主动“体验”异域经验的证明,——这一特点,连日本学者也觉察到了。伊藤虎丸认为:“像《沉沦》那样的作品,如果出现在日本文学中,终归不能列入为佐藤春夫称为‘艺术派’那样含义的‘艺术派’中去,也就是说,像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如果出现在日本文学中,与其称之为‘艺术派’,不如称为‘社会派’。”“创造社文学运动在小说方面的最初成果是郁达夫的《沉沦》(1921)。我认为,这篇小说是在当时的新进作家佐藤春夫的出世作《田园的忧郁》(1918)的影响下写出来的,两者确实有共通的地方,如作品的结构和小说的手法,共同受到‘世纪末的颓废’的影响。但是,《田园的忧郁》所描写的是‘世纪末的倦怠’,如前面所说过的那样,是第一次大战前后,日本资本主义出现的经济繁荣的反映;而在《沉沦》中,郁达夫所描写的乃是‘世纪末的颓废’,但那其实是青年人性的苦闷的告白,同时也是对于日本人的轻视而说出的留学青年的悲愤,和对于祖国富强的切盼。”(28)
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一强烈的反差又生动地反映出了创造社青年一代由自我实现欲求所冲击裹挟下的精神世界的某些紧张与困扰。作为创造社一代青年自我实现的强烈渴望,留日时期的生活与事业的桎梏往往带来了他们情绪上高度的焦虑和不安,这最终又转化为他们对于文学艺术的姿态上:一种充满矛盾的文学艺术追求。我们阅读那样的文论与表述,常常能够读出其中的自我矛盾来,即使那些主张艺术至上的意见,也常常出现另外的声音。郭沫若在1922年《时事新报·学灯》发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时一面批评“艺术上的功利主义动机”,一面却认为艺术“它是唤醒社会的警钟,它是招返迷羊的圣箓,它是澄清河浊的阿胶,它是鼓舞革命的醍醐,它的大用,说不尽,说不尽。”后来将文章收集时,又进行较大的修改,进一步突出了对文学功利作用的肯定。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既要“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又要总结出“新文学的使命”:“新文学,至少应当有以下三种使命:1.对于时代的使命,2.对于国语的使命,3.文学本身的使命。”“我们的时代已经被虚伪、罪孽与丑恶充斥了!生命已经在浊气之中窒息了,打破这现状是新文学家的天职!”茅盾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如郭沫若‘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成仿吾两篇文章都是以后半篇反对前半篇的;前半篇宣扬功利主义的文艺观,后半篇则从纯艺术、有时是纯美的观点反对亦即取消了前半篇的论点。”(29)到30年代中期,早已经“左转”的郑伯奇干脆也说:“真正的艺术至上主义者是忘记了一切时代的社会的关心而笼居在‘象牙之塔’里面,从事艺术生活的人们。创造社的作家,谁都没有这样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成仿吾的批评,以及其他诸人的作品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和社会的热烈的关心。所谓‘象牙之塔’一点没有给他们准备着。他们依然是在社会的桎梏之下呻吟着的‘时代儿’。”(30)以当年的“一面”清洗掉当年的“另一面”,实在也是“时代的需要”了!
自我矛盾的出现在本质上来自内心深处对多种人生艺术可能的感受、理解与设想,他们似乎很难决定自己的割舍,或者在这个“污浊、混沌”的世界上,一时无法判断人生艺术选择的结果,最终只能发出多重指向的声音。刚刚走上文坛的时候,郭沫若就曾引用歌德的话对宗白华表白,自己是“真理要探讨,梦境也要追寻。理智要扩充,直觉也不忍放弃。”(31)他也对田汉说:“我的灵魂久困在自由与责任两者中间,有时歌颂海洋,有时又赞美大地;我的久未在Idea和Reality寻出个调和的路径来,我今后的事业,也就认定着这两种的调和上努力建设去了。”(32)《创造十年》中,他描述自己“实在是有些躁性狂的征候”,还借剧作《湘累》中的话“夫子自道”:“‘从早起来,我的脑袋便成了一个灶头;我的眼耳口鼻就好像一些烟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烟雾,飞起火星,我的耳孔里还烘烘地只听见火在叫;灶下挂着一个土瓶——我的心脏——里面的血水沸腾着好像干了的一般,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在当时我自己的生理状况就是这样的。我在目前也多少还是这样。”(33)
牢骚怨愤、焦躁苦闷,这是我们在郁达夫自述中常常读到的情绪。(34)
“我生如一颗流星,/不知要流往何处;/我只不住地狂奔,曳着一时显现的微明,/人纵不知我心中焦灼如许。”这是成仿吾当年的心声。(35)
“风儿一丝也不吹动,/我胸中却有无限的波浪奔腾/也没有鸟儿的鸣声/和我这抑郁顿挫的心弦和应。”这是郑伯奇的烦恼。(36)
总之,创造社青年的焦虑来自他们在日本的挣扎生存,文学既是他们焦虑中努力挣扎的选择,同时却又不时添加着他们焦虑的内容和形式。
挣扎着开始了文学的群体性“创造”,1921年6月8日,带着泰东书局赵南公的初步承诺,为出版文学杂志而来回奔波、殚精竭虑的郭沫若终于在东京与他的伙伴们达成了共识,“创造”之名确立,创造社算是大致形成,但创造社的成立却只是一系列新的挣扎与焦虑的开始。
注释:
①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6、4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钱理群:《周作人传》第10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③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65、72、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④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郁达夫文集》第7卷第179页,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
⑤郁达夫:《鸡肋集·题辞》,《郁达夫文集》第7卷第170页,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
⑥见田汉:《三叶集·田汉致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⑦郑伯奇致曾琦,见《少年中国》1920年2卷1期。
⑧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⑨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3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⑩蔡震:《文化越界的行旅》第11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11)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第268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2)郭沫若:《评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原载1922年8月4日《时事新报·学灯》。
(13)郭沫若:《暗无天日之世界》,原载1923年1月《创造周报》第7号。
(14)郑伯奇:《国民文学论》,《创造社资料》(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5)郁达夫:《〈沉沦〉自序》,《郁达夫文集》第7卷第149页,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
(16)参见黎杨全:《论厨川白村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海南大学学报》2005年2期。
(17)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1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18)鲁迅:《野草·死后》,《鲁迅全集》第2卷第2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原载1922年8月4日《时事新报·学灯》。
(20)郑伯奇:《国民文学论》,原载1923年12月至1924年1月《创造周报》第33至35号。
(21)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原载1923年5月20日《创造周报》第2号。
(22)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3)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册第43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
(24)郑伯奇致黄仲苏,见《少年中国》1920年2卷1期。
(25)郁达夫:《茑萝集·自序》,《郁达夫文集》第7卷第153页,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
(26)张资平:《我的创作经过》,见《文艺创作讲座》第2卷,上海光华书局1931年版。
(27)例如郁达夫所写《创造日宣言》:“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
(28)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第221、2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9)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原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5辑。
(30)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31)郭沫若:《三叶集·郭沫若致宗白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32)郭沫若:《三叶集·郭沫若致宗白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33)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34)郁达夫:《鸡肋集·题辞》,《郁达夫文集》第7卷第171、172页,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
(35)成仿吾:《流浪·序诗》,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9月初版。
(36)郑伯奇:《梅雨》,原载1922年10月《创造季刊》1卷3期。
标签:文学论文; 郭沫若论文; 郁达夫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创造社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鲁迅论文; 功利主义论文; 文艺论文; 沉沦论文; 郑伯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