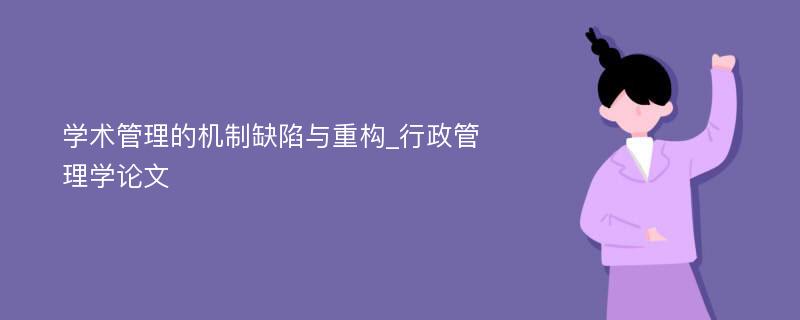
学术管理的机制缺陷与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陷论文,机制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36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7-905X(2003)03-0054-04
记者:朱彤晖(以下简称朱)
采访对象:张国功(以下简称张),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文学硕士
朱:目前,我国学术领域存在着学风浮躁现象,甚至出现了诸如钱学交易、权学交易 、学术评价不公等学术腐败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道德方面的因 素、社会环境的因素,而学术管理机制本身存在问题也是学界公认的重要原因之一。您 认为目前学术管理机制的弊端在哪里?
张:政治生活领域的管理机制失效容易导致政治腐败,学术管理机制失效则导致学术 腐败,这是一种共通的常识。“内圣”是靠不住的,学者亦无法超越“人性本恶”,因 而需要外在的监督、他律。应该说,今天的学界对眼下学术管理机制方面的缺陷及其导 致的负面影响,已经不存在认识上存有歧见或模糊的问题了,近年以“学术批评网”和 《学术界》杂志等为代表的媒体刊发的大量相关文章,都可以印证今天的学界中人对此 已经有了足够明晰的认识与警醒。而难以超越的一点是,因既得利益的关系,使得大多 数“学人”依旧心照不宣地认同现实,或者是随波逐流式地从众。换个角度说,就是因 为没有促成优胜劣汰效果的管理、激励机制,所以人们多在“劣币驱逐优币”的格雷欣 定律困境中向现实妥协,而迈不开改革的步伐。
如果一定要追究现行学术管理机制的弊端,则主要在于其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化 管理体制,学术管理机制与权力(这是指现实权力而非指下文提及的“学术权力”)、现 实利益相纠结,所奉行的完全是以权力为资源、以利益为目的的“准官场”权力游戏规 则。政企不分和过分僵化的计划经济,容易导致企业竞争力低下等弊病。市场经济时代 推行的经济改革,其取向即在于给企业以足够的市场自主权;而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入的 今天,学术管理尤其是人文社科管理,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导 致“政学不分”或“政研不分”等不正常现象。自然,它极易导致学术没有市场自主权 ,本来应由学术文化“市场”来评判、解决的问题,却被非学术力量(如行政官员、公 务员等)寻租(如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得学位、行政部门编写教材等),而采用与政治管理 同质的思维方式来管理。如学术管理中无处不在的等级体制,就是其重要的表现。课题 、奖项等分国家级、省级、校级等三六九等;学者出专著,要斟酌出版社是国家级还是 地方级等。这些状况实际上是简单挪用了政治管理方式中的等级制,剥夺了具有同等研 究水平的人文社科研究专家的“国民平等待遇”。以笔者所在的出版行业为例,在管理 上实行的是等级行政管理体制,尽管新闻出版总署曾声明管理上的行政级别并不代表出 版单位学术上的级别,但因为受官本位的影响,人们——包括学界,常常习惯于把出版 单位的行政级别的高低等同于其学术水平的高低,而人为区分出所谓的国家级和地方级 。学者所出著作,即使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等业界公 认的、遴选机制严格的一些优秀出版社出版,还是比不过地处京城的一些“国家级”出 版社,高校给予的学术补贴等利益也因此而极为悬殊。至于刊物,诸如《中华文史论丛 》、《中国学术》等优秀刊物不在“核心期刊”、“重点期刊”或者一些高校认可的刊 物之列,更是时有耳闻的咄咄怪事。这是典型的以身份论高下。至于“钱权交易”、“ 钱学交易”等现象,则是学术管理者利用隶属于一定社会序列中的级别这一“社会资本 ”来寻租“学术资本”,进而反过来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以致形成既得利 益与将得利益互相驱动的循环。而由于这种相互“通用”的不正常关系,对学术资本的 渴望,极容易导致对特定意识形态的无条件屈从或认可,从而妨碍学术的自由与公正。 朱国华在《学术界》2002年第4期发表以《学术合法性是如何可能的》为题的文章,指 出:“社会资本,是特指具有某些重要的学术体制的成员资格,比如某学会的会长,某 某学术委员会的理事。他们具有分配或再分配学术资源甚至经济资本的权力。我们这里 谈论的这些研究性组织不是指民间性质的,而是指具有一定行政级别、隶属于一定主管 部门的学术机构。这些机构负责评审优秀论著论文,审批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 博士后流动站,确定人文社会科学的课题指南,从而以符号奖励和经济资助的形式组织 学术的生产。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机构为文化生产活动规定意义和 标准,因此,这些机构的领导通过上述活动,通过符号利润和经济利益的分配,成为控 制学术场的统治者,但是他们是以意识形态人格化的身份(尽管在学术场域,他们为了 适应该场域的游戏规则,不得不尽量表现出摆脱这种角色形象对自己的束缚的样子), 而不是以历史形成的学术权威的名义来获得话语霸权。当他们为学术场的基本信念发布 合法定义时,学术场本身应当具有的‘纯粹理性结构’就变得非法了。”朱先生借用布 尔迪厄的权力理论,剖析了这一现象阐述的内在本质。如要说得直白些,就是以利益为 中心,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学术资本极易在今天政学不分的管理机制中达成合谋。再 如高校及社科院的科层化管理现象,也是行政管理体制、现代社会科层化在学术领域的 类同移植。学院式专业管理让位于堂而皇之而且名目繁杂的现代管理体制,组织管理与 学术自主相互冲突,管理主义大行其道,这在近年的学界是一个日趋明显的事实,后生 的行政权力压倒了大学等学术机构出现初期拥有的学术权力。1989年教育学者鲍尔(Stephen J.Ball)在《管理学:一种道德技术》一文中就曾尖锐地指出:现代主宰学校 运作的管理主义,体现了福柯所说的“权力技术”。管理主义的办学方式把层级监视、 常态化评断(normalizing judgement)与审查等制度引用到学校的日常运作上,不但形 成了对学习者的“规训”,而且“评审对工作表现量化”,也使教研人员与学校本身被 异化为“一堆可以被描述、计算并能互相比较的数据”[1]。管理学与教育行政的力量 支撑起了无形的监控与审查。再如经常受人质疑的学术评判专家系统(如包括多学科专 家所组成的学位评定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以及各类评奖委员会),其受人质疑的原 因主要是其大面积行政化倾向。通常是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其成员 则相当部分是单位的中层以上领导,如高校中的校级领导、院长、系主任、所长,还有 一部分则是老教授。大部分评委会委员与行政官员身份重叠。独立的学者——尤其是与 行政管理相冲突的学人,根本不可能跻身其中,因此很难保证其学术公正。黄安年教授 在《谨防学术“官僚化”倾向》中列举了十大现象:学术机构的管理衙门化现象,职称 评定、项目立项、评奖活动中的“赛跑”现象,学术评价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现象 ,政府官员兼任院校长的现象,学术刊物主编官员化倾向,“腐败文凭”中的权钱学交 易现象,学界新闻传媒活动凸显政府行政官员现象,一些学术团体官方色彩明显,职称 评定、奖金、住房等待遇向行政官员倾斜的现象,政府官员兼任学术项目主持人日益增 多现象[2]。应该说,这些都是普遍的现象了。再如各种级别的课题制,因其能够凭借 学术资本分配经济资本,使其在制度性导向上将原本应是自发形成的学术研究异化为一 种依照评审者主观意愿来调整学术取向的人为性设计,甚至使许多学者将自己交付给一 种与自身学术兴趣呈异己状态的东西。
追根究底,学术管理机制缺陷背后所潜藏的是学者独立精神与学术自由地位的缺乏这 一老话题。中国迄今为止不过百年的学术职业化进程(北大摆脱官学传统是在1917年蔡 元培入主之后,而美国的哈佛学院建立于1636年,更遑论学术职业化历史久远的西欧) ,不足以抵挡年深日久的理性工具论与实用主义学术观的传统,这是学术独立在中国缺 失的一个原因。而由于现代学者所存身的社会性、制度性环境,无法促使、规范他们在 纯粹知识、学术本位的理性基础上进行有效与必要的践履,进而使这种来自“他律”要 求的纯粹的学术思维与学术本位信念在不断的践履中得到巩固与加强,更使得独立的学 术管理机制的建设异常艰难。
朱:在学术研究的评价机制方面目前许多机构采用的是量化标准和弹性化标准相结合 的方法,有人对这种评价机制提出了质疑,并提出学术管理应实行弹性化机制,您对此 作何评价?
张:像许多概念与说法一样,“弹性化机制”也只是一种概称,对于学术评价,当下 学界有着不同的具体操作与执行方式。但本质的精神,即在于帮助学者能够从以数字化 、量化指标为特征的“现代性”中突围出来,能更加宽容地使学者有从容优游、沉潜反 复的问学空间,使学术更多地遵循“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有规则有特例, 弹性化管理无非是在这两者之间找一个恰当的位置。不管其具体方法如何,支撑弹性化 机制的关键,在于学术管理部门对弹性程度的认可与尊重。实际上多少要看管理者是否 业务内行这一具体情况,看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听取、尊重学术权威的意见——因为只有 真正的学术权威,才能既立足于规则而又能超越规则,不至于使同仁把弹性机制看成是 无规则、流于随意化,也不至于使管理者将其僵化为机械性条例。蒋寅在《与学术进步 相关的几个概念》一文中说:“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正处于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就拿中 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来说,郑振铎、何其芳、吴世昌、钱钟书那个时代的学者,可谓博 通今古,学贯中西,他们的论断一言九鼎。听前辈学者说,当年文学所一级研究员仅何 其芳、俞平伯、钱钟书三位。何其芳是所长,俞平伯是何其芳的老师。钱钟书当时仅四 十出头,评职称时著作只有《谈艺录》,何其芳认为他够一级研究员,就定一级研究员 。另有一位搞当代文学批评的学者以两部专著申请副研究员,学术委员吴世昌说他的著 作不能算是学问,结果他就没评上。这就是权威的力量,它能使人信服。说到底,一切 评估标准都是软性的,具体成果的价值评定最终取决于评估的主体。没有高水平的法官 ,再完善的法律也难以产生效力。在没有权威的时代,学术标准就形同虚设。”[3]清 华创办国学研究院时,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格先生担任导师。曹问梁:“他是 哪一国博士?”梁回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说 :“也没有著作。”校长说:“既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气愤地说: “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总算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数百字有价值。”陈 先生后来成为清华园中“教授中的教授”。梁先生敢于如此理直气壮地大声说话,固然 由于他的地位名声使他底气十足,更重要的是当年没有文凭高低、论著多少等方面的刚 性化管理指标。上世纪40年代北大学者汤用彤先生的力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 得了教育部的最高奖,面对这名至实归的荣誉,他却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 ,我的书要谁来评奖!”这种真诚与自信,正是来源于弹性管理的支持。
因此在今天如果要说“弹性化管理”,首先是需要有能够确立弹性机制的人。而与西 方如美、德等国中诸多大学由大师们决定学者的升级、聘用等不同,在今天的中国,主 管学术机构的官员们或者是由官员们所决定的学术委员会影响着学者的评估。德国社会 学家马克斯·韦伯八十多年前在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中说过:“民主”只应当用 在适当的地方。当今天的学术评估习惯于以“民主”的方式进行时,它就必须采用“民 主”的形式主义——诸如数字量化等刚性的规则。
朱:提到学术管理,就必然涉及学术权力问题,将学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可能会让 人感觉不舒服。您认为学术权力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它对学术管理应该产生什么 样的影响?它的存在方式、性质、相互关系及运行机制应该是怎样的?现有的学术权力分 配合理吗?谁应该拥有这种权力?
张:“学术权力”的问题,是上述两个问题的“接着说”。
学术权力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不认为权力仅仅是政治系统中的概念的话。有体 制就有权力分布,体制与权力的关系构成了一种普泛性的社会关系,其中包括了制约学 术活动在内的一切学术权力,以及实现并维护这种权力的机制架构。我们不必因为在当 代中国学术领域里学术权力特别容易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力量达成重叠错位的复杂关 系,就否认甚至对抗它的存在;我们也不必认为一定要借用福柯、布尔迪厄等人的西方 理论才能揭示其本相。学术权力应该在学术管理中起到绝对性的作用。至于谁该拥有这 种学术权力,直接体现者即是上一问题中提到的像俞平伯、何其芳、钱钟书以及弗里德 曼、朱德熙那样公认的学术权威。一个一流学者一定要比二、三流学者拥有更大、更多 的学术权力,这才正常。否则,就会使学术界出现逆向淘汰现象。应该有一、二流学者 作为学术权威,但不应把学者分为一、二等,不可有学霸与学阀。学术权力不像政治权 力,需要一种在各方面达成的平衡与调和,作为一种参照与标杆。简单说,就是在专业 领域的发言权。它的存在应该是一种无为的、软性的。专业权威不应以形式上的行政职 权专断地命令别人,而是以其学问、人格影响他人,以其学术水平、学术资历、学术贡 献所构成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来吸引他人。从现实关系讲,学术权力不是一种类似于行 政权力的纵向的科层性隶属关系,可以通过行使命令等要求非学术权威无条件屈服,而 是以春风化雨、民主平和的方式使人信服。专断的政治权力会导致“一言堂”式的专权 ,而学术权威则有着一言九鼎的人格魅力。至于其运行机制,如果我们不仅仅满足于将 其定位为一种清议的力量,则理应将学术权力完全交付给学术权威执行,如现行的委员 会一类评定机构应最大限度地由真正的学术权威组成。现在的学术权力分布不合理,即 在于权力过于集中于行政系列人员身上。由今天的委员会一类的专家系统中,行政领导 角色者往往多于毫无行政职务的老教授们——而往往是后者,才是真正的学术权威—— 就可以看见学术权力的行政化色彩。
朱:学术管理应该充分认识和尊重知识生产的特点和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在目前中 国,您认为应该有什么样的学术管理的组织机构、职能配置、运作方式和管理效果?
张:目前学者谈论学术管理机制失效这一问题时,多是批判性质疑,而欠缺建设性意 见。上述问题太大,更不是笔者区区普通编辑可以完全回答的,但可以说一些想法。首 先,应该承认学术管理尤其是人文社科的管理,没有绝对统一的模式,更不能追求一元 化、万能性的管理方法,而应该容许多元化的管理机制存在。比如说评估机制,在学科 分化严重的今天,某一特定学者很难说在其他领域的学术管理方面有多大发言权,你要 一个由固定数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评估所有的专业学科的成就,他们可能不是力不从心 ,就是敷衍地表态。其次,学术管理部门不能仅仅习惯于计划机制,还应当创造性地推 行市场机制和督导机制,对学术的管理应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由微观管理转向宏 观管理,由集权转向分权,由集领队、裁判员、赛事主办者于一身转向只做裁判员与主 办者,最大限度地取消行政介入,须知人文学术管理从根本上讲宜粗不宜细。最大可能 地取消社科基金项目这种不合人文学术规律的急功近利的行为(学术研究以跻身项目为 目的,以能否跻身项目为水平高下的标志,本身即是不合理的),以社会公议化的形式 启动“学术市场”,将学术评估的权力更多地交给社会及学界本身而不是集权在行政管 理部门。即使要评奖,也宜交由社会中介机构来操作执行而不是政府直接说了算,或者 说更多地提倡民间性奖项。再次,尊重各种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平等权,在京出版社与 地方出版社、公开刊物与内部刊物、省级课题与国家级课题等应一律平等对待,不要人 为地设置如“重点学科”、“核心期刊”一类的学术等级制。取消“学术带头人”之类 固定身份的认定,而仅就其某一科研成果进行评估,让流动的“市场”来确定学术成就 的价值,而不是以一劳永逸的封号来论定其身份的高下。再如严格推行高校不留本校毕 业生以杜绝“近亲繁殖”的做法,将聘用或不聘用某一人选的决定权下放至所在院系的 教授(师)手中。再如可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学术管理者不能直接参加学术成就的评定;可 以考虑职称专利化,甚至规定其有效期——在今天,产品与发明等都有其时效性,惟有 职称是终身的,这无法促进职称拥有者不断推出新成果。
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专门成立了“研究诚实办公室”(ORI),负责处理由政府资 助的研究项目中出现的不诚实行为,随时公布违规者姓名、单位、违规情节和处罚决定 [4];在英国,对于不正当学术行为,主要由资助科研的基金会和各研究机构自行调查 并作内部处理,有时学术杂志也会参与对过错方的处罚[5]。在中国,虽然学术管理机 构很多,但像ORI这样的机构似乎没有。中国的学术管理部门大多热衷于对学术研究进 行设计甚至是参与,而不是只止于监督其公正性。在这方面中国应向外国学习。
机制是由许多细化了的有效性措施与规则组成的。我们必须研究、评判每一条措施、 规则的合理性,并随时在实践中磨合它们之间的冲突性。如此,才可能真正使机制不断 走向完善。
朱:在应用理论研究领域,目前出现了颇有市场的咨询服务机构,咨询服务的过程也 是针对个案的调查、分析和研究的过程,其研究结果会有偿提供给服务对象。有人说科 学咨询服务是应用理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必然选择和明智选择,科学咨询产业的兴起 指日可待。那么,您对应用理论研究的管理有什么看法?
张:与文史哲等纯理论的人文学科稍异,对于应用理论研究,如心理咨询、市场分析 、法律学、经济学、媒体咨询等领域,应有不同于前者的管理方式。应用理论研究的“ 产品认证”并不像纯理论研究完全由“学术市场”本身来评定,而是由外在的社会来认 定的。笔者总的看法是应该完全让其走向社会,将由政府为惟一的学术产品购买者与资 助者,转向让广泛的社会成员成为购买者与资助者。而学术管理部门,只应有对其实行 监督的责任,尤其是不必实行奖惩评比和课题制等。因为,在市场中竞争的独立法人永 远比管理者更知悉社会需要哪些课题,何者为优何者为劣。
收稿日期:2003-03-01
标签:行政管理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