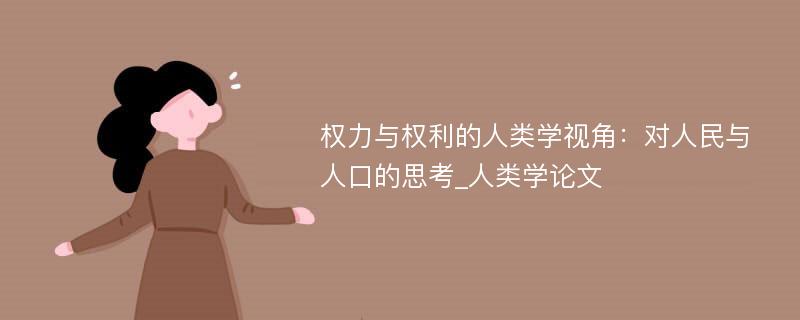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人类学笔谈——何以为人:关于人民与人口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人类学论文,权力论文,为人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学不擅俯视,而更习惯平视。经典人类学观察与分析的是具体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而像“人民”和“人口”这些属于现代国家政治与治理范畴宏大的描象概念,人类学早先并不讨论。但随着国家日益深入我们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人类学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并思考这些大概念了。当然,人类学关注的终究是社会思想,也就是具体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观念,以及依循这些观念的社会实践与行动。这种审视自然也就跟哲学或政治理论里针对这些概念所作的更加偏于本体论的讨论与争论不同。
“实名制”里的名指人名。人名跟物名不同,除用于指涉外,更是称谓,是语言呈现社会交往的见证。作为后者,这个名有跟谁来用关系密切。现在孩子没出生,父母就要琢磨怎么起名,要独特,吉利,好听,还不能留下起绰号的隐患。这都是现代医学提高了妇幼保健水准的结果。在一个谁都没有把握孩子一定能生下来,生下来一定能活下来的年代,“小二”、“小三”、“阿猫”、“阿狗”,都是人名。你叫他的小名,他就会回头,就跟“桌子”、“凳子”不同,就能满足自家人的指涉和称谓要求。超出最为近密的社会圈,就要用大名来承载更多的社会关系。老气的大名里的姓与辈都不属于个人,而是用作核心家庭之外社会纽带的标志,可以左右由这些社会纽带连接起来的不同个人之间交往的方式。
我在中原农村做田野调查时,在一座老坟前见到一块新立的墓碑,上端刻着死去祖先的名字,下面按辈分排列出他的四代男性后人的名字。这家人我很熟悉,也曾经做过他们家族的谱系。这位祖先尊姓大名我是在碑上头一次看到,我做的谱系图里他就是“曾祖”,当地方言叫“老太(爷)”,因为他的后人也多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碑上其他人的名字我都能照实录入谱系,但这些文绉绉的大名他们之间也很少使用,关系稍远的一点也未必定记得。晚辈都知道,对长辈是不能直呼其名的。碑上还刻个十分出格的名字,姓氏后面单单一个“胖”字。他刚刚成年,却因幼时脑疾,未曾上学读书,他父母也就从未给他起过学名,只是叫“胖子”而已。“老太”和“胖子”都不是专名,却在生活中起到称谓的作用。“老太”是社会身份,在为其修墓立碑这个托显一个宗亲家族成员间社会纽带的仪式中被扮演了祖先的角色。唯有这时他的大名才会出现。死了是否能成为祖先,能在石碑上留下体面的大名,则要看后人是否争气,是否活得体面。生死两界,息息相通,正是宗亲社会的标志。民间习俗若是带上一些官气,就成了过去旺族修族谱这种持续更为久远的礼仪。同时,这种实践本身还是自上而下的教化的途径。而“胖子”在石碑上也终不能立名,足见其社会角色中不可消抹的缺陷。至于祖先的配偶在石碑上有氏无名,出嫁后妇女就不再有自己的姓名,则是宗亲社会里男妇社会角色差别的结果。
如何成为社会一员,扮演什么角色,角色背后有什么样的人格,这些是法国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在1938年作的讲演中想要回答的问题。[1](PP1-25)依照他的说法,现代西方社会人观里对“个人”(personne)的个体化认识并非古来有之,更不是普世无别。这位年鉴派学者从词源、历史及当时他能读到的民族志中找到证据,提出虽然自我意识是人类心智的一个固有范畴(a category of the human mind),却又不是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先验范畴,因为其内容会因社会而异,因历史而别。同样以人名为例,他指出,北美的许多印第安人部落的成员反复使用固定有限的且含义特定的名字,因而构成氏族的实际上是由命名而指派的角色或“人物”(personages,characters)。所谓“个人”则在整体的氏族生活中被他们担当的角色左右、掩盖、消融。[1](PP6-7)礼仪是展呈氏族生活及社会结构的舞台。这些部落的成员戴上先辈留下的面具在这个舞台上表演,这时他们才获得了在他们社会最为完备的“个人”,最为丰满的人格。在莫斯的历史构想里,这种不以个人为角度的人观似乎更为本真,更为古老。其实,我们自己的社会至今也对脸面十分看重,不能说没有这种古老人观的痕迹。德行与表演同一,乃至“八荣八耻”,都是借“要脸”之力实现社会规训。
莫斯注意到,拉丁文“个人”(persona)的本意竟然就是“面具”。再往前溯词源,意义还是一样。[1](PP15-16)但西方人观却自古罗马就开始变化,变得越来越不古老,成了今天人们熟悉的“个人观”。这种“个人观”也正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基石。在莫斯看来,这种转变是罗马时代赋予“个人”以“权利”(rights)时发端的。权利得使个人不再是并不属于自己的社会角色,而是可以拥有财产、身体和名字的自由民——“公民”。没有这些权利的奴隶,当然也就算不完整意义上的人或个人,也无“人格”(personalité)可言。[1](PP16-17)经过其后漫长岁月的积累,角色(personages)背后“人格”的涵义逐渐彰显和充实。起初是寡欲重德的斯多噶派,把道德与责任的意识加进获得了权利的面具后面的头颅里。而基督教则更是打破古罗马有脸与无脸的社会区格,让所有得神灵者都成为具备道德人格的个人(individual,指不可分割的完整个体)。基督教里多年的神学辩论的另一至关紧要的结果是在对人的认识与界定时加进了与神灵相通的理性。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哲学更是以意志和理性来丰富个人的人格,直至康德把“自我意识”(das Ich)看作是人类心智的范畴(category)。①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是,莫斯的这番描述,从他在政治上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与支持来看,很难说是在颂扬西方文化与社会里日见成长的个人主义,更不是在为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辩护。一如他更为知名的著作《礼物》,莫斯是在表达他对逝去的古式社会的惋惜,更是在表达对现代被自由主义与经济理性驱使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失望与担忧。与其说莫斯在他的演讲里对个人主义在西方社会的长育作了一个思想史的追溯,倒不如说他是在描绘自己的社会,把这个社会里视为天经地义的人观推出普世理论,使之如同人类学视野中他族的宇宙观、神话或观念体系。莫斯着眼于社会与历史演进的比较研究,把康德的“先验的范畴”还原成了“超越的错觉”(“transcendental illusion”)。[2](P283)顺着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界定,我们不妨把莫斯对西方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历史描述看作一种意识形态的解析,进深一层的意义在于这样的学术实践所起的作用,是揭示那些原本被视作必然乃至自然事物中的社会历史成因,及文化的相对性,因而也是可以改变的。莫斯自己是否看到这一点,从他的言说与文字里还不能确定。但这种批判实践的确成为后来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成分,尤其是以研究本族社会与文化的人类学。尽管莫斯没有教出一个出色的学生,凭他字数不多的著述在今天的学府也很难立足。但他的这种以我为他的人类学目光却对后来的人类学颇有影响。研究路数与轨迹与莫斯相仿,可以说深受莫斯影响的出色人类学家里有法国的Louis Dumont和美国的Marshall Sahlins。两人都是在早年研究他族文化之后把目光转向他们自己的社会,对构成西方“宇宙体系”诸如个人、理性、经济理性等核心观念进行社会、文化及历史角度的意识形态剖析。
莫斯不觉得他是“坐在椅子上的人类学家”(armchair anthropologist),却承认自己是一个“泡博物馆的人类学家”(museum anthropologists)。后来的Dumont与Sahlins与他也十分的相像。跟跑田野人类学家有所不同,他们分析的素材大都出自他人之手,而非来自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与体验。视野宽广使他们看到平视所不易发现的规律与关联,但他们眼里古今东西间的差异重文化,重宇宙体系,重历史传承,难免显得刻板。这一缺憾正好提示了我们今天的研究面临的问题。意识形态或文化体系的变更的推动力究竟是什么?历史传承里文化逻辑(这是Sahlins喜欢用的一个概念)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消逝的观念体系被什么替代,如何替代?还有更为具体与紧迫的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所及之地的政治文化又会有什么影响?国家的政治与权力意涵又会因此产生什么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日“人民”这个词就写进了我们的国名。其意指十分明确:构成民族国家的“人民”是这个主权政治体的终极主体,通俗地讲就是人民当家做主,是国家的主人。
在经验层面上,如果我们留意“人民”这个语词使用时的不同语境,就不难发现其复杂的内涵与外延。同时,这个语词在社会政治生活的意义不仅仅是来自对既有事实的指涉,更是来自言语行动(speech acts)施行时对社会事实的创造与重申。“劳动人民”就对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民”作了相应的限定,泛指的“人民”,或可用语言学家Roman Jakobson的术语,“无标记的”(unmarked)的“人民”则与专指的、“有标记的”(marked)“敌人”形成对立,孰强孰弱也自然明晰。
我们不妨听听跟莫斯差不多同时代的德国政治哲学家施密特(Carl Schmitt)的看法。斯密特在纳粹时代留下政治污点,很难让人喜欢,也总是说出些让人听了不舒服却又不易打发的话。他认为,政治是国家的前提,而政治则是建立在敌我对立的标准之上的。这个原则独立于其他诸如道德、审美、经济上的判断,成为界定政治领域,解释国家政治行为的独特标准。[3](PP1,26)顺着这个思路,施密特提出,敌我之别的极致是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敌对方士兵之间在个人层面并无恩怨可言,却依旧进入了你死我活的境地。而在作为政治体的国家内部,同样的政治原则就要求敌我之别中的我,也就是人民,能维持高度的同一。不难发现,我们的人民概念的疆界是不明确的。很长时间内,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内部保留了“敌我矛盾”,而在人民之中也还有“内部矛盾”。显然,这样灵活多变的“人民”是一个比国民外延更小的概念,在这点上与古罗马时代的“公民”更为接近。而在“人民”这个语词使用最多的年代,国家内部的敌我冲突也最为激烈,人民内部的同一性最为明显。当然,这个人民概念的政治化是由一个人类进步的普世冲动促成的。与敌人斗,目的是改造敌人,使其成为人民。
在政治主张上,施密特偏向极权,始终持怀疑与反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格局。他推崇主张“君权至上”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一书,并著书对其进行阐释。[4]但是霍布斯君权至上的前提是民与民乃至民与君之间的社会契约。民首先是由在所谓“自然状态”相互为敌的独立个人构成,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同质的、具有一致政治标志与觉悟的人民。虽然莫斯没有讨论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但霍布斯政治思想里所包含的人观却与莫斯讨论的个人主义成长史吻合。这一点从《利维坦》1651年版封面上的版画就可以看出。“利维坦”大人的身体是由一个个细节清晰的小人构成。这种构想与基督教里关于灵、教、教众之间的贯通一致,也与基督教关于灵与肉的分别一致。君不是神,而是神权的替身,而世俗化后神权就成了民与民之间契约总和即国家政权,或者说是社会本身,这是我们已经十分熟悉的涂尔干(E.Durkheim)的思想。权的“神授”与“人授”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这里的“人”必须是具备独立意志与人格的个人。在这种的政治思维里,君就有了两个身体,一个是生老病死,而另一个则是抽象君权的化身,或者说是一个身份,一个角色,谁来扮演并不改变其“人格”。[5]看过莎士比亚剧的人都听过“国王已死!国王万岁!”这两句台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可以万岁,而领袖是万万不可万岁的。当领袖俯视人海,迎着滚滚而来“万岁”声浪,呼出一声“人民万岁”时,作为范畴的“人民”就失去了以个人为指涉的外延。
几年前我住北京,孩子刚在小学学了一篇关于卢沟桥的课文,我就在周末带他去看真桥。桥上的几百个小石头狮子果真个个有脸,跟别的狮子不一样的脸。欣赏完桥上的狮子再去参观桥边的抗战纪念堂。纪念堂内四周高高的墙面上刻了许多为国捐躯的英雄的名字。每个名字下还刻了一行小字,标出这些英雄生前的军衔官职。我们要仰视才能读出这些名字。儿子幼时我带他去看过华盛顿的沉入地下的美国越战纪念碑,碑上不仅密密麻麻刻了每个这场战争中死去的军人的名字,还为失踪军人留下几块黑石板。对前来凭吊的亲人和战友,这些伸手就可触摸到的名字都能唤起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回忆。儿子问卢沟桥的英雄里怎么没有一个士兵,我不知如何回答,就替他问门外站岗的哨兵。哨兵也许觉得我的问题不怀好意,连理都没有理我。也许,卢沟桥的纪念堂与华盛顿的纪念碑可以形象地告诉我们“人民万岁”与“We the people…”这两句话之间依旧存在的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差别。②
这几年我在手机上装了谷歌地图,做田野就不像从前总是要问路。仔细想想,觉得卫星定位做田野并不是件好事。以前以问路为由让我可以跟很多原来陌生的人交谈,问成习惯了就觉得自己是不会认路的,但我却因此获得了丰富的“人文地理”,真正进入了田野。谷歌地图也不是白给的,这个技术可以让公司收集使用这个技术的人的方位信息,有潜在的商业价值,也普遍引起了人们对隐私的担忧。眼下正是梅雨天,让我想起网上看到很多在雨天出行检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照片,他们身后会跟着替他们撑伞的下级。③收集这些照片放到网上,大概是想展示真正被颠倒的主仆关系。但言与行,孰正孰反,也只能见仁见智了。有一点是清楚的,领导若是在做调研,后面是否跟了撑伞的,他听了的东西很可能就会不一样。“治人”者深入基层,亲自与“治于人”者打交道,至少从观念上讲还是获取治理信息的途径,尽管这样做更像是在摆镜头。现代国家框架下的治理,对象是人口,关于人口的各种数据远比跟人民中的个人打交道重要。这一点就是自己撑伞、竞选时要亲无数个小朋友的脸的国外政客也会同意。从这些小小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技术与知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通融。人口这个属于国家治理术的概念的产生与运用正是这种通融的结果。其实,统计学从一开始就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④
最近我去中原农村的一个田野点,忍不住炫耀我的新手机。他们的手机比我的更新更高档,可他们却还不知道也不需要谷歌地图。我载入当地的卫星图片,就能清楚地找到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地,他们地里的坟。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陌生的视觉世界。以前跟着他们走过逝去亲人的坟头,听过他们跟坟里的人说话。现在从天上看,老坟集中的地方看起来像十多年前的发“热病”皮肤上发出的片片疹子,让他们发憷。“热病”不是天咒,而是他们的身体成为市场经济的因子(factor)后付出的代价;也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所要付出的代价。国家权力得助于经济知识,经济知识又使国家权力转变为经济权力,治理与经营融为一体,这不是我们的市场经济独有的现象。但是,在优越与自卑感相参的所谓“中国模式”的呼声中,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口里我们应该看到的、关注的、关心的究竟是“人”还是“口”?
经历了半殖民地的中国跟遭受全殖民地统治的印度不同。在新兴经济里至少眼下是看好中国,而不是印度。在政治上,印度多少被接受了所谓“以民为主”(popular sovereignty)理念,但其“脏,乱,差”,没有高效的城管执法,都会给我们的游客印象深刻。其政府效率低下,腐败起来也不输人,更是让我们当中不少人深感“中国模式”优越。对于我们眼下政府与经济日益见长,而能独立于政府和经济的社会日见消萎,我们当中也有不少人深表担忧。印度的学者会怎么看呢?
在一本应该译为《治于人者的政治》书里,印度学者Partha Chatterjee表述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6]要读就读这本书的头一部分,他200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系列讲座里三次演讲。书的副标题是“关于大部分世界里的公众政治的思考”,有些费解,他在书中作了解释。所谓“大部分世界”(the most of the world)指的是欧美民主政治区域之外的世界,印度跟咱们中国都在其列。现代社会理论传统的主体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这位Chatterjiee是印度“底层研究群”(Subaltan Studies Collective)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典型的殖民后与后殖民的学术群体要树起“他方”(the rest)的旗帜,重现被“西方”(the West)思想遮挡的底层视角。若不听他在书中究竟说些什么,还真会觉得他是在讲印度模式呢。副标题中的另一个词“公众政治”却意味深长。“公众政治”(popular politics)是指底层庶众借用“以民为主”的政治形式与力量才达到其自身的目的。他们聚散不定,也没有明晰稳定的政治意图,更不能成为政治力量的主体,而仅是民主政治过程中的社会中其他政治力量的资源。
在印度这个所谓世界最大的民主社会里,只有社会上层与精英才有资格、知识、资本、权力、权利去参与欧美学者所讲的资产、中产阶级“公民”参与的“社会”。就是在去殖民时代甚远的今天,“他方”里这个“社会”还是跟“西方”的社会不同,跟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也依旧不可同日而语。⑤原本高低有别的社会阶序,英国人一来就给拉平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兼任印度女皇之后,一群群本属于不同种姓的印度子民也就成了一个个带上殖民政府行政标签的人口,“贱民”还得到女皇的特别关照。⑥但女王陛下要的是印度货,而不是人。心底里也没有把印度人完全当人看。⑦
于是,印度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史上就出现Chatterjee指出的现象。福柯描述了欧洲17世纪后的政治转型,由“国家权力至上”(coup d'Etat)转向“国家利益至上”(raison d'Etat),权力的戏剧化暴力展陈不再盛行,而是被更为缜密、更为弥漫、更为精准人性化权力渗透所替代。人性以及人身的研究和统计生产了把握人群、人口的知识,成为国家权力更新、更有效的支撑。与此过程相伴的是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没有资产阶级也就不会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殖民地,情形就有所不同了。法国的三色旗唤起了殖民地海地的黑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向往。他们派代表到巴黎向共和国讨公道,却碰了一鼻子灰,从吃马的法兰西人那里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从来也不曾想过要跟我们的骡马平起平坐。”⑧西方毕竟是西方,原来就有区格,殖民时代把范围放大了而已。但这种区格,并不妨碍西方将其新治用于新地。庶民的视角是从下往上看,由此他们学会了不再上当,不去硬充公民和中产阶级,而是在既有的政治格局里去争得他们可争得的利益。这就是所谓公众政治,是没有被赋予完备主体人格的底层民众的政治。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也就没有理由空谈法治了。
去年上海胶州路大火,事后最先被抓的就几个点火的焊工。他们无证上岗算违法,该抓。但要是早把所有无证焊工都抓完了,也就不会出现这场悲剧,但一定会严重影响我们楼市,造成更难以控制的价格上涨。法是有情的法,不会做出这种不合情理的事。出了事再抓,那是在辟防火带,保护事故还没烧着的人。过了半年,市领导出来检讨认责,处罚几个区领导,让几个公务员离职,让几个承包商坐班房。这些都不是因为突然法变无情了,而是要经营舆论,稳定大局。法依旧是挡箭牌,依旧在保护我们社会中需要保护的人。抓进去的焊工早就被人遗忘得干干净净,伤亡的民工就更没人提了。
如果焊工是印度来的农民工,情况也许会有些不同。他们也许会抱成团,利用盯上他们选票的人民代表,让国家或者老板出钱。当然,事成之后,这个群也就不再众了。Chatterjee笔下的公众政治的案例都是这个味道。当然,都这样扯皮拉筋,政府治理效率一准低下,GDP也高不过咱们。
注释:
①Charles Taylor认为,欧洲哲学的把自省作为知与德的起点的“自省转向”(inward turn)是自奥古斯丁(St.Ausgusttin)开始的。笛卡尔的“我思”(cogito)正是这一传统的重要发展。见Charles 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②“we the peope…”是美国宪法的头三个字。人类学家Greg Urban把J.L.Austin关于言语行动的理论与哈伯马斯(J.Habermas)和安德森(B.Anderson)关于公民社会与印刷资本主义相结合,近版的著作里对这个文本作了十分精致的分析。最为显著和典型的言语行为往往见于具有创造性的言语行动,而这种言语行动通常会以第一人称的口气发出,我们经常听到的是“我宣布大会开幕!”之类的官腔。但这个文本以及这个文本所创造(“宪法”与“构成”同源)的是一个由the people构成的独立政治体。与一般言语行动不同,言说者既由复数的第一人称代词“We”指涉,又因这个代词而产生,而仅用“the people”则指涉掩盖创造。稍早成文的《独立宣言》有语气是针对英国国王的,而《宪法》里的“We”是语言学上所说的包含听者的(second person inclusive)第一人称复数,相当于“咱们”,而不是国王专用的“royal we”,也就是“朕”。因此,后面跟着的“the people”是一个具包容性的外延开放的概念。这一个创世文本,同时也更是一份契约,是一份抗税商人首先发起的一份契约。作为一份大契约,也只有在印刷时代才能起到应有的效应。(见Urban,2001,Chapter 3,“The Nation Will Rise Up,”Metaculture:How Culture Moves through the World.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又见Benjamin Lee,1995,“Performing the People,”Pragmatics,5(2):263-280;Benjamin Lee and Edward LiPuma,2002,“Cultures of Circulation:the Imaginations of Modernity.Public Culture,14(1)191-213.)为了准确引用,我在网上查找了新中国的创世文本,这深深刻进我脑子的一句宣言的录音,网络搜索的回报比我的预期高多了,我竟然找了原来的录像。原话是这样的:“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直接成立的是政府,间接成立的才是国家。我找到的这段视频还加上一段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镜头。现代网络技术可以促进传播与流通,却没有改变信息政治文化的含义。
③这里我们看到是两种不同的技术,导航应位看似外在,却已经不知不觉改变我们的习惯,产生了内在的依赖;而给领导撑伞还是莫斯所说内化的“身体技术”例子,领导还有领导,撑伞提包成了不假思索的行动。两者都是权力的见证,但其显其隐又正好相反。哪一种权更有力,也就不言自明了。
④关于统计学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历史研究,最为精彩的是哲学家Ian Hacking(1990)所著The Taming of Ch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福柯(Michel Foucault)1977-1978年度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也有论述,见Foucault,2007,Security,Territory Population: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ance 1977-1978.New York:Picador.两人都提到“统计学”(statistics)本意就是“治国术”,词源就是“国家”(state)。若是用广东普通话念“统计学”,就可以“治”“计”不分,返璞归真了。
⑤而我们社会学界热衷中产阶级研究,却还是在西方视角与预设前提下进行的,似乎只要你一心想当中产阶级,并拿出你做的统计数字,你就真的会成为中产阶级,我们的社会也就真会变成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就真的会出现公共空间和公民社会。
⑥Nicholas Dirks刻薄地称殖民地国家为“民族志国家”(ethnographic state),无非是说那里的人还没来得及变成人民,就先做了“臣民”,也就是民族志描述的“对象”,这两个中文词在英文里都是“subjects”。这里的歧义在人民变成人口后也就随之消失了。见Chatterjee,op.cit.,p.37.
⑦当然人也可以成为货,成为资源,能想到的例子很多。
⑧“In proportioning the number of deputies to the population of France,we hav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neither the number of our horses nor that of our mules.”Chatterjee,p.29.相反,我们颇善效颦的中产阶级一呼百应开车去北京外环路上营救一卡车运往东北的菜狗,是不是可以解读为曲线求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