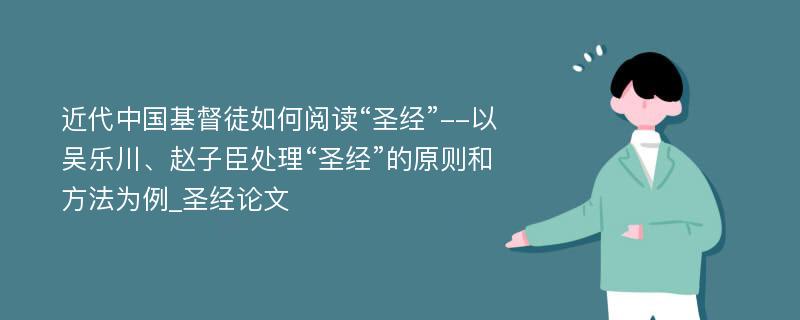
中国现代的基督徒是如何读圣经的——以吴雷川与赵紫宸处理《圣经》的原则与方法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圣经论文,基督徒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化的古老历史和宗教的多元化决定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多元宗教经典”构成的世界,不同时代的社会处境也对他们的信仰提出了各种挑战,会创造怎样一种阅读圣经的方法,用来诠释基督教经典并确立自己的身份意识。本文选取吴雷川与赵紫宸为个案的研究对象,以他们读《圣经》的原则与方法为例,考察中国现代基督徒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和阐释经文,试图以此为亚洲处境下的圣经诠释学提供研究的一个范本。
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位中国的基督教信徒,他是如何处理与阅读《圣经》的?他的阅读与西方的信仰皈依者有何不同?他从圣经中读出了什么样的富有中国文化特色与历史处境的信息,这种信息对于《圣经》的启示抑或基督教信仰而言,究竟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挥还是一种误读,甚或僭越?吴雷川与赵紫宸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基督徒,以他们读《圣经》的原则与方法来检视中国信徒面对圣经的态度和独特的文本阐释,以此反思中国神学所作的贡献及其不足之处。
一、讨论读《圣经》的缘起
1921年,在《生命月刊》第一卷第六期,赵紫宸、吴雷川和吴耀宗联名发表了《我为什么要读圣经?用什么方法读圣经?》(注:载于《生命月刊》第一卷第六册,1921年,第1页。)专题文章,在这篇言简意赅的短文中,这三位中国现代神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发表了各自对于读《圣经》的看法,阐述的主要内容围绕两个方面,第一:我们读圣经的动机、缘由何在?第二:用什么方法解读《圣经》及其相关的教义?对此,三个人基于自身对于基督教的理解,做出了不同的回应。简略地总结,赵紫宸读经的出发点是“要得生命”,吴雷川的是“救己救人”,吴耀宗的是“基督徒的人格高尚、基督教的事业令人钦佩”,相形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赵紫宸和吴雷川阐述的读经之动机较为清晰明确,比较能够代表当时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仰需求,以及那一代信徒对于《圣经》经典的处理态度,而吴耀宗的看法相对较为笼统。以下,我们对赵、吴两人的读经观和读经方法作较为详尽的论述。
二、“我为什么要读圣经?”
对于“我为什么要读经”,赵紫宸的回答是“圣经是生命书,我读圣经,为是要得生命,要从这生命利己利人救国济世,小子不敏,未敢自弃。”(注:载于《生命月刊》第一卷第六册,1921年,第1页。)曾在美国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大学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神学教育、深受19世纪自由派神学影响的赵紫宸看待基督教是“一种意识、一种肯定的个人与社会存在,一种新生命,耶稣基督已实践出来”(注:L.M.Ng(吴利明),Christianity and Social Change:The Case in China 1920-1950(Ph.D.dissertation, Princeton Seminary, 1971),P.96-97,此书的中文版为《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此处转引自邵玉铭的“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态度”一文,载于刘小枫主编的《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83页。),他认为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以经文,乃是以耶稣基督为依据,这不是提倡基督徒不去遵守经训,而是强调“基督教不是经本的宗教,乃是以基督为中心,以生命为根基的宗教”(注:赵紫宸:《宣教师与真理》,《生命》Ⅲ,3.1922,第9页。)。如何理解他的这句话?在他的早期神学观中,赵紫宸曾经有将宗教和生命等同的做法,一方面受施莱尔马赫等经验神学的影响,将圣经看作是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变化并在此过程中呈现了适应时局处境的各种宗教经验的文本,而这些经验在耶稣那里得到了总结,因此基督教的信仰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另一方面,他又将进化论引入神学,认为人通过宗教经验最终会来到耶稣面前,因为只有耶稣才将人类的经验推向高峰。由此,他指出“我们不要在老远的不知找上帝,乃要在直接的、人心交射互透的意识里,生命里,找上帝”(注:赵紫宸:《基督教哲学》,中华基督教文社,1925年版,第340页。),人是在生命中找到上帝的实存,而上帝也正是在人的生命中显现其真理,并推动生命一直“鼓铸向前”,直至“得到最丰盛的生活”。从这个意义而言,基督教又是以生命为根基的宗教。宗教与生命是统一的。赵紫宸“要得生命”的读经理由,发表时间较早,他所提及的“生命”概念是否已涵括了上述的独特涵义,对此他没有展开说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从其早期神学观来看,还是一生的主要思想倾向分析,他还是比较重视基督教与个体的关系,强调个人的精神生活与宗教经验,因此在回答基督教何以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作用时,他提供的方案也是人格救国,首先要达到的目标是灵性更新,即人格之更新,其次才是社会政治的变革,他认为只有实现了前者,才能促成一个完善社会的到来,他所提到的“要从这生命利己利人救国济世”这句话蕴含的大致就是这样的意思。
同赵紫宸相比,吴雷川的回应则更为详尽,他说:“我未作基督徒之先,是因为研究基督教的圣经,信仰总得确定。及至既作基督徒之后,更知道基督徒不但要增进自己的灵修,也应当将自己所信的,传给别人。若是不研究圣经,便一切没有基础。所以我为要自救救人的原故,在近五年中,读经的功夫,可说是没有什么间断。”(注:赵紫宸、吴雷川、吴耀宗:〈我为什么要读圣经?用什么方法读圣经?〉,《生命月刊》第一卷第六册,1921年,第1页。)他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中国旧式知识分子阅读圣经的动机。吴雷川曾是十足的儒家学者,后与赵紫宸同在燕京大学任教,担任校长。由于没有接受西方教育的背景,他对圣经和相关书籍的阅读只能限于中文译本,这是他的苦恼,他描述:“基督教的教义,本是宏通普遍,真适应各时代的要求。可惜我于科学哲学,一点不懂。又不通外国文,凡是研究圣经的名著,没有译成汉文的,都无缘参考。偶然有一知半解,也算不了甚么心得。不得已勉强回答,只可说藉着每日读经,叫我不忘记我是基督徒。又因读经之后,稍用思想,有时也能策励自己的行为,叫我不至于成为腐败无用的基督徒罢了。”(注:赵紫宸、吴雷川、吴耀宗:〈我为什么要读圣经?用什么方法读圣经?〉,《生命月刊》第一卷第六册,1921年,第1页。)但这些问题并不妨碍他读圣经的热情,他自述读经是为了确立信仰,为了自己的得救,做了基督徒后,读经的动机转变为灵修,一方面是增进对于教义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以此检视日常行为。然而,研读圣经若仅为修身省察,这是不符合吴雷川的人生观的,内蕴于生命中的儒家伦理思想使得他倡导“人生唯一的原则,就是个人应当将所有的良知良能尽力发展,在言论,品德,事功,各方面,对于人类有所贡献。”(注:吴雷川:〈人格——耶稣与孔子〉,《生命月刊》第五卷第三期,1925年,第5页。)因此,将自己所信的传给他人,寻求以基督教的真理改造社会、救济民生,成为他读经的第二个动机,而事实上,在他信仰耶稣基督之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将学术研究的重心都放在了宗教如何“救人救世”,“自救”成为“救人”的前提,但也是在“救人”中得以成全。从这个意义而言,基督教对于他不仅是个人的福音,也是社会的福音,两者皆不可偏废。
从以上对赵、吴两人读经动机的考察中,我们看到,尽管他们都关注基督信仰在特定的历史处境下对于中国的贡献,提倡人格救国的方法,但是在具体的进路上,赵紫宸偏重个人的得救与灵性更新,而吴雷川则看重信仰的实践和社会功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要得生命”与“救己救人”也分别代表了他们读经的取向,构成各自诠释基督教经典的原则。
三、“用什么方法读圣经?”
确立了读经的原则,在回答“用什么方法读圣经”时,两人作出了不同的表述。赵紫宸的读经方法简单扼要,他说:“我读经之法有二,即是批判法与尚友法。批判圣经是要知每卷的人,地,时,文,旨;而免盲从,而得真知。用尚友法的缘由,是要与贤,圣,救主,上帝相通,藉以诚心以见天心,使我得到灵修充分的效果。但此二法的好处,也不外乎使我得生命,又使我所接触的人,都从我言行文章得着生命。”(注:赵紫宸、吴雷川、吴耀宗:〈我为什么要读圣经?用什么方法读圣经?〉,第1页。)在这里,赵紫宸提到了他读经的两种方法,一是“批判法”,具体而言,就是历史批判法,这是现代释经学常用的方法,注重的是经文被写作时的历史处境,即作者的身份背景、写作的对象、成书的原因、文本的体裁、格式等,这种方法能使读者“明白经文的历史背景及其用意”,但是它的局限在于“不能让我们窥见文学的特征及诠释过程中读者、经文与阅读本身的功能”(注:李炽昌教授编:《亚洲处境与圣经诠释》(亚洲处境神学论丛[二]),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导言部分,第1页。),即忽视了读者的社会处境对于诠释经文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意识到这一方法的不足,赵紫宸在“批判法”的基础上,又使用了“尚友法”,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与古代的贤人、圣人、耶稣基督以及上帝心灵相交,明白其教训和旨意,要达到这一点,只能通过一种“诚心”,即“宗教的虔心”才能做到,在这里,赵紫宸承认历史的、科学的方法不能帮助人完全解读经文,读经在很大的层面上是人与上帝的交通,一方面是人“对谒上帝”,聆听他的话语,另一方面是上帝对人说话,向人自我呈现。尽管在赵紫宸神学思想的早期,他还是倾向于从理性和科学的角度去解读圣经,但是他也认识到“诚心”对于读经的不可或缺性,关于这一点,到了30年代末,他有了更深入的体认,曾说:“我觉得读别的书比较容易,只有读圣经最难。在读的时候,我无论如何热心,依然不免怀疑而批评,而不懂经句中的真意思。历史的批判,科学的研究,好像害了我似的,使我不能直截了当地信受,纯粹彻底地享用。我读圣经,非有专籍的指引不可。其实,这并不可以为训。许多信徒诚心读经,把不懂的地方搁在一边,把了解的章句当作灵粮,受益要比我多的多。”(注:赵紫宸:〈谈谈我的心灵修养〉,载于徐宝谦编的《灵修经验谭》,上海青年协会1947版,第21页。)赵紫宸“批判法”和“尚友法”兼而并用的做法,表明他既想遵循圣经的诠释学传统,但又试图从个人的生命情境中领受经文的意义,因此,他的读经是历史的阐释与个体宗教经验的一种综合。
相对于赵紫宸的“批判法”和“尚友法”,吴雷川使用的是“与时俱进”的方法,即“我常盼望我的知识,能随着世界进化,也能就着现世界的情(形),与圣经上所说的事理,互相印证。凡是前人陈旧的解释,与现在社会不相合的,一切都不拘守。这或者可说是我内心所用的方法。”(注:赵紫宸、吴雷川、吴耀宗:〈我为什么要读圣经?用什么方法读圣经?〉,第1页。)我们看到,吴雷川是用进化的观点解读圣经,一方面,认为圣经上的事可与现世界相印证,另一方面,若前人的解释古不符今,则不拘守。
作为一个儒学背景浓厚的中国现代基督徒,吴雷川对于圣经的阐释不是基于西方的解释学传统,他的方法直接来自于其对宗教的体认,即与他特定的信仰公例有关。尽管信奉基督教,但是吴雷川是以一种十分宽泛而多元的意识来看待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首先,他没有特别强调基督信仰的唯一性和优越性,而是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处境中,基督教较之其它宗教和中国旧有的文化传统,更能为国家的变革提供具体有效的贡献,因此,他阅读圣经是要读出经文的当下意义,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表达,即他寻求的不是历史处境的相符,而是试图印证经文与现时代观念的契合。为了维护自己的解经立场,吴雷川提出了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宗教观念,即进化的宗教观。在其代表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他对这个观念作了详尽的论述,概括而言,他考察人的本能,认为宗教起源于欲求,欲求推动人生不断向上,因而宗教成为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既然它是社会进化的动力,因此它本身也必与时代一同进化,言下之意,宗教也是与时俱进的(注: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以下简称《基》),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1936年初版,1940年再版,第1章,第3页。)。基于这一认识,当他解读基督教经典和儒家经典时,他就不能接受那些灵异的内容,认为宇宙在进化,宗教在进化,这些存在于原始宗教中的神秘东西应该被去除。因此,他在读圣经时,无论对于基督教的教义,还是经文和材料本身,都是有所选择地加以解读和阐释的,挑选的依据就是自己进化的宗教观。对于吴雷川的“宗教是推动社会的原动力”这一主张,同时代的人是如何看待的?赵紫宸的批判可说最具代表性,他指出上述观点的缺陷在于:“他没有说宗教怎样能为推动社会的原动力,更没有以人对上帝的信念为这个力量”(注:赵紫宸:《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理与生命》第十卷第七期,1936年12月,第413页。)。他认为吴雷川从儒家的“人生而有欲” 出发,将欲求作为宗教的起源,是否表示宗教即是欲,“若然是欲,那末是哪一种欲?因为宗教发展欲,也禁止欲,限制欲?”(注:赵紫宸:《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理与生命》第十卷第七期,1936年12月,第414页。)他觉得吴雷川没有说清楚什么是欲,也没有解释欲是如何使得宗教成为社会进化的动力。另外,如果将宗教看作是与人的欲求有关的推动力,那么上帝何为?他仅是一个宇宙公例的奥妙,抑或大自然的法则?人神之间还需要沟通吗?显然,赵紫宸质疑在进化的宗教观之下,吴雷川所信仰的基督教已不是耶稣所传的宗教,他对于圣经作出的那些出人意外的阐释,例如“耶稣为基督”是“要取得政权以复兴犹太国”这样的代表性观点被认为是“没有历史根基的”,也不符合圣经所载的事实(注:赵紫宸:《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理与生命》第十卷第七期,1936年12月,第424页。)。在这里我们看到,赵紫宸是以其“批判法”(他的第一种读经方法)来评价吴雷川的诠释,强调解经“要知每卷的人,地,时,文,旨;而免盲从,而得真知”,因此对于吴雷川这样忽视“历史的阐解”的做法,就不能苟同。
对于赵紫宸的上述批评,吴雷川并没有直接撰文回应,但是若仔细考察他其后所写的重要著作《墨翟与耶稣》,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他的隐晦的辩解。在该书第四章的“耶稣略传”部分,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四福音书不是正统意义上的历史。具体而言,他发现这些著作“都不是耶稣在世时他的门徒所记载的。各书的著作年代,前人论说不一”,尽管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如何,它们的写成,总在耶稣去世后数十年乃至一百年, 自然它们所记的就不能认为是耶稣在世时的‘起居注’了。这些写福音书的人,既不会亲见耶稣的生平,他们或是根据前人所留下来的零星记载,或更加入当代所口传的耶稣故事,集和成篇。” 因此,“它们的性质本和正宗的历史不同。”(注:吴雷川:《墨翟与耶稣》(署名:吴震春),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1940年,第80页。)在这里,吴雷川对“何谓是历史的耶稣”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四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是有异同的,这与各著者的成书目的、“搜采之材料与编辑之方式”等有关,在著作中难免会加入自己的主观意见,而且又由于生活的年代晚于耶稣在世的时候,著者会将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与历史情势带入到写作中,这都会使得四福音书所记述的耶稣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历史的耶稣。既然经典本身存在这种主观意图的倾向,吴雷川认为涉及到个人的读经,当然可以“于其中选集材料,自不妨依照我们的观点以为取舍的标准。”(注:吴雷川:《墨翟与耶稣》(署名:吴震春),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1940年,第79至80页。)因此,他觉得从自己的宗教观念出发,对于经文加以剪裁选取,重新排列,读出“耶稣为基督即是改造社会”的原理,也是行之有效的。当然,鉴于赵紫宸的激烈批评,他在《墨翟与耶稣》中不再提及耶稣“是要作犹太人所想望的君王”,但是继续保留了其他的诠释和宗教观念。赵、吴二人不同读经法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传统的历史批判法和个人处境神学之间的张力,它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圣经的阅读者,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据经文的历史背景及其用意,但又不受其限制,同时又能在多大的空间上寻求建构适应当下处境的圣经诠释,又不使得阐解背离基本的信仰,这些问题相信对于每个时代的基督徒都是存在的。
其次,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及吴雷川对于宗教范畴的特定理解。在中国现代基督徒知识分子中,他一般被公认为是“最富折衷性的一位思想家”(注:邵玉铭:〈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态度〉,载于刘小枫主编的《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84页。),其基督教思想正是多种学说、主义、理论的混合。这很大程度上与他对宗教本身的体认有关,没有严格界定宗教的性质,以及它与其他学科、知识之间的区别。他在讲述宗教的概念时,一个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将它与人生哲学相提并论,他认为“人生自有史以来,宗教与人生,总是有着重要而密切的联系。所以在文化史中,宗教这个名词,与哲学,文学,科学,艺术,经济,政治等类的名词,早处于同等的地位。尽管它的内容或是幼稚而蒙昧,或是衰老而腐化,我们尽可以就着它不合理的事项竭力制止,并期望它的蜕化而演进,似乎不能就说它应当完全消灭。”(注:吴雷川:〈基督教更新与中国民族复兴〉,载于张西平、卓新平主编的《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此文节选自他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在这段话中,吴雷川提到了他对宗教的两个看法:一、宗教与哲学、科学等都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们在根本上无异。二、宗教不是“妨碍社会进化”的力量;它本身是在不断演进的,因此,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于他的第一个见解,他作过具体的论述,“进化的宗教即是人生哲学”便是从中延伸出来的观点,他自述这受到哲学家冯友兰的影响,后者即是将宗教与哲学等同起来,除了指出宗教“掺有神话及由之而起之独断及仪节形式,而哲学则无之,此其异也。”(注:参见冯友兰的《人生哲学》,转引自《基》,第5页。)吴雷川对此颇为赞成,认为宗教随着自身的进化,当铲除其神话及独断的因素,却可以保留它的仪式,以激发人的情感,他自己便对基督教的礼拜仪式极为推崇。但是,将宗教放置在人生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它还是信仰本身吗?赵紫宸对此提出过两点质疑:首先,“人生哲学乃是宗教经验的解释,不能便当作宗教”,言下之意,宗教不能与人生哲学划等号。其次,宗教作为信仰,它追求的对象当不仅限于人的幸福,但吴雷川更多地是关注宗教服务于人的向度,却忽视它同“超人超自然的对象”——上帝之间的关系。因此,他认为吴雷川对于宗教范畴的体认是人本主义的,是将一种宗教性当作了宗教(注:参见赵紫宸的〈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理与生命》第十卷第七期,1936年12月,第414-415页。)。
至于他的第二个见解,还是与当时的整个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回顾20世纪“五四”运动以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西方科学主义占据了中国社会的思想主流,无论是本土的儒、释、道等文化传统,还是外来的基督教信仰,都处在一个艰难的边缘化位置上。1922年北京大学学生发起了非基督教运动,得到了当时中国知识界领袖的支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场夹杂着民族主义成分的抗议:“基督教是洋教,所以要坚拒。”因而会以为反对的主旨在于“基督教与中国的精神不相称”,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读,以研究赵紫宸见长的西方学者古爱华曾指出:“正如前些时期评估儒家思想一样,现在人们要摆脱基督教,乃是因为它无关重要,而且在科学上也显得过时的缘故。”(注:古爱华:《赵紫宸的神学思想》,邓肇明译,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他将之称为是一个源于西方的理由。这种评价是一语破的,可以这样说,反基督教运动给中国教会人士带来的最大挑战不是基督教能否传入中国,而是它可否对中国社会适用。在这种情境下,寻求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显然让位于探求它对中国社会变革提供的实际功效。从这个视阈出发,吴雷川以进化的、发展的观念来看待宗教,正是试图为进化论和基督教神学之间的冲突作出某种调停的尝试。因此,除了提出“宗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这一主要观点,他也强调宗教自身处在不断进化的过程,它从原来原始宗教之“猥琐的供奉与祈祷,甚至杂用魔术”进化到“显然有高尚的理想,扩大的同情,热烈的毅力”的现代的宗教,即是明证。为了进一步调和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剧烈对抗,他更是提出了“进化的宗教与科学不冲突”的主张,按照其进化的宗教观,他认为宗教独断、摧残科学已成陈迹,证据是“宗教与科学,同起源于人的本能,也同循进化的常轨。”譬如,近人承认古代魔术(或术数)是科学的前身,科学就是魔术的进化。宗教也如此。因此,宗教与科学都为人类所需,“同彰显人类有管理世界的功能”。概括而言,宗教与哲学、科学同为不息的演进过程,故有永久存在的价值(注:《基》第1章,第5页。)。
如何评价吴雷川对于宗教与科学等之间关系的阐发?事实上,如前所述,这个问题也是当时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不能回避的,宗教与科学,经验与理性,究竟要哪一个,还是都要,这确实极大地困扰着教会内外。即便是对吴雷川作出激烈批判的赵紫宸,他也一直处在该问题引发的紧张的神学夹缝中,1950年初,他在写给何明华会督的信中,道出了一个中国基督徒在那时从事神学研究的窘迫境遇:“像我这样的人,要面对的是一个‘边缘处境’——我站在两个冲突的意见和两个冲突的时代中间,既不完全属于这一边,亦不完全属于那一边,我因此常常生活于紧张状态之中,有时非常的痛苦。但我决定了接受这种复杂性、相对性、悲观主义、自然主义、蒙昧主义的挑战,既要科学,亦要宗教,不是认为可以到上帝那里,乃是为他所掌握。”(注:此信写于1950年1月12日,现归于日内瓦普教协档案,转引自古爱华的《赵紫宸的神学思想》,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在赵紫宸神学思想的早期,他确实是想宗教、哲学和科学并举,并试图努力消除它们之间的不协调,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科学和宗教还是分属不同的范畴,譬如“不在科学界内的生活实体,如何可说是无存在的?”(注:赵紫宸:〈圣经在近世文化中的地位〉,《生命》第一卷第六册,1921年,第11页。)因此,他又认为宗教超越于科学和哲学之上,要达到它们之间的完全融合是不可能的。
较之赵紫宸对于宗教和科学的复杂看法,吴雷川考虑得更多是基督教的现实处境,他认为答复这个问题不仅是为了回应对基督教的排斥,更是出于“基督教能应付现实需要的真实性”之考虑,因此,讨论的重心就应该放在“基督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能有什么贡献”这一问题上(注:参见吴雷川的〈基督教更新与中国民族复兴〉,《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71-74页。)。在这个大前提下,他以进化论神学的观念看待基督教,指出其教义宏通普遍,当是适应各个时代的要求,因而,它不会与科学、哲学等产生冲突,同时作为亘古常新的真理,它又可以将现时代各种盛行的学说、主义纳入到宗教的范畴中,从中加以综合,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最有效的路径。
四、结语
如何评价赵紫宸、吴雷川的圣经诠释?作为中国现代自觉关注读经问题的两位神学家,他们代表了当时国人研读圣经的两种进路:一种是仍以历史的、经疏的解释为依据,强调圣经文本对于个体生命和灵性生活的意义,读经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达到人格的更新,其次是实现救国。另一种是从社会需求和读者处境出发,以预设的目的和观念解读圣经,重建基督教神学,寻求经文能够为特定时代提供的帮助。它们各自的利弊,我们在前面已经涉及。从对赵紫宸、吴雷川读经个案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的是基督教永恒不变的真理与不同时代地域下的解读之间的对抗与张力,而这种冲突反过来又丰富和延续了经典的生命,经文正是在不同向度和多重视阈的再诠释中拥有它的活力,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现代基督徒对于圣经的阅读,无论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挥,还是越出传统之外的“误读”,都为基督教圣经诠释学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样本。
标签:圣经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赵紫宸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基督教教育论文; 基督教论文; 耶稣论文; 科学论文; 读经论文; 经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