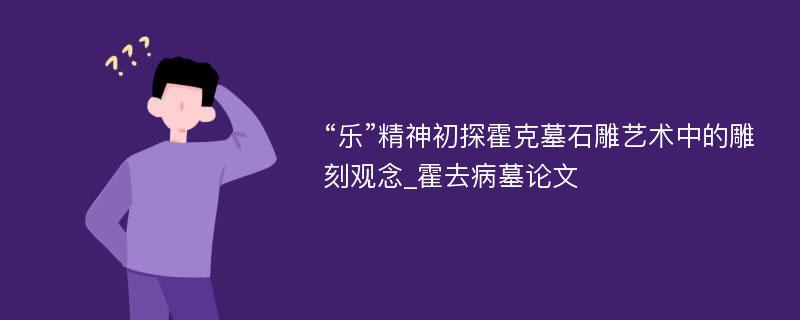
“乐”的精神——霍去病墓石刻艺术中的刻戏观念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石刻论文,观念论文,精神论文,艺术论文,霍去病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雕塑画意的审美境界
在我看来,中西传统的造型观念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即表现出的空间决然不同。以自我为中心的空间,把审美转化为自我通过艺术向世界敞开的活动是中国雕塑的母题。宗白华先生对绘画和雕塑作了比较,他说:“从绘画和雕塑的关系而论,中西就有不同。希腊的绘画立体感强,注重凹出形体,讲究明暗,好像把雕塑搬到画面上去。而中国则是绘画意匠占主导地位,以线纹为主,雕塑却有了画意。”(注:宗白华 《美学与意境》第3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一方面雕塑具有静止的、占有实在体积的物质形态,另一方面又向人类展示自身发展的演变历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雕塑呈现出自己本民族的特征,能长久地存留下来,并能直观地、形象地反映社会的精神面貌,以及人的心理状态;同时,这也是一个民族审美精神、人文底蕴、生命理想和历史衍变的集中体现。
重“道”轻“器”的古代社会风气,使古代中国人重“劳心”轻“劳力”。在艺术领域里,重文学轻绘画,苏轼谈到他的好友文同时说:“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也,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也,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拭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益寡,有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悲夫!”(《东坡全集》)古代中国人对绘画如此薄情,对雕塑更是不愿留下文字史料。被视为“匠意之作”“雕虫小技”的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未获得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立形态发展。或依附于宗教信仰,或依附于丧葬习俗,或依附于建筑装饰和工艺性的需要。对于同属于造型艺术范畴的绘画就更加依靠,“有画意”就成为其区别于西方雕塑的重要特征。这种“有画意”的雕塑,魅力独具的审美精神向往,自然自觉的隐藏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
中国雕塑滥觞于原始社会,成熟在秦汉。汉代石刻,是继夏、商周美术“文·素之变”后的又一个高峰,“表现在具体形象、图景和意境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注:李泽厚 《美的历程》第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汉代石刻的这些特征,在茂陵霍去病墓的景观石刻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二、意与象浑的无意识母题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霍去病死)上悼亡,发属国玄甲,军阵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司马贞《索引》引崔浩注云:“去病破昆邪于此山,故令为冢象之,以旌功也”。即霍墓之巨冢,具有表彰战功目的。
如果说,仅仅是为了纪念霍去病这样一位英雄人物而使用石刻,那可以用一尊雕像来表现,或者列置礼制性的仪卫形象。这类例子虽未见诸石雕,然而据历史文献记载,到秦代,中国雕塑由过去多为建筑装饰和工艺性雕塑向纪念碑意义的大型雕塑转变。
《水经注》卷十九“谓水”说:“秦始皇造桥,铁镦重不胜,故刻石作力士孟贲等像以祭之,铁镦乃可移动也。”
《西安府志》记载:“始皇引谓之长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为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尺,亦为兰池陂。”
从“秦俑坑”所发现的俑马群来看,汉之前已有类似的纪实性雕塑形式。然而,霍去病墓的石刻作品并未完全采用写实的雕刻技法和分组的排列方式,却使用分散置于树林的方法,还雕刻一些似乎与纪念意义无关的写意形象,如《鱼》、《牛》、《虎》、《蟾》、《蛙》、《野猪》、《卧象》等。雕刻者通过对点缀物的刻画,将霍去病将军转战祁连山,河西走廊大捷,破昆邪王的思想主题,巧妙地再现出来。早先置于墓前的《马踏匈奴》无疑是人格化的“以战马暗示和歌颂英勇善战的青年将军霍去病,用马间接地表现了人的精神。”(注:孙振华《雕塑文化论》第40页,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不塑立霍去病本人的纪念像,却以一马一人的形象,表现出强烈的开拓、征服和进取欲望。“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这里不会出现“罗可可(Rococ)”式的精巧繁密的装饰风格,也不需要牧歌式的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黄老思想”“楚风”(注:“世人多言秦汉,殊不知秦所以结束三代文化,故凡秦之文献,虽至始皇力求变革,终属于周之系统也。至汉代焕然一新,迥然与周异趣者。熟使之然?吾敢断言其受‘楚风’之影响无疑。汉赋源于楚骚,汉画亦莫不源于楚风也。何为楚风,即别于三代之严格图案式,而为气韵生动之作风也。”(邓以蜇《辛已病》))等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渗溶于汉文化之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融为一体的霍去病墓石刻的艺术观念母题,不像西方古希腊、罗马雕刻那样旗帜鲜明的用完美的人体来追求属于人自身的美。集理想化与现实化于一身的雅典卫城女像柱,表现了希腊人最真实的观念:“人是宇宙间最高贵的性灵,她可以战胜一切,克服一切,自然界的物质力量在她面前是渺小的,所以她无须为其皱一下眉头:人就是人。”(注:王可平《凝重与飞动》第145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8年第1版。)西方古代雕刻家把人类与非人类世界截然分开,将人类文化征服自然视为人类取得的进步。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不热衷于纯粹思辨而善于直觉体悟的联想思维方法,把人类和人类以外的世界看成是连续的,这与艺术创作的内部规律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写载其状”、“曲得其情”、“情境交融”、“意与象浑”的艺术原理是极有利于中国艺术创作与感悟的。
霍去病墓石刻是与大自然息息相通的艺术,无生命的石头却蕴含了丰富的“情”。对于天然形成的石头,古希腊雕刻家利用它雕刻肌肉的张驰紧松。以“对立的方式保持躯体的平横为准则,创造了诸如《掷铁饼者》、《荷矛者》和谐、优雅的希腊模式雕刻,应用比例、均衡、节奏,追求最美线形的目的都是为了让现实的感性生命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形式相结合。”(注:孙振华《雕塑文化论》第98页,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页。)汉代雕刻家利用它触发灵感,充分体现道家从出世立场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进一步强调人的精神和情感的交流是霍墓石刻的一个重要特征。首先,雕刻家“因材施雕”,把相似于马形的雕成“马”,把相似于虎形的雕成“虎”,把相似于鱼形的雕成“鱼”。其次,是“因势相形”,或卧、或立、或跃。依照其自然形成的朦胧轮廓,顺势稍作刻画,即造成一种生动的境界,达到“自然天趣”的神韵。表现为一己身心与自然、宇宙相沟通、交流、融解、认同、合一的神秘经验。
三、“刻戏”艺术观念的缘起
从“环境塑造文化”到“特定的环境塑造特定的文化特征”,再到“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形成了对环境理解的不同方式”。即多样的文化,取决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以“生态学”(Ecologies)的角度来看,“自然与文化是同一完整系统的组成部分,彼此分开但互相影响。”(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人类学的趋势》第31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德国表现主义画家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在《论我的绘画》中,鲜明地表明西方人的传统艺术创作态度:“艺术的创造是为了认识,而不是娱乐,是为了美化,而不是游戏。”艺术是认识世界、美化自然的手段。与之相对,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们则认为:兴邦济世、治国平天下的事业才是真正的事业;著书立说,是退而求其次;吟诗作画,仅仅是涵养性情,作画不过是诗余的墨戏而已。
从宋代米芾所提绘画“墨戏”说,到元代倪瓒称作画“乃写胸中之逸气。”中国文人画开始作为一种体现时代文化精神的潮流出现在绘画艺术中,元代以后至今,仍有来自个人情感体验的写意画之思潮,一直持续发展,统领中国画坛近千年。确实,这种“墨戏”的风格,似乎也只有从唐代以后的绘画作品中去寻找。
无独有偶,只要仔细看过霍墓石刻的人,都不难发现这样一种风格,笔者以“墨戏”为启发,把这种风格定名为“刻戏”。
从艺术形式的表现力而言,《马踏匈奴》在霍墓石刻中并不是最成功的作品,在处理马和人的形象上,由于受题材的影响,稍显拘谨,它历来为史论家述赞,多是因为它的主题思想突出,在表现祁连山大捷的内容上,具有代表性。关于雕刻家创作的自我意象淋漓尽致的发挥,却体现在仅作为“祁连山”点缀物的雕刻中。凶悍的《虎》、矫健的《马》、憨厚的《牛》、温驯的《鱼》等,经过雕刻家用园雕、浮雕、线刻相混合的技法,不拘一格地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充满英雄主义气魄,又极有浑厚气魄的《人搏熊》,作者对形体作了极度的概括与大胆矜夸,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以雄强古拙的气势和力量表现了人征服占有外部世界的胜利和乐观精神。”(注:李泽厚 《美的历程》第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在这一点上,又通过雕刻作品与自然环境、历史事件结合,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内涵,一种那个时代凸显出对人的本性和自然意识的折射。
霍墓设计意图是围绕着“象祁连山”的主题,包含主体活动的原因(目标、动机、假想),把石兽、石人、树木散置于积土成山的墓冢上,演一场“霍去病转战于祁连山”的“戏”。政治、经济力量的强大,在汉武帝时期得以实现。人对客体的支配能力胜过以往时代,在艺术创作实践中的“刻戏”意识得到充分体现。没有酷刑下的恐怖,没有对不可知命运的茫然无望。因此在霍墓石刻中没有秦兵马俑呆滞的形象,雕刻物体如作游戏般妙趣横生。《怪兽吃羊》的变形处理,尽管远离具体的外形,却更接近雕刻家来自内心的独白;《伏虎》以自然形成的曲线,构成虎的躯干部分;《怪人》的形象十分模糊,在关键处稍加刻画,刀法拙朴,舍做作求真挚。“刻戏”这种艺术样式,为探讨古代石刻艺术,增添了一份新的“意味”,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象,我们会蓦然发现自己在“戏”的情景中,产生了对时间与空间的再认识。
当西方人孜孜不倦地求证如何使艺术再现事物物理真实的时候,古代中国人在不断努力地探讨艺术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实践行为与思想方法的互补关系。以表意见长的中国艺术家对雕刻的理解,是永恒的万物相连的统一体,展现一种“乐”的精神。以天地为心以寻常生活为乐。中国雕塑的核心是同天地之和——重“艺”、重“神”,不重“技”。从对中国文化影响较大的《周易》来看,“夫象者,生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育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例·明象》)这其中的“得意忘象”理论在艺术创作上的意义,即是只有不拘泥于客观物质的外形定式,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意象”,影响着艺术创作在自然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的绘画,从古至今一直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而异于西方绘画。中国的雕塑,在佛教还未流传的西汉,以其纯真的中国面目,而令后世高瞻仰止。霍去病墓石刻集中体现出的深沉浑厚的撼人气势,其中焕发的生机,真挚与朴拙的宏大气魄以及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感染力贯穿于“乐”的精神之中,构成汉代雕塑艺术的主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