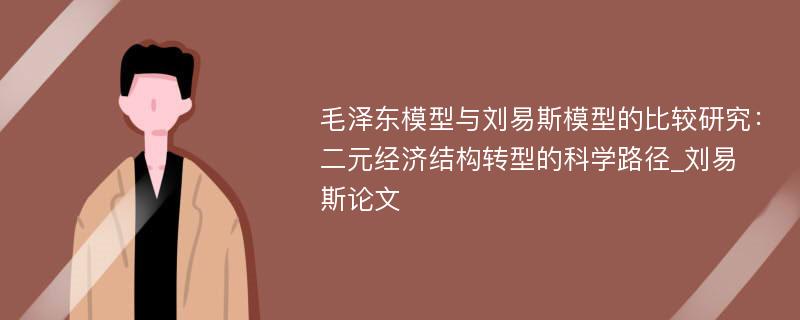
毛泽东模型与刘易斯模型比较研究——转变二元经济结构的科学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型论文,经济结构论文,路径论文,刘易斯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07-0050-04
毛泽东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生动体现①。本文把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称为毛泽东模型,受到中共党史专家鲁振祥教授研究成果的启发,并试图从刘易斯模型即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角度对毛泽东模型②即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科学性进行新的诠释,并通过比较研究提炼出转变二元经济结构的科学路径,为构建更加宏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大厦添砖加瓦。
一、毛泽东模型与刘易斯模型的同构性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作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流派,成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是其代表性学者。刘易斯认为,欧美发达国家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是由两大部门构成的,一个是停滞着的、劳动力过剩的、较大的农业部门(亦称为传统经济部门);另一个是较小的、不断增长着的商业化工业部门(亦称为现代经济部门)③。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即发展现代经济的基本途径是:现代部门以相当于传统部门生活水准的低廉工资成本吸收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进行资本积累。经济学界通常把这一理论称为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或刘易斯模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对于分析判断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的基本特点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也正是因为如此,刘易斯获得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由学者传入我国的历史不过三十年。但是,我们党从本质上科学界定中国的国民经济具有两类性质的经济部门并存的基本特点,则要比刘易斯早二十年,当然,字面上并没有直接使用“二元经济结构”概念。这一伟大理论贡献的“知识产权”属于毛泽东。
1928年毛泽东从井冈山起步走上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成熟。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出发论证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科学性:一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二是敌人的强大,三是红军的弱小,四是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毛泽东强调,在这四个特点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特点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做了如下阐释:“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隶属于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④
在这段话中,略过有关军事的内容,单纯看毛泽东用几个“同时存在”对当时中国经济状况的描述,就不难发现,“经济发展不平衡”作为概念所指称的客观事物同“二元经济结构”完全一致,只是政治家与经济学家的表述不同而已。毛泽东这样概括基本国情,既把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区别开来,也把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区别开来。正是这一理论,把中国的基本国情说透了,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科学根据;也正是这一理论,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沃土,并奠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崇高地位。
毛泽东所谓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中共党史上更一般的理论表述为中国社会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所谓“半封建经济”,就是传统地主经济主导下的小农经济,所谓“半殖民地经济”,就是鸦片战争后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这就是说,“两半”社会在经济上也是指二元经济结构。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早就把农村包围城市的具体实现形式即建立农村根据地称为“模型”。1941年5月,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的双重进攻,毛泽东充满信心地预言:“各根据地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⑤
那么,二元结构国家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动力产生于何处?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转变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现代部门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资本积累。或者说,在刘易斯模型中,“剩余劳动力”这个要素是最为重要的,它的转移形成经济发展即资本积累过程的基本推动力。无独有偶,毛泽东也高度重视农业剩余劳动力。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分析到:“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⑥农民进入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又因为他们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贫农”⑦,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贫农阶层便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群体。在毛泽东模型中,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⑧
基于上述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与“二元经济结构”的概念比较,我们便不难发现,毛泽东模型与刘易斯的模型具有同构性。不同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是从政治层面改造二元结构社会,而“转变”二元经济结构,是从经济层面改造二元经济结构。或者说,“包围”与“转变”也属于同构要素。更进一步,毛泽东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目的,不是由农村取代或领导城市,恰恰相反,是由城市领导农村,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工业国,消除经济发展不平衡,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现代化或一元化。
二、毛泽东模型与刘易斯模型的实践效果差别及其原因
毛泽东模型与刘易斯模型虽然具有同构性,但对比实践效果,后者却相形见绌。毛泽东从理论萌芽(1928年)到夺取全国政权(1949年),仅用了短短的二十年。相比之下,刘易斯完整地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已逾半个世纪,很多发展中国家也确实以该理论为指导发展国民经济,但至今还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是按照他的理论顺利完成现代化进程的⑨。如此巨大的实践效果(实证)反差提醒我们,有必要对毛泽东模型与刘易斯模型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
前述研究结果已经为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如下前提:(1)毛泽东与刘易斯对发展中国家(本文局限于中国)经济结构的判断是一致的、科学的;(2)“包围”与“转变”的目的都是以“现代”取代“传统”;(3)“包围”与“转变”的动力来源都是以“贫农”为主体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既然如此,一般的逻辑常识告诉我们,“包围”或“转变”的快与慢,取决于作为剩余劳动力的“贫农”们参与的意愿以及实际行动。更进一步,逻辑常识还将引导我们认识到,由意愿以及实际行动形成的“动力”有无与大小,取决于利益激励机制如何。不论是毛泽东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刘易斯信奉的市场经济原理,都能够得出这样的逻辑结论。依照这样的逻辑再回到毛泽东模型与刘易斯模型,就不难清晰地透视到,两者实践效果存在的巨大差别之根源在于利益激励机制:在毛泽东模型中,贫农获得了最大化的利益激励;相反,在刘易斯模型中,看不到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利益激励。
毛泽东指出,“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拥有战胜“强大”的统治城市的反动派的力量,是“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⑩众所周知,毛泽东所说的“自己的利益”是指土地。对于所有农民来说,拥有土地是他们的最大利益,对于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来说尤其如此。曾经积极参与国共合作的毛泽东之所以称蒋介石集团为“反动派”,正是因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早就规定了的“平均地权”的民主革命原则。历史的结论是:给不给贫农土地,成为决定国共两党战争胜负的终极原因。
但是,在刘易斯模型中,贫农就没有在毛泽东模型中那么幸运了。刘易斯创造了“生计工资”(11)概念。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被现代经济部门充分吸收干净之前,受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原理支配,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或城市经济部门)的劳动力只能获得与原来生活水平相当的劳动报酬,在劳动报酬之外的其余财富价值都作为利润归资本所有。然后利润不断资本化即再投资,继续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有当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了,工资水平才在供求关系作用下有所提高。
运用现代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工具考察毛泽东模型与刘易斯模型,便不难发现:毛泽东认为,贫农应当而且必须从“增量”——新建立根据地或根据地面积扩大中获得利益,即获得土地;而刘易斯却认为,在剩余劳动力还存在的条件下,贫农只能为“增量”——由于工业部门出现并扩大而增加财富价值做出贡献,却不能从中分享利益。
毛泽东从经济方面概括出来的中国基本国情,并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形成后得到了新的诠释,足见毛泽东之伟大;刘易斯创立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能够与毛泽东对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基本国情的概括相吻合,足见刘易斯之卓越。但他们最终在贫农亦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利益面前分道扬镳,则是由于他们各自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存在立场层面上的差异。毛泽东的理论理所当然地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对于本文把刘易斯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进行评论也许不以为然。其实,刘易斯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刘易斯指出:他的理论遵循了“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家”的基本假定,即“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12)。但是,在如何看待资本家对雇佣工人仅“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这一事实及其后果问题上,刘易斯又与马克思分道扬镳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资本,刘易斯的理论恰恰相反。显然,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按照刘易斯的理论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必然是占人口大多数、劳而又苦的农民和雇佣工人难以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这样,微观经济层面上劳动力难以形成拼命工作的动机,宏观经济层面上则因为大多数人购买力低下而难以形成广大的国内市场。在这样的国家,现代经济部门发展的利益被少数社会精英群体垄断,很难形成持久而强大的发展源动力。所谓“发展陷阱”,也许就是这样造成的。
三、先进群体引导激励落后群体:转变二元经济结构的路径选择假说及其检验
在毛泽东模型中,用于激励劳动者的利益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从表面上看是进行土地革命即靠暴力手段平均地权。但是,如果把中国革命的成功仅仅归结为平均地权,则会大大低估甚至是歪曲毛泽东模型中的主导性要素即“党的领导”的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通过平均地权化解因农民无地或者少地造成的社会危机,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在以几百年为一个周期的改朝换代中,有作为的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多多少少都要推行均田政策。在皇帝专制下,即使一时实现了均田,仍然不可能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实质,因为皇帝本质上就是地主(13)的代表,或者说皇帝就是拥有无限权力的最大的地主。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传统地主没有任何联系,虽然中共党员可以出身于地主家庭,但作为政党,她诞生的条件是中国近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城市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形成了独立的工人阶级群体。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城市而非农村,她是城市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非农村的农民团体。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伊始就公开宣布,她领导下的土地改革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用目前中国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制度经济学术语解读这一政治纲领,就是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而非修复旧制度。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是影响社会经济运行成本与效率的基本要素。以好制度取代坏制度,必然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利益。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中,富人尤其是地主不劳动或很少劳动,却获得了大量财富,农民和雇佣工人拼命劳作却温饱不得。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入手,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理所当然地会产生巨大的制度变迁收益。作为这种制度变迁收益的实证数据,新中国成立最初三年,全国工业与农业的总产值年均递增率分别达到34.8%和15.3%(14),此后,中国农业生产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增长,比较好地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难题。形成这样巨大的制度变迁收益,首先因为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这里不仅是贫农生产热情高涨,也包括把占人口10%左右的地主由寄生阶级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次还因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还为农业技术创新和组织制度创新(如办合作社等)开辟了道路。
毛泽东模型中“党的领导”作为制度要素,其最大价值不仅在于实现平均地权层面上的制度创新,更在于实现这种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表明她要代替国民党,单独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共产党如何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决策层最初选择的革命道路是“城市武装暴动”。“城市武装暴动”模型并不是不要进行土地革命,而是主张主要依靠工人在城市搞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以后,自上而下地把土地作为革命成果分给农民,甚至是“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进展”(15)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1927年中国共产党相继发动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大大小小的城市武装暴动全部失败(16)。在残酷的流血斗争和党内理论争论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共产党人探索出完善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17)。与“城市武装暴动”模型相反,在毛泽东模型中,“党的领导”的作用不是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直接把农民带入社会主义社会,让其坐享其成,而是共产党到农村发动农民起来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这样,“党的领导”在毛泽东模型中就成为重要的制度变迁变量,其功能是实现科学的路径选择。农民一旦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形成了推翻旧制度的排山倒海般的力量,不仅他们的最大利益诉求得以满足,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也得以实现。
对城市武装暴动模型与毛泽东模型做更进一步的比较还会发现,两者在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形成不同的路径选择,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如何看待二元经济结构中处于落后地位上传统农民。前者仍然把参加了土地革命的农民与传统农民同等看待,认为他们落后、保守、自私,甚至还把共产党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方式”,反映出“党的政策带有农民意识”(18)。后者与此相反。毛泽东认为,“革命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19)这就是说,毛泽东并不是没有看到农民落后的一面,而是他认为,在“落后的农村”中引入“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制度变量,就可以使之变为“先进”。
我们党认识到现阶段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深层次矛盾突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科学认识的升华。我们重新领悟毛泽东模型提示的转变二元经济结构的科学路径,对于更加自觉地推进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
注释:
①(17)(18)鲁振祥:《探索的轨迹》,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261页;第181~203页;第88页。
②参见鲁振祥著《史事追寻——中共思想史上若干问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③参见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④⑦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第643页;第190页。
⑤⑥⑧(19)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页;第626~627页;第785页;第635页。
⑨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1期。
(11)后来,费景汉和拉尼斯两位教授又把“生计工资”改称为“固定制度工资”。
(12)刘易斯著《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3)这里的“地主”概念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土地改革时划分农村成分意义上使用的。
(14)(15)(16)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第81~83页;第74~84页。
标签:刘易斯论文; 二元经济结构论文; 刘易斯模型论文; 毛泽东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 科学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