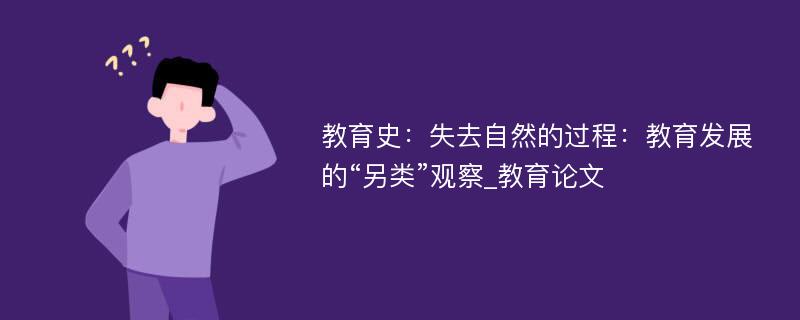
教育历史:本性迷失的过程——对教育发展的“另类”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性论文,另类论文,过程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3)02-0001-05
本文旨在对近80多年来先后对我国教育史研究(本文主要涉及外国教育史研究)发生较大影响的三种教育史观进行反思,并就如何认识教育进步和发展历史的本质提出初步的见解,以就教于大家。
一
近80多年来,由于社会发展、意识形态和知识状况的不同,影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历史观念前后具有明显的差异。大体上,主要有三种教育史观对外国教育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其中包括:
(1)20世纪20-30年代中期的进化论教育史观。在这个时期,由于我国现代师范教育的发展,作为师范院校课程体系组成部分的西方教育史学科很快形成,出现了如姜琦、蒋径三、雷通群、瞿菊农等著名的教育史家,先后出版了《西洋教育思想史》、《西洋教育通史》、《西洋教育史》等著作。这些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受到美国教育史家孟禄(Paul Monroe)和克伯莱(Ellwood Cubberley)等人的进化论教育史观的直接影响。
根据这种进化论的教育史观,教育历史所反映的主要是教育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例如,孟禄在其著名的《教育史教科书》(1905年)中,当叙述到原始社会的教育时,就曾明确指出:“原始社会以最简单的形式展现了它的教育。但是,教育过程的早期阶段却包含了在其高度发达阶段所具有的全部特征。”(注:Paul Monroe.A Text-Book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New Youk:The MacMillan Company,1905,P.1.)从这段话可以看到,尽管与先前的一些教育史家不同,孟禄并不完全否定原始社会教育的意义,但仍然把它作为一种低级阶段的教育,并认为它的意义主要在于是更高阶段教育发展的基础。克伯莱在《教育史》(1920年)中,则把教育的历史当作西方文明兴起和进步历史的一个方面(注:Ellwood P.Cubberley.The History of Educa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20,Preface.)。
(2)从20世纪50-80年代,苏联教育史家米定斯基、康斯坦丁诺夫等人的著作对我国教育史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载体是曹孚先生编译的《外国教育史》。它是以后多种外国教育史著作、特别是教材的模本。
米定斯基、康斯坦丁诺夫等苏联教育史家的教育史观主要是依据《联共(布)党史》中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认为人类教育与人类社会一样,先后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
与20-30年代进化论教育史观的影响不同,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教育史家的这种教育史观不仅是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同时也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凭借着强大的制度力量,而渗透和影响着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因此,它所产生的力量是极为巨大和根本性的。由于这种原因,1949年以后由国内学者编写的外国教育史教材,无论在体例、历史阶段分期上,还是在人物评价的主要结论方面,都受到这种教育史观的直接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它的影响。
(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运用现代化理论的方法和概念,对教育历史发展的本质进行分析。根据这种研究范式,教育的历史进程被认为是教育现代化的过程,教育的制度化、世俗化、法制化、普及化、科学化等被认为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指标,现代性的获得被认为是教育现代化过程的目标。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张斌贤等人的《西方教育思想史》(1994年)、储宏启的《英国教育现代化的路径》(2000年)等。
上述三种教育史观尽管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其思想的实质是一致的,即它们都强调人类教育历史的本质是教育本身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从非正规到正规发展和进步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线形的、不可逆的,同时也是普遍的和必然的。另一方面,它们通常都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教育发展和进步的过程设定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并认为这个目标是历史过程内在的和逻辑的结果(而不是人为确定的)。
这种把发展、进步当作历史进程本质的历史观念,不管它们自认为受到何种理论的启发,本质上都反映了西方近代以来形成和不断系统化的进步观念的巨大影响,本质上都是进步观念在教育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英文中的“进步”(progress),是拉丁文pro(向前)和gress(走)的合成词,它最初出现于15世纪,此后,其语义一直保持相对的稳定:表示向上、向前或更高阶段和状态的运动、行动、活动。(注:J.A.辛普森等.牛津英语词典[Z].牛津:克莱伦顿出版社,1989.593-596.)
从16、17世纪开始,进步不仅作为一个名词,而且逐步形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观念。在这个时期,进步主要被看作是知识或智力领域中的事情,或者说确认知识、智力处于进步过程之中是进步观念的基本特征。哥白尼、培根、笛卡儿等人为进步观念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到18世纪,由于启蒙运动的影响,进步观念逐步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支配社会生活和历史创造活动的大观念。孟德斯鸠、杜尔哥、孔多塞、狄德罗、亚当·斯密、赫德尔、康德等人为进步观念的扩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了19世纪,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对进步进行了历史逻辑的证明,圣西门和孔德等人确认进步是社会演变的规律和组织机制,斯宾塞等人运用进化论,使进步观念超越历史和社会领域,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注:参见姚军毅.论进步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彼得·欧皮茨:“‘进步’:一个概念的兴衰”,中国社会科学季刊[J].香港:1994年夏季卷.)
根据进步观念,发展、进步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人和社会都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人性不断改进,日臻完善,社会则朝着更加美好和繁荣的理想状态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是永远不会停滞和终结的。正如S.波拉德(Sidney Pollard)所概括的那样:“……一种进步信念暗含着这样的假设:人类历史中有一种变化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可知的,它构成不可避免的仅仅朝着一般方向——人类事物由不甚令人满意的状况逐步改善为更令人满意的状况——的变化。”(注:S.波拉德.进步观念——历史与社会[M].引自姚军毅:论进步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12.)孟禄、克伯莱、米定斯基、康斯坦丁诺夫等人的教育史观,以及在现代化理论影响下形成的教育史观,实际上正是这种大观念在不同时期中的不同作用结果,是不同形式的进步教育史观。
二
但是,人类教育的历史果真如进步教育史观所断言的那样,是教育在一种近乎宿命般的规律作用下,朝着一个同样宿命般的美好目标坚定向前的过程吗?
刚刚过去的20世纪,被公认为是教育取得决定性发展的时期,是教育现代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凯歌行进的黄金时代。但当我们冷静审视近百年来、以至于几百年来世界教育发展和教育现代化的结果,我们看到了什么?或者说,教育发展和教育现代化除了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益处的之外,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1、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教育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在世界多数国家,教育已经成为最大的公共事业:在教育事业中活动的人员(教师、学生、管理人员)数量日益增加,教育经费在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教育占有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占有了巨大社会财富的教育,本来应如她曾经承诺的那样,为社会的真正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我们所能看到的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为人们描绘的通过普及教育、传播知识和发展理性,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幻影。在当今世界,教育在自诩推进社会正义的同时,却使人群之间、阶层之间、社会之间、民族之间、种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2、教育全球化(或国际化)的洪流所到之处,世界各地、各民族和种族在教育的价值、文化、方法、内容、体制等各个方面的差异日益减少,各国教育在整体上日益趋同,教育传统的多样性正如生物的多样性一样不断减少;世界教育的生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
3、教育的泛工具化。在当今时代,教育已经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国家安全、文化建设等的纯粹意义上的工具,学校正在成为巨大的社会服务站和知识超市,以尽可能地满足不同人群的千变万化的需要。而当教育和学校在履行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的同时,教育和学校最为基本的职能——促进人作为独立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却被遗忘了或消失了。
4、教育的高度制度化使教育和学校日益成为机器,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环节都被加以严格的规定和程序化,都被要求按照严格的工艺、技术标准进行操作。教育活动的艺术性、创造性在高度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技术化的指令中被扼杀了。一个人在其一生中什么时间接受教育、接受什么教育、以何种方式接受教育(包括由谁进行教育)、所受教育应达到何种标准、何时完成某种教育,等等,都被某种权威预先以种种方式加以确定。教育活动几乎是天然的人性、灵性和个性要素在学校这个巨大机器的运转中湮没了。对教育历史有兴趣的人们常常叹息,为什么在杜威之后,世界上几乎没有再产生可与杜威相比肩的伟大教育家?如果这个问题能够成立,那么,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度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教育和学校运行既不需要、甚至也不允许具有创造性和个性的思想和理论的出现。在日益机械化的教育制度的运行中,指令完全取代了独立的思考。
5、教育本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基本的内在需要,但是,由于教育权利逐步从家庭权利变成为公共权利,(注:秦惠民:走入教育法制的深处——论教育权的演变[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教育却成了被强制履行的义务,成为与人自身的需要几乎没有关系的活动,教育活动最为根本的基础——人自身的本质需要,被公共的意志和需要所取代。由此造成了教育过程与生活过程的割裂、教育过程与生命过程的割裂。在这种情形下,教育从人的内在的活动变成了纯粹外在的活动。
6、不仅我们的教育行为发生了严重的偏差,现代人对教育的基本认识或信念也同样出现了扭曲:
(1)我们或者把教育当作一种义务,当作是人生历程中不得不完成的一门必修课,教育成为一种强制;
(2)我们或者把教育当作是一种职业,当作社会劳动分工的一个环节,当作是谋生的一种手段;
(3)我们或者把教育当作是一种专业,当作培养未来教师的一个阶梯;
(4)我们或者把教育当作是高等学校中讲授的一门科目,当作学者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
(5)我们或者把教育当作是某种专业或职业技能的训练,当作是未来从事某种职业的准备;
(6)我们或者把教育当作是提高个人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一种阶梯,当作在激烈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武器;
(7)我们或者把教育当作是实现社会目的的工具,当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手段;
(8)我们或者把教育当作是在某个我们现在称之为学校的机构中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进行的某种专门活动,……如此等等。
尽管现代人自觉对教育的认识已经或正在不断深化、拓展或进步,但真实地说来,由于人们更多地是从教育可能承担的功能或实际承担的功能,更多地依据现代社会某种方面的需要、现代社会的某些价值观来认识教育的使命,来理解教育的属性(并且把现时代的认识和理解投放到对一切时代教育的把握),我们现在离教育的真正意义是越来越远了,远到我们实际上已经很难把握教育的本性(如果还不是不可能的话)。
三
以上种种,不禁使我们反思,迄今为止的教育历史究竟是如进步教育史观所坚信的那样,是教育自身不断发展和日趋完善的过程,是教育本质不断呈现的过程,还是教育本性不断丧失、不断被遗忘的过程?
按照我的观点,迄今为止的教育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教育本性在实践中不断消解、不断丧失,在认识上不断狭窄、混乱的过程,是教育日益远离其真正本性的过程。
为了认识教育的本性,我们必须重新回到人类教育的原初状态。史前时期是人类教育的童年时期。从民族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教育的雏形,而正是在这种雏形中,我们看到了人类教育的天性。正如我们可以在儿童身上看到人类的天性一样。
教育史家孟禄、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等人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史前时期,教育的主要方式就是未成年人对成年人行为和活动的模仿,这种模仿是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进行的,它无时不在,它与生活过程是一致的,它本身就是生活的一种形式、生活的内容,它是在生活中、通过生活、为了生活而进行的。就其本性而言,教育产生于人类种族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基本需要,教育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式。教育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生活的东西,而是与人的生活具有天然的、内在的联系。(注:Paul Monroe.A Text-Book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Chapter 1.)
随着人类教育制度化的发端,教育本性迷失的过程就开始了。这个过程经历了四个关键的阶段:
首先是书面语言(文字)的出现。书面语言的出现大致在距今6000年前。按照教育史家以往的观点,认为文字的出现被认为是“提高了文化积累和传递的效用,提高了对新生一代教育的效用。它是由非正式教育过渡为正式教育的关键。”(注: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20.)但在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书面语言的出现,使人类种族的经验得以抽象化,并固化为符号。它固然扩大了意义表达的范围,但由于把种族经验逐步限定在书面语言,更重要的是,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书面语言对口头语言的压迫、形成了对书面语言的崇拜,一切非文字形式的种族经验逐步被排斥在教育活动之外,人类种族经验的传递在数量和内容上,被大大缩减了。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书面语言的出现,人类经验的性质和传递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抽象的、间接的经验取代了具体的和直接的经验,文字记录代替直接的生活成为教育活动的主要媒介,教科书成为人类种族经验的权威象征。从这个时候开始,教育就逐步脱离开与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天然联系,逐步正规化和形式化。
其次是学校的出现,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最早的学校出现在公元前3500年前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注: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29-42.)学校的出现使人类的教育活动逐步被限定在这个被称之为学校的场所,又逐渐被限定在教室,并由此逐步形成了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严格区分,进而逐步形成了正规教育对非正规教育的歧视、压迫。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包括教学计划、课程表、学期制、学年制、班级授课制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制度的形成和不断严密,学校的各项活动日益正规化、制度化,学校日益成为专门化的、具有高度排他性的教育机构。其结果是,一方面,形成了受过教育(有教养)和未受过教育(没有教养)人群的区分,由此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了社会等级的鸿沟。不仅如此,在大多数文明社会中,接受学校教育、特别是接受较高程度的学校教育,成了区分身份、地位的标志。教育这个纯粹人道的事业被用于完全非人道的目的。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教育与生活的界限,并开始出现学校与社会的割裂。教育的日益专门化、制度化,是以教育更大程度上脱离生活现实为代价的。正如杜威所说的那样:“从间接的教育转到正规的教育,有着明显的危险。参与实际的事务,不管是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在游戏中参与,至少是亲切的、有生气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优点可以补偿所得机会的狭隘性。与此相反,正规的教学容易变得冷漠和死板——用通常的贬义词来说,变得抽象和书生气。低级社会所积累的知识,至少是付诸实践的;这种知识被转化为品性;这种知识由于它包含在紧迫的日常事务之中而具有深刻的意义。但是,在文化发达的社会,很多必须学习的东西都储存在符号里。它远没有变为习见的动作和对象。……正规教学的教材仅仅是学校中的教材,和生活经验的教材脱节。永久的社会利益很可能被忽视。”(注: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3-14.)
教育制度的建立。在西方,学校教育制度的基本结构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中世纪出现了现代大学的雏形,文艺复兴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学,宗教改革时期产生了近代最早的小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实行统一的国民教育,最终形成了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教育制度的建立及其组成部分相互关系的不断重组,使教育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王国,成为一架巨大的、高效运转的机器。各种关于入学、课程、考试、评价等的规章、规定、条例、措施,不仅决定了人学习什么,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怎样学习,而且决定了应当达到的标准。由于教育制度的无所不包,它不仅控制着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而且支配了人的一生,甚至决定了人将成为什么。正是在这样一个被精心设计的过程中,人的社会化实现了,而人的个性却被湮没了。
教育国家化。自有国家之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就不断受到来自国家机器的种种影响。国家以各种方式(颁布饬令、上谕、法律,建立教育管理机构和开办官学)对本国教育施加影响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但是,只是从19世纪、特别是从20世纪以来,国家才真正获得了完全控制本国教育的能力,教育才真正从个人权利变成公共权利,才真正成为国家的职能。通过教育立法、建立教育管理机构、支付教育经费、开办学校以及制定相关规定、标准,国家日益全面和深刻地控制了本国的一切教育事业,教育因此日益成为国家意志的产物,人因此也完全成为按照国家意志而培养和造就的产物。
对进步教育史观的批判和对教育发展的“另类”观察,既不是对进步教育史观的全面否定,更不是对迄今为止的人类教育发展的否定,而主要在于通过转换视角,提供一种思路,以便进一步深入和全面认识、理解教育发展和进步历史的本质,从而使我们不至于完全被现代主义的教育历史观和教育价值观所束缚。在今天,这样一种视角转换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对教育发展和进步本质的全面、深刻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科学地确立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制定教育全面发展的战略,从而使中国教育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