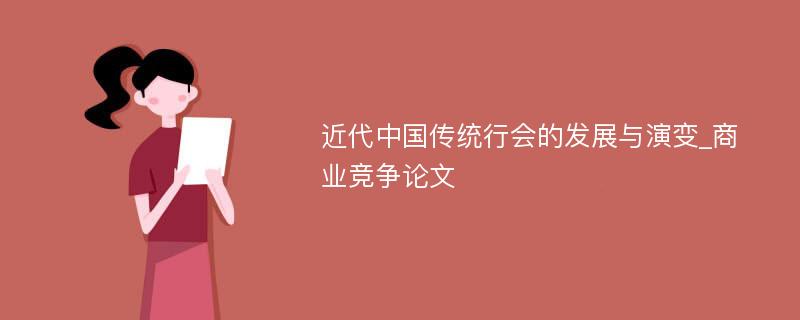
中国传统行会在近代的发展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会论文,中国传统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的行会,是进入近代以前就已存在的同业组织。这种传统的同业组织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曾在社会整合与经济运作进程中产生过比较重要的作用。但到晚清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日益入侵,中国传统经济逐步瓦解,新的经济成分不断增长,面临着这些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的行会组织在许多方面明显表现出难以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缺陷,于是也不得不出现若干新的嬗变,到民国以后更被新型同业组织——同业公会所替代。考察传统行会在近代所遭遇的困境及其演变,对于了解同业公会的产生与作用将不无裨益。
一、传统行会在近代面临的前所未有挑战
关于中国传统行会的功能与作用,外国学者较早即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进行过探讨。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行会在政治方面的势力与影响较弱,但也有学者认为行会这方面的功能较强。前者以魏复古、韦伯、梅邦等为代表,后者以哥尔、朱尼干等人为代表。日本学者清水盛光曾详细分析上述各家之说,其结论是中国行会在政治方面的影响是软弱无力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割据主义而受到外延的限定,另一方面因为国家官僚势力的存在而受到内涵的限定”,归根结底则是由于“都市之空气并不自由”。清水盛光还认为,“中国行会的特征是政治势力的脆弱性和其活动范围只限于经济生活”,换言之,行会在经济上对成员的统制力非常强大(注:〔日〕清水盛光:《传统中国行会的势力》,日文原载《满铁调查月报》1936年第16卷,第9号,中译文载〔台北〕《食货月刊》1985年第15卷,第1、2期。)。这一结论大体上是能够成立的,因为中国的行会确实在政治上不仅没有多少权力,实际上也较少开展这方面的活动。同时,中国行会在经济上对同业的限制与约束较为严格,由此可以说行会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的势力。
事实表明,在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行会确有其独特的功能与作用。特别是到明清时期,行会已较为普及,在经济方面所产生的多重作用与影响更是令人注目。就一般情况而言,传统行会的功能与作用,主要体现在限制招收和使用帮工的数目,限制作坊开设地点和数目,划一手工业产品的规格、价格和原料的分配,规定统一的工资水平等(注:刘永成、赫治清合撰的《论我国行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载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业内和业外的竞争,维护同业利益,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手工业和商业的运作具有某种规范作用。对中国传统行会的这些功能与作用,绝大多数学者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也有学者强调,行会虽采取各种措施限制竞争,并不意味着行会内部就因此而不存在竞争。
不过,除了经济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之外,中国的传统行会还具有西欧行会所不具备的某些功能。例如许多行会都十分重视联络乡谊,救济同业,办理善举,尤其是外地工商业者和商人建立的会馆、公所,更是将其作为重要职责。因为外乡人在他乡异地无论是经商还是经营手工业,往往会遭遇更多的困难,需要相顾相恤。传统的中国又是一个非常重视乡土人情的国度,外出经商者常常按地域籍贯形成商帮,遇事即互帮互助,行会作为工商业者的组织也自然而然地承担了这方面的职责。如同苏州蜡笺纸业绚章公所建立碑文所说:“身等朱蜡硾笺纸业帮伙,类多异乡人士。或年老患病,无资医药,无所栖止;或身后棺殓无备,寄厝无地。身等同舟之谊,或关桑梓之情,不忍坐视。……现经公议,筹资……建立绚章公所,并设义塚一处,……身等同年,轮流共襄善举。”(注:南京大学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8页。)这表明中国传统行会在慈善公益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功能与作用。
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受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作为传统经济组织的行会也面临过去所没有的新处境,在许多方面或被动或主动地相应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关于鸦片战争后中国行会的演变,学术界的论断并不一致。
一部分学者认为传统行会的功能与作用在近代已逐渐消减,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与发展,对行会制度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并导致其衰落。新式商人团体商会的诞生,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工商各业传统行会组织的功能与作用受到削弱,行会已呈现出解体的趋向。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城市经济结构和功能的外向化和资本主义化,上海、汉口、广州、天津等外贸中心城市的传统行会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不仅没有走向衰落,相反还在数量上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并且在性质上开始逐渐资本主义化。
上述两种不同意见,从表面上看是相互矛盾的,但实际上却揭示了行会在近代同时存在的两种历史命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经济逐渐被动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部分传统的手工业和商业,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冲击,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渐走向衰落,这些行业的行会也难以为继。不过,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出口贸易获得了迅速发展,又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商业和手工出口加工行业,并在这些行业中相应产生了新的行会。同时,中国原有的一部分与进出口贸易相联系的工商行业,在鸦片战争后受对外贸易发展的刺激,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些行业的行会组织也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并未明显出现衰落的现象,有些行业甚至还成立了新的行会。
类似的情况,在一些通商口岸城市是比较突出的。例如上海的洋布公所、洋油杂货公所、震巽木商公所(洋木业)、集义公所(进口海产业)、蛋业公所、报关业公所,汉口的西皮杂货公会、洋广杂货公所、猪鬃公所、混元公所(蛋业)等,都是随着这些新兴的外贸行业的产生发展而成立的。旧有行业在对外贸易中获得迅速发展而建立行会组织的行业,在上海有丝业会馆、茶业会馆、煤炭公所、丝绸业公所,在汉口有茶业公所、皮业公所、油业公所(桐油业)、钱业公所、商船公所等。
应该注意的是,进入近代以后,无论是原有的传统行会还是新成立的行会,都面临着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形势,在各方面承受着较大压力,需要进行自我调适,不断采取新的举措,否则就很难发挥其作用。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行会的传统功能与作用在新的条件下已难以像过去那样得到切实的贯彻。我们知道,传统行会对同业的种种限制措施,包括限制招收和使用帮工的数目,限制作坊开设地点和数目,划一手工业产品的规格、价格和原料的分配,规定统一的工资水平等,都是为了防止业内和业外的竞争,垄断市场以获取高额利润。行会对同业的这些限制,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很发达的历史条件下,一般能够借助官府告示的形式得以顺利执行,很少有违规者表示不服或是采取反抗行动。但是到了近代,封建经济已逐渐解体,不仅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而且民族资本主义随后也产生并不断发展,商品经济成为不可阳挡的历史潮流。不仅如此,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自由竞争。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行会如果一成不变地保持传统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在开店设厂、招收学徒、以及产品规格和价格、原料分配等方面继续用行规加以严格限制,力图防止和阻挠竞争,不仅成为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而且在实践中常常受到抵制。
例如苏州煤炭业坤震公所1910年重订行规,要求“凡各店出货,秆皆由公所较准,一律十五两作一斤为公秆,发给各店”使用;售价“由公所集议”,各店“照单出售,不准高抬,并不得贱卖”;进货也“由公所发给盖戳起货票,方准起驳”。如有违例者,“公所即发知单,邀集同人开会,酌量议罚,以戒不谨之风”(注:苏州市档案馆藏档:苏州商会档案,第32卷,第9页。)。但是,这种沿袭传统限制同业的旧式行规,并未得到该地170余户同业的一致接受,迁延达4个月之久也未获通过。最后,坤震公所不得不对其作了重大修改,有关统一使用公秆和管理进货的规定被删除,统一售价的规定也改得较前松动(注:苏州市档案馆藏档:苏州商会档案,第401卷,第19页。)。与此相似,苏州靴鞋业履源公所草章中有关“公所会议定价,不得自行高低”的行规,在重订章程中也被删去(注:苏州市档案馆藏档:苏州商会档案,第1181卷,第4页。)。
在近代,工商户突破行规的限制与约束,向行规挑战的事例也屡有发生。1909年苏州肉业敬业公所为限制新店开设,垄断店行交易,在旧方式难以控制的情况下,又与猪业公所订立了一个“联盟信约”,试图切断新设店铺的货源。尽管如此,公所也仍然不能切实控制新店铺的开设。就在敬业公所与猪业公所的盟约订立不久,即有张氏、任氏两家新店“违规”开业。猪业公所恼羞成怒,多方阻止,张氏和任氏对公所的压力坚持不从,直至双方对簿公堂,最终公所也未能制止张氏、任氏开店。尤其令公所业董十分恼火的是,在双方激烈争讼之际,同业中的杜某等十余人不仅不站在公所一边,相反还联禀控告业董勒捐肥己的劣迹,公开支持张、任二人向公所挑战(注:苏州市档案馆藏档:苏州商会档案,第205卷,第13页。)。行会陷入这种尴尬的处境,在过去是很少见到的。
到民国时期,行会的传统权威更进一步受到侵蚀而遭遇挑战。当时,一部分外国人在华考察时也明显感觉到这一情况。例如1919年美国商务官员阿诺尔德出版的《中国商业便览》一书写到:“在中国,竞争尚处于极其旧式的状态,行会成员以低于规定的价格出卖产品的情况一再发生,对此,行会实际上已不可能防止”;驻广东的美国领事也说:“由于行会要求其成员采用相同的工资和价格,大多数行会成员甘冒被行会除名的危险,秘密地违反行会的这些规定”;日本学者在北京进行实地调查后,同样指明“由低价出卖所引起的同业之间的纠纷是很多的。绸缎洋货行、药行、烟草行、制鞋行,如果问到纠纷之事,首先都会举出这种竞争所引发的问题”(注:王翔:《近代中国手工业行会的演变》,〔北京〕《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63页。)。
类似的现象,在其他许多地区也是屡见不鲜,实际上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因此,晚清时期即有行会不得不在限制约束同业开店等方面有所放松。就一般情况而言,鸦片战争以后,通商口岸的行会虽然对同业行号的业务活动仍有种种约束,但已不如以前那么严格。比较明显的是外贸行业的行会对其成员的经营规模和经营方式没有什么限制,只是对新设行号征收入会费,对各成员行号的营业额进行稽核,以便按一定比例提取经费。因此,新老从业者都可以根据外贸行情的起落和自身资力的厚薄,随时新增或停歇自己的行号,不像以往那样受行规的限制。如上海茶业中的徐润,自1859年设立绍祥字号兼营茶叶后,随后几年又在温州、上海等地另设茶栈多家。五金业中的叶澄衷,先后在上海开设老顺记、新顺记、南顺记、可炽钱栈、可炽顺记等行号,老顺记还在汉口、九江、芜湖、镇江、烟台、天津、营口、温州等地设立分号,经营范围包括五金、煤油、机器、钢铁、洋烛、食品等多种进口货物。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例如与叶澄衷相似,周舜卿起初在上海设立升昌铁行和震昌五金煤铁号,随业务的发展后又在上海、汉口、无锡、苏州、温州、常熟、常州等地设立10余家分号,经营范围也扩大到油麻、杂粮的出口(注:虞和平:《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行会的近代化》,〔北京〕《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第128-129页。)。
上述这些事实都说明,行会在近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传统的经济功能与作用在实践中已很难像以往那样得到落实。面临这种境遇,即使行会想固守过去的行规也无济于事。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从总的方面看,手工业行会的规章从形式到内容都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变化。行会最基本的防止竞争的职能已经难以执行,行会成员使用工徒的人数已经突破了以往的限额,对生产的限制亦已放松。一些地区的行会对会员的生产额已经无法加以任何限制,每一手工业者只要不低于同业公会的定价,可以尽量生产,尽量出售,……即使以低于行会的定价进行竞争,行会纵想干涉,也多半心有余而力不足。”(注:王翔:《近代中国手工业行会的演变》,〔北京〕《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66页。)于是,一部分行会不得不逐渐顺应时势,或被动或主动地对行规进行了修改。
在近代中国,尽管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波三折,但其总体趋势是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进一步加深,从而迫使工商业者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冲破传统行规的束缚,想方设法推陈出新。更为严峻的是,这种激烈的竞争不仅来自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内部,而且还必须随时应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力排斥和挤压。相比较而言,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一般都是资本更为雄厚,技术与管理更为先进,加上通过不平等条约而享有种种特权,在与中国民族资本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民族资本的发展由此而处处受阻,困难重重。行会如果一如既往地用陈规陋俗对同业加以限制和约束,只会使同业处于更为不利的艰难处境,在与资金与技术都非常先进的外国资本的激烈竞争中败下阵来。这也是行会在近代遭遇的两难困境,并促使行会自身不得不进行变革。
对此,许多行会实际上已有切身感受。一些行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破除传统的壁垒森严,联合同业,才能利用团体的力量与外人竞争,抵御外国资本的扩张渗透。例如清末的上海水木业公所已意识到自身的这一新职能,认为“自立者,自强之原素;而团体者,自强之妙用也。今之公所,非团体之机关部乎”?过去公所从事的慈善事宜,只是“团体之余绪,非团体之精神命脉。精神何在?在捍御外侮,而爱护其同类;命脉何在?在联合心志,而劘其智识材能”,其目的是“共求吾业之精进而发达,以之对外则优胜,以之竞争于世界则生存,而自立之效果始成”(注: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2页。)。这显然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行会重在限制同业的功能。
到清末,还有些行会深感势孤力薄,迫切希望打破行帮和地域的壁垒鸿沟,联合各业力量以与外商竞争。1908年,湖南旅鄂商人将汉口湖南会馆改为商学会,明确表示:“外人商务之竞争,转瞬万变,迫不容待,又何能以一陂一障之低力,当此汪洋巨海之潮流乎?故欲言竞争,当从商务下手,更当从汲汲以普及于一般商人之教育学会下手,不容缓也,毋庸疑也。”由此可见,此时已有行会不仅不惧怕竞争,而且主张联合起来与外商竞争,“老少贫富之商人,一律结一大团体”,“考究中外商业竞争之所以然,以便预为改良进步”(注:《江汉日报》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另见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4-305页。)。
关于行会制度在近代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业兴起之后的分解与衰落,已有学者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意见。早期西方学者如玛高温、马士、甘博尔等人的研究成果一般都认为,晚清和民初的行会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强制同业者遵守行规,包括产品价格、工资和劳动条件、招收徒工的数量等方面的规定(注:王翔:《近代中国手工业行会的演变》,〔北京〕《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60-61页。)。但后来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刘永成认为,清代乾隆以后行会即已开始分解,“标志着行会开始分解的重要特点,是大量的会馆向公所的转变”。进入近代甚至到民国,之所以还存在着行会制度,是因为这种分解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注:刘永成:《试论清代苏州手工业行会》,〔北京〕《历史研究》1959年第11期,第29页。80年代初刘永成与赫治清合写的《论我国行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一文,认为清代乾隆以后行会的内在矛盾也已开始暴露,首要表现就是行会的分裂,其次是会行会旧规的“废弛”和行会约束作用的逐渐减弱。参见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第130页。)。不过,彭泽益认为此说所举的例子,如苏州武林会馆改为杭线公所等等,都是清末的事情,不能作为乾隆年间行会“分解”标志的论据(注:彭泽益:《中国工商业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氏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导论”,〔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页。)。从有关史实看,说清代乾隆时期行会制度已出现分解似乎太早,但到晚清时期行会传统的主要功能与作用受到挑战和削弱,却确实有不少具体表现。
另有不少学者进一步对此进行了论述。全汉升认为行会在近代的衰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究其根由则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注: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台北〕食货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210页。)。柯昌基强调行会在近代的功能与影响已明显消减,特别是辛亥革命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行会的势力日减,只在少数古老的行业里留下了一席容身之地。有些地方的行会即使勉强保持,“也是有名无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注:柯昌基:《试论中国之行会》,《南充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第6-7页。)。但这一结论似乎过于夸大了行会势力的消解,实际上行会的作用与影响在一些地区和行业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彭南生认为,清末民初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行业变迁的加速以及民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旧式行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新式工商同业公会(注:彭南生:《民国时期工商同业公会政治参与行为的实证分析——以民初上海工商同业公会为考察重点》,〔武汉〕《近代史学刊》第1辑,第18页。)。王翔认为工场手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的兴起,是对行会制度的致命威胁,而手工业行会很少能够组织起坚强的抵抗,无法阻止自身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但是,也不能说处在衰落过程中的行会已全然不起任何作用。许多手工业行会仍然试图对其成员之间的竞争加以种种限制,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和影响(注:王翔:《近代中国手工业行会的演变》,〔北京〕《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63-68页。)。唐文权认为苏州商会诞生之后,其“作用大大加强,使工商各业公所名存实亡,呈现出解体的种种迹象”(注:唐文权:《苏州工商各业公所的兴废》,〔北京〕《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72-73页。)。
总而言之,绝大多数学者都肯定行会在近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遭遇到十分严峻的挑战,其作用与影响也开始逐渐削弱。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有些行会在近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也曾一度获得新的发展,只是其发挥的功能与作用与以前相比有所不同。因此,要考察近代行会的历史命运,除了分析其衰落的一面,还应论述其革变趋新的一面,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行会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了解同业公会这一新型同业组织诞生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根基。
二、传统行会在近代的变革趋新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部分行会的业董及成员也逐渐向近代新兴工商业者转变,不再属于传统的旧式封建商人和手工业者,这是行会在近代能够出现变革趋新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行会成员的这一发展演变,则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紧密相联。鸦片战争以后,在通商口岸即逐渐出现了经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工业产品的新式商业行业,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传统行业也开始发生变化,从旧式商业向新式商业演变。例如19世纪50年代,上海的商业中就已出现一些过去所没有的新式行业。大约在1850年左右,上海诞生了第一家专营洋布的同春洋货号,此后专业洋布店逐年增加,到50年代后期已达十五六家。1858年振华堂洋布公所的成立,标志着这一新式行业已经形成。上海新兴的五金业店铺也在60年代初开始建立,此后不断增设,至19世纪末已达50余家。除此之外,上海新形成的商业行业还有西药业、颜料业、呢绒业等(注:参见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第7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新兴行业的商人,与传统行业中的商人显然有所不同,在各方面都与资本主义经济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属于近代新兴的商人群体。
一部分原有的行业,在与资本主义经济发生联系之后也开始逐渐产生变化,其中丝业、茶业、钱业等行业的表现尤为突出。其原因是旧式的丝、茶行栈,在鸦片战争后与外商洋行直接发生了密切联系,在经营方式、利润来源等许多方面都较诸过去有所改变,并且促进了一大批新式丝茶行栈的设立。钱庄作为中国传统的金融机关,在近代也越来越多地与进出口贸易和新兴资本主义工商业发生密切的业务往来联系,其繁荣盛衰逐渐与新兴工商业发展的起伏紧密相关。与之相适应,这些行业的商人也开始从旧式商人向新兴的工商业者转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些原本即是行会中的成员,有些则是后来才加入行会,但都对行会成员的演变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也直接促进了行会在近代的变革。
有学者指出,行会成员转向对外贸易和投资于新式企业而转化成为拥有巨资的新式工商资本家,是近代行会成员资产阶级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从实际情况看,这种现象确实比较普遍。例如上海丝业行会中的黄佐卿,以丝商出身,于1881年创办公和永丝厂;黄绅记丝号主黄播臣也于1884年开办绅记缫厂。上海五金洋货业行会中的叶澄衷,以开办顺记五金洋货行起家,于1890年创办燮昌火柴厂,1894年又创办纶华丝厂。1895年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行会成员投资创办新式工商企业者也为数更多。在汉口,洋广货业行会董事宋炜臣,投资创办了既济水电厂、扬子机器厂等企业。棉布、烟土业行会董事韦紫封,集股组织应昌公司承租湖北纱、布、丝、麻四局;另一董事李紫云,于清末出任汉口商务总会总理,1912年入股楚兴公司承租湖北四局,1914年又创办汉口第一纱厂。杂粮杂货行会董事徐荣廷是楚兴公司的主持者,为汉口最大纺织业资本集团裕大华纺织公司的创建者和首脑人物(注:虞和平:《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行会的近代化》,〔北京〕《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第126页。)。正是行会成员的这一变化,才使一部分行会意识到随着各方面形势的变化,不能继续固守传统的成规陋俗,必须变革趋新。
与此同时,许多行会的管理功能和组织制度也逐渐发生了某些变化。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一部分行会,包括在近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成立的新行会,在性质上与传统的行会相比较已有所改变。例如,这一时期的许多行会在宗旨方面即发生了某些变化,其具体反映是不再强调行会的独占性和垄断性利益,而是希望整个同业联合起来共同发展。晚清苏州的糖食公所,公开阐明以“联络商情,亲爱同业”为宗旨。广货业唯勤公所也是“联合团体,讲求保护自治”;“开拓风气,集思广益”;“振兴商业,保全捐数”为宗旨和目的。上海的振华堂洋布公所,更是以“联络商业,维持公益,研究商学,兴发实业,以冀同业之发达”为宗旨(注:参见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38页。)。还有许多行会强调要联合同业,共同与外人进行商战。如沪南钱业公所认识到:“中西互市以来,时局日新,商业日富……顾商战之要,业欲其分,志欲其合。盖分则竞争生,而商智愈开;合则交谊深,而商情自固。公所之设,所以浚商智、联商情也。”(注: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8页。)这些与传统行会采用落后的行规限制竞争、维持少数人的狭隘利益相比较,显然有所不同。
在组织制度上,不少行会也开始由封闭性逐渐向开放性转化。其具体表现是对入会的限制和增设商业店号的限制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严格。许多行会对待新生的同业者,只需其承认会规,缴纳会费便准其入会,有的甚至还采取自愿入会的办法,体现了近代社团的自愿原则。有关十家之内不得增设同业店号的规定,在许多地区的行业中实际上也已经废除。因此,考察有关史实即不难发现,鸦片战争后不仅行会的数量进一步增加,而且各个行会的成员也不断扩大。例如上海洋布业在1858年成立公所时有成员店号16家,1884年增至65家,1900年又增至130余家(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纺织品公司棉布商业史料组编:《上诲市棉布商业》,〔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页;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7-358页。)。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中是相当普遍的。
到清末,联结各业的新式工商社会团体——商会在各地相继成立,所在地区的行会纷纷加入,成为商会的基层组织,这也是行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个具体表现。商会虽然属于近代新式工商团体,与传统的行会在各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区别(注:有关商会与行会的区别及其联系,参见马敏、朱英:《浅谈晚清苏州商会与行会的区别及其联系》,〔北京〕《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但是,各地商会又“大都以各业公所、各客帮为根据”(注:苏州市档案馆藏档:《苏商总会呈工商部条陈》1912年6月5日。)。这并不是说商会通过强制方式要求各业行会加入,而是本着自愿的原则,以其促进工商业发展和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独有的功能及凝聚力,吸引各业行会主动加入。近代中国的商会有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两类成员,所谓团体会员主要即是清末的行会和民国时期的同业公会。从实际情况看,尽管商会并未强行要求各业行会加入,但商会确实在许多方面都具有超越行会的功能与作用,“商会之设,为各业商人互相联络,互相维持,以期振兴商务,自保利权起见”(注:《保定商务总会禀呈试办便宜章程》,见甘厚慈编《北洋公牍类纂》,第21卷,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商务二”。),自其诞生之后即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所以工商各业认识到“公所为一业之团体”,商会为“各业之团体”,是“众商业之代表人”,因而大多数行会都积极踊跃地加入了商会。行会加入商会之后,其封闭性明显削弱而开放性更趋增强。因为商会是包容工商各业的新式团体,而不是像公所、会馆等传统行会那样依赖业缘或乡缘关系组织而成,商会的宗旨就是“联络各业,启发智识,以开通商智”(注: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在商会定期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各业商董经常聚议,“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各商如有条陈,尽可各抒议论,俾择善以从,不得稍持成见”(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年,第12期。)。通过商会召开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各业商董联席会议,使传统行会彼此封闭隔膜、壁垒森严的落后态势明显改观,大大加强了工商各业之间的联系,从而得以朝着互通商情、共谋实业发展的开放性发展。正因为如此,一些地区的工商业者交口称赞:“盖自设立商会以来,商情联络,有事公商,悉持信义,向来搀伪攘利、争轧倾挤之风,为之一变。”(注:苏州市档案馆藏档:苏州商会档案,第72卷,第5页。)
行会组织制度在近代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其内部机构较诸从前完备,职员分工也更加明确。传统行会内部的职员以往只有司年、司月和执事,到近代有些行会则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增设议长、监议员、评议员、调查员等,并一律经由“投票公选”。1907年成立的苏城糖食公所,在组织形式上就给人以一种新异之感。其职员与旧有的司年、司月、执事显然有别,除推举总董一员外,还设有“经济董事”、“评议董事”各8人,专理各项经济事务,并揭明以“联络商情、亲爱同业”为宗旨,规定“每年正月同业皆诣公所,谈议商情一次”。凡议定一事,须经总董酌核、同业中十分之六同意,“始可准行”。这些含有一定民主色彩的改革,使旧式公所在向近代同业公会转变的途程中迈出了第一步。1909年苏州广货唯勤公所为认捐发起组织“同业研究议会”提出以“联合团体、讲求保护自治”;“开拓风气、集思广益”为宗旨和目的。其内部设有议长、监议员、评议员、调查员等旧公所不曾有过的职员,并一律“投票公选”,所议范围包括“生计盛衰,捐项多寡以及各种善举、一切公益改良进步、将来推广实业学堂、制造出品等事”(注:苏州市档案馆藏档:苏州商会档案,第68卷,第3-5页。)。这些内容明显超出了旧有行规议条所包含的范围。20世纪初商会成立,也进一步促进了行会的演变,有的行会虽仍属同行商业性组织,但却将名称也改为行业商会。还有的实际上已开始向同业公会转化,如上海的洋货商业公会、踹业公会、保险业公会等,已体现出同业公会的某些特点。
在实际功能方面,一部分行会也产生了较为突出的变化。其表现之一是旧有功能逐渐丧失,尤其是对所属行号生产经营范围和雇员数量的限制,对商品价格和市场的强制性垄断等,行会已逐渐失去了以往那样的实际控制能力,有的甚至干脆较少加以限制和干预;其二是新的功能不断增强,包括作为商会的基层组织,协助商会联络同业,开通商智;以团体力量帮助同业抵御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与外国资本竞争;调解同业纠纷,改善同业关系,提高相互间的凝聚力等。
需要特别指出,在近代不少行会的功能主要体现于采取新的举措,帮助同业提高生产和经营水平,增强竞争能力,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与外国资本进行激烈竞争的艰难情况下得以生存和发展。因此,许多行会都非常强调在经营中不准弄虚作假,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例如上海的茶业会馆,为了保持本业的商业信誉,防止外商借故索赔、退货,提高竞争能力,在1870年制定的规条中拟订了多项严禁舞弊的规定,包括“不准再做样箱尾箱,总要一律,不得高下”;凡收购进栈之茶均由“栈司随手开箱,以装样罐”;无论华洋行栈,一律不准对客商留难勒索等(注:虞和平:《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行会的近代化》,〔北京〕《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第129页。)。珠玉业新汇市公所为维持信誉,也要求“珠宝玉器各商入市贸易者,莫不以信实为主。故定章不论珠宝翠玉,凡属赝品,概不准携入销售,致为本汇市名誉之累”(注: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9页。)。
还有一些行会更顺应时代的发展,采取若干新的方式,引导同业积极参与研究商学,提高商智,培养新型人才,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例如上海洋布公所意识到“世界潮流趋新革故,公所为私法机关,不得不一遵新法,俾洽时宜”,并在清末相继创办振华堂补习学校、英文补习学校、振华义务学校等各种新式学校,其宗旨为“研究商学、兴发实业,以冀同业之发达”(注: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8页。)。此外,水木业公所为使同业之中“弊相除,利相兴,相师相友,共求吾业之精进而发达”,也在清末筹办了“两等小学一、艺徒夜学四”(注: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2页。)。此外,还有金业办的金业初等商业学校,水果业办的华实学堂,豆米业办的豆米业学校,衣业办的衣业学校,苏沪帮鲜肉业办的香雪义务学堂,水炉业办的水炉公学等。苏州的一些同业公所同样曾经创办新式学校,例如1906年苏州纱缎业“以同业独立,学堂不假外求,既为一业广陶成,且为各业树标准”,发起创设初等实业学堂,分本科、预科两级,均定四年卒业,所需经费由“同业担任,不假外求”(注: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44页。)。紧接着,苏州经纬业和米业也为兴学育才、开通商智而创办新式学堂。
除上所述,传统行会的功能与作用在近代的变化,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具体反映,这里难以一一列举。实际上行会功能的变化,在当时已引起了相关人士的注意。有人将其概括地表述为:“会馆有时行公议裁判等事,俨如外国领事馆;公所为同业之机关,俨如商业会议所。其始不过曰联乡谊、营慈善而已,浸假而诉讼冤抑之中为之处理矣,浸假而度量衡归其制定矣,浸假而厘金归其承办矣,浸假而交通运输之规则归其议决矣。”(注:钱荫杭:《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商务官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12期。)尽管各个地区行会组织变化的情况不一致,但其发展的总体趋势却十分明显,这就是朝着适应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趋向转变。
还有学者考察了行会在近代向同业公会的转变。20年代美国学者甘博尔(S.D.Ganble)即通过调查,用表排列出北京前清旧有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在同业公会组织形式下的演变状况。此后,国内一些学者也进一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李华认为鸦片战争之后至清末民初,北京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渐发展起来,行会组织也相应地起了某些变化,不少行业的资本主义同业公会组织相继成立。“这些资产阶级同业公会,其中有一些是由封建行会组织转化来的”(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北京〕《历史研究》1978年第4期,第71页。)。彭泽益也主要以民国时期北京的情况为例,阐明原有工商业行会在民国时期有的衰落下去了,有的仍照旧维持其存在,但在同业公会的组织形式下发生了演变,可以说“同业公会是转化中的行会变种”(注:彭泽益:《民国时期北京的手工业和工商同业公会》,〔北京〕《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79页。)。王翔也曾剖析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由云锦公所向铁机公会嬗变的个案,他认为同治年间“重建”的云锦公所性质已经开始变化,逐渐由苏州丝织业的全行业组织向纱缎庄“帐房”的同业组织演变,亦即由旧式行会组织向资产阶级的同业团体转化,具备了中国早期资本家同业组织雏形的特征,只不过仍然沿用着旧的习称而已。到民国年间,云锦公所不仅完成了自身的转化,由资产阶级同业组织的雏形演变为它的成熟形态——“纱缎庄业同业公会”,而且从其内部还派生出了一个“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注:王翔:《晚清苏州丝织业“帐房”的发展》,〔北京〕《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第117页;又《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近代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的嬗变》,〔北京〕《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11页、第113页、第121页。)。魏文享指出:同业公会的根本目的仍是为维护同业发展,这一点与旧式行会保持了一致,但由于公会产生与发展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不同,其会员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与管理方式不同,又使公会的效能与行会产生了几乎迥异的分野(注:魏文享:《试论民国时期苏州丝绸业同业公会》,〔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39卷第5期,2000年9月,第86页。)。彭南生则从成员构成、经济功能、活动机制等方面比较了同业公会与旧式行会的诸多不同,认为从行会到同业公会的转化,标志着工商同业组织近代化的基本完成(注:彭南生:《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制度的现代性刍论》,〔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32-138页。)。
徐鼎新认为20世纪初上海行会开始向同业公会转变,进入新旧工商团体并存的历史时期。到民国建立以后,又有不少行业组织相继把原来的公所改组成公会,或建立跨地区的公会、联合会。但较多的同业团体仍然沿用公所或会馆名称,或者一个行业内公所与公会并存,各立门户,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组成人员。因此,在近代中国“行会制度的多种变化”确实是存在的(注: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90-92页。)。宋钻友认为从会馆公所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是同业组织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大致分为从开埠通商至1904年,从1904年商会诞生至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从1929年至1948年这三个阶段。推动同业组织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清末西方民主思潮、法律知识的广泛传播,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有关政策也产生了重要作用(注:宋钻友:《从会馆、公所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兼论政府与同业组织现代化的关系》,〔上海〕《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3期,第40页、第43页。)。黄汉民指出: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已有较多的从旧式行会演化而成的商业同业公会,民族工业行业中也开始有少数试办“公会”,但大多还没有完全摆脱旧式行会组织的影响,是“一种具有资本主义经济某些特征的混合型同业组织”(注:黄汉民:《近代上海行业管理组织在企业发展与城市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第176页。)。魏文享也认为,近代工商同业公会最常见的是由旧的行会组织改组、分化或合并而成,其次是由新兴行业直接遵照有关工商同业公会法令建立。在近代,虽然行会的衰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由于维护同业发展的根本需求、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恶劣以及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与掠夺的需要,行会仍有继续存在的可能与必要(注: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分析1918-1937》,《近代史学刊》第1辑,第52页、第49页。)。朱榕通过考察上海震巽木商公所到上海特别市木材同业公地的发展演变,阐明行业组织近代化进程的快慢、程度的深浅,往往与其内部成员的构成、观念的更新、组织形式的演变、功能设置的转化,以及外部社会环境(尤其政治环境)变迁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因素与作用相互关联紧密,互为因果(注:朱榕:《上海木业同业公会的近代化——以震巽木商公所为例》,〔上海〕《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3期,第53页。)。
以上介绍的各种观点虽然各有侧重,但大体上都认为向同业公会这一新式同业组织的转变,是传统行会在近代发展演变的一种总体趋势。但应该注意的是,不能否认行会在近代的变革趋新仍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尽管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冲击,以及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许多行会都或被动或主动地进行了一些变革,但不可否认也有不少行会力图维持旧有行规,对同业及外来者的经营活动继续进行限制,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揆诸史实,这方面的事例同样也不少见。据当时的报纸透露,“粤省工艺之流,行规最严。其或为外行搀夺,则必鸣鼓而攻,无滋他族,实逼处此。凡有各业,所在皆然。”(注:《字林沪报》光绪十八年五月初十日。)直到辛亥革命前广州商会成立时,类似的情况也仍然存在。广州商会曾感叹:“本商会以生利为目的,无如风气未开,诸多阻力,如激励工艺,反为行规压制;制造新款,指为搀夺;烟通机器、伐木开矿,毁为伤碍风水;工厂女工,诬为藏垢纳污;土货仿造洋式,捏为妨碍厘税。”(注:《广东总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年,第12期。)
另据《申报》记载,1880年奉化江沛章等人到宁波销售伞骨,宁波伞骨匠首马上聚集同业加以阻止,并“拉货擒人”。江氏告之官府,得到的结果却是“谕令奉化人此后如至宁波销售,必须随众入行。如不入行,不准潜来宁波生意。至于奉化人赴慈溪、余姚销货,应听慈、余旧处旧规,不得私专其利”(注: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页。)。这样的结局,显然是仍沿袭了行会禁止外地人随意售卖的传统的规定。
对于同业违反规定减价销售,许多行会也沿用旧规严加制止,并予以处罚。例如1887年杭州有一豆腐坊“为招徕生意起见”,自行将豆制品改样放大,暗中“较常减价”,同行共相抵制,要求整顿行规,最后议定“悉照旧定价”,“倘有私收小钱,及私自改样减价者,即罚戏一台”(注:《申报》光绪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二日。)。次年,杭州又有一家新开染坊,对各色染价“照旧章格外减便”,使得“城厢哄动,生意颇形热闹”,其他一些染坊也被迫紧随其后而减价,引起同业强烈不满。“于是各染坊会议于公所”,议定“染价一律遵照旧例,不得私相低减,违者察出公罚”(注:《字林沪报》光绪十四年四月初六日。)。
对于违反行会规定多招收学徒的作坊,在有些地区更是受到严厉的制裁。“同治壬申,苏郡有飞金之贡,先是业箔者,以所业微细,自立规约,每人须三年乃授一徒,盖以事此者多,则恐失业者众也。其时有无赖革某者,以办贡为名,呈请多授学徒,用赴工作。既得批准,即广招徒众,来从学者,人贽六百文,一时师之者云集。同业大忿,于是援咬死不偿命一言,遂群往持其人而咬之,人各一口,顷刻而死。吴令前往检验,计咬伤处共一百三十三口。然何人咬何处,人多口杂,不特生者不知,即起死者问之,恐亦不能知也,乃取始谋先咬者一人论抵。”(注: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4,第5页。另见《申报》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样的事例虽然并不多见,但也反映了传统行会势力的影响在近代仍不能小视。
除此之外,一些地区的行会在近代仍不准同业私自领货、学徒出师不入行,对于于违规者也继续给予处置。例如1877年苏州陆寿所开的浆坊,因“不守行规”私自领,同行查知后“公同议罚,呼陆吃茶”理论,进而导致“互相斗殴”。又如1880年间上海南市挑皮匠郭洪根,“近因其徒满年,故另置一担,令其随同生理”。同行得知,“以郭徒未尝入行,不独不准挑担,且将其担拉去;又拉郭洪根至县喊控,称伊不遵行规,请为究办”。1891年间上海茂丰祥乌木作有学徒满师,因未出捐入行,行头遂“攫其器具,使不能作工”。该作坊主投诉县衙,行头不仅“抗不将器具交还”,而且还号召同业抵制,“令各工匠一律停工,各作亦闭门不作贸易”(注: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207页。)。
以上事例表明,进入近代之后,虽有一部分行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采取措施逐渐变革趋新,但同时也有一部分行会在某些方面仍试图固守传统的陈规陋俗,继续用行规对工商业者的经营活动予以种种限制和约束,这显然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甚至起了阻碍作用。因此,行会的整体变革尚有赖于制度性的更新,而不能仅仅是局限于小范围的改变。这样,同业公会这种新型同业组织的诞生,就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迫切需求。
标签:商业竞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汉口论文; 经济学论文; 工商论文; 商业论文; 手工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