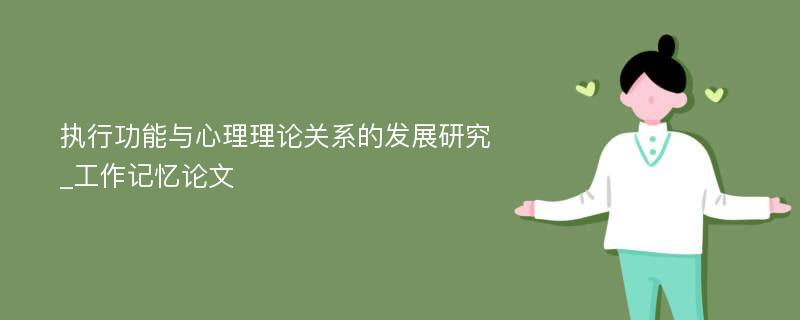
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关系的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关系论文,功能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一些关于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相关联系的实证研究,但是直到1996年Russell[1]才首次提出关于二者关系的理论。其后,许多研究者都证实了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关关系。
一、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
(一)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EF)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EF)这一概念出自前额叶皮层损伤的研究,前额叶皮层的损伤引起了一系列神经心理的缺陷,如:计划、概念形成、抽象思维、决策、认知灵活性、利用反馈、按时间先后对事件排序、对动作的监控等方面的困难[2],因此,执行功能常常被看作是由前额叶调节的认知功能。目前,关于执行功能及其发展的研究是国际发展心理学研究的新热点,但其含义相当广泛,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从整体上讲,它指有机体对思想和行动进行有意识控制的心理过程[2]。
Pennington和他的同事们[3][4][5][6]证实了执行功能的三个维度: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WM)、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IC)和注意灵活性。Lezak[7]则把执行功能划分为4个心理能力的功能范畴。包括:(1)明确目标的能力;(2)计划机制;(3)为了目标成绩(goal achievement)实施计划的能力;(4)有效的完成这些活动。完整的执行功能能促进人的警惕、推断、创造性及参与对本人意义重大的活动的能力。如果执行功能由于脑伤而不完整,人就不能在相应事件中采取适当的行为方式。执行功能的损伤和缺失常会降低个人产生或维持自主性和社会创造性行为的能力。
关于执行功能的发展研究总体上揭示了:(1)执行功能最早出现在发展早期,约在出生第一年末;(2)执行功能发展的年龄跨度很大。重要的发展变化出现在2—5岁,12岁左右达到许多标准执行功能测试的成人水平,某些指标持续发展到成年期;(3)在学前期及以后,执行功能各方面都存在系统性的变化,它们之间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4)执行功能的发展与心理理论、语言、记忆等能力的发展密不可分;(5)不同的儿童发展障碍(如孤独症和ADHD)可能引起执行功能不同方面的缺陷[8]。
(二)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ToM)
心理理论是指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如需要、信念、愿望、意图、感知、知识、情绪等)的认识,并由此对相应行为作出因果性的预测和解释[1]。简言之,心理理论就是关于心理领域的内隐观念。尽管早在婴儿期,就有对他人心理的朦胧认识,但是心理理论在学前期才真正地迅速发展。心理学家们一致认为能够完成错误信念(false belief,FB)任务是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
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被认为是学前期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就。普遍发现,4岁以下的儿童在标准误念任务上有相当大的困难。近年来,研究者已着手揭示3—4岁间在心理理论上的行为转变的潜在机制。一种突出观点是理解表征的领域特殊性切换。这些研究者指出许多相关能力随误念理解相继出现,而支持这种概念切换观点。比如,外表一事实理解的出现和视觉观点采择的发展也发生在4岁左右。
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则认为这种转变至少是部分反映了更普遍的认知成熟,很多研究者坚持认为学前儿童执行功能能力的增加明显有助于在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从而凸现出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的关系问题。
二、对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关系的研究
一些研究者在执行功能研究和心理理论的研究中,发现3—6 岁间这两种能力均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因此,研究者们发出了疑问: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的发展到底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还是因为二者都要受到某些共同因素的影响而伴同出现呢?于是,研究者们自然地联想到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关系。
许多直接证据来自论证两者间关系的相关研究。首先,即使在控制年龄和言语能力的情况下,执行功能成绩仍保持和心理理论任务成绩的高度相关;其次,通过训练被试的心理理论能力可以提高他们的执行功能能力,训练执行功能也能提高被试的心理理论。因此,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间肯定存在着相关。
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描述,一种观点认为,执行功能的发展是心理理论的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心理理论的发展促进了执行功能的发展;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心理理论也许并不是执行功能的先决条件,执行功能也不是心理理论的先决条件,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存在某种共同的认知因素,它对于解决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的发展都是必要的。
许多研究者试图用两种方式来剖析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的关系。一种方法是通过提供大面积的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测试来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关,第二种是在实验中操作心理理论任务的执行性要求以便了解执行性要求的变化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例如,Carlson等[9]、Hala和Rusell[10]发现,降低策略欺骗任务(一种心理理论任务)的抑制性要求会使儿童易于解决该任务。与之对应,Leslie和Polizzi(1998)[11]发现,增加心理理论任务的抑制性要求,增加了4岁儿童完成任务的难度。
另一些研究者发现,降低心理理论任务的工作记忆要求促进了儿童在心理理论任务中的成绩。例如,Freeman和Lacohée[12]发现,在意外内容任务中, 让儿童张贴一幅他们所认为的盒中物的图片,有助于他们后来报告自己的错误信念。他们提出,张贴的图片加强了儿童先前信念的记忆痕迹,从而使之易于回忆。
由此可见,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都与心理理论成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工作记忆在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中的作用
工作记忆是在头脑里积极保持众多事件的能力。工作记忆随年龄发展,而且被认为是制约执行功能发展和表现的主要原因。一些研究者考察了工作记忆的发展是怎样与儿童的误念理解联系起来的,得到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儿童若要完成误念任务,必须具备一定的工作记忆能力。在意外地点任务中,为了说明主人翁不在现场的情况下,一个物体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儿童若要对关于主人翁的信念的问题作出正确反应,必须记住整个叙述的场景。此外,儿童必须了解到头脑里的两个交替表征——儿童自己所知道的物体的真实位置和主人翁认为它所在的位置——是不同的。同样,在意外内容任务中,儿童也必须了解到他现在所知道的真实物体和他先前所认为的物体是不同的两个表征。
就目前来看,关于工作记忆在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中的作用的研究结果是有分歧的。一些研究发现了误念任务成绩和工作记忆的相关,一些则没有。对这种不同的研究结果的一种解释是,这些相互独立的研究仅仅考察了工作记忆或心理理论的某些不同方面。此外,在这些研究中,有的仔细地控制了其他认知能力,如语言能力,有的则没有控制。这就难以对这些研究进行相互对比。Hughes[13]发现,在控制年龄和言语能力的情况下,心理理论和工作记忆间的中度相关便不复存在。这似乎暗示着存在某种中间变量,该变量是儿童理解他人信念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桥梁(比如:语言能力)。这也在对孤独症儿童和聋童的心理理论发展的研究中得到证实。
ZIV & Frye[14]在一项关于儿童的愿望—信念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地结论。他们在心理理论任务中使用了两类靶物体——令人喜欢的和令人厌恶的。同时,在实验过程中又分别向儿童说明(或不说明)剧中人的明确喜好(如:他非常不喜欢洋葱)。结果发现,无论在什么情形下,3岁儿童都能很好地完成愿望问题, 记住剧中人的愿望或初始的“人物—物体”连接。但始终不能完成信念问题。这表明,即使儿童在能顺利完成记忆任务的前提下,仍然不能完成误念任务。
另一些研究结果肯定工作记忆发展的作用,即使在控制年龄和言语能力的时候。然而,在这个出现较大相关的研究范例上,我们发现该任务也表现出明显的抑制性要求。例如,通过评估学前儿童的正向和逆向数字广度能力(forward and backward digit span ability),Davis和Pratt[15]发现逆向数字广度和心理理论成绩的相关。为了成功完成这件任务,儿童不但必须要能够记住数字的顺序,还要以相反的顺序报告出来。很明显,这可能不仅仅是对工作记忆的要求,也可能是对抑制控制能力的要求——儿童或许有着按先前顺序报告数字的优势反应,他们需要正确抑制这种优势反应才能成功完成任务。
(二)抑制控制在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中的作用
抑制控制是按要求压制不合适的反应的能力,并被认为是执行功能的核心成分。抑制控制发展的重要时期是人生的前6年,而且在3—6岁之间发生显著性变化。查证抑制控制和心理理论关系的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结果。Hughes[13]发现,一旦控制年龄和智力年龄(mental age),抑制控制仅仅和欺骗能力而不是误念理解相关。或许欺骗本身就要求更多的抑制控制,以避免露马脚。
在一项验证抑制控制的研究中,Carlson和Moses[16]区分了仅仅抑制不适当反应的执行功能任务和同时涉及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的执行功能任务。她们把两种执行功能任务划分为“延迟”(delay)类和“冲突”(conflict)类。结果发现,尽管“延迟”任务有一定的预测价值,但“冲突”任务更能预测心理理论成绩,这可能是因为“冲突”任务除了抑制控制外还要求较高程度工作记忆。Hala&Hug[17]研究发现,在抑制控制和误念成绩间没有显著的特殊联系。Perner,Lang,and Kloo[18]也报告说,go/no-go 任务(一种抑制控制测试)与心理理论成绩也没有关系。根据上述结果,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抑制控制本身并不是心理理论成绩的有力预测指标。很有可能是因为抑制控制只是心理理论能力的一个方面,心理理论能力是一种更为综合,参与的成分更多的整体能力体现。不能用单一的指标来对心理理论成绩进行预测。
(三)工作记忆与抑制控制的结合在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中的作用
由于工作记忆是一种通用的认知能力,是许多认知活动的共同基础,因而它与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能力也表现出相关。Carlson等[19]又考察了“冲突”任务的预测能力是否可能是处于基层的工作记忆成分独立于抑制控制成分的结果。与早期结果一致,Carlson 等发现只有“冲突”类任务成绩是心理理论任务的成绩的显著预测指标,而单一的工作记忆成绩的效应在分析中不显著。Carlson等断定,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的结合才是心理理论发展的关键。
Hala & Hug[17]的研究进一步证明,抑制控制本身并不是心理理论成绩的有力预测指标,而且,把工作记忆从明显的抑制性要求分离后,单独的工作记忆也不是心理理论成绩的有力预测指标,只有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结合的执行任务能很好地预测幼儿误念任务的成绩。这说明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的共同作用可能正是联系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的纽带。原因可能是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在活动时都要竞争工作记忆资源,而这种比较只有在二者分别与工作记忆结合起来时才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为这种假设找到生理依据。完成执行功能任务和心理理论任务都必须前额叶的参与,它暂时保存着需要加工的信息,同时抑制干扰反应。即通过前额叶,两种执行性要求结合起来。孤独症患者完成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任务的能力被削弱,其原因就是二者共用同一脑区。
我们认为,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混合的执行功能任务可能是心理理论成绩的有力预测指标。因为儿童为了在心理理论任务上获得成功,必须抑制不适合的反应(如儿童自己知道的现实)而在头脑中保持矛盾反应(如故事中主人翁认为物体所在的地方)。
Frye和Zelazo[20]提出的认知复杂性和控制理论(Cognition Complexity and Control theory),从另一角度解释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的关系。他们把执行功能描述为规则理解和规则间的灵活转换,并根据规则来完成计划、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该理论,儿童需要从蕴含规则中选择高级规则,这在规则相互冲突的时候,对幼儿显得尤其困难。Zelazo和Jacques[21]认为,day-night任务和tapping任务都包含了蕴含的规则。例如,在daynight任务中,儿童需要理解“看见太阳图片就说晚上”和“看见月亮图片就说白天”的规则,但这些规则与其潜在的默认规则是相冲突的。Zelazo等认为,这类任务可以预测误念成绩主要是基于这些任务中所蕴含的规则的复杂性。关于这一说法尚有争议,但仍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可以把此类任务的完成看作是基于规则的推理能力发展所致。儿童首先要理解规则,并运用规则;当规则改变时,适时转变已经形成的优势规则。
三、结语和展望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证据的不断累积,越来越多的人同意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之间存在着相关。许多研究发现,单独减低工作记忆或抑制控制要求并不足以提高误念任务的成绩。也就是说,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就其本身而论,皆非误念测试成绩的有力预测指标。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是否要同时降低记忆要求和抑制性要求才可能提高幼儿的成绩呢?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执行功能的发展使得心理理论的出现成为可能。Hughes[22]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儿童3、4岁时的执行功能能力是一年后心理理论成绩的有力指标;相反,心理理论成绩则不够有效预测执行功能能力。而Perner和他的同事们[18]主张,应该用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来解释执行控制的发展。他们认为儿童在运用获得目标所必需的执行控制能力之前,必须有能力表征他们的心理状态——形成元表征能力。但是,由于支持上述两种观点的证据都是基于相关研究的结果,缺乏因果研究的数据,故上述两种解释都有可能是正确的。不过,我们看到,尽管很多研究都证明了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间的稳定的相关关系,但这些研究又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因此,关于执行功能能力和心理理论能力的相互可预测性,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来阐明。
此外,目前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在考察幼儿期——儿童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对于婴儿期的心理认识——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心理理论的萌芽——和执行功能的早期表现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却鲜有报道。我们认为,追本溯源,要想真正揭示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的关系的实质,还必须了解二者在早期的发展。
标签:工作记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