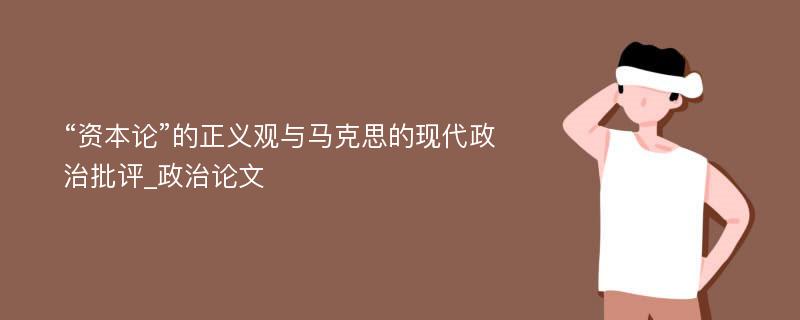
《资本论》的正义观与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资本论论文,正义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透过《资本论》理解马克思的正义观是当前学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些关注无疑深化了西方学界时至今日仍争论不休的《资本论》正义批判问题。但是,这些关注也由于过多局限于探讨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是否遵循现代正义原则,而少有研究如何透过《资本论》的正义观来阐发马克思对于现代政治的批判与超越问题。鉴于此,本文通过辨析西方学界围绕《资本论》的正义批判问题所展开的激烈讨论,尝试探索重新理解《资本论》的正义观的新视角,并以此作为重新阐发马克思现代政治批判思想的切入点,深入剖析马克思对于现代政治的批判与超越问题,以期为推动学界透过《资本论》的正义观进一步探讨马克思的政治观有所助益。 一、普遍正义:《资本论》的正义观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围绕《资本论》的正义问题就马克思的正义观展开了持久而激烈的探讨。这些探讨基本围绕两个截然对立的观点展开:其一,以艾伦·伍德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正义何以实现”对于《资本论》而言并不构成真实的理论问题,因为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理论的批判说明,诸如正义、权利、自由、平等概念,它们仅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真实的存在,而马克思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颠覆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也就彻底颠覆了这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法权观念,因此,“正义”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法权概念是马克思所厌恶的“道德说教”。①其二,以齐雅德·胡萨米为代表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入阐发,特别是对于剩余价值所透露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结构的揭示,这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批判的正义批判。从早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理论对于资本逻辑正义的美学批判和人类学批判,到后期《资本论》对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以及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正义批判是一以贯之的;而且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更是明确探讨了共产主义的分配正义问题。② 按照第一种观点,我们对于《资本论》正义观的探讨隐含着巨大的理论陷阱。这就是,即使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但并不能说明这种批判是基于正义原则,或者说,《资本论》与正义问题无关,探讨《资本论》的正义观是一个假问题。第二种观点虽然基于分配正义立场给予马克思的正义观一种积极的辩护,但却引发了更为棘手的问题:如果马克思是站在分配正义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那么《资本论》如何能够跳出资本逻辑的分配正义框架完成对资本主义的分配正义批判?或者说,马克思以分配正义批判分配正义何以可能?况且,在《哥达纲领批判》等后期著作中,马克思只是批判了拉萨尔基于资产阶级的权利观念对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庸俗化理解,而并非想创建关于共产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③那么,这是否又说明马克思在对待分配正义的态度上前后矛盾呢?可见,从分配正义的角度不仅无法完成对马克思正义观充分的理论辩护,反倒使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对于以上争论,笔者认为,伍德的论断在结论上是正确的,即马克思的正义标准仅在运用于相应的生产方式上才有意义,比如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工资关系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正义标准。④但是,如果基于这一结论就认为《资本论》的资本逻辑批判无关乎正义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资本论》并非与正义问题未有关涉,而是在对现代政治正义观的批判中,创建了一种超越现代性正义的正义观。为了验证以上判断,我们不妨换一种提问方式:现代政治的分配正义是不是正义的唯一理论形态?《资本论》是不是采取了不同于分配正义的别样的正义立场?回答上述问题,要求我们跳出现代政治哲学的正义观视域,重新理解《资本论》的正义观。 跳出现代政治哲学的正义观视域,我们可以尝试回到古典政治哲学的正义观视域。作为古典政治哲学正义观的标志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所展现的正义观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关注城邦整体政治德性的“普遍正义”和关注具体经济活动的“特殊正义”。“普遍正义”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伦理品质以及个体潜能能否充分实现的政治问题,“特殊正义”关注的则是关于财富分配和享有的“经济学考量”。⑤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对于社会正义的探讨总是同对于城邦中公民的经济交往方式的描述结合在一起。但更应该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所关注的公民经济生活中的“特殊正义”问题是为实现整个城邦的“普遍正义”服务的。正如美国学者乔治·麦卡锡所言:“在《政治学》第一卷中,他(指亚里士多德,引者注)致力于发展两大主题:(1)经济在维系城邦和美好生活的统一上面是重要的;(2)交换从实物交换到商业贸易(kapelike)的发展演变在城邦中瓦解了对一个共同体而言最重要的相互分享、公平、团结和社会正义。”⑥亚里士多德对于“普遍正义”和“特殊正义”的区别,可以作为我们重新理解《资本论》正义观的重要思想资源。 如同亚里士多德把城邦交换方式的转变看作影响城邦整体善的重要因素,并把实现城邦公共善这一“普遍正义”作为其正义理论的出发点一样,对于马克思而言,正义关涉的并不是利益分配所遵循的法权规则的“特殊”问题,而是关涉每个人个性的自由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德性风尚的“普遍”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关注的并不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是否符合自由与平等的抽象法权理念,而是在这一交换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及其所构建的一切社会关系是否促进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资本论》蕴含的是一种“普遍正义”观,而非“特殊正义”观。 进而言之,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分配正义是《资本论》关注的显性政治逻辑,那么,分配正义背后的生产正义就是《资本论》贯彻的隐性政治逻辑。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活动不仅是利益分配的前提条件,更是人类生命的基本存在方式。从分配正义视角探讨正义问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正义立场就是分配正义,生产正义作为一个“普遍正义”问题才是《资本论》正义观的隐性逻辑前提。而西方学界关于《资本论》正义观的争论焦点是交换主体、交换行为和交换过程的自由性、公平性和程序合理性。这些争论局限在现代政治关注的分配正义框架内,局限在对资本主义经济交换方式上诸多“特殊正义”问题的争辩,缺乏在“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张力关系中把握正义问题的超越性视野。其导致的结果是,在探讨《资本论》正义观的过程中,只纠缠于资本逻辑批判是否基于现代正义原则等问题,而无法看到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内在一致性。由之,一个悖论性的结论随之产生:《资本论》对资本主义作出了最为深刻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却与正义无关。 《资本论》的“普遍正义”立场表明,对于深受古典政治哲学正义观影响的马克思而言,正义从来不是纯粹的道德形而上学问题,而是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实践问题。但是,与亚里士多德“普遍正义”所处的古希腊城邦的政治语境不同,马克思探讨“普遍正义”的实践语境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因而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彰显对于正义的独特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马克思的正义观就贯穿在《资本论》对于资本逻辑的批判过程中,《资本论》的资本逻辑批判与正义批判是内在一致的。 二、正义批判:《资本论》的资本逻辑批判 在现代政治的“特殊正义”视野下,资本逻辑所把控的物质生产和分配方式遵循的是商品经济的自由交换原则和价值互惠原则,因此,资本逻辑是最能体现现代性个体自由和社会公正的正义逻辑。但是在《资本论》的“普遍正义”视野下,资本逻辑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却暴露出其更为深层的正义问题,即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普遍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产生现代社会正义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造成人类劳动本性的异化:劳动这一原本确证人之为人的活动方式,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以雇佣劳动的形态反过来与人相疏离。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正义批判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性质的审美批判,那么到了《资本论》等后期著作中,这一批判则旨在科学地揭示资本逻辑的形而上学结构与现代政治的隐秘耦合。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的正义批判经历了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理论语境的重大转变。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正义批判从科学分析资本逻辑的商品交换原则及其所导致的拜物教迷雾开始。马克思认为,劳动之所以被异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劳动的抽象化,而劳动的抽象化则是由于具体劳动所生产的使用价值被资本逻辑所同质化为可以量化的交换价值。劳动价值的这种“神奇”转换,从根本上变革了劳动作为发掘人类创造潜能的社会正义功能,其结果是劳动创造潜能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被资本逻辑及其商品交换原则所同质化。由此,劳动的社会正义功能被转变为一种基于自由、平等交换的现代正义原则,而这种正义原则的同质性无疑遮蔽和窒息了人类劳动本性所固有的多样性。因此,渗透在资本主义整个生产过程中的现代正义原则必然是伪善和虚假的。 在《资本论》的开篇处,马克思指出:“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⑦这里有必要对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微妙”和“怪诞”之所指加以分析和说明。就商品作为使用价值而言,它并没有神秘性,它不过是自然物质在人类行为作用下一种形态的变化而已。问题的关键在于,商品除了具有使用价值,还具有交换价值。商品交换所秉持的量的同一性原则似乎可以摆脱商品实用属性的“纠缠”,从而使商品获得一种与任何其他商品进行“普遍交往”的魔力。可见,正是商品交换价值所暴露出的劳动抽象化,使得劳动产品一旦变成商品就获得了“谜一般的性质”。而这种“谜一般的性质”在马克思看来并不神秘,它不过是被抽象化了的人类劳动而已。但是,商品形式对于劳动的抽象化使得人类经由劳动结成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马克思为此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⑧而这时,商品无疑获得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意味的拜物教性质:“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把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⑨其结果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像虔诚的信众匍匐在图腾面前一样匍匐在商品脚下,人类的精神世界看似得到了物质的充实,实则被其所崇拜的对象所掏空。 因此,商品的形式同一化原则不仅仅是一种局限于经济交往过程中的基本原则,当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变成人类精神生活的根基时,这种形式同一化原则还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资本逻辑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异化并不是某一生活领域的特殊异化,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普遍异化。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物化现象同它们存在的经济基础、同它们的真正可理解性的基础的这种分离,由于下面这种情况而变得较为容易:要使资本主义生产完全产生效果的前提成为现实,这种变化过程就必须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⑩可见,商品拜物教及其背后所贯彻的资本逻辑已变成主宰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普遍性逻辑。在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商品社会中,形式同一化原则成为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贯彻的隐性法则,它逐步被潜移默化地变成大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形式,变成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现有正义原则的合法化工具。 由上可见,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的正义批判,所秉持的是西方古典传统固有的“普遍正义”精神,即人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自身的各种潜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揭示的是西方现代社会非正义的普遍强制结构,这种强制结构被马克思称为“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政治和国家的异化。(11)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的非正义性的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强制结构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资本论》的正义批判简单地看作对商品流通和交换过程中发生的分配不公的批判,这恰恰违背了《资本论》资本逻辑批判的政治真义。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2)可见,跳出资本逻辑的商品流通和交换领域所贯彻的现代政治原则及其构筑的政治强制结构,进而剖析资本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异化,从而揭示由资本逻辑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普遍正义”危机,才是《资本论》资本逻辑批判的政治真义之所在。 《资本论》的“普遍正义”观及其对于资本逻辑的正义批判表明,《资本论》的资本逻辑批判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证经济学批判,更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哲学存在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是由资本逻辑的形而上学结构所引发的“普遍正义”危机,剖析和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必须切断资本逻辑的形而上学结构与现代政治的耦合,瓦解现代正义原则所赖以立足的现代政治哲学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资本论》的正义观成为重新阐发马克思现代政治批判思想的重要切入点。 三、超越“道德政治”: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 《资本论》的资本逻辑批判之所以就是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逻辑批判所批判的实质对象是资本逻辑正义性。表面来看,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的科学分析是基于事实视角,不涉及价值判断,资本逻辑批判似乎与政治判断无关。但是,资本逻辑批判得以可能的逻辑前提却要求必须跳出资本逻辑的政治自洽性才能实现对资本逻辑的真实批判。因而,《资本论》的资本逻辑批判不可能仅仅停留于表层的经济批判,它在更深层意义上是对支撑资本逻辑正义性的政治基础的哲学批判。事实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正是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伪善本质,才深刻揭示和批判了现代政治的狭隘性和有限性,建构了一条从根本上超越现代政治的思想道路。 众所周知,正义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因为正义被看作判断国家和城邦是否是好的国家和城邦的首要标准。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理想国家必须由真正的哲学家掌权,因为哲学家重视正义并能够使整个城邦走上正义的轨道。(13)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科学和技术都以善为目的,政治学作为最主要的科学尤其如此;而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14)可见,在古典政治哲学语境下,政治判断的对象主体是政治实体,判断其存在的正义性要看其是否能够提升城邦公民的整体德性和社会伦理品质。在这里,正义实际上是被当作一个社会伦理概念来加以探讨的,它意味着个体之善与共同体之善的统一,共同体的政治合法性即在于个体的伦理认同。 正义重新作为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肇始于现代政治哲学的诞生。在现代政治哲学看来,古典政治哲学主张的伦理正义需要接受个体理性的现代反思,在个体理性觉醒的前提下,个体之善与共同体之善的统一被瓦解,从而导致政治合法性的前提由古典政治的伦理认同转变为现代政治的道德反思。因此,在现代政治哲学语境下,政治判断的对象主体是权利个体,判断其行为是否具有正义性,要看其逐利行为是否符合相应的道德准则。也就是说,正义是被当作一个道德概念加以探讨的,判断正义的标准是以对个体的道德认识为前提的。 尽管现代政治哲学存在不同的思想谱系,但是它们都以对人性的道德判断作为理论基石: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对于人性趋利避害或自私自利本质的阐释是如此,卢梭、康德对于人性的纯朴无瑕或善良意志的定位也是如此。由于道德反思而非伦理认同成为现代政治的哲学基础,因此,现代政治诸理论形态具有共同的思想特征,这就是它们都是在一种“道德政治”的谱系中探索政治的合法性问题。(15)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现代政治关于正义问题的探讨,实质上是在探讨一种作为“道德政治”的正义概念何以可能。“道德政治”视域下的正义问题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从社会总体出发,正义意味着守护整个社会的公平法则,使得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其二,从权利个体出发,正义意味着保障个体权利不受共同体的越界性侵犯。由此,现代政治哲学的“两个信条”也被创建起来,即“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权利”是个人的首要美德。(16)这“两个信条”在以罗尔斯和诺齐克为代表的当代政治哲学关于“正义优先还是权利优先”的论争中引发了新的回响。 通过梳理政治思想史中的正义观念,笔者发现了如下事实:正义虽然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但是它的理论形态却并非一成不变。在古典政治哲学语境中,正义是一个社会伦理概念,作为道德概念的正义则是从现代政治的道德哲学前提中生发出来的。因此,正义观念构成透视现代政治作为“道德政治”的重要切入点。马克思对于现代政治的批判也正是抓住了现代政治的这一基本特征,以古典政治哲学的伦理正义视角跳出现代政治哲学的道德正义结构,从内部揭示了现代政治作为“道德政治”的结构性困境。 马克思对于现代“道德政治”的批判是在以《资本论》为标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完成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实现了对正义问题发生语境的重大转换,即把正义发生的“道德哲学语境”转换为“政治经济学语境”,从而颠覆了现代政治正义问题发生的思想前提,瓦解了现代政治对于正义的道德哲学定位及其所构建的二元正义结构。 如上所述,现代“道德政治”的正义问题基于一个两难选择的二元结构,即个体的权利优先还是社会的公平正义优先。西方政治哲学围绕该结构展开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但是他们只是各自坚持了这一结构的某一个层面,而从未真正超越这一结构。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未摆脱共同坚守的道德形而上学方法论,未跳出“正义到底意味着公平优先还是权利优先”这一“道德政治”问题域。与此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把正义从一个道德理论问题转化为社会现实问题,不再追问“公平优先还是权利优先”,而是对形成这一问题的社会现实前提展开了批判。这个前提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正义从一个关涉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和社会伦理问题,沦落为关涉个体利益在社会总体分配过程中是否得到尊重的道德问题。基于这一前提,正义的现代二元结构与资本逻辑的实体形而上学完成“联姻”,其导致的结果是,在资本逻辑的粉饰下,现代正义的二元结构获得了角色转换:一个是象征个体权利正义的“自由买卖原则”,另一个是象征社会公平正义的“平等交换原则”。 显然,按照上述两种原则,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似乎是最为公平与正义的,也最合乎现代政治所要求的两个正义原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自己也对这种公平正义进行了描述:“货币占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劳动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劳动就归他所有。劳动力维持一天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发挥作用或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决不是不公平。”(17)马克思这里真的是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做辩护吗?我们再看《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一章,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后,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政治经济学家在本国,即在宗主国,可以花言巧语地把这种绝对的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描绘成同样独立的商品占有者即资本商品占有者和劳动商品占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18)显然,从这段论述不难看出,马克思认为对资本逻辑正义性持辩护态度的,正是那些“花言巧语”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正如上文所说,资本逻辑的公平正义仅限于商品的流通和交换领域,一旦跳出这一领域而进入到生产领域,资本逻辑的非正义性便暴露无遗;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跳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狭隘视域,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逻辑的政治伪善本质。 在马克思看来,从根本上揭露资本逻辑的政治伪善本质,必须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就是现代政治的现实形态。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一个棉纺织厂的工人是不是只生产棉织品呢?不是,他生产资本。他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通过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19)“所以,资产者及其经济学家们断言,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千真万确呵!如果资本不雇用工人,工人就会灭亡。如果资本不剥削劳动力,资本就会灭亡,而要剥削劳动力,资本就得购买劳动力。”(20)“但是,生产资本的增加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权力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力量的增加。”(21)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政治的权力控制是以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这种形式实现出来的,因为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实质正是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内在的结构性危机的揭露,就不仅在于瓦解资本逻辑所组建的经济剥削体系,它在更深层意义上旨在揭露资本逻辑背后所贯彻的“自由买卖原则”和“平等交换原则”的正义伪善性,瓦解资本逻辑所组建的政治权力体系。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深层意蕴在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完成对现代政治的批判。我们只有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批判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政治观的思想高度和独特价值。 在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标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马克思开创了透视现代社会危机的新型正义观点:正义不应该被局限为只关涉物质财富何以公平分配的特殊性问题,更是关涉全人类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何以可能的普遍性问题。透过《资本论》的正义观,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下,立足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一“普遍正义”立场,超越了现代政治基于人性道德判断所面临的“公平还是权利”的“特殊正义”抉择,开辟了与现代“道德政治”截然不同的政治思想道路,完成了对现代政治的根本批判与超越。 注释: ①②李惠斌、李义天:《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3页;第5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06页。 ④(16)艾伦·布坎南:《马克思与正义》,林进平译,人民出版社,2013,第68页;第6页。 ⑤⑥乔治·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82页;第97页。 ⑦⑧⑨(12)(17)(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88页;第89页;第89~90页;第204~205页;第226页;第881页。 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61页。 (11)(19)(20)(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页;第348页;第348页;第348页。 (13)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310页。 (1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95页。 (15)张盾:《“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康德、马克思》,《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标签:政治论文; 资本论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政治学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