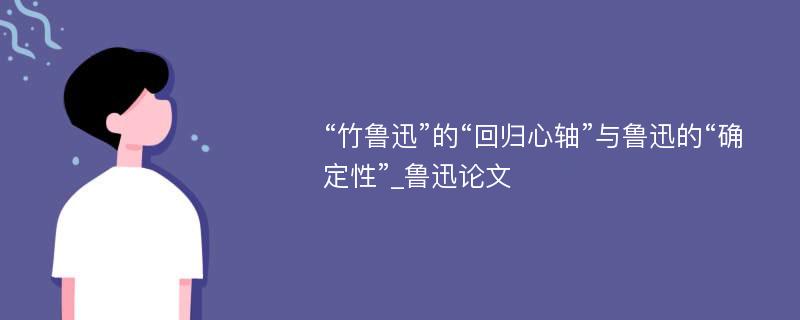
“竹内鲁迅”的“回心之轴”与鲁迅的“确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确信论文,回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5939/j.jujsse.2015.05.012 竹内好在他自己称之为“不成熟的研究笔记”[1]16的《鲁迅》中,提出了著名的“回心”说,认为在鲁迅的生命中有一次决定性的“回心”成就了这位伟大的文学者。而这种“回心”运动的力量之本,他则称之为是“回心之轴”。在《鲁迅》中,“回心之轴”一词的首次出现是在谈论《呐喊·自序》之时: 他不能像虚构过去那样来说明现在的心情,甚至回避做出说明。他说“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却并没对“确信”做出说明,至少没在话语上做出说明。这一点虽然也和他不是思想家有关,但我觉得与此相比,似乎还有略为深刻的意味。可以说,这关系到他的回心之轴。[1]8 在此,关系到鲁迅“回心之轴”的,既是鲁迅的“确信”,也是鲁迅未在话语上对其“确信”做出说明这一事实。在竹内好的理解中,“自有我的确信”者不只是追忆之中那个即将写作《狂人日记》(1918)的“我”,也是“现在”正在写作《呐喊·自序》(1922)的“我”,因此,“在话语上做出说明”就成为无法做到的事情。竹内好认为,鲁迅之所以无法在话语上说明自己的“确信”,与他不是思想家有关。这里的“思想家”似应理解为“职业哲学家”,竹内好的意思是,鲁迅不擅长以思辨性的语言进行逻辑解析和理论建构。就此而言,说鲁迅“不是思想家”并不为过。然而我们不能不追问的是,为什么在竹内好看来,鲁迅的“确信”必须以“哲学”的方式来说明? 从《呐喊·自序》本身的文意线索来看,“我的确信”就是指“铁屋子”是“万难破毁”的,即使“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也只能是“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而已。[2]441在一些常见的解读中,将鲁迅以这个譬喻表达的思想看做是对旧社会、旧文化之顽固与改革之艰难的清醒认识,而他终于决定投身新文化运动,并努力地为《新青年》创作,则被认为体现了他战斗的决心与毅力。与此相应,关于“确信”的解读则是:当时的鲁迅还没有找到变革中国的“正确道路”,尤其是还没有看到人民和先进思想的力量,因此有些偏于悲观,这也是五四时期鲁迅思想还不够成熟的表现。 可以说,不同的解读角度,正是体现了不同的问题意识,而多个解读角度的并存,则恰与鲁迅及其作品的丰富性相互映衬。上述解读方式与竹内好的解读相比,最大的不同正是在于将这里的“确信”看做是暂时的和相对的,由此也就不会认为鲁迅有对此做出进一步说明的必要。那么,竹内好为何要“多此一举”,偏偏追问鲁迅为什么不对此作出话语上的说明呢?显然,这是因为他觉得鲁迅这个“我的确信”不像字面上那么简单,当鲁迅写下这四个字的时候,其实触及了自己相当根本性的“信念”,这个“信念”甚至与他的“回心之轴”有关。从这里入手,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一窥竹内好所谓“回心之轴”的真实面貌。 我们沿着竹内好追问的思路继续探寻,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面临这样的提问:鲁迅在此所说的“确信”是来自何处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一方面,来自鲁迅到那时为止的人生体验;另一方面,也来自鲁迅自身的心灵与性格。更准确地说,是这两个方面在特定时空中的结合,造成了鲁迅的这种“确信”。然而历来论者多留意于前一方面,尤其是《新生》杂志和辛亥革命的挫折;竹内好的“回心之轴”说,却尤为重视后一方面。这里,就不能不提到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中另一个分量很重的概念:“赎罪”。 鲁迅并不认为自己是殉教者,而且很讨厌自己被看作殉教者。正像他不是先觉者一样,他也不是殉教者。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表达方式却是殉教者式的。我想象,在鲁迅的根柢当中,是否有一种要对什么人赎罪的心情呢?要对什么人去赎罪,恐怕鲁迅自己也不会清晰地意识到,他只是在夜深人静时分,对坐在这个什么人的影子的面前(散文诗《野草》及其他)。[1]8 “要对什么人赎罪的心情”与“殉教者”式的表达方式,在竹内好的文章中是一体的,可以互为注解。问题是,这两种表述对于我们来说都不容易真正理解。 “殉教者”的本义是为了自己信仰的真理而失去生命的人,那么什么是“殉教者”式的表达方式呢?大概,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点是对于生命的态度吧。正是从这一点来说,既要明确鲁迅“不是殉教者”,他有着“人得要生存”的顽强本能;也能体会到鲁迅的“表达方式却是殉教者式的”。他对于“生”所带来的种种物质享受,比起一般人来都颇为淡漠和轻视——也许只有美术所带来的视觉享受是个例外,但那已不是单纯的物质享受了,或者说那主要不是物质享受。这样,“生命”对于鲁迅来说就主要不是意味着肉身的感受。这从他一生不喜欢游览公园、到杭州西安等名胜之地旅游也觉得乏味,但却喜欢看反映异域风光的影片等轶事中也可见一斑。因此,在他的文字“表达”中,总是会自然地流露出萦绕着“义务”感的生命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人得要生存”这句话之于鲁迅的真正含义。这样的生命观,使得他虽然一生绝不皈信任何宗教,却具有类似于“旷野试炼”的生命质感。他之让人觉得“严酷”、“不近人情”,和让人觉得“善良”、“温暖”,大概都与此有关。 鲁迅一生大概不止一次将自己比喻为“牛”,更多人记得并且常常引用的,除了“诗无达诂”的一句“俯首甘为孺子牛”之外,是许广平在文章记录的谈话:“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3]62。这句话之所以会让许广平女士记忆深刻,大概是因为正与她心中对于鲁迅的尊敬与爱怜之情相契合吧。而我们今天若以鲁迅的文章、信札和其他人记录的鲁迅谈话作为参考来看,会觉得此语很可能只是鲁迅工作疲劳之时的一句调侃而已。他将自己的工作和“挤牛乳”放在一起说,是在《并非闲话(三)》(1925)这篇文章中,其大意是讲自己的文章并不是什么“创作冲动”的产物,只是他人催促才匆匆写出的。这也正可以和《呐喊·自序》的文脉相衔接。自有“我的确信”者,是不可能有文章“喷涌而出”的冲动的,惟有“得意于生存”或“有所求于生存”者才能获得这样的“创作冲动”,而鲁迅是“得要生存”的。他不以为自己的生存多么了不起,甚至恰恰相反,他常常为自己的生存感到惶恐。因此他也不愿意教导别人该怎么生存——与其说是“不愿意”,不如说是“会为此感到羞赧”更准确。这样的作家,是惟有“挤”才有文章的,因为这“挤”的动作便表示着“挤”者认为这“牛乳”对自己有用。在1926年写的《〈阿Q正传〉的成因》中,他说得更明白:“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4]394-395 这里重申自己的文章是挤出来的,而且再次将自己比喻成牛。但这次的“牛”却和“挤牛乳”不存在直接的关联了,在后文中还调侃说自己是公牛,并无牛乳。这段话的内在逻辑是:因为没有什么话要说,没有什么文章要做,所以自己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所谓“挤出来”者,意思是给人们添点热闹;若以为自己能堪大用,那么就会有话要说、有文章要做,然而既然已明知自己不堪大用,那么若别人还觉得可以废物利用而特地来“挤”,那也不必过于吝惜自己的力气和形象。联系其后文来看,只要不是利用自己以谋财害命,还给自己以自由觅食和喘气的工夫,不把自己占为私有之物,不把自己杀戮吞噬,那么就是不介意别人来“挤”的。鲁迅自言这是一种“自害的脾气”,而正是在这种看似自嘲实则严肃的写作中,我们可以感知到他的确不是“殉教者”而却有“殉教者”式的表达方式。 然而,这“殉教者”式的表达方式,又为何可以言说为“要对什么人赎罪的心情”呢?这正与他为自己的生存而感到惶恐有关。在《记念刘和珍君》里,他称自己为“后死者”、“苟活到现在的我”,说“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4]290《论语》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第九》),此语历代儒者多解释为君子之气节虽历患难、诱惑而必不改,但就其喻体来说,标举的却是困境中的生存力。而事实上,也确有以在“这样的世上”活下去、活得长久为人生智慧的文化,《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将“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之类的对联悬挂在书房里,就是这种文化的体现。《怀旧》中关于秃先生的议论更是一针见血:“人谓遍搜芜市,当以我秃先生为第一智者,语良不诬。先生能处任何时世,而使己身无几微之痏,故虽自盘古开辟天地后,代有战争杀伐治乱兴衰,而仰圣先生一家,独不殉难而亡,亦未从贼而死,绵绵至今,犹巍然拥皋比为予顽弟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5]228 能够不管世道怎样、他人怎样,都保证自己的身体毫不受到损害,这就是“智”,而其事迹,就是“独不殉难而亡,亦未从贼而死”,在这样的“智”者看来,“后死”二字绝不是什么可愧的词,他们最多只会看似怜悯而实则居高临下地历数“先死者”的种种不“智”之处,以训导人们学习自己擅于“处任何时世”的“智”。我们再深究一步:何以他们会如此?或者说何以鲁迅不会如此?那是因为在这些“智”者的价值视野里,自己肉体感官的享受是“有”比“无”好、“多”比“少”好、“优”比“劣”好、“难得”比“常见”好……而这一切的底线就是“生存”,所以尊奉后死者也就顺理成章;而鲁迅在人生意识的根本上就和他们存在分歧,“智”者们标榜和追求的那些,之于鲁迅来说最多是人生的余暇或点缀,并不进入他的价值视野,在他看来,有价值的是精神之力和精神之美。这也是他希冀于自己人生的。在《呐喊·自序》中他说自己学医时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2]438笔者以为,这些自述是可以照字面来理解的,这些真的就是他立志学医时的所思所想。治病之于病人来说当然是关乎肉身、物质的行为,然而从鲁迅当时梦想中作为医生的角度而言,却是精神之力的实现,即凭自己的所学为他人、为祖国造福。这正是鲁迅本来心地的真实写照。他最初的发想是:实现自己的精神之力,展现自己的精神之美,为世界创造一些幸福。然而世界给予他的一直都是一个答案:此路不通。父亲去世时,他遵“礼俗”大喊父亲,从此自己在父亲临终时造成父亲痛苦的心灵伤痕挥之不去;离开绍兴去南京读“新学”,是一次逃离;离开中国去东京留学,又是一次逃离……他不是在逃离别人对自己的伤害,而是在逃离无法做到不伤害别人的环境。当然,这“不伤害”是以他自己的标准,以他只想创造幸福不想创造任何不幸的标准,这标准太过严苛,以至于他总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最为众所周知的就是他的婚姻。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他不得不有违自己的理想;他发现自己终难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当世界逼得他逃无可逃的时候,他从自己的内部产生了“要对什么人赎罪的心情”,也形成了竹内好所谓的“回心之轴”。可见,无论是“要对什么人赎罪的心情”,还是“殉教者”式的表达方式,其实质都是鲁迅独特的人生态度。 战后,竹内好写作《鲁迅入门》,沿用并深化了自己独创的“回心”、“回心之轴”、“赎罪”这些理论话语。在第3章《作品的展开》中,他这样评述鲁迅写作《朝花夕拾》的精神动因: 它是《孤独者》所涉及的主题的变形,是一种通过回顾自己存在的根本而确定现在所处位置的欲望。作为对《呐喊·自序》不足的补充,不如通过从那里重新走到过去来即时地解决《呐喊·自序》所提出的问题。……从年代上讲,好像并不是写到辛亥革命完成,而后一直探索到《呐喊·自序》为止。不过也不是开始写时就打算到此截止。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不截止,就没有穷尽。他作为作家的条件不允许他运用这种写法,一直走到《呐喊·自序》和《孤独者》这条线。结果,对于他的回心之轴来说,本质上的契机难道不是由于写了《范爱农》才获得了满足吗?[6]132 竹内好的这段议论中,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最后一句话。在中外鲁迅研究界,还很少有人将《范爱农》这篇回忆散文重视到如此程度,而竹内好对于此篇的重视,又恰恰与“回心之轴”这个概念密不可分。竹内好在此以《朝花夕拾》作为鲁迅对《呐喊·自序》的补充与应答,接续了《鲁迅》的研究思路;而他又认为《朝花夕拾》的主题是《孤独者》主题的变形,这样一来,《呐喊·自序》、《孤独者》和以《范爱农》为终结的《朝花夕拾》,就构成了围绕着鲁迅“回心之轴”的一组连带关系。“回心之轴”本身是无法言说的,因此在鲁迅作品文本中也是不可见的,竹内好只能致力于寻觅鲁迅怎样在写作中“满足”“回心之轴”的“契机”。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在竹内好看来,《呐喊·自序》最核心的谜题,就是“我的确信”,那么《朝花夕拾》尤其是《范爱农》所力图“解决”的“问题”,自然也是指此而言,至于他所谓《孤独者》的主题,也必然与此相关。从《鲁迅入门》中我们可以看到,竹内好认为从《孤独者》“可以观察到鲁迅的内心,因为我觉得这是根据他自己内心逃离的体验,为了使这一体验存在下来而写成的作品。我不能详细地分析这种体验。我觉得如果理解了这部作品也就能够理解鲁迅了”。[6]115笔者在前面曾论述,鲁迅的“逃离”不是为躲避外来的伤害,而是想从体制性创造的不幸的环境中脱身,而“逃离”的结果是终于发现那样的环境似乎无处不是。《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将此称之为“运命”:“自然,世上也尽有这样的人,譬如,我的祖母就是。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7]98这话并不是说魏连殳和他的祖母是一样的人,而是说作为新知识分子的魏连殳也感到自己心中有一种像他那作为旧家族续弦女子的祖母一样将自己完全从世界孤立出来的冲动,然而即使真做到像他祖母那样了,也难求死后一个哭他的人都没有——他仍然不得不存在于世界既成的秩序之中。当然,笔者这样的分析,也绝非能够达致竹内好“详细地分析这种体验”、“理解了这部作品”之期许,只是尽量去追踪竹内好的思路而已。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或许就是:鲁迅写魏连殳,其实是写自己的“确信”,而他在范爱农这个现实中的友人之精神与生平中,也看到了同一个“确信”。周作人关于鲁迅日本留学时代言行的回忆文章可能是竹内好写《鲁迅入门》时也还不曾看到的。在周作人的回忆中,《范爱农》中范爱农在徐锡麟遇难后的留学生同乡集会上惹得“我”勃然大怒的主张——不发抗议电报,其实却也是当时鲁迅自己的主张。[8]104若依据此说,那么《范爱农》中同乡会上的“范爱农”甚至可以看做是鲁迅以青年时代的自己为原型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竹内好虽未提及这一材料,但却敏锐地指出:“他把范爱农看作另一个自己。也许他内心对范爱农有一种负疚感。这与几年后失去年轻的朋友柔石时的悲叹如出一辙”。[6]135无论是现实中的朋友范爱农、柔石以及刘和珍、韦素园,还是自己作品中虚构的人物魏连殳,这些人的死都最能够激发起鲁迅身为“后死者”的自觉,因为这些人的死犹如他心中那“确信”的惨烈回声——铁屋子是万难破毁的,醒来的人惟有承担受难的命运。鲁迅相信范爱农的死其实是自杀,而《孤独者》中魏连殳其实也等于是自杀而死,因而比起在政治活动中遇害的柔石、刘和珍来,他们的受难尤为分明地表现为精神的受难。《朝花夕拾》的追忆只写到范爱农之死就结束了,而范爱农的死,是鲁迅“另一个自己”的死。这“另一个自己”的死,是鲁迅先已“确信”的事,好友范爱农的经历将这一心理事件作为残酷的现实呈现于鲁迅眼前。也正因为这世界毫不留情地逼迫这样的人去死,所以鲁迅必须活,而且不能像魏连殳那样自杀式地活,他活着,“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2]《坟·题记》,4他以要对什么人——其实这个“什么人”正是他的另一个自己——赎罪的心情生活和写作。在这样的生活者和文学者周围,任何外来的影响都无法包裹在“现实”、“新思想”、“真理”、“权威”的外衣之中,而只能如竹内好所说,“被投入到他回心熔炉”[1]53、“作为形成他回心之轴的各种要素之一”[1]57。而这“回心之轴”的主体,则是他的“确信”和他对这“确信”的执拗抵抗。至此,我们或许方知,在鲁迅写下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一语之中,正是这“虽然”二字,才最终实现了竹内好所谓“回心之轴”的形成,归根结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确信”才关系到他的“回心之轴”——与现实世界无尽的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