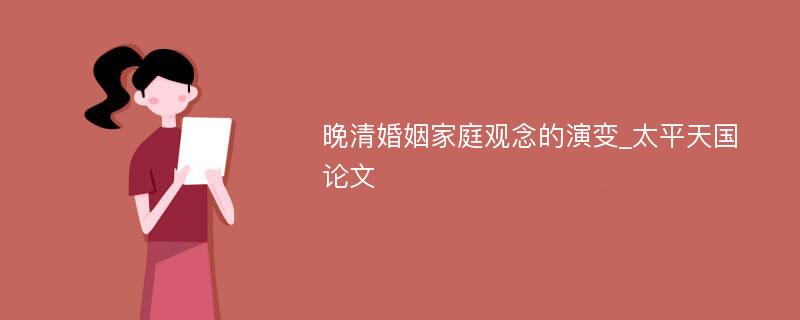
晚清婚姻与家庭观念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观念论文,婚姻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K252
中国封建婚姻家庭发展到明清之际,已经孕育着新的时代因素。当时的早期启蒙学者如李贽、俞正燮、冯梦龙等纷起对封建礼教进行抨击,倡导男女平等、婚恋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即是婚姻家庭观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本土之萌蘖。降至晚清,随着国门的洞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所有组成部分逐渐展示在中国人面前,直接地刺激、启动着传统社会结构从形式到内容的蜕变。在这种时代大变迁的背景下,当时社会中的一些不同类型、层次和范围的进步与新兴阶级力量先后“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和各自的理想抱负出发,相率对处于传统社会文化核心层次的封建婚姻家庭进行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反思和评判,力图在此基础上确立符合本阶级需要的新婚姻家庭观,展现了婚姻家庭变革和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共同趋向。
一、太平天国对封建婚姻与家庭观念的冲击
晚清中国最早向封建婚姻与家庭发起冲击的是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洪秀全受过儒家的正统教育,又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他对现实社会的严重不满,加之出于对独一无二真神上帝的排他性崇拜,产生出对儒家提倡的君臣、父子、夫妇等区分尊卑贵贱的封建礼教的朴素反抗心理。例如,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说:“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注:《太平天国》(一)第87—88页。)在《原道醒世训》中又写道:“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注:《太平天国》(一)第92页。)这些话虽然未能揭示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封建主义本质,但毕竟触及到了以往被奉作“卷舌而不可议论”的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的封建人际关系禁忌。
洪秀全的这种思想必然反映到太平天国的婚姻家庭政策上。早在金田起义之初,洪秀全就发布了“别男行女行”的命令,后来在《太平条规》中又规定男女官兵“要别男营女营”,严禁夫妻同居,违者轻则罚罪,重者格杀勿论,这实际上是取缔了太平天国社会军事集团内部的婚姻与家庭生活。一时间太平天国内部呈现出“父母兄弟妻子立刻离散”,“虽夫妇母子不容相通”(注:《太平天国》(四)第695页。 )的生活局面;绵延了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婚姻与家庭观念骤然受到了前所未遇而惊世骇俗的猛烈一击。
奠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其中在婚姻方面明文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旨在以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原则,废除以权势和门第观念缔结的封建买卖婚姻制度,彻底更新婚姻与家庭观念。但造反可以“废婚”“毁家”,治国却终究以“安民”为本。为聚扰因“不准有家”而“涣散思去”的人心,太平天国于1854年被迫下令恢复了天京城内军民的夫妻家庭生活,并“许(未婚)男女配偶”。(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1册第113页。)为此,太平天国特设立了“婚娶官”专门负责婚姻事务。《金陵纪事诗》云:“寻常婚娶浑闲事,要向官家索票签。”诗原注说:“男女配合,须由本队主禀明婚娶官,给‘龙凤合挥’方准。”(注: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第338页。)“龙凤合挥”即结婚证书。 这是一种基于男女自愿结合的一夫一妻制度,完全不同于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封建父母包办和买卖婚姻制度,“从而他们的结婚也就成了爱情的结合”。另外,在太平天国,“离婚不仅是不准许的,并且实际上也根本没有人懂得或想到离婚这件事。”(注:[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44—245页。)这对封建的所谓“七出”离婚惯约是个根本的否定。
然而,洪秀全毕竟是一个受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学说长期熏陶的农村知识分子,太平天国也依旧是一场旧式农民战争。随着太平天国革命后期洪秀全革命锐气的消退和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逐渐封建化,洪秀全自觉不自觉地又对他曾大张挞伐过的封建婚姻家庭观念加以汲取和利用,这可从以下文献记载中窥见一斑。如洪秀全在《钦定前遗诏圣书批解》中说:“朕是太阳,朕妻太阴”。(注:金毓黻田余庆等编辑《太平天国史料》第86页。)在《劝学诗》中的“男道”中又说:“乾刚严位外”,而“女道”应是“幽闲端位内”,(注:《太平天国》(一)第 234页。)并认为“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注:《太平天国印书》(上)第62页。)在此思想基础上,洪秀全甚至规定自己的妻妾嫔妃若有“服事不虔诚”、“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讲话极大声”、“面情不欢喜”等言行举止,均在“十该打”(注:《太平天国》(二)第435—436页。)之列。另外,太平天国还根据官爵品秩的高低,规定诸王和属官可拥有数量不等的妻妾。凡此种种,充分说明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后期的婚姻家庭观念几乎已回归到以前封建礼教所宣扬的“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原始起点,个别之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从背离、反对封建的婚姻家庭伦理到回归、宣扬封建婚姻家庭观念的心路历程,从根本上说是农民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落后性、分散性和狭隘性合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长期生息在小农经济社会结构中的农民起义领袖们,虽然能够雷厉风行地暂时革除了某些封建的婚姻形式,拆散了家庭的生活单位,但不仅未能正确地导引人们真正地转变旧的婚姻家庭观念,而且也跳不出封建纲常伦理的思想藩篱。这样的既“叛道”又不“离经”的矛盾思想与举措,就使他们对晚清婚姻家庭变革所做的贡献受到了很大的历史局限。
二、西方近代婚姻家庭观念的引入与传播
19世纪60年代后,因洋务运动兴起而引发的新的一轮西学传播大潮开始从中国沿海到内地,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到基层社会广泛传播开来。伴随着西方各种自然科学技术和部分社会科学学说的涌入,有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思想和婚姻家庭的观念也被介绍到中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婚姻家庭观念的产生。
传教士是播种近代西方婚姻家庭文明的“不自觉的工具”。寓华的传教士不但通过撰写、翻译西方宗教、史地、政治、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创办报刊,专门介绍了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而且直接批评了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主张禁止一夫多妻,结婚年龄要适当,不宜早婚,三十而娶,二十而嫁。(注:花之安:《自西徂东》卷2。)尽管这些“转口”输入的西学颇为庞杂琐碎, 且仅为其沧海一粟,但对当时热切关心时务的知识分子们了解西方社会文明,扩大认知空间,孕育近代婚姻家庭新意识,毕竟起了一些启蒙开新的作用。如曹亚伯曾自叙其早年受韦廉臣《格物深源》一书影响道:“见此新书,极其快意,……顿悟守旧之非”,“于是家庭革命、社会革命之思想,日往复于胸中,不顾自身之一切,时与旧习惯相抗矣。”(注: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第1页。)
与此同时,清政府派赴欧美的出使官员通过奉命按月咨送回国的载记,叙述了他们对西方国家社会风情的观察与思考,成为当事者与时人转变婚姻家庭观念的另一路径。这以1876年随郭嵩焘出使欧洲的刘锡鸿、张德彝最为典型。据载,他们抵达英国不久,就有一连串奇异的感觉:“到伦敦两月,细察其政俗,惟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全未之讲,自贵至贱皆然。”(注: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09页。 )“西人不知有父母,……凡为子者,自成人后,即各自谋生,不与父母相闻。闻有居官食禄之人,睽离膝下十数载,迨既归,仍不一省视者。”“男女婚配皆自择,女有所悦于男,则约男至家相款洽,常避人密语,相将出游,父母之不禁。款洽既久,两意投合,告父母互访家私,家私不称不为配也;称则以语男女,使自主焉。”(注: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82页。)“西国女子之嫁也,……不待父母之命, 不须媒妁之言”,“男女私交,不为例禁”。(注: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473页。)显然, 面对这些与中国的婚姻家庭伦理迥然不同的生活情景,刘锡鸿和张德彝在惊诧之余,又流露出颇多赞许的态度。饶有意味的是,刘锡鸿之所以能随使出行,是因守旧派大臣看中了他反对把“夷狄之道”“施诸中国”的坚定立场,刘亦以“此行能左右郭公(嵩焘)这个洋务派思想家”及“用夏变夷”为己任,但经过这番文明的洗礼后,他却“抵不住,宣告破产了”。
自此以后,更多的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接踵出洋,饱览域外文明,并从中吸纳大量新鲜信息反馈回国内。毋庸置疑,这些出自国人切身体验和思想整合的“真知灼见”,比起外国传教士的宣传来更容易产生社会震荡效应,从而使近代婚姻家庭意识较多的在其周围的人群尤其是交往的开明学者中逐步扩散。
三、资产阶级的新婚姻家庭观及其社会影响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面对民族生存危机和封建统治危机的交相刺激,开始急切地对中国社会进行较为全面的诊断和反省,而不再囿于学习外国船坚炮利的肤浅认识。于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重要构成的婚姻家庭,便在戊戌思潮的冲击下,面临着直接的挑战。而酝酿多年的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所具有的背离传统婚姻家庭的观念,随之成为一种自觉的主观整体意识。
康有为是晚清中国第一位能比较清醒地认准封建婚姻家庭阴暗作用的思想领袖。他构思于19世纪80年代的《大同书》,也就是一部向封建婚姻家庭挑战的宣言书。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评论说“全书数十万言,……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四。)当然康有为完全不同于农民领袖洪秀全,他的“不得有夫妇旧名”、“去家界”说里蕴含着比较完全意义的近代意识,也具有更多的对封建婚姻家庭关系的深刻剖析。康有为指出,男女婚姻家庭“不得自由”,有悖于人伦公理,而“一家之中妻之于夫,比于一国之中臣之于君,以为纲,以为统,”(注:康有为:《大同书》第155页。)更完全违背了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 他认为所谓“在家从父”,婚姻完全听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际上是侵犯了妇女的自主自立之权;所谓“出嫁从夫”、“烈女不事二夫”、“为夫守节”,“既背孔子之经,又苦人生之道”,实有“害人”、“逆天”、“损公”、“伤和”四大害,“万不可行”。“全世界人欲致大同之世……,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注:康有为:《大同书》第253页。)对于封建家庭,康有为尖锐地揭露道:“凡中国之人, 上自簪缨诗礼之世家,下至里巷蚩氓之众庶”,由于封建家长的专制,家规、家法的禁锢,表面上“太和蒸蒸”,但“叩其门内”,就会发现“怨气盈溢”,充满了“强合之苦”,而其“礼法愈严者,其困苦愈深”,乃至虽“史迁之笔不能达其怨愤,道子之画不能绘其形相,累圣哲经子语录格言而不能救”。(注:康有为:《大同书》第155页。)那么, 这般困苦是怎样造成的呢?康有为进而阐述说:“夫天下之至大者莫如意见矣,强东意见而从西意见,既已相反,既难相从;不从则极逆,从之则极苦”。(注:康有为:《大同书》第182页。 )这就揭示了谦谦家礼的外衣下,封建家庭伦理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指出了封建家庭流弊的根源。不过,康有为最终没有努力去冲破旧的家庭藩篱,而只是勾画了一个纯属空想的没有家庭的大同世界来代替眼前的“家界之累”,这样就在事实上减弱了其思想的攻击力。
谭嗣同克服了康有为知行脱节的毛病,他不但在其公开发表的名著《仁学》中大胆揭露了父母包办婚姻对男女青年的危害,谴责了封建贞节观给广大妇女造成的生活灾难,而且进一步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主张以“朋友之道贯之”父子、夫妇、兄弟之伦,(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50页。 )即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原则代替封建主义的婚姻家庭伦理,这就超越了同时代其他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闪射出“家庭革命”的思想光辉。
1898年7 月由维新妇女创刊的《女学报》也颇为重视对封建婚姻的批判。该刊站在被压迫女性的立场,揭露和斥责了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宗法社会施加于妇女婚姻生活中的种种迫害。有人撰文指出,女子“以自有之身,待人主婚,为人略卖,好恶不遂其志,生死悉听众人”,(注:《女学报》第5期。)已属不幸,而出嫁后,还要“从夫”, “夫自命为纲”,常常给予非人待遇,更加悲惨。不仅如此,夫死后,还要“从子”,做“节妇”。至于“为人玩弄”,或“忍为婢媵”,或“流为娼妓”,更在所不免。她(他)们强烈要求破除具体体现“夫为妻纲”的“三从四德”之说,改变女性现实生活境遇,实现“权利平等”,婚姻自主。
如同这一时期其它领域的社会改革一样,维新派的婚姻家庭主张也引起了当时封建顽固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诘骂维新派所论“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是“直似只须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召乱无已,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4118页。)攻击维新派专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大为骇怪”,“无异叛逆”。此时的洋务派亦自觉地变成了封建婚姻家庭伦理“国粹”的卫道士。1989年,张之洞发表了《劝学篇》,其中说道:“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张之洞尤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注:张之洞:《劝学篇》内篇第三,《明纲》。)反面文章正面读,顽固派与洋务派的交相驳难,倒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维新派婚姻家庭观念的进步性,并反映出它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和维新运动的迅速失败,维新派对封建婚姻家庭的清理与批判未及深入展开便告一段落。因此他(她)们的婚姻家庭观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观念体系,并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例如,康有为既主张毁灭阻碍社会发展的封建家庭,又认为奠基于其上的封建家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系中华民族内聚力的作用:“万国有人伦而族制莫如中国之盛,故人类最繁”。(注:康有为:《大同书》第171页。)又如,谭嗣同虽然看到了父子、夫妇之纲是乘着“君为臣纲”的威势而肆虐于民人社会生活,但并未清楚地认识到前者的推行从根本上保障了后者的实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尽管如此,维新派的种种议论,仍形成了晚清第一次初具规模的婚姻家庭改良思潮,推动了新婚姻家庭观念的演进。
四、推进与反复
新世纪开始后,婚姻家庭领域的思想变革又有了扩张之势。其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更加全面深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清政府更加腐败,无可挽救地走向崩溃;新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力量不可遏止地生长;民主革命思潮与运动风雷激荡,蓬勃兴起。新的严峻的形势,使人数剧增起来的革命派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一切革命思想的准备显得十分紧促,对封建婚姻家庭的批判自然也相应少了些夫子式的学理探讨,而多了些“斗士”的火药味儿。首先,革命派知识分子不再作变与不变的复杂论证,而是以简洁、通俗有力的言词,直接倡导婚姻家庭革命。他们指出,封建婚姻“当其始,有所谓问名纳采者,则父母为之;至其中,有所谓文定纳币,则父母为之;及其终,有所谓结褵合卺者,亦莫非父母为之。”而当婚之两主人翁,自始至终却“不得任一肩,赞一辞,惟默默焉立于旁观之地位”。(注:见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855页。)这种专制型父母包办婚姻造成“男女不相见”、“媒妁哄骗”、“卖婚”、“聘仪奁赠”、“繁文缛节”、“早聘早婚”、“迷信流行”等弊害,不仅“坏夫妇之爱情”,给人们带来“终身恨事”,而且也影响了家庭生活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既婚后,入其室,有慨其叹者;睹其人,有啜其泣者。乃浸而妇姑勃溪矣,浸而兄弟阋墙矣,而大好之家庭,自此遂终无宁岁”。(注:见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854页。)“盖婚姻为人道之大经,未有夫妇不和而家庭能欢乐者,亦未有夫妇不和而能专心致志以为国家社会建事业者”。(注:《留日女学会杂志》第1期。)革命派认为,人类婚姻的历史经过“掠婚”、“卖婚”、 “赠婚”和“自由结婚”四个时期,“如今西方各文明国家”,“其婚姻之制已入于第四期”,即“自由结婚时代”,“独中国之婚姻尚在卖婚时代”。(注:《安徽白话报》第17期。)“今日家长之威严,直有第二君主之权利”,(注:《江苏》第7期。 )所以他们下决心要“以自由结婚为归着点,扫荡社会上种种风云,打破家庭间重重魔障,……为男女同胞辟一片新土”。(注:见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858页。)在这种全新意识的主导下,当时像破除“礼法婚姻”、“专制婚姻”、“毁家革命”之类的呼声不绝于耳;《三纲革命》、《家庭之革命》、《家庭革命说》、《女子家庭革命说》等文章连篇累牍,充溢于报刊杂志和有关论著中,大有章太炎所谓“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的冲天气势。
平心而论,革命派思想家的一些激进时论并不完全符合婚姻家庭生活实际,矫枉过正的负作用也非没有,但它却顺应了当时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迎合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自由平等的急躁追求,因而在晚清学界中颇具号召力和影响力。惟因如此,这一时期反对封建婚姻家庭思潮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达到了相对的统一,这以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女界学生精英最为勇敢突出。秋瑾挣脱封建婚姻束缚,走出家庭的事例自不待言,其他如陈撷芬、梁绮川、徐慕兰、庄汉翅、宋雪君等都是在亲身反对封建婚姻家庭的斗争中,获得了革命的青春。至于留学生和国内学堂学生创办“自由结婚演说会”,带头举行文明婚礼,宣唱《自由结婚歌》,反抗家长压制之事,更是所在皆有,屡屡发生。(注:参见拙作:《辛亥革命与婚姻家庭变革》,《河北师院学报》1989年第2期。 )这种身体力行地变革婚姻家庭意识的情形,恰恰回应了丁初我1904年在《家庭革命说》一文中的呼唤:“欲革政治之命者,必先革家族之命,……而革家族之命者,尤必先革一身之命。”(注:《江苏》第7期。)
冲击变革必然引起磨擦对抗。在这个社会剧烈动荡和变化的过渡时期中,社会上大多数人依然恪守着封建婚姻家庭的观念,视鼓吹破旧立新的革命派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为离经叛道的罪人,指责学生中出现的“家庭革命,秘密结婚”是革命党人蔑视“君父之尊”,破坏“男女之防”(注:《东方杂志》第5年第3期。)造成的恶果。他们认为“我国古圣垂教,首重道德,经传所载,皆纲常伦理之精言”,若一旦废除,“其殆害于人心世道,较洪水猛兽为尤烈,其危险不可思议”。(注:《东方杂志》第5年第3期。)强调“天尊地卑”乃“自然之序”,“阳动阴静”是“造化之机”,“男刚女顺”、“夫唱妇随”是“终古长存之至理,万年不变之常规也”。(注:《东方杂志》第5年第3期。)与此同时,清政府学部专门发布了《札饬各省提学司可严禁自由结婚文》,亟令各地方官员加强对学堂学生的思想控制和行为规范,严禁学生演讲“自由结婚”、“男女平权诸谬说”,“以维风化”。(注:《四川学报》1907年第5期。)另颁示停闭了“倡言自由”的女子学校, 要求对其他学堂中“沾染恶习者”,“立即斥退”。(注:《四川学报》1906年第6期。)一些封建家长也自动以“教子”为道德己任, 对倡行婚姻家庭革命的“不肖”子孙儿女进行压制。如“顾颉刚在辛亥年,是一个临近毕业的中学生”,主张“实现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家庭、没有金钱的社会”,被百般疼爱孙儿的老祖母严词质问:“既经没有家庭,把我放在哪里?”而“请你住在养老院”的答对,则招致勃然大怒。(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99页。)又如贵州一位任姓女生争取婚姻自由, 竟“被父母驱逐,官长拘押”。(注:《民立报》1911年9月25日。 )民主自由平等,本与“三纲五常”格格不入,变革时期日趋明显的思想分野和代沟,更扩大了彼此理解的难度,增加了冲突斗争的激烈性。
民国告成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些旨在蠲除“旧染污俗”的政令,许多革命党人予以响应,相继成立了“南京女子参政同盟会”、“社会改良会”等移风易俗的社团,立意“实行男女平等”、“废止早婚”、“提倡自主结婚”、“实行一夫一妻主义”、“禁止无理离婚”、“承认再嫁之自由”等章约。(注:《宋教仁集》下册,第378—379页。)看起来,在婚姻家庭观念及其问题上的一场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变革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了。然而,随着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和共和政府与封建势力的始终共存,维护旧礼教的舆论与社会势力逐渐复活起来。原香港实践女校的许多学生因反抗包办婚姻而“出家革命”,但民国建立后工作生活均无着落,返回乡里,家长又以前约相逼,迫使她们再度出走,“以避其锋”。(注: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 集,第321页。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洎洎青春热血换来了民主共和政府,却不但没有实现“为男女同胞辟一片新土”的终极理想,反而连本属于自己的“共和之国民”法定应享有的自由权利也未得到。
辛亥前后婚姻家庭变革进与退的悲剧性事实表明,时代赋予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构建20世纪中国婚姻家庭新观念的任务,但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去深入思考和实践。这样,历史就把重新探索和建设的重任留给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
标签:太平天国论文; 洪秀全论文; 家庭观念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婚姻与家庭论文; 男女婚姻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走向世界丛书论文; 大同书论文; 康有为论文; 东方杂志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太平天国运动论文; 远古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