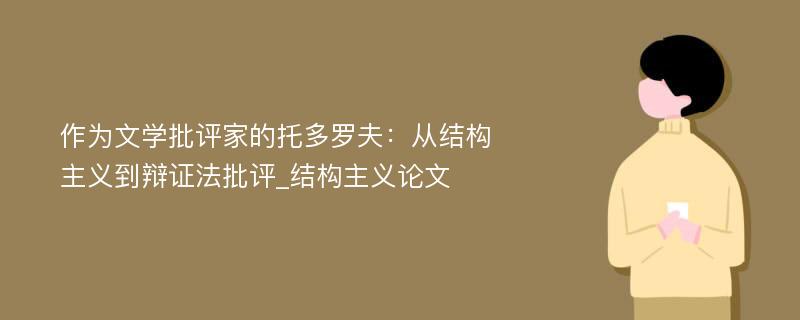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托多罗夫——从结构主义到对话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批评家论文,多罗论文,批评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茨维坦·托多罗夫(Tzvtan Todorov)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界占有重要地位。他1963 年从保加利亚移居法国, 30多年来,笔耕不辍。综观托多罗夫的主要著述,可以将他的研究活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3—1972年,托多罗夫主要从事结构主义诗学和叙述学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1965年,托多罗夫在罗兰·巴尔特的指导下完成了他的第一本批评著作《文学与意义》(Littérature etsignification)。同年,他搜集、整理并翻译的《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论文集》(Theorie de lalittérature,textes des formalistes russes réunies)出版。〔1〕60年代中期,结构主义批评在法国方兴未艾,托多罗夫很快成为这一流派的主将。他在1968年发表的《诗学》(Poétique)一书中阐述了结构主义诗学的理论要旨和分析方法。〔2〕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托多罗夫致力于叙事语法和体裁理论的研究,《〈十日谈〉语法》(Grammaire du Décaméron,1969)和《幻想作品导论》(Introductionà la littérature fantastique,1970)分别代表了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此外,1971 年出版的《散文诗学》(Poétique de la prose)一书收集了他写于1964至1969年间有关结构主义叙述学的十几篇论文。
第二阶段:1972—1981年,托多罗夫主要从事象征与阐释理论的研究,同时他对西方批评史和自己结构主义的批评道路进行反思甚至批判,最后提出了对话批评主张。〔3〕在此期间, 托多罗夫首先出版了两部专著:《象征的理论》(Théories du symbole,1977)和《象征与阐释》(Symbolisme etinterprétation,1978)。他通过对西方美学史及批评史的回顾与考察,认为在文学观上一直存在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在批评观上历来存在教条论与内在论的对立。托多罗夫认为这两组对立的方面都有着各自的局限。1981年出版的《米哈伊尔·巴赫金:对话原则》(Mikhail Bakhtine:le principe dialogique)一书标志着托多罗夫研究活动的转折点,他从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思想中得到丰富的启示,修正了自己对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看法。继而托多罗夫在《批评之批评》(Critique de la critique,1984 )中反思了自己的批评道路,提出并实践了对话批评。此外,在这一阶段的前期,托多罗夫还对话语的种类进行过研究,《话语的种类》(Les genres du discours,1978)一书收集了1971—1977年间的有关论文。
第三阶段:1981年至今,托多罗夫的研究活动突破了文学范畴,扩展到文化人类学领域。托多罗夫一方面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意识到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研究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另一方面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面临的危机促使他将目光投向文学以外的世界,关注更广泛的文化问题。普遍性和相对性、文化的多样性与同一性、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是他思考的中心,他的研究活动因而扩展到了文化人类学领域。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征服美洲》(La conquête de L'Am érique,1982)和《我们与他人》(Nous et les autres,1989)。
本文主要观照的是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托多罗夫的理论建树和批评实践,尤其是尚未引起我国学界重视的他的思想演变。
叙事语法与体裁理论
当我们谈到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时,托多罗夫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他从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两方面为这一学术流派作出了重要贡献。
托多罗夫的《诗学》是《何谓结构主义?》丛书中的一部,托多罗夫以其简练清晰的文笔系统地阐述了结构主义诗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托多罗夫而言,建立新的诗学意味着对文学的功能和意义的再认识。他将历史上对文学的功能与意义的认识归结为两种:“第一种是将文学作品本身视为认识的对象;第二种则认为每一部个别作品都是某种抽象结构的具体表现。”〔4 〕他称第一种态度为“阐释”(interprétation),即“道出被研究作品的含义”,〔5〕第二种态度则从属于“科学”(science),即“其目标不再是描述某一个别作品, 明确一部作品的意义,而在于建立起一些普遍规律,而个别作品即是这种普遍规律的产物。”〔6〕这些普遍规律,因不同的批评家而异, 或是哲学的,或是社会学的,或是心理学的等等。托多罗夫认为,新的诗学即结构主义诗学应该打破文学研究领域中阐释与科学的二元对立。诗学不同于对个别作品意义的解释,应该寻求凌驾于具体作品之上的普遍规律,诗学也不同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科学方法,不应在文学之外而应在文学内部去寻求这些普遍规律。因此诗学对待文学的态度既是“抽象的”,又是“内在的”。也就是说“任何作品都只被看作某种普遍的、抽象的结构的具体表现,它只是这种结构可能实现的多种形式之一。正因为此,诗学所关注的不是真实的文学,而是可能的文学,换言之:使一部文学作品具有其特殊性的那种抽象特征,即文学性。”〔7 〕总之,诗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起关于文学话语的结构及其运作的理论。
从托多罗夫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结构主义诗学的要义在于一方面化繁为简,试图超越作品的具体内容而发现普遍结构对个别作品的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力图避免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批评方法游离于作品之外的缺陷。
结构主义诗学虽然是作为一般的批评原则提出来的,但是它的基本方法却决定了它必然将叙事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于叙事作品的研究又必然侧重于叙事的结构研究。托多罗夫于1969年出版的《〈十日谈〉语法》一书,就是一个结构主义者试图将纷繁复杂的叙事文本简化为容易把握的结构和规范的尝试。托多罗夫为自己规定的研究课题是总结“叙事语法”。所谓“叙事语法”就是潜藏在一切叙事作品之中的共性,即普遍而抽象的结构。
托多罗夫首先辨析了叙事的三个方面:语义、句法和词语。语义指的是叙事所表达或隐含的具体内容,即作品的“主题”;句法指的是叙事单位的组合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词语指的是构成一个叙事的具体的句子。当然,叙事的这三个方面在作品中是交织在一起的,只是在对作品进行分析时,才将它们区别对待。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不同时期,这三个方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所有重视阐释的流派都将语义放在第一位,近代的文体学研究则将注意力放在词语方面,相比之下,句法则一直不被重视。直到本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者开始注意到句法研究。《〈十日谈〉语法》的研究重心正是叙事的句法方面。
托多罗夫将叙事话语的句法分析建立在两个基本概念之上:分句(proposition)和序列(séquence)。分句是最基本的叙事单位,它意味着一个不可再分的行为,如“X是一位少女”,“Y抢走X”。 一个分句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成分,即行为者(X,Y)和谓语(“是一位少女”、“抢走”)。一连串分句组成一个序列,它意味着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故事。以《十日谈》中的一个故事为例:佩罗涅拉趁丈夫不在家时与情人相会。一天丈夫提前回家,佩罗涅拉将情人藏在一只大桶里,告诉丈夫有人要买桶,正在查看。丈夫信以为真,很高兴有生意可做,便去打扫这只桶。这时佩罗涅拉以头和手臂堵住桶口,继续与情人调情。
托多罗夫分别用X、Y代表行为者佩罗涅拉和丈夫,将人物和行为看作动词,上面的故事就可以转换成这样一连串分句:X犯下过错,Y应当惩罚X,但X采用伪装的手段逃避了惩罚,继续原来的行为。托多罗夫指出其中的主要动词只有三个:犯过错、惩罚和伪装,《十日谈》中有近一半的故事符合这个模式。
根据托多罗夫对《十日谈》一书的分析,一个故事至少包含一个序列,但通常包含多个序列,这些序列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构成叙事。托多罗夫将序列的组织方式分为三类:嵌入式,即整个序列在另一个序列中充当分句的作用;连接式,即几个序列以先后顺序出现;交替式,即两个序列中的分句在叙述中交替出现。
不难看出,托多罗夫采用的方法受到了俄国民间故事形态学研究者普洛普以及法国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和巴尔特的启发,不过,他的方法更偏重于语言形式。他先将每个故事简化成纯粹的句法结构后再作分析,换言之,也就是将每个作品看成一种扩充后的句子结构。这种分析方法是否合理呢?托多罗夫认为,如果说他在《〈十日谈〉语法》一书中建立起来的叙事语法不尽合理的话,叙事语法这一构想本身却是不应该受到怀疑的,因为这一构想建立在语言与叙事的深刻统一性之上:“如果懂得作品中的人物是一个名词,动作是一个动词,就能更好地理解叙事。为了更好地理解名词和动词,则需要联想到它们在叙事中担任的角色。归根结底,只有学会去思考语言最本质的表现形式即文学时,才能理解语言。反之亦然:将一个名词和一个动词组合到一起,就是迈向叙事的第一步。事实上,作家让我们读到的不过是言语而已。”〔8〕
托多罗夫借助于语言学术语和语法分析模式建立起来的这种叙事语法,的确向我们清楚地展示出了作品最基本的叙述结构。与以前那些只局限于诠释作品意义或进行修辞分析的批评方法相比,叙事语法更注重作品的系统性,即作品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观察角度无疑为文学研究引入了新的内容。此外,叙事语法力图在复杂多样的叙事话语中寻求普遍性的规律,这对于我们把握叙事的本质以及认识个别作品在文学系统中的地位是不无裨益的。但是,这种高度综合概括的批评方法同时有着严重的缺陷。首先,叙事语法剥离了文学作品的具体内容,将作品简化为一个纯粹的语法框架,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对构成文学作品审美价值极为重要的细节部分,从而妨碍了对作品的正确审美估价。其次,叙事语法将作品的结构看作一个自足的体系,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不考虑其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这样做不但忽视了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而且排斥了文学作品情感、想象诸层面上的意义,使任何价值判断成为多余。
文学作品不仅有结构,还有内容,对作品的系统性和普遍性的强调不应以放弃作品的具体内容为代价,叙事语法乃至整个结构主义批评在这一点上都有失偏颇。单纯追求文学的“内在性”和“抽象性”,无异于将文学看作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必然远离文学中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和情感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等于抹杀了文学的魅力。因此,避开文学作品具体内容的批评难免枯燥乏味,其诞生时具有的生命力终将在单调的批评模式的多次重复中渐渐丧失。
在对叙事作品作了语法结构的“还原”之后,托多罗夫把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于体裁理论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就是《幻想作品导论》。体裁意味着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一类文学作品的总和,作为强调文学作品的普遍性和系统性的结构主义者,托多罗夫对体裁问题感兴趣是很自然的。在这部著作中,托多罗夫继续沿用了他在《诗学》和《〈十日谈〉语法》中对叙事作品的三个方面——语义、词语和句法的划分。他对幻想作品的这三个方面一一作了分析。与《〈十日谈〉语法》一书不同的是,托多罗夫的研究重点不再是作品的句法方面,而是语义方面。
我们前面提到过,语义指的是作品的主题。提起主题,人们往往联想到对作品意义的阐释,然而托多罗夫声明,他的主题研究与阐释无关。他指出“结构”和“意义”分别是两种不同的活动即“诗学”和“阐释”的目的:“任何作品都具有一个结构,它由文学话语中各种不同类型的因素交织而成;这个结构同时也是意义的所在之地。”〔9 〕托多罗夫认为诗学的任务只限于建立起这种结构而无需顾及作品的意义。在他看来,体裁体现了某种结构,是一些文学特征的总括,因此在体裁研究中,应该采取的是诗学而非阐释的态度。他进一步指出,在对文学作品语义方面的研究中,如同在词语方面和句法方面的研究中一样,意义与形式是可以分离的:“我们并没有试图去阐释主题,而只是考察它们在作品中的出现。”〔10〕可见,托多罗夫的主题研究并没有回到传统的阐释批评上,他对作品语义方面的分析是站在结构主义的立场上进行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幻想作品导论》中,托多罗夫在坚持结构主义分析模式的同时,他的思想方法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幻想作品的定义上。他指出:“幻想(le fantastique)存在于悬而未决之中,一旦人们选择了这样或那样的答案,就不再是幻想作品,而是相近的另一种体裁——志怪(l'étrange )或神话(lemerve-illeux)了。幻想,是一个了解自然规律的人,面对一个超自然事件时感到的犹豫不定。”〔11〕究竟是谁在犹豫不定呢?托多罗夫进一步解释道,在大部分幻想作品中,是作品中的人物感到了犹豫,也有少数作品,其中的人物并未产生犹豫。但无论哪种情况,幻想作品都要求读者加入到人物的世界中去,要让读者也感到模棱两可,“读者的犹豫是幻想作品的首要条件。”〔12〕在一些非幻想作品中也存在着超自然事件,但它们并不能引起读者的疑问,例如寓言故事中动物说话以及诗歌中的某些修辞手法。“幻想作品不但意味着要有一个离奇事件以引起读者和作品主人公的犹豫,它还意味着一种阅读方式。”〔13〕
托多罗夫于是将幻想作品的特点归纳如下:“幻想作品包含三个条件。首先,作品要求读者将人物的世界看作一个真实的世界,要求读者在解释发生的事件时在合乎自然和超自然的解释之间产生犹豫。其次,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要产生同样的犹豫;这样,读者的角色由一个人物担当起来,犹豫因此在作品中得以表现并从而成为作品的主题之一。最后,读者的阅读方式至关重要:读者不能对作品进行‘寓言式’或‘诗意’的理解。这三个条件具有不同的重要性:第一和第三个条件是构成这一体裁的真正条件;第二个条件可以不满足。但大多数幻想作品都具备所有这三个条件。”〔14〕
这段话很值得注意。如果说在《〈十日谈〉语法》中,托多罗夫还完全在作品的句法结构中寻找叙事话语的基本特征,那么在《幻想作品导论》中,他的目光已不再囿于作品本身,转而在读者的体验和阅读方式中去寻找文学体裁的特征了。从注重作品的内在结构到在读者的活动中去寻找理论基础,托多罗夫已经在有意无意之间打破了文学话语的封闭系统,这种研究方法如果说不是与结构主义一贯强调的“内在性”大相径庭,起码也是有所偏离了。
历史考察和对话批评
从70年代初开始,托多罗夫的研究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他对西方历史上有关象征与阐释的理论进行了历史考察,其结果是《象征的理论》(1977)和《象征与阐释》(1978)两本书的问世。
象征意味着某种符号系统及其解释方法。历史上对符号问题的思考渗透到了逻辑学、语言学、经文阐释学、修辞学、美学及诗学等多门学科。在《象征的理论》一书中,托多罗夫将研究重点放在与语言符号系统密切相关的理论上。他回顾了亚里士多德和18世纪末德国浪漫派的美学思想,古代修辞学家和弗洛伊德的修辞学理论,以及索绪尔的语言学和雅各布森的诗学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关语言象征系统的不同理论实质上反映了两种文学观——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对立。
古典主义文学观以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为代表,认为现实世界是艺术的蓝本,诗是用语言来再现现实的艺术,正如绘画是用形象来再现现实的艺术一样。因此,语言只是诗的工具,而非目的,文学作品的目的是外在的。以悲剧为例,其目的在于引起观众对人物所受灾难的怜悯和恐惧,从而净化情感,有利于心理健康。“摹仿说”强调的是文学的认识作用和社会功能,这一理论在西方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古希腊到18世纪末一直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学观。
然而,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美学的兴起使形势发生了逆转。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提出了相反的理论主张,他们认为艺术作品如同客观世界一样具有自主性,作家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写道:
真正的艺术品,一首好诗,本身就是一件完整的东西,是为自己而存在的,它的价值在于其自身各部分的协调关系中。……那些读过《荷马史诗》之后还会问:“《伊利昂纪》意味着什么?《奥德修纪》意味着什么?”的人,并没有感受到这些诗篇的美妙。——一首诗所有的含义都在其自身……〔15〕
诺瓦利斯也区分了语言的两种不同功能:实用语言是作为工具的语言,在自身之外获得价值;文学语言是自足的语言,是为表达而表达。
这样,作品与其外部事物之间的关系遭到了贬斥,而其内部的结构、情节和形象则受到了关注。托多罗夫将这种新的文学观称为浪漫主义文学观,它很快取代了古典主义文学观而成为现代的主导文学观念。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托多罗夫使用的“浪漫主义”一词并非专指19世纪的文学运动。托多罗夫摒弃了这个词通常所包含的对非理性的推崇和艺术家对表现绝对的向往,他说:“我所谈到的是我认为堪称这次运动理想模式的浪漫主义而不是作为历史现象的浪漫主义。”〔16〕在托多罗夫那里,“浪漫主义”一词主要是指与古典主义文学观相对立的文学内在性观念,他之所以坚持使用这一词汇,还由于他将这种现代文学观的建立归功于早期的一个浪漫主义派别,即以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谢林等人为首的耶拿派。
托多罗夫通过对象征理论的历史考察,从语言这个符号系统的功能层面上肯定了所谓“浪漫主义”亦即内在性的文学观,这对于理解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批评的观念嬗变是很有意义的。在完成了这个历史考察之后,托多罗夫又开始思索从符号学的角度说显得更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语言信息传递与信码结构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托多罗夫仍旧采用历史考察的方法。他在《象征与阐释》一书中,探讨了西方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两种阐释观——以教义阐释学为代表的目的论阐释(interpr étationfinaliste )和以语文学为代表的操作论阐释(interprétation opérationnelle)——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西方的文学批评始于对《圣经》及教会圣师们著作的阐释。从公元初年直到17世纪,占统治地位的阐释原则是:阐释活动以两种意义的划分为前景,即《圣经》经文的字面意义和《圣经》所具有的神授的意义,后者即所谓基督教教义。这两种意义之间经常存在着差距,阐释的目的就是消除两种意义间的距离,使其合二为一。
古罗马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更是明确规定了阐释的对象:要对所有的转义进行阐释。何谓转义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辨别一个表述是本意还是转义的方法。简而言之,在《圣经》中所有取其字面意义既不能与善行美德又不能与信仰的真理相符的表述,应当被视为转义的。〔17〕
圣·奥古斯丁还进一步列举了转义的几种具体情形,在此不赘。总之,教义批评的宗旨是通过阐释转义的表述,使《圣经》的文字与基督教教义相吻合,以此来证明教义的正确性。因此,在教义阐释家的眼中,文字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使其与预先确定的真理,即基督教教义相符,因此,托多罗夫认为不妨称之为教条论批评。
同样针对《圣经》的阐释方法,斯宾诺莎在其著作《神学政治论》中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他认为阐释的目的在于寻找《圣经》中文字本身的意义而不是其中所包含的真理,阐释活动应杜绝任何先入之见,并且只能依靠语言的运用和《圣经》中的内在逻辑去确定一段话语的真实意义。为此,斯宾诺莎规定了阐释的三个具体方面:语法、结构和历史。日后的语文学就是在斯宾诺莎所倡导的这种“科学的”阐释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对象本身受到了重视,此外方法论在阐释活动中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真理问题则遭到了冷落。托多罗夫认为可以将这种新的批评观称作内在论批评观。
在客观描述了历史上两种对立的阐释观之后,托多罗夫进一步分析了内在论阐释观取代教条论阐释观的历史原因。托多罗夫指出,语文学的某些阐释方法其实早在古代就被亚历山大学派的教义阐释家们使用过,只是直到近代才在斯宾诺莎手中形成理论体系,并在与教条论的斗争中赢得胜利。那么是什么历史因素使语文学恰好在这个时代推翻了教义阐释学的统治地位呢?托多罗夫认为,教条论阐释诞生于一个绝对真理及其占有者统治一切的时代,而斯宾诺莎提出的无需参照绝对价值体系去寻找作品真实意义的阐释方法实际上意味着争取人的平等和自由,两种阐释观地位的逆转正好发生在欧洲历史上一个特定的时期:封建基督教社会让位于宣称个人平等的资产阶级社会,“语文学诞生于欧洲最早的资产阶级城市之一的阿姆斯特丹并非偶然。只有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宽松环境中,斯宾诺莎才得以形成其理论纲领,而在此之前,有关的实践活动只能以隐秘的方式进行。”〔18〕
显然,托多罗夫认识到不同的社会要求有不同的批评观与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在他写作《象征与阐释》的年代,他为自己选择了一种什么样的批评观呢?托多罗夫认为自己处于一个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共存的时代,其历史命运迫使他选择一种“双重外在”的立场,即不从属于受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影响的批评观。“这不是一种优势,也并非必然就是一种不幸,这恰好是我们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既承认对立的双方都有理由,而又不知在其中作出选择:似乎我们文明的本质就是在选择时迟疑不决,试图去理解一切却无所作为。”〔19〕
难道托多罗夫从历史考察中得出的结论就是“无所作为”吗?作为一个不倦探索的批评家,他并没有停留在“双重外在”的立场上,如何建立起超越上述两种二分法的文学观和批评观才是他真正的历史命运。在托多罗夫新的文学观和批评观的形成过程中,巴赫金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在1981年出版的《米哈伊尔·巴赫金:对话原则》一书中,托多罗夫将巴赫金誉为“苏联人文科学领域里最重要的思想家和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理论家”,〔20〕其钦佩和敬慕之情溢于言表。托多罗夫加在巴赫金头上的这两个最高级形容词也许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成份,但不也表明了后者给予他的丰富启示和深刻影响吗?
巴赫金认为人文科学应采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二者的研究对象具有不同的性质:在人文科学中,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口头或书面的文本,即他人思想或经验的表述,因此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更确切地说是作为文本制造者的人:
人文科学是关于人的特性的科学,其对象不是一个没有声音的物或一种自然现象。人的特性在于他总是在表达(说话),也就是说在制造文本(也许是潜在的)。如果在文本之外去研究人,就不再是人文科学(如解剖学和人体生理学等)。〔21〕
言下之意,在人文科学中存在着两个说话的主体:研究者和被研究者。
自然科学是一种独白式的知识:人的理智观察一个事物,然后谈论它。这里只有一个主体,认识(观察)和说话(陈述)的主体,他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事物。但在观察和研究主体的时候,我们不能将他视为一个事物,因为如果没有声音,他就不再成其为主体:因此,只能以“对话”的方式去认识主体。〔22〕
我们将看到,在巴赫金的思想中,“对话”一词的含义是广泛的。它不仅意味着人文科学领域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同样还意味着艺术创作活动中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的关系。在巴赫金看来,这种“对话原则”在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完善的体现。
在他(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人物的声音就像在一本普通类型的小说中作者本人而非人物的声音那样表达出来。人物有关自己和世界的议论与平常一位作者所发的议论具有相同的分量;它不是作为人物性格的一方面用来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但它也并非作者的传声筒。它在作品结构中有着特殊的独立性,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作者所发议论的应对,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作者以及享有同等地位的其他人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23〕
巴赫金因此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称为“复调小说”,作家与人物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进行思想交流。作家与人物不再是“我——他”,而是“我——你”关系。巴赫金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中得到了如下的启示:
人生的本质是对话性的。生活就意味着参与对话,提问,倾听,回答,赞同等等。〔24〕
巴赫金坚信人只能存在于对话之中,人际关系是构成人的要素,只有将人放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才能获得关于人的存在的正确认识。巴赫金文学研究的成果最终突破了文学范围,导向了哲学人类学。
巴赫金对托多罗夫的影响是深刻和多方面的,不仅他的“对话原则”成为日后托多罗夫新的批评主张的思想基础,而且他自己的研究道路让托多罗夫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文学理论家还应思考文学以外的问题。正如巴赫金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使被研究者最终成为研究者的精神导师一样,托多罗夫也在对巴赫金的研究中找到了通向新的文学观和批评观的道路。
1984年出版的《批评之批评》是托多罗夫自《象征的理论》和《象征与阐释》而开始的历史考察的最后一部分,但这本书并不是前面两部著作在历时背景上的简单延续,托多罗夫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分析方法在这本书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托多罗夫声明写作此书的目的是:
首先,我想考察一下人们对20世纪文学与批评的看法;同时,试图弄清什么样的文学观及文学批评观是近乎正确的。
另外,我打算分析本世纪对文学的思考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意识形态潮流;同时,试图弄清哪一种意识形态立场更有道理。〔25〕
为此,托多罗夫选取了20世纪中期(约1920—1980年前后)十几位不同批评流派和思想倾向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甚至历史学家作为研究对象。他选择这些批评家并不完全依据他们享有的较高声誉,还因为所有这些作者都曾对他本人的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们是:俄国形式主义者,德国作家德布林和布莱希特,法国的萨特、布朗肖和巴尔特,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赖,英国批评家伊昂·瓦特和法国历史学家兼批评家保尔·贝尼舒。上述批评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18世纪末德国浪漫派内在论文学观的影响,同时他们的思想中又都包含着否定和超越这一观念的成份。正在寻求新的文学观和批评观的托多罗夫说道:“我所感兴趣的是所有能让人超越已具雏形的二分法(内在论、外在论)的东西。确切地说,在我分析的作者中,我将探求对‘浪漫主义’美学与思想提出质疑并且也不为此就回到‘古典主义’教条中去的那些思想观点。”〔26〕托多罗夫一方面对这些作者的思想进行述评,另一方面也坦率地陈述了自己思想的转变,因此,这本书不仅从一个侧面回顾了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批评思想的演变,也是托多罗夫对自己批评道路的反思。
托多罗夫的反思是从对他的结构诗学理论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俄国形式主义开始的。
诺瓦利斯区分过语言的两种用途:作为工具的语言和作为诗的语言。俄国形式主义者对语言也作了类似的划分,他们认为实用语言是作为传达思想的手段被使用的,其价值在自身之外,在人际交流之中。而诗的语言拒绝任何外在意义,其全部价值都存在于自身。这种划分的目的在于从文学材料的特殊性中寻求一种超越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永恒的“文学性”。然而他们自己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种“文学性”其实是不存在的,如形式主义者蒂尼亚诺夫在1924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
要给文学下一个一成不变的定义越来越难了,不论哪个我们的同时代人都能指给我们看什么是文学现象……一生中曾见过一次、两次或更多次文学革命的长辈会告诉我们:从前,某一事件不是文学现象,而现在则成了文学现象,反之亦然。〔27〕
更加发人深省的是,“政治压迫在20年代末就降临到这一流派头上,所有他们讨论过的问题在苏联其后的几十年中都成了禁忌。形式主义运动这一猝然结局给我们留下的唯一积极教训是:显而易见,文学和批评都不能在自身找到它们的目的;如果能找到的话,国家就不会想到要来干涉它了。”〔28〕从托多罗夫的这段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思考已经从它的理论构想转向它的历史命运,注意到了理论(文本)的命运与它所处的历史“语境”的关系。
在萨特那里,不再是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的对立,而是诗与散文的对立:
诗人乃是一些拒绝使用语言的人。……他完全摆脱了作为使用工具的语言,最终选择了诗的态度,即把词语看作物,而不是符号。〔29〕
与诗人相反,散文家的任务则是揭示世界与人生。然而萨特又说:“尽管文学是文学,道德是道德,在美学必需的深处,我们也感到了道德的必需。”〔30〕
罗兰·巴尔特曾经将他的写作比拟为“语言的飞翔”,将他与周围事物的关系比作一间“回音室”——不能很好地再现思想,但能追踪词语。巴尔特的这两个比喻,究其根本,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他对思想本身并不关心,而更看重其表述形式;其次,他不对自己的话语承担责任。然而,托多罗夫注意到巴尔特晚年的人道主义倾向却促使他写下了这样的话:
渐渐地我产生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愿望:我愿我收到的作品“容易阅读”,我愿自己的创作亦“容易阅读”……。这使我产生了一个古怪的想法(由于人道而显得古怪):“人们永远想象不出创作过程中倾注了人类多少的爱(对他人、对读者)。”〔31〕
可见,人道主义最终战胜了“语言的飞翔”。
上述理论家和批评家思想中超越浪漫主义的成份给托多罗夫以深刻的触动是不足为怪的。托多罗夫身为结构主义者,和他们有着同样的“内在论”倾向,故而他们在实行内在论批评的同时表现出的动摇、困惑、甚至带有批评意义的反思都不能不促使托多罗夫对“内在论”重新进行一种价值的和历史的思考。更值得注意的是,使用传统批评方法的保尔·贝尼舒对托多罗夫同样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批评之批评》中,专门论及贝尼舒的一章题为《作为事实与价值的文学》,在这一章里,托多罗夫以与贝尼舒相互提出和解答问题的方法同这位坚持传统批评的学者进行了名副其实的对话。
贝尼舒反对把文学降格为纯美学观照的对象,他明确指出所有的文学都有艺术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在《批评之批评》一书中托多罗夫经常使用的“意识形态”一词并非指为某种政治或物质利益服务的思想,而是指“社会成员共有的一种思想、信仰和价值体系,它与意识、科学或真理等并不相悖。”〔32〕)贝尼舒认为抽象的思想概念在具体的文学中总是以形象表现出来的,因此在分析文学作品时,他注重揭示构成作品的材料所包含的意义,文学不应当仅仅被看作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作品内容必然包含着某种价值体系,对纯粹实体的寻求是徒劳无益的。在托多罗夫看来,贝尼舒的批评著作成功的秘密正在于“给予他的分析以活力的对真理的探求。”〔33〕
在对历史的考察和对自己批评道路的反思之中,托多罗夫的文学观发生了巨大转变,他终于认识到文学不仅是语言的构造,还包含着思想内容,文学与价值有着必然联系;文学与社会和时代的意识形态紧密相关,“作品中的历史构想与结构构想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容易分辨。我过去一直以为是中性的方法及(我的)纯描述概念的东西现在却成了某种明确的历史选择的结果(这些结果本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另外这种选择也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对此,我总是没有接受的准备——反映出来。”〔34〕
托多罗夫的自白不禁令我们联想到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施莱格尔的一段话:
诗是共和的言辞,这种言辞的法则和目的都在其自身,其中所有的成份都像自由公民一样,为了达成一致而有畅所欲言的权利。
当他这样表述其文学内在性的观念时,难道没有透露出一点政治的气息吗?
在剖析了自己一贯坚持的批评方法之后,托多罗夫宣称:“文学是与人类生存有关的、通向真理和道德的话语。”〔35〕
文学观的转变必然导致批评观的转变。托多罗夫认为“批评探索的真理与文学所探索的真理是有共同属性的,即是事物的而不是事实的真理,揭示出来的而不是附会上去的真理。”〔36〕批评是对真理的探求,而内在论批评和教条论批评都难当此任。
教条论批评家无视作品的真正意义,他们武断地解释作品以达到用作品去附会他们预先确定的教条的目的,作家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失去了说话的权利。这种态度不是探索真理,而是自以为真理在握。内在论批评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只满足于确定文本的意义或描述作品的结构及形式功能,读者听不到批评家的声音。批评家放弃了价值判断,而放弃价值判断无异于放弃对真理的探求。
因此,托多罗夫提出“批评是对话,是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汇合”。〔37〕也就是说,不能将被批评的作品看作起“元语言”作用的物,而应看成是作为主体的作家的话语,被批评的作家不是“他”,而是“你”,是与批评家一起探讨人类价值问题的对话者。
至此,我们看到,从结构主义批评的主将到“对话批评”的倡导者,托多罗夫的批评思想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我们同样看到,从拒绝对文学作品进行价值判断,只关注文学话语的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到在文学和批评中探求真理,托多罗夫的思想变化并不是朝夕之功,而是一位批评家多年辛勤探索的结果。经过对文学观和批评观漫长的发展历史的考察和对自己思想历程的反思,托多罗夫不再固守结构主义立场,公开宣称文学和批评与真理和道德紧密相关,这不仅需要长期的思索,更需要真诚和勇气。
当然,对话批评在实践中是否真正可行还有待于更多的批评家通过实践来检验。当托多罗夫宣称“我所向往的那种真理只能通过对话去探索,反之,在巴赫金那儿我们已经看到,为了进行对话,应该把真理当作一种前景、一个调节原则”〔38〕时,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与其说托多罗夫在倡导一种新的批评模式,毋宁说他在告诫我们:我们无法占有真理,却不能放弃对真理的探索。
从结构主义诗学到对话批评,托多罗夫思想的演变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演变不仅体现在其研究领域的扩展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其思想方法的深刻变化上。对照前后不同时期,托多罗夫思想方法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托多罗夫的研究兴趣从建立文本的抽象结构转向了探究作者的思想。在早期结构批评阶段,托多罗夫对待被分析作品的态度是避开作品的具体内容而仅仅关注文本的抽象结构。从历史考察阶段起,托多罗夫的注意力渐渐转向对作者思想意图的理解。
第二,托多罗夫在研究方法上不再拘泥于某种单一的分析模式。这一变化与上述第一点变化密切相关。与从众多作品中抽取出来的话语普遍而抽象的结构相比,这些作品中包含的作者的思想显然更具复杂多样性,既然托多罗夫的研究重点从前者转向了后者,那么,类似以前“叙事语法”那样的固定的分析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研究工作的要求。在其后期的著作中托多罗夫不断强调他在提倡并实践着“对话”,从他本人的“对话”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对话”实际上就是两条原则:第一,让被研究的作者享有充分的发言权;其次,要求研究者表明自己的态度。至于“对话”具体应该怎样进行,托多罗夫从来没有规定一套固定的程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托多罗夫倡导“对话”的真正目的远非企图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模式,而在于倡导一种超越一切刻板的、封闭的思想体系的思想方法。
第三,托多罗夫抛弃了文学批评中内容与形式的对立,从而转向反对一切机械的二分法。在其研究活动的第一阶段,托多罗夫强调文学的内在性和抽象性,即只描述文学话语的结构及其运作方式而不作任何价值判断。通过历史考察,托多罗夫认识到了教条论批评与内在论批评各自的缺陷,指出作品既是文学的结构,也是对真理的探索,因此他提出“对话批评”主张以超越文学批评领域中教条论与内在论这一简单的二分法。托多罗夫反对一切机械的二分法的精神实质在于以探索真理来取代占有真理与放弃真理的简单对立。
托多罗夫在批评思想和文化观上获得的这些新的认识本身也许并无新颖之处,但这位批评家思想发展的历程却是发人深省的:从积极投身于结构主义的纯形式批评到承认文学不是唯结构的,它还包含观念和历史的成份;从强调文学作品的内在性,到突破狭隘的文本研究甚至文学范畴本身,托多罗夫表现出了一位批评家不断超越自我的勇气和追求真理的热忱。我们无法占有真理,却不能放弃对真理的追求,这是托多罗夫30多年辛勤思考和探索得出的结论,也是对他本人走过的发展道路的最好注脚。
注释:
〔1〕此书有蔡鸿滨先生中译本,题为《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此书收在弗朗索瓦·瓦尔(Francis Whal )主编的《何谓结构主义?》丛书中。
〔3〕“对话批评”是托多罗夫在《批评之批评》(Critique delacritique)一书中提出的理论主张。该书出版于1984年,但其大部分内容是在1981年之前写成的,故应将此书归入托多罗夫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
〔4〕〔5〕〔6〕〔7〕Tzvetan Todorov,Poétique,Seuil,1968,p.15,p.16,p.18,p.19.
〔8 〕Tzvetan Todorov,Grammaire du Décaméron,La Haye,Mouton,1969,p.84.
〔9〕〔10〕〔11〕〔12〕〔13〕〔14〕Tzvetan Todorov,Introduction à la litterature fantastique.Seuil,1970,p.149,p.148,p.29,p.36,p.37,p.37.
〔15〕Tzvetan Todorov,Théories du symbole,Seuil,1977,p.195.
〔16〕〔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Tzvetan Todorov,Critiquede lacritique,Seuil,1984,p.15,p.2,p.14,p.35,p.37,p.55,p.57,p.81,p.12,p.143,p.182,p.188,p.190,p.185,p.187.本论文所引用的此书中的文字,除个别字句略作改动外,均采用王东亮、王晨阳所译《批评的批评》(三联书店,1988年)中的译文。
〔17〕〔18〕〔19〕Tzvetan Todorov,Symbolisme et interprétation,Seuil,1978,p.92,p.159,p.164.
〔20〕〔21〕〔22〕〔23〕〔24〕Tzvetan Todorov,Mikhail Bakhtine,le principe dialogique,Seuil,1981,p.7,pp.31—32,pp.33—34,pp.161—162,p.149.
标签:结构主义论文; 十日谈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艺术论文; 作品分析论文; 人物分析论文; 巴赫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