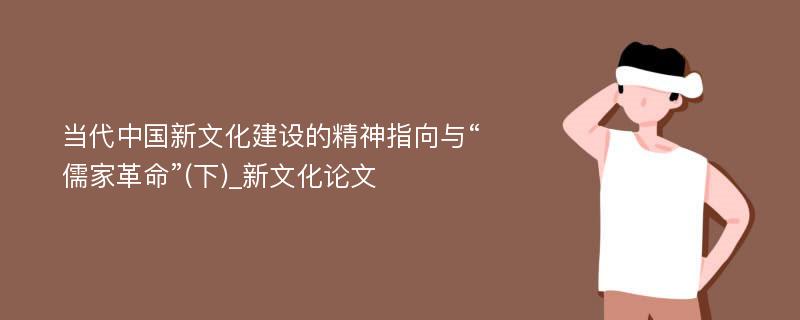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新文化建设的精神指向与“儒学革命”(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新文化论文,之二论文,中国当代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没有超越“时空”的文化形态
“儒学回归论”在理论的设定上陷入了根本性的误区,即他们事实上认定,在人类历史无限发展的时空之中,会存在一种永恒的精神力量,成为一切时代的主体性思想。在中国,他们认为,这种“永恒的精神力量”,这种可以“成为一切时代的主体性思想”,就是距今已经有2400年左右的、由孔子创立的“儒学”。
列宁曾经告诉我们,历史常常会跟我们开玩笑,当我们自以为走进了甲房间的时候,结果,却发现呆在了乙房间。当前我国文化运动中的以儒学为中心的“古典回归”,恰似“无神论者做弥撒”。从民族文化的最根本处来说,这是我国新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非常壮丽的悲剧。
要回答这个问题,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其实,都不是很困难的。现在,被人们谈论的很多的,作为“儒学回归”的国际实例,便是基督教与欧美社会的精神关系,Max Weber (玛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观念,在我国知识界的相当层面上,成为不易之论。然而,人们毕竟是误解了基督教的历史。简言之,就基督教的历史说,从耶稣出生至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五百年可以作为“早期基督教时期”;此后,基督教开始在欧洲传播,逐步地改造了早期的教义,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 可以称为“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文明时期”;16世纪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发动宗教改革运动,成为迎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到来的信号;继而,Jean Calvin (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式的长老制教会;继而在英国和北欧各国,世俗君主也摆脱教皇控制,把教会置于本国君主的控制之下。以此为标志,基督教内部对原有教义的革命不断进行,陆续产生了表达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脱离罗马公教的各种新教宗派。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宗教改革”的旗帜下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封建的社会政治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它造就了在原有的宗教旗帜下的符合其利益意志的新教。欧洲基督教的改革运动,是与欧洲工业文明的发展,与资产阶级夺取政治的权利,几乎是同时代发展的。假如没有16世纪以来对基督教的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造,基督教怎么可能成为当代欧美社会思想文化的主体形态之一呢?实际上,Max Weber (玛克斯·韦伯)所指的是“基督教新教”,而不是“基督教”。这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文化形态——“基督教新教”一方面是对“基督教”的继承,一方面是对“基督教”进行了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后形成的“新宗教”。
实际上,思想文化史的事实昭示我们,人类在自身的精神形态的发展中,至今还没有创造出一种“随着时空的发展,而能永恒不变的精神形态”。
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是人类在工业社会时代所创立的关于揭示社会本质,并预示人类社会未来的最精粹的思想体系——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预示人类未来社会时,也具有他们当时实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非常鲜明与深刻的烙印。指出这一点,对认识文化的“时代性”是十分有益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它运用于中国社会实际的时候,总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异而变异,于是便有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发展的轨迹。
马克思主义发展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够想象,孔子,以及由孔子等所创立的儒学,会成为一种永恒的精神形态?怎么能够想象一个公元前四五世纪左右中国农耕时代前期的一种思想认识,会成为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时代,即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的主体和核心呢?
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遗产?
我们说,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根”,存在于当代中国人民从事的伟大的现代化的实践之中,这绝不是要苛求它的形成和发达离开中国文化发展的大道而孤独运行。事实上,任何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集团、阶层和阶级,对它自身民族的历史与传统,都不可能采取漠然的态度,他们总是依据自身的利益,或加摘取,或加剔除。所谓“全盘继承”和“全盘否定”,都只是文化思想学派的口号,而不可能是文化运动本身的实际。许多人都认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时代是对中国文化遗产“全盘否定”的时代。但是,这个说法显然是情感形态的,与实际不合。因为当时以“四人帮”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在最广泛的民众层面上发动的例如所谓“评法批儒”,就是对于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的一种处置办法。有人说,中国文化遗产经他们这一折腾,便被彻底破坏了,所以还是可以说是“全盘否定”,但是,从学理上说,这是一种价值性判断,与实际的文化运动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事情。我们的任务,是应该揭示并使国民认清他们在利用文化遗产与历史传统的背后所隐藏的凶恶的政治企图,以及处置文化遗产与历史传统的伪科学性质。
既然“全盘继承”和“全盘否定”,都只是文化思想学派的口号,而不可能是文化运动本身的实际,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和发达,当然既不会也不能离开我们悠久丰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我们和“古典回归”论者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继承文化遗产,——甚至本文著者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海内外从事中国文化遗产的收集和整理,并致力于揭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所以争论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分歧在于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第一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根”,究竟在于“现实”,还是在于“回归”?究竟是立足于“创造”,还是立足于“弘扬”?(有人说,不要这么对立么,创造中有弘扬,弘扬中有创造。这确实不失为中庸的思维,但生活的辩证法并不中庸,它客观上就存在着“根”和“流”的主次之分——著者)第二是,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继承文化遗产?我们要在文化遗产中继承什么?——即我们要把文化遗产的什么内容交给今天的中国民众,以养成他们科学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中国文化遗产究竟有没有“真善美”与“假丑恶”之分?我们在运用文化遗产时,究竟要不要以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精神指向”为导标?
本来,“弘扬”文化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激越人心的口号。但是,由于我们在什么是“文化的民族精神”,以及究竟怎样“弘扬”这样的关键上,在学理方面似乎未能理顺,于是,在“继承”的旗帜下,历史上最丑恶的成分竟光天化日泛起于社会主义生活之中。——行文至此,著者收到1998年2月12日首都一报刊, 上面竟然有《把玩“三寸小金莲”》文章一篇,并有“小金莲”照片四帧。标题使用“把玩”之词,读者自可闻嗅其心态与情趣。其实,这毫不奇怪,影视中每天在渲染帝王生活、寄生情趣,其宣泄的力度则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皇帝节”、“皇后节”又隔三差五地在“弘扬民族文化”声中反复登场;用民脂民膏建起的充满了光怪陆离的鬼怪的游乐园,尽管毫无文化价值可言,却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难道不是每天每日在腐蚀着国民精神而使民风奢靡吗!而最为严重的是,在一片“尊孔”声中对儒学的政治思想、道德范畴、生存原则……诸多方面的精神回归,有人说,此种儒学,它使官僚圆滑,以混差事为日务;使文人既迂拙又狡猾,以误人子弟为职业;使墨客才子风流放诞,除逢迎拍马外对社会兴亡漠然视之——如果我们还纪念着伟大的鲁迅,那么,鲁迅曾说,这些文化,其实就是“吃人”二字!诚如前述,此种状态,势必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乃至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东亚已有先例,不能不为之戒!
现在,我们应该以科学的和平稳的心态,镇定自己的狂热,从学理上做一些必须的探讨,以替代情绪化的操作。
列宁在著名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曾经有过这样著名的论断:“在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列宁的论断是根据当时俄国的文化形势而作出的。这个判断的价值,远远超过为解决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如崩德派)关于“民族文化”的错误见解,它对于观察社会主义之前各个时代的文化的本质,具有指导意义。(有人不同意以理论指导某种讨论,主张弄清事实,再谈结论。要弄清事实,是没有分歧的,但是为了弄清事实,也是可以使用别人已经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结论,这种结论于我便成为理论。其实,此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理论——著者)
古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在长期封建专制主义时代,其文化的主体,是体现了剥削阶级的意志,表现了剥削阶级的政治要求、经济利益、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生活情趣……,如果以社会主义精神指向作为检验的导标,它们在总体上是落后于新时代的,其中有不少是“腐朽”和“已经死亡”的成分。但是,因为在每一个过去了的时代中,社会是由多种阶级和阶层组成的,他们也创造了表现他们自身意志的文化;就是作为剥削阶级,乃至其核心政治统治集团,也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例如,面临外族或外国的入侵等)也会造就实际内容不同的精神文化,因此,在一个“主体文化”已经死亡的时代中,必然还存在着若干不是属于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成分,例如,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对于生养的土地山水的眷恋,对于劳动的歌颂,对于压迫与剥削的斗争精神,对于民众苦难的同情,对于民族和睦的向往,各种具有民主性的人文主张,各种具有辩证思想的治国安邦策略……因而,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中就必定会有两种文化。
目前,学界有一种隐现的意识,即在当代社会现代化的建设中,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极大地淡化了“阶级”的意识,于是便认为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例如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几乎不存在“阶级”、“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于是,也几乎不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腐朽与进步之分,有丑恶和光明之分,有专制与民主之分。谁要是谈到古代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压迫,谈到中国剥削阶级文化的腐朽性质,顷刻之间,“左倾”的帽子、“卖国”的帽子就会盖过来——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目前这是两把最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杀手锏。于是,被歪曲的历史与被歪曲的文化盛行于世,好像今日强大的祖国,过去就不应该有阶级压迫的历史,就不应该有曾经存在过的非常黑暗的文化——把中国历史说成一片光明,把中国文化描成一片辉煌。完全忘记了我们民族真实的过去——在历史上我们大多数人遭受的苦难,忘记了被压迫的民众对统治阶级所进行的殊死的斗争。天天向人民展现的是帝王的金銮殿,所谓的“满汉全席”!殊不知,这金銮殿是我们无数的父辈的尸骨所堆成!这“满汉全席”是我们无数的父辈的血肉所做成!这里或许正用得着列宁的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首先是要正视我们民族过去的全部历史,以及与历史相一致的文化形态。应该以新文化的精神指向作为导标,以新文化的真实的内容作为基础,检验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一切文化,区别两种文化的性质,拒绝一切与新文化的指向相悖的文化内容,即剔除其腐朽性的糟粕;抓住文化遗产中一切不仅属于过去,而且也是属于未来的文化成分,即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些民主性的精华,不应以旧文化的姿态贴附于新文化之上,而应该以新文化为体,对其“变异”而成为新文化的有效成分。这样,新文化便从传统文化中获得了真正有益的养分,使新的文化的潮流,变得更加丰富又多姿,使国民获得的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更加生动又坚实。
有人认为,“这就是取消了儒学的生存权”,真是大谬不然。我们保卫“儒学的生存权”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假如我们真的是为了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那就应该赞成让中国文化中具有“优势的基因”,在新条件下融入新的生命之中,犹如人类生命的延续,是依靠了新的生命的不断的诞生,而不是依靠祖先的万岁万万岁,否则就将成为干瘪的木乃伊了。假如我们纯粹是为了保卫“儒学的生存”,那尽可以建一个博物馆,大一点也可以,可是,鲁迅先生说,假如把中国的文明与文化,当作博物馆来欣赏,先生留给他们的那将是“永远的诅咒”!
七、“儒学革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不可少的任务
其实,这些问题,又都可以集中到一个问题,即人文学者究竟应该怎样来对待中国文化中最沉重的思想文化遗产——儒学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在精神领域中,如何处置儒学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未来的命运问题。
当前,作为我国当代文化建设中一个极为紧迫的任务,便是文化研究者要以充分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创造表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化”。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根”,生成于中国当代社会之中;中国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即这种文化中不仅包含着属于过去,同时也包含着属于未来的成分),它们是中国当代文化的“流”。历史上的文化遗产,究竟能不能进入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大流”之中,必须经过当代新文化的“精神指向”的检验,最终决定其“入流”还是“不入流”。这种“检验”,这种“入流”或“不入流”的“甄别”和“扬弃”,就是对旧文化进行的“革命”。中国当代新文化的重要任务,便是应该对儒学进行革命。道理十分浅显,儒学,作为一个主要是活跃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体系,尽管它的内部进行了多次的变革,但每一次变革,都使它对封建专制政治具有更强的黏附作用。当中国社会已经从以小农生产为主体的农业经济,进入到了大工业经济与信息时代,儒学的体系性的文化意义,在我国现代新文化的建设中,其消极性与腐蚀性已经有了相当的弥漫,它对中国国民精神与人格的销蚀力,无论是其显现的还是潜在的,都是极为严重;它是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一种极为严重的惰性力量。这里,我们重新提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是极为有意义的。鲁迅说:“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
说到“革命”这一个词,有些人会感到厌烦,甚至感到憎恶。于是就有哲学家提出了“告别革命”,以取媚于大众。至于说提出“儒学革命”,学界一定更会众说纷纭。其实,我们重提“儒学革命”,不过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精神指向。由于本世纪中国政治革命的繁复,五四所开辟的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尚未完成。北京大学是五四的圣地,我们是五四的传人,当中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新文化的创建,获得了以往未曾有过的历史机遇,也为文化学者们在学理上研讨古往今来的文化,创造了安定平静宽松的环境,因此,当代中国的学者有责任也有条件来继续五四的先辈们未能成就的事业。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与反对者,尽可以本着事实与道理,开诚相见;对于“儒学”的革命,也不用低头认罪,更不必高帽示众。所谓“革命”,就意味着“弃旧图新”,意味着“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改造,意味着“创造”和“进步”。当代的生活告诉我们,“传统是巨大的保守力量”。以对民族的责任和使命而言,我们并不惧怕,因为中国最反动的“四人帮”曾经推行过“批儒”,而不敢再提对“儒学”进行革命。
为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着中国民族未来的精神建设,以科学的精神,展开对儒学的革命,乃是时代赋予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
历史将最终证明在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中进行“儒学革命”的必要性。
标签:新文化论文; 基督教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