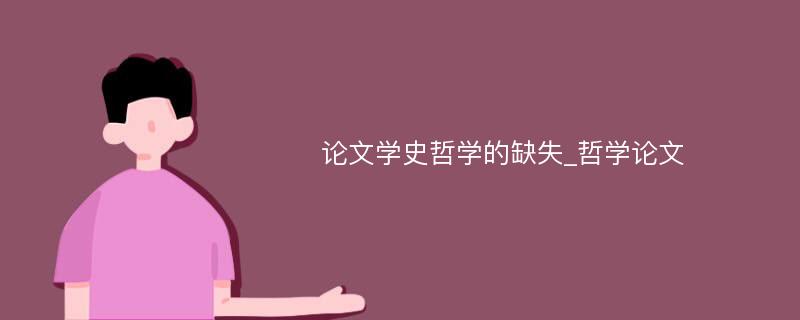
文史哲学阙略管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见论文,文史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西方人文学术的强项在于纯粹哲学和文史哲学飞扬,我国传统文化的长处则在于文史浑然和文思粘连:文化典籍丰富的史料和细致的考证常常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在深层的文史哲理和周密的文史思辨方面一直未脱疲软的状态。重要的问题不仅在于这一环节的疲软,而且在于国人对疲软现象的视若无睹,即阙而略之的学术观瞻。
一、文史哲学阙略寻思
这里讲的文史哲学是个集合名词,既指人们常常提到的文化历史哲学,也指吸纳了文艺和历史资料的哲学思想。这两方面的渗润与耦合形成了人类思想文化史上独特的景观:既不同于非常抽象且思辨逻辑化了的纯哲学,也有别于赏析评鉴和史料罗列的文史编著,而是文史哲真正的融合体。
欧洲是文史哲学发达的地区。古希腊的爱智哲学是文史哲学的滥觞,而且一直是欧洲文化的灵魂。中世纪为文史哲学包上了神圣的外衣,文艺复兴创造了文史哲学的再度辉煌,启蒙运动又一次将文史哲学的发展推向人类文明史的巅峰,20世纪西方文史哲学则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生发。从本质上说,古希腊“轴心时代”的文史哲学种子,在此后的各个时代都有不俗的表现。说文史哲学是欧陆文化的精髓决非夸张之词。深层次的思辨和高强度的概括固然有其磔裂感性和剥离直觉等弊端,但其在超越世俗偏见和突破实惠理性局限方面则有过人之处。
纵观中国历史文化长河,文史典籍之弘富堪称洋洋大观,然而文史哲学却始终是其薄弱环节。周易的文思在巫占的卵翼下破壳,老庄的冥想在求生的本能中酿成,儒墨的学说是血缘伦理怪圈内外的呻吟,法兵术势是以强权诡道的谋略遮蔽文史,史乘著述的思辨羽翼始终没有丰满。可以说中国上古“轴心时代”抽绎出了宗法血缘制所能有的华夏文化脉络,但是没有完成对文史的高度哲学概括。两汉最突出的文化成就是史录和歌赋,而思想则处于被阉割的境地。魏晋的玄学清谈,南北朝的文史盛况,唐宋以来的学术大要,均未在思辨哲学包括文史哲学方面迈出大的步伐。
中国自古就是诗文大国。从上古起我们就有散见于各类文章中的诗文见解,但是它们尚未经过哲学的洗礼,也未升华到文史哲学的高度。我们有一部令国人骄傲的《文心雕龙》,但是这部典籍经验多过理论,体悟胜于抽象,丰赡而不深沉,论列而欠思辨。就思想艺术的角度讲,有情致梳理和现象类比的长处,却有待思维的再一次升华和理论的进一步提炼。我们有《诗品》、《二十四诗品》以及异彩纷呈的散文、戏曲、小说点评,然而它们有的细碎,有的疏阔,有的东鳞西爪,有的拖泥带水,兼文史或有独到,攀哲理终欠火候。
中国在史学方面的著述最为骄人,同代编史和异代编史的规模和数量堪称世界之最,可是在史学学说方面却让人掩卷而迷茫,寻思而惆怅。让“乱臣贼子惧”、使礼乐昭日月的宗法道德观念笼罩史林,如司马迁“究天人”、“通古今”、“成一家”的思想大端常常是封建王朝和御用文人误解、诟病、甚至憎恶的对象。事实上司马迁只是开了个好头,在史学的思辨和文理的抽象以及历史哲学的提升方面原本有许多工作要做。二十四史乃至二十五史都有中国特色,《史通》、《史纲评要》、《读通鉴论》等论著也不乏史德、史才、史胆、史识方面的评价,但是未见史学哲学的迸发。
中国在编辑类书方面成就非常辉煌。类书的雏形在汉代已经显露头角。魏文帝时,儒臣编成第一部类书《皇览》。南北朝以后,皇家或私家编修类书成风。唐有《艺文类聚》,宋有《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明有《永乐大典》,清有《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民国至今,“丛刊”、“备要”、“丛书集成”之类的工程颇为时行。但是对这批宝藏的学术使用,基本上局限于辑校考释。浩如烟海的资料并未得到深加工,更没有改造制作为哲理的宏构伟制。
有人会说,《易经》、《老子》、《庄子》不就是非尚实的文史思辨吗?确切些讲,这是玄学,而非文史哲学。玄学与哲学名近实异,貌合神离。玄学尚虚——得意忘言,神悟为先,目击道存,一步登天;玄学又非常务实——捕捉机运,趋吉避凶,驾驭局面,逍遥自适。此类思想是自然与超然、务虚与务实的统一体。而文史哲学则是从史实蒸馏出的观念,是抽象过滤出的理路,是思想归证后的文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淮南鸿烈》、《文心雕龙》是突破了玄想的文史之思,规模大,气象新,文采斐然,思接天地鬼神。人们在笼统的归类时也常常把它们纳入“文史哲”一体的典藏。然而从学理上看,这些典籍专注于道气的泯化性和经验的生发性,实质上是囊括式思维和一揽子综述,是自然性的玄道遐想,是德性的气化神思。叩道性的玄想神思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独创,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史哲学。其中缺乏概念→范畴→理念的逐级思辨,缺乏透解文史资料后的多维反思,缺乏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当我们将玄想和文史哲学进行对比之时,不仅要为中国先贤的优长而欣喜和自豪,也要为华夏思想艺术的不足而警觉和奋发。在上个世纪,国人已经在开放性的学习方面迈出了重大的步伐。我们接受了西方的一些史学思想和文艺观念,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史理论,中华文史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文史哲学的道路上进步非常明显。但是跟老马识途,不等于明了老马何以识途;随西学流转,还不是在西学胜我之处刨根问底。不可否认,20世纪中国出了一批文化大师。他们对西方的思想观念、理论框架和治学方法有多方面的汲取,但是缺乏综合了文史而又另辟蹊径且称得上巨型叙述的文史哲学。许多大学问家程度不等地意识到了中国缺乏文史哲学的问题,于是有的依新学编文史,有的译介西学以开风气,有的融贯文史思而逼近文史哲学。他们都为中国化的文史哲学问世而呕心沥血,厥功甚伟。
人们在一般“哲学”(即思想)的意义上也将他们称为综合文史哲的领袖,但是确切些说,应该将他们称为促合文史思的先驱。哲与思有所不同。思近于哲,尚在抽象经验情绪。哲中有思,已经突出套路意识。文史哲学是使文学和历史思想峻拔的天窗,是使一般的思想趋于逻辑严密的阶梯。20世纪的文化大师在文史思的层面借道而行,拿来而用,照讲接讲,惨淡经营,启民智于蒙昧功昭日月,解华夏于倒悬气贯长虹。在文史哲学方面,前贤从异域学到的主要是模式、框架、套路和器用,即通常所说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工具,而对于产生方法之法和创新方法之法则悬而未决。师夷御辱到这个程度已经难能可贵。但是百尺竿头,还须更进一步。历史期待21世纪中国学人的自然是国学的创造性复兴,而创设中国式的文史哲学是当代人和后来者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二、文史哲学阙略探源
在思想文化创造方面,我们的基本目标是见贤思齐,而终极的追求则是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独创性贡献,即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超,人超我化。而在文史哲学阙略的情况下,首先必须弄清楚为什么人有我无。对此,笔者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之思。中国传统思想中文史哲学阙略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之中。文史哲学以及超验哲学需要超自然之思,苏格拉底等人的辩证乃至诡辩之思如此,柏拉图的对话哲学如此,古罗马人的基本精神也是如此。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罗马人是用利剑刺入了自然的心脏。后来的思想家们在超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国人的传统思维是自然之思,或曰与自然同气连理之思。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及后世文人学士无不崇尚自然之思。儒道及各家典籍莫不是亲近自然、植根血缘的产物。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根深蒂固的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造就了独特的宗法血缘文化:勤劳务实,情思绵密,孝悌忠信,礼仪廉耻,经史子集一如春华秋实,天人合一依赖自然脐带。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关于三才源于“自然之道”的概括可谓切中肯綮。而这也是中国旷古大家所能达到的文史哲思的极致。其优点包含局限,其缺点亲切动人。我国传统文化中文史哲学不孕症的根源就在这里。
2.暴虐之余。中国传统思想中文史哲学阙略也是奴隶制、封建制残暴统治的留白。西方文史哲学几次大的腾飞都得益于思想解放的巨大机遇,古希腊的贵族民主制、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本主义、启蒙运动和后现代思潮,这些放飞思想的社会契机都让那些时代的哲人智者相对摆脱了实惠心理和直接利害牵制,从而完成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基础建制,进行洞察天地人神关系的抽象思辨,将文学和历史史料提炼为高洁度的思想成果。而我国残酷的奴隶制和暴虐的封建制在思想文化中盛产两种事物:一是维护抑或揭露强暴统治的历史记载;二是刀兵师、刀笔吏和刀俎人组成的人才队伍,他们分别是帮凶、帮办、帮闲和处于底层或边缘的离心文人以及反抗者。有人矢忠矢勇报效主公的恩典,有人呼天抢地宣泄遭遇的不幸,有人以可怜的忠孝节义论证所述制度的合理,有人以仁义礼智斥责所批判对象的荒谬。残酷而强暴的专制制度和兵连祸结的历史现实把人才逼向了这几个狭窄的通道。愤怒出诗文,自由育哲人。暴虐逼迫出来的只能是非常乖巧而又非常实用、非常激烈同时非常激情的文史成就,而能使文史升华并让社会循序渐进的思辨之花则一误再误。
3.教化之偏。知情意足备的方块汉字是最适合多向拓展的人类文字之一。传统文化对汉字开发最多的是诗文。以诗擢人的科举方式推动了诗才培养,以八股取士的科考制度造就出故纸腐儒。诗才不是哲思,腐儒不识通变。以祖庙宗祠为枢纽的国家和以文庙儒宗为精神的学统都不尚思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家国一体的统绪维系着社会历史的延续,迂腐不堪的教育培养着专制体制的顺民。这与西方人本主义传统文化以创造为鹄的之教育理念判然有别。在宗教领域也是如此。人们常说西方的宗教是窒息灵气的精神鸦片。然而一个在理论上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与君臣和父子类比的家国理性有着大公与宗亲的重大区别。从思想的深度而言,西方人创造出上帝不啻创造宇宙观念式的恢弘,怀疑和推倒上帝则是宗教理性向文史哲学飞跃的重要环节。而我国的文教历史有温情而乏思辨,我国的宗教传统无沉思而有随宜。中国的宗教都是很实际的宗教,与中国的文化一样,是实惠理智;不仅务实,而且取巧,甚至把外来宗教都改造为实用教派,如中国禅宗、拜上帝会、一贯道。在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方面也是如此。如前所述,20世纪我们向西方学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定为一尊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拿来育猫、抓鼠、摸石头过河,非常重视“实践观”,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在思想艺术的层面和文史研究领域,应该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努力研究马克思得以提炼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文学、艺术等史料的高强度思辨水平。
不难看出,文史哲学的生发和盛行需要放飞思想的非自然或超自然之思,需要思想的自由和解放,需要琢磨史料、化解块垒、提升精神的理念化之思,需要别开生面、另辟蹊径、和而不同的原创性之思。长期以来人们关于文史哲学不要史料的误解可以冰释,因为它是在文史资料实证基础上的二次实证和思辨性归证。长期以来人们关于文史哲学不属文史的偏见可以消除,因为它是文史而哲理化,是哲学而文史化。长期以来人们关于文史哲学古已有之的说法可以商兑,文史哲学其实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文史和哲学的整合,而我国传统的文史思想所缺乏的正是逻辑和哲学对文史资料的提炼和归证。当然,缺乏文史哲学并非别无所长,更非一无是处。如果说西方文史逻辑化、思辨化、哲学化,那么也要看到中国文史史料化、诗学化、玄学化,二者各有千秋,适可互补。长期以来人们关于中学西学扞格难通的顾虑或可通变化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歌近史学,文史诗意化,史通诗心,诗可证史;西方古代史料学薄弱,文史哲学胜出。20世纪以来西方寻求哲学的文史化、诗意化,但是中国需要而且必须进行文史的思辨化、哲学化,二者在许多方面都可以择优而学,取长补短,在未来的国际化人文大潮中殊途同归而各呈异彩。这对国人对西方人都一样,各自的道路都很曲折,任何一种择取和互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
三、文史哲学前景展望
当亨廷顿之流肆意鼓噪文化战争的喧嚣时,国际学术界是多么需要一种澄明透彻的文史哲学以其祥光驱散重重迷雾。当我们面对高句丽历史的现代歧读时,一种笼罩群言的文史哲学对于化解短浅的目光是何等的重要。当我们披阅勒维纳斯对《塔木德》的解读时,作者那种穿破历史迷障深化犹太民族反思的笔触是多么宝贵。当我们聆听德里达等哲学大师消解逻各斯霸权主义的演讲之时,长久以来那种将语言当工具的理解显得多么肤浅。当我们看到西方人业已展开的中国文史资料的哲学释读时,华夏一族数千年一贯制的文史辑校考订是否少了点什么?
未来我国学术界的生存、发展与作为,都依赖于文史哲学的繁荣。在改造治学方法、在提高思想艺术方面,笔者以为至少有如下工作亟待展开:
1.让母体思维方法得解放。一个博大而有出息的民族,至少应有一批哲学工作者从事纯哲学、纯逻辑、纯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根本性方法即母体思维方法的研究。而对于广大的文史研究者和通常所说的文史哲学工作者而言,可以不去钻研纯哲学和纯逻辑,但是不可不涉猎母体思维方法的研讨。因为母体思维方法研究涉及到了哲学、逻辑的变通,涉及到了文学、史学的升华,涉及到了原创性思想的根本性解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文史哲学是根本性思维方法的产物。简言之,对母体思维方法的钻研既是纯哲学研究者的基本功,也是人文各科工作者的必修课。要想在文史哲学领域有所造就,必须在母体思维方法上有所建树。让母体思维方法从各类遮蔽和既定的束缚中放飞,实际上是促使人类思想的一次解放,也是推动人类文史的熔铸。这是非常艰难的任务之一,也是我们不得不有所努力的领域之一。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都与其母体思维方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扬长避短就得改善其自然文化,改造母体思维方法。解放是改善和改造的同义语。如果说改造国民性是漫长的历史任务,那么改善思维方法则是当下性中的历史重任,也是历史性中的现实追求。文史哲学的崛起有赖于此,国民性的改造得益于此。
2.让思想巨人生长成气候。首先应有好的大环境:学术和思想自由。假如没有轴心时代的王纲解纽和自由裂隙,全球几处文史集群不会生根抽芽从而为文明立心。倘若没有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的教权决堤和人权升腾,文史哲学之花不会适时怒放且多彩多姿。如果没有国际领域的思想解放和反霸潮流,后现代主义不会激浪冲天奔雷动地。这是说大环境的成熟是思想生态的基本条件。其次要有比较好的小环境:学风和文风的补正。朴学、玄学、科学、诗学、哲学、神学……各种学科及其流派,风气不尽相同,科别派别都有可能造成门户之见。人们往往是己非人,以己度人,其结果难免以偏概全,挂一漏万。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各种学风的互补,互补的目的是为了求正。正中含真但不只讲真。“真”考究的是过去,“正”执着的是现在,而“补”追求的是未来。西方人的文史哲学是“真”基础上的“补”。中国人的实学是在“真”衍化出的“正”。为了把握未来,中西方都需要在“补”字上下工夫,使既成的研究四面洞开,八方来风,使当下的探求吸纳众流,更上台阶。这是说小环境要有开放性。第三要有思想的献身群:学者要有识胆才力。其中识见和胆魄尤其重要。无识不能见隐微而成独拔,无胆只可由庸俗而进市侩。大好局面的出现当然是时势使然,但是圆通而言,时势也是人物识胆才力的作为。倘若汉武时代有群体司马迁,不仅司马迁的命运大不相同,就连中国的思想、政治、社会、学术建树都会格外辉煌。当时有识如司马迁者寥若晨星,而胆魄似司马迁者更是少得可怜。当学术和思想自由成为大势所趋,当学风和文风的补正蔚成风气,当思想的献身群灿若星河,我国的学术事业一定会云蒸霞蔚,文史哲学人才必然车载斗量。
3.让人文研究融贯变通途。一是从义务制教育即基础教育抓起,强调综合涵养。提高国民素质应重视三位一体,即文化知识(关于文史资料、科技知识和建设规划)、思想精神(包括思想内涵、思想艺术和思想境界)和健全体魄(涉及增进体质、发展体能和强化体魄)的统一体。二是在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方面重点突破,提倡博识性教育,鼓励淹通性研究。三是为文史哲学的生成当催化者、衍生者、接生者和培育者。老师要有眼光和抱负,努力在自己的工作中栽大树以擎苍天。学生要有思想兴趣和追求,不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都要不懈地发掘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学术慧根。刊物要开放,不可文学类只做一点史文的考据和鉴赏,史学类仅仅恪守“合纵”和“连横”的两条线,哲学类片面地维护本体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三段式。我们非常感慨欧陆和英美一大批文史哲刊物对人文类学说的兼收并蓄,尤其关注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文史哲融贯的研究潮流。欧美的学术变化让我们想起中国古代会通性治学传统的某些优点。一个刊物,如果只把同人认定的东西作为刊容,只把某种类型的东西作为“家珍”,其他任何东西不得染指禁圈,那只能画地为牢。还需要说的是文教以及社会各领域的通化性协调问题。各相关门类在用人方面要有通识性和超越性的大格局,舍此无法让跨学科的人才有生存或用武之地,也无法营造一个文史哲学化、哲学文史化的氛围。
上述三个大的方面,不仅是世界文史思想化和哲学化的大趋势,而且也是国人必须面对的世界性挑战和必须承担的时代重任。我们应该反思和变革传统的治学方法。无可非议,每个人都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得心应手的研究方法。可是我们务必正视这样的现实:从文史的故实整理而言,科技化的程序简缩了传统考索的许多环节,如果许多人热衷用电子工具重复考证或翻版拷贝并依此繁衍“课题”和堆积“成果”,实在有浪费人力物力之嫌。我们经常听到保护传统文化的疾呼和看到考订补救的各类工程,但是在赞同之余也让人产生难乎为继的忧虑。克服国故危机固然需要保护性整理,但是还需要创造性开发。顺着前人的套路“照着讲”和“接着讲”必不可少,然而深化和更新前人的观念“创着讲”尤其重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崇尚“述而不作”、坚信“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守成性民族,强调和鼓励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提倡文史哲学建设,说到底就是用另一种方法治文史,也是用另一种方法治哲学。广而言之,是对中华民族弱项的一个补充,是沟通古今,重整时空。
我们有非常深厚的文史积淀,有非常丰富的玄学储藏,将这些资源思想化、哲学化,实在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令人欣慰的是有一批国内外学者正在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国文史的思想化方面,关于中国传统文史的国际对话必将形成,史料学、史学学和文史哲学有望成为一种商量培养的融通性学问——人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