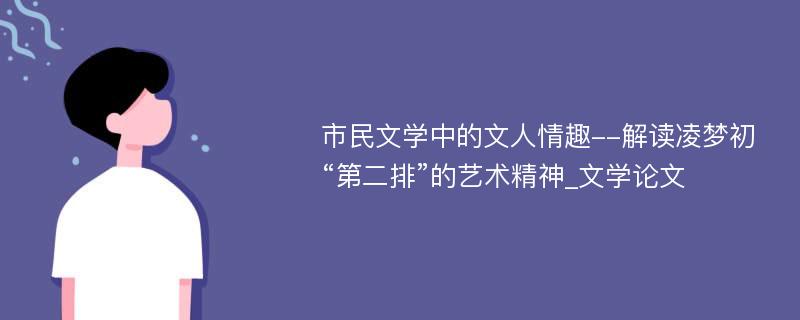
市民文学中的士人趣味——凌蒙初“二拍”的艺术精神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趣味论文,市民论文,精神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明代士人作家凌蒙初的拟话本小说集“二拍”通常被认为体现的是市民的鄙俗趣味,与作者在政绩德操方面的传统正统形象形成了冲突。但实际上“二拍”所体现的并不完全是市民趣味。早期话本所体现的典型的市民趣味在于耳目之外的离奇故事,而凌蒙初的拟话本的兴趣则在市民社会本身。“二拍”中许多故事来自以前流传的市民话本,但在加工整理之后,文化意蕴增强了,人物形象表现出儒与商、士人与市民两重性格交融的特点。这种两重性格的文化根据是明代东南地区的都市文化中士人文化与市民文化的交融:一方面文人士大夫们向市井生活沉落,另一方面商人市民却热中于向士大夫阶层的趣味与生活方式靠拢。两种文化、趣味的交融造成士人的二元道德观,由此而产生了“二拍”一类文人作品中特有的道德矛盾现象。
关键词 凌蒙初“二拍”市民趣味 士大夫趣味 两重性格 道德矛盾
一
在明代文学创作中,文人的拟话本小说具有突出的位置。而在这些拟话本小说作家中,晚明时期的文人作家凌蒙初则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凌蒙初的主要作品《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即所谓“二拍”)历来与冯梦龙的“三言”并提,被当作明代文人创作的通俗作品的代表。人们对凌蒙初作品价值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没有多大异议,就是认为这些作品表现的是市民阶级的通俗趣味。确实,“二拍”中的故事写的是市民的生活、市民的性格和市民的趣味,这同传统的文人创作大不相同。这是否意味着文人阶层已经归附到市民阶级中去了呢?
然而当我们注意到凌蒙初这个人物的性格与他的创作的关系时,就会发现问题要复杂得多。在凌蒙初的墓志上对他一生的主要行状是这样概括的:
崇祯中,以副贡授上海丞,署海防事。清盐场积弊,擢判徐州,居房村。治河时,何腾蛟备兵淮、徐,御流寇,慕其才名,征入幕。献《剿寇十策》,又单骑诣贼营,晓以祸福,贼率众来降。腾蛟曰:“此凌别驾之力也。”上其功于朝,授楚中监军佥事。不赴,仍留房村。甲申正月,李自成薄徐境,誓与百姓死守,曰:“生不能保障,死当为厉鬼杀贼。”言与血俱,大呼“无伤百姓”者三而卒。众皆恸哭,自死以殉者十余人……[①]
在这段记载中,我们看到的是标准的传统士人楷模,一位文天祥、于谦式的国士形象。这样的国土形象与专意于街谈巷语的通俗小说作家身份如何统一起来呢?上述的记载没有给出答案。没有必要怀疑墓志记载的真实性。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主要不是凌蒙初是否有过上述的那些业绩,而是他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问题。在墓志中,他的政绩与德操得到了高度评价,而作为通俗小说作家的文学业绩却被隐去了。这当然表明他的形象的上述两个侧面具有不同的价值,墓志的性质要求把那些不足为训或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隐去,而他所作的那些行世最广的通俗小说就在被黜落之列。他本人似乎并不想贬低自己所创作的小说的价值。据他自己称,小说“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观……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则可谓云尔已矣。”[②]这里他把自己的小说创作解释为有补于世道人心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自己的创作是受书商怂恿的游戏之作:
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非曰行之可远,姑以游戏为快意耳。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抄撮成编,得四十种。支言俚说,不足供酱瓿;而翼飞胫走,较捻髭呕血、笔冢研穿者,售不售反霄壤隔也……[③]
他称许小说“小道可观”,但同时又谦称自己的小说是“支言俚说,不足供酱瓿”,只是因为“翼飞胫走”,销路极好而为书商所求才一而再地“抄撮成编”。在他的创作中,“补世”的苦心与射利的欲望哪一样更重要,这恐怕是个说不清的问题。尽管他在几乎每一篇小说中都要不厌其烦地讲一通戒世的大道理,但无论他或书商都明白,使这些小说畅销的原因决不是那些大道理,而是他所谓的“耳目前怪怪奇奇”,耸人听闻的“支言俚说”。他由于两部《拍案惊奇》而传名后世,在他的墓志上却只字未提。这一事实表明,凌蒙初作为一名士人的地位毕竟与通俗小说作家的身份不大相符。这毫不足怪,因为这同我们所知道的传统价值观念是吻合的。然而有趣的是,这种不相符并没有妨碍他大量地写作通俗小说以迎合书商的要求,与此同时,他却仍然保持着正人君子的声望和节操。当时的人们尽管不认为他的通俗小说创作成就值得在墓志上加以旌扬,却也没有因此而贬损他的清望。凌蒙初在事关君子大节时的表现是典型的士人风范;而在一般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中看上去则又像是个不乏精明的市民。他的性格与社会形象具有双重性。
二
“二拍”中的故事大多取自宋元以来的民间话本或其他故事,因而往往被笼统归入市民趣味之中。然而仔细分析起来,像“二拍”这样的拟话本与真正的话本毕竟还有一些不同之处,其中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二拍”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与市民趣味不完全相同的趣味。作者在为《初刻拍案惊奇》中所写的序中说:
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
作者明确地说他所写的是“古今来杂碎事”,是“耳目前怪怪奇奇”,而不同于“今之人”所感兴趣的耳目之外的牛鬼蛇神。他所谓的“耳目前怪怪奇奇”,具体地说就是“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从他所写的故事内容来看,确乎大半可算作他所说的“古今来杂碎事”。除了少数从稗官野史演绎出的历史故事外,“二拍”中的大部分故事内容是描写当代市民生活或以市民生活为蓝本虚构的故事。故事的内容是市民的生活,而故事的趣味又是市民所感兴趣的“谲诡幻怪”之事,因此把这些故事说成是市民趣味的表现似乎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结论。
然而事实往往并不总是那么“理所当然”的。自宋代以来盛行于勾栏的“说话”艺术典型地体现着当时城市市民的趣味。据宋代耐得翁《都城纪胜》载: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扑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④]
这里大致可以看出民间话本内容所涉及的大概。而在罗烨的《醉翁谈录》中,罗列了一长串小说名目,分别归入“灵怪之门庭”、“烟粉之总龟”、“传奇”、“公案”、“扑刀局段”、“杆棒之序头”、“神仙之套数”、“妖术之事端”等题材类别中,并极力渲染说讲的效果:
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
从宋代人所记载的话本的题材门类与煽情效果来看,这类文学作品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而其中尤以凌蒙初所说的耳目之外的牛鬼蛇神与稗官野史中的谲诡幻怪之事为多。而属于城市市民自己的生活内容的故事倒显得无足轻重。这当然不能说话本不是市民自己的艺术,恰恰相反,这正是市民趣味的表现。荒唐离奇、惊心动魄、悲欢离合、因果报应之类的故事大半是远离市民自己的生活经验的幻想,然而正是这类能够激发想象力的或富于刺激性的故事情节最能够满足喜欢热闹的勾栏瓦舍中市民听众的需要。
凌蒙初的“二拍”是对民间话本的模拟。与真正的话本相比,这类作品的特点不仅表现为更加书面化的艺术特征,而且在题材内容方面表现出兴趣视野的改变:市民感兴趣的是耳目外的幻想世界,而文人感兴趣的却是市民社会本身。“二拍”中的故事无论多么谲诡幻怪或者说“怪怪奇奇”,无论故事中的时间与空间听上去多么遥远,其实都是在“耳目之内”,都是在以明代市民社会为背景的世界图景之中。
“二拍”中明代商人气息最重的首当推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鼋龙壳”中主人公文若虚航海发财的故事。这是个离奇的意外发财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背景是闽广一带商人从事航海贸易活动的情况,故事中的基本情节本来已流传在社会上。同时代人的笔记《泾林续记》中便记载了这个故事,其中关于航海遇巧的情节与《初刻拍案惊奇》中的有关内容几乎一模一样。显然这个故事中的真正属于“谲诡幻怪”的耸人听闻的情节并不是凌蒙初的创造,不过是他用来织造自己的故事的素材。那么他的创造在哪里呢?首先,《泾林续记》中所记载的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是“闽广奸商”中的一个,只是因为“本微,不能置贵重物”而专门打主意卖福橘的。而“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中的主人公文若虚却变成了苏州人,是个“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的风流才子一类的人物。这个人物身份的转换可以看出作者的趣味所在:他不是在简单地传播一件逸闻,而是想借此描绘出一个他所感兴趣的世界图景。原故事中的主人公的身份是“自动”产生的,也就是说,是故事本来的背景条件(闽广一带航海贸易活动)所给定的(“闽广奸商”)。而文若虚的身份则是作者刻意构想出来的,这个人物的籍贯、身份给故事规定了新的视野:故事不再是海外奇谈,而是作者身边的江南社会的一景;主人公也不再是传奇式的航海冒险家,而是带上了几分士人气的苏州市民。
在“转运汉遇巧洞庭红”的故事中,航海冒险的故事之前增加了一段文若虚做生意屡屡倒运的描写:
一日,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来。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拓了几笔,便值上数两银子;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也就哄得人过,将假当真的买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下等的无金无字画,将就卖几十钱,也有对合利钱,是看得见的。拣个日子装了箱儿,到了北京……开箱一看,只叫得苦。元来北京历沴却在七八月,更加日前雨湿之气,斗着扇上胶墨之性,弄做了个“合而言之”,揭不开了。用力揭开,东粘一层,西缺一片,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者。一毫无用。止剩下等没字白扇,是不坏的,能值几何?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本钱一空……
在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江南一带的市民的艺术趣味实际上是在追随士人的趣味。文若虚的出身似乎是商人家庭,至少不属于正统的士人阶层。然而他的生活趣味却与江南文人士大夫很接近:粗通琴棋书画,能学得出沈、文、祝等名家的字画。而即使是模仿的字画,也可找到买主,显然是因为社会上有许多缺少艺术素养却有钱也有兴趣附庸风雅的市民。这段描写虽然不算太长,却写得很生动,显示出作者生活经验的丰富,同时也正表明作者对这种市民社会生活的浓厚兴趣。因此,“二拍”中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的故事便具有了与《泾林续记》中的闽广奸商意外发财的故事不同的视野:后者只是一件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海外奇谈,前者却是精心描绘出的社会生活。市民的兴趣多在耳目之外,而文人的兴趣则在市民社会本身——这正是文人拟话本与民间话本的不同之处。
《初刻拍案惊奇》卷六“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是书中色情意味最浓厚的故事之一,应当说比较典型地表现出市民趣味中猥亵恶俗的一面。这篇故事的入话部分讲的是一个唐代的故事:一位美丽而贤淑的狄夫人因姿色而名动一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一位士子叫滕生的看到。滕生一睹芳容后魂销魄散,想尽办法用重金贿得狄夫人心动,终于如愿以偿地与狄夫人幽会。原故事在元代的《说郛》中就已收入。[⑤]在《初刻拍案惊奇》的“酒下酒赵尼媪迷花”一卷的入话中,又将这个故事加以渲染描绘。尽管作者在序言中强调了自己的道德意图,毕竟这种渲染描绘使我们无法高估作者的趣味和教化意图。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认真比较一下《说郛》中的故事情节与“酒下酒赵尼媪迷花”中入话故事的区别,不难看出后者的趣味毕竟与《说郛》有所不同。在原来的故事中,滕生见到狄夫人后“悒悒不聊生”,想尽办法寻访到了与狄夫人亲近的尼姑慧澄,通过她了解到狄夫人喜欢珠宝,便搞到了两囊大珠,声称“直二万缗,愿以万缗归之”。当尼姑说一时不能办到这么多钱时,滕生急忙说:“四五千缗,不则千缗、数百缗皆可。”甚至说:“但可动,不愿一钱也。”尼姑便带着珠宝去见狄夫人,并谎称滕生是为求复官的事而来。狄夫人果然动心了,尼姑便乘机安排了会面,使滕生终于遂其所愿,得谐鱼水之欢。到此为止,这个故事与“酒下酒赵尼媪迷花”中入话故事的情节可以说完全一样。但此后的结局部分两个故事便有了很大的差别。《说郛》中讲到滕生与狄夫人来往数月,直到狄氏的丈夫回来——
生,小人也,阴计已得狄氏,不能弃重贿。伺其夫与客坐,遣仆入白曰:“某官尝以珠直二万缗卖第中,久未得直,且讼于官。”……生得珠,复遣尼谢狄氏:“我安得此?贷于亲戚,以动子尔。”
这里的滕生翻脸变成了无赖小人。但这并非故事意在谴责滕生。有一点逻辑上的理由使故事不得不如此发展:从情理上讲,滕生一介书生何以有如此贵重的珠宝轻易送人?假如滕生是巨富子弟当然可以,但那样一来,故事的情趣将大打折扣。事实上,故事中也确实没有那样交代。这样一来,滕生的无赖行径便成了合情合理的结果。这个合情合理而又出人意料的结局显示出了一种市井无赖式的智慧,如同鲁迅在《上海文艺界之一瞥》中批评“鸳鸯蝴蝶派”小说时所讥刺的那种“才子+流氓”式的下流市井才子所感兴趣的“嫖学”智慧。
在“酒下酒赵尼媪迷花”中,作者却把这段故事的结局中关于讨回珠宝的情节完全删去了:
此后每夜便开小门放滕生进来,并无虚夕……过得数月,其夫归家了,略略踪迹稀些。然但是其夫出去了,便叫人请他来会。又是年余,其夫觉得有些风声,防闲严切,不能往来。狄氏思想不过,成病而死。
变成了一个近乎伤感的结局。这个结局的改动并非无足轻重,它实际上意味着叙述人视角的转换。在《说郛》中,叙述人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讲述这个故事的。叙述人所关心的是故事情节的巧妙和引人入胜,而不是对人物情感、命运的关注。滕生的形象以风流才子起,却以市井无赖结束,使这个人物性格的统一性大打折扣。这并没有使叙述人感到不安,充其量轻描淡写地批评一句“小人也”拉倒。显然在叙述人眼中这件事本来就不足为训:滕生既是小人,狄夫人也有几分是咎由自取。只有事件的过程可供一笑。而在“酒下酒赵尼媪迷花”中叙述人的态度不同了。叙述人在故事末尾明确地对这件事的道德意义进行了批评:
本等好好一个妇人,却被尼姑诱坏了身体,又送了性命。然此还是狄氏自己水性,后来有些动情,没正经了,故着了手。
他首先谴责的是尼姑,其次旁及狄氏,而滕生却被轻轻掩过了。这同故事结尾删去滕生讨回珠宝的情节一样,都有一些为书生讳的意思。这样一来,滕生究竟如何欠下的珠宝债的问题被回避了(这本来应当是比较重实惠的市井听众感兴趣的问题),故事情节变得不尽完整;然而滕生的性格却更统一了:他变成了一个多情种子——一个合乎晚明时期文人士大夫的欣赏趣味的形象。
三
两部《拍案惊奇》中的故事,据凌蒙初自己说是“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就是说内容多有所本。后代的研究者经过搜检爬梳,寻索到了其中大部分故事的更早的出处。[⑥]相比较而言,收入“二拍”中的故事与其原出处的情节相差往往不大。主要的差别在于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故事的原出处主要是一些零散的笔记小说或早期的话本,重点记载的是耸人听闻的故事情节,而更具体的细节描绘较少,人物形象大半比较粗简;“二拍”对故事所作的加工主要是细节描绘的丰富,尤其是人物形象描绘的生动。经过凌蒙初加工后的故事中人物形象,不仅在艺术上有了提高,而且有了更丰富的文化意蕴。
“二拍”中所描绘的人物林林总总,三教九流各种人都有。有些是话本和民间传说中已有的脸谱化了的人物,如油嘴滑舌的媒婆、偷鸡摸狗的和尚等;还有一些则是凌蒙初加入了自己的体验和想象力而创作的更现实化的人物,其中较有性格特色的人物形象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士人或儒生,如《初刻拍案惊奇》中卷十“韩秀才乘乱聘娇妻,吴太守怜才主姻簿”中的韩秀才,卷十一“恶船家计赚假尸银,狠仆人误投真命状”中的王生,卷十二“陶家翁大雨留宾,蒋震卿片言得妇”中的蒋震卿,《二刻拍案惊奇》中卷十一“满少卿饥附饱扬,焦文姬生仇死报”中的满少卿,卷十八“甄监生浪吞秘药,春花女误泄风情”中的甄监生,卷三十四“任君用恣乐深闺,杨太尉戏宫馆客”中的任君用等等;另一类是商人,如《初刻拍案惊奇》中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鼋龙壳”中的文若虚,卷二十二“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时刺史当艄”中的郭七郎,《二刻拍案惊奇》中卷十“赵五虎合计挑家衅,莫大郎立地散神奸”中的莫大郎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儒与商两种人物构成这个时期江南城市社会的主要阶层,因而毫不奇怪,这两种人物也成为凌蒙初在讲述故事时所关注的主要人物。
然而,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一下“二拍”故事中的那些士人儒生和商人,就会发现这些人物形象的更有趣的特征。比如《初刻拍案惊奇》卷十“韩秀才乘乱聘娇妻”中的韩秀才,一出场时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他年十二岁上,就游庠的,养成了一肚皮的学问,真个是:才过子建,貌赛潘安。胸中博览五车,腹内广罗千古。他日必为攀桂客,目前尚作采芹人。
完全是一副典型的酸腐儒生面孔。然而就是这个酸秀才,处世却不乏精明之处。当时风传朝廷点绣女,一位开当铺的商人金朝奉急急忙忙就要把女儿许给韩秀才。秀才此时却不迂执:
子文分明晓得没有此事,他心中正要妻子,却不说破。慌忙一把搀起道:“小生囊中只有四五十金,就是不嫌孤寒,聘下令爱时,也不能彀就完姻事。”朝奉道:“不妨,不妨……待事平之后,慢慢的做亲。”子文道:“这到也使得。却是说开,后来不要翻悔……先请令爱一见,就求朝奉写一纸婚约,待敝友们都押了花字,一同做个证见。”
显然对这件事考虑得很周到,后来当金朝奉赖婚时,他权衡利害后决定要实惠而不是争意气,只要求金家加倍赔偿聘金了事。后来当太守看出事情蹊跷而追问时,他立刻随机应变,转口道出实情,结果是人财俱得,皆大欢喜。在这位秀才的处世方式中,可以看出一点商人式的精明与机变。
另一方面,故事中的商人形象则又多多少少带着士人气,如文若虚在趣味与素养方面所表现出的士大夫情趣、莫大郎在处理家族嫡庶关系时所表现出的君子风度以及“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谭侠”中的徽州商人程元玉的儒雅风度等等都是此例。而卷二十二“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时刺史当艄”中的商人郭七郎则是个反面的例子。这则原出于《太平广记》的轶事被凌蒙初渲染得有声有色,主人公郭七郎在求人帮忙花钱买官时说:“小弟家里有的是钱,没的是官。况且身边现有钱财,总是不便带得到家,何不于此处用了些?博得个腰金衣紫,也是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就是不赚得钱时,小弟家里原不希罕这钱的;就是不做得兴时,也只是做过了一番官了。登时住了手,那荣耀是落得的。”这位郭七郎是个商人兼花花公子式的人物,当然谈不上有什么士人气。然而在上面那番话中可以看出,商人的精明、花花公子的豪奢与对士人地位的羡慕在他身上是融为一体的。
“二拍”中人物形象所表现出的这种儒与商、士人与市民两重性格交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前面已经提及,凌蒙初本人的性格就可以看出这种两重性。其实这不是凌蒙初一个人的特殊性格。同时代还有一个比他更有名的人物也同样矛盾复杂。这个人就是董其昌,一个在奸臣严嵩倒台之后名重一时的朝廷权要,门生、交游满天下的绅士名流,大书法家、画家,以“南北宗”之说擅名的艺术评论家,同时却又是一个工于算计的商人和投机者。据史书记载,就在他任宰相期间,还雇用着许多女工为他家纺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从事着纺织品贸易。他把松江地区收取的赋税纳入自己的金库,让税吏拿着缴税的清单进京,到他的相邸取银子,而相邸的银子是专门请人熔铸的“以七铢为一两”的劣银。董其昌的人品当然不足为训,但士人兼作商人的事在当时经济繁荣的长江下游地区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据于慎行《谷山笔麈》记载:“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凌蒙初和董其昌的两面性格说到底是时代环境的产物。
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到近古的几百年间,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经济、文化生活多次遭到破坏。而地处中国东南部的长江下游地区经济、文化却在这几百年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保持着持续的繁荣。尤其是在宋朝国都南迁临安后,中原的士人阶级大批涌到江南,一方面影响了江南都市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士人阶级也受到江南都市商业文化的强烈影响。如林升的诗所描写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样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固然是对偏安一隅苟且偷生的南宋士大夫的嘲讽,其实也是自南宋以来士大夫阶层融入都市市民文化的一个真实写照。
自南宋以后到晚明时期,东南地区的都市文化中士人文化与市民文化交融的色彩越来越浓厚。据《客座赘语》说,明代嘉靖以前士风还比较正统,文人墨士谈吐高雅,举止彬彬有礼;而此后则士风日见浇漓,衣巾士人谈吐之间俚鄙如村巷之人。这不仅是少数纨绔子弟离经叛道的问题,而是东南文人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如另外一位通俗小说作者冯梦龙就很喜欢收集市井流行的俚俗小调、奇闻轶事乃至下流笑话之类,将收集来的这些东西裒辑成书出版,在文人士大夫当中颇为流行。他所收集的笑话集《笑府》中有一则说的是某人有三个女婿,其中三女婿甚呆。有一次这位丈人要三位女婿作诗形容他的马快疾,三女婿苦于无词可对,忽听到丈母娘放了个屁,于是随即答道:“丈母撒个屁,丈人骑马到会稽,骑去又骑来,孔门犹未闭。”在《广笑府》中有一则说某县官写字潦草,他写条子派人去买猪舌,“舌”字写得太长,被误认为“千口”二字,于是差役遍乡寻买,只得到五百口,只好向县官哀求减半。县官笑着说:“我让你买猪舌,如何认作买猪千口?”差役听了便答道:“今后若要买鹅,千万写短些,休要写作买我鸟(diao)!”前一则笑话津津有味地拿放屁来打诨,只好说是鄙俗;后一则更是猥亵恶俗了。诸如此类的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话在明代文人中流传的很不少,由此可见当时士人趣味之一斑。
当我们阅读像“三言”、“二拍”或《笑府》、《笑林》一类文学作品时,不大容易把这些东西与我们心目中峨冠博带、道貌岸然的文人士大夫形象联系起来。相反,却很容易把这些作品的作者与读者想象成一帮不学无术、趣味鄙俗的小市民。然而事实上这些文人士大夫们却是近古社会文化中的精英阶层。自明代中期以来,江南的文人士大夫已成为一种与朝廷和正统观念相抗衡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政治与文化势力。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然要数东林、复社党人。尽管作为政治派别,东林、复社的势力与影响尚属有限,然而这些党人所代表的是一个相当大的文化圈层。他们在政治上持不妥协的理想主义立场,人格上注重标举个人的节操,争意气的热心更甚于争是非,这在明代中后期蔚成风气,甚至连大臣触怒了皇帝而当廷被裸衣杖责都被视为荣耀。至于在生活方式、趣味与个人气质等方面更是推崇那种不同于官方和习俗的独特个性。晚明时期江南文人士大夫对市民趣味尤其是鄙俗趣味的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显示其悖离正统文化的精神。
就在文人士大夫们沉湎于都市声色之娱、混迹于市井生活之中的同时,商人市民们却热中于向士大夫阶层的趣味与生活方式靠拢。台湾学者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指出,明清时期的商人与士人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方面表现为一部分士人“弃儒就商”,加入了商人阶层;另一方面则是商人的“儒意”,即对儒家学说与道德的向往。[⑦]其实,这个时期的商人、市民所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儒意”,而且包括能够体现士大夫文化与趣味的各个方面。经济繁荣的长江下游地区同时也是文化繁荣的地区,这同商人的介入文化活动是分不开的。商人市民们的附庸风雅使得士大夫的趣味如书画、古董的鉴赏收藏等活动流行了起来,并加强了士人与市民社会的联系。像董其昌以及同时代的其他许多文人画家如吴门画派、虞山画派的不少人都成为商人们所追逐的目标,以至于有人说明代的文人作每一幅画都是在制作商品。总之这个时期的儒与商、士人与市民在文化上开始杂糅了起来。凌蒙初的人物形象中最有魅力的东西就是那种折射出时代文化色彩的儒商杂糅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讲,“二拍”是一卷体现晚明时期文化特色的人物画廊。
四
文人的拟话本体现的是文人的趣味。然而这种趣味又不同于正统意义上的文人趣味,凌蒙初书中经常可以看到与正统文化与趣味相悖的东西。《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二“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是这部书中较明显地涉及淫亵内容的章节之一。作者自己在本书的序中提到“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诬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表明了他自己对于亵秽内容的否定态度。对于本书中的淫亵内容,他在书的凡例中解释说:“是编矢不为风雅罪人,故回中非无语涉风情,然止存其事之有者,蕴藉数语,人自了了;绝不作肉麻秽口,伤风化,损元气。”这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在书中对淫亵内容的描写是蕴藉得体、无伤大雅的;他的意图只是劝戒而非欣赏。
然而事实上并不尽然。“乔兑换胡子宣淫”的故事在万历年间出的《觅灯因话》中已有记载,情节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主要是,《觅灯因话》中侧重于借这个故事宣讲人生哲理,在铁生招来卧法师禳灾一段借仙人之口说:“盖天非他,理而已矣。福善祸淫,理之可信者也。栽培倾覆,人之自取者也。尔名世儒家,乃昧自取之理,为无益之求,不可为太息哉?”铁生的祖先绣衣公与南北二斗的问答内容在故事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基本涵义就是要人处世豁达、相信天理。从整个故事来看,作为事件过程的情节描写比较简约,而说理的部分却不厌其烦,滔滔不绝。显然故事的兴趣主要不是在情节方面而是在哲理方面。这是比较典型的文人作品。而“乔兑换胡子宣淫”则与此不同:后面的说理部分大部分被删略了,对故事情节中男女偷情的细节则进行了渲染。更重要的是两个故事的不同结局:《觅灯因话》中结局是偷淫的胡生遭到了天罚——痈疽大发而死,从而确证了天道的公正。这是个说教意味很浓的结局。“乔兑换胡子宣淫”却不同,在讲到胡生痈毒大发后,又增加了铁生看望胡生并进而勾搭胡生妻子门氏的情节。这正应了“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的老话,证明天道轮回、善恶报应的道理。看起来这两个结局的道德意义相同,而其实不然:前者着眼于社会道德意义上的公道与惩罚;后者关注的其实是个人的利害关系——胡生淫人妻子固然应当受到惩罚,而铁生的妻子被人勾引则应受到补偿,所以结局是他反过来勾搭胡生的妻子。表面看来胡生的受到惩罚是对道德的维护,其实却由于两个人相互偷淫而形成了对道德的双重破坏。这是个道德的悖论。这种似是而非的道德观基于一种实利化了的道德意识:不相信天道的意义,只相信现实利害的平衡。故事中对胡生与铁生相互偷淫对方妻子的行为描述得津津有味,这表明偷情之事虽然在观念上讲是一种罪孽,而从感性经验的角度来看却是一种趣味、一种利益。因此,胡生偷情的后果虽然是为他的罪孽而遭到天罚——痈疽大发,却没有使受害者的利益得到补偿,这使得读者的心理无法得到平衡,因此需要有铁生反淫胡生妻子的情节来加以弥补。这是市民式的道德观,是对正统道德的销蚀。
显然,《觅灯因话》体现的是正统的道德观,而“乔兑换胡子宣淫”则表现出市民的道德观。这并不意味着凌蒙初在作品中简单地充当了市民的道德代言人,而是表明了文人士大夫的一种反传统道德的倾向。自明中叶以后,王阳明的心学大行于世,王的传人中有不少近于狂禅的怪人如王艮、李贽等,都具有强烈的反传统道德的倾向。这些人在晚明时期江南文人士大夫中有很大的影响和号召力。在这一时期文人所收集的笑话中就有相当多的内容是借市民和其他三教九流人物之口对正统的儒家思想与道德观念进行讽刺嘲谑的。可以说,这些离经叛道的文人士大夫与市民社会在道德观念上距离并不很大。《拍案惊奇》故事中对市民趣味的欣赏也包括着对市民那种非正统道德观念的欣赏,这种欣赏本身就是一种反传统的态度,表明士人在道德上向市民社会沉落了。
关于“二拍”中故事的道德意义,作者自己在《拍案惊奇凡例》中讲得很明白:“是编主于劝戒,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这就是说,他是非常注意故事的道德意义的。然而正如我们在分析“乔兑换胡子宣淫”故事时所看到的,故事中的内在的道德意义与作者所“致意”的道德劝戒二者之间往往是矛盾的。因此后来的人们常常倾向于认为“二拍”故事中作者所标榜的正统道德观念只不过是一层意识形态伪装而已。确实,像“乔兑换胡子宣淫”一类色情意味较浓的作品,其中的趣味与所标榜的道德意义很难协调,道德说教的内容必然是空洞无力的。但是,这似乎还不足以证明所有故事中的道德内容都是虚假的。像“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李克让竟达空函,刘元普双生贵子”、“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等都是典型的宣扬正统道德观念的故事,其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的道德意义与叙述人的道德说教也是吻合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故事所描写的是被作者肯定的、基本上符合正统道德的正面人物,通过故事情节表达了忠厚、仁慈、侠义、智慧等价值。因此从整体上看,似乎道德意义很难统一。这显然与故事来源的复杂性有关:凌蒙初所摭拾的那些“古今来杂碎事”本来就是来自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阶层的东西,代表着不同的道德意识。尽管如此,这种种“杂碎事”经过凌蒙初的加工创作,毕竟融入了他的趣味和价值观。在形形色色的道德意义矛盾背后,存在着作者自觉不自觉地赋予作品的统一的道德意识。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作者有意掩饰自己的道德意识,而只是表明了作者在故事叙述中表现出矛盾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二元的道德观。
像“乔兑换胡子宣淫”一类的故事中趣味与道德的矛盾比较明显地暴露出作者道德意识中的矛盾,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而在更多的描写道德上的正面人物的故事中,似乎又表现出正统的道德观念。然而只要仔细注意一下就会看出并非如此。传统道德观念的核心是“忠”与“孝”这一对范畴,这是由传统社会结构中权力与血缘这两组基本关系所决定的。然而在“二拍”故事中,忠孝观念退隐到了若有若无的地位。从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例子就可以看出,这类故事中道德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诚信、义气、公正、睿智等品德上,而这些品德其实更多地属于市民社会中更广泛的人际关系所要求的道德。总之,“二拍”故事所体现的道德意识矛盾表明这个时期江南的士人阶层正在从正统的意识形态中蝉蜕出来,士人的道德观与市民的道德观在相互靠拢、相互影响,成为一种新的、城市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形态。
注释:
① 《光绪乌程县志》,引自《中国小说史料》第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 《拍案惊奇序》,引自《初刻、二刻拍案惊奇》第1页,岳麓书社1989年版。
③ 《二刻拍案惊奇·小引》,同上书第421页。
④ 引自《中国小说史料》第1页。
⑤ 《三言两拍资料》第607—609页。
⑥ 参看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⑦ 参考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下篇《中国商人的精神》,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