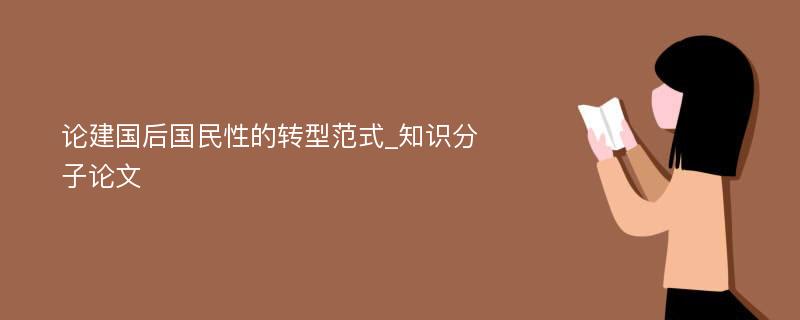
论建国后的国民性改造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性论文,范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69(2003)02-0076-05
国民性改造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非中国的一种国别现象。“国民性”一词,最初由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等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引进;而且,它也并非日本语汇的原生词,而是英语词汇"National character"、"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是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术语。对国民性的反思,是各国自文艺复兴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不同的国家,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面临不同的现代化的任务,因而国民性改造的范式也不尽相同,包括国民性改造的主体、客体、内容的区别及转换。然而学界对于建国以后国民性改造的状况,却表现出一种集体沉默,似乎形成一个盲区。这关系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有无国民性改造这样一个大的理论问题。
一、建国后国民性改造主体的转换:历史的误会还是理论的偏差
欧洲的现代化因其文化传统的相似与历史背景的一致性,在国民性改造范式上也具有相似性。从十三世纪的意大利开始到十七世纪的英国、法国止,文艺复兴的主角和弄潮儿始终是知识分子。他们倡导的思想解放,使处于中世纪的人们逐渐从宗教的桎梏中觉醒,促成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国家革命或改革,并先后建立了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实现了各国国民性的改造。
在日本的国民性改造中,启蒙知识分子并非唯一主体,政府作为权力持有者的作用使得知识分子的思想在国家的制度化建设中得以实现。以福泽谕吉、西周、津田真道、加藤弘之、中村正直和森有礼为代表的维新启蒙思想家批判以中国文化为母体的日本传统文化,赞扬西方文化;以大久保利通、井上馨、伊藤博文等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制度化建设的过程中,随着维新思想家的推波助澜,日本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其社会习俗、宗教心理、生活方式等都逐渐欧化[1],从而实现了日本国民性的现代转换。无疑,给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以直接影响的是这种日本式的国民性改造范式。中国的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面批判中国的封建制度,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和社会理想;一面试图影响光绪皇帝推行“新政”,以期在制度建设中实现国民性改造。然而,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这种制度建设的努力也随之付诸东流。于是,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又陷入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思想家在黎明的曙光中孤军奋战改造国民性的时期。康有为的“开民智”、梁启超的“新民说”,后来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对中国国民性的反省、批判,对理想人性的探求,都是在一种分散的、独力难支的状况下进行的。比如,在鲁迅的国民性改造著作中,一方面有着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懑,另一方面却是充斥于字里行间的孤独与无奈。[2]
这似乎成了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的宿命:启蒙思想家杜鹃啼血式的呼吁始终只流行于觉悟了的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广大的民众,依然受着封建压迫和帝国主义的精神奴役而不自觉。这期间,辛亥革命如昙花一现,根本来不及与启蒙思想结合,其后的蒋介石政权非但不与启蒙思想结合,反而在1934年发动“新生活运动”,企图通过制度建设贯彻实质为封建伦理道德的价值标准与行为准则。事实上,这种状况迫切要求实现国民性改造范式的转换。
新中国的成立,为实现日本式的国民性改造范式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全会上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3]中央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4]这里虽然没有明确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明确地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任务。按照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唯物分析,毛泽东确信“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5],而因为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6],因此,“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样,知识分子在建国初便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地位,一方面是“要使用他们”,“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一方面又要“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7]。并于1951年夏至1952年冬掀起第一场全国性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而后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更是接连不断。
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作为新政权中国民性改造的先锋的主体地位受到了根本的动摇。从前述可以明显看出,不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启蒙知识分子,还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维新派思想家,乃至我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急先锋的启蒙思想家,都是代表着当时的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用资产阶级理论向封建制度宣战。而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及以后的过渡时期,还未涉及从经济制度上消灭资产阶级,但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发动看,至少可以说明一点:资产阶级文化在新中国已不再是先进文化。此时,已不再代表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自身都需要进行整体的国民性改造,它又何堪以当国民性改造的主体?按照这一思路,只有代表无产阶级文化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与政权,才能堪当此任,“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8]事实上,建国后的头三十年正是由中共及其政府独力支撑起国民性改造的重任,中共及其政府成为国民性改造的唯一合法主体。国民性改造主体的这种转换影响了建国后头三十年国民性改造的实践及其特点。
二、建国后国民性改造内容的转换:如何完成双重使命的历史重任
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进发的几次高潮,都是在资产阶级运动受挫,封建主义复苏的契机上。第一次是甲午海战宣告洋务运动破产之后,严复、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思想家根据当时“民力已忝、民智已卑、民德已薄”的现状[9],奋起批判封建专制乃“坏民之才,散民之力,离民之德者”[10];封建纲常名教与学术制度使“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因而要新民救国,“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11]提出了明确的反封建纲领。
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五四时期以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从爱国救亡、民族革命的角度充分认识到:要救国,必须改造国民性;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根本上变革文化。于是有了陈独秀对封建学说的分别厘清;李大钊前期在列举众多的国民劣性后,深刻地揭示了这些劣性是封建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产物,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进一步揭示了更深一层的根源:经济基础。鲁迅对国民性改造内容的分析,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尤为尖刻而精到。封建学术制度因酷刑、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12]如此“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13]鲁迅后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方法,使他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国民性改造内容上的注目点是封建主义;即使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在国民性改造只是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武器,国民性改造的内容只是封建主义。这便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国民性改造内容范式。
新中国成立使整个政治经济制度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势必影响国民性改造内容范式的变化。还早在1949年6月中共建党28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8]这就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而国民性改造的内容,就是“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对于人民也要“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8]“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8]。
建国后的具体国民性改造实践中,则更加明确地分别出国民性改造内容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比如,在批判封建主义方面,既通过土改从根本上消灭地主阶级存在的经济制度前提,又强迫地主劳动以改造为新人;对于农民则“由群众自己批驳落后群众中长期存在的错误思想,比如贫穷是由于命运,分土地是不道德行为等等。”[3]在“三反”和“整风”运动中试图消除封建政治文化官僚主义的根柢。在“大跃进”运动中试图通过“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破除封建中庸观和君子耻于言利的价值观;通过“轻视过去,迷信将来”破除封建厚古薄今传统[14];通过“破除迷信,打倒贾桂”破除封建传统的“奴隶精神”[14]。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中毛泽东认为“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15]在评《水浒》运动中毛泽东特别强调鲁迅的观点:“因为不反天子……终于是奴才”[16]。
批判封建主义仍然是建国后国民性改造的重要内容,但从毛泽东的主观认识程度看,他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有时甚至冲淡了反封建的力度。事实上,建国后历次伤筋动骨的批判,主要矛头是对准资本主义的。从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50年代中期的反“右派”运动,50年代末的反“右倾”运动;从60年代初的“反修防修”运动,到文革初的“斗批改”运动,文革后期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等等,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改造的力度从思想批判到群众运动、政治斗争到暴力性的阶级斗争。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国民性改造的内容范式平添了复杂性,一方面仍要完成资产阶级启蒙的任务,清除封建主义传统对国民性的影响;一方面又要彻底批判已经走向反动的资本主义,反修防修,从国家角度防止和平演变,从国民角度防止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诸如惟利是图等劣性的影响。
三、国民性改造客体的转换:改造的彻底性就是主体的客体化吗
客体是指与主体相对而言的国民性改造的对象。欧美启蒙知识分子,一般都有着一种救世的悲悯性质的宗教情怀,在神权崩塌之后充当了救世主的角色。日本也与此相似,启蒙知识分子在“国家神道观”破灭之后以一种先知的身份自居。那么,实际上,主体这种状况决定了客体的状况,即启蒙知识分子一般不把自己作为国民性改造的对象或客体。
这种情况,在中国资产阶级启蒙知识分子那里也同样如此。纵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到邹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留下的思想资料,很难看到对自己需要改造的自觉。而康有为,虽然在妇女的国民性改造问题上抓到了根本,认为夫权和封建家族宗法关系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他提倡一夫一妻制,“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夫妇之道”[17]。但在实际生活中,自己却三妻四妾浑然不觉。这不免成为世人非难启蒙思想家们的口实。这种不觉自身需要改造的救世悲悯情怀产生了启蒙思想家的另一层历史局限。那就是,把国民性改造仅仅作为救亡和阶级解放的工具和手段,并且认为这种工具和手段的作用只能由启蒙思想家来实现,改造客体的觉醒,需要启蒙思想家的鼓吹和把握。他们大多是从“强国保种”的角度出发来提倡国民性改造。
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到了鲁迅开始了范式的转换。鲁迅开始意识到自己也是这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改造别人首先得改造自己。他常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18]他对国民性弱点的认识与批判,是从自己的实际体验出发的,是在“煮自己的肉”[19],作历史的中间物,以期使国人“在进化的链子上”实现新旧蜕变。他认识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为的就是使下一代“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0]鲁迅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中自觉将自己置于国民性改造客体的第一人。
正是为了鲁迅的探索,建国后,作为一生都非常崇敬鲁迅的中共领袖毛泽东,接过了鲁迅的这一思想火花。毛泽东在1957年3月的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此作了全面的阐发:“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6]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继续他的思路:不仅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人人需要改造;“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6]此后,他又多次讲过自己有许多不足,需要学习之类的话,并多次强调:“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21]较之于鲁迅在黑暗中苦苦摸索解剖自己向夜空呐喊的孤立无助,毛泽东所处的独特地位使他有可能在认识到自身需要改造后将之付诸广大范围的实施。
毛泽东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作无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家人,对身边的人,推而广之,对全国人民,都要求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实现人民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6]。国民性改造主体自觉将自己放在改造客体的位置上,通过自我教育改造实现国民性的现代转换目标,这是建国后国民性改造客体范式的第一层转换。
国民性改造客体范式的第二层转换包括对客体认识的具体化程度及深刻度。在鲁迅之前,启蒙思想家们对于改造客体的认识,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角度的一种宏观认识。这种从民族精神的整体观照的角度来探讨国民性的方式的优点在于,能直接给人们提供一个具体的总体印象;并可从整个民族都已堕落至如此地步这样一种严重状况的强调来唤起国人特别的注意。确实,他们将一种或多种国民劣性的表现斥为全民族的共性,灭种亡国的悲惨前途在很大程度惊醒了一些迷惑着的国民。但是,这种宏观分析也就免不了以偏概全的粗疏。比如,梁启超就曾经把虚伪、狡诈、懒惰、圆滑等笼统地说成是民族性格的特点,然而,他同时又称道劳动人民中普遍存在着诸如刻苦耐劳、诚实正直、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如此一来,颇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嫌。其实,前者只是普遍存在于统治阶级身上的劣根性,并非普遍存在于整个民族。
这种情况到鲁迅开始改变,鲁迅在他的国民性批判著作中,将客体进行了基本的划分,而其批判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其次是农民。他分别揭示了传统知识分子和农民身上的种种劣性,并分别开了药方。但很明显,鲁迅的划分与批判并不完全。
建国后,毛泽东则是按照阶级划分方法,细致地划分了中国的阶级状况,并针对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指出其阶级劣性。比如他说农民“一有机会就讲平均主义”[22],“农民的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22];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批评工人运动中“片面的、狭隘的、近视的所谓工人‘利益’”[3];知识分子的崇美心理与民族奴性,等等。在如此分阶级厘清各自的阶级劣性以外,毛泽东也从整体上对民族精神的缺陷进行了剖析。可以说,建国后以对国民性改造客体认识的具体与深刻程度为特征的第二层次的转换也已基本完成。
四、建国后的国民性改造:一个亟待展开的课题
历史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在建国后实现国民性改造范式的转换;思想发展的逻辑使这种转换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以往国民性改造的经验教训作为历史文化营养在新时期仍应吸收,它涉及到如何有效转换与吸收的具体问题。对具体问题的妥当解决又是保证正确方向的唯一途径。对于建国后国民性改造范式的历史反思,应秉承这一思路才是建设性的,不苛求历史的。
对于建国后知识分子国民性改造主体地位的缺失,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理论无疑有着很大的局限,但知识分子本身也难辞其咎。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鲁迅在内都有一种“原罪感与自卑感,以至由此产生的依附感”[23],它使得在原则立场上坚持了鲁迅精神的胡风在面对被批判时也“绝不声辩”,对法院审判“不请辩护人自己也不辩护,事后我也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我不上诉是从相信党的立场出发的”[24]。关于这点,在1986年1月15日胡风的追悼会上,贾植芳作为一个曾经的“胡风分子”的评说可谓一语中的:“胡风这个人有忠君思想”[25]。在那三十年中,又岂止是胡风,面对批判时又有几个不是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有问题,真心诚意地接受批判和改造呢?作家巴金过后曾反思“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的高高兴兴”,“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26]。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事与愿违的结局?除开知识分子本身的奴性以外,另一原因恐怕就是当思想与权力相结合,该思想又被权力拥有者视为唯一正确的思想时,就产生了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话语霸权”,它使人们对于真理的理解仅限于此一思想而不会出现对该思想的叛逆性的怀疑与挑战。于是便产生了巴金所谓的“奴在心者”的“精神奴隶”。对历史的阐释还不能到此为止。
当然,凡此等等的关于建国后国民性改造的功过得失,是无须规避,但也必须详尽评说的另外的论题;但它不影响此间国民性改造的事实上的存在。同时也可以断言,新中国的成立,就是国民性改造范式转换的开始。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全面改革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开始了社会制度化运行秩序的建设;与此同时,伴随思想解放的春风,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又勃发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制度建设进程中,辅以疗救国民的劣根,实现了国民性改造范式的再次转换。然而,不弄清建国后前三十年国民性改造的状况就无法对改革开放后的国民性改造作出公正、客观、全面的评价。
收稿日期:2001-09-11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范式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鲁迅论文; 毛泽东论文; 梁启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