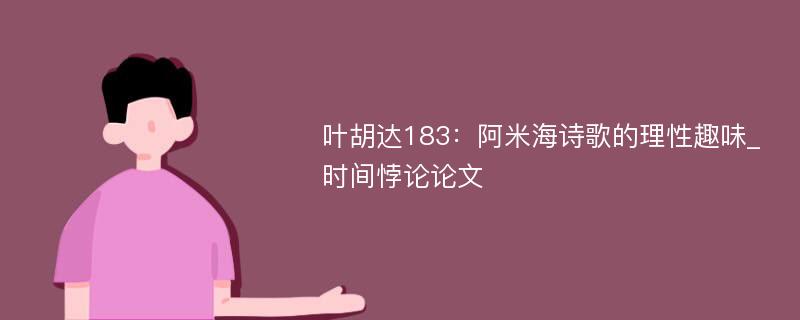
耶胡达#183;阿米亥诗中的理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中论文,阿米论文,耶胡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5)04-0020-06 与新欢幽会的好 时机同样是 安放炸弹的好时机。① 乍一看,好突兀,怎么会从“与新欢幽会”这样的美事联想到“安放炸弹”这样的凶险之事呢?二者之间的相似点何在呢?诗人自有道理: 在季节与季节的 在蓝色的心不在焉中, 卫兵换岗的一丝混乱, 在接缝处。 原来二者都是利用某种间隙、某种机会的隐秘行动。但即便如此,这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到的类比。正所谓会者不难,如果我们了解到诗人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1924-2000)既是个情种又是个战士,那他能作如是想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些都出自他本人真实的体验和记忆。其实,把性与死相提并论在西方文学中是个老传统,阿米亥只不过在《好时机》(“Good Time”)这首寥寥八行的短诗中把所用意象换成了当代的而已。17世纪英国玄学诗人但恩(John Donne)就善于以死亡比性爱,以性爱喻死亡。例如《封圣》(“The Canonization”)一诗中有句云:“任你们怎么骂,我们被爱造就:/骂她是一飞蛾,骂我是另一只;/我们还是蜡烛,自付代价而死。”(31)在17世纪英国,死亡是性爱高潮的一个流行暗喻。时人认为,性爱一次会缩短一天寿命。诗人则以飞蛾扑火,蜡炬成灰的形象表出之。蜡炬亦象征阳具,会自我消耗而亡。 自从艾略特(T.S.Eliot)于1921年发表书评《玄学派诗人》(“The Metaphysical Poets”)以来,以但恩为首的玄学诗人惯用的论理手法——奇喻、悖论、反讽等——就成了英美诗人竞相仿效的时尚,甚至成为学院诗评家评判诗作好坏的一个标准。受艾略特影响的诗人和评论家有奥登(W.H.Auden)、泰特(Allen Tate)、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沃伦(Robert Pen Warren)、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等。阿米亥自称从事诗歌创作之初就受到艾略特和奥登等英语诗人的影响。(232)他营造奇喻和悖论的天赋受到启发,可谓青出于蓝,以至于成为一种思维习惯,给其作品打上了明显的标志。 所谓奇喻,顾名思义,就是令人惊奇的比喻,是玄学诗的特点之一。艾略特指出,但恩……运用一种有时被认为是具有“玄学”特点的技法;一个修辞格被精炼到智巧所能达到的最远地步。……但是在别处我们发现,并非仅仅一个类比的内容的阐释,而是一种通过迅速联想的发展,这要求读者方面有相当的灵敏。(23) 这种具有玄学特点的技法指的就是奇喻,或特称“玄学奇喻”,用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话说,即基于“最不相干的观念被用暴力强拧在一起”的类比或比喻。(Eliot:24)约翰逊还指出,玄学诗人往往“从普通诗歌读者所不大经常造访的学问的幽僻处汲取他们的奇喻”。(Grierson:viii)《约翰·但恩诗集》(The Poems of John Donne,1912)和《17世纪玄学诗选》(Metaphysical Lyrics and Poem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Donne to Butler,1921)的编者格瑞厄森(H.J.C.Grierson)也如是说:“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玄学诗人是在学问中——不是在其自己意识和常识所揭示的,而是在科学和哲学所报导的世界中——寻找灵感的诗人。”(1)例如但恩就喜欢以当时尚未过时的地心说为喻说明爱的崇高或坚贞,例如《热病》(“A Feaver”)、《爱的成长》(“Loves Growth”)、《赠别:不许伤悲》(“A Valediction:Forbidding Mourning”)等;以当时热度未减的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新知比拟爱人身体的部位,如《旭日》(“The Sunne Rising”)、《爱的进程》(“Loves Progress”)等;以中古经院玄学的无稽之谈解释恋爱中灵肉的关系,如《空气与天使》(“Aire and Angels”)、《出神》(“The Extasie”)等。 与玄学诗人不同的是,阿米亥营造奇喻靠的不是书本知识之类的间接经验,而是生活经历之类的直接经验。他的生活经历中有太多的真实事件可以提炼成诗,他只需如实处理应接不暇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为而已。然而其效果同样令人惊叹,又不显得那么牵强附会。 考古学家回家了, 收拾起他们的黑白棒棒。 一切都测量过。 他们丢下他们的线 像吐出的丝网。 古罗马遗址的挖掘现场 坑穴大开仰躺着, 像一个被强奸的女人遗弃 在旷野里。 全都在露天, 尽管她没有尖叫。 这首《隐基底考古季的结束》(“The End of Archaeological Seasons in Ein-Gedi”)第二节中的奇喻意象令人感到震撼、错愕,但细细品味起来,又不得不佩服诗人联想之奇崛,造喻之贴切。 《从前一场伟大的爱》(“Once a Great Love”)一诗开头就是个惊人的奇喻:“从前一场伟大的爱把我的生命切成两段。/前一段在某个别的地方/继续扭动,就像一条被砍成两段的蛇。”随后,诗人笔锋一转,在两行直接陈述之后,又来了个更微妙、更有创意的类比: 岁月的流逝使我平静下来, 给我的心带来痊愈,给我的眼带来休憩。 我就像有人站在 犹大沙漠里,看着一块标志牌: “海平面。” 他看不见海,但他知道。 就像这样,我处处记起你的脸 在你的“脸平面”之前。 这结尾两节中的奇喻在一般读者看来或许有些费解,其实也不过是基于真实生活经验的联想而已。1994年1月的一天,阿米亥夫妇特意驱车带笔者去游览死海。死海是世界上最低湖泊,湖面海拔为负422米。从耶路撒冷沿高速公路一路向西,感觉就像乘飞机下降一般,两耳鼓膜胀得难受。中途停车,见路边一块石碑,上画一水平标志线,线上下分别是阿拉伯文和英文字样:“海平面”,表示从此往下即进入海平面以下。然而该地位于沙漠深处,四周根本看不到海。尽管如此,看到这块石碑上的字,笔者马上就想到了存储在脑海中的遥远的海。同理,诗人在看不见爱人的地方,只要遇到任何有关提示——“你的‘脸平面’’’,就会立即忆想起“你的脸”。“脸平面”当然是个无中生有又有点儿顽皮意味的生造语,被生拉硬扯来与真实的“海平面”相类比,可谓虚实相生,也不无道理。类似的还有《空中小姐》(“Air Hostess”)一诗中的生造语: 空中小姐说熄灭所有吸烟材料, 但她并未特指,香烟、雪茄或烟斗。 我在心里对她说:你拥有美丽的恋爱材料, 我也不特指。 空中小姐所谓的“吸烟材料”被理解为“香烟、雪茄或烟斗”之类用来吸食烟草的材料的概括性名称。可是,何谓“恋爱材料”?诗人故意不特别指明,这倒更令人想象飞跃,想入非非吧。 所谓悖论,即貌似矛盾、似非而是的陈述,多见于哲学和神学著作中。“新批评家”布鲁克斯认为,诗的语言即悖论语言;科学家陈述真理需用毫无悖论的语言,诗人则只能用悖论语言来说明真理。(3)例如但恩的《神学冥想之十四》(“Holy Sonnets XIV”)结尾那两行著名的惊人之语: 然而,我深深爱恋您,也乐于为您所爱, 可是我,却偏偏被许配给您的寇仇死敌; 让我离婚吧,重新解开,或扯断那纽带, 抢走我,归您所有,幽禁起我吧,因为 我永远不会获得自由,除非您奴役我, 我也从不曾保守贞洁,除非您强奸我。(241) 阿米亥同样是制造悖论的高手。他在《一个人没有时间》(“A Man Doesn't Have Time”)的开头如是写道: 一个人没有时间 有时间做一切。 他没有足够季节以有 一个季节实现每个目的。《传道书》 在这一点上错了。 希伯来圣经中据传为所罗门王所作的《传道书》(“Ecclesiastes”)第三章第一至八节云: 凡事都有季节,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收获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新旧约全书》:752—53) 一派老生常谈,阿米亥反其意而用之,顿生陌生化效果,且道出对失常的生存状态的无奈之感。“没有时间/有时间”和“没有足够季节以有/一个季节”不是简单的否定句式,而是矛盾修辞,故而才形成悖论。原因则是有时候人们必须在同一时间做不止一件事。 一个人需要在同一时刻爱和恨, 以同一双眼睛笑和哭, 以同一双手抛掷和捡拾石头, 在战争中制造爱,在爱中制造战争。 仇恨宽恕记忆忘却, 整理和弄乱,吞吃和消化 花无数岁月所做的一切。 一个人没有时间。 当他遗失时他寻找,当他找到时 他忘却,当他忘却时他爱,当他爱时 他开始忘却。 现代人的生活,尤其是现代犹太人的生活,早已不像古代人的生活那样循规蹈矩,起居有常了。传统上,犹太人似乎天生逆反,一向喜欢与上帝、先知、圣贤之类辩论,挑战他们的权威。阿米亥的许多诗正是源于这样的辩论。他十五岁时对犹太人的上帝失去了信仰,这就使他得以以一个深知其底细又敬而远之的叛徒身份与上帝平等对话,言语中往往不乏调侃、抱怨甚至诅咒的意味。他曾说:“我认为,即使我反对历史和上帝,我的历史观和上帝观也是典型的犹太式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学校有时也讲授我的诗的原因。与上帝搏斗,厉声咒骂上帝是一种古老的犹太观念。”(239) 《相对性》(“Relativity”)一诗从题目到内容都不免令人想到《庄子·齐物论》中关于事物相对性的著名论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然而阿米亥不是意在诡辩,而是强调注重常识。 有一艘玩具轮船上面画有波浪。 有一件衣衫上面印着航行的轮船。 有回忆的努力和开花的努力, 有爱的怡然也有死的怡然。 一只四岁的狗等于一个三十五岁的人, 而一只一天大的苍蝇——一个年迈之人 充满记忆。三个小时的思索 好比两分钟的大笑; 一个叫嚷的孩子在游戏中暴露出他的藏身处, 而一个静默的孩子被遗忘。 黑色早已不再是悼亡的颜色: 一位少女把自己挤进一件黑色的比基尼, 厚颜无耻地。 墙上一幅火山图画 使坐在屋里的人们镇静。 一座公墓由于 其死者人数众多而宁静。 庄子借先哲王倪之口设问: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侈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鰌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王先谦:22—23) 以一连串悖论说明万物各有适于自身情况的标准,故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这又不免令人想到爱尔兰诗人叶芝(W.B.Yeats)的《印度人论上帝》(“The Indian upon God”)一诗。 我在潮湿的树木下沿着湖岸漫步而行, 我的魂魄摇荡在暮霭里,双膝深陷在水草中, 我的魂魄摇荡在睡眠和叹息中;看见水鸡 成群湿淋淋在草坡上踱步,又见他们停止 彼此绕圈嬉逐,听那最年老的开口演说: 把世界衔在喙间,把我辈造就得或强或弱者, 是一只不死的水鸡;他居住在那九天之上; 月光洒自他的眼,雨水降自他的翅膀。 我继续向前走不远,听见一朵荷花在高谈: 创造并且统治世界者,他悬挂在一根茎端, 因为我就是依他的形象塑造,这叮咚的潮水 不过是他那广阔的花瓣间一颗滚动的雨滴。 不远之处的黑暗里,一只雄獐抬起他那 满含星光的眼睛,他说:重重天穹的铸造者 是一只高雅的獐鹿;否则的话,请问,他怎能 构想出多愁善感,像我这样的高雅生灵? 我又继续向前走不远,听见一只孔雀说: 创造百草创造千虫创造我悦目的羽毛者 是一只巨大的孔雀,他整夜在我们头顶上面 挥动疲倦的尾羽,上面闪亮着亿万个光斑。(19—20) 类似地,此诗借印度人坎瓦之口,以寓言形式表达了对“上帝的本质”亦即真理的认识,是“叶芝最坚定的信念之一——真理在观者眼中——的早期陈述”。(Unterecker:70)这是印度哲学中常见的一种观念,也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一因多果悖论。而阿米亥所谓的相对性与庄子的诡辩和叶芝的虚拟不同,基本上是出于对人生和世界的直接观察,当然诗人所道是经过其智慧的洞察力滤过的。每一组意象看似信手拈来、互不相干,但同样是在暗示着一个道理,即一切判断都是相对的,都有赖于他者的对照。这与犹太教对上帝的看法有相反也有相通之处。犹太人认为上帝是独一无二的绝对存在,但又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又有了人只能通过返观自身认识上帝的说法,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悖论。一切都是相对的、变易的,就连上帝也不例外。阿米亥与叶芝一样,也是对一神教失去信仰者,所以,在诗的末节,他点明了这番理论的用意: 一个人告诉我 他要南下去西奈,因为 他想独自与他的上帝相处: 我警告了他。 有人指出,阿米亥往往“使我们从联想跳跃到联想,从暗喻跳跃到暗喻——最终抵达理解的静默”。(Locher:21)此诗就是一个典型之例,诗人的惯用技巧由此可见一斑。 在《上帝的命运》(“God's Fate”)一诗中,阿米亥用近乎怜悯的反讽口吻道出了上帝在现代人心目中的真实地位。 上帝的命运 树木、石头、太阳和月亮的命运。 这些他们已不再崇拜, 一旦他们开始信仰上帝。 但他是被强留与我们共处的, 一如树木,一如石头 太阳、月亮和星星。 全能的上帝居然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这犹如说“全能的上帝造不出他举不起的石头”,同样是个悖论。 有人说,阿米亥的诗没有诗学理论,只依赖诗人的丰富经历,就能够以“诚实”的自白方式道出人世间的真理。(Wieseltier:24)这话没错。从以上的引证分析可以看出,他的诗原料充足,只要稍加料理就会好吃——用烹调为喻来说(阿米亥曾告诉笔者,他喜欢烹调)。他的烹调技艺也可谓炉火纯青,做出的东西几近天然去雕饰的境界,但重复使用得过多,有时也不免给人以烂熟之感。在他的诗里,思想是具体可感的,可谓情理交融,浑然一体,相较但恩和叶芝,更少些说理论辩的味道。艾略特说,英诗在17世纪玄学诗人之后发生了“情思分离”现象,此后一直未复元;后来的诗人虽有思想,但不再能“像闻到玫瑰花香那样直接感受到思想”。(Eliot:27)到了阿米亥这里,可以说,诗又恢复到了但恩甚至以前时代的境界了。而他的诗又与文胜于质的当代英美诗有所不同。诚如罗森特尔(M.L.Rosenthal)评论阿米亥的诗时所说:“它再次证明,当真实事物出现时,时髦的批评术语——‘后现代主义’、‘反诗学’等等——都毫无用处了。”(25)既然当代西方文论对于阿米亥的诗无能为力,那我们倒不妨试以中国古典文论。南宋理学家包恢日:“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有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犹造化自然之声也。”(717)此论阿米亥的诗或可当之。 阿米亥是公认的以色列最优秀的希伯来语诗人,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著有诗集十余种,作品被译入三十余种语言。据说以色列大学生应征上前线时,每人自备的装备是一杆步枪和一本阿米亥诗集,由此可见其诗受欢迎的程度。1991年《外国文学》双月刊第一期发表拙译阿米亥诗十五首之前,我国一般读者对他几乎还一无所知;现在他在我国可以说已成为最受欢迎的外国诗人之一了。拙译《耶路撒冷之歌:耶胡达·阿米亥诗选》(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收录译诗182首,是国内第一本汉译阿米亥诗集。后经增订,更名为《耶胡达·阿米亥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再版,增加新译诗64首,共收录译诗246首。这两版译诗集对向我国读者介绍这位风格独特的诗人起到了一定作用。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第三版《耶胡达·阿米亥诗选》则收录译诗多达573首,将是对这位大诗人的一次最全面的介绍。 ①本文所引用阿米亥诗译文均出自傅浩译第三版《耶胡达·阿米亥诗选》(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