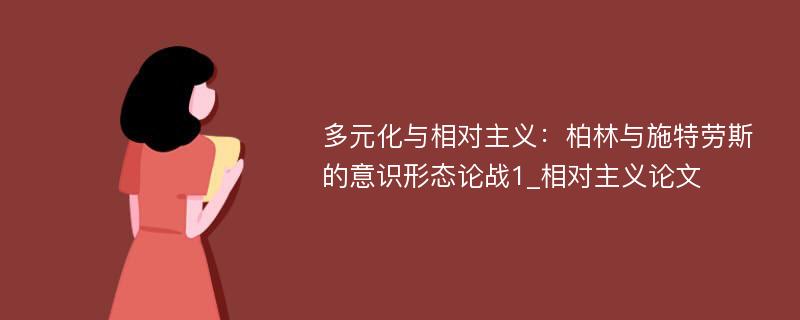
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林与施特劳斯的思想争论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施特劳斯论文,相对主义论文,主义论文,思想论文,伯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4)2-0032-09
1961年,列奥·施特劳斯在一篇数十年来为人所淡忘的文章《相对主义》②中对以赛亚·伯林的传世经典之作《两种自由概念》③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评。他忧虑地指出,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是“自由主义危机的范本”④因为伯林的自由主义抛弃了绝对主义,从而走向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却是20世纪极权主义的根源。因此,伯林的自由主义暗藏着极权主义的危险。
然而,伯林晚年似乎对施特劳斯的批评不以为然,他语露不屑地言道:“我无法答复他,因为他已经在其坟墓中了,而我对他的众多信徒丝毫提不起兴趣。”⑤但是,伯林并非真的对施特劳斯的批评缄默不语,其实他早在分散于各处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系统的回答。而且,伯林还曾斩钉截铁地反驳其批评者道:“我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⑥
那么,伯林到底是不是相对主义者呢?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伯林研究的两大焦点问题之一。⑦学术界就此主要形成了两大阵营:第一个阵营认为伯林是相对主义者,他的多元主义只是相对主义的某种类型,主要代表人物是施特劳斯、潘格尔(Thomas Pangle)⑧、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⑨、比尔格拉米(Akeel Bilgrami)⑩、刘小枫(11)等;第二个阵营认为伯林不是相对主义者,他的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不同,主要代表人物是加利波(Claude J.Galipeau)(12)、卢克斯(Steven Lukes)(13)、费雷尔(Jason Ferrell)(14)、克劳德(George Crowder)(15)、裘尼斯与哈代(Joshua Cherniss and Henry Hardy)(16)、钱永祥(17)等。
就目前的文献而言,刘小枫与钱永祥对伯林与施特劳斯之间的争论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梳理,两位学者的观点恰恰相反。刘小枫的立场沿袭施特劳斯,认为伯林的多元主义是一种相对主义;而钱永祥则认为刘小枫混淆了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本文将对刘小枫的观点提出批评,并对钱永祥的观点进行补充,从而论证伯林的多元主义不是一种相对主义。本文的论证脉络将采取两条路径来展开:第一条路径是伯林文本中明言的论证,伯林认为相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主观性与不可理解性,而他的多元主义的核心特征却是客观性与可理解性。第二条路径是伯林文本中隐含的论证,施特劳斯所理解的相对主义的核心特征不是伯林所谓的主观性与不可理解性,而是主观性、特殊性与不可评价性,而伯林的多元主义的核心特征却包含了普遍性与可评价性。因此伯林的多元主义不是相对主义。
一、伯林反施特劳斯:客观性与可理解性
施特劳斯认为伯林是相对主义者,伯林的多元主义是一种相对主义,但是,伯林明确表示自己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的多元主义不是相对主义(18)。伯林反驳相对主义的第一条路径是其明言的路径,即他认为相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主观性与不可理解性,而他的多元主义的核心特征却是客观性与可理解性,因此多元主义不是相对主义。
伯林区分了两种版本的相对主义,第一种是强势版本的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以事实判断为核心,认为我们无法获取关于事实的客观知识,“因为一切信念都是被其所处的社会系统的位置所决定的,并且因此而被理论家有意或无意的兴趣所决定,抑或被其所属的团体或阶级的兴趣所决定”(19)。第二种是弱势版本的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以价值判断为核心,认为我们无法获取关于价值的客观知识(20),其思想渊源是德意志浪漫非理性主义、叔本华与尼采的形而上学等。(21)
伯林所要讨论的不是第一种相对主义,而是第二种相对主义。弱势版本的相对主义有两个核心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主观性(subjectivity),即一切价值都是主观的与相对的。因为我们的价值与我们所处的历史、语言、环境等紧密相关,我们的历史、语言与环境等因素塑造了我们的价值,因此,价值是相对于我们所处的历史、语言与环境等因素来说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一种环境有一种环境的价值,所以,其逻辑结果是,“一切判断都是相对的,一切评价都是主观的”(22),易言之,“所有客观性都是主观的,都是相对于其自身所处的时空而言的;……无物永恒,一切皆流。”(23)第二个特征是不可理解性(unintelligibility),即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与不同个体之间的不同价值是无法相互理解的。(24)相对主义所能言的只能是:“我爱喝咖啡,你爱喝香槟。我们有不同的品味。此外我们再也无法说什么了。”(25)因为在伯林看来,我们之间的品味是无法相互理解的,你无法理解我为什么爱喝咖啡,正如我无法理解你为什么爱喝香槟,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使我们能够互相理解。
针对相对主义的这两个核心特征,伯林的反驳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客观性(objectivity),即并非所有价值都是主观与相对的,有些价值是客观的。因为“倘若没有什么(判断)是客观的,倘若客观性在原则上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主观’与‘客观’这对相反的术语就会毫无意义,因为一切互相关联的东西都是同起同灭的”(26)。人类的价值不止一个,而是有许多,价值是多元的,并且这些价值都是客观的,或者是同等客观的,这些客观价值之间常常是互相冲突的。那么,如果存在着客观价值,这些客观价值是什么呢?(27)从伯林的诸多文本中可以分析出,自由、平等、正义、和平与安全等价值均是客观价值。(28)客观价值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并非如相对主义所言,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都是主观的,因此就没有什么客观价值了。
如果多元价值是客观价值,那么,客观价值存在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客观价值存在的依据来自伯林的人性观:“我认为这些价值是客观的——这就是说,它们的本性以及对它们的追求,是人之为人的组成部分,而这是客观给予的。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而不是猫狗桌椅,这个事实是客观事实。而当人依旧是人时,人就会追求某些特定的价值,并且只追求这些价值,这也是上述客观事实的组成部分。”(29)因此,“客观的”意味着这些价值是人之为人的组成部分,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一个正常人都会认可的东西,“它们广为接受,并且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真实本性之中……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正常人的本质组成部分”(30)。而且,伯林刻意解释了何为他所理解的正常人:“当我说一个人是正常人的时候,我的意思一部分是,他不可能轻易地破坏这些规则而毫不顾忌他人的憎恶”(31),也就是说,这些多元价值不但构成了正常人的本质,而且构成了人的本质,他不可能轻易地放弃这些价值,否则他就不是一个正常人,甚至不是人类了。概言之,这种被伯林做了特殊处理的人性观赋予了客观价值之客观性。
第二个部分是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即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与不同个体之间的不同价值是可以互相理解的。不可否认,人类的诸多价值是在其自身所处的时代与文化等语境中逐步而缓慢地形成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也被它们所塑造,并且被它们所改变,这些多元价值和其时代与文化等语境息息相关,但是,这并不是说,多元价值是被其所处的时代与文化等语境所决定,犹如居住在“没有窗户的盒子里”,因而人类无法超越其自身所处的时代与文化等语境,从而无法理解其他异质文化领域中的价值。(32)伯林并不同意相对主义的不可理解性的主张,他认为,一个人理解另一个不同于自己的文化领域中的价值是可能的,即便纳粹主义也是可以理解的。(33)
那么,理解是如何可能的呢?人类凭什么去理解异质文化中的价值,何况他们的价值可能与我们的价值是激烈冲突的?伯林认为,理解异质文化需要一种特殊的人类官能(faculty)——“移情”(empathy)的能力。伯林的“移情”概念来源于维柯与赫尔德,(34)维柯称之为fantasia(35),而赫尔德则称之为Einfühlen(36),它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想象性洞察能力(imaginative insight)或者想象性的同情理解能力(imaginative sympathy)。具体而言,移情就是想象性地把自己置身于他人的时代与文化语境之中,进入到他人的思想世界与情感世界之中,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人在他自己的整个语境中是如何思考的,是如何看待各种问题的,他人的价值观又是如何形成的,这些价值观为什么与我的不同。建立在这种想象性的洞察力基础之上,我不是把你当作我自己,像我自己理解我自己一样来理解你。相反,我把我自己当作你,并且像你自己理解你自己一样去理解你,或者说,用你的眼睛而不是我的眼睛来看你自己,以此来破译(decipher)你的情感与思想世界中被你的整个语境加密(enciphered)了的神秘信息。即便你所处的时代与文化语境和我的时代与文化语境截然不同,即便你我的价值观激烈冲突,即便你是来自远古的原始人,即便你是来自偏远蛮荒之地的部落民族,只要我拥有足够的想象力与充分的耐心,我就可以努力地进入你的世界来理解你。如果这种理解是不可能的,那么,过去就永远僵死在过去,甚至人类学与历史学这两门学科也将从此消失,而更可怕的是,一切学术都将毫无意义,因为学术就是建立在这种想象性地理解他人的基础之上的。此外,理解另一种文化中的价值并不代表认可这种文化中的价值,例如,我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为什么你会为了平等而牺牲自由,但这并不代表我认可你的这种观点,或许在我看来,自由是不能以平等的名义来剥夺的,但这依旧不会妨碍我理解你,只要我有足够的想象力。(37)
此外,要使理解成为可能,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必须有一座架通双方心灵世界的桥梁,光有移情的能力似乎并不足以使理解得以可能。一个人可能有充分的移情能力,但是他可能依旧无法进入对方的心灵世界,例如,一个中国人渴望理解一个英国人的心灵世界,但是他不懂英语,而且也不懂英国人的肢体语言所表达的具体含义,这样,即便他有充分的移情能力,他可能也无法进入对方的心灵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若要使移情能力发生效力,似乎需要某种中介,需要一座桥梁来架通它们,语言就是这样一座桥梁。伯林认为,“如果任何事情都是被‘人类’这个术语所赋予意义的话,那么,所有这些人类一定充分共享(common)着某些东西而使理解成为可能,理解是这样子的:通过充分的努力进行想象,去理解这个世界对于居住于偏远时空的造物来说是什么样子的,去理解谁在践行着这类仪式,谁在使用着这类词汇,谁创造了这类艺术作品,而这类东西都是人类表达自我的天然形式,他们正是凭借着这类东西使自己得以理解与解释自己所处的世界。”(38)换言之,只有双方共享着某些东西,双方的互相理解才能真正开始,移情才真正开始发生效力。因此,移情能力发生其效力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共享着某些东西。
那么,哪些共享的东西使移情得以可能呢?伯林认为是共通的人性(common human nature)(39)使得人类之间的互相理解得以可能。虽然各个时空中的人性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但是,人类也共享着某些共通的人性,共通的人性赋予人类某些共通的“基本范畴”(basic categories)、“人类的基本目标”(basic human goals)、“共通之处”(common ground)、“共通的视域”(common horizon)以及“共通的价值”(common values)(40)。伯林认为,即便相对主义也无法排除我们共享着某些共通的预设(common assumptions),“我们可以正确无误地把这个共通之处称为客观的,正是这个共通之处使我们能够确定,其他人也是人,其他文明也是开化的”(41)。这个共通之处使我们能够互相理解,互相沟通,如果这个共通之处丧失了,那么人类之间的理解就是不可能的。伯林言道:“不同时空中的文化之所以能够互相沟通(intercommunication),正是因为使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对人类来说都是共通的(common),而且也正是这种共通性成为人类之间的桥梁。”(42)伯林论述共通的人性的方式,与上述的人性观相似。他主张,共通的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不可否定的。如果没有这些共通的人性,人就不是人了。只要人还是人,那么人类就互相分享着这份共通的人性。因此,移情的能力,通过共通的人性以及建立在共通的人性基础之上的共通视域,得以穿越不同时空的不同文化壁垒,最终使人类之间的互相理解得以可能。
基于以上的分析,伯林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相对主义宣称,一切价值都是主观的,但是伯林认为,有些价值是客观的,这些价值的客观性是人性赋予的;同时,相对主义认为,不同文化领域中的价值是无法互相理解的,但是伯林认为,人类通过移情的能力、共通的人性与共通的视域,可以理解异质文化领域中的价值。
二、伯林反施特劳斯:普遍性与可评价性
伯林论证自己不是相对主义者诉诸的是相对主义的两个核心特征——主观性与不可理解性,然而,施特劳斯对相对主义的界定却跟伯林不同。施特劳斯理解的相对主义是从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演化而来的,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思潮孕育了相对主义,并且最终把人类推向虚无主义的深渊。在施特劳斯看来,相对主义有三个核心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主观性;第二个特征是特殊性,即不存在普遍价值,一切价值都是相对于特定的时代与特定的文化来说的;第三个特征是不可评价性,即价值判断已经不再可能了。第一个特征与第二个特征结合起来导致了第三个特征。
施特劳斯指出相对主义的特征是主观性,并且这种主观性导致了价值判断的不可能性,最终走向了虚无主义。他在《相对主义》一文中如此界定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目的都是相对于选择者而言的,因而都是平等的”。(43)正是因为所有目的都是相对于选择者而言,所以所有目的都是主观的。这个观点更加清晰地表述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历史的标准……无法宣称历史进程背后的神圣权利赋予其神圣性。留下的仅有的标准(the only standards)具有一种纯粹的主观性,这些标准只能从个体的自由选择中得到支持,此外别无其他。因此,没有客观的标准允许我们区分好的选择与差的选择。历史主义的结局就是虚无主义……”(44)而且,历史主义也反对普遍性,从而强调特殊性。历史主义认为“具有地方性与时间性的事物优越于普遍的事物”(45),并且,普遍性原则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特殊性原则,而特殊性原则是相对于“特殊时代或特殊民族”(46)而言的,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已经丧失了全部有效性。而客观性与普遍性被取消的悲剧性结果是食人者的社会与文明的社会具有同等的正当性:“……所有社会都有其理想,食人者的社会与文明的社会同样都有。如果各种原则被一个社会所接受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其正当的话,那么同类相食的原则跟文明生活的原则就同样站得住脚,且同样正确了。从这个观点来看,前者的原则当然不能被当作邪恶的而加以拒斥。”(47)既然没有普遍的标准来判断好坏对错,那么,我们就无法判断食人者的社会与文明的社会孰好孰坏。要而言之,相对主义的困境是价值判断已经不可能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高贵的,什么是低贱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野蛮的,什么是仁慈的;这一切价值判断都已经烟消云散了,人类再也无法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了。我们可以对纳粹集中营做出事实性的描述与解释,但是,我们不能下判断说纳粹集中营是野蛮人的行径。反过来说,我们甚至同样也无法把帮助弱势群体的行为判断为善良,更加无法把宽恕他人的错误的行为视为仁慈。“每一种偏好,无论是邪恶的、卑鄙的,还是无辜的,都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被判定为跟任何其他偏好是同样正当的。”(48)
而伯林似乎没有特别针对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性与不可评价性做出进一步的论述。主观性仅仅是主观主义的核心主张,而不是所有相对主义的主张。同样,可理解性也只是认识相对主义(cognitive relativism)的核心主张,而不是所有相对主义的主张。即便某种相对主义(例如价值相对主义)承认有些价值是客观的,并且也是可以互相理解的,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够把这种相对主义排除出相对主义的阵营,主观主义与认识相对主义之外的其他相对主义同样也可以承认客观性与可理解性。因此,伯林上述的批驳并不那么有力。
价值相对主义的核心特征恰恰是施特劳斯所理解的特殊性与不可评价性,其基本表述是,各种价值之间的好坏对错,都是相对于它们所处的特殊的时代、文化与语境等因素而言的,没有什么普遍的标准用来判断它们之间的好坏对错。(49)因此,若要进一步证明伯林不是相对主义者,就应当为他的弱势版本的相对主义额外加上两个特征:第一是没有普遍价值,价值的好坏对错都是相对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个体等因素而言的,因此,第二是价值判断不可能了,我们再也无法用一条普遍的价值标尺来丈量各种观点、态度与行为等之间的好坏对错了。然后,再进一步证明伯林相信普遍价值与价值判断的可能性。尽管伯林没有特别针对这两部分撰文论述,但是,我们依旧可以从伯林分散在各部论文集中的文字背后提炼出他的这两部分内容。(50)
伯林反驳相对主义的第二条路径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普遍性,即普遍价值是存在的。贾汉贝格鲁曾问伯林:“您不是认为普遍性原则与文化相对主义是对立的吗?”伯林答曰:“我不这样认为。民族之间以及社会之间的差异可能被夸大了。我们所知的文化中没有一种文化缺乏善与恶、真与假的观念。例如勇敢,就我们目前所见,它在我们所知的每一个社会中都是被赞美的。普遍价值是存在的。这是关于人类的经验事实,这就是莱布尼茨所谓的事实真理,而非理性真理。这些价值是大多数人类在大多数地域与环境中,并且在差不多所有时代实际上都共同(common)主张的价值,不管是有意无意,还是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以及行动之中。”(51)
共通价值都是普遍的,并且是客观的,是整个人类的价值交集。即便是人类的差异性也无法掩盖人类的共通性这个事实,只要人依旧是人,那么,人类总是分享着某种共通性以维系对人类这个族群的最低限度的认同:“关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不同社会中的人民历经时间长河依旧有着广泛的共识。传统、观点与态度是千差万别的(different),这当然没错,但是,一般性原则(general principles)依旧可以穿越众多需求而存在。”(52)当然,人类的共通价值也不能像人类的异质价值(different values)那样被过分夸大,以至于互相淹没对方的存在,共通价值与异质价值都存在于人类世界上。共通价值是“在可以考证的历史当中,大多数人都会坚持的价值”,否则,人类社会难以持续维系下去,在这个意义上,共通价值是社会赖以正常运行下去的最底线。(53)贾汉贝格鲁还特别问过伯林,问他是否认为有普遍的道德准则,伯林明确答复普遍的道德准则是有的,“我所相信的道德准则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国家,并且在非常长的时间里都遵守的道德准则。接受这点,使我们能够共同生活”(54)。也就是说,共通的道德是普遍的,是隐含在人类共同生活这个前提之下的,人类共同生活这个经验性事实赋予了共通价值之普遍性。此外,伯林还认为,人权也是普遍的,人权之所以是普遍的,也是因为人类若要共同生活下去,那么就必须认可人权,人权是唯一正当并且唯一让人能够容忍的共同生活下去的方式。(55)并且,人权也是共通的人性所赋予的:“人权的观念建立在下列真实的信仰之上,即存在着某些善(自由、正义、追求幸福、真诚与爱),这些善符合所有人类本身的利益,而不是符合作为这个或那个民族、宗教、职业、性格的成员的利益。……有些东西是人类本身所要求的,不是因为他们是法国人、德国人、中世纪学者或杂货商,而是因为他们过着男人和女人的生活。”(56)
第二部分是可评价性,即价值判断是可能的。因为人类关于好坏对错存在着广泛的共识,每个社会都会赞美勇敢,(57)同样,“如今,没有人会为奴役辩护,没有人会为在宗教仪式上杀人辩护,没有人会为纳粹的毒气室辩护,没有人会为出于快感、利益抑或政治目的而折磨人类辩护,没有人会为法俄革命中所要求的孩子有义务控诉其父母辩护,也没有人会为毫无情由的杀戮(mindless killing)辩护”(58)。所以,好坏对错之间是可以进行价值判断的,人类对好坏对错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共识,普遍的共通价值本身蕴含着价值判断的可能性。
价值判断的可能性还可以从可理解性中推出来。伯林之所以认为不同文化以及不同时代之间是可以理解的,是因为人类具有移情的能力,人类可以凭借其自身的想象性洞察力,设身处地地进入远古时代抑或异质文化,从而得以理解这些时代抑或文化何以是如此形成的,何以会奉行与我们不同的价值观。正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移情的方式去理解对方,我们也可以依此而赞赏对方的价值,或者谴责对方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移情的理解开放出了批判(criticise)的可能性,也即开放出了价值判断的可能性。(59)而移情的理解又是共通的人性赋予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共通的人性赋予了价值判断的可能性:“我们强迫孩子接受教育,我们禁止公开执行死刑。这些确实都是对自由的约束。我们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比之于强迫所施加的限制程度,无知、野蛮的教育抑或残忍的快感与兴奋是更糟糕的。而这个判断又相应地基于我们如何确定善恶,亦即,基于我们的道德、宗教、思想、经济与美学价值,而这又相应地与我们的人类观(conception of man)紧密相关,与人类本性的基本需求(the basic demands of his nature)紧密相关。换言之,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基于我们对何为圆满人生的想象(vision of what constitutes a fulfilled human life),正是这个想象有意无意地指导着我们。”(60)
并且,当伯林说价值是多元的时候,他同时暗含或者说预设了一个逻辑前提,即多元价值指的是价值,而不是没有价值的非价值,这是多元主义区别于相对主义的关键。伯林的价值冲突案例都是自由、平等、正义、仁慈等普遍价值,而从来不是自由与奴役、正义与非正义等。相对主义认为自由与奴役之间的好坏对错是无法判断的,因为价值判断的普遍标准丧失了。但是,伯林的多元主义却认为自由与奴役之间的好坏对错是可以判断的,无法判断的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高下优劣。因此,价值不是指纳粹集中营里的杀戮行为,不是指苏联大清洗的野蛮行径,不是指施特劳斯所举的食人者同类相食的例子,也不是指活人献祭的行为。这些都不是价值,而是没有价值的非价值,是可以批判的,是可以评价的,是可以大声谴责的。
施特劳斯说,相对主义的困境是好坏对错再也无法判断了。但是,伯林却认为,多元主义不是相对主义。在多元主义看来,好坏对错是可以判断的,我们可以判断恐怖分子是灭绝人性的,我们也可以判断勇敢是值得赞美的,不能判断的是,好与好之间到底哪个更好,价值与价值之间到底哪个更具有优先性。我们不能判断自由是否比平等更具有优先性,我们也不能判断正义是否比仁慈更可取,同样,我们也无法判断宽恕是否比勇敢更重要。因为我们无法像功利主义那样找到一个共同的价值天平,来称量到底自由重一些,还是平等重一些。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无法在好坏对错之间做出价值判断。价值之间的相对有效,指的是价值之间的相对有效性,而不是价值与非价值之间的相对有效性。在自由与平等这两种价值之间,我们无法确定自由比平等更具有优越性,也无法确定平等比自由更具有优越性,两者之间是无法排序的,因此,自由对于平等,平等对于自由,都是相对有效的。我们不能用功利主义的方式宣称,由于自由值五元,平等值十元,所以平等比自由更有优越性。然而,自由与奴役之间却可以清晰界分。在伯林看来,自由高于奴役,天堂优于地狱,这些都是可以进行价值判断的。
相对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好坏对错都是相对的,因此好坏对错无法区分,而伯林的多元主义则认为好坏对错是截然分明的,不能分辨的只是好与好中哪个更好,好与好之间是相对有效的,伯林承认相对价值,但是否认相对主义。
在伯林与施特劳斯的思想争论中,施特劳斯认为伯林的多元主义是一种相对主义,因此,他的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危机的象征。但是,伯林却明确宣称自己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从以上分析可知,伯林的文本中有两条路径来澄清自己的多元主义不是相对主义:第一条路径是客观性与可理解性路径,即伯林所理解的相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主观性与不可理解性,而伯林的多元主义的核心特征却是客观性与可理解性,因此他的多元主义不是相对主义;第二条路径是普遍性与可评价性路径,即施特劳斯所理解的相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主观性、特殊性与不可评价性,而伯林的多元主义的核心特征确是普遍性与可评价性,因此他的多元主义不是相对主义。正如施特劳斯所言,伯林的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是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的中间立场,但是,施特劳斯认为伯林的这个中间立场是不可能的。(61)然而,施特劳斯的这个论断有待商榷。正是因为多元主义认为价值与非价值之间的好坏性是可以判断的,所以多元主义不同于相对主义;正是因为价值与价值之间的优先性是无法判断的,所以多元主义不同于一元主义;正是因为多元主义宣称普遍价值的存在,但同时跟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价值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使之区别于绝对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多元主义是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外的第三种立场。
根据施特劳斯的观点,相对主义是极权主义的根源;而根据伯林的观点,绝对主义(一元主义)是极权主义的根源。这样,无论相对主义,还是绝对主义都潜藏着极权主义的危险。而正是因为多元主义是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的中间立场,多元主义也许是极权主义黑夜的曙光。
注释:
①本文的写作得到刘擎教授、许纪霖教授、邓正来教授以及林尚立教授的指导与鼓励,并得到顾霄容女士的指正。本文还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使我在美访学期间可以便利地利用英文文献,特此感谢。
②Leo Strauss,“Relativism,” in Thomas Pangle (ed.),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p.13-26.First published in Leo Strauss,“Relativism,” in Helmut Schoeck and James Wilhelm Wiggins (eds.),Relativism and the Study of Man,Princeton:D.Van Nostrand,1961,pp.135-57.
③Isaiah Berlin,“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Henry Hardy (ed.),Liber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66-217.
④Strauss,“Relativism,” p.17.
⑤Isaiah Berlin and Ramin Jahanbegloo,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New York:MacMillan,1991,p.32.
⑥Isaiah Berlin,The Power of Idea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11.
⑦伯林研究的两大焦点问题是:第一,伯林的多元主义是不是相对主义;第二,伯林的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否能够兼容。
⑧Thomas L Pangle,Leo Strauss: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egac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p.19.潘格尔一开始也遵循施特劳斯的论述步骤,但是,他引出伯林自相矛盾的方式与施特劳斯略有不同。施特劳斯认为伯林的自相矛盾是“相对主义似乎需要某种绝对主义”。而潘格尔则认为伯林的自相矛盾是,一方面,伯林认为消极自由的疆域是绝对的,另一方面则认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都是同等绝对的,那么,积极自由就有同等的权利否弃消极自由,如果消极自由可以用积极自由的方式来否弃,消极自由的疆界又如何继续保持其绝对性呢?
⑨Arnaldo Momigliano,“On the Pioneer Trail,”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23,No.11,1976.
⑩Akeel Bilgrami,“Secularism and Relativism,” boundary 2,Vol.31,No.2,2004.
(11)参刘小枫:《刺猬的温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1,184,186,223-224页
(12)Claude J.Galipeau,“Pluralism,Freedom,and Human Nature,” in Isaiah Berlin's Liberali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pp.48-83.
(13)Steven Lukes,“Must Pluralists Be Relativists?” in Liberals and Cannibals:The Implications of Diversity,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3,pp.100-06.
(14)Jason Ferrell,“The Alleged Relativism of Isaiah Berlin,”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Vol.11,No.1,2008.
(15)George Crowder,“Pluralism,Relativism and Liberalism in Isaiah Berli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e Australasian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Tasmania Hobart,2003,George Crowder,Isaiah Berlin:Liberty,Pluralism and Liberalism,Cambridge,UK:Polity,2004,pp.114-23.[澳]乔治·克劳德:《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会,2006年
(16)Joshua Cherniss and Henry Hardy,“Isaiah Berlin,” (Fall 2010 Edition) May 25,2010 [cited September 1 2013]; available from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0/entries/berlin/,Henry Hardy,“Isaiah Berlin's Key Idea,” 2000 [cited September 1 2013]; available from http://berlin.wolf.ox.ac.uk/writings_on_ib/hhonib/isaiah_berlin's_key_idea.html.
(17)钱永祥:《多元论与美好生活:试探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两项误解》,邓正来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一辑,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1-77页。
(18)Isaiah Berlin,Liber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45-54.Isaiah Berlin,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Pimlico 2003,Berlin The Power of Ideas,pp.1-23.
(19)(21)Berlin,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p.74,p.77.
(20)Ibid.,pp.74-81,Berlin,Liberty,p.146.
(22)(26)Berlin,Liberty,p.146,153.
(23)Ibid.,p.147.
(24)克劳德在论证伯林不是相对主义者之时,认为相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我们无法评价或理解其他文化领域中的价值,即不可评价性与不可理解性,而在《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一书中则加上了相对主义反普遍性的特征。我认为,克劳德的概括并没有错,伯林的确谈到了价值的不可评价性与反普遍性,但是,伯林在批驳相对主义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把不可评价性与反普遍性当做核心特征来批驳,而仅仅稍带提及,因此在重构伯林的反相对主义论证时,我并不把不可评价性与反普遍性当做伯林的核心论证来处理,对不可评价性与反普遍性的讨论将在下一部分详细展开。要特别指出的是,克劳德对相对主义的把握并不特别符合伯林自己的界定,他没有提到弱势与强势版本相对主义的区分,也没有把弱势版本相对主义的主观性特征作为核心特征来处理,see Crowder,“Pluralism,Relativism and Liberalism in Isaiah Berlin.”,亦参克劳德:《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第52-54页。裘尼斯与哈代合作完成的《以赛亚·伯林》一文则把伯林理解的相对主义简单地归结为主观主义,而没有注意到,伯林除了强调主观主义之外,同时把文化相对主义与历史主义也纳入到相对主义的整体理解中了。而奇怪的是,他们把伯林理解的相对主义归结为主观主义,却没有注意到伯林文本中反主观性的论证。同时,他们也没有注意到伯林对弱势版本与强势版本相对主义的区分,因此,他们的理解也不够充分,解释也不够贴近伯林的文本,see Cherniss and Hardy,“Isaiah Berlin”.
(25)Berlin,The Crooked Timk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p.11.Berlin and Jahanbegloo,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p.107.Berlin,The Power of Ideas,pp.11-12.
(27)Berlin,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pp.11-12,79-84,87.Berlin.The Power of Ideas,p. 12.
(28)这些客观价值中有一类比较特殊,就是共通价值(common values),有关共通价值的内容,我将在下文讨论。
(29)(32)Berlin,The Power of Ideas,p.12,p.60.
(30)Berlin,Liberty,p.210,Berlin,The Power of Ideas,p.12.
(31)Berlin,Liberty,p.211.
(33)Berlin and Jahanbegloo,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p.38.
(34)Berlin,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pp.49-69.Berlin,The Power of Ideas,pp.53-67.Isaiah Berlin,Vico and Herder: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London:Chatto & Windus,1976.Isaiah Berlin,“Vico and the Ideal of the Enlightenment,” Social Research,Vol.43,No.3,1976.Berlin and Jahanbegloo,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pp.37-38.
(35)Berlin,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pp.62-64.Berlin,The Power of Ideas,p.60.
(36)Isaiah Berlin,Against the Current: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79,p.10.Berlin and Jahanbegloo,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pp.37-38.
(37)Berlin,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pp.11,60-62,79-86.Berlin,The Power of Ideas,p.12.Berlin,Liberty,pp.147-52.Berlin and Jahanbegloo,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pp.37-38.Berlin,“Vico and the Ideal of the Enlightenment,”pp.640-53.
(38)Berlin,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p.60.
(39)Common human nature 这个术语出现在伯林的绝笔之作中,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有了common nature,see Berlin,The Power of Ideas,pp.8-9.
(40)Berlin,Liberty,pp.148-52.Berlin,The Power of Ideas,pp.9,12.
(41)Berlin,Liberty,p.152.
(42)Berlin,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p.11.Berlin,The Power of Ideas,p.8.
(43)Strauss,“Relativism,” p.15.
(44)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18.
(45)(46)(47)(48)Ibid.,p.14,p.16,p.3.,pp.42,52.
(49)Swoyer把这种版本的相对主义称为normative relativism。另外一种版本的相对主义是descriptive relativism,描述性相对主义仅仅认为各种不同的群体拥有不同的态度、观点、行为与价值等,它并不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做出价值性的诉求。而规范性相对主义则在价值方面比描述性相对主义走得更远。由于描述性相对主义没有做出价值方面的诉求,所以,本文不会对它加以讨论,仅在此处做出说明,以供参考,see Chris Swoyer,“Relativism,”(Winter 2010 Edition)[cited September 1 2013]; available from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relativism/.
(50)伯林反相对主义的缺陷似乎可以用来解释克劳德的不足之处,克劳德把伯林理解的相对主义界定为无法理解与评价异质价值,而伯林在文中主要强调的是可理解性,很少提到可评价性,而在克劳德的观念中,可评价性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特别突出了这点,但是,伯林提到的客观性却被他忽略了,所以,他在重构伯林的反相对主义论题方面并不全面。
(51)(54)Berlin and Jahanbegloo,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p.37,p.108.
(52)Berlin,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p.18.
(53)Ibid.,p.114.
(55)(56)Ibid.,p.39,pp.11-79.
(57)伯林的每个社会都会赞美勇敢的论断似乎有点过分自信了。例如,一个弱小的幼童勇敢地与歹徒搏斗,以至于喋血街头,死于非命。或许对某些社会来说,这是值得赞美的行为,但是对另外一些社会来说,赞美这种勇敢恐怕就是赞美一种残忍了,这种勇敢无异于自杀。
(58)Berlin,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p.18.
(59)Ibid.,pp.11-79.
(60)Berlin,Liberty,pp.214-15.
(61)Strauss,“Relativism,” p.17.
标签:相对主义论文; 施特劳斯论文; 客观与主观论文; 文化相对主义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人性论文; 客观性论文; 客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