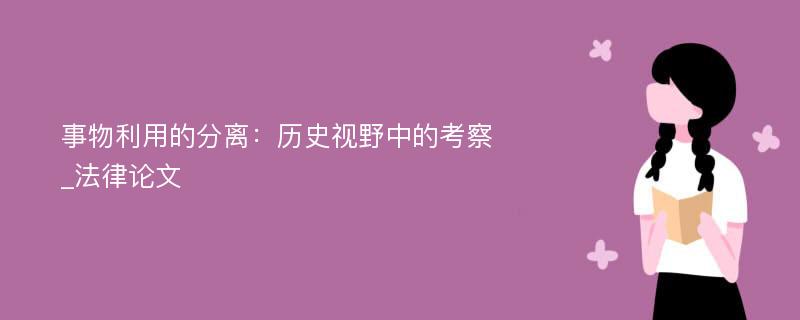
物的利用的分离——从历史角度进行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角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8)02-0029-07
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然而我已飞过。
——泰戈尔
前言
现代生活中,对于物的利用日趋重要。而对物的利用最重要者莫过于用益物权和租赁权。在此基础上,笔者把租赁权称之为债权性质的利用。把某些用益物权称之为物权性质的利用,这其中包括地上权,佃权,居住权、建筑权等人役权。这两者看似差别很大,最明显的莫过于一为物权,另一为债权。但两者在实际上究竟有多大的差异,却很值得深思。基于此种考虑,本文将首先从分析法学的角度对这两种权利作出分析,发现它们的相似之处,然后力图揭示法律语词背后的历史图像。这个图像被抽象的语词所遮蔽和屏障(由此我们可看到抽象语词的弊端)。“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然而“我已飞过”,笔者试图在法律的“天空”中展示“飞过”的“痕迹”。
一、对于物权性质和债权性质的利用权的实证性分析
物权的特点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直接支配物的权力,另一是绝对的对抗力。而绝对的对抗力又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对所有权人的对抗力,二是对不特定人的对抗力。笔者试从以下几个维度对租赁权和物权性质的利用权进行比较。
(一)权利基本结构的分析
我们运用“权利”一词时,必须意识到权利是一个关系概念,即“权利是一种法律关系”。这一点,在债权领域,大家都意识到了,在对债权下定义时,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而在对物权的分析中,我们也应看到物权本质上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在对权利进行分析时,就应注意把分析的基点放在法律主体的关系上。每一种关系实际上都具有一种规范形式,法律关系的基本规范形式,即法律关系的元形式,按照王涌博士的研究共有四种,他们是(狭义)权利—义务关系,自由—无权利关系,权力—责任关系,豁免—无权力关系。下面笔者就运用此种框架对债权性质的利用权(租赁权)和物权性质的利用权加以分析。
笔者先对租赁权的基本结构进行分析。① 租赁权作为一种法律关系可分为对内关系群和对外关系群。即承租人(乙)与出租人(甲)之间可能涉及到的关系和承租人与第三人(丙)之间可能涉及到的关系。
1.对内关系群:承租人(乙)——出租人(甲)
(1)(狭义)权利—义务。乙有权利占有、使用租赁物并取得基于此种行为所获的收益。甲有义务不妨碍乙的行为。
(2)自由—无权利。乙有自由对租赁物占有、使用并取得收益,而甲无权利要求乙不进行这种行为。
(3)无权力—豁免。乙无权力处分租赁物,其处分行为亦对甲不生效力。
(4)责任—权力。甲仍有处分物的权力,他的处分行为对乙亦生效。
2.对外关系群:承租人(乙)——第三人(丙)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对外关系群是承租人与不特定第三人的关系,这一关系实际上可化约为多个承租人与任意一个第三人的关系。而每一个关系都可能涉及到以下方面:
(1)(狭义)权利—义务。乙有权利占有、使用租赁物并取得基于此种行为所的收益,丙有义务不妨碍乙的行为。
(2)自由—无权利。乙有自由对租赁物占有、使用并取得收益,丙无权利要求乙不进行这种行为。
(3)无权力—豁免。乙无权力处分租赁物,处分行为亦对丙不生效力。
(4)豁免—无权力。丙无权力处分租赁物,其处分行为亦对乙不生效力。
我们再用这种框架对物权性质的利用权作一分析,会发现我们得到了与租赁权相似甚至可以说是相同的架构,在这里笔者就不对它逐一分析了。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在物权性质的利用权和债权性质的利用权(租赁权)在基本结构上并没有大的差别。
(二)权利效力等级的分析
上面所作的分析是在物权的对物的支配在法律上的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影响的意义这一方面进行的,这一结论也被许多民法学家所阐述。例如拉伦茨就写到:“使用占有人、用益承租人、借用人根据债务关系而享有的占有和使用的权利也应算是对物的支配权,尽管他们不是《德国民法典》意义上的‘物权’。”“从债权债务关系发生的占有的权利,就其结构说,也是一种支配权,而不是债权”这样,我们对债权性质的利用权(租赁权)和物权性质的利用权就不能从支配这一点上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那么,我们又该从哪一点上进行分析呢?我们仍然希望从拉伦茨的论述中发现一点蛛丝马迹。拉伦茨论述道:“它们之所以不属于《德国民法典》意义上的‘物权’,因为它们只是针对某个通过债务合同而与之相联系的个别的人,而不是像真正的物权那样,所有人对所有物的关系是针对所有的其他人的。所以,根据债权成立的对物的占有和使用权是一种‘相对的支配权’。”“但因为它的基础是债权债务关系,并且原则上只能针对债务合同中规定的人,从而对物的支配也只是一种有限制的对物的支配,因此,它是一种‘相对的占有权’。”[1]285 梅迪库斯也是从这个角度论述的。[2]58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我们必须从绝对权与相对权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而这个角度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物转让后,权利人对新所有人的对抗力问题,这涉及到物权与债权的效力等级问题。二是对其他不特定人的对抗问题,即权利的保护问题。我们先论述第一部分。
按照德国法的理论,物权具有优先效力,其中一部分内容即是物权优先于债权。而债权具有平等性,债权之间不发生优先问题。所以,按照严格的理论推理,租赁权既为债权性质的利用权,那么租赁权就不能对抗租赁物的受让人。因为租赁物的受让人享有的是物权,物权优先于债权。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当然可以说债权性质的利用权与物权性质的利用权在结构上有重大差别。
但大陆法系确定了“让与不破租赁”的原则,② 《普鲁士普通法》第1部21节第2条至第5条,《德国民法典》第571条第1款,《法国民法典》第1743条,《奥地利民法典》第1095条,《瑞士债法典》第260条,《日本民法典》第650条都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虽然要件并不相同)。所谓让与不破租赁,即租赁关系存续中,承租人对于取得租赁物所有权或其他物权之人,亦得主张其租赁权,亦即所谓对抗力是也。这个原则确立以后,债权性质的利用权(租赁权)则拥有了优先于物权的效力。在这一点上,债权性质的利用权与物权性质的利用权的效力已经没有多大的差别。而租赁权如果先设立,那么因为物权性质的利用权与租赁权不相容,那么于租赁存在之范围,在租赁消灭前,不得成立。[3]226 这已经颇类似于先设立的物权优先于后设立的物权。所以说,债权性质的利用权与物权性质的利用权在对抗新所有人、其他物权取得人方面,债权性质的利用权人与物权性质的利用权人的相互关系方面已经没有多大的差别,都按照设立的先后来决定效力等级。
(三)权利保护的分析
绝对权与相对权区别的意义主要在于对权利的保护。如果物权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受到了来自他人的妨碍或侵犯,可以通过诉讼要求排除这种妨碍或侵害,在持续的受到侵犯的情况下,可以要求他人停止侵害。这种请求权一般被称之为物上请求权。在物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如果乙方有过错,权利人可以根据侵权请求损害赔偿。而债权人则不享有物上请求权,而且基于相对性,如果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债务人履约不能,债权人不能基于债权直接要求第三人赔偿,而只能以履约不能要求债务人赔偿。
那么对于租赁权是不是也只能这样呢?前面已引用拉伦茨的见解:“基于债权债务关系发生的占有的权利,就其结构说,也是一种支配权,而不是债权。”[1]303 那么,在租赁权人占有租赁物后,实际上他已经享有了一种对于占有的保护。“承租人取得占有时,基于占有权,得为此主张,殆无疑义。”[3]149 因为,使用、收益等权能都是以占有为前提的,对占有的侵害,也就是对使用、收益等权能的侵害。而不侵害占有但却侵害了使用、收益等权能,在利用这方面,笔者实在想不出来。所以,通过对于占有的保护,实际上也保护了使用、收益等一切对于物的自由权利,实际上,基于物权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能也是通过占有制度保护的。[1]303
但是,租赁权人是否可以基于租赁权本权而主张呢?在这一点上,见解多有不同。在德国,拉伦茨认为:“这个对占有的‘相对’的权利也属于第823条第1款规定的‘其他权利’权利人由此可以通过损害赔偿和要求他人不作为的请求权来保护自己的占有不受到来自第三人的侵害。”[1]303 这里,他显然认为租赁权人可以基于租赁权本权而主张。因租赁权非物权,不认有妨害排除请求权。在瑞士,只能受占有的保护。在日本,租赁权人得以租赁权受侵害为理由,请求损害赔偿。多数认为承租人因取得占有而其租赁权物权化后,得基于其租赁权,请求妨害的排除。判例也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这一点。台湾地区也部分同意这一点。[3]149 我们可以看出,租赁权在权利的保护方面,虽然与物权性质的利用权仍有差距,但这个差距在逐渐缩小,在权利保护方面的结构也因此趋近。
另外,拉伦茨引用胡塞尔的观点认为,债权时间上的存在并不是债权本身的目的,而仅仅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债权一直存在到它的目的达到为止,而所有权在时间上的存在本身就是它的意义。[1]260 拉德布鲁赫也认为:“债权系法律世界中之动态因素,含有死亡之基因,目的已达,即归消灭。”在这里,我们应看到,只有所有权在时间上的存在本身就是它的意义,租赁权和物权性质的利用权都有结束时间规定的,它们都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结束,在这里,物权性质的利用权与所有权有很大的差异,而与租赁权有相同的时间结构。至于权利的可转让方面,因为它更多的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结构,笔者这里就不讨论了。③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债权性质的利用权与物权性质的利用权在结构上是近似的,但学界仍多将租赁权的这种事实称之为“租赁权物权化”,而不愿认为租赁权是物权,王涌博士认为这可能与“租赁权”概念的模糊使用有关,将交付前的租赁权与交付后的租赁权等量以观,不加区分。另一个原因在于物权的法定主义。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律要作出这种分离,将物权性质的利用权确立为物权,而将租赁权确立为债权呢?法国学者马洛里·埃勒斯认为:“事实上,人们将其中一种(用益权)视为武器而将另一种(租赁权)视为对人权,并不是基于物的性质,也非基于纯粹的技术上的原因,而是基于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取决于政治因素,受制于经济生活及地产的经营利用方式,其尤其取决于社会生活,取决于所有者阶层和各种佃农政治力量的对比”。[4]38 因此,笔者想作一简略的历史考察。
二、物的利用的历史探源——利用权的分离史
罗马法为现代私法的源头,我们的考察就以罗马为开端。④ 在罗马法中,租赁的范围远比现在为广,包括物件租赁、劳务租赁、劳务成果租赁。起初,土地为公地,市民在国家拨给的土地上建筑房屋,一般不需租赁,只有牛马的价值为高,不是家家都有。农忙时,没有牛马的人家向有钱人家借用,习惯上要送礼回报,此刻逐渐演变为物件租赁。而土地的利用权方面,最早的先例是罗马的“公田占有(possessio del ager publicus)”制度。这种公田是因战争而掠夺没收的土地。市民可以耕种,每年交纳赋税,称“占耕地”,虽然在法律上国家一直是这些土地的所有,但占有者在事实上被视为这些土地的主人。他们不仅可以继承、转让,而且可以对土地加以改变。后来,出现了“赋税田的出租(locatio degli agri vectigales)”。刚开始,这种出租仍然是一种债的关系,但后来,大法官乃给予承租人以令状保护,并允许提起一种对物之诉——“赋税田之诉(actio in rem vectigalis)”。
在公元4世纪中叶,帝国皇帝为了增加税收,接受了地方政府和寺院的财产,继续出租,租期以永久性为原则,于是佃租权改称“永佃权”。同时皇帝又将其私有地产,包括土地和农舍,租给市民垦殖使用,其期限如果是永久的,成为永租权。大地主也开始仿效政府的办法。优帝一世时,合并永佃权和永租权,统称为永佃权。而在此之前,古典法学家时代起,人们就争论“赋税田”的出租是否属于真正的租赁。到芝诺皇帝时期,他说:“我们规定,永佃权既非租赁亦非买卖,而是同上述两种合同毫无关系或相似指出的一种权利,是一个独立概念,是一个正当、有效的合同的标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权利的截然区分,实际上是由于皇帝的命令而确立下来的。另外,在罗马法中,租赁权是一种债权,实行的是“买卖破租赁”的原则。这是把租赁权作为债权的必然逻辑结果。这时,对物的出卖并不真正是租赁结束,租赁关系仍然在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存在,因而承租人只能对将土地租给他的人或者继承人行使诉权。不仅对土地是这样,对于房屋的租赁权也是这样。在罗马,房屋原每家都有,不发生租赁问题。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房屋租赁。由于罗马对于外邦人,在公元212年前,一直不把他们与罗马市民同等对待,而“让与破租赁”对房屋的所有人(大部分是罗马人)有利。后来,由于转让出租物的出租人一般经济情况比较差,承租人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赔偿,且诉讼也有成本,所以,地奥克莱体亚努斯帝于是规定凡买卖中附有维持租约效力的条款的,买受人既有遵约的义务,“让与破租赁”的原则也就被限制了。[5]773 对这种租赁权加以强化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奴隶的价格急剧上升,对奴隶的需求说明使用奴隶比自由劳动力具有更大的赢利的可能性。而后来,奴隶制出现了衰落,这反映了其盈利性的下降。当奴隶的价格十分高时,使用自由劳动力的价格就有利可图了。[6]134 而这种使用主要是通过土地租赁来实现的。罗马皇帝对租赁权加以强化,是为了大地主能够把他们的土地更大程度上租给自由劳动力,从而增加税收,也有利于社会稳定以及帝国的延续。
但是在罗马,租赁权的基点仍然放在对所有权的保护上。关于在罗马法中,对所有权的保护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租赁权也要受到这个限制,在所有权处于优越地位的法律世界中,租赁权必然处于臣服地位,而受到压抑。这与罗马的简单商品经济的背景有关系。商品经济以交换为中心,交换要以所有权为前提,这就导致重在物的抽象的经济价值,重在对物的全面的、包括的完全支配权。这样,把对物的租赁权确立为一种债权,而使所有权优先就合乎情理了。
在日耳曼法中,关于物的所有观念很晚才出现。它是以马尔克制度为基础。“原始德意志马尔克制度是整个德意志法的基础。”[7]215 这就决定了他是以农业社会为背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这就决定了像罗马法那样一切以对物的支配为中心的权利体系在日耳曼不可能产生。“罗马法及其对私有财产关系的经典的分析,在日耳曼人看来简直是荒谬的。”[8]500 在日耳曼法中,所有权的本质在于对物的利用,其权利体系是以“利用”为中心而构建起来的,而对土地的利用也包括让他人耕种土地而自己仅收取其产物(佃租等)这决定了他们法律体系的特点。而且,在日耳曼思想中有一个特点是,对于精神的统一体赋予感觉的形式,通过其统一把握精神的东西[9]114 这样,虽然罗马法中,对于物事实上的支配既是占有,对于物的法律上的支配便是物权,事实关系与法律关系截然对立,但由于日耳曼人的上述特点,导致他们只注重他们所能直接感受到的东西,所以,在日耳曼法中只有占有,相关规定也就相对复杂。这种思想特性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物权和债权作出区分。而由于一切以利用为中心,所以,在日耳曼人看来,物权性质的利用权与债权性质的利用权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强使它们泾渭分明丝毫没有必要,它们都是一种不完整的所有权。在日耳曼法中,“仅有完全的所有权和不完整的所有权,自由的所有权和有负担的所有权,以及收取全部收益的所有权和缴纳佃租的所有权之分别。”[10]30 而没有物权性质的利用权与债权性质的利用权的分别。
在封建制确立以后,马尔克制度日益崩溃,西欧的经济以领主庄园制为中心,这时,领主、僧侣和农奴之间的身份的隶属关系,农奴相互间的共同体关系,领主和僧侣之间的关系,以及领主相互之间的主从的权力秩序关系,构成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支配性法律关系的总体。拥有大量土地的领主和僧侣让农奴耕种他们的土地,农奴缴纳佃租,构成了这时的经济生活的主旋律。而当时相对的谈判实力在领主和僧侣这一方,国家也必须保护领主和僧侣的利益一维持他们的统治。这样一种现状反映到法律上,便是对佃权的着力规制,而这种规制的基点便是保护领主和僧侣的利益的保护。更重要的是这时的利用权制度渗透着身份因素,而这种身份因素对于封建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必须对这种利用权予以稳定化,所以,相较之债权性质的利用权,物权性质的利用权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但在后期,骑士制度衰落,商人们的频繁交往改变了过去素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状况,而且,经过一场大的瘟疫之后,农奴人口大量减少。这种相对的谈判实力从领主转向了农奴。[6]152 而农奴则大量逃往城市,因为城市法将人从各种封建的身份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人仅受城市君主的支配。再者,由领主和寺庙把持的对于土地的支配权现今由君主进行支配,所以,这时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便不受领主和僧侣的拘束和干涉,市民可以把土地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同时,由于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所有人对于货币的需求较之对实物的需求更甚,而渴望人身自由的佃户此时也极端厌恶身份上的从属关系。这样,对土地的利用权便出现了一种逐渐从各种极其繁琐的身份关系中解放出来而成为一种纯粹的没有人身关系的财产关系的趋势,但这时也仅是一种趋势而已。对土地的物权性质利用权仍然处于优势地位。
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尤其在圈地运动中,大量无地农业人口流入城市,而他们被强迫成为雇佣者,不许流浪,而他们必须有居住之处。这样,房屋的租赁逐渐增多。这又涉及到社会的稳定,因此,租赁权重新进入政府的视野,受到他们的重视。而为了更好的实现社会稳定的目的,房屋的承租人为弱者的思维模式在这时形成并影响了以后的一系列立法。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那就是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大生产迅猛发展。而这种发展必须以大机器设备作为基础。这些机器设备一般都比较昂贵,这样,以前不受到重视的机器设备租赁也受到了重视,它和房屋租赁一起使得债权性质的利用权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一方面高扬起个人主义的旗帜,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的保留有身份的因素,这注定了法国民法典只能是被梅因称之为“从身份到契约”这一运动的一个里程碑,而不是它的终点。在法国民法典的利用权体系中也不可避免的染有这种色彩。它规定了租赁契约,保护承租权,并含有一系列有利于承租人的规定(第1743条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但它也以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为着眼点规定了物权性的利用权。这也与中世纪以来罗马法的复兴有直接的关系。
法国民法典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对物权和债权作出明确的区分,这也注定了它不可能对物权性质的利用权和债权性质的利用权作出彻底的分离。在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中,作出了对物的物的权利和对人的人的权利的区分,但物权和债权还没有明确的区分,债务法被归入物权法中。在1811年的奥地利民法典中,“物权”这一概念被首先使用,但该法典中物权概念的含义和现代民法中的物权的含义有很大的差别。而物权与债权的明确区分是在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中确立的。在德国民法典中,物权性质的利用权和债权性质的利用权都有了明确的区分和规定,实现了它们之间的分离。但是,德国民法典仍然规定了“让与不破租赁”的原则,这时物权性质的利用权和债权性质的利用权仍然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再者,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尤其是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的到来,人类由身份关系发展到契约关系,物权关系成为了一种纯粹没有人身因素的财产关系。而且,对物的利用的重视导致了利用权不再以所有人的利益而是以促进物的利用为着眼点。各种物权性质的利用权不再从属于所有权,而被看作所有权的限制,从而优先于所有权。这样,物权性质的利用权和债权性质的利用权的功能逐渐趋近。
二战后,由于战争的破坏,大量人口没有房屋居住,房屋所有人乘机哄抬房屋租赁价格,并在合同中规定了大量不利于承租人的条款。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各国政府作出了许多保护承租人利益的规定,如德国1951年关于住宅所有权及继续居住权的法律,瑞士1953年关于租金统制及终止权限制的命令,法国1948年关于居住及营业用场所租赁的法律,日本原已制定借家法,战败后又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保护承租人。对于耕地和基地的利用也制定了很多的规定。这些措施主要包括租金限制,出租人终止权的限制,租赁合同内容的法定,租赁处分的缓和等。这些措施似使得债权性质的利用权的效力越来越相似于物权性质的利用权,从而是使得它们的权利结构越来越相似。民法学界称这种现象为“债权的物权化”。其中,我们应注意到一个新趋势的发展,法国1953年制定了关于商工业用建筑物之更新之命令,1949年关于因战争破坏之商工业用建筑物租赁之法律,日本借家法也适用于因承租他人工厂店铺为营业者的情况。这些规定以维持建立于租赁权上的企业与营业为目的,这一点也与以居住为目的的租赁权有不同之处。
从以上关于利用权的历史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债权性质的利用权和物权性质的利用权在罗马前期没有明确的区分,在罗马后期开始分离,在日耳曼法中两者并没有明确的区分,而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利用权仍然是统一的一体。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两者在中世纪后期出现了分离的趋势。在近代民法典中,两者便出现了明确的区分,但两种利用权仍有着关联,二十世纪以来,两者越来越趋同。这种统一、分离以及趋同受多种因素影响,最主要的有经济上的需要,利用关系中身份的强弱,支配和利用哪个占据优势地位,物权与债权是否明确区分,政治要素的分配,阶层力量的对比,以及某个时期社会政策的影响,等等。而着眼点也迭经变化,由最初的保护所有者到保护利用者,再到保护弱者,最近又有企业和营业维持的目的,而这些变化当然也与各种因素相联系。
三、结论
上面已经提及,虽然两者的权利基本结构相似,但基于各种因素,近代法遵照罗马法作出了物权性质的利用权和债权性质的利用权的区分,而二十世纪以来,二者出现了趋同。无论是区分还是趋同,逻辑因素都没有起到主导的作用,真正的决定因素是社会现实和社会需要。我们研究现时代的法律设计都应以此为出发点。而且我们应该看到,趋同现象仍然是以两者的区分为基础的。我们也应坚持这种区分,最明显的理由仍然是近代民法的精髓——意思自治。虽然,“所有人总是试图利用其事实上的强有力的地位及法律上的绝对自由,尽可能强化其支配地位”,“土地所有人趋于追求更强的支配力”,[9]12 但在摆脱了不平等身份束缚的平等主体之间,被允许利用与允许利用实际上是博弈的产物,不同的利用方式有不同的价格。虽然按照科斯定理,资源的权利的初始分配并不重要,因为有了好的条件,资源总会得到最有效的使用,但这是从社会来着眼的,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利用方式的不同意味着成本的不同。古典经济学所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理性人的定位,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的判断者,政府要做的是作好条件的准备。所以,法律要做的就是两种利用方式的区分,使得主体按照自己的利益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法律越俎代庖,伤害的就是主体的意思自治。而且,这种做法往往会伤害法律原本所要保护的人。因为,法律利用强制性规定作出保护承租人,但这往往使得租赁的价格提升。而那些本来作出判断,不需要这些保护而宁愿要更低的价格的被保护对象,这时失去了选择的机会。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举的租金管制所引起的后果的例子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而这种区分要我们做的还有很多。如房屋、设备的物权性质的利用,我国还付之阙如。比方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最终还是将多次草案提到的居住权问题给拿下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现实生活中对这种权利的法律保护和支撑已经显露出必要性。[11] 我们的法律应为主体自发性的合理选择作出最充分的前提准备。基于社会本身的变迁,新的规定着眼点也应有所变化。现在,虽然融资租赁可以解决设备的一部分的供应问题,但我们还是应该把传统的租赁制度的着眼点也放到这上面去。而且,在我国,办公楼的租赁现象也大量出现,法律必须面对这一现实,为之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归根结底,这些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营业及企业的维持,这也是立法的一个趋势,⑤ 利用制度当然也不能对之视而不见。
[收稿日期]2007-05-16
注释:
① 这里只是分析这两种权利的基本结构,而不是结构的全部。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篇幅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因为笔者认为决定某个权利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权利是由其基本结构所决定的,而权利类型之间的相似相应地更是因为两种类型的权利的基本结构相似。
② 大陆通用的说法是“买卖不破租赁”。但是因为“买卖”是一种合同,是债权关系,而租赁也是一种债权关系,债权当然不能“破”债权,所以,“买卖不破租赁”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从各国规定来看,不仅是“买卖”不破租赁,其他有如赠与等也不破租赁,所以,这种说法又是不准确的。究其含义,实际上是说由于法律的特别规定,物权性质的权利移转不影响租赁权,所以,本文从我国台湾学者的说法,即“让与不破租赁”。
③ 其实,在现代民法中,各国都直接或间接的促进租赁权的可转让性。在这一方面,两者的结构同样趋近。具体可参见史尚宽:《债法各论》,第149页以下。
④ 本节的论述参考了周枏:《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72页以下,以及第414页以下;[意]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页以下。
⑤ 请参见我妻荣先生在《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一书中的第三章第四节所做出的细致而精彩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