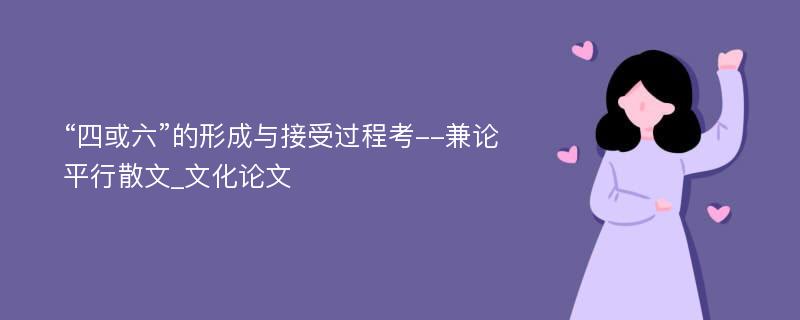
“四六”指骈文之形成与接受过程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骈文论文,过程论文,四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1)03-0001-05
“四六”是骈文的别称。“四六”的名称定名问题已有分析[1],但其形成与接受过程仍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追溯这一过程不仅可以弄清楚“四六”的形成过程,而且可以了解骈文观念的变迁。这个名称的产生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从柳宗元合成“骈四俪六”到李商隐提炼为“四六”是一个创造性的飞跃。而这种提炼的基础应该是在中晚唐“四六”指骈文逐渐成为了文坛的共识。
“四”与“六”只是数字。中国古代单纯用数字来指称文体很少。古有所谓“七”体,明人徐师曾解释:“问对凡七,古谓之七。则七者,问对之别名,而《楚辞·七谏》之流也。”[2]138这是从结构形态来总结,并不是从句法角度来命名。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篇最早专门讨论文章句法,其中提到了四字句和六字句:
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3]572
上述文字最早明确了骈文章句的句法规律以四字句和六字句为主。“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还揭示了四字句和六字句的句意浓缩、节奏分明和声韵快慢结合的特点。这里是就文章的句法来讨论的。虽然并没有专门针对骈文立论,但是刘勰所处的齐梁时期正是骈文最为流行的时期。当时文坛上最为推崇的是骈文,生活中应用最多的是骈文。所以,上述文字讨论的章法基本上是指骈文的句法,应该是无异议的。事实上,齐梁时期的骈文,四字句和六字句确实成为了骈文的句式主体。所以,刘勰标示出四字句和六字句是骈文的句式主体,正揭示了骈文的句法规律。可以说,刘勰最早从句法数字角度拈出“四”“六”二字。这是骈文学史上骈文观念明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到了中唐时期,柳宗元在《乞巧文》中又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文字:
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4]214
这里暂且不讨论柳宗元对骈文的态度。从句法来看,“骈四俪六”前后各两字是并列结构,但却是可以互相重组的词,也就是“骈”与“俪”、“四”与“六”可以重新组合为更密切的词。这是最早把“四六”与“骈俪”放在了一起,从而酝酿了后来骈文的两个名称“四六”和“骈俪文”,这也是“四六”第一次联系在一起使用。可以说,柳宗元在《乞巧文》中构思了“四六”名称的雏形。这是“四六”概念形成的重要一步。
孙梅在《四六丛话·凡例》中称:“四六之命,何自昉乎?古人有韵谓之文,无韵谓之笔。梁时‘沈诗任笔’,刘氏‘三笔六诗’是也。骈俪肇自魏晋,厥后有齐梁体、宫体、徐庾体,工绮递增,犹未以四六名也。唐重文选学,宋目为词学,而章奏之学,则令狐楚以授义山,别为专门。进考《樊南甲乙》,始以四六名集。而柳州《乞巧文》云:‘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又在其前,《辞学指南》云:‘制用四六,以便宣读。’大约始于制诰,沿及表启也。”[5]10一般公认,四六指骈文是在唐代,具体来说是李商隐在《樊南甲集序》中的发明。《樊南甲集序》云: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后又两为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人或知之。仲弟圣仆,特善古文,居会昌中进士为一二,常表以今体规我,而未焉能休。
大中元年,被奏入岭当表记,所为亦多,冬如南郡,舟中忽复括其所藏,火燹墨汙,半有坠落。因削笔衡山,洗砚湘江,以类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未足矜。
十月十二日夜明月序。[6]1713
这篇序作于大中元年(847)十月十二日。李商隐在《樊南乙集序》也再次确认这一点。从大中七年所作《樊南乙集序》中“舟中序所为四六,作二十编”云云可知,“四六”之称在当时已经成为公众熟悉的词语。《樊南甲集》为李商隐离开桂林郑亚幕府时结集,收录了他在桂林几乎所有的骈文作品。从中可以看出,李商隐骈文名声远扬,除例行代郑亚作的公牍文章外,周边县城很多公共庙宇落成或祭祀亦请李商隐执笔。
从李商隐这段解释来看,李商隐以“四六”命名骈文还有一些自我调侃的意味。“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不过为博戏,不登大雅之堂,雕虫小技“未足矜”。这透露出其四六骈体应用文章虽已名声远扬,但是李商隐自己并未看重。他原本胸怀大志,却最终以这种文字技巧谋生,正如“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一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在“《李义山集》八卷、《樊南甲乙集》四十卷”后有一段分析,其评云:
《甲乙集》者,皆表章、启牒四六之文。既不得志于时,历佐樊府,自茂元、亚之外,又依卢弘正、柳仲郢,故其所作应用若此之多。商隐本为古文,令狐楚长于章奏,随以授商隐。然以近世四六观之,当时以为工,今未见其工也。[7]483
近人孙德谦在《六朝丽指》中也指出:
骈体与四六异。四六之名,当自唐始,李义山《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知文以四六为称,乃起于唐,而唐以前则未之有也。且序又申言之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使古人早名骈文为四六,义山亦不必为之解矣。《文心雕龙·章句篇》虽言“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此不必即谓骈文,不然彼有《丽辞》一篇,专论骈体,何以无此说乎?吾观六朝文中,以四六作对者,往往只用四言,或以四字五字相间而出,至徐庾两家,固多四六语,已开唐人之先。但非如后世骈文,全取排偶,遂成四六格调也。彦和又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可见文章体制,在六朝时,但有文笔之分,且无骈散之目,而世以四六为骈文,则失之矣。[8]
他指出四六与骈文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四六”是指全用四六句的骈体,其实骈文不仅包括全用四六句的骈体,还包括骈散合一的骈文。
李商隐在《樊南甲集序》中两度用到“今体”与“古文”对比。可以看出,在晚唐李商隐时代通行的是用“今体”指称骈文,因为从六朝开始就是用“今文”“今体”指骈文。但这应该不是正式的文体名称,只是通行的俗称,指当今流行文体之意。孙德谦《六朝丽指》云:
义山《樊南甲集序》云:“始通今体”,其上则云以古文出诸公间,是义山固以今体对古文矣。所谓今体者,义山既自名其集为《樊南四六》,则今体固指四六言也。然梁简文帝《与湘东王论文书》有云:“若以今文为是,则昔贤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由此观之,六朝时已目骈文为今体矣。
这说明到了李商隐,“今体”才被“四六”取代。“四六”这一从文章句法概括出的文体名称从此流行文坛,至“骈文”一词出现、流行,仍然并行不悖,直至近代才被“骈文”概念取代。清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二载:
容斋洪氏《随笔》又曰:
唐世节度观察诸使辟置僚佐、以至州郡差掾属,牒语皆用四六,大略如诰词。李商隐《樊南甲乙集》,顾云《编藁》、罗隐《湘南杂稿》皆有之,故韩文公《送石洪赴河阳幕府序》云“撰书辞,具马币”李肇《国史补》载崖州差故相韦执谊摄军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时只以吏牍行遣也。①
指出在唐代后期,各级官府用“四六”撰述公文成为时尚,从而推进了四六文集的出现。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四六”被人们普遍认同接受。所以,李商隐“四六”命名骈文成为必然,因为四六句式已经成为骈文的经典句式。
对于四六在晚唐官场的流行以及文人因此而竞相追逐,《全唐文》卷七九五载晚唐孙樵的一篇墓志铭《唐故仓部郎中康公墓志铭(并序)》对此有生动的记叙:
唐尚书仓部郎中姓康氏,以咸通十三年月日,薨於郑州官舍。其年月日,前左拾遗陈昼寓书孙樵曰:“与子俱受恩康公门,今兆还有期,其孤徵志于子,子其无让。”樵哭之恸,已而挥涕叙平生。公讳某,字某,会稽人。曾祖讳某,赠某官。祖讳某,赠某官。父讳某,赠某官。公幼嗜书,及冠,能属辞。尤攻“四六”文章,援毫立成,清媚新峭,学者无能如。自宣城来长安,三举进士登上第,是岁会昌元年也。其年冬得博学宏词,授秘书省正字。明年,临桂元公以观风支使来辟,换试秘书郎。五年调,再授秘书省校书郎,大中二年复调授京兆府参军。……咸通元年改检校礼部郎中兼侍御史,充转运判官。李公始以廉平知,终以章奏加厚。常称于班行间曰:“康公宜掌帝制。”或与宰相言,必慰荐之。明年诏授海州刺史。廉而不刻,明而不抉。案牍符檄,公一以口授之,群胥辈徒搦管捉纸,字字书出。蓄缩汗栗,何暇为奸犯耶!以故老吏猾胥,畏之如神明。[9]卷七九五,3696
文中称康氏“幼嗜书,及冠,能属辞。尤攻四六文章,援毫立成,清媚新峭,学者无能如”。因为“能属辞”“尤攻四六文章”从科场到官场一路青云直上,众人对其文辞之敏捷无不叹服。“案牍符檄,公一以口授之,群胥辈徒搦管捉纸,字字书出。”据墓志文字所记,墓主死于咸通十三年。该文亦当作于咸通十三年,在李商隐《樊南甲集序》作年的大中元年之后23年。孙樵本人擅长古文,曾以得韩文公真传自居,但这里在“四六”之后加上“文章”,意在强调是“四六”文章非“古文”文章。这说明“四六”已成为了吕常通行之语。
晚唐“四六”概念出现后迅速流行。据《新唐书·艺文志》卷六十记载有以“四六”名集的作品:
崔致远《四六》一卷。
李巨川《四六集》二卷韩建华州从事。
崔致远为新罗人。生活在857年至928年之间,也正是晚唐的后期。其骈文多创作在广明年间。身为异域人士都可以大量写作四六文,并且可以成集,说明四六文流行之广。李巨川也是晚唐后期的人,生活在僖宗、昭宗年间。生年不详,卒于901年。《旧唐书》卷一九○下有传。《新唐书纠谬》卷十二:“艺文志第五十卷有李巨川《四六集》二卷,注云‘韩建华州从事’,今案:李巨川已见《叛臣传》,此注重出也”。
晚唐到五代除了上述两位外,还有其他作家的四六文结集。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载:
薛逢《四六集》一卷,唐秘书监河东薛逢陶臣撰。
田霖《四六集》一卷,南唐田霖撰。[10]484-487
薛逢生卒年不可考。据新旧唐书可知,其于会昌元年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后为崔铉辟为幕府从事。田霖事迹不详。
“四六”到了宋代更是成为最流行的词语。作家四六结集更多。宋代作四六结集的,据《宋史》卷二八○记载,有“郑昌士《四六集》一卷”、“象台《四六集》七卷”,这是宋代四六作家的结集状况。以上这些人除崔致远外,均无甚名气。南宋郑樵在《通志》卷七十记录了唐宋时期《四六集》的存录状况:
《樊南四六甲集》二十卷李商隐撰又《樊南四六乙集》二十卷
崔致远《四六》一卷 唐人
李巨川《四六》一卷 唐人
樊景《四六集》五卷 唐人
郑准《四六》一卷 五代人
白岩《四六》五卷 后唐人
关郎中《四六》一卷
蹇蟠翁《四六》一卷
邱光庭《四六》一卷
殷文圭《四六》三卷 赵文翼注
王禹偁《四六》一卷
丁谓《四六》二卷
宋齐邱《四六》一卷
萧贯《四六》一卷
凡《四六》一种十五部六十四卷
《通志》记载的四六结集有15部,共64卷。这肯定是不完整的。据《钦定续通志》卷一六三记载,宋明时期的四六集有:
《格斋四六》一卷 宋子王俊撰
《橘山四六》二十卷 宋李廷忠撰
《四六标准》四十卷 宋李刘编
《壶山四六》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
《四六法海》十二卷 明王志坚编
以上见文渊阁著录
《南塘四六》一卷 宋赵汝谈撰
《臞轩四六》二卷 宋王迈撰
《巽斋四六》一卷 宋危昭德撰
《四六膏馥》七卷 旧本题宋杨万里撰
《群公四六续集》十卷 不著编辑名氏
《四六丛珠汇选》十卷 明王明嶅编
《四六类编》十六卷 明李日华编
《古今濡削选章》四十卷 明李国祥编
《四六霞肆》十六卷 明何伟然撰
以上见《四库全书存目》
四六凡十四部
这里补充的宋代四六结集又有9种,其实这仍未完整。②可以看出,宋明时期“四六”一词已经广为使用,作为骈文的基本名称已经定型。关于宋代的几部代表性集子《格斋四六》《橘山四六》《四六标准》《壶山四六》,《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六有所点评:
《格斋四六》一卷
宋王子俊撰。子俊有《三松类稿》,今已散佚,此即其类稿之一种也。杨万里称其四六追步欧苏,不论汪藻孙觌。推挹稍过,然即此一本而论,典雅流丽,渐近自然,与汪孙亦分路扬镳也。
《橘山四六》二十卷
宋李廷忠撰。明孙云翼笺注。北宋四六大都温雅,南宋渐变为纤巧,廷忠当淳熙绍兴之间,正风气升降之际,故格意不免稍卑,又嗜博矜新,亦或伤繁冗,然组织工稳,其佳处亦不可没。云翼所注,颇为芜杂,存以备考云尔。
《四六标准》四十卷
宋李刘撰。其门人罗逢吉编。明孙云翼笺注。刘事迹无可称述。惟以四六为专门。大抵以流丽稳贴为宗,无复唐以来浑厚之气。亦世变为之也。凡分七十一目,一千九十六首。逢吉欲尊其师傅,故题曰标准。云翼尝注《橘山四六》,颇为芜杂,此注亦略相同。
《壶山四六》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南宋中叶号壶山者凡四人。以其《除福建漕司谢乔平章启》考之,似当为方大琮作,而大琮集中又不载。岂其族孙良永等掇拾遗文,偶未见欤?疑以传疑,姑置于大琮集后。
从上可以看出宋代四六的流行状况。四六之所以流行,其实是官场需要决定的,崇尚浮华的形式决定了文坛流行四六的风气。《文献通考》卷三三引叶适的分析可谓精辟,其云:
叶适论宏词曰:法或生於相激。宏词之废久矣。绍圣初,既尽罢辞赋,而患天下应用之文由此遂绝。始立博学宏词科,其后又为词学兼茂,其为法尤不切事实。何者?朝廷诏诰典册之文,当使简直宏大,敷畅义理以风晓天下,典谟训诰诸书是也。孔子录为经常之词,以教后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谓重矣。至两汉诏制,词意短陋,不复仿佛其万一,盖当时之人所贵者武功,所重者经术,而文词者虽其士人哗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笔吏之所能无几也。然其深厚温雅,犹称雄於后世,而自汉以来,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对偶铭檄赞颂,循沿汉末,以及宋齐,此真两汉刀笔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谓之奇文绝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于朝廷,何哉?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尝知义,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操纸援笔以为比偶之词,又未尝取成于心而本其源流于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10]卷三三,317
《文献通考》卷三七引洪迈《容斋随笔》之分析更为直接: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铨选以身、言、书、判择人。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今郑畋《敕语堂判》犹存,世俗喜道琐细遗事,参以滑稽,目为花判,其实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笔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国初尚有唐余波,久而革去之。但貌体丰伟,用以取人,未为至论。
按唐取人之法:礼部则试以文学,故曰策,曰大义,曰诗赋。吏部则试以政事,故曰身,曰言,曰书,曰判。然吏部所试四者之中,则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皆可以此觇之今主司之命题,则取诸僻书曲学,故以所不知而出其所不备,选人之试判则务为骈四俪六,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词,然则所得者不过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士耳。[10]卷三三,353-354
正是唐代科举取士及官场的形式主义作风,造就了文人行文和公文崇尚形式浮华的四六文风,这才助长了四六的流行,助长了四六作品的结集。这也是四六多应用文字而绝少文学抒情佳作的原因。而宋代官场陈习未改,也是四六流行的主要原因,亦为“四六”被作为骈文的名称继续接受的原因。
由于四六创作的兴盛,宋代还因此诞生了专门的四六批评“四六话”,这是骈文批评的最早形态。四库全书收录了宋代两部四六话,也是最早的两部四六话,即王铚《四六话》和谢伋《四六谈麈》。《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二十对此有精辟的评论:
《四六话》二卷
宋王铚撰。古无专论四六之书,有之自铚始。所论多宋人表启之文,大抵举其工巧之联,而气格法律皆置不道,故宋之四六日卑,然就一朝风气而言,则亦多推阐入微者,如诗家之有句图,不可废也。
《四六谈麈》一卷
宋谢伋撰。其论四六多以命意遣词分工拙,所见在王铚《四六话》上,其论长句、全句尤切中南宋之弊也。[11]卷二○
由于四六基本上是官场公务文书,所以王铚《四六话》和谢伋《四六谈麈》基本上谈的是字词句法对偶等琐碎问题,而对文章内容主题避而不论。
明代还产生了两部四六总集,即王志坚的《四六法海》和托名杨万里编的《四六膏馥》。其内容应该也是宋四六为主。③《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九载:
《四六法海》十二卷
明王志坚编。四六亦古文之变体,犹古诗之为律诗,面貌虽殊,根源不异,世俗溺於华藻,遂判两途。志坚此编,实能溯骈偶之本始,其随事考证亦皆典核。虽人人习见之坊刻,实四六中第一善本也。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七载:
《四六膏馥》七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宋杨万里撰。其书割裂诸家四六字句,分编次以备挦撦,其曰膏馥者,盖取元稹作杜甫墓志铭“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语也。然万里一代词宗,谬陋不应至此,此必坊贾托名耳。
这些总集的出现,是因书商看到了社会的需要和市场的需求,说明了宋以后直至明代,四六成为了官场必备的文字技能,这样“四六”指代应用性骈文成为了所有人的共识。
注释:
①又见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十六“唐世辟寮佐有词”条,四库全书本。
②详细内容可参见施懿超《宋四六论稿》下编《宋四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③详细内容可参见《宋四六论稿》下编《宋四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