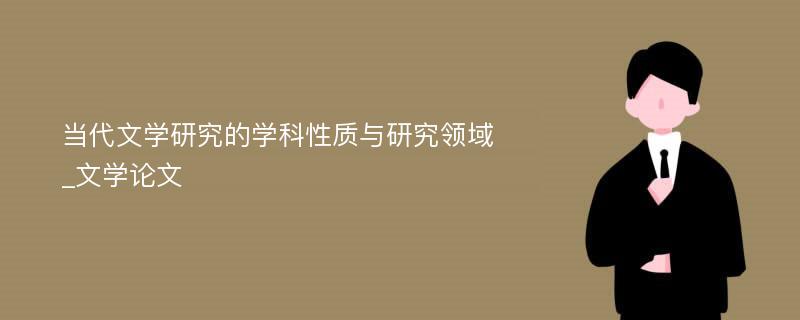
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性质与研究界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界域论文,当代文学论文,学科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I2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00)03-0104-04
今天,尽管人们已经开始习惯于用“现当代文学研究”来称呼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把它们视为一个完整的学科,但在实际研究和教学中,“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学科却仍然显得畛域分明,壁垒森严。这种隔膜是一种人为运作的产物,它们作为两个文学学科的区别缺乏一种内在的规定性,因此,打破人为的壁障,实现二者的沟通和分治,不仅事关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也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按照通常的现、当代文学划分,现代文学是指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建国以前这段时期的文学,而当代文学则是指建国以来的文学。这样一种对现当代文学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同的学科面貌。一方面,由于现代文学被置于一段已经闭合的历史中,现代文学研究也就获得了一个明确而稳定的研究对象,从而具有了标准的文学史学科的特征,也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学科体系和话语规则。另一方面,这一定位,却使当代文学研究陷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建国以来”这样一个开放的时限,使它的研究界域被留出了一道难以封闭的口子,因此,这一人为划出来的学科只有上限,其下限则随着文学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向后延伸着。研究界域的这种流动性和延伸性,使当代文学研究在难以获得一个稳定的研究对象的同时,也难以确立其自身的学科特性。说它是一个文学史学科,它却没有为自己设定作为“史”所应有的边界。也就是说,从研究客体看,它缺少一个稳定的研究对象,它所关注的并不限于已经过去的文学史,当下发生的纷至沓来的文学现象也在不断地挤进它的研究范围,突破着它作为“史”的防线;从研究主体看,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不仅置身于自己所研究的这段文学史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其发展进程,而且由于他们必须对当下文学现象进行追踪研究和即时的评论,因此也就往往把有较强主观色彩的感悟式、预见性批评不自觉地当成了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式。这样一来,当代文学研究就与文学史学科的“历史性”要求、与同研究对象保持历史距离的相对客观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不无违逆。说它是当下的文学批评活动,它也缺乏对“当下”的限定,它的研究范围常常超越“当下”,而把已进入历史的文学包括进来,其上限一直延伸到了整个50年代。而为了使当代文学研究获得某种学术上的合法性,一些研究者也力图强化这门学科的文学史性质,主张为它设定有效的研究界域,确立它的文学经典,由此来使研究主体与对象保持一种历史距离和冷静客观的叙述态度,并使它的研究对象得以稳定。这种对当代文学的文学史品质的追求和经典化在一些当代文学史的专著和作品选本中有所体现。从这个角度说,当代文学研究又带有文学史的特征。这种模棱两可的学科性质反过来也加深了研究者在有关如何建设这一学科的问题上的分歧。主张把当代文学研究作为文学史学科的人,要求强化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性质,为它设定一个时间的下限,以将它置于一段闭合的历史框架中,为研究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对象,从而营造文学史研究所要求的整体感、历史感,使研究更具客观性;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更注重的是当代文学学科的即时批评性质,要求保持当代文学批评活动的动态性、当下性和生动性,在他们看来,“对当代文学的研究是一种不断的追踪,需要的是投入的精神,等待那些丰富生动的文学现象成为‘历史’再对它进行‘冷静’的‘总结’的研究方式,显然不适合这一学科的特点。”[1]
当代文学学科这种两不着边的处境和研究者看法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它作为学科的不成熟。而这种不成熟实际上源于对它的定位一开始就缺乏学理上的考虑。
50年代中期以前,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一直被看成一个整体,并不存在现、当代文学的划分。当时除了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年)外,大多数学者采用的都是“新文学”这一命名,从50年代初教育部委托一些学者拟订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到王瑶、蔡仪、张毕来、刘绶松等老一辈学者撰写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早期“新文学”史,大抵如此。这些著作的叙述下限都以1949年为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1949年以后的文学已被自觉地看成了另一种性质的文学,而主要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重大事件作为旧时代的结束标志,为叙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提供了一个便于史家把握的合适的历史下限,同时也是由于从建国到50年代中期以前的文学发展只有几年时间,它还处在当时的“当下”过程中,尚来不及沉淀,因此也就难以进入历史,对这一段未被纳入到史的叙述中的文学是以即时批评的方式叙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早的当代文学研究就是一种即时批评。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中国社会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从新民主主义时代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也随着建国以来一系列文艺思想斗争对“革命”、“进步”、“反动”作家的定位和对“主流”、“支流”、“逆流”文学的分梳,确认建国以后这一时期文学的独特性质,就成为本时期“主流文学”强化自己独立地位的需要。于是,“新文学”这样一个自五四以来就开始流行的概念,便逐渐为“现代文学”这样更具意识形态含义的概念所取代。之所以说“现代文学”是一个更具意识形态含义的概念,是因为如一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改变不仅仅是一种称谓上的变化,而更重要的是它“为‘当代文学’提供了生成的条件和存在的空间”[2]。它使得过去相对于传统文学而言的“新文学”, 从铁板一块的整体,变成两个不同时段中两种有着不同等次和性质的文学。
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性质上的差别是依据革命史的尺度来规定的,按照这一尺度,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而当代文学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这两个时期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的差别,也就决定了这两个时期文学的性质、对象和任务的差别。表面上看,“时期”这一时间规定把处于这一时期的所有的文学现象都纳入进来,但实质上,“性质”的规定,又把那些“异端”的文学现象过滤出去。显然,在这种“现代”与“当代”的划分中,意识形态的标准成为最关键的决定标准。因此,这种命名,反映了那一特定的政治化的文化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话语阐释权的控制需要。
然而,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将“新文学”强行分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从学理上说又是缺乏充分的内在依据的。首先,单从词义上看,无论在现代汉语里还是在西语中,“现代”与“当代”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所指的都是现在的、目前的时代。因此,现、当代文学的划分在语义上往往显得十分勉强。即使人们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接受这种人为制造的先后顺序,也难以接受一种恒定不变的“现代”与“当代”,因为在时间的刻度上,“现代”或“当代”都不是凝固的、永恒的,而是变动不居的、暂时的。从字面上讲,五十年前的“当代”或一百年前的“现代”到今天仍然被称为“当代”或“现代”,是颇为荒诞的一件事,犹如将一位耄耋老翁称为小伙子一样不可思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荒诞性也日益显著。其次,从内涵上说,划分现、当代文学采用的“时代”依据,只是政治史的“时代”依据,而不是文学史的“时代”依据,这一依据是主流意识形态按照中国政治革命不同时期的政治任务而制定的。它强调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意在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提出任务并进行规约,这是一种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对文学所作的政治定性,而并非是从文学自身内在性质和特征上对文学考察的结果,因此,它也就难以成为一个稳定的衡量文学史的内在尺度。由于政治定性往往随着政治权利的复杂运作、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动在游移,以它作为考察文学的尺度,也常常使文学史无法维系自身的内在逻辑的整体性,同政治尺度相悖或不符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往往不能够进入它所圈定的“当代”范围里,它们不是受到否定、批评,就是干脆被摈除于学科视野之外。因此,经过政治定性后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只是主流意识形态容忍和认可的文学。它在概念的内涵上是排斥“异端”的,在概念的外延上是不周延的,这样,所谓“当代文学”也就往往名实难副。
正是由于现、当代文学与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这种密切关联,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最强烈地意识到了上述的困扰,因此摆脱这些困扰的需求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就表现得尤为强烈。近20年来,学术界一直在寻求着对这一时段的各种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进行概括、表述的方式,不仅取得了许多有影响的成果,而且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讨论。其中,有关“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有关“二十世纪文学”“百年文学”的构想以及有关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探讨,都可以被视为突破这些困扰的尝试。我以为,就重写文学史的依据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中现代性尺度的提出。按照这一尺度,经过几千年独立发展的中国文学是在适应着近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适应着中国社会、文化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而开始了自己的现代转型的。有的学者把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起点延伸到了清末,因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借王德威一篇文章的副题)但五四文学革命却是这种“现代性”在文学中主导地位最终确立的标志,所以,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是有充分理由的。正是这种“现代性”赋予了五四以来的文学以一种有特定历史内涵的全新的精神品格,使它同已延绵了几千年的古典文学之间划出了一条鲜明的界限。对于文学史学科的建设来说,重要的是,“现代性”尺度为五四以来的文学进程提供了一种衡量历史的内在尺度,在这一尺度下,文学不必再依赖当下的政治话语来确定其自身特性,从而与这一话语的纠缠保持了适当的间距,维护了自身内在的整一性。因此,把“现代性”作为确立五四以后文学特质的依据,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可。如果说,当初人们在以“现代”和“当代”来命名新文学的两个时段的时候,主要是出于某种当时的政治策略的需要,这些命名中更多包含的是意识形态的含义,那么,当我们以“现代性”标准来衡量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并在这个意义上将它称为“现代文学”时,这一命名中原先的意识形态含义就被一个以文学自身为依据的历史和美学的含义所取代,由此“现代文学”这一命名获得了坚实的学理上合法性。但是,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当代文学”的时候,它作为独立学科的存在却受到了质疑。因为在“现代性”的标准中,“当代文学”并不能找到确立自己与“现代文学”学科性质区别的依据,它与现代文学的差别,与其说是由文学的“时代”性质所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政治的“时代”性质所决定的。在文学的“时代”性质上,“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并无根本的区别。它们都是这一百年来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是文学的“现代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因此,无论是从“当代”一词的语义上说,还是从“现代性”这一被普遍接受的衡量尺度上看,“当代文学研究”作为文学史学科的存在都是无根的、暧昧的。
那么,应如何为“当代文学研究”定位?我认为,回到“当代”一词的原本含义上去理解“当代文学”才是正途。首先应把“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还原为当下的、正在发生着的文学现象。既然这种“当下”是在不断迁移、不断流动的,因此,动态性、即时性才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特征;这样,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就不是封闭了的、相对静止的文学史,而是正在发生着的文学现象,是丰富的、变动着的当下文学创作,它的研究方法不是远距离地对历史中的文学作静观的审视、评估和总结,而是置身于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思潮中,身临其境地感受、追踪、观察其中闪现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去发现、归纳和提炼出有规律性的东西,并对文学发展的趋势与走向做出富有洞察力和预见性的评析。这种切身的近距离研究,使当代文学的研究者能够把自己对当代人生的鲜活感受、思考和体验带入对研究对象的审美感悟中,这正是当代文学研究者无可比拟的真正优势。从这个角度说,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在“冷静”“客观”上去和文学史家一竞短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研究主体保持一种深厚的历史感的必要性。恰恰相反,当代文学的研究者除了须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和洞察力之外,历史感是他们不可缺少的支撑,这种历史感可以使研究者在“入乎其内”的观察中,获得一种“出乎其外”的高瞻远瞩的概括力。因此,我认为,一些论者有关强化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学史学科特性的主张是不足取的。“当代文学”的“目前”性质,和“史”的“过往”性质使得“当代文学史”这一称谓本身就成为一种悖论。与其说应为“当代文学”设定一个封闭的下限,使当代文学研究成为文学史学科,还不如说最好为其设定一个暂时的上限,使它保持自己的“当代性”。就目前文学发展的情况而言,这一上限宜定在“新时期文学”结束以后。因为尽管从政治上看,新时期标志了一个新的开端,但就文学的形态和内在特征而言,“新时期”文学仍然是部分衔接了五四传统,部分衔接了“十七年”文学。而“新时期”以后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反映了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模式的转型过程,而且也表现了文学自身从一元到多元、从理想主义到世俗人生、从先锋性到大众性的内在发展。这些特征是否意味着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现代文学”时期的到来,在目前当然是很难说的,对我们的论题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的这种发展还在持续着,尚未完成和闭合。我们正置身其中,感受、思考甚至直接参与着这一进程,因而它才是与我们当代人生活体验切身相关的当代文学,是当代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
至于那些已成为历史的文学,包括“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等,由于它们实际上已逐渐远离我们目下的“当代”,而且它们本身也从属于自上世纪末开始的文学现代化进程,是此前所谓“现代文学”史在新历史环境中的延伸,将它们逐渐并入“现代文学史”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其实,“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而“新时期”文学又是对五四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续接,所以,它们与现代文学的阐释框架、话语规范和叙事规则并无根本冲突,完全可纳入现代文学研究框架。只不过“文革”文学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而“新时期”文学则因距我们太近需要进一步沉淀和淘洗,所以难以完全纳入史的叙述中,只能等到条件成熟,再作计议了。
收稿日期:2000-01-10
标签:文学论文; 当代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现代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