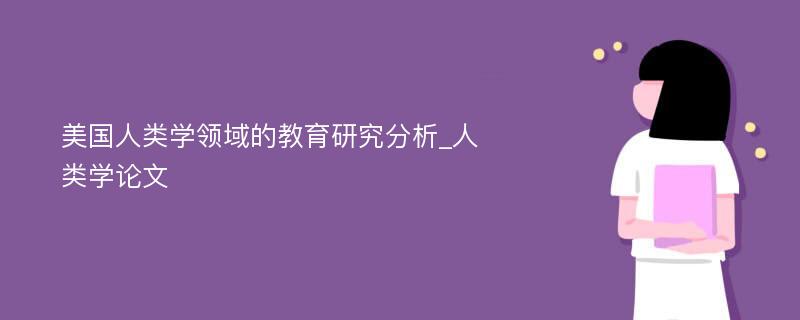
试析美国人类学领域中的教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美国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学是对人类的所有创造物——产品、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社会关系——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1]根据对人类学的这种界定,教育应该是在人类学研究范围之内的。实际上,在人类学领域的发展过程中,涉及到教育的有多个方面的研究。以美国人类学界为例,自20世纪初以来就开展了对教育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我国的教育研究领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具有多个方面的意义,可以供教育学领域更为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人类学领域关于教育研究的情况,有利于教育学领域拓宽研究的视野、借鉴有关研究方法、丰富教育学研究的途径和反思教育学领域关于教育的研究,等等。
关于美国人类学领域中的教育研究状况,已有学者进行了分析。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的人类学家奥格布(J.U.Ogbu)在其为胡森(T.Husén)主编的《国际教育大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1994)所撰写的“教育人类学:历史和概述”(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History and Overview)这一词条中的有关论述。该词条从研究领域和理论流派两个角度评述了教育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其中涉及到人类学领域中的教育研究情况。[2]纳斯(R.J.Nash)回顾了人类学与教育联姻的历史,其中通过选取介绍九位人类学研究者的研究情况,梳理了人类学领域对教育进行研究的历史。但是,上述分析均不是专门论述人类学领域关于教育的研究,分析不够全面和系统,对这些研究的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影响等相关方面涉及很少,甚至没有涉及到,使相关研究人员不能深入与全面地了解和把握人类学领域关于教育的研究。本文则以人类学领域中的教育研究为主题,根据教育研究在人类学领域中的地位,分为三个阶段对不同历史时期这方面的研究情况进行介绍与评论,同时选取其中的重要研究进行深入地分析。
一、20世纪50年代之前——作为人类学研究附带产品的教育研究
在美国人类学领域中,最初的有关教育问题的研究不是专门的关于教育的研究,而是人类学家在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探讨中,因涉及到教育问题而进行分析的结果。这种研究始于19世纪后半叶,当时美国在经历了南北战争之后,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社会的其他领域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导致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的产生。人类学家在对这些新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涉及到对教育的分析。1898年范德沃克(N.C.Vandewalker)发表了《论教育对人类学的若干要求》(Some Demands of Education upon Anthropology)一文。随后,著名的人类学家、新墨西哥大学人类学系的创建者及第一任系主任休伊特(E.L.Hewett)于1904年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上发表了《人类学与教育》(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一文,指出要使教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就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必须运用人类学的知识。1905年,他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教育中的种族因素》(Ethnic Factors in Education)一文,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当时教育中的种族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美洲印第安人、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学校迫使他们学习美国的文化,而没有考虑到他们自己民族的文化。由此,他提出建议,要分析和解决印第安本土人民和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需要对教育领域中的文化与种族因素给予关注。他还指出,有关不同群体的教育取得成效的话,应该考虑到这些群体的文化。[3]
人类学中文化相对论派代表人物、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博厄斯(F.Boas)在其研究中,有很多方面涉及到教育的分析,其名著《人类学与现代生活》(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1928)中有一章的标题即为“教育”。在研究中,他摒弃当时流行的生物解剖学方法,而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认为人的发展不是由遗传决定的,而是由环境和教育决定的。在《人类学与现代生活》的“教育”一章中,他集中探讨了教育的文化作用、教育对心理自由的影响、教育对个人生活危机的影响、受教育阶级的文化状况等问题。认为人的发展与教育、文化与教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他的许多观点是以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为基础的,例如,他认为教育通过帮助人养成一定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对文化的稳定性产生着影响的观点就是以对爱斯基摩人的分析为基础的。[4]
博厄斯对教育的关注与观点对他的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本尼迪克特(R.F.Benedic)就教育对国民性形成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二战结束后,她接受美国情报局的委托,对日本这个民族进行研究。她的研究也从文化对个体和民族产生影响的角度出发,根据有关日本的文化现象,对日本的国民性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其中,涉及到日本儿童的教养方式及其对日本国民性形成的影响的分析。例如,对于日本国民性中的强迫性特征的分析,认为这是因为日本的儿童很早就接受排泄训练,“……他们只体验到每天必须如此,不能逃避……这种无情的训练为婴儿长大成人后服从日本文化中最繁琐的强制性作好了准备”[5]。她认为,通过研究个体在儿童时期的经验,例如承受了外界的什么样的压力和期望,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他的行为和性格。此外,本尼迪克特还就教育对美国文化发展的三个功能进行了分析,这三个功能是传递、转变和改造。其研究多数依据对美国文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导致美国正规教育和早期非正规抚育过程中出现的某些恐怖的危机的观察。[6]
博厄斯对教育的关注与观点也明显地体现在她的另外一位学生、著名的教育人类学家米德(M.Mead)的研究中。博厄斯为了反对当时种族主义的遗传决定论,论证其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便计划对当时美国青年人中普遍存在着的青春期的困境进行研究,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影响的结果,而非是这个年龄阶段自身所具有的心理与生理发展的结果;于是在1925年,委派米德去距离美国本土社会万里之遥的萨摩亚地区,对那里的年轻姑娘们进行研究。在根据在萨摩亚地区的研究的基础上所写成的《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1928)一书的最后两章中,米德系统地介绍了萨摩亚人养育儿童的方式,将之与美国养育儿童的方式进行了比较,并根据前者对后者进行了分析。[7]之后,米德又对新几内亚的马努斯儿童的教育与成长进行了研究,据此写成了专著《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Growing up in New Guinea,1930)。此外,她还在关于人类性别角色的形成与教育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米德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男女两性不同的特征和社会行为方式是由两性不同的生理结构决定的。米德根据其在新几内亚的三个原始部落中田野调查研究所写成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Sexand Termperarnent: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1935)一书中提出,男女两性在人格特征上的许多差异与性别差异本身无关,而是与两性受到教养的内容和方式方面的差异是紧密相关的,而这种差异又是与该社会中的文化相联系的。[8]
在这一阶段中,其他一些产生较大影响的研究还有海尔什科维奇(M.Herskovits)在非洲西部的达荷美开展的有关教育与文化变迁的研究、雷德菲尔德(R.Redfield)在危地马拉对所谓的本土教育对文化发展的作用的研究、怀廷(J.Whiting)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社会化与教育的研究,等等。
这一阶段人类学领域中的教育研究具有下面几个方面的特征:(1)教育研究是作为人类学研究的附带产品,几乎没有人类学家专门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或以教育问题的解决为研究目的;(2)主要是人类学中文化与人格学派的人类学家开展的。如博厄斯、本尼迪克特、米德和怀廷等都属于文化与人格学派;(3)很少有研究是关于西方现代社会中教育的,主要是关于本土教育(indigenous education)的研究;(4)很少有研究涉及到学校教育,主要是关于学校之外的非正规教育的研究。
二、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教育问题作为研究主题的教育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有关教育问题的研究逐渐从人类学的研究中分化出来,人类学家开始对之进行专门的研究。其原因有:第一,随着人类学领域有关教育问题的研究的日益增多,教育越来越引起人类学家的关注,并且得到更多的重视;第二,二战期间,很多人类学家被要求在政府机构中服务,二战结束后,则将重点转向人类学学科领域的研究,因而有了更多时间与精力进行纯学科性的研究;第三,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类学家主要研究的是本土社会(indigenous society),而本土社会中没有类似于西方社会中制度化的学校教育,没有专门性的教育机构,因而难以将教育从社会中分化出来进行研究;第四,1954年6月份由斯宾德勒(G.D.Spindler)发起、美国人类学会与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和教育学院在斯坦福大学联合召开的人类学与教育大会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1953年,当时著名的人类学家、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克鲁伯(A.L Kroeber)所编写的《今日人类学》(Anthropology Today,1953)中还没有“教育”这一条目,人类学界普遍没有有意识地认识到教育这一研究领域。而该大会的主题是:教育与人类学的联系问题、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问题、教育中的跨文化问题,这些主题将人类学与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将教育从人类学领域中突出出来。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人类学领域中的教育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大大地提高了教育问题在人类学领域中的地位,使更多的人类学家对教育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有意识的关注,继而开展了大量的专门性的研究。
如斯宾德勒(G.D.Spindler)关于学校教育行政人员的研究,亨利(J.Henry)编写了关于教育的跨文化研究的大纲,金博尔(S.T.Kimball)开展了文化对儿童成长的影响的研究,等等。其中,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收录在斯宾德勒编写的论文集《教育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Education and Culture-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1963)中。
到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领域关于教育的研究更为多样,而且许多是针对美国社会的教育问题的。当时,促进人类学家对教育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因素有三个方面[9]:第一,人类学家在研究美国社会出现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时,感到需要制定措施解决国家的教育问题,尤其是贫穷的人和少数群体(minority)(注:minority这个词在国内的相关学术领域多被译为“少数民族”,而本文在此将之译为“少数群体”。这是因为,在美国的人类学或相关领域的研究中,这个词所指的对象包括来自于各个国家的移民、美国本土人民、有色人种群体、社会贫穷群体等,即与美国社会的主流群体而言处于非主流地位的群体,因而将之译为“少数民族”则缩小了其所指代的对象。本文根据其所指的群体是处于非主流的地位,认为将之译为“少数群体”比“少数民族”更为恰当(同样地,下文的“多数群体”译自于majority)。但是,笔者感觉“少数群体”仍然不能准确地表达minority的意思。究竟如何译minority这个词,期待着相关人士的探讨。)的教育问题。人类学家斯坦利(Stanley Diamond)在1963年所开展的“学校文化研究”的课题就是这样的情况;第二,对教育领域中有关文化的观点的回应。在当时的教育领域,把少数群体和低收入阶层学生学业失败问题解释为“文化剥夺(cultural deprivation)”的结果,即他们的学业失败问题是因为与中产阶级群体的文化特征相比可以发现,他们没有那样的文化特征,也就是说被“文化剥夺”了。而人类学家根据人类学的有关研究,从概念、方法论和具体立场上对这种理论进行了驳斥,认为少数群体具有不同于中产阶级的可以自足存在的文化,他们的孩子在学业方面的失败是因为学校没有采用关于他们文化的内容进行教学和评估,也就是说学校教育中所涉及的文化与少数群体的文化是不同的。对于少数群体的孩子而言,学校教育中的文化与他们的文化是不连续的。因而,人类学家主张用“文化非连续性(cultural discontinuity)”理论替代“文化剥夺”理论,来解释少数群体孩子的学业失败问题。这方面的具体研究如瓦伦丁(C.A.Valentine)对美国的非裔群体孩子的学业失败现象的研究。[10]第三,在公立学校教育中设置人类学课程的需要。为了促进公立学校中人类学课程的开设与教学,美国人类学协会设立了课程研究委员会,负责有关人类学课程的研究,为此促进了人类学家对学校课程的研究。例如,美国人类学协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AAA)与其他机构合作赞助了研究课题“人类学课程研究项目”。人类学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设置带来的相关问题,如人类学对文化多样性的强调与促进美国统一民族文化的形成和众所公认的民族自豪感这些目标之间的矛盾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关注,并促使他们对学校课程进行了研究。
这一阶段的研究具有下面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第一,对美国的所谓现代社会的研究越来越多。其原因一方面是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上出现一些新取向的影响,这些新取向如社会学领域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另一方面是在二战后美国人口流动性较大,人口特征具有明显的变化,这引起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与教育问题,这些所谓现代社会的问题的解决促使人类学家的研究出现了转向。具体的研究成果如斯宾德勒的《转型美国文化中的教育》(Education in a Transforming American Culture,1955)、纳斯(A.J.Reiss)编的《变迁社会中的学校教育》(Schools in a Changing Society,1965)、李(D.Lee)的《美国文化中的教学差异》(Discrepancies in the Teaching of American Culture,1963)、罗森(B.C.Rosen)等主编的《美国社会中的成就》(Achievement In American Society,1969),等等。第二,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民族志的研究。民族志是人类学领域中的一种方法论,是指通过在自然背景下参与观察一定人群的生活方式、行为和他们所制造的产品及所做的事情。运用这种方法开展的研究通常又被称为民族志研究。在人类学关于教育领域的研究中,民族志方法论的运用几乎与这种研究具有同样长的历史。如米德在萨摩亚地区开展的研究就是关于教育的民族志研究。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运用这种方法的研究增加了许多,这与当时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及缺乏对其解决措施有关。具体来说,人类学家在大量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用“文化非连续性”理论取代“文化剥夺”理论就是对当时少数群体学生的学业失败问题的回应。这一阶段优秀的民族志研究有杰克逊(P.Jachson)的《课堂教学中的生活》(Life in Classroom,1968)、史密斯(L.M.Smith)和杰弗里(W.Geoffrey)的《城市课堂教学的复杂性》(The Complexities of an Urban Classroom,1968)、史密斯(L.M.Smith)和基斯(P.M.Keith)《教育革新的剖析》(Anatomy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1971),等等;第三,研究的应用性较强。具体来说,很多研究是人类学家将人类学的有关研究成果运用到教育领域中,进行有关教育问题的研究。这与当时主要接受的是人类学学术训练的研究者们对解决教育问题的观念有关,即认为在教育问题的解决中可以应用人类学的有关研究成果和采用人类学的研究途径。例如,斯宾德勒在1955年出版的1954年人类学与教育大会的论文集“导论”部分中就指出,人类学对教育研究的意义在于能够对教育背景中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正如解释工厂、医院、农村、空军基地、印第安人保留地、新英格兰的城镇和各种类型的原始社会中的行为……人类学领域中有一些(与教育)直接相关的具体领域的概念与资料,如人格与文化(心理人类学领域内)、文化动力(cultural dynamics),可以用于教育问题的解决中。[11]
三、20世纪70年代之后——作为人类学独立研究领域的教育研究
在人类学领域中,教育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的标志是教育人类学学科的诞生,其时间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而当前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教育人类学产生的标志则是1970年在人类学协会(AAA)中成立了人类学和教育委员会(Council on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CAE)。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开展教育研究的人类学家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关于教育的研究,促进这个领域研究的发展。这个委员会出版一份工作简讯,该简讯于1978年改为杂志,名为《人类学与教育季刊》(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关于教育研究的人类学专业性研究机构与研究刊物的出现大大地促进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的发展,也大大地提升了其在人类学领域中的地位。
这一阶段的研究有几个重要方面的特征:第一,一些研究者提出了研究的理论模式。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有斯宾德勒的工具性理论模式(Instrumental Model)。该理论模式是在对若干理论模式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一模式所基于的假设是,“只要社会接纳的行为常常产生能够预期的和符合人们愿望的结果,社会不接纳的行为产生能够预期的而不符合人们愿望的结果,那么文化系统就能够运行”。[12]行为或活动是实现生活中各种目的的工具,行为或活动与目标之间的关系是“工具性关系”。教育可以培养儿童特定的行为,使儿童的行为能够产生某一文化所期望的结果,并且使儿童从中得到相应的回报,例如社会地位、金钱等。通过教育建立的这种工具性联系,社会文化得以运转起来。斯宾德勒用这一模式在北美、德国不同的群体中进行了试验研究。在德国,他将这个模式运用到关于农村学校里孩子的研究中,以了解城市化如何影响学校内和学校外的文化传播。他通过这种研究认为,尽管新的课程的引入促进了当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但是村民的态度仍然倾向传统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其原因是社会原先的文化对他们具有保护作用,即给他们更多的回报。斯宾德勒还为这一模式的运用开发了一种专门的技术——工具活动调查表(IAI)。除了这一理论模式之外,还有研究者提出了其他理论模式,如交换理论、结构一功能主义理论、生态学理论等。
第二,出现一些主题相对集中的研究领域。尽管奥格布认为,根据对随机抽取的《人类学与教育季刊》的统计以及关于一些研究学者的调查表明,人类学领域关于教育研究的主题比较分散。[2]但是,深入分析一下可以看出,相对而言,在研究的具体领域方面有几个主题是集中的。本文在此对双语教育、城市中社区与学校的关系和课堂教学三个方面作具体分析:
(1)双语教育。这个方面的研究是由20世纪70年代之后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所引起的。人类学领域关于双语教育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从不同参与者和不同背景的角度对双语教育进行了具体分析。例如,保尔斯顿(C.B.Paulston)在其较有影响的《双语教育:理论与议题》(Bilingual Education:Theories and Issues)一书中将双语教育实施的背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状况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并据此提出,双语教育的文化、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对解释的其结果是必不可少的。施佩勒(D.Spener)则详细地分析了社会背景是如何决定双语教育发展的。例如,在对美国双语教育转型的研究中,他细致地分析了将双语教育看作使移民获取有限工作的合法化方式的政治和经济背景。[13]另有一些研究者还对双语教育领域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如皮斯—厄瓦瑞斯(L.Pease-Alvarez)的研究,他对北加利福尼亚农村中说英语的社区如何开展以所有学生双语能力的提高为目标的教学进行了分析,深入细致地探讨了导致多数群体(majority)和少数群体的孩子不同的双语能力的社会因素。[14]
(2)城市中社区与学校的关系。社区与学校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人类学开始关注教育时就已经出现过,如引起较大影响的人类学家刘易斯(O.Lewis)的研究。刘易斯在研究中提出,社区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学前阶段儿童的学习与学业成就必定会产生影响。不过,当时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少的。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大量的有关城市中社区与学校关系的研究。引起出现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中有关的教育问题引起了人类学家的重视;另一重要原因是学校被认为是消除城市中的贫穷与种族隔离的重要因素,为此,人类学家被要求提供进行学校与外部社会关系的方面的研究。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奥格布等人的研究。奥格布指出,已有的有关研究主要限于学校与社区之间的互动层面。他本人的研究更为明确地分析了影响社区一学校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结构性因素。在关于加利福尼亚斯托克顿的一个名叫“布格斯德”的社区研究中,他说明了关于黑人学生学业失败的解释为什么必须要考虑到诸如居住方面的隔离状况及其对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的影响等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他认为,黑人形成了一种“理论”,这种理论不会使他们在学业上作出努力,或形成对学业的积极与乐观的态度,而会导致他们将学校看作是对他们自己身份的威胁。这使黑人青年难以接受和遵守有助于他们学业成功的学校中的规范,使得他们寻求其他的基于个人的(通过卖淫等方法)或基于集体的(通过反抗或法律行动)“实现成功”的方法。[15]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希思(S.B.Heath)的研究涉及到语言在学校教育与社区关系中的作用,在《词汇之路》(Ways with Words,1983)一书中分析了白人工人阶层社区和黑人工人阶层社区中的孩子语言的社会化,以及这种社会化对他们在主流学校中所经历的学习困难的影响。[16]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城市中社区关系的研究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如受到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在理论上这种研究变得更为复杂化;同时,研究者参与课程开发和师资培训,使这种研究的服务性更强;另外,引入和借鉴了批判理论的一些研究成果,更为关注学校内外的行政人员、教师、家长和学生的态度与行为的政治、社会和教育意义。
(3)课堂教学。20世纪70年代之后,人类学界出现了关于课堂教学的专门性研究。影响人类学领域开展关于课堂教学的研究具有多个方面的原因,如学术思潮的影响、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课堂本身的特征等。具体来说,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众多的人类学家认识到要深入与全面地了解学校教育教学的状况,则需要对教育的重要背景“课堂”和过程“教学”进行研究。这种研究的出现表明人类学界对教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专门化。
具体来说,人类学界关于课堂教学的研究有几个相对集中的方面,如课堂话语结构、认知活动、学业失败问题等,在这些具体方面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课堂话语结构为例,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有米恩(H.Mehan)提出的I-R-E结构。具体来说,课堂中的对话是由三个有先后次序的部分组成的,这三个部分是:“教师启发”(Initiation,即教师提出一个已知的问题)、“学生反应”(Response,即学生对问题的反应)和“教师评价”(Evaluation,即教师对学生回答的评价)。[17]卡茨顿(C.B.Cazden)则指出,在这种I-R-E模式中,包含了超越于这种对话形式的更为丰富的内容,它体现了学校教育的一种结构形式,也表现了学校教育中的权威关系。并且,由于这种话语结构的存在,使得学校教育的结构形式和权威关系得以继续循环下去。[18]。
第三,对作为研究方法论的教育民族志进行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学领域中教育研究的进展,研究方法论教育民族志也得到了发展。在如何进一步改善这种研究方法论方面,一些研究者也进行了探讨。在胡森主编的《国际教育大百科全书》中就有一个词条专门介绍教育民族志,该词条是由奥格布等人撰写的,主要概述了民族志定义、民族志应用于教育中的历史、教育民族志的类型、教育研究中运用民族志的优点与缺陷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内容。另有研究者则在一些方面进行了详实与专门性的研究。例如,有的研究探讨如何开展教育民族志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斯宾德勒夫妇的《教与学:如何开展教育民族志研究》(Teaching and Learning:How to Do the Ethnography of Education,1988);有的研究分析如何将这种方法论运用于教育评价中,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费特曼(D.M.Fetterman)主编的《教育评价中的民族志》(Ethnography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1984);有的研究就完善这种方法论进行了探讨,如戈茨(J.Goetz)和勒孔特(M.LeCompte)的《教育研究中的民族志与质性研究设计》(Ethnography and Qualitative Design in Educational Research,1984);有的研究细致地分析了教育民族志研究的类型,如奥格布的《学校教育民族志:多层次的方法》(School Ethnography:A multilevel Approach,1981);有的研究分析了新的学术思潮的影响,如安德森(G.Anderson)《教育研究中的批判民族志:起源、现状与新的方向》(Critical Ethnography in Education:Origins,Current Status,and New Directions,1989)分析了受新马克思主义等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批判民族志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有的研究涉及对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与地区教育民族志研究的介绍,如丹尼尔(A.Y.Daniel)的《教育民族志的历史概述》(Highlights Overviews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Ethnography,2003);等等。
第四,出现了专门的研究组织和专业性的研究人员。1970年美国人类学协会中人类学与教育研究委员会的成立,使得人类学领域的教育研究有了专门的组织,可以开展这一领域内的交流活动,就有关问题开展合作研究,大大地促进了研究的发展。同时,出现了专业的研究人员,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专门对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开展关于教育的更多方面的系统与深入的研究。
近些时期,人类学领域的教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例如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等影响,出现了一些文化与政治学视角的分析;与相关的领域进行合作,例如,在人类学与教育委员会的会议中,经常邀请教育学领域的相关专家参与;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在教育政策、教育管理这些之前很少被人类学家关注的方面也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对本土教育的新视角的研究(注:如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erterly最近出版了主题为Indigenous epistemologies and Education的专刊,见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2005, 36(1).);等等。
标签:人类学论文; 教育论文; 教育研究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双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