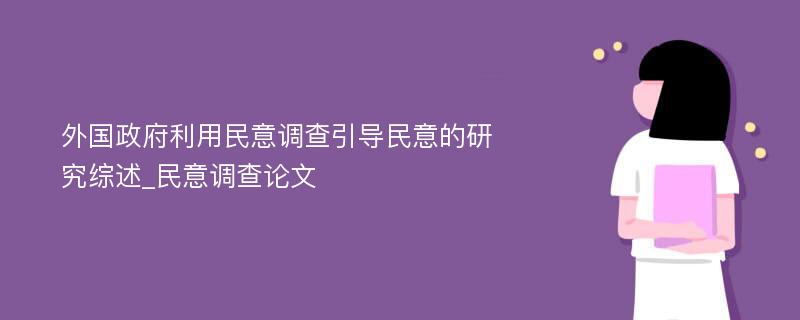
国外政府利用民意调查引导民意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意论文,国外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07)02—0125—04
在国外政府的政治过程中,民众的态度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影响因素。因此,影响和引导民意,成为决策者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证明,由于民意调查可以扮演双重角色,既可以反映民意,也可以塑造民意,决策者在利用民意调查时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决策者是不愿被一堆统计数据牵着鼻子走的,而更希望利用民意调查来引导民意,为其政策服务[1]。正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说,通过大众传媒,精英们塑造他们想要的公众态度,民意调查只不过是操纵民意过程中的一种工具而已[1]。本文主要介绍国外政府如何重视民意调查、怎样利用、影响和塑造民意。
一、国外政府对民意调查的重视
民意调查也称民意测验,是“运用系统性、科学性、定量性的步骤,迅速、准确地收集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意见,以检视公众态度变化的社会活动,其主要功能是真实反映各阶层民众对公共事务的态度,以为政府或相关单位拟订、修正、执行政策的参考”[2]。盖洛普认为应该把民意测验当作一个“公民复决”来看[3],并在所著的《民意测验指南》(A Guide to Public Opinion Polls )中说明民意调查的功用:民意调查供给政治民意的准确判断;提供准确、快速的民意报告,从而加速民主政治的过程;显示一般民众能做正确决定;协助人们注意现时的主要问题;发现许多人们不注意的领域;使政治领袖要在烟雾弥漫的房里当选总统候选人,更加困难;民意调查显示,不像许多政客预想的,人们在投票时,只受到自己利益的激励;民意调查几乎是制衡日渐做大之压力团体的惟一力量[3]。可见,民意调查的政治功能使得国外政府不得不重视。
有学者将国外的民意调查看作是:公共舆论的“晴雨表”[2]。公共舆论作为国外政府决策“风向标”,长期以来不仅受到利益集团的重视,而且更受到从国会议员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他们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常常想尽各种办法借助公共舆论为自己服务,民意测验就是议员利用公共舆论的一种好办法。在美国政治中,民意测验可以说无所不在,从组织竞选到制定具体的政策。美国学者本尼杰(Beniger)和基乌弗拉(Giuffra)民意测验认为,竞选过程中9个重要的决策都依赖于民意测验:决定参选;筹款、聘请顾问、获得关键人物的支持;增加知名度和形象;决定选民的喜好;攻击竞争者的弱点;发展媒体广告;分配资源;影响党代表并选择副总统候选人;追踪竞选的每日状况[4]。民意测验的结果,往往可以帮助选民发挥“临门一脚”的效果,选民们的投票行为往往与所获得的选举民意测验结果、人际传播资讯以及它们对选举气氛的感觉有关。不管哪一种选民,他们的投票行为都依赖于对选战形势的判断,而民意测验就是为人们提供这种选情的预报,其影响力可想而知。受此影响,大多数引起公共舆论纷争的政策问题,民意调查也会出来凑热闹,展示社会上对某一个问题的基本态度。可以说,在选举和政策结果一锤定音之前,“不断变化的民意测验数字犹如富有魔力的灵巧手指,拨弄着上至总统候选者,下至选民以及各式旁观者的心弦。美国的民意测验实际上不仅是大选形势的晴雨表,更是大选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4]
民意如流水,民调如探针。美国新闻界的民意测验和各类民调机构的测验数据,可以帮助政治竞选人和政府官员了解有关社情民意的重要情况。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在进行任何决策的时候,都不敢轻易忽视民意测验反映出来的公共舆论情况。当年林肯就表达了这方面的意见,“我所想的,是做好人民希望完成的事情。对我来说,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准确地把它找出来。”[5] 不用说,民意测验为美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了解民意的渠道。尤其对于作为代议民主机构的国会,更注重通过民意测验了解公共舆论的动向,尽量拉近决策和民意之间的距离。特别是国会领袖,民意测验帮助他们解决了决策过程中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民意测验帮助他们了解公众在想什么,以便于在争论激烈的问题上建立“支持阵线”;二是民意测验有利于聚集和确定有关的信息,在错综复杂的问题网中找出最重要的问题;三是民意测验可以帮助提供支持立法立场的象征性的姿态,为人们确立一盏“立法指路明灯”[6]。即使那些轻视民意测验的议员,在起草立法的时候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民意测验获得的有关信息作为依据,看上去民意测验的力量不同于利益集团和政党的力量,不是外部的压力,但是这种力量实实在在地作用于议员内心决策天平,只不过没有表现为社会压力体系而已[7]。
事实证明,在总统和国会对外事权力的争夺中,民意是一个重要的筹码。一般而言,国会议员与民众的关系比较密切。为了赢得决策上的主动,总统更需要“走近公众”(goingpublic),寻求他们的支持,以期促使民选代表投票支持其政策[4]。
在国际政治的层面上,民意可以使外交决策者在与他国谈判时更具讨价还价的筹码[4]。民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外交决策者执行外交政策的一种资源。民意越一致,越支持政府的政策,决策者在与他国谈判时讨价还价的能力就越强。而且,即便民众在政策形成过程中保持沉默,决策者在谈判桌上也可以说某项拟议的让步是美国民众所不能容忍的,或者说某项政策是出于民众的意志,并由此而获得相当大的谈判优势[1]。
既然民意测验可以方便组织者操纵,而且能够严重地误导公共舆论,那么,究竟应不应该允许其卷入美国政治进程?不少人提出要禁止或者限制民意测验,尽管存在众多的批评,取消民意测验显然是不可能的。美国是一个自命为自由民主的国家,这个国家应该由谁来领导,应该解决哪些普遍的问题,对于制度的运转和完善是极其重要的。民意测验恰好反映了选民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这个过程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它是民众参与政治并得到政治修养训练的重要实践活动,不了解政治竞选的情况,就如同观看一场篮球比赛或者足球比赛而不知道比分一样。民意测验的存在帮助人们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了解政治运作的历程,实在是善莫大焉。至于其中存在的问题,按照美国人的政治思维和民主理念,只有靠制度的完善加以解决,而不是通过禁止其存在得到解决。这就是美国的政治逻辑。因此,民意测验仍将是美国政治及其政治报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力量如此强大,根本无法抛弃。本杰明·富兰克林早在200多年前就说过,世间只有两件事情是必定无疑的:一是死亡,二是纳税。如今,他或许会把民意测验算进去[1]。
二、国外政府对民意调查的利用
国外政府对民意的利用,在许多研究中是显而易见的。以美国为例,美国外交决策者对民意的看法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让民意影响外交政策的选择是否明智;二是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是否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据此,道格拉斯·福伊尔(Douglas C.Foyle)将美国总统分为四类:民意的代表(delegate)、民意的执行者(executor)、民意的实用主义者(pragmatist)以及民意的监护人(guardian)[4]。有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总统中,杜鲁门、约翰逊和里根属民意的监护人,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福特和老布什属民意的实用主义者,卡特和克林顿分属民意的执行者和民意的代表[1]。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总统大部分属民意的监护人或民意的实用主义者。这两种人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让民意影响外交政策的选择是不明智的。前总统肯尼迪的一位幕僚这样说:“没有哪一位总统有责任遵从民意的指示……他有责任尊重民意,并以此来引导它,塑造它,告知它,拉拢它,并且战胜它。民意既是他的罗盘,又是他的刀剑。”[1]
例如,1994年9月,在克林顿命令美军入侵海地的前几天,《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刊登了一幅漫画:满载军人的登陆舰正靠近海地,甲板上的克林顿口中振振有辞:“难道不应该让民意测验人员打头阵吗?”[1] 这幅漫画充满了作者杰夫·麦克内里(Jeff MacNelly)对克林顿的讽刺,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的决策过程中,民意扮演何种角色?早在1984年,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尔·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在关于美国向海外派兵的适当前提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列举了6个必要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须有某种合理的保证能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但其内阁同僚、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则公开反对这所谓的“温伯格主义”(Weinberger Doctrine),认为这实际上成为不行动的借口,即便美国在海外的重大利益受到潜在的威胁[1]。陈文鑫研究认为,虽然存在着对民意的诸多诟病,美国总统还是很重视民意测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首开雇用专业民意测验顾问的先河。1936年,盖洛普、克罗斯利和罗珀三家民意测验机构准确地预测出罗斯福将大选获胜,罗斯福本人因此成为民意测验的热衷者。他聘请普林斯顿大学的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考察与之相关议题的民意,尤其是民众对欧战的看法[1]。罗斯福之后的许多总统也很重视民意测验。在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执政期间,“民意分析成为总统直辖的政府机构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智囊们担负着跟踪民意测验数据的任务。此后的政府也成为“民意数据的名副其实的仓库。”[1]
又如,法国的报纸虽然全都标榜其独立性和公正性,但每家报纸的政治倾向也是公开的秘密。不同政治倾向的报纸所公布的调查结果有时相互矛盾,大相径庭。原因也很简单,尽管民意调查机构标榜客观公正,但毕竟是靠客户来挣钱吃饭的,那么,客户“有倾向性的需求”,自然不能不反映在调查的结果上。“调整”调查结果的方法很多,像调查时拟订的各种问题便有“文章”可作。然而,广大民众难以看透其中的玄机与奥妙,于是民意调查常常成为政客们掌中的玩物。在大选期间,他们利用普通百姓的“从众心理”或“投胜利者票”的心态,纷纷展开有倾向性的“民意调查”,在新闻媒介上大造自己必将获胜的声势,诱导选民投自己的票。民意调查的本意是反映民众意愿,但此刻却本末倒置。这不能不说是民意调查的一种悲哀。这种弊端在1990年代中期的法国总统大选中暴露无遗:在第一轮投票之前,媒介公布的各家民意调查机关的预测几乎一致认为,希拉克将以得票率最高进入第二轮。然而实际结果出乎意料,并不看好的社会党人若斯潘却以极大的优势超过了希拉克。人们被民意调查预测着实地戏弄了一番。究其原因,各派实力对比的真实情况完全被媒介中硝烟弥漫的“民意调查大战”给扭曲了,而行使选举权利的广大选民则始终处于茫然之中[8]。
有研究认为,外交决策者对民意调查的热情应该主要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以美国对外政策与民意关系为例,虽然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关于民意与外交决策的关系一直存在着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1],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威尔逊自由主义外交理论走向终结,现实主义的民意观逐渐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流观点[1]。理查德·巴尼特(Richard J.Barnet)在其讨论美国历史上民意与对外政策之间关系的著作《火箭的红光:美国走向战争时,总统与人民》一书中说,“美国总统们为了把他们对外政策的构想包裹在‘民意’这一合法的斗篷里,不断斗争以限定民意。他们大都接受一个支持其政策的‘沉默的大多数’的存在,他们大多相信被‘我们人民’(We,the People)事实上想要的东西指导是既不可能也非明智的。”[1] 西奥多·罗斯福直截了当地说:“我没有去占卜(divine)人民会想什么,我只是主观断定他们应该想些什么,然后尽我最大的努力让他们去这样想。”[1] 同样,杜鲁门顾问乔治·埃尔西(George Elsey)也坦言:“总统的工作是去引导民意,而不是去做(民意的)盲目追随者。你不能坐等民意来告诉你该做什么……你必须决定你将做些什么,并照此做,然后再试图去教育民众你这样做的原因。”[1]
在此过程中,民意调查是一个重要手段。通过民意调查,决策者得以了解民众对某项对外政策的看法,从而采取措施,通过宣传或其他手段调整民意。有调查显示,在约翰逊1965年宣布他的越南政策之前,只有42%的民众支持这一政策;但在政策公布之后,有72%的民众支持。美国入侵柬埔寨之前只有7%的人支持,但在尼克松宣布1970年入侵之后,则有50%的人支持。1989年5月,在诺列加宣布巴拿马的选举结果无效之后,有59%的人反对美军入侵巴拿马以推翻诺列加,到10月反对率上升到67%。但在布什政府12月的行动之后,80%的人认为美国派武装力量进入巴拿马,推翻诺列加是正当的[1]。这种现象被称为“团结在国旗周围”(rally-round-the-flag)[1]。自从约翰·穆勒把这一术语引入政治学后,它就成为有关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的论著中经常出现的术语。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学者之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爱国主义高涨是导致此种现象的原因;有人则将之归因于危机初期精英批判的缺席或媒体对批评观点报道的缺少,因为这个时候政府是媒体信息的首要来源。在诸多因素中,政府的政治宣传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海湾战争期间,在美国的政治宣传中,萨达姆比希特勒还坏[1],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时,伊拉克则是“邪恶的轴心”之一。此外,美国的新闻媒体也不断刊登各种民意调查结果,表明支持政府的立场[1]。
美国非常重视利用民意调查进行舆论同化,例如,2002年,美国颇具影响的民意调查机构皮尤人与新闻研究中心,在皮尤基金会以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的支持下,启动了“皮尤全球态度项目”(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s),每年就全球范围的若干重大问题在世界主要国家中进行民意调查取样,并形成年度报告。该调查报告涉及全球44个主要国家和地区,样本空间超过6.6万人。奥尔布赖特认为,“皮尤全球态度项目……是通过对成千上万的世界民众所做的深入的几乎是面对面的访问而得来的调查结果。它是同类民意调查中最广泛、最深入的,其目的是提供给公众、媒体以及决策者以关键的、及时的信息”[19]。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皮尤人与新闻研究中心的主席安德鲁·柯哈特(Andrew Kohut)指出,该民意调查的目的是展示全球公众舆论“对于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领导下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美国文化、价值观和商业操作等在世界的扩展等问题的态度”[9]。
三、民意调查对民意的影响与塑造
自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在1935年10月把民意资料提供给了35家报纸,以此开创了用科学的手段测量公众舆论并把结果公之于众的方法,对于国外政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民意测验本身就是新闻,正如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第一个顾客《华盛顿邮报》当时的发行人尤根·迈耶(Eugene Meyer)所说:“民意测验改变了新闻本身。”[3] 有研究认为,20世纪60、70年代是美国调查性新闻风起云涌的时代。针对越南战争、五角大楼文件案、水门事件进行的一系列调查,从单纯地挖掘黑幕新闻扩展到揭露全国性问题及其有争议的事件,引导舆论,特别是《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揭露,对以后总统和新闻界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
法国新闻媒体十分看重民意调查,认为它可以“客观公正地”反映民情民意,对于读者来说,一份简单的调查数字表要比一篇记者报道更具有说服力。因此,各报无不在民意调查栏目上下功夫,翻开每天巴黎出版的报纸和刊物,读者总会看到一项或几项民意调查结果,篇幅一般并不大,但处理得十分醒目:有的用图表方式、一目了然;有的用图解方式,形象生动;有的把重要的数据套色印刷,重点突出。巴黎出版的政治性刊物《巴黎竞赛》、《新观察家》、《快报》、《星期四事件》等对某个重要事件或题材进行深入报道时往往要配发有关的民意调查结果来加以佐证。法新社则选择重大的民意调查结果作为消息向全世界公布,公布结果时一并公布承办调查的机构,因而有关的民意调查机构和新闻媒体的声望也随之提高。
有研究认为,在民众接受民意调查的过程中,传统看法认为,民众具有先验的态度(preexisting attitude),他们只是把这种态度流露给民意调查机构。但威尔逊(Timothy D.Wilson)和霍奇斯(Sara D.Hodges)反对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民众经常性地建构他们的态度,而非只汇报精神文件(mental file)的内容。”也就是说民意测验得出的民意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一种“临时建构”(temporary construction)[1]。
约翰·扎勒(John R.Zaller)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发现民众在回答问题时,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历时不稳定性(over time instability)。1980年1月和6月,美国的民意测验机构就美国是否应该努力和其冷战对手前苏联合作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在1月份支持对前苏联采取强硬立场的人中有60%到6月份仍然坚持其立场,其余40%则分散到其他三个选项(与苏联合作、中间立场、无观点);那些在1月份的调查时持中间立场的人中,只有24%到6月份依然如此,其余的大部分人转而主张合作或不合作。总共只有50%的人在两次测验中持相同的立场。对这种现象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一些人在不同的调查中的确出现意见改变,但扎勒认为,已有的证据不支持这种解释。他认为,出现在民众公开的意见表达中的波动是由“测量误差”(measurement error)所致[1]。
第二,回答效应(response effects)。20世纪70年代有一个关于美国人对前苏联新闻工作者看法的著名调查。在分开的一半样本中,37%的受访者同意允许共产党记者进入美国。在另一半样本中,受访者先被问及美国记者是否应被允许进入前苏联,结果同意允许前苏联记者进入美国的比率达到73%,几乎翻了一翻。扎勒认为,每个人可被假定为至少有两种考虑,一种关于共产党,另一种则关于公平对等原则。关键是看哪种考虑会被问卷凸显。
第三,问题措辞效应(questiorrwording effects)。1983年《纽约时报》的民意测验发现,民众对当时的一个热点问题——“冻结”核武器生产的支持率在18%和83%之间的波动,取决于问题如何设定。这说明问题的不同措辞方式通常对民众某一问题的统计学层面上的支持率有很大影响,而且即使根本的问题完全一致,民众也会有不同的反应[1]。
上述民意调查的特点使我们看到,民意调查及其机构具有塑造民意的可能性。问题的关键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国外政府通过实施有关策略,利用民意调查及其机构影响和塑造民意。劳伦斯·雅各布斯(Lawrence R.Jacobs)和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Y.Shapiro)通过研究尼克松政府与两大民意调查机构——路易斯·哈里斯(Louis Harris)和盖洛普组织(Gallup organization)的关系后发现,尼克松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策略,与哈里斯和盖洛普调查机构合作,从而操纵民意调查结果和民意。虽然白宫没有能够以其所希望的方式来控制这两个机构中的任何一个,但是通过与这两个机构接触,尼克松及其助手们获得了三个好处:首先,民意调查机构使白宫在民意调查结果公布之前就可获得信息,使白宫可以采取措施扬长避短;其次,白宫促使民意调查机构选择对之有利的问题和措辞方式;最后,白宫影响调查的结果。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哈里斯因白宫的压力而修改其公布的结果[1]。
为什么民意调查机构要与政府合作,来塑造民意?陈文鑫分析认为,原因之一是在美国,外交政策常被看作是“高于政治”(above politics)。根据这种观点,国内政治服从于国家利益。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美国人会搁置他们的党派分歧,支持政府的政策。莱斯利·盖尔布(Leslie Gelb)在《越南的嘲弄:加工过的体制》(The Irony of Vieinam:The System Worked)一书中说,“有一个美国神话,政治止于水边”[1],即“正常的党派竞争和分歧在对外政策上让位于团结一致。这个神话是虚幻的,但仍然有说服力。”[1] 其次,白宫也会利用民意调查机构的爱国心,把合作等同于国家责任。在研究中,劳伦斯·雅克布斯和罗伯特·夏皮罗采访了路易斯·哈里斯和盖洛普的高层,这些人员告诉他们说,他们会和接近他们的每位总统合作,包括比尔·克林顿,因为他们把这视为是“对国家的一项公共服务”。小盖洛普解释说:“当白宫召唤的时候,你不能说,‘走开!’”[1] 在尼克松政府时期,民意调查机构和白宫的联系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哈里斯在民意调查结果公布十天前,就把结果呈送白宫并询问科尔森(Charles Colson)[1] 对此有何看法[1]。
沉默螺旋理论认为,个体拥有一个多半是无意识的、可能源自遗传且根深蒂固的孤立恐惧。这种孤立恐惧使他们不断去确定,哪种意见及行为方式被环境所赞同或反对,以便采取哪种意见与行为方式,排除哪种[10]。而基于抽样调查产生的民意一经发表,本身又成为一种舆论,使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运转起来。因此,被有些政治学家称之为“乐队花车效应”(bandwagon effect)或“羊群效应”(herd instinct)。也就是说,民意调查结果公布之后,它本身又会成为一种社会舆论,反过来对民众的态度产生影响[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