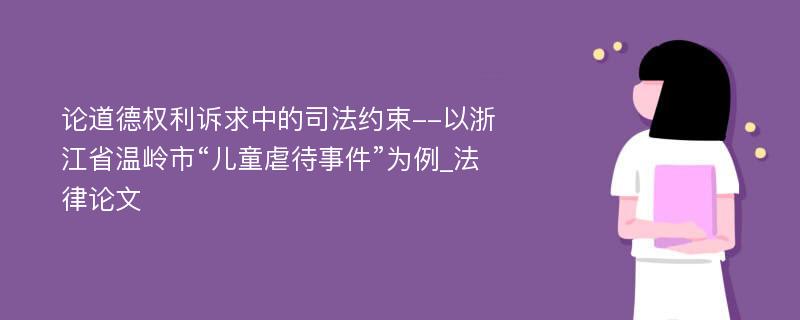
论道德权利诉求中的司法克制主义——以浙江温岭“虐童事件”为分析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岭论文,浙江论文,司法论文,权利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与深层转型,以工商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和以市场经济为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正推动了一个以陌生人社会为突出特征的现代社会格局快速形成。与传统熟人社会相比,陌生人社会既是一个高度依赖法治的社会,更是一个高度依赖道德尤其是职业道德和公共道德的社会。因此,陌生人社会需要通过法治来保障公民的权利尤其是法律权利,也需要通过道德尤其是职业道德和公共道德,来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尤其是道德权利。在社会转型时期,道德的义务感和责任感甚至处于一种明显“缺失”的状态,我们的社会似乎正迎来了一个“道德相对失序”的时代。在一个“道德相对失序”的社会状态里,人们在道德权利的诉求当中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往往集中地倾轧到司法领域当中。正因为如此,司法和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当前转型中国社会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在相关具体的道德权利诉求当中,社会舆论总是希望司法担当“明辨是非”的角色,并发挥“惩恶扬善”的社会效果;而对于司法而言,法治社会中“依法司法”的基本理念,则要求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等应该严格依法司法,排除法律之外相关因素包括社会舆论的影响,并依据法律的理性精神进行合法性的司法和客观公正的司法。与张学英案和彭宇案等涉及社会道德问题的司法个案相比,在浙江温岭“虐童事件”中,针对肇事者颜某严重侵犯幼儿道德权利的虐童行为,尽管社会舆论进行了强烈谴责和批评,甚至要求通过“重判”来迅速遏制此类虐童事件的再发生,但是浙江温岭的司法部门,最终还是以一种明显克制的司法姿态办理了该案。而对于这一结果,社会舆论也正在以一种较为理性和冷静的方式予以接受。 应当指出的是,在近些年来所发生的社会热点事件当中,浙江温岭的“虐童事件”集中地反映了当前中国教师职业道德所浮现出的相关危机。面对幼童在幼儿园被颜某虐待的惨况和无奈,浙江温岭的“虐童事件”似乎更触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神经,幼童的道德权利保障和诉求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深度思考的一个社会问题。就司法层面而言,司法部门在浙江温岭“虐童事件”当中所采取的克制司法姿态,却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司法在道德权利诉求当中的一种克制主义发展趋势。尤其就刑事司法层面而言,“克制主义的刑事司法”乃是克制主义司法的集中体现,这既是刑事司法在适用和解释刑事法规范当中遵循“刑法谦抑原则”的基本体现,也是未来中国刑事司法发展的重要方向。 二、浙江温岭“虐童事件”中司法的克制主义 近些年来,随着影像技术的普及,有关幼师在幼儿园虐待甚至是体罚幼儿的事件不断被网友曝光,从而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据媒体报道,就在浙江温岭“虐童事件”发生稍前,于2012年10月15日,在太原市某幼儿园,一名五岁的女童因为不会算术题“10+1”,在短短的十几分钟时间里,被女幼师狂扇了几十个耳光。事发之后,肇事者被行政拘留了十五天,该幼儿园也被依法取缔,太原市相关部门迅速组成联合执法大队,对辖区内幼儿园进行了集中清理和整顿。①十天之后,即2012年10月24日,在浙江温岭某幼儿园,女幼师颜某因图“一时好玩”,竟强行揪住一名男童的两只耳朵猛向上提,被揪耳幼童双脚离地近20厘米,表情痛苦,号啕不止……事发之后,颜某因其“近乎残忍”的虐童行径,激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愤慨,并迅速被推倒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随后,经过警方查明,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有关颜某的形形色色“虐待”幼童的照片,竟达700余张,照片内容包括诸如“在嘴上贴胶布”、“垃圾斗盖头”、“挤嘴”和“将幼童倒插垃圾桶”等。② 面对浙江温岭所发生的这起“虐童事件”以及之前媒体报道出的系列虐童个案,社会舆论认为,“虐童事件”反映了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幼儿教育中,普遍存在着幼儿教育不规范、幼童被幼师虐待和幼师缺乏基本的教师职业道德等诸多社会现实问题。针对浙江温岭所发生的这起极其恶劣的虐童事件,社会舆论普遍要求司法部门对肇事者颜某,应该通过法律尤其是通过刑事法律来予以“重判”,以迅速遏制此类虐童事件的再发生。③可以看出,对于近些年来频发的“虐童事件”,社会舆论出于对幼儿在幼儿教育中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的关心和焦虑,出于对未成年人权利的法律保护尤其是刑事法律保护的理性思考,和对幼师缺乏基本教师职业道德的震惊以及出于对幼师残忍虐童幼儿行为的“零宽容”,要求对肇事者颜某施予“重判”,这既体现了社会对未成年人尤其是儿童权利保护的迫切法律诉求,也体现了社会对幼儿教育以及其它相关职业(例如,保姆职业和医生职业等)自我规范和自律的强烈道德权利诉求。 与此前所发生的系列虐童个案相比,在浙江温岭的“虐童事件”中,颜某的虐童行为具有主观恶性大、危害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和违背基本人性观念等突出特点。正因为如此,社会舆论要求对颜某的虐童行为“通过‘重判’予以严厉惩罚”,这在捍卫社会的基本“道义”观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因为如此,事发第二天,温岭市公安局以“寻衅滋事罪”,对颜某展开立案侦查,并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对于为何是以“寻衅滋事罪”展开立案侦查,温岭市公安局专门作出了“新闻说明”。温岭市公安局法制室教导员蔡黎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对以“寻衅滋事罪”展开立案侦查的法律依据和刑事司法政策等进行了详细阐释。 他指出,在法律依据上,在此之前,虐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多以“虐待罪”、“侮辱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名进行立案侦查,而在温岭“虐童事件”发生之后,检方也曾经将上述罪名纳入考量范围,但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均有所不符。根据刑法规定,其中,“虐待罪”是发生在家庭成员范围之内,犯罪对象所针对的对象是家庭成员;而幼儿园老师虐待幼儿,幼儿不属于家庭成员,所以无法适用该罪名。在“故意伤害罪”中,被侵害者的具体伤势要达到“轻伤”以上才符合立案标准,而本案则明显达不到。“侮辱罪”是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只有当事人“自行”到法院提起诉讼才受理。在本案中,颜某的虐童行为,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动机和目的是“藐视社会公德、寻求心理上的刺激、内心无聊”;在客观方面,颜某在近两年时间里,多次对幼儿实施了虐待行为,严重侵害了幼儿的身心健康,造成幼儿产生了心理恐慌甚至是恐吓;在侵害的客体上,颜某的行为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而在刑事司法政策上,近些年来,在保护幼儿权利方面,虽然国家做了大量的立法和司法工作,但依旧存在着盲区。例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例,由于缺乏相关的具体实施细则,这就导致司法在对幼儿权利的法律保护上,还多停留在口号性层面。不仅如此,尤其是对于发生在非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案件中,司法部门往往由于难以收集有力证据,来证明嫌疑人是“故意”且“多次”犯罪,在此种情况下,司法通过惩罚嫌疑人来保护幼儿权利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假如国内设有类似于国外较为成熟的“虐待罪”,那么司法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就会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这个处理还将是比较妥当的。因此,我们应该正视当前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当中所存在的这一差距。④ 针对这起社会反响极大的“虐童事件”,温岭警方在立案侦查阶段所作出的上述“新闻说明”,无论是在法律依据上,还是在刑事司法政策的考量上,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也指出了以“寻衅滋事罪”来立案侦查本案,可能面临着的相关问题,更详细地正面回应了社会舆论要求“重判”肇事者颜某的社会舆情。正是在司法和社会舆论之间的这种互动当中,社会舆论对浙江温岭的“虐童事件”再度掀起了热议。因为,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虐童罪”的法定罪名,而“寻衅滋事罪”和虐童行为之间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由此,有律师认为,既然目前我国法律对“虐童行为”并没有明确的法定罪名,依据“罪刑法定原则”,颜某的虐童行为就不应该被定罪。对于此,有社会舆论却认为,颜某的行为伤天害理,完全超出了社会道德的底线,必须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寻衅滋事罪”不是太重,而是太轻,甚至不足以惩罚其恶劣的虐童行径。⑤之后,浙江温岭市检察院拒绝批捕,认为本案需要补充侦查。颜某的亲属也提出对受害者进行司法鉴定的要求。2012年11月5日,温岭市公安局向检察院撤回案件,继续侦查。2012年11月16日,温岭市政府新闻办发出公告:“警方经深入侦查,认为涉案当事人颜某不构成犯罪,现依法撤销刑事案件,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羁押期限折抵行政拘留期限。”⑥2012年11月16日,温岭警方依法释放了颜某。 以上不难看出,尽管社会舆论对浙江温岭“虐童事件”的肇事者颜某,表达出了一种强烈的愤慨和道德谴责,并发出了“重判”的呼声,但相对于以往的司法个案而言,对于这起典型的侵犯幼儿道德权利的“虐童事件”,司法部门最后还是采取了一种较为克制的司法姿态,司法行为恪守了现行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的基本理念。这种克制主义的司法姿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司法的依据上,温岭市司法部门基本上贯彻了“罪刑法定”和“疑罪从无”的刑事司法原则;其二,在刑事司法政策的考量上,温岭市司法部门针对当前我国刑事法律中没有“虐童罪”的立法现实,司法部门最后还是恪守了司法与立法之间的基本界限,并没有走向超出“刑事实体法”的范围而展开回应社会舆论的“能动型司法”,也没有走向“通过‘个案刑事司法’来创立‘刑事司法先例’”的方向;其三,在刑事司法的自由裁量上,就在温岭警方以“寻衅滋事罪”为立案侦查方向,从而再度引发社会舆论热议时,检察院不是从“刑事实体法”、“刑事法规范的相关解释方法”、“刑事司法政策”和“社会舆情”等考量,而是以“需要补充侦查”为由拒绝批捕颜某,这种“技术性”的司法处理方式,更是集中体现了道德权利诉求中刑事司法的一种“克制主义”姿态。 三、道德权利的“法律化”与“泛法律化” 由于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内在关联性甚至是相互重叠关系,在道德权利的诉求当中,道德权利的“法律化”一直是人类社会法律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从“应然的权利”向“实然的法律”这一转变,“实在法的产生经历了两个过程,一个是道德化的过程,另一个是合法化的过程,道德化是对原初的利益关系进行道德调整形成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合法化则是在此基础上作的再一次调整,从而形成法定的权利和义务”。⑦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同法律一样,道德也可以被描述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社会实在,并衍生出一套规范性体制,从而确立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与道德责任等。但从规范分析的角度来看,法律是一种普遍性的合法性权威,道德和其它社会规范都要从属于这一权威。同时,道德观念的多元性也决定了道德权利诉求的多样性和弱强制性。对许多人来说,某些具体的道德权利只是一种纯粹的价值观念,一种没有权威性的社会诉求。因此,在一个权利社会中,人们对相关道德权利的诉求,往往容易催生出道德权利的“泛法律化”现象。道德权利的“泛法律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人们出于对相关道德权利诉求的强烈愿望,迫切地主张通过法律的途径,甚至是不惜突破现有法律的基本框架,来实现对特定道德权利诉求的“法律化”,并对侵犯道德权利的行为,予以法律的惩罚,“道德法律化主张内隐着两个子命题:其一,善的合法化和恶的非法化;其二,道德约束手段的刚性化”。⑧在社会实践当中,尽管道德观念可以影响人们在法律领域中的思维方式,但是道德可能更依赖于法律。尤其是对于弱势群体的道德权利保护而言,某些具有道德正当性的道德权利,其确认和保护都离不开法律的强制,“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当原则,在所有的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约束力的增强,当然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⑨这充分地说明了道德权利在立法上进行“法律化”的重要性,霍姆斯在这一意义也曾经指出,“我并不认为,不存在更为宏大的视角,而且通过这一视角的审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区分将退居次席或者变得无关紧要了,正如所有数学上的差距在无限集合之中均趋向于零一样”。⑩ 不过,在道德权利的诉求当中,道德权利的“法律化”不仅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而且也要受制于诸如客观的社会条件、社会的主观认识以及法律自身的相关可形式化要求等。例如,在人类法律史上,对于“非婚生子女的地位和权利”,就一直得不到法律上的承认,人们长期只是将其视为一种“道德权利”来加以讨论。直到19世纪以后,随着医学的发展,非婚生子女才获得了与婚生子女同样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利。(11)可见,当我们直觉地主张“通过法律的途径来保障相关的道德权利”时,就有可能陷入到道德权利的“泛法律化”危机当中,即主张一切道德权利,都应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加以保障和强制。需要指出的是,一个道德社会的形成和维系,并不一定需要法律的强制出场,而道德权利的“泛法律化”,则可能直接导致道德在其社会整合性功能上的削弱,“毫无疑问,大部分道德观念的训导和坚持并不需要法律惩罚的威慑,而在利用它来教化道德的情况下,总会存在这样的危险:服从的唯一原因是对惩罚的恐惧”。(12) 不仅如此,道德权利的“泛法律化”现象,还会引发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被搁置的危机以及私权观念的绝对化等,而这些往往会加剧社会的冲突。例如,在美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民权运动当中,建立在权利观念基础之上的相关道德权利诉求,就呈现出急剧增加的发展趋势,美国法学界的创新者迅速地将个人权利的方兴未艾,认同为是时代最重大的法律剧目。而批评者则认为,“就其绝对化而言,我们的权利话语促进了不切实际的期盼加剧了社会的冲突,遏制了能够形成合意、和解、或者至少能够发现共同基础的对话。就其对于责任的缄默而言,它似乎容忍人们接受生活在一个民主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利益,而不用承担相应的个人和社会义务”。(13)同时,权利的绝对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法律权利悖论的困境,“这是一个倡导个人主义和法律机会平等的社会。然而有一些问题似乎不具备享有这种平等机会的资格,也不适合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在传统上由国家控制的公共领域或不受国家控制的私人领域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14)可见,并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都可以通过法律强制的方式来加以实施,也不是所有道德权利的实现,都需要借助于法律的强制。依据富勒的观点,道德可以划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如果放任将“愿望的道德”进行“法律化”,就可能导致“选择性司法”成为某种必然。(15) 在有关道德权利的“法律化”讨论当中,道德权利所拥有的广泛社会性、群体性、社会阶层性和公共性等特点,使得人们在道德权利的诉求当中,容易陷入到一种非理性的公众情绪宣泄当中。人们在道德权利诉求当中所采用的话语,往往体现为一种大众化的道德话语,具有普遍的可理解性。但是,这种大众化的道德话语,很容易出现以占据道德“制高点”为立场,对侵犯道德权利者展开相关道德说教、批评、指责和抗议等“舆情”,甚至直接就是“借题”来发泄个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在一个权利社会当中,道德权利的背后总是承载着人们对实现社会公正的渴望和情感,公民积极参与对“热点事件”当中相关道德权利的讨论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也是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和表达自由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当我们对道德权利的诉求,仅仅停留在一种非理性层面的“情绪宣泄”时,就容易出现某种建立在道德审判基础之上的“舆论暴政”。例如,在药家鑫一案中,当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药家鑫的个性和行为时,就立刻遭遇了一场群体性的道德围攻,社会舆论甚至直接将她的这一行为,视为意图在为药家鑫开脱。(16)实际上,在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当中,尽管参与者的意见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其主观的专业倾向和个人偏好,但是,在参与者的意见表达与具体的社会实践之间,我们还是应该划分出一条“相对分离”的界线,只有这样,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行动才可能走向理性化。与法律体现人类对社会秩序建构的理性一样,道德也同样体现了人类对社会秩序建构的理性,“‘道德’被视为是‘自然的’,是平静地、理性地和有原则地反映世界的本质以及人类在其中的位置的产物”。(17) 在一个开放社会里,针对社会的道德权利诉求,法律机构、权力组织和政府机关等国家权力部门,往往容易被暴露于公共舆论和公众压力之下,它们也必须努力做出相关的回应。在一个不断迈向微观法治发展的未来中国,社会对道德权利的确定、保护和救济越来越集中于司法领域。在司法领域当中,一般而言,道德权利的“法律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人们主张通过法律的适用(尤其是通过拓展法律适用的标准)或者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即通过“司法性的法律创设”,间接地将“道德权利”转化为一种“法律权利”。不过,在司法领域中,我们既要承认司法对于反映、引导和建构社会良好道德秩序的重要积极意义,但同时也要看到,司法如果以一种全面“能动”的姿态,通过“司法性的法律创设”来推进道德权利的“泛法律化”,就会模糊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之间所存在的必要界限。其结果,司法不仅会引发社会纠纷的加剧,而且也增加了司法自身的负担。 四、道德权利诉求中司法缘何要保持“克制” 如果说法律权利主要是来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那么道德权利则主要来源于社会道德的一种“集体认同”。当然,某些社会习俗也承载着部分道德权利的内容。这些社会道德,既包括一般的社会道义和家庭伦理,也包括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共道德等。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法律控制属于“正式的社会控制”的形式之一,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性的社会控制手段;而道德控制则属于“非正式的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只具有弱强制性。不过,法律控制的国家强制性是由专门化的国家法律机构、形式化的法律技术标准和具有可预测性的法律制裁等内容来加以保证的,并以正确地实施行为规则为前提,“法律制度的另一基本职能是社会控制,实质上是实施正确行为的规则”。(18) 与法律控制相比,道德控制则明显不具有专门化、形式化和可预测性等特点。尽管社会中的很多职业道德规范也都被加以形式化了,社会中大量围绕着职业道德的纠纷解决模式,也正在模仿着诉讼模式而运行(例如,医疗纠纷的解决模式等),但是,职业道德规范自身必然具有在规范内容上的职业性、在规范形式上的模糊性、在运行方式上的激励性和在制裁手段上的内部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就决定了社会对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具有在诉求方式上的私人性、在认定标准上的难以操作性、在救济途径上的宽泛性和在制裁后果上的不确定性等特点。而对于社会当中的公共道德规范,由于其还远远达不到职业道德规范所发挥的社会控制功能水准,社会对侵犯公共道德规范的行为,大多也就只能停留在日常的社会舆论“批评”和“教化”的层面。可见,与法律控制对侵犯法律权利的救济相比,道德控制对侵犯道德权利的救济,其能力总是相对有限的。 一般而言,在社会控制系统当中,当道德控制出现疲软、失效、难以维系和无法获得时,人们便会要求法律控制来“填补、强化和引导”原属于道德控制范围之内的相关情形。此时,道德权利的“法律化”要求,首先就会在司法领域当中凸现出来,进而还会蔓延到立法领域当中,前者表现为对侵犯道德权利的一种“司法救济”要求,而后者则表现为对具有正当性的道德权利的一种“立法确认”要求。司法是法律控制体现最为集中的领域,而刑事司法则是“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最严厉的司法途径之一。伴随着社会的变迁,法律控制的范围在日益地扩展,越来越多的行为不断地被界定为“犯罪行为”,而针对这些特定犯罪行为的刑事制裁措施也就应运而生,刑事司法的工具性角色不断被凸显。由此,在司法的姿态上,刑事司法开始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能动”甚至是“‘全面’能动”的发展趋势,“一个有罪的人不应当仅仅因为他的行为虽然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看是危险或有害的、但却无法被纳入到现有罪名目录上的某个子目录当中去便被允许逃脱定罪……在必要的情况下,既定的刑事制裁应当被类推适用于刑法中尚无明文规定的危险或有害的行为”。(19) 不过,任何一种社会控制手段要实现从“社会层面”向“法律层面”的转变,都需要借助于一个“合法化”的过程。具体在司法领域当中,能够促成被侵犯的道德权利获得司法上救济的主要因素有:“道德上的义愤”、“关于秩序的一种高度的价值”、“对威胁的反应”以及“政治上的策略”等。(20)尤其是在刑事司法领域当中,即使某一个具体侵犯道德权利的行为,在上述因素的综合考量下,都达到了施以刑事司法制裁的必要条件,但是,该行为也并不因此而必然地就能受到刑事司法的制裁,我们还需要从诸如刑事制裁的合法性和可罚性、刑事司法的成本和相关的社会效果等方面进行深入考量。否则,“全面能动”的司法尤其是“全面能动”的刑事司法,就可能催生出一种惩罚性法律形态的出现,“所以,法律道德主义倾向于惩罚性法律,即,它把一种惩罚倾向筑入诉讼程序……道德的强制实施是刑事执法过程中专横武断的一个普遍根源”。(21)而对于上述问题,无论是克制主义司法,还是能动主义司法,它们都有着自己不同的评判标准。 作为两种相对应的不同司法哲学,司法克制主义和司法能动主义有着诸多不同立场和视角的界定。在一般意义上而言,人们认为,司法能动主义是指:法官在司法判决当中,涉及在公共政策等相关因素方面,允许用个人意见来指导判决的作出,甚至是在背离宪法与忽视先例的情形下进行司法;而司法克制主义是指:法官在涉及“公共的善”的方面应该避免受个人信念的影响,相反,在解释法律时应严格遵守法律或与先例保持一致。(22)然而,作为司法谱系上的两极,人们对司法克制主义和司法能动主义的上述一般界定,只是从法治社会中司法的一般原则上所作的一种描述性立场的大致划分。而这一大致划分,并不能清晰地展现在社会对道德权利的诉求上,这两种不同司法姿态所存在着差异的关键依据。与上述描述性意义上的划分不同,巴拉克则从一种规范性意义上指出,对于司法克制主义和司法能动主义的划分,只有当存在着司法裁量时才是有意义的,即只有当司法裁判在司法合理性的范围内依法进行时,对两者的划分才能发挥其作用。(23)实际上,无论是克制主义司法,还是能动主义司法,都只是司法如何在“法律的确定性与社会的变迁”之间,进行左右权衡的一种司法立场性的流变,既没有绝对的克制主义司法,也没有绝对的能动主义司法。而就道德权利而言,司法克制主义意味着:司法不能救济未法律化的道德权利,其权利诉求或者不能进入诉讼程序,或者在诉讼程序当中应该被忽略掉;而司法能动主义则意味着:司法应回应社会的诉求,在司法程序中应考略个案的实质正义,必要时以司法的手段来维护社会中的道德权利。(24)具体而言,在道德权利的诉求当中,对作为一种应然性的道德权利进行救济时,司法需要保持“克制”的原因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道德权利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在救济被侵犯的道德权利时,司法在权能的行使上必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有限性。就西方司法能动主义的发展经验而言,司法能动主义从来都是以“守法主义”的基本司法传统为背景的。“守法主义”既是一种法律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基本的司法意识形态。而所谓的“守法主义”,“是指一种伦理态度,它把是否遵循规则当作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将道德关系视为由规则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25)从对法治社会建构的意义上来看,“守法主义”既是人类法治主义传统和“依法司法”理念的一种高度概括,也是司法在处理“有关法律与道德之间相互关系”问题上的一种基本立场选择。 具体在司法权能行使的要求上,“守法主义”要求司法权能的行使,必须建立在适用客观的法律规则和遵守相关法律解释的原理原则,司法自由裁量不能建立在司法部门和司法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基础之上。同时,司法权作为一种被动型的国家权力,并不能承担起重新安排社会制度的角色,而只能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法院擅于摧毁已经失败的制度并命令当事人为他们的行为找到新的正当性,但是法院尤其不擅于制定具体详细的指令”。(26)因此,“守法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要求司法必须坚持克制主义,克制主义的司法乃是司法的常态,而能动主义的司法则只是司法的例外。尽管司法应该与社会的变迁保持一致,也尽管司法必须体现、反应和塑造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尤其是主流的社会道德观念。但是,司法在“回应”社会对道德权利的诉求当中,对于诸多具有争辩性的道德权利和尚未展现、定位的社会价值方面,则需要保持足够的克制,“此或意味着人们认为法院太过奉守法制主义了。但很抱歉,我想情形恐非如此。除了严格而彻底的法制主义,没有什么能为有关重大冲突的司法裁决提供安全保障”。(27) 与法律权利的法律属性不同,道德权利是一种具有鲜明社会属性的权利形态,司法在“回应”社会对道德权利的诉求时,实际上就担当了一种为社会进行“道德立法”的角色,而这明显违背了法治社会中民主立法的基本原则。在具体的道德权利个案纠纷当中,司法在追求个案的实质正义与法律的一般形式正义之间,总是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法律之外相关的非法律因素也不可能不影响到个案司法。但是,道德权利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司法中的道德论证必须局限于法律规则的基本框架上来展开。将道德权利直接作为司法权能行使的依据,这既违背了法律论证中的外部论证是以内部论证为基础和前提的这一基本司法论证的规则要求,而且最终也危害了道德调整的社会属性,“道德规范调节自然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人际冲突,这些自然人之间彼此同时承认是一个具体的共同体的成员和一个不可替代的个体。这种规范所诉诸的,是通过其生活历史而个体化的人们……能够在法律上受到调节的,仅仅是那些涉及外在关系的问题”。(28)尤其是对于那些特定职业要求的道德权利诉求而言,对道德权利的侵犯和歧视,往往是由于政府和相关的行业协会对市场管理的松懈或者市场未充分竞争所带来的,“如果竞争性市场赶走了歧视,那么当前联邦政策存在的问题就不是缺乏有力的反歧视法律,而是缺乏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市场”。(29)而通过司法直接“回应”特定职业中的道德权利诉求,司法实际上就承担了市场管理者的角色,这无疑加剧了法治社会中司法与自由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二,道德权利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司法的自由裁量在道德权利的“认定”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与之相伴随的高风险性。在当今媒体发达和网络普及的时代,与以往相比,当前的中国司法无疑面临着更加强大的舆论压力。在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上,司法不得不抛弃某些因“立法滞后而僵化”的法律教条主义,“司法性法律创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社会生活,包括法律与司法活动呈现政治化、行政化趋向”。(30)同时,伴随着政府追求和谐与社会稳定的理念在不断增强,司法通过“能动”甚至是“‘全面’能动”的姿态来回应社会需要的职权和责任感也在不断增强,“因而他兼有主持最需以同意为基础的调解以及以强制力为基础的审判这两项能力,这样他的职权比我们会遇到的大部分西方法官都要大得多”。(31) 不过,在社会控制系统当中,与行政管理和道德调整不同,法治社会中司法发挥社会控制的功能,需要建立在明确的法律规范基础之上。在对社会纠纷解决所倚仗的思维方式上,司法思维乃是一种典型的具有独断性特征的法律思维。司法权对未经法律化的道德权利进行救济,在法律上既没有充分的合法性依据,也超出了司法自由裁量所必须局限的“合理范围”。而如果完全以行政管理思维和道德思维来替代法律思维,司法的行政化、道德化与法律的理性化之间则必然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相互冲突,“规则的精髓在于它限定了相关事实的范围”。(32)在司法具体“认定”被侵犯的道德权利诉求当中,个案中的道德权利总是充满着高度的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必然意味着法官自由裁量的广泛运用,其结果也就会反过来加剧司法自身的不确定性。在当前工具主义司法观凸显的转型社会阶段,司法的社会整合角色(政策实施型司法)和工具理性(纠纷解决型司法)之间相互冲突的现实,无疑带来了司法的高风险性,“合议制和官僚制两种不相容的制度在人民法院中共存,构成了中国司法奇特的景象。在这幅景象中,两种价值——公正和效率,发生剧烈的冲突和碰撞”。(33) 从西方回应型法治重构的历史经验来看,回应型法治往往是以司法的“能动主义、开放性和认知能力”三者作为基本特色和相互结合的。其中,能动主义往往会削弱法律约束官员和要求服从的能力,过于开放的法律秩序则会丧失法律在社会中节制权力作用的能力,而由此所带来的司法自由裁量也在加剧司法认知能力的责任和风险,“回应型法的鼓吹者在欢呼一种更有目的、更开放的法律秩序时,则选择‘风险大’的观点”。(34)尤其是在涉及道德问题的司法自由裁量当中,如果司法坚持用某些“正确答案”的道德话语来表达某些价值层面上的判断,司法的不透明性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欧洲法律方法论的一个主要(且令人遗憾)特点就在于其本身内在的实质性方法并未明确地被表露出来,也即:缺乏透明性”。(35) 近些年来,伴随着欧洲在反形式主义法律改革当中实现了对实质主义的凸显,克制主义司法的基本原则再次被视为当今时代的征服和渴望,“之所以将这些原则视为‘基本’,其实质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坚信它们不仅代表了一种文明的司法裁判制度基本的最低限度,而且也是文明的司法裁判制度中永恒不变的组成部分”。(36)而在美国,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对抗制法条主义”的诉讼能动主义的洗礼之后,尽管其作为政府管理和法律治理的结构以及法律实践仍然在流行,但对抗法条主义并没有整齐划一或完全彻底深入美国的法律秩序当中去。(37)相反,对抗法条主义的诉讼能动主义正在遭受诸如繁琐拖沓、费用高昂和高风险等危机。批评者普遍认为,司法能动主义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法律失去了其约束法官和要求服从的能力,对程序形式尊重的降低以及规则处于不断被怀疑的状态,法官和公民的行为就更容易变得随心所欲。(38) 五、克制主义司法立场中道德权利纠纷解决机制的相关构建 在社会控制系统当中,相对法律控制而言,尽管道德控制自身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但是从另一层面而言,道德控制的有限性恰恰就是其优点之所在。相对于法律控制而言,道德控制在以下的一些社会情形当中,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法律规则无法适用的场合”(例如,没有借条证明的借贷行为)、“不构成法定条件的人身伤害”(例如,轻微的人身伤害)、“法律无法认定的事实”(例如,“彭宇案”中彭宇是否“撞”了老人)、“难以被法律确定的义务”(例如,通过“搬弄是非”来侵犯别人的利益)、“基于个体自愿的行为”(例如,在公交车上给人让座)、“某些私人领域”(例如,夫妻同居的义务)以及法律还无法预测到的新问题等。不仅如此,法律控制所具有的高度形式化特点也决定了其只能针对“正常的人”考虑“一般的正义”,甚至有时还会以牺牲个案的实质正义为代价来保障形式正义的实现,“法律只考虑正常人,也就是说,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从正常人的理性、情感出发,不要迁就那些非理性的、情感过于脆弱的人……法律和执法部门如果考虑‘那些时时等待着被诱惑的过于敏感者’,就会给社会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且负面影响极深”。(39) 因此,无论是法律控制还是道德控制,都是两种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当然,针对某些行为,法律控制和道德控制甚至可以同时发挥作用,两者都不具有排他性。尽管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里,法律控制显得尤其重要,但如果要将本属于道德控制范围之内的行为,转交给法律控制来完成,这首先就需要面临“道德控制是否可以强制执行”的难题,“道德规则和道德原则自身并不是可强制执行的,即,为了保持它们的道德属性,它们不必是可强制执行的”。(40)尤其是在一个法治国家,司法必须尊重既有法律控制所设置的基本框架,如果超越了这一框架,就会导致法律控制违背“不得溯及既往”和“具有可预测性”等的一般法治原则和克制主义司法的基本理念,“这就使我们考虑到有效法律行动的局限性,即那些阻止我们经由法律手段去从事伦理观点或社会理想推动我们去进行的一切事情的各种实际限制”。(41) 具体在浙江温岭“虐童事件”当中,颜某的虐童行为,所折射出的不仅是幼师的职业道德自律问题,还包括当前中国幼儿教育资源的供给严重不足、幼儿教育师资良莠不齐、幼儿教育宗旨的定位不清、幼儿教育主体的职权与责任在范围上的模糊、幼儿教育缺乏社会监管、幼儿权利内容在认识上的模糊和幼儿权利救济渠道的不健全甚至是缺失等诸多的社会现实问题。基于此,针对颜某的虐童行为,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采取“以暴制暴”的大众化道德话语来惩罚颜某,这种惩罚行为既无法实现保障所有幼儿道德权利的目的,也无助于提升中国社会幼师队伍整体职业道德的水平和改善相关幼儿教育的制度建设。其结果,无疑只是上演了一场“道德绑架司法”的法律悲剧,也纵容了司法的专横,“涉案民意具有多元、流动、易变性,谁有权在多种不同的意见中确定哪个是‘民意’,谁的意志势必就凌驾于法律之上。结论是分明了:民意审判徒有民主的外衣,骨子里却是法官专横”。(42)而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主张通过法律化的途径来保护幼儿的相关权利,所导致的结果恐怕就会引发中国幼儿教育甚至是整个教育体系的“混乱”,尤其是教育主体的相关职权和责任也就会因此而无法落实。不仅如此,接二连三所发生的虐童事件表明,整个社会体系对于保护儿童的权利在道德、法律、教育、监管和相关善后事务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和缺失。不仅如此,《北京青年报》“今日社评”文章还指出,“无论就数量或比例而言,虐童都是极端个案。但极端的背后,可能是相对普遍的社会情绪。生气、焦虑、愤怒,互不信任乃至相互猜忌、仇视,成为很多人的日常情绪状态”。(43) 可见,社会对道德权利诉求的实现和保障,乃依赖于一个更加广泛的社会管理机制、纠纷解决机制和相关的其它制度建设。而从“认真地对待权利社会中的道德权利”这一立场而言,在坚持克制主义司法的基本理念上,我们迫切需要对围绕着相关道德权利纠纷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建构。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加强并完善特定职业中侵犯道德权利的公正有效纠纷解决机制。在一个权利社会中,纠纷构成了权利社会的常态,法治社会中的法律控制不是要消灭纠纷,也不可能消灭纠纷,而是需要认真地对待纠纷。在纠纷解决当中,法律控制的有限性决定了法治社会还需要建立法律控制之外的相关纠纷解决机制,尤其需要建立准审判过程的相关纠纷解决机制,以广泛发挥其确认社会公共道德和社会规范的积极作用,“在有些准审判过程中,共同体一般成员作为利害关系人或旁听人参加纠纷处理。这种情况也加强了该准审判过程确认规范的作用”。(44)纠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由诸多的社会因素所造成的,尤其是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中,由于职业分工更加的精细化、人口多样性和流动性的增强、价值冲突和利益冲突的凸显和资源有限等诸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既有的规则不足以解决纠纷、满足社会需求;另一方面,纠纷解决机制的正当性、权威性和有效性都受到严峻挑战”。(45)尤其是对于特定职业中的职业道德问题,我们既要防止国家或者社会对特定职业良性市场竞争的额外干预的出现,也要防止特定职业基于既有垄断优势或者资源优势而侵犯社会道德权利现象的出现,“市场经济竞争的基础和前提是合同自由,而与这种自由密切连在一起的是自由的滥用……商业道德令人担忧,这里触犯的不只是企业和一般民众的权益,经济结构改革也因此受到了损伤……”(46) 例如,针对浙江温岭“虐童事件”,有关针对幼师侵犯幼童道德权利的第三方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就显得尤为迫切。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家长或多或少都能觉察出幼童的相关道德权利被幼师所侵犯的事实,但由于幼师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幼童的道德权利被侵犯的有力证据难以收集、侵犯幼童道德权利的行为与正常的教育训诫行为之间界限的模糊、通过私人途径来解决相关教育纠纷往往会带来更加无法控制的不利局面以及幼童道德权利保障的人身依赖性等诸多现实难题,这些都导致家长和社会难以对侵犯幼童道德权利的现象展开及时、有效和切实的救济。尤为关键的是,传统幼儿教育中用于规范幼师教育行为的相关职业规范,由于其内部性、不透明性、激励性和单纯服务于行政管理需要的治理性等诸多特点,往往导致其发挥社会监管和职业规范的作用不明显,这就导致家长和社会针对侵犯幼童道德权利的行为甚至无法获得可靠的救济渠道。因此,设立一个中立的第三方纠纷解决机构来专门负责疏导、提醒、公开、激励、调查、监管、救济和奖惩等事务,就显得尤为必要。 第二,在加大公共资源供给和改善市场竞争环境的基础上,加强政府的行政管理和完善相关的行政立法工作,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制度。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当中,人们对道德权利的漠视和侵犯绝不单纯的是一个“道德相对失序”的表象,也是无法通过单纯的“道德宣教”和“道德激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其中,公共道德意识的削弱往往是与社会和政府的公共资源供给不足所造成的,而职业道德意识的削弱则往往是与市场竞争环境和政府监管不力所造成的。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引发权利社会中“道德相对失序”的整个社会宏观环境,而将司法置于解决上述问题的前沿位置,不仅增加了司法的负担,浪费了司法的资源,而且也极大地削弱了司法的权威性,“司法能动主义是发达的,但司法活动是有限的。法院决定把相对利益的权衡权交给市场或者交易”。(47)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把社会中所发生的大量侵权行为只作一种“道德化”的处理,将司法发挥引导、回应和塑造社会道德观念的功能,简单地视为是“舆论司法”和“道德司法”的胜利,那么其结果不仅搁置了我们对侵犯道德权利现象的深入思考,同时也搁置了社会对道德权利的强烈诉求。 法治社会建构的理念反映了人类对美好和理想社会的一种憧憬,任何一个社会的法治秩序无疑都是以某种潜在的道德秩序为依托的,“然而,国家制定法中仍然残留着强制和暴力的骇人遗迹。内在道德秩序诉求在遮蔽它们的同时也推动了它们的发展”。(48)司法舆论往往是社会问题的预警器和晴雨表,而热点个案当中的司法舆论则往往构成了驱动相关社会改革的直接动力。就如何改善当下我们社会中的潜在道德秩序而言,首先,需要通过增加公共资源的供给来改善社会的公共道德状况,需要通过推进市场的良性竞争和改善市场竞争环境来改善社会中的职业道德状况。诸如,近些年来社会中所凸现出来的教师职业道德和医生职业道德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公共资源的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公共资源的投入是社会福利的重要内容,福利国家不仅需要寻求法治来实现权利在保障形式上的可操作性,也需要通过创设公共服务来减少社会、道德和经济上的紧张关系。(49)而就职业道德而言,职业道德与市场良性竞争状况和竞争环境紧密相关,法律治理模式绝不是由市场所导出的唯一社会治理模式。行业自治组织、经济活动的竞争状况和运行良好的行业评价机制等,无疑都直接制约着相关的职业规范甚至是整个社会的伦理规范。(50)其次,要加强政府的行政管理并完善相关的行政立法工作。在现有公共资源供给不足的现实社会背景下,资源的稀缺性往往加剧了社会的利益冲突和道德观念冲突,尽管每个社会都会努力通过法律来控制这些冲突,但过度的法律控制只会简单地压制着潜在的社会纠纷。从疏导社会纠纷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司法而言,政府的行政管理尤其通过完善的行政立法进行社会管理,则更具有直接性。尤其是在突发的自然灾害和重大社会矛盾当中,依据法律思维来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都面临着严峻的拷问。(51)不仅如此,政府的行政管理不能仅仅局限于“设定标准”(例如,许可证的颁发)和“对那些未服从标准的行为加以惩罚”(例如,行政处罚),还需要“通过预防”(例如,审查和调查、民事监管)来发挥政府管理的能力。而对于责任追究而言,在重大侵权事件中,不仅要追究侵权者的责任,还要追究相关单位的责任,甚至还要追究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责任。 在浙江温岭的“虐童事件”当中,针对这起典型的侵犯幼童道德权利的行为,尽管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最终采取了一种值得“充分肯定”的克制姿态来办理该案,但面对来势汹涌的“司法舆论”,司法与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度构成了我们反思的焦点:缘何这起典型的道德侵权事件或者一般民事侵权事件,能够迅速地被转化为一个热点的“司法个案”尤其是热点的“刑事司法个案”呢?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社会舆论对肇事者颜某所表达的强烈愤慨情感是需要我们予以充分地尊重的,但是这种主张“重判”倾向的司法舆论,却无疑映射出社会中所存在着的某种相对落后的法律观和司法观,例如,“刑本位主义”法律观、“重刑主义”的司法观、工具主义司法观、朴素的“道德司法”意义上的能动主义司法观和“唯法制主义”的社会治理观等。尤其对于那种主张“通过司法尤其是刑事司法来严惩侵犯社会道德权利”的“舆论司法”而言,其明显背离了法治社会中“守法主义”的基本克制司法理念。如果这样,那么司法也就成了纯粹的道德宣教工具了,“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司法过程便成了宣教活动,法庭则成了教化的场所”。(52)而在当下中国的司法时代,对于正处于社会舆论高度关注中的中国司法而言,上述相对落后的法律观和司法观却无疑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 就司法与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司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定的社会状况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司法只忠实于法律而非受制于社会舆论”这一司法理想或多或少难以贴近司法现实,正因为如此,对于社会舆论尤其是热点司法个案当中的司法舆论,司法需要予以一种更加理性和克制的关切。对于当下中国的能动司法实践而言,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权、扶贫、服务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进法治和良好社会治理等方面,能动司法逐渐显露出“目标拥挤”、“使命不清”和“宗旨模糊”等相关弊端。由此,在司法与舆论之间,我们要严格恪守司法与舆论之间的合理界限,防止中国司法陷入到“从‘司法舆论’到‘舆论司法’”的逻辑怪圈当中。而对于社会中不断涌现出来的道德权利和其他权利的强烈诉求而言,司法的使命就是“……给所有庭前涉诉的人提供平等和精准的判决”。(53)当然,在一个权利社会中,无论是对法律权利的讨论还是对道德权利的讨论,都需要将它们服务于实现更加广泛的社会公正的需要,只有具备充分的社会公正性和合理性,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社会可接受性。 ①来源:http://home.cnstock.com/thread-50192-1-1.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1月18日。 ②来源:http://v.pps.tv/play_33R6LC.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1月18日。 ③凤凰卫视2012-11-17日一虎一席谈节目——“虐童教师该不该重判”,来源:http://v.ifeng.comnews/society/201211/a4f5acf0-0d26-4a07-aa0c-ae4ff45bfa12.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1月18日。 ④来源:http://www.iqiyi.com/life/20121029/e5ad71672f34755c.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1月18日。 ⑤来源:http://v.pps.tv/play_33R6LC.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1月19日。 ⑥来源:http://www.chinanews.com/hb/2012/11-21/4346980.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1月20日。 ⑦曹刚:《法律的道德批判》,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⑧杨孝如:《道德法律化:一个虚假而危险的命题》,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页。 ⑩[美]霍姆斯:《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霍姆斯法学文集》,明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页。 (11)[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12)[英]H.L.A.哈特:《法律、自由与道德》,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13)[美]玛丽·安·格伦顿:《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周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14)[美]萨利·安格尔·梅丽:《诉讼的话语》,郭星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 (15)[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页。 (16)来源:http://share.renren.com/share/258787446/5712466028,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1月27日。 (17)[澳]皮特·凯恩:《法律与道德中的责任》,罗李华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6页。 (18)[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19)[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与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20)[美]史蒂文·瓦戈:《法律与社会》,梁坤、邢朝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页。 (21)[美]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22)See,Black,Black's Law Dictionary,Edit by Bryan A.Garner,7th ed,West Group.,1999,P.850-852. (23)[以]巴拉克:《民主国家的法官》,毕洪海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40页。 (24)徐顿:《论司法能动的道德风险》,载《法律科学》2011年第2期。 (25)[美]朱迪丝·N.施克莱:《守法主义》,彭亚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6)[美]麦德福、强世功:《司法审查:技艺理性与法治》,载《读书》2003年第8期,第31页。 (27)许章润、徐平:《法律:理性与历史——澳大利亚的理念、制度和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 (28)[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37-138页。 (29)[美]凯斯·R.孙斯坦:《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金朝武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页。 (30)吴英姿:《法官角色与司法行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1页。 (31)[美]马丁·夏皮罗:《法院:比较法上和政治学上的分析》,张生、李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32)[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 (33)翁子明:《司法判决的生产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34)同前引(21),第86页。 (35)[荷]马丁·W.海塞林克:《新的欧洲法律文化》,魏磊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87页。 (36)[意]莫诺·卡佩莱蒂:《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徐昕、王奕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 (37)[德]沃尔克玛·金斯纳、[意]戴维·奈尔肯主编:《欧洲法律之路——欧洲法律社会学视角》,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 (38)同前引(21),第82页。 (39)何柏生:《法律只考虑正常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40)[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41)[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6页。 (42)周永坤:《民意审判与审判元规则》,载《法学》2009年第8期。 (43)张天蔚:《从虐童事件中反思什么》,来源,http://bjyouth.ynet.com/3.1/1210/26/7556333.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2月5日11:30。 (44)[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45)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3-74页。 (46)[德]何意志:《法治的东方经验》,李中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5页。 (47)[美]尼尔·K.考默萨:《法律的限度》,申卫星、王琦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页。 (48)[美]罗伯托·曼格贝拉·昂格尔:《法律分析应当为何?》,李诚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页。 (49)[美]理查德·A.波斯纳:《道德与法律理论的疑问》,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50)[美]柯提斯·J.米尔霍普、[德]卡塔琳娜.皮斯托:《法律与资本主义》,罗培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51)胡建淼:《法律思维与现代政府管理》,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52)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53)罗东川、蒋惠岭:《探寻司法改革的成功之道》,黄斌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