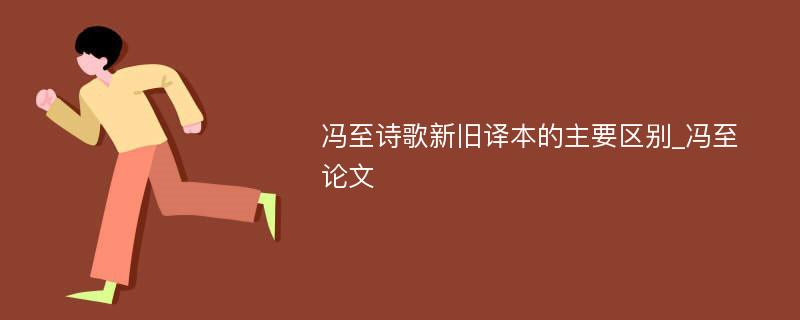
冯至诗集新老版本的重大歧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歧异论文,诗集论文,新老论文,版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6)04—0039—006
冯至(1905—1993)是曾被鲁迅称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1—p251] 的中国新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1949年之前,冯至曾经结集出版过三本诗集:《昨日之歌》(收录1921年至1926年上半年的诗作52首,1927年4 月北新书局出版)、《北游及其他》(收录1926年秋至1929年夏的诗作41首和译诗5首,1929年8月北平沉钟社出版)、《十四行集》(收录1941年创作的十四行诗27首,后附杂诗6首,1942年5月桂林明日出版社出版;1949年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后附杂诗改为4首)。1949年后,陆续出版了几种冯至作品选:《冯至诗文选集》(1955,人民文学出版社)、《冯至诗选》,(1980,四川人民出版社)、《冯至选集》(1985,四川文艺出版社)、《冯至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1999年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冯至全集》。1949年后出版的选集中的前三种都是由冯至亲自选编的。每次编选作品集的时候,冯至都要对自己以前的作品做一些改动。在这些作品选中,收录1949年以前的诗歌共89首,其中有过改动的有88首,改动较大的有49首,修改后内容发生重大改变的有34首。凡是1955年收入《冯至诗文选集》中的作品,在《冯至诗选》和《冯至选集》中基本上保留了其在《冯至诗文选集》中的面貌;《冯至全集》于这些“作者在编入其他选集时曾多次予以修订”的作品,“都依作者最后的修订本编入”,其中改动较大的地方,编者择要作了简单说明[2]。
在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冯至选集》的《诗文自选琐记(代序)》中,冯至谈到作者在编选自己以前的作品的时候是否可以进行修改的问题,他在肯定作者有权修改的同时,也认为自己在1955年编选《冯至诗文选集》的时候,对于以前的作品“还是删改的多了一些”,从而对于旧作的删改定下了这样几条原则:“第一,二十年代有人写作,有时在文句间掺入不必要的外国字,这样就破坏了语言的纯洁性,我当时也沾染了这种不良的习气。如今我读到这类的文句,很感到可厌。因此我把不必要的外国字都删去了,用汉字代替。第二,有个别诗句,尤其是诗的结尾处,写得过于悲观或是没有希望,我不愿用往日暗淡的情绪感染今天的读者,我把那样的句子作了改动。”“第三,文字冗沓,或是不甚通顺的地方,我改得简练一些,舒畅一些,但不另作修饰。还有古代的用词,必要时我改为今语。”根据以上几条原则,冯至认为在《冯至诗文选集》里删改的地方,“有的是恰当的,有的是过了头的,恰当的我在新的选本里延续不变,过了头的我作了纠正,……”但在实际上,冯至对其旧作的修改,绝不仅仅限于这三条,被改动的也不只是“个别诗句”;改得“过了头的”也很少加以“纠正”。所以,对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来说,以《冯至全集》或1949年以后出版的冯至选集为依据来研究冯至作品,是很危险的。
为了说明问题,现以《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十四行集》(1949.1,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为底本,以《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选》、《冯至选集》(1985.8,四川文艺出版社)、《冯至全集》(1999.12, 河北教育出版社)为校本,将原作和经过修改后的诗歌进行比较,归纳其差别为四类:
一、经修改后,作品的题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类作品最突出的为《归去》、《月下欢歌》。现分别介绍如下。
《归去》作于1923年,收入《昨日之歌》,在《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选》、《冯至选集》、《冯至全集》中均题作“新的故乡”;文字也改动很多。由于改动太大,只好将两首诗分别引录如下:
归去 新的故乡
灿乱的银花, 灿烂的银花
在晴朗的天空飘散;在晴朗的天空飘散;
黄金的阳光, 金黄的阳光
把屋顶树枝染遍。 把屋顶树枝染遍。
驯美的白鸽儿 驯美的白鸽儿
来自神的身旁,来自什么地方?
它们引示我翘望着 它们引我翘望着
迷濛的故乡。 一个新的故乡:
“汪洋的大海,汪洋的大海,
浓郁的森林——浓绿的森林,
故乡的朋友, 故乡的朋友,
俱在彼处歌吟。” 都在那里歌吟。
一切都在春暖的这里一切安眠
被里安眠,在春暖的被里,
我但愿身如我但愿向着
蝴蝶的翩翩! 新的故乡飞去!
题目“归去”和“新的故乡”很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归去》中,诗人所向往的,是在“来自神的身旁”的“白鸽儿”的“引示”下所翘望到的、而且必须“身如蝴蝶的翩翩”才能到达的“迷濛的故乡”,这是一个迷离恍惚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特别是结尾处所强调的“我但愿身如/蝴蝶的翩翩”,显然是用庄周梦见自己化身为蝴蝶的典故,进一步突出了这境界的梦幻性。正如鲁迅所说,以冯至等为主要成员的浅草社(成立于1922年,在1923年至1925年间出版《浅草》季刊,1925年《浅草》停刊后,又成立沉钟社,出版文艺刊物《沉钟》)“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1—p250~251] 这“迷濛的故乡”就是基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所追求的“真和美”的境界;但这在当时的“这世界”里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诗人只能寄望于自身的化为蝴蝶了。而《新的故乡》则是写其对美好未来的追求,结合修改时的社会环境和通行话语来看,可以理解为对“新社会”、“新时代”的向往。这就与“为人生的艺术”相一致了。
《月下欢歌》作于1928年,收入《北游及其他》,在《冯至诗文选集》中,诗题改为“我的感谢”,在《冯至诗选》、《冯至选集》、《冯至全集》中,诗题恢复为“月下欢歌”,内容则基本同于《冯至诗文选集》中的《我的感谢》。现引《北游及其他》中的《月下欢歌》如下(为节省篇幅,引录原诗时以“/ ”表示分行,以“//”表示一章的结束):
不要哀哀地诉苦了,欢乐吧,/美满的圆月已经高高地悬在天空!/我无边的希望都充满了,/在这无边的月色当中。/“无边的月色啊,/请你接受吧/我的感谢!”//我全身的细胞都在努力工作,/为了她是永久地匆忙;/宇宙的万象在我的面前轮转,/没有一处不是爱的力量。/“博大的上帝啊,/请你接受吧,/我的感谢!//我“生”了;我显示在她的面前的/既不是苍苍的白发,也不是啼泣的婴孩,/是和她同时代的青年,/肩上担负着同时代的悲哀。/“父亲同母亲,/请你们接受吧,/我的感谢!”//她不是热带的棕色的少女,/也不是西方的金发的姑娘:/黄色的肌肤,黑色的眼珠,/我们哪,在同一的民族里边生长。/“中华的民族啊,/请你接受吧,/我的感谢!”//我从母亲的口中学会了朴厚的方言,/又从她的口中学到了音乐般的谈话,/我大声地唱出我的诗歌,/把这两种声音都在一块儿溶化。/ “祖国的语言啊,/请你接受吧,/我的感谢!”//温暖的黄土把我栽培,/我的枝叶尽量地向着天空伸长,/我愿在风雨里开放着我的花朵,/在冬季的雪中忍受着我的苦创。/“温带的气候啊,/请你接受吧,/我的感谢!”//我的灵魂是琴声似的跳动,/我的脚步是江水一般地奔跑,/我向着一切欢呼,/我向着一切拥抱。/“宇宙的一切啊,/请你接受吧,/我的感谢!”
这是一首热情洋溢的爱情诗,全诗以爱情为中心而展开。诗中的“她”既是“中华民族”的“少女”,与诗人“我”是“同时代的青年”,对诗人的影响又与其母亲的同样巨大,以致诗人的“诗歌”乃是把“她”与自己母亲的“两种声音”“溶化”在一起的结果;而且,诗人为了她而“全身的细胞都在努力工作”,并感到“宇宙的万象在我面前”“没有一处不是爱的力量”,这样的“她”显然只能是诗人的恋人。由此也就可以知道:诗人之所以感谢“博大的上帝”,是因为“上帝”创造了“宇宙万象”而且使它们无不洋溢着“爱的力量”,并以这种“爱的力量”来引导诗人为了爱“她”而全身心地“努力工作”。同时,诗人是为父母将自己和“她”生在同一时代而感谢“父亲同母亲”;为两个人生在同一个民族而感谢“中华的民族”;为两个人以及诗人的母亲都使用同样的语言,并且诗人可以用这语言将她与母亲的声音“溶化”为自己的诗歌而感谢“祖国的语言”;所以,这些“感谢”都源于爱情。最后一段的“灵魂是琴声似的跳动”,“脚步是江水一般地奔跑”,显然也是爱情的驱使;从而诗人的“向着一切欢呼”、“拥抱”,“感谢”“宇宙的一切”,同样是缘于爱情。至于诗人的“在风雨里开放着我的花朵”,这“花朵”当然是喻示爱情;在“无边的月色当中”所“充满”的“无边的希望”,当然也是爱情所带来的,因而诗人对“无边的月色”和“温带的气候”的“感谢”,也都是缘于爱情。
这首诗作于1928年,此时冯至初识姚可崑(后来二人结为夫妇);与冯至以前的哀怨缠绵的情诗风格完全不同,这是一个拥有爱情以后的心灵的幸福歌唱。整首诗以爱情为主题,也正是当时尊重个性和爱情的个性解放精神的体现。
但是,在此诗的新版本(包括《冯至诗文选集》中的《我的感谢》和《冯至诗选》、《冯至选集》、《冯至全集》中的《月下欢歌》)中,“我全身的细胞都在努力工作”这一章被完全删掉了,因而“我”“为了她”而“永久地”“努力工作”,“宇宙的万象”都“是爱的力量”等歌咏恋爱的内容消失了;其下第三章中的“我从母亲的口中学会了朴厚的方言,/又从她的口中学到了音乐般的谈话”被改成了“我从母亲的口里学会了朴素的语言,/又从许多人的口里学会了怎样谈话”,使这整个一章都与恋爱无关。经过这样的改动,整首诗就不再是以爱情为中心而展开了。至于诗中出现的“她”和诗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也就不清楚了,似乎只是“担负着同时代的欢乐和悲哀”的“同时代的青年”而已;而且,第三章的结尾,原是“父亲同母亲,/请你们接受吧,/我的感谢!”,在新版本中已被改成了“我们的时代,/请你接受吧,/我的感谢!”,表现个人感情的内容全被清除,诗人和“她”之间除了是“同时代的青年”以外,又还有什么个人感情的纽带呢?
总之,在此诗的新版本中,已经看不到由恋爱导致的巨大的欢乐和感激,却看到了并不是从个人遭际出发的对“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祖国的语言”的深深感谢。陆耀东先生在《冯至传》中说:“《月下欢歌》请求‘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祖国的语言’接受‘我的感谢’,是爱国情的直接抒发”[3—p250]。这里显然是就新版《月下欢歌》而言的(因为“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都只见于新版)。我想,新版的《月下欢歌》除了“爱国情的直接抒发”以外,确实已看不到对爱情的无限深情的歌唱了。
此外,如《北游·12.雪五尺》(作于1928年,收入《北游及其他》)的结尾处,原诗是“这时的月轮像是瓦斯将灭,/朦朦胧胧地仿佛在我的怀内销沉;/这时的瓦斯像是月轮将落,/怀里,房里,宇宙里,阴沉,阴沉……”,但在新版本(《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选》、《冯至选集》、《冯至全集》)中,却改成了“我不能这样长久地睡死,/这里不能长久埋葬着我的青春,/我要打开这阴暗的坟墓,/我不能长此忍受着这里的阴沉”。原来是无边的绝望,经过修改,却变成了坚强的反抗之歌了。
二、经修改后,作品原有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点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不但不能充分体现当时的时代风貌,有时甚至加以严重扭曲。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北游》之《5.在公园》(作于1928年,收入《北游及其他》)与其改本的差别。其原文如下:
一切都模糊不定,隔了一层,/把“自然!”呼了几遍,把“人生!”叫了几声!/我是这样地虚飘无力,/何处是我生命的途程?/我思念,/世纪末的诗人——/用美人的吻来润泽他们的焦唇,/用辛辣的酒浆灌溉他们憔悴的灵魂。/我呀,灵魂憔悴,唇已焦躁,/无奈我的面前美人也不美,醇酒也不醇。/我爱护,/那样的先生——/他能沉默而不死,/永久作一个无名的英雄。/但是呀,我又怕在沉默中死去,/无名而不是英雄。/我崇拜,/伟大的精灵——/使我们人类跌而复起,/使我们人类死而复生,/我们倚仗他不与草木同腐,/风雨后他总给我们燃起一盏明灯。/无奈呀我的力量是那样衰弱,/风雨里我造不出一点光明。/我羡慕,/为了热情死去的少女少男——/在人的心上,/留了些美的忆念:/啊,我一切都不能,/我只能这样呆呆地张望——/望着市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各各的肩上担着个天大的空虚,/此外便是一望无边的阴沉,阴沉……
鲁迅在评述包括冯至在内的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沉钟社作家的小说时曾说:“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 Wilde),尼采(Fr.Nietzsche), 波特莱尔(Ch.Baudelaire),安特莱夫(L.Andreev)们所安排的。‘沉自己的船’还要在绝处求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虽是冯至的饰以诗情,莎子的托辞小草,还是不能掩饰的。”[1—p251] 这虽是就沉钟社人的小说而言,但也同样适合于沉钟社同人冯至的诗歌。正因其摄取来的乃是“世纪末的果汁”,所以有“我思念/世纪末的诗人”这一章;正因为“心情”是“热烈”而又“悲凉”的,所以他爱护“无名的英雄”,“又怕在沉默中死去”,“成不了英雄”;“崇拜”伟大的心灵,① 而又悲慨于自己力量的微弱;羡慕为了热情而死去的“少女少男”,但自己却只感到空虚与阴沉。
在此诗的新版本(《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选》、《冯至选集》、《冯至全集》)中,虽然保存了原诗的“空虚”、“阴沉”之感,“我思念/世纪末的诗人”这一章却全被删去了,于是也就泯灭了吸取“世纪末的果汁”的痕迹;“我的崇拜/伟大的精灵”被改成了“我崇拜/伟大的导师”,于是“导师”就成了“使我们人类跌而复起”、“使我们人类死而复生”、“使我们不与草木同腐”的大救星,这是典型的个人崇拜,正与“五四”精神背道而驰。
再如《北游》之《10.“Pompeji”》(作于1928年,收入《北游及其他》)中:“我也要了一杯辛辣的酒,/一杯杯浇灭我的灵魂;/我既不为善,更不作恶,/忏悔的泪珠已不能滴上我的衣襟!/我同这些青年,舞女,都融在一起,/大家狂跳吧,在这宇宙间最后的黄昏!/快快地毁灭,像是当年的Pompeji,/第一个该毁灭的,是我这个游魂!/明天呀,一切化作残灰,/日月也没有光彩,阴沉,阴沉……”,这种对自己的极度不满,也正是当时已经觉醒的智识青年的“热烈”“然而悲凉”的心情的真实写照。但是在新版本(《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选》、《冯至选集》、《冯至全集》)中“我同这些青年,舞女,都融在一起”,“第一个该毁灭的,是我这个游魂!”被改成了“看这些男女都拥在一起”,“最该毁灭的,是这里的这些游魂!”原有的对自己的极度不满乃至诅咒,都被清除了,并且被改成了仅仅是对“这些男女”的谴责。而这种对堕落者的谴责,正是“五四”新文学所力图突破的道德文学的特色。
三、经修改后,原作与上世纪50年代以降通行的政治观念不一致的内容消失了。
这类作品数量相当多。现举三个例子如下:
1.《北游》之《7.中秋》(作于1928年,收入《北游及其他》):“工人,买办,投机的富豪,/都是一样地忘掉了自己——/不知道他们的背后有谁宰割,/不知道他们的运命握在谁的手里?”在新版本(《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选》、《冯至选集》、《冯至全集》)中,“工人”被改作了“官僚”,这显然是因为将“工人”与“买办”、“投机的富豪”相提并论乃是丧失阶级立场的表现。
2.作于1943年的《我们的时代》(收入《十四行集》)中:“我们到那时/拥抱住我们的朋友,就是向/忏悔的敌人我们也可以/伸出手来,微笑着向他们说:/‘我们曾经共同分担了/一个共同的人类的运命。’”《冯至诗选》、《冯至选集》、《冯至全集》所收此诗,这几句改为“我们到那时/将要拥抱着我们的朋友说:/‘我们曾经共同分担了/一个共同的人类的命运。’”冯至原诗之所以要对“忏悔的敌人”这样说,不知其究竟出于何种考虑;但这显然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通行的政治理念不能相容,所以在新版本中,这些内容消失了。
3.《帷幔》(作于1924年,收入《昨日之歌》):“她的父母,是朱门旧户,/她并不是,为了饥寒;……怜她本也是贵族的闺女,/教她静静地修养,在庵后的小楼。……”诗中对这个女子显然是深为同情的。在新版本(《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选》、《冯至选集》、《冯至全集》)中,诗人对她的同情态度并未改变,但“她的父母,是朱门旧户”、“怜她本也是贵族的闺女”等句都被删去了。因为按照当时通行的政治观念,同情“朱门旧户”的“贵族的闺女”,把她作为作品的主人公,也是丧失阶级立场的行为。
四、经修改后,诗歌中一些可能被极“左”观念指责为道德上不符合规范的描写被删去了。
这种情况实在颇为可笑,因为冯至诗里本就没有什么色情的东西,但却不料还有需要避忌之处。现也举三个例子:
1.《北游》之《6.Cafè》(作于1928年,收入《北游及其他》):“……/我望着那白衣的侍女是怎样苍茫,/我躲避着她在没有人的一角;/她终于走到我的身边,/我终于不能不对她微笑!/‘深深的酒杯,深深地斟,/深深的眼睛,深深地想——/除去了你的肩头,/我的手已经无处安放。……”在新版本(《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选》、《冯至选集》、《冯至全集》)中,“深深的酒杯”以下四行都被删去了。这里的要害,想是“除去了你的肩头,/我的手已经无处安放。”——这样地对待咖啡馆的一个侍女,衡以极“左”观念当然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
2.《北游》之《9.秋已经……》(作于1928年,收入《北游及其他》):“她终于挽不住那西方的落日,/却挽住了我的爱怜,/我们吻着,绝没有温暖的情味,/无非是彼此都觉到了衰残。”在新版本(《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选》、《冯至选集》、《冯至全集》)中,“我们吻着,绝没有温暖的情味”改成了“爱怜里没有温暖的情味”,这显然是为了把“我们吻着”加以放逐。
3.《北游》之《10.“Pompeji”》(作于1928年,收入《北游及其他》):“我怀念着酒池肉林的Pompeji城,/坐在一家地窖的酒馆里,/酒正是一杯一杯地倒,/女人们披着长发,裸着身体”,在新版本(《冯至诗文选集》、《冯至诗选》、《冯至选集》、《冯至全集》)中改为:“我怀念着古代的Pompeji城,/坐在一家叫做Pompeji的酒馆里,/酒正在一杯一杯地倒,/女人们披着长发,唱着歌曲。”这种改动的目的也很清楚:“酒林肉池”的糜烂生活是不应该“怀念”的,女人们“裸着身体”当然更不行,何况这也是其所“怀念”的内容。
由以上材料可见,冯至诗集的1949年以后的版本,较之其原来的版本是有很大差别的。当然,正如冯至自己所说,作家有权修改自己以前的作品;但研究者却不能根据其修改过的作品去了解作家在过去的文学成就、特色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所以,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必须注意到版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比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版本问题更重要。因为古代诗人(例如杜甫)的现存诗集的几种版本间的差异,绝不会有冯至诗集的新旧版本的差异那样大。同时,对研究古代作家来说,研究者只要找出其作品的原来面貌就够了,在传抄或刊刻过程中产生的不符合其原貌的异文并无多大研究价值;而对研究现代作家来说,由于作家自己的改动而产生的异文却是大有研究价值的——这其中不仅可以看到作家自己的思想变化,更可以看到时代的影响。也正因此,现代文学的文献学研究是到了亟须提上日程的时候了。
[收稿日期]2006—04—30
注释:
① “伟大的精灵”中的“精灵”一词,出于汉代傅毅《舞赋》的“绎精灵之所束”,为心灵之意。强调心灵的伟大作用,也即鲁迅所说“掊物质而张灵明”(《摩罗力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