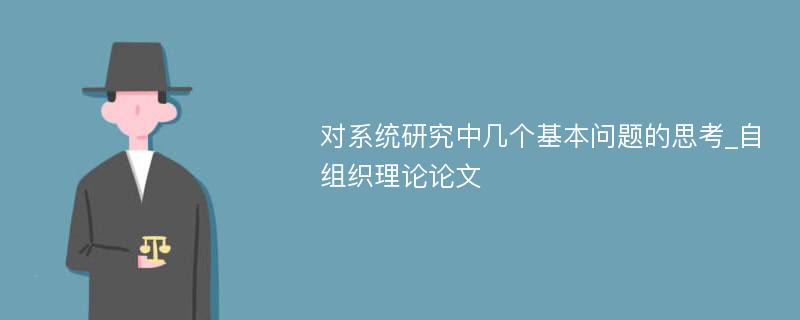
对系统学研究中若干基本问题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系统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自从贝塔朗菲(Bertalanffy L V)于1937 年提出“一般系统论”一词、1945年发表“关于一般系统论”一文[1]以来, 系统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2]。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本文将对系统学研究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反思,并简述对这些问题的见解。
2 关于“1+1>2”
整体性的主要含义并不在于比较“整体”和“各部分之和”的量的大小。而且,仅就量的关系而言,“整体”和“各部分之和”之间不仅可能存在“1+1>2”的关系,而且还可能存在“1+1<2”或“1+1=2”的关系。因此,将整体性简单地理解为“1+1>2”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例如,在韩国,大型企业集团的形成曾为韩国经济的腾飞起过重要的推进作用,但是大型企业集团无节制的多角经营和官商勾结产生了降低企业效率、削弱国际竞争力等诸多弊端,现又成为严重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系统所强调的整体性的本质并不在于整体与各部分之和的量的关系上,而在于整体与部分的质的关系上;研究系统与要素之间的关系不仅要重视整体与整子之间的静态关系(如非加和性、加和性和同一性),而且要重视整体与整子之间的各种动态关系(如整子的一体化倾向和自肯定倾向)。
3 关于“结构决定功能”
“结构决定功能”的原理常被看作是一条基本的系统原理,并且被看作是现代系统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早在系统研究兴起之前,生物学家们已强调生物结构对其生理功能的决定作用,工程师们也已清楚地知晓机械结构对机械功能的决定作用。
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上,现代系统研究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它静态地阐述了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对结构起反作用,而在于它阐明了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各种动态关系。在系统学看来,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不是单向的一者决定另一者的关系,而是双向的相互决定的关系;也就是说,结构与功能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结构转化为功能,功能转化为结构,两者的统一在于系统过程。
上述的理解是以对结构与功能的科学认识为基础的。首先,结构与功能被看作是同位概念,而不是主从概念。其次,结构被定义为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分布关系的总体,而功能被定义为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活动关系的总体。有了这种认识,就不难阐述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动态关系。
4 关于子系统与分系统
无论从经验上还是从理论上可将一个系统的下层系统分为子系统与分系统。在理论上,子系统是基于系统构成成分的概念,而分系统是基于系统构成活动的概念。在系统结构与要素的关系侧面上,系统的下层系统可称为子系统,而在系统功能与要素活动的关系侧面上,系统的下层系统可称为分系统。如果我们根据一定标准将系统要素的活动分成若干类型,并将系统要素看作是各种特定活动的承担者,那么就可将承担特定活动的特定要素的集合体看作是系统的分系统[5]。这样, 系统功能可视为各分系统功能的总体,而各分系统的功能可视为系统功能的特定侧面。
在系统研究中,一方面要研究系统的各层次子系统,另一方面要研究系统的各种分系统,并在此基础上要建立系统的子系统—分系统矩阵,或称子系统—分系统表。在为各种具体系统建立子系统—分系统表时,米勒(Miller J G)先生所编制的生命系统子系统—分系统表多有借鉴之处。
5 关于熵、负熵与信息
在系统学领域,围绕熵、负熵、信息等进行的许多争论中有些是物理学等其他领域长期争论的重演,有些是在系统研究中新出现的。
在探讨系统的可逆性与不可逆性的关系时,人们虽然广泛承认热力学熵与统计力学熵的科学性,但是围绕对热现象的统计解释仍然争论不休。当统计力学熵被示为微观状态的概率分布的函数时,以可逆结果的可能性之极小来解释热力学系统的不可逆性依然是引起争论的根源。实际上,对热现象的统计解释只能给出大量事件中某一事件出现的概率大小,不能给出各种事件出现的时间上的先后次序。
在熵、负熵与序的关系上之所以发生各种混乱,是因为讨论者忽略了下列几点:物理熵(热力学熵与统计力学熵)与序不是同一论域中的概念;就其含义而言,热力学熵与序无关,统计力学熵也不能直接用来表示热力学系统微观状态的无序程度;熵具有可加性,而序不具有可加性;对于序需要考虑其层次性和内容;负熵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它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错误的。因此,用熵或负熵概念来讨论一般系统,尤其是社会经济系统的有序性和无序性是不可取的。
在物理熵与信息的关系上,也不能建立两者之间的普遍的对应关系。信息是一切系统的三个基元(指要素、活动、信息)之一,因此信息与物理熵也不是同一论域中的概念。不仅如此,信源熵不能直接表示信源的无序程度,信息量也不是系统有序性的普适测度。
各种喻义熵(如社会熵、经济熵、精神熵、管理熵等)概念的非科学性或伪科学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概念的引入不可能为科学的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
6 关于自组织与他组织
在理论上,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系统的自组织与他组织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正确理解。这里,区分他组织与自组织的根据在于系统赖以组织化的信息是否来自系统的外部。自组织是系统新模式的自创生过程,是系统新信息的自创生过程;与之相反,他组织是系统在现成外部信息的输入下进行组织的过程。
在实践上,当利用自组织与他组织概念讨论具体系统进化时,重要的是如何判断所发生的是自组织过程还是他组织过程,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实际上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区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两者的区分,一是与系统边界的划定有关,二是与所选取的时间尺度有关。
就社会文化系统而言,所出现的事件通常是自组织与他组织的统一过程。例如在经济系统中,市场调节属于自组织过程,计划调节(或政府干预)属于他组织过程。对经济系统来说,如何处理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自组织)与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他组织)的关系始终是经济系统的运作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许多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为此提供佐证。
7 关于“系统进化的周期发展规律”
在系统进化论中,我将系统进化的趋势明确地分为层内进化与层间进化,并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指出:在大量复杂系统的层内进化中,在封闭—开放、平衡—非平衡、线性—非线性三对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系统依次经历平衡有序结构、准平衡结构、活性结构、混沌结构[6];当系统经过层间转化进入新的层次后,在新的层次上也将重演这四种有序结构的依次更替。我把这一结果称为系统进化的周期发展规律。
但是,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这一规律虽然在大量复杂系统中广泛起作用,但是它的适应范围尚不清楚,并且它尚未具备较严紧的数学描述。不仅如此,对现实的具体系统来说,由于各种内部和外部原因,实际的进化进程可能有非常不同的表现,甚至会出现某些阶段的缺失或系统的突然瓦解(例如,一个国家可能因外国的侵略而突然灭亡)。因此,任何机械地将这一规律套用到具体系统进化研究的研究方式都是不可取的。
当运用系统进化的周期发展规律研究具体系统时,对其中的各种因素和各种结构都应加以具体化。在社会经济系统研究中这一具体化操作通常是极为艰难的。但是,无论怎样,只有全面系统地考虑政治波、经济波和文化波(包括科技波)以及它们之间的谐振机制,人类才有可能在社会生活中驾驭系统进化的周期发展规律,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8 关于吸引子与系统演化趋势
用数学语言来讲,在理想情况下,系统从简单到复杂的层内演化序列可表示为不动点→极限环→二维环面(→高维环面)→混沌吸引子。在其他情况下,亦可出现与之不同的演化道路。例如,在系统进入混沌的倍周期分叉序列中,混沌不是来自环面的分叉,而是来自极限环的无穷多次的倍周期分叉;在阵发混沌道路中,又可观察到另一种形成混沌的方式。
吸引子概念之引入系统演化研究,确实为系统进化过程描述的数学化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手段。有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将用吸引子概念描述的系统演化序列的各阶段和系统进化的周期发展规律中所说的各种结构有机地统一起来。如能在两者之间建立适当的对应关系,系统进化的周期发展规律将在描述的数学化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从而为这一规律的应用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9 关于系统演化判据
在系统的无序—有序、有序—有序、有序—混沌的转变中,既有前时性发展,又有退化。为了判断系统进化的方向、程度和速率,必须有相应的判据。人们已为解决系统进化方向、各种结构的生成条件、各种吸引子的发生条件、系统有序度的增减等问题提出了各种判据,如物理熵判据、维数判据、李雅普诺夫指数判据等。
这些判据从不同的角度刻划了系统的演化。它们都有其可取之处,但又都有不足之处。似乎至今没有一个判据是普适的,每个判据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或适用侧面。考虑到系统及其演化的复杂性,能否在现有的各种进化判据的基础上开发出一个统一普适的综合判据体系,仍然是一个谜。在为开发这种综合判据体系作出努力的同时,有必要进行其他方式的努力,例如对不同类型的系统建立与之相应的演化判据。不管怎样,系统演化目前特别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无疑是系统演化判据问题。
10 结语
上面提到的问题都不是什么新问题。这些问题中有的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显然,这些问题都是系统学的基本问题。如能圆满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21世纪的系统学将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长足的进步。
收稿日期:1998—11—17
标签:自组织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