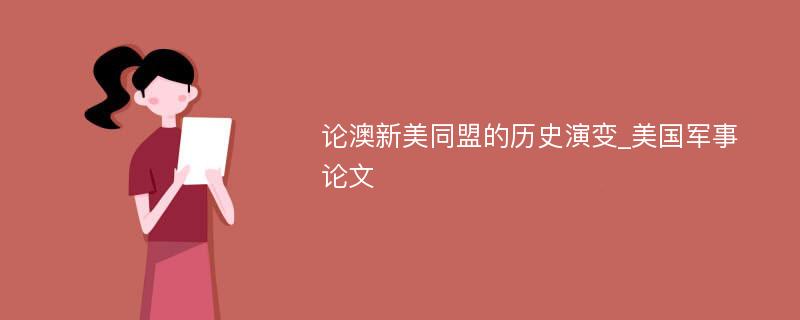
试论澳新美同盟的历史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盟论文,试论论文,历史论文,澳新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1年形成的澳新美同盟是美国亚太地区重要的三边同盟,作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南锚”,该同盟对于美国全球军事部署尤其是军事技术的部署具有特殊的作用。澳新美同盟自形成以来,经历了冷战时期的发展、持续和裂变的过程,并发展到冷战后的松散状态。在21世纪,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中,澳新美同盟主要是澳美同盟的作用又变得十分突出。因此,回顾澳新美同盟形成演变的过程,对于认清该同盟的实质并预测未来的走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澳新美同盟的形成
《澳新美安全条约》(ANZUS)于1951年9月1日签署于旧金山,正式实施于1952年4月29日。这个条约标志着澳新美军事同盟的正式形成,澳新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美国继军事占领日本之后,在太平洋地区新的用于遏制共产主义力量和影响的多边安全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签署后的该条约也成为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核心。(注:J.G.Starke,The ANZUS Treaty Alliance(Melbourne: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65),P.1.)
澳新原是英国殖民地,20世纪初取得了英联邦自治领的地位,但是它们的外交、政治、军事和经济基本上仍受英国控制。但澳大利亚一直渴望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形成这一地区的独特力量。1939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就曾设想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太平洋强国的协作。接着新西兰总理弗兰瑟(FRASER)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8月提出了太平洋安全构想。(注:Ibid,pp.7-8)
由于日本加速向东南亚扩张,以新加坡为基地的英国军事力量迅速崩溃,英国已无力保卫其在太平洋上的自治领。澳大利亚政府开始从过去完全依附英国转而寻求美国的保护。从二战结束到1949年末,美国对澳新关于缔结太平洋公约的倡议并不热心。当时美国显然并不愿意与那些共同利益相对较少、对集体安全只能发挥有限作用的国家进行安全合作。澳新地区在美国全球布局中只是“边缘地带”。1950年1月2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记者联谊会谈到的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务范围,仅仅“自琉球群岛起,到菲律宾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没有被列入这道“环形防务线”内。(注:Department of State: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950-1955,p.2317)在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以及在对日和约等问题上需要获得澳新的支持,才对澳新的建议改变了态度。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务范围扩大为“日本—硫球群岛—福摩萨(即中国台湾省)—菲律宾—澳大利亚这条近海岛屿链”。(注:FRUS,1951,VOL.VI,pp.135-136.)
1951年2月14日,杜勒斯开始与澳大利亚外长斯彭德、新西兰外长道奇举行会谈,讨论签订条约问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原先提出由太平洋地区多数国家组成太平洋公约,美国不同意。美国提出由澳、新、美、菲、日五个国家签订类似于北约组织的多边联盟体系。澳新反对日本参加。在澳新的坚持下,最后一致同意由澳新美三国订出安全条约。美国签订三国条约的前提条件包括:(1)将三国公约与对日和约挂钩,从而促进对日和约的缔结;(2)建立澳新美理事会,但坚持区别对待欧亚事务,不与北约组织等其他地区性组织或国家集团挂钩;(3)以‘一系列安排’代替“单一性安排”的主张,(注: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5,Vol.VI,p.183,P.293.)即分别与日本、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条约,同时把这三个安排拼成一个系列,全部纳入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和政策的轨道。
三国条约反映了美国的基本战略意图,即首先明确美国作为保护者的特殊地位及合法性;其次,表明美国在当时既想称霸西南太平洋地区,又不想承担过多责任。
1951年签署的ANZUS条约则为美澳新正式结盟提供了一个基础。1951年9月1日签订的《澳新美安全条约》,连同8月30日签订的《菲美共同防御条约》、9月8日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则是美国根据新的国际形势,为搭建亚太地区军事体系所迈出的“第一步”。
美澳新条约中相互援助的主要保障体现在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款上。与北约的第三条相适应,盟友应“维持和发展各自和集体的抵御战争的能力”。这一条款体现了美国参议院1948年通过的范登堡决议案,即持续和有效的自助和互助应成为美国参与集体安全安排的前提。从一开始,美国即期待其盟友对联盟体系做出贡献,即至少在地区范围内创立一个控制共产主义势力范围的军事力量链。
条约第三款规定:无论任何一方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威胁,条约方将进行协商。为了使磋商更为主动,威胁不仅仅限定在武装进攻,包括不稳定、颠覆、甚至是重新武装政策也被视为主动进攻。另一方面,盟友只需进行磋商,并不一定要采取特殊行动。而且,威胁必须在地理上限定于条约规定的太平洋地区。但在北约中没有这一限制。
条约的地理限制体现在条款四和五之中。尽管条约适用范围包括整个澳大利亚全境,但条约中对太平洋地区这一概念并没有准确的界定,这就留下了按照变化的形势来判定这一概念的空间。朝鲜半岛和越南均可能包括在澳军事介入的范围中。
条约第六款规定:每一方认识到对太平洋地区任何一方的武装进攻将是对自身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但在如何做出反应的表述为“将采取符合其宪法程序的行动”。(注:《国际条约集》(1950-1952)[M],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326-328页。)而北约对使用武力有详细的条款。
由此可见,澳新美安全条约虽然使澳新统治集团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安全保证”,但获利最多的还是美国。美国虽然在亚太地区形势(主要是东北亚地区形势)出现巨大变化后才加快了对南太平洋控制的步伐,但通过澳新美安全条约,排挤了英国势力,增加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在南太平洋上获得了“牢靠的战略后方”。
具体而言,驱动澳新积极与美结盟有这样一些因素:
首先,澳新等国对被排挤在西方集体安全体系之外深感不安。美国与西欧诸国签署大西洋公约使澳新认为美国先欧后亚甚至重欧轻亚的作法实际上将南太平洋地区置于安全防范的真空地带,加剧了南太地区的不安全性。“1949年上半年,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签订北大西洋公约后,澳新两国领导人担心:‘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承担义务的日益增加,可能导致他们对南太平洋事务的忽视’。”(注:Survey of British common wealth Affairs,1951,p.354.)因此刚刚上任的新西兰总理霍兰赶紧向美国呼吁,希望仿照北大西洋公约,签定一项太平洋公约。(注:New Zealand Foreign Policy Documents and Statements,1943-1957,p.27.)1950年3月9日,澳大利亚新外长斯彭德在众院发表外交政策演说,再次呼吁“所有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有密切关系,并能承担军事义务的国家,作出集体防务安排”。(注: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1948-1950,p.1065.)
其次,由于亚太形势的改变,澳新等国认为自己面临“共产主义扩张”和战后潜在的地区军事大国的崛起尤其是军国主义复活的双重威胁。当时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需要,正急于同日本签署和约,澳新等深受日本侵害的亚太国家认识到它们最为关切的日本的潜在军事威胁已被置于次要地位,因此他们惟一的方案就是以一个对美条约来抵消美日和约使他们感到的不安全感。1951年,斯彭德多次强调与美国签订亚太地区集体安全公约的迫切性,指出“现在订立太平洋公约显得比任何时候更加必要了”。(注: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1,p.478.)新西兰外长也声称:“新西兰政府认识到共产主义威胁是我们面临的真正危险,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如何建立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屏障。”(注:Foreign Relational Affairs,1951,P.478.)他们要求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承担军事义务,把缔结太平洋公约作为澳新两国签署对日和约,支持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前提条件。
第三,澳新等国欲在南太地区发挥特殊影响,就必须借助美国的力量。二战后,澳新政府都希望保持和发展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从防卫上讲,澳新领土广阔,人口不足,防卫能力有限,作为一个“中等国家”,它必须“与强者为伍”,也就是说必须与正处于“全盛时代”的美国“政治上合作,军事上联盟”。(注:杨宇光:《试析澳新美条约签订前后美、澳、新、英关系》,《战后国际关系论丛刊1984》,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印。)其次,由于澳新经济在二战中不仅没有受到损害,反而由于英美战时军事订货骤增而使其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到战后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水平,因此实力的增长,也使澳新政府特别是澳政府希望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与此同时,美国也出于全球遏制战略的需要,最终决定将澳新纳入其联盟体系之中,从而使美澳新联盟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扩充防务范围之后的产物。
通过对美澳新三国条约形成过程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战后初期澳新美关系形成的新格局,反映了战后国际形势,特别是亚太地区形势的深刻变化。日本的战败,“向苏联一边倒”的新中国政权的建立,英法荷殖民主义的迅速瓦解,以及苏联实力的有限和美国军事实力的强盛。(注:虽然苏联战后成为一个大国,但它的力量投送能力十分有限,并且主要集中在欧洲而不是亚洲地区;而美国则是当时惟一的核国家。)标志着亚洲战略平衡的巨大转变,使美国成为这一地区具有支配地位的大国。
第二,该条约充分反映了同盟中较弱的一方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主动强化与地区和世界性大国军事安全合作的过程。(注:澳大利亚一直有一个在南太平洋地区发挥特殊影响的战略构想,其中的一个具体步骤是及早地控制住东南亚。因此,它一直主动介入这一地区的军事安排。在主动性方面胜于美国其他的双边盟国,从建立到发展均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与老牌帝国合作的安全模式让位于与新兴大国的合作,这是与国际力量的起承转合相一致的。澳新美条约的缔结是三国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澳新对美关系上的主张和做法在某些中小国家中有一定典型性。美澳新同盟的建立反映了利益界定在同盟合作中远远大于文化认同。从传统上看,美澳新之间文化上的相似性要比美国的其他亚洲盟国更多,但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联系和融合则比美国更多,因此文化意识形态的因素只能在一定情况下发挥作用,而本身并不能成为第一前提。(注:值得注意的是,最早由防范日本而起的美澳同盟后来与日本间接成为盟友,并渴望加强合作,美澳同盟经几十年进行了二次威胁目标的转换:先是防范日本后转为防范苏联。)
第三,在遏制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背景下,从ANZUS的形成和其一般特征来看显然是想以北约为代表的西欧安全模式的构想为依据,但是从一开始两者就有着起点上的不同。亚太地区的国家对苏联威胁程度的感受不同,各国地缘战略上具有多样性特点,再加上这一地区一些国家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难以形成针对一个共有目标的凝聚力。因此,ANZUS并没有在太平洋地区建立起一个广泛的安全体系,并不是一个能够与北约相提并论的组织。
第四,ANZUS并不是一个能够满足各种目的的机构,美国并没有承诺在各种条件下支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即避免了传统军事联盟中自动卷入的条款。同时ANZUS也没有完全取代英国在这一地区与澳新的合作关系,澳新两国虽然强调ANZUS在太平洋安全领域的首要性,但仍然与英国保持了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注:比如1949年成立的澳大利亚的情报安全组织(A-SIO),就是在英国的情报组织协助下组建的;在东南亚条约组织中,澳大利亚仍然以英联邦的重要成员身份与英国保持合作;再有,澳大利亚在这一时期希望发挥英国与美国利益调停者的作用。)因此,ANZUS并不是一个完全排他的条约。另外,该条约的非排他性还表现在自条约签署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扩大条约参与国的建议和争议。
总之,ANZUS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惟一的三边联盟,是美国为搭建亚太地区军事体系所迈出的“第一步”。它反映了美国的基本战略意图:既明确了美国作为保护者的特殊地位及合法性,又不想承担过多的责任。另一方面,该条约又很难成为真正意义的多边联盟,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三国规模和实力的明显不对等:美国是世界大国,澳大利亚算是地区大国,但新西兰连地区强国都不是。这种差异决定了它们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协调的复杂性。
二、澳新美同盟的持续发展和裂变
冷战时期,澳新美三国同盟的持续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亚太地区局部热战时期的三国同盟: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
在朝鲜战争中,尽管澳大利亚反对美国轰炸鸭绿江边的目标和支援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担心这类举动会引发中国入朝参战,但是澳大利亚也认为中美之间公开的敌对是其安全的一大威胁,因此对美国入侵朝鲜的举动最终给予支持,并把它视为联盟协议所要求的一部分。
在50和6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认为该联盟是澳大利亚防务的保护者,保证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承诺又是澳大利亚防务的关键目标。为了保证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安全承诺,澳大利亚必须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给予足够支持。于是澳大利亚于1962年卷入越南战争。最初是派出三十个军事顾问到越南,两年后其顾问的人数翻了一番,1965年初增加到100人。这些决定均是因美国的要求而做出的。澳大利亚外交部的文件认为:澳对越南的军事援助不是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对越南防务援助要求的反应,而是美国频繁表达的希望朋友和盟国给予政治支持的结果。(注:Joseph A.Camilleri,The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US Alliance: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Nuclear Age(Boulder:WEST-VIEW Press,1987),P.13.)1965年,澳新同意派部队参战。1967年10月,澳大利亚派往越南的部队增加到8000人。在整个越战期间,澳新军队总计配合美国作战7次,付出了伤亡3000余人的代价。除军事介入外,澳大利亚还支持了美国所有的军事行动计划,比如空袭越南北方、扩大空中打击等。
1964年,澳大利亚外交官阿伦·鲁道夫说:“我们的目标是拉近与美国的关系和形成一种互助联盟的意识……参加越战可以形成广泛的相互信任”。(注:M.Sexton,War for the Asking:Australia's Vietnam Se-crets(Melbourne:Penguin,1981),pp.44-45.)另外,澳大利亚还试图通过支持美国在防务、通讯和情报的部署来巩固美国的存在,这就导致了1963年在贺尔特的西北角通讯站和1966年在松峡的卫星情报设施的建立。而美国则从50年代中期起就有意识地发掘澳大利亚的战略潜力。1957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战略报告认为:澳新均拥有可用的军事潜力;在远东其他地区被否定后,东南亚的脆弱和不稳定更增加了他们的战略价值。(注: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Long-Range US policy in-terests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NSC 5113/2,23 August,1957,p.10.)60年代的肯尼迪政府出于军事和技术合作的迫切需要,决定提升澳新美同盟的价值。1962年5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给予ANZUS很高的评价,说它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共同理想和相互信任的条约。(注:Joseph A.Camilleri,p.15.)于是,澳新美同盟形成了60年代的所谓联盟发展期。
第二阶段:冷战转型期的同盟关系:从依赖到在联盟下的自主。
1969年7月,尼克松在关岛提出的新政策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的亚洲政策,也成为澳新美战略关系的转折点。尼克松主义的核心在于美国在今后将减少对亚洲大陆的军事承诺,而由当事国承担防务的更大责任。在美国推出尼克松主义之后,澳大利亚开始强调本土防御和与东南亚的亚洲国家保持双边或多边合作。
在7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从自身利益出发,开始推行“面向亚洲”的经济政治政策,放弃了依赖于大国的防务和前沿防御原则(比如放弃了所谓对越南的前沿防御),转而倾向于强调自主本土防务。1972年,惠特拉姆领导的工党上台后,认为在美苏关系趋于缓和之后,澳大利亚的安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另外由于澳大利亚在地理上远离霸权争夺的主要地区,因此即使存在威胁,本土遭到袭击的可能性也不大。地区性冲突才是澳大利亚防范的重点。这就使得冷战初期结成的面向全球争霸的澳新美联盟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
然而到8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发现其自我防务的政策并不能使澳大利亚走出防务的困境,反而维持和扩大了与美国的战略联系。因为只有美国能够向澳大利亚提供情报、防务技术和职业的军事训练,而这些帮助又是澳大利亚能够独立地处理地区威胁的前提条件。这就是联盟管理理论强调的独家援助对于维系联盟的重要性。(注:根据联盟理论,提供经济、军事支援能够促成联盟的形成和巩固,当援助物具有专属性而且无法替代时,援助国的影响力会更大。)正如1987年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所说:“澳大利亚自我防务政策是在联盟和协议的框架中实行的……澳大利亚加入到广泛的美国情报网中。这些情报不仅限于全球大国竞争,它也是澳大利亚在地区政治和军事发展中的情报补充。”(注:诸如,JINSALEE海岸雷达系统,F-111和F/A-18战斗机HARPOON反舰导弹加上最先进的和复杂的电子辅助系统,均是由美国提供的。1969年签订了在澳大利亚南部的乌麦拉的卫星地面站的协定,最初的设想是对苏弹道导弹发射进行早期预警以及监视核爆炸,后来成为监视东半球广泛的弹道导弹发展的工具。1991年在海湾战争期间提供了对伊拉克导弹发射的第一预警。Barry Rubin and Thomas Keaney(eds.),US Allies in a Changing World,(London:FRANK CASS,2001),p.250.)
但是,正是在这一阶段,澳新美同盟中的新西兰却出现了离心倾向,致使联盟发生了裂变。(注:核战略分歧是引发美新联盟裂变的重要原因。从澳新美同盟的裂变过程可以看到,该同盟的裂变只能称为有限裂变。它没有引起美国担心的连锁反应——澳大利亚没有脱离该联盟,美国的其他亚太联盟也没有相类似反应;虽然1984年新西兰立法禁止核武器船只进入其港口后,美国也于1986年暂停了对新西兰的安全义务,不过双方从1994年起已提升了政治和军事的接触,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接触能持续发展至恢复ANZUS的联盟关系。)
三、冷战后澳新美同盟的变化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原有的世界力量对比,也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格局。亚太地区形势的变化也反映在美国和其盟国澳大利亚的对外安全政策中。
对于美国而言,保持军事优势、维持地区平衡、发挥主导作用仍然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联盟体系的根本原因。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曾指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和盟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需要美国在太平洋这一地区保持强大和永久的存在。(注:Barry Rubin and Thomas Keaney,p.168.)澳大利亚,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新西兰,仍然是美国太平洋战略的关键,其作用已由地区战略平衡器得到进一步拓展。澳大利亚方面能够在保护五国联防、协助美国军队在印度洋的驻防,使澳大利亚的领土和设施为美国发展和更新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提供保证等方面发挥特殊作用。因此,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美澳同盟仍然在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澳大利亚的联盟政策在冷战后经历了一些变化。冷战结束时,澳大利亚的自主倾向上升,希望以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发挥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特殊作用,将战略重点从ANZUS的利益和重点中分离,将地区合作集中在经济安全、非殖民化和非军事化等三个目标上。从地区稳定和它自身的长远利益来看,澳大利亚希望限制所有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尤其是拒绝所有的核活动。但是从1996年开始,随着东南亚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印尼局势的变化,(注:主要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印尼国内局势的动荡——包括东帝汶独立问题上,澳大利亚都表示出特别的关注并希望在这一地区发挥更大影响。)澳大利亚的政策开始改变,表现为更多地向美国的政策靠拢,并向东南亚回归,强调同盟的地区性,在同盟的框架内对这一地区增加的安全的复杂性和不稳定做出反应,以同盟的合作来提升自己的防务能力;另一方面参加广泛的多边安全合作。1996年7月,澳美再次提高了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两国签署了军事协议并发表了《澳美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强调两国合作对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的重要性。双方还决定于1997年3月在澳昆士兰州肖尔特湾进行二战以来最大的澳美军事演习。另外,澳大利亚还扩大了美国在澳的情报基地,签订了一项新的十年租借条约,允许美国使用对美全球军事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的澳松峡湾的情报基地,同意美国反弹道导弹太空预警系统在澳建立地面中继站,同时还加强了同美国在军事技术、情报分享和后勤支持方面的紧密合作。(注:Bany Rubin and Thomas Keaney,p.246.)霍华德政府在1997年10月发布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中指出,计划能力发展的关键步骤就是“决定我们如何将我们做出的优先目标和各种不同类型的任务之间的平衡”。(注:Department of Defense,Australia Strategic Policy,1997,p.35)
20世纪90年代,美澳同盟在合作方面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同盟的地区因素增加,强调地区威胁和地区冲突的复杂性,力图在新的地区安全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随着美国对亚太地区重视程度的加强,尤其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澳大利亚也增强了其政策的地区性,它力图改变此前一直被排除在地区合作之外的状态,重返亚洲并积极介入该地区的事务。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澳为了提高在亚洲的发言权,希望密切与美日在防卫方面的关系。这是因为,由于马来西亚等国的反对,日中韩与东盟的对话机制‘东盟+3’和东盟自由贸易区都将澳排除在外,澳对自己‘在亚洲的发言权极其低下’感到非常焦急。”(注:[日]大石信行:《美澳强化军事关系引起各国警惕》[N],《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9月6日。)1997年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也指出:对于美澳双边而言,“随着美澳联盟被公认为冷战后亚太地区的战略框架的重要因素,维持和强化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联系和地区主导作用在近些年已变得更为重要了。”(注:Department of Defense,Australia Strategic Policy 1997,p.19)
其次,同盟体系与多边安全合作并行。多边安全合作是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组成部分,但是在90年代初期,除了冷战期间建立的双边联盟之外,亚太地区几乎没有安全合作,(注:即使ANZUS是一个正式的三边条约,但在80年代中期美新关系受到严重损害,只有双边职能发挥作用。澳新关系也受到损害,但美澳关系却得到加强。)随着各国决策者对该地区安全的不断关注,从1992到1997年,安全合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地区范围的安全对话机制正式地建立,其中尤以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简称ARF)最为突出,大量的信任和安全措施 (CONFIDENCE-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已经建立,包括高官互访、联合演习及联合训练计划迅速增加。(注:到了1997年,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防层面的合作由于费用问题而锐减。)
第三,技术合作得到加强。技术合作、设施共享一直是美澳同盟的一大特色。随着军事革命(RMA)的发展,军事技术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美国的战略技术计划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密切的盟友澳大利亚和日本将成为美国信息主导进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注:Department of Defense,Australia Strategic Policy 1997,p.56-57.)澳大利亚也把接受军事革命视为将澳大利亚防务引向高科技阶段的必由之路。1997年澳国防决策者的报告指出:在现代战争中,赢得战事取决于是否在开始时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手和他们的企图,因此优先发展的最高能力即是“知识优势”,即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使澳大利亚相对弱小的力量达到最大效益。
第四,横向联合增长,美日澳三边联合势头上升。2001年7月在河内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澳大利亚外长唐纳向日本外相田中真纪子提议由日美澳三国建立一个协商亚洲安全问题的新框架。澳希望以三国“非正式对话”的形式来补充东盟地区论坛的作用。据认为,在这个新框架中,三国将就为应以新冲突的发生和原有冲突的扩大而如何分担维和行动作用的问题进行协商。澳国内甚至有人提出应该寻求让日本加入《美澳新太平洋安全条约》,使其成为《日美澳新太平洋安全条约》。(注:[日]大石信行:《美澳强化军事关系引起各国警惕》《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9月6日。)对澳大利亚向日本提出的建议,美国表示支持。因为对美国来说,澳大利亚是日益不稳定的亚太地区内一个“坚定的同盟国”,并且几乎是美国在南太地区惟一的安全伙伴,因此ANZUS已成为与日美安全条约相并列的亚太地区防卫的支柱。
2001年“9·11”事件之后,ANZUS又呈现出一些新的动向。澳大利亚成为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的最积极的同盟者之一,无论是阿富汗战争还是新近发生的伊拉克战争,澳大利亚都给予美国军事物资和人员方面的大力支持。比较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国,澳大利亚的举动尤其引人注目。显然,联盟的传统价值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找到了新的契合点。澳大利亚虽立足于南太平洋地区,但其投射的影响已经不仅局限于南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而是跟从美国的战略向中近东延伸。冷战后关于澳美联盟价值的争议暂时得到平息,东南亚的反恐形势也为澳大利亚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或许反恐战争可能导引出一个更紧密和更强势的南太平洋地区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