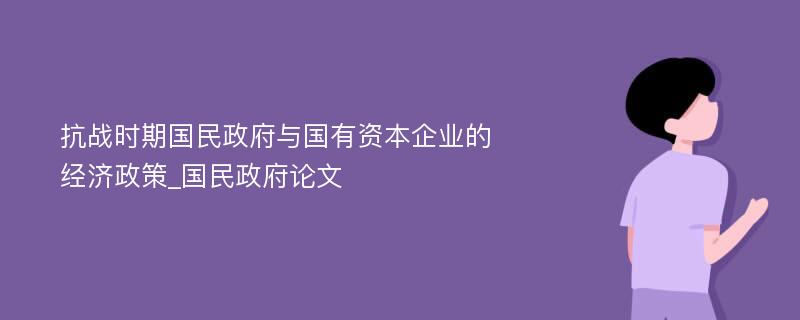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统制经济政策与国家资本企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国民政府论文,经济政策论文,资本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G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4-0140-11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海内外学术界有关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政策以及国家资本企业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①。但是就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统制经济政策与国家资本企业而言,有待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抗战时期,统制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国家资本企业的发展,是支撑战时后方经济的两大重要支柱,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确立以及国家资本企业发展的基本描述,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一具体的考察分析。
一、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提出与形成
1.统制经济政策在战前的初露端倪和战时的确立
统制经济政策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以国防建设为核心的总方针下,制定和推行的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国民政府战时施行统制经济政策的最重要原因,固然是战时的特殊环境和条件所使。但是,从思想和政策的逻辑准备上看,实际上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正式提出,在战前已经具有了一些基本的准备与大致的轮廓。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国民政府战前实行的基本经济政策究竟应该是界定为“计划经济”②,还是“统制经济”③,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表述和看法。而这两种表述及提法又都能在当时国民党、国民政府重要的会议文件,以及正式颁行的法律、法规、制度、规程中找到依据。也就是说,无论是当时国民政府领导人的讲话,还是有关的文件、规程中,我们都既可以看到“计划经济”的提法,也可以看到“统制经济”的提法。这是因为在此时期中,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尚处于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对于当时国际上各种经济思潮和经济发展模式还有一个认识和择取的过程;加上当时国内的思想界、学术界对“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认识也颇不一致,一些论述和解释本身也较为模糊,由此造成国民党、国民政府对于经济政策的表述,尚缺乏一个统一的定论。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一些讨论。
首先,一般来说,所谓“计划经济”是指政府通过经济管理上的一系列计划手段,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通过各种计划措施来指导、调控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引导整个国民经济按计划发展,并最终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它集中反映了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意志;而统制经济政策一般发生在非正常社会状态下,如战争、经济危机时期,政府在控制国家财政的前提下,通过法律、行政的手段,直接干预生产、流通、分配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大力发展国有经济,以确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对金融、税收、物价、外贸等各种经济活动施行强力管制,从特征上看,统制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强调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强力干预,更大张旗鼓地主张建立国有经济和国家资本体系。
其次,从上述出发,尽管统制经济政策一般多实行于非常时期,但从1927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从国民政府所施行政策的实际内容和发展轨迹上看,推行统制经济政策,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统制权是其一贯的方针。从金融整顿开始,建立和强化国家财经控制系统,到加强对工业和交通的控制,大力发展国家资本,并把私人资本工矿业发展纳入国家计划指导范围,基本上实行的是一种发展统制经济的政策,至少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施行统制经济的意向越来越明确。早在1933年实业部拟定的四年实业计划中,就已经有对保险、粮食、棉花、煤炭等重要产业实行国家通盘筹划,以求积聚经济实力的内容,表明国民政府至少已经流露出施行统制经济的意向。1934年,国民政府陆续出台了一批有关物资统制的计划、纲要,如国防设计委员会计划部制定的《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运输动员与统制初步计划》、《粮食存储与统制计划》等;资源委员会制定了《统制全国钨锑矿方案初稿》、《钨锑统制实施纲要》,以及对“食品、及重要农产原料、矿产品、工业、贸易、交通、财政金融、人员等七大类数十项临时统制动员计划”④,更是标志着国民政府对物资管理施行统制经济的政策,已经完全提上议事日程⑤。 1935年蒋介石在《全国总动员要义》中提出:“全国总动员的基本前提是组织与统制”,同年10月又进一步提出:“一切人、财、物力,都要在中央政府整个国策与全盘计划之下,严密地统制起来。”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经济统制政策的意图已成定局,从初步意向到局部计划再扩展至较为全面的考虑,国民政府施行统制经济政策的步骤在战前已经悄然展开。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应对突发的战局,果断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施行战前已经开始酝酿的经济统制。1937年8月至年底,紧急颁布了《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增进生产及调整贸易办法大纲》、《战时粮食管理条例》和《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条文,以求迅速地将平时经济转入战时经济状态。紧接着,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和《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标志着国民政府实施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经济方针已经基本确立。1939年3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明确宣布“依于战时人民生活之需要,分别轻重,斟酌缓急,实行统制经济”⑥,正式明确使用“统制经济政策”这一概念。此后一直到1941年,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陆续颁布了数十个有关经济统制的具体法令,其范围涉及国民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对包括工矿、农商、粮食、金融、外汇、物价、物资等国民经济各个重要部门进行了全面统制。1942年3月,在严峻的战略相持阶段下,国民政府又颁布并实施了《全国总动员法》,声称“对全国任何一人一物,悉加以严密组织与合理运用,使成为一坚强之战斗体系”。由此,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的政策体系在逐步完善和不断加强中得以完全确立。
2.战时统制经济政策实施的组织准备
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国民政府在统制经济政策意向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对国民经济的一些重要领域已经表现出图实施和推行统制经济政策的倾向。如在金融行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四行二局”的建立和改组,两次币制改革的完成,标志着国民政府对金融业实施统制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还逐步强化了国家财经的统制机制。其次是建设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等一系列国家经济管理机构的建立,以及实业部“四年计划”、资源委员会“三年计划”、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等等的推出,更是标志着经济统制已经由政策意向阶段开始进入具体的准备组织实施阶段。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配合和保证统制经济政策的全面施行,国民政府对原有的国家经济行政机构陆续进行了调整。1937年8月国防最高会议设立后,即将原中央政治会议下辖的财政、经济、交通三委员会移交其名下。1939年1月成立战时党政最高权力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其下属中央设计局主持全国政治、经济设计的审核,形成最高政治、经济决策机构。1941年2月,在行政院内正式成立了“经济会议”,1942年“经济会议”又改为“国家总动员会议”,成为战时最高统制机构。与此同时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将原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并将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部分,以及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第三部、第四部并入经济部;将军事委员会对外贸易调整委员会以及经济部国防贸易局并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将军事委员会农产、工矿及贸易调整委员会下属运输联合办事处改隶交通部;将铁道部及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部分并入交通部,并建立了若干专事经济管理的新部委。
上述国家经济行政管理部门的调整和改组,确保了战时国民政府在实施统制经济政策的总目标下,逐步确立国家资本在战时后方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建立国家资本体系的计划得以具体执行和落实。这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资本企业的相继形成,又为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最重要、最基本的保证。
3.统制经济政策下发展国家资本企业政策的确立
发达国家资本是国民政府初建之时已经确立的基本方略,在经济统制政策由形成意向到战时得以确立的同时,以国防建设为核心以及在基本工业中发展国家资本企业的经济建设基本方针也更加明朗。国民党四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国防建设初期方案》,提出以国防为中心,有限举办煤、铁、石油等原材料工业以“立国家之基础”⑦,国民党的五次代表大会又有代表提出:“国家如无重工业,更不可言国防”⑧,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经济建设方案》,更明确强调中国经济建设的首要目标就是“充实国防需要”⑨,而“钢铁、机械、煤油、飞机、汽车等重工业”是“经济建设之根本,国防设备之基础”⑩,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和《非常时期经济方案》, 提出“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目前之生产事业,应以供给前方作战之物质为第一任务”和“树立重工业的基础”,进一步强调了国防工业建设基本的政策,可见,建立以国防工业为中心,以基本工业为基础的国有工业体系,已经成为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和最重要的中心工作,建立有效的国营工业体系不仅成为建设足够强大的国防经济的最主要的手段,同时也是贯彻实施统制经济政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举措。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即提出:“抗战期间关于经济之建设,……凡事业之宜于国营者,由国家筹集资本,从事兴办”的原则;6月,经济部制定《抗战建国经济建设实施方案》强调“基本事业宜以国力经营”,具体包括“建设煤、钢、铁、铜、锌、钨、石油、机器、电工器材等工矿事业”(11)。这不仅符合国民政府战时经济服从“国防至上”的原则,同时也是统制经济政策下,国家资本向工矿领域渗透的表现。国民政府发展国家资本工矿企业,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国家机器的强大作用。首先,国民政府为战时国家资本企业的发展在法律上提供了依据,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实施的《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把“战时必须之各矿业”,“制造军用品之各工业”,“电气事业”划归为国家资本独家经营;同时还规定凡属有关日用品生产者、无力经营者、应迁移而无力迁移者、经营未能改善者、技术上有发明或专利者,均可由政府没收、接办、合并、代管、收买、合办、改组;其次,南京国民政府在投资方针上把战时国有资本企业的发展放在首位,1939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全国生产会议开会训词中提出:“要集中资本,扩张生产……我们今天要发展国家资本、奖励私有资本、欢迎友邦资本,来扩大战时生产”;其三,国民政府制定的产业统制政策,明确“以军需工业为中心”,并据此规定了“建立重工业,以此为自主发展一切工业之基础;开发矿产,自给工业原料;充实电业事业,使各种工业得有优廉之动力供给;奖励轻工业,力求日用品之自给自足;辅助乡村工业,使国有手工业渐次改良,而农产品得以加工制造”(12)等具体政策。这样,国民政府在法律、方针、政策各方面,为战时国有资本企业的迅速壮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战时统制经济政策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形势下,顺应战前的基本思路,针对战时时局的需要,作出的最重要的政策选择。推行统制经济的直接目的在于加强战时政府对物资、人力的控制,以政府可控的、足够壮大的物质基础支持长期战争对于资源的巨大消耗需求。在这样的背景和逻辑联系下,经济统制与国有资本企业的发展必然成为战时国民政府控制物力、人力的两大强有力措施,成为战时国家经济政策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确立战时统制经济政策必然需要发展和壮大国家资本,而国家资本的发展反过来又支撑和支持了经济统制政策的贯彻和实施。
二、统制经济政策下国家资本体系的确立
1.国家资本金融体制的进一步强化
国家资本企业是国有经济政策的直接产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即有着手建立国有、国营经济系统的基本打算,1927年到1937年十年中,发展国有资本已逐步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国家经济政策中的重要内容,并在国民经济部分重要领域付诸实施,其结果是不仅初步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国家金融体系,还设立了若干专门机构,创建了一批国家资本企业(13)。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战前初步形成的国有金融资本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迅速构建战时金融体制。1937年8月,为稳定剧烈动荡的金融市场,国民政府公布了《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并在上海成立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后改组为“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由蒋介石亲任,下辖“战时金融委员会”,以统制全国金融。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规定由四联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1940年颁布“非常时期管理银行办法”,以控制全国的银行。1942年7月,又规定全国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并发布了一系列财政金融措施。四联总处的建立,使国家银行的职能得到更大加强,它不仅掌管着四行本身的业务,还综理金融设施和经济策划,成为战时金融的最高决策、管理机构。战时国家行局不仅有支付饷汇、调剂金融的权利,还有配合政府经济政策,扶植后方工业、矿业、农业、商业、交通等各项生产和建设事业发展的义务。1941年 12月,财政部公布了《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规定银行经收存款的20%作为准备金,须“转存当地中、中、交,农四行任何一行”,1942年6月,根据国民政府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钞券,四联总处制定了《统一发行办法》,规定从当年七月一日起,所有法币之发行,统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7月,财政部又颁布《中央银行接收省钞办法》,规定所有各省地方银行的存券和准备金,均归中央银行保管。国民政府为加强战时金融统制,确立的国家银行集中准备金制度,既有利于增强国家银行的财力,又有助于扶植工矿企业、增强抗战的经济实力,作为战时后方惟一可以提供大量信贷的银行机构,四联总处成了发展战时国家资本的最高掌控机构。
2.国家资本企业在基础工业、重工业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
抗战之初,后方工矿业十分有限,为此国民政府曾组织了上海等地大批的民营工矿企业内迁,但是这些内迁工矿企业的数量和生产能力均远不能满足后方经济的需要,于是,加速创建国家资本的工矿企业,就成为国民政府实现为抗战提供必须的物质条件的重要措施,成为开发和建设抗战时期大后方工矿业基地的主要依靠。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以军需工业为中心”,“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的工业发展方针,这个方针具体包括五方面的内容:(一)建立重工业,以为自力发展一切工业的基础;(二)开发矿产,自求工业原料;(三)充实电气事业,使各种工业得有优廉之动力供给;(四)奖励轻工业,力求日用品之自给自足;(五)扶助乡村工业,使固有手工业渐次改良。标志着国民政府工矿业建设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大规模投资发展国家资本企业上,国家资本企业首先将在基础工业、重工业领域取得主导地位,并成为战时后方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作为承担战时国家资本工矿业建设的主要机构,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在战时得到极其迅速发展,战前资源委员会名义上要计划建设的单位虽然有23家,其中根本未建或流产未建成的有12家,真正属于资源委员会自办的只有中央无线电制造厂、中央机器厂和电工器材厂3家(14)。到1941年,资源委员会所经办的工矿企业已经猛增至78家,其中工业企业34家,矿业企业27家,电业企业17家(15),到1945年底,资源委员会所经办的工矿企业更是进一步上升到99家,其中工业企业44家,包括冶炼企业7家,机械企业5家,电工企业5家,化工企业27家;矿业企业30家,包括煤矿14家,石油开采2家,金属矿14家;电业企业25家(16)。资源委员会战时增加的企业,从资本投资以及产权结构上看,已经是以国有独资经办以及与地方政府合办为主,参股主办或者参股不主办(即控股或参股)为辅。从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战时建立起来的国家资本工业体系主要集中在冶炼、动力、能源、机械、电器等重工业、基础工业部门,以及特殊合金钢制造、电解铜、精密机床制造等新兴工业部门;从主要生产能力看,战时后方经济中所有的汽油、煤油、柴油、代柴油冶炼生产,以及铜、铅、锌、锰、钨、锑、锡、汞等有色金属的开采、冶炼全部都由国家资本企业生产;钢锭产量,1941年时国家资本企业的产量还只有民营资本企业的52%, 1942年国家资本企业的产量已经是民营企业的1.59倍。1943年为1.70倍;其它如电动机、发电机、变压器、电线等电工器材的生产,国有企业的产量也远在民营企业之上(17)。
可见,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经济中,以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为主体的国有资本企业基本上已经确立了其在重工业、基础工业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其生产几乎覆盖当时中国有能力生产的所有工业类别。这些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对严重缺乏重工业基础的中国工业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对增强抗战的物质力量,以满足战时军事和民用的基本需要,作出了积极贡献,并使国民政府实施统制经济政策得到了有力的支撑。
3.国家资本企业的全方位扩张
战时国家资本企业的扩张,除了上述以资源委员会为主体的国有企业在重工业、基础工业领域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外,还表现在战时其它政府机构或者独资建立国家资本企业,或者以合股、参股民营企业等形式向重工业、基础工业之外的其它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发展,从而使得国家资本企业在战时得以实现全方位的扩张。
有资料显示,除资源委员会外,战时国民政府的不少部门皆以接办、合办、创办、参股等形式,投资参与了一些工矿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战时中央其它部门下辖的工矿企业至少还有几十家之多,如交通部下属有19家,军事委员会下有3家,教育部下有2家,中央工业试验所有4家,兵工署下有24家(18)。此外,各战区经济委员会、各省政府也以各种方式投资组建工矿企业,加上国家银行也直接参与投资,这些都使战时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在工矿企业中的比重迅速上升。据1942年的统计,该年国家资本在后方工业资本总额中大约已占到69%以上(19)。在当时所有的国家资本工矿企业中,省营企业公司是除了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国家资本系统之外,最具重要意义,而且相对完整、规模较大的一个国家资本体系。这些省营企业公司大多在地方政府行政以及经济力量的主导下,采取官商合办的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经营着本省地域内各种重要的工、商、农、金融、贸易事业,无论是近代中国企业制度的演进形态上,还是在维系战时统制经济的作用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以著名的贵州企业公司为例,该公司在战时先后创办的企事业单位共计多达42家,其中自办单位12家,合办单位有14家,参与投资单位16家。所办企业涉及机械制造、煤矿开采、电力工业、公路运输、化学工业、水泥工业、制糖业、机制面粉、火柴工业、丝织业、陶瓷业等40多个主要行业(20)。到1942年,据经济部省营公司监理委员会的统计,这一中国抗战以来的新兴企业组织或筹备机构已经遍设于贵州、云南、四川、西康、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陕西、甘肃、宁夏、山西、山东及安徽等16省区,超出全国省份的半数以上,并且逐渐居于各省省营经济事业的中心。其中资本最多者1亿元,最少的也有 500万元,一般多在则在3000~5000万元之间,合计资本高达3亿元以上(21)。到1942年底已建和筹建的各省省政府经营的工厂总数已经达到141个;各战区经济委员会经营的已建和筹建的工厂也达到了50家之多(22)。 如果说,战时资源委员会经营的工矿企业主要集中于重工业和基本工业领域,那么省营工业企业以及各战区经济委员会经营企业的大批出现,使得国家资本在重工业之外的其它工业领域也获得了显著的扩张(23)。
战时国家资本企业的全方位扩张还体现在战时国家资本在交通运输、商业外贸等方面显著发展上。在交通运输方面,国民政府持续加大了对国有铁路、公路、邮电、航政的投资和经营力度,赶筑了包括滇缅路、滇越路、桂越路、甘新路和中印路等多条国际和省际的交通要道,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其它一些铁路支线和公路线。据统计,战时国民政府投资修建的铁路共达1900公里,修建公路14331公里,改善公路108246公里,超过战前全国公路里程的13.3%(24)。战时国有交通运输的发展对打破日军的封锁和维持对外联系,及其军队调动和物资输送起到了巨大作用。商业外贸方面,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负责统一主管全国内外贸易,为了切实实施商贸统制,贸易委员会下设富华贸易、复兴、中国茶叶和世界贸易四家国有商业企业,这四家国家资本的商业企业成为实际负责经营内外贸易的业务机构,不仅垄断了茶叶、猪鬃、生丝、皮毛等重要土特产以及桐油的统购、经销业务,而且还统制着全国相关的主要出口贸易。战时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统制”,从财政金融到工业建设,从物资管理到进出口贸易,国民政府正是利用和依靠了国家资本以及国家资本企业的迅速扩张,才得以使统制经济政策在战时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战前已经形成的金融统制和国家资本金融体系的建立,实际上已经为战时国民政府全方位推行统制经济政策和建立国家资本体系作了重要的铺垫和准备;而战前为加强国防建设开始着手计划、建设的国家资本企业,到战时一一逐步落实,在此基础上迅速扩大、发展起来的国家资本企业,不仅使国家资本企业在大后方的重要基础工业、重工业领域形成为战时后方经济的重要支柱性产业,同时在此之外,国家资本体系也逐渐得以向其它工业领域和经济领域延伸和强化。尽管在战时的条件下,发展国有资本企业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加强和实施统制经济,为了战时经济的现实需要,从这点出发,发展国家资本企业无疑有其充分的理由和历史必然性;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我们也可以认为,正是由于抗战时期严峻的战时条件的存在和现实的形势需求,才使得国民政府有可能在国家陷入残酷的全面战争的历史条件下,以战时的需求为充分理由,将国家资本和国家资本企业推到了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
三、战时统制经济政策与国家资本企业的互动作用
1.统制经济政策为国家资本企业发展提供契机与支持
国家进入战时状态后,国家经济政策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保障战备。经济政策的内容决定着经济活动的内容,以国防建设为核心的统制经济政策,决定了国家资本体系在战时的重要地位,作为支撑统制经济政策实施的实体,国家资本企业发展为施行统制经济政策和建立国防经济提供了基本保证。战时国家资本企业发展是以统制经济政策为前提,反过来又成为统制经济政策实施的强有力依托,这种互动作用在战时国家资本工矿企业中反映最为明显。
抗战爆发促使国民经济转入战时,国民政府以统制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干预和控制,使得国民政府对国家资本的依赖增加,以保证庞大的军事消耗和国计民生,由此也为国家资本企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契机。
首先,国民政府的统制经济政策以及依据该政策而颁行的一系列有关法令、法规等等,为战时国家资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据,使得国家资本企业无论是在在重工业、基础工业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还是在其它工业行业和经济领域的全方位扩张都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其次是统制经济政策下国家资金的实质性支持。国民政府对国家资本企业发展最实际、最有力的支持当推国民政府在国家预算资金分配,以及国家行局的有关放贷款上,对国家资本企业的明显倾斜。无论是国库拨款还是四行的投资、贷款等等,都是促使国家资本企业在重工业、基础工业领域迅速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因素。以战时对资源委员会的资金投入为例。战时国民政府对资源委员会资金上的支持,仍然沿袭战前的做法,一为财政总预算的拨款,据统计,从1936~ 1945年度,资源委员会历年从国库得到的库拨资金高达法币117亿元。其中电力、煤炭、钢铁、机械行业居投资额的前四位,所获资金都在总投资额的10%~20%以上(25);二为对外易货和对外借款获得的利润和外汇的投入,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同苏联签订了5次易货合同,金额高达3.06亿美元,向美国4次借款共达1.7亿元美元,其中大部分由资源委员会以其所统制产销贸易的钨、锡、锑等特种金属产品进行偿还,少部分由前述国家资本控制的贸易公司以所统制的猪鬃、茶叶、桐油等农产品偿还,这些易货贸易所取得的利润以及外汇借款基本上都被用于国家资本企业的经营和扩张。1936~1943年,资源委员会由“钨锑盈余项”下投资企业的专款至少就达到3356万元(26)。三为国家银行的贷款,一般来说,资源委员会众多企业的建厂开办经费多由国家拨款,但企业建成以后的营运资金很大程度上需要国家银行的贷款支持,在这方面,四联总处以及下属的国家行局所给予的贷款支持是十分重要的。在1941年之前,.四联总处核放的贷款总额中,国有企业所获的贷款额要高于民营企业。1940年,经四联总处核准贷放给资源委员会的借款总额高达5495万元,其它公营工矿业1145万元;而同时期民营工矿业得到的贷款总额仅为2524万元(27)。
2.国家资本企业发展为战时统制经济政策实施提供条件与保障
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东南沿海大片国土沦陷以后,西南、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迅速上升,国民政府在动员大批东部沿海地区工业企业内迁的同时,开始着手投资国家资本工矿企业,以建立新的经济中心。这个意向到1939年1月,更以国民党决议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今长江南北各省既多数沦为战区,则今后长期抗战之坚持不懈,必有赖于西南、西北各省之迅速开发,以为支持抗战之后方。”(28)以主要负责国营工矿业的资源委员会为例,其所属的大多数企业都属于基本工业,投资大,见效慢,技术难度高,许多都是当时的私人资本难办或不愿意办的事业。但资源委员会在战前资源调查的基础上,除了对煤、铁、钨、锑、组、汞、金等矿产资源进行继续调查和开发外,还开发了铝土、磷、锰、铬等一批新矿藏,为西部地区重工业的建立提供了原料、动力等主要物质条件;根据煤铁产量和品质以及运输等条件,在川、滇大量投资兴建冶金工业基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钢铁需求的紧张状况;大力创立内地电力工业基础,以国家资本电力企业提供工业用电,努力发展水力发电,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西部工业开发的需要。对战时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政策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抗战期间,由于西部地区重工业的长足发展,使战前那种轻重工业比例的状况有很大改变,在工业企业总数中重工业上升到35%、资本上更上升到50%以上(尚不包括军工企业)。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基础,重工业以国营为原则,已形成全国上下的一致共识,在国民政府政策倾斜的前提下,国家资本工业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据经济部统计,战前在全国工业资本中国家资本只占11%左右, 到1942年国家资本已占到国民政府实际控制区工业资本的69%以上,国家资本企业无论在资本、动力设备、人工多寡诸方面较之于民营企业都占有很明显的优势(29)。从企业种类上看,虽然国家资本企业和私人资本企业各有所强,前者在冶炼、水电、机械、电器、化学等重要的国防工业行业占有绝对优势,后者则主要在木材建筑,服饰品、饮食,文化、杂项等轻工业中占优势,但由于重工业决定着整个工业的发展水准,同时又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家资本企业在基本工业、重工业领域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足以说明其在维持战时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
国家资本企业与私人资本企业类别比较表
企业类别国企% 私企% 企业类别国企%私企% 企业类别 国企% 私企%
水电工业89 11木材及建筑工业 4 96土石品工业49 51
冶炼工业90 10化学工业饮食品工业 75 25服饰品工业8 92
机器制造工业73 27纺织工业23 77文化工业 16 84
电器制造工业89 1149 51杂项工业 6 94
资料来源;经济部统计处编《后方工业概况统计》1942年度,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藏资料, A074《关于论述中国事业建设报刊资料(1936~1947)》。
当然,战时西部地区新工业基地的形成,是在国家资本企业同私人资本企业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其中私人资本企业在这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抗战初期东部地区大批工厂内迁,到战时民用工业的发展,这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从战时的舆论一直到现在学术界的研究,始终有部分人认为,战时国家资本企业不如私人资本企业效率高。实际上,诚如当时就有人所指出的,“国营民营事业各有短长,不能一概而论”(30),“有些国营事业比民营事业效率高,有些民营事业比国营事业效率高;某些部门国营事业比民营事业强,某些部门民营事业比国营事业好”(31)。这样的评价似乎比较客观、公允。国家资本企业和私人资本企业的经营效率以及各自的经济贡献,如果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资料比较,似乎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如以各自在工业行业中的地位比较,可以看出国家资本企业基本占据了重工业、基础工业的主要部分;如从企业的生产成本比较,以酒精工业的单位成本为例,国家资本酒精厂最高为104.45元,最低为95.09元,平均为102.87元;而私人资本酒精厂最高为142.68元,最低为122.10元,平均为131.50元(32)。显然,国家资本企业的平均成本要明显低于私营企业;再有就是企业的经营环境和条件,在战时的情况下,一般说来,国家资本企业多为国防所需,必须服从政府的有关计划,并不完全以赢利为目的,同时又有国民政府资金上的保证,所以即便处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其经营条件应该说总要优于民营企业。也正因为这些,战时国家资本企业在整个后方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其产值从1940年的15.2%上升到了1944年的35.9%(33)。从而成为国民政府实行经济统制政策最重要的基础性保障。
3.战时统制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资本企业发挥的具体作用
统制经济政策实施范围包括从生产到流通,涉及工、农、商、交运、金融物价等各方面,出于持久抗战的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企业来控制重要物资的产销环节,用以保证实施统制经济政策,是国民政府抗战时期自始至终坚持的原则。为此,国民政府在工矿领域以发展重工业、基础工业为基本方针,大力扶持国家资本企业,建立起以资源委员会为主体的国家资本工矿体系,这一点前文中已有论述。而在内外贸易领域,国民政府以“统购统销”和“专卖制度”为基本方针,设立了各种专营企业和统制机构,如专办农产品贸易的复兴、富华公司;专办茶叶销售的中国茶叶公司;收购棉产品的花纱布管制局;专管工业品产销钢铁管理委员会的、燃料管理委员会、液体燃料委员会,以及采金局、水泥管理委员会、各种特种矿产管理处等等,更是以国家资本企业的直接经营来实现政府的统制经济政策。可以说,国民政府在实施统制经济政策过程中,在积极扶持国家资本企业的同时,也得到了国家资本企业经营效益的支持,反过来,国家资本企业在获得国民政府扶植的同时,既要接受统治经济政策的规范,同时又要为统治经济政策的施行发挥具体作用,这在资源委员会特种矿经营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国民政府对特种矿的统制从战前已经开始,早在1935年资源委员会成立之时,即被授权“通盘整理国内钨锑矿业”,国民政府明确表示:以外国借款关系,极力增进出口矿产品的生产;以为偿债和易货之用其对特种矿产进行统制,不得不加强钨、锑、锡、汞之统制及产运工作,以供出口(34)。为此,资源委员会首先成立了江西钨业管理处、湖南锑业管理处对钨、锑施行统制。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之时,资源委员会对特种矿的统制还只仅限于上述两项。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了《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之后,钨、锑、锡、汞等14种金属及其制成品都被列入统制管理范围,钨、锑、锡、汞各矿产品的收购运销皆由资源委员会执行。这样,资源委员会在国民政府授权下,先后成立了生产、管理有色金属的相关处、厂、矿共24个单位,而国民政府通过资源委员会对特矿的统制,也随之扩大到锡、汞、铋、铜、钼等多种矿产,其统制方式从统一收购、组织运销,到建立厂、矿直接生产;从抵押、易货换取信贷和物资,到开拓内销市场,资源委员会对特矿的统制,几乎完全垄断了特种矿产品的全部生产、运输和销售,为国民政府掌控战时出口贸易、偿还债款,换取外汇、增加财力,从整体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资源委员会也通过对于特种矿的生产、销售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并以此用于扩大再生产。1939年2月,国民政府根据资源委员会请求制定《钨锑专款处理办法》,明确规定将该外汇提成20%作为资源委员会运营经费。据此一项,资源委员抗战八年中共获利4910万元,约为战前币值632万元(35),同时《钨锑专款处理办法》又明确规定钨、锑统制盈余,除了分拨各省用于各省经济建设外,全数留作资源委员会所办的国防重工业之用。据此规定,资源委员会仅1936年7月到1939年3月,即盈余840万元。有学者认为,1936~1945年间,资源委员会通过经营特矿和易货偿债等方式得到的外汇收入,折合成战前法币大约有1.8亿元之巨(36)。资源委员会也正是由于有了包括特矿专款这样稳定的资金来源,才得以在总体资金供应匮乏的战时条件下,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甚具规模的国家资本企业集团,并由此而奠定大后方重工业、基础工业的基础。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战时统制经济政策实行的直接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障战备。施行统制经济政策的目的就在于加强战时国民政府对物资、人力的控制,增强抗战的物质力量以满足军需、民用和保障战备。而实现这一目的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对现有物资的合理分配和创造更丰富的物资。在战时特定经济条件下,要对有限的物资进行合理分配就必须动用强制手段,要迅速有效地生产新的物资,只有依靠国家力量发展国有资本,因此,对物资实行统制和管制以及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企业,就成为国民政府战时经济政策两大最重要的核心内容。
2、发展国家资本企业是国民政府落实和强化统制经济政策的重要举措。一般而言,实行统制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受战争状况驱使而采取的不得已选择,也是战争状况下所能选择的最佳战时经济政策。“加强战时经济体制的基本政策”,可以说就是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基本定义。作为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经济体制,它至少包括三大方面的内容:这就为,一是以法律、法规、纲领、条例等构成的政策内容;二是设立各种的管理机构,具体实施各种管制政策;三是建立起支撑政策施行的经济实体,即国家资本企业。所以,战时统制经济政策首先表现为对财政、金融、工农业产品、进出口贸易等施行的管制措施;其次就是设立一批对应管制对象的经济机构;再次是创建国家资本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战时的经济条件下,国家资本企业实际上是扮演了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支撑统制经济政策实行的最重要的经济实体;或者说国家资本企业本身就是国家实行统制经济政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3、战时统制经济政策与国有资本企业发展互为依存。确立战时经济政策为统制经济政策,也就意味着发展国家资本企业势必成为实施这一政策的必要途径与手段,同时也意味着国家资本企业的发展必然受统制经济政策的控制与扶植。战时国家资本企业在统制经济政策下,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一发展对维持战时经济,支持持久抗战发挥了相应的作用,成为战时实施的统制经济政策诸方面中较有成效的一个方面。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施行,使有限的经济力量得以集中,从而不仅保证了战时的国防需要,也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大后方最基本经济生活,对持久抗战起了应有的作用;而战时国家资本企业,尤其是工矿业国家资本企业的发展,既保障了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实施,支持了战时经济,同时对于改变近代以来中国工矿业地缘格局以及内地工矿业的拓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果更进一步看,战时国家资本企业的扩张和发展对于当时以至战后中国的企业制度、公司制度的演进变化,对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走向都有着十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6-11-24
注释:
①参见朱英、石柏林《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伟保《实业计划与国民政府: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天工书局2001年版;徐建生《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赵兴胜《传统经验与现代理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工业研究》,齐鲁出版社2004年版;薛毅《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何长凤《抗战时期贵州股份有限公司》,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陆仰渊《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虞宝棠《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政策论析》,《史林》1995年第2期;刘殿君《评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统治》,《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何刚《抗战时期国民党战时经济政策述评》,《黄淮学刊》(社科版)第12卷第1期,1996年3月;吴王文《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政策述评》,《河南大学学报》第38卷第5期;董长芝《论抗战时期后方的国营工矿业》,《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赵兴胜《论抗战以前国民政府的国营工业》,《文史哲》2001第 2期;张殿兴《论抗战时期的资源委员会》,《历史教学》2001年第10期;彭世畦《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控制全国经济的努力和国家资本的发展》,《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虞和平《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早期现代化建设——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现代化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郑会欣《试析战时贸易统制实施的阶段及其特点》,《民国档案》2005年第3期;郑会欣《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1期等。
②参见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
③参见虞和平《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早期现代化建设——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现代化研究》第2辑。
④郑友揆等:《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⑤这些计划虽然大多数要到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才真正开始实施,但所执行的方案却基本上都是战前就确定的。
⑥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著:《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2集,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1984年印行,第416页。
⑦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76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151页。
⑧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9、614页。
⑨周开庆:《经济问题资料汇编》,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版,第52页。
(11)谭熙鸿:《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18页。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经济部所属单位档案,转引自董长芝《论抗战时期后方的国营工矿业》。
(13)张忠民、朱婷《略论南京政府抗战前的国有经济政策(1927~1937)》,《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
(14)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68~869页。
(15)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藏资料,A074——关于论述中国事业建设报刊资料(1936-1947)。
(16)资源委员会编:《工业概况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八(2)957。
(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四/34914-1。
(18)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916-939页;章伯锋、庄建平主编:《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抗日战争》第五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4-445页。
(19)章伯锋、庄建平主编:《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抗日战争》第5卷),第25页。
(20)参见何长风编著《抗战时期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言,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21)杨及玄:《省营公司发展声中的川康兴业公司》,《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4期;彭湖:《论省营企业》,载《贵州企业公司成立三周年纪念特刊》。除了省营的企业公司之外,据1944年2月22日赣南《民国日报》所载,在蒋经国管辖下的江西赣南第四专员区,各县都设有“企业公司”,这些公司在行政业务上受蒋经国的管辖。参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773页。
(22)《省营事业监理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四/34741。
(23)关于诸如贵州企业公司等投资设立的企业的行业分布可参见张忠民《略论抗战时期内地省区企业公司的制度特征》,《上海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24)吴申元:《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147、156页。
(25)《资源委员会历年库拨资金总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八(2)415-1。
(26)《资源委员会投资数目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二八(2)415-1。
(27) 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45-446页。
(28)李生平:《烽火映方舟——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广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29)国家资本企业与私人资本企业相比,前者资本平均每单位200万元,后者每单位尚不足20万元;前者每单位有100匹马力,后者则每单位只有30匹马力,前者每单位可达200余人,后者仅有50余人。
(30)《关于工业建设的几个问题》,《资源委员会公报》第10卷第1、2期合刊。
(31)《中国工业建设之途径》,《资源委员会公报》第5卷第4期。
(32)《中国战时酒精工业之研究》,《资源委员会季刊》第5卷第1期。
(33)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140页。
(34)《战时经济法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2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35)许涤新、吴承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4页。
(36) 参见张燕萍《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特矿统制述评》,《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标签:国民政府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重工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银行资本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贸易金融论文; 经济学论文; 银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