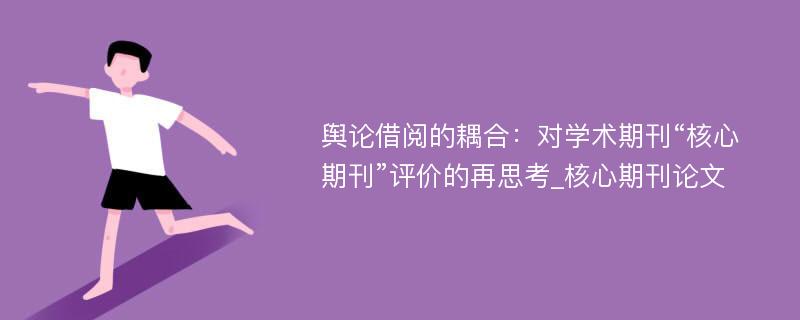
耦合舆借鑒:“核心期刊”之於學術評價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核心期刊论文,舆借鑒论文,於學術評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圖分類號]G3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6)01-0108-08 截至目前,對於“核心期刊”與學術評價問題的論爭,已基本告一段落。這個受到學(科研)者、期刊出版(管理)者、科研管理者等群體廣泛關注的社會話題探討,尤其是對“核心期刊”僭越學術成果評價功用的清算,己基本釐清了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這兩個不同問題的混亂糾葛關係。但是,“核心期刊”與學術評價並非不相關,而且有著很多直接的目標耦合因素。大數據時代,如何合理借鑒並利用好“核心期刊”這個檢索工具,更好地輔助於科學的科研成果評價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一、關於“核心期刊”之於學術評價問題的研討述評 (一)我國引入並研製“核心期刊”之主要成果 “核心期刊”理論是個舶來品。“核心期刊”起源於英國文獻學家布拉德福(S.C.Bradford)於1934年提出的“文獻離散定律”。後經美國情報學家普賴斯(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尤金·加菲爾德(E.Garfield)等人的研究,特別是在加菲爾德於20世紀中後期創造性地系統提出了引文分析理論後,美國科學情報所(ISI)分別於1963年、1973年、1978年研製了《科學引文索引》(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藝術和人文科學引文索引》(A&HCI)三大檢索工具。發展到現在,國際上知名的引文索引數據庫有:SCI、EI(工程索引)、ISTP(科技會議錄索引)三大科技文獻檢索系統和SSCI、A&HCI、ISSHP(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會議錄索引)三大人文社會科學索引庫。 據錢榮貴考證,我國傳媒首次提及了“核心期刊”問題的開篇之作,是1973年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創刊的《國外書訊》中“世界重點科技期刊”一文。當時,國外學術期刊價格飛漲,如何用有限的經費採購到有價值的外刊,成爲介紹者的直接目的。①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始,我國對“核心期刊”的研究逐漸升溫,研究機構紛紛建立。但從國內正式的系統公開出版、發佈“核心期刊”研製成果情況看,可能最早見於1992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即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文核心期刊”(由北京地區高等院校圖書館期刊工作研究會和北京大學圖書館聯合研究課題成果)。 1996年,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推出了我國第一個自然科學領域的引文數據庫——“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光盤版,收錄了國內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582種,即“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來源期刊”。 1999年,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中心推出了我國第一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引文數據庫——“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1998版),收錄了來源期刊496種,即南京大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 另外,1997年起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中國科技論文統計源期刊”(又稱“中國科技核心期刊”)、2004年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2009年起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的《中國學術期刊評價研究報告:RCCSE權威、核心期刊排行榜與指南》、2012年起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的“複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期刊等等,也相繼正式公開出版或對外發佈。 (二)我國關於“核心期刊”應用之濫觴 客觀地看,“核心期刊”②這個舶來品一開始並沒有引起學界、期刊界、科研考核管理部門的普遍重視。一是國內對此較陌生,需要一個熟悉、認知的過程;二是國內科研考核尚不偏重量化指標,③學術期刊的地位或評價尚處於由歷史形成的行政級別或同行認可的階段。但是,大約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我國論文數量和期刊數量的迅猛增長,④以及各種“核心期刊”表的誕生和傳播,對處於“苦海”困境中的科研評價管理者而言,這個基於引文量化數據基礎上的“核心期刊”表猶如一副靈丹妙藥,成爲“核心期刊”之評價功用濫觴的主要推手。因爲它有如下“優點”: 1.科研考核工作簡單化。論文數量的激增,客觀上增加了科研考核的操作難度和成本。有了“核心期刊”這個範圍界定,無疑簡便易行、客觀公平。這一點無需贅述。 2.“核心期刊”標準貌似公正公平公開。科研成果的評價是一件涉及評價目的、評價主體、評價客體、評價方法、評價程序、評價結果等複雜因素的價值判斷過程,同行評議應當是評價全過程的主角。但同行評議也非萬能,對有些領域科研成果評價標準不易把握,比如社會科學領域裡創新性強、很超前的成果,或者是人文學科領域裡那些具體化、個別化的研究成果,或者交叉學科領域裡的研究成果,評價結論有時出現失誤或爭議。而用數據考量則用貌似客觀的標準,剛性地解决了許多主觀判斷解釋不清楚的“質疑”和分歧。 3.人們更認同量化評價。在沒有“核心期刊”量化評價前,雖然對同行主觀評議法也有爭議,卻是科研成果評估的唯一選擇。但在學術科研和學術評價十分功利、學術規範和學術誠信嚴重缺失的環境下,一旦有了量化數據指標或標準,人們自然就拋棄了有爭議、有疑問並可能引起無窮麻煩的主觀同行評議法,轉而採用量化評價法。特別是當大多數人對“核心期刊”生成的數據、指標、計算等複雜因素不知其詳,對引文分析法的應用局限不甚瞭解的情况下,盲從心理反而使之認同度更高。例如,在很多人的文章或言論中把“核心期刊”與學術成果評價、與學術期刊評價這些問題混爲一談,把論文評價標準與“核心期刊”研製標準等同看待,就明顯在誤用或誇大“核心期刊”的功用。 4.與國際接軌。實行對外開放、加快與國際接軌,也帶來了一些負面的東西。比如在學術界湧動著的崇洋心態就十分突出。在學術評價領域,以SCI、EI、ISTP、SSCI、A&HCI爲代表的“洋”索引在一些人心目中成爲至理聖經,唯“洋”是瞻,不管學科、地域、文化差異,照抄照搬,一概拿來,與“國際標準”看齊。 (三)我國關於“核心期刊”僭越評價功能之反思清算 國內各種學術研討、大量文章集中對“核心期刊”僭越評價功用現象進行了痛徹的鞭撻。概括起來主要有: 1.(引文)數據崇拜。表現在:數據就是水平。在我國現階段各種學術評價、評選以及職稱評聘、項目評定等活動中,普遍重視數量和數據。引文數據、轉載數據,往往直接就是質量和水平的代名詞。由此導致了嚴重的後果:一是催生了剽竊、編造研究論文和假期刊產業,二是造假引用數據層出不窮,三是抑制了科研人員的創新動力,搞短、平、快的“硬產出”以提高泡沫化的學術GDP。曹衛東曾撰文指出,在量化考核體系下,學者的研究成果被量化爲一個個具體的數字,表面上看,這種方法簡單易行,是一種合理甚至公平的學術評價機制,但事實上是把複雜的智力勞動簡化爲單一的機器生產,抹殺了個人創造潛能的多樣性。⑤ 2.“核心期刊”崇拜。表現在:(1)以刊評文,唯“核心期刊”論英雄。我國大多數教學科研單位都規定了不同職稱級別晉升與聘期考核、博士畢業要發表的“核心期刊”論文數量。大到考評一個單位的業績或競爭力,小到考評個人的職稱、科研、項目與結項等等,都要看在“核心期刊”上的發文數量。錢榮貴尖銳指出,有些單位“六親不認”,只認“核心期刊”,且輔之以重獎,這樣一來,許多人做學問、寫文章的終極目標似乎就是在所謂的“核心期刊”上發文章,至於科學研究的根本目的、文章的價值作用己無暇顧及。⑥(2)極度推崇所謂國外“索引來源期刊”。在國內“核心期刊”之學術評價功用大肆泛濫的情况下,一些大學和科研單位逐漸不滿足於中文“核心期刊”的數量和聲譽,開始不分領域、不分學科、不顧歷史文化背景,甚至弄虛作假,或花費大量金錢,⑦狂熱追求在SCI、EI、ISTP、SSCI、A&HCI等索引來源期刊(國際會議論文集)上發表論文的數量,以其多寡作爲單位和個人評價的最高標準。 值得警惕的是,推崇國外“索引來源期刊”,不僅使我國學術資源外流嚴重,而且助長了學術泡沫的國際化傳播,影響了我國的國際形象,負面效用越來越明顯。有學者更爲隱憂地指出,這些國外引文索引數據庫基本上是以西方英文期刊作爲統計來源刊的,在人文社科領域,其選擇來源刊的旨趣顯然具有地域、文化、歷史、民族甚至意識形態色彩。而且,近些年這些商業化的引文索引數據庫還逐漸形成了資源壟斷霸權,收取我國用戶高額的使用費且不容談判。爲保持其壟斷稀缺性,還對我國學術期刊的加入設置了很高的門檻和收取不菲的系統使用費。 二、關於“核心期刊”與學術評價關係的再思考 在人們對“核心期刊”越位或出位學術評價功能情況幾乎一邊倒地進行清算時,卻鮮有從“核心期刊”與學術期刊評價、與學術成果評價的正相關關係角度進行分析研究。理性分析看,“核心期刊”之於學術成果評價功用的濫觴,既有客觀需求的外力推動,也與“核心期刊”和學術評價之間存在目標耦合直接相關,非常需要學界深入開展分析,也需要學術評價活動合理借鑒。 (一)“核心期刊”與學術成果評價 “核心期刊”與學術成果評價是兩個主客體迥異、內涵不同的領域。各種“核心(引文索引來源)期刊”表,只是引文索引數據庫功能的很小一部分,引文索引數據庫的主要功能是文獻信息的查詢。因此,“核心期刊”的目標定位就決定了它不能成爲學術成果評價的標準,更不能簡單地“以刊評文”。 但也必須認識到:表面上看,各種“核心(引文索引來源)期刊”表研製的對象是刊物,實際上是在研究論文的質量屬性表徵。“核心(引文索引來源)期刊”研製的目的,是從海量的期刊中找出那些水平與質量較好、在所涉及的學科或專業中的地位與作用處於“核心”位置的學術期刊。由於各種“核心(引文索引來源)期刊”表研製的具體方法、側重領域、來源數據、指標體系權重等等的不同,導致結論有差異,但其理論依據和基本方法是相同的,即都根據學科論文構成要素的多種屬性表徵在期刊中的集散規律,採用文獻計量統計並輔之同行判斷開展研究。這些期刊和論文的屬性表徵體現在統計指標上有:載文量、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即年指數、他引率、被引半衰期、學科影響指數、均被引、地區分佈率、基金論文比、WEB即年下載率等,以及各種大量衍生指標如“五年影響因子”、“剔除自引的影響因子”、“網絡影響因子”等。這些指標都是從不同側面反映論文對期刊的影響力。 而且,不少人誤以爲“核心期刊”研究只關注引文數量,根據筆者的觀察,國外的“核心期刊”研究一直在從“量→質”演進:發文數量→引文數量→引文質量(論文影響因子、論文被哪些刊被誰引用、影響分值等)。演進階段大致如下: 第一階段:1930—1940年代英國圖書館學家布拉德福的文獻集中與分散規律(簡稱布氏定律),加上1950年代普賴斯的文獻增長與老化規律(曲線、指數),以發文數量爲中心構建“核心期刊”評選理論框架。 第二階段:1960—1990年代加菲爾德創建引文分析理論體系(簡稱引文集中定律),以文獻或期刊“被引頻次”(引文數)爲指導、以“影響因子”爲核心指標,構建“核心期刊”綜合評價體系。我國後來引進並發展的各種“核心期刊”研究都遵循了這個體系。 期刊或學術文獻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形式是內容的外在表現。在西方成熟的學術研究、評價、出版的環境裡,一般情况下,國外的“核心期刊”研究儘管有具體指標應用上的爭議,但基本達至了以下共識:“核心期刊”評選=學術期刊評價≈期刊學術質量評價≌學術論文質量評價。在我國,由於歷史文化、國情現實等差異,“核心期刊”的研究成果在應用層面上出現了變異,從而遭致了普遍的批評。但是,這並不能否定“核心期刊”研究本身的科學性。恰恰相反,借鑒、改造、吸收的過程,必然經歷這種水土不服的階段。 “核心期刊”對於學術成果評價的參考價值體現在: 1.耦合現象客觀存在。至目前,一些研究側重在批判“核心(引文索引來源)期刊”之功用被濫用、被放大而“誘導”的科研成果量化評價的弊端方面,沒有認真客觀地分析“核心(引文索引來源)期刊”與學術成果評價結論之間的耦合現象。比如,“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的作者影響力、論文質量水平普遍較高;引用率高的論文大多數是那些有創新突破的科研成果,或權威機構、權威學者研究發佈的成果;“核心期刊”上的論文被引用量(率)普遍高於一般期刊等等。這些耦合現象不是偶然的個別存在,而是比較規律性的普遍存在,那麼,其中必然存在內在的邏輯關聯性。“核心期刊”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要探索這種關聯性的規律,界定其關聯的條件、內涵及使用範圍,從而更加完善其科學體系,發揮文獻計量學意義上的評價功能。 2.科研成果評價有合理借鑒“核心期刊”的經驗。科研考核管理部門轉向“核心期刊”的路徑依賴,並非毫無依據。我們在大加批駁科研量化評價的惡果並將之歸罪於“核心(引文索引來源)期刊”時,不能走向極端,應充分認識引文索引在立體展現文獻之間的引證關係,顯示科研成果之間、刊載文獻的期刊之間以及文獻所屬學科之間的內在聯繫方面的價值。只要我們不將“核心(引文索引來源)期刊”上的論文與學術價值完全等同、不將高引用與高水平等同、不將影響力與創新力等同、不將來源期刊收錄標準與科研評價標準等同,那麼,就完全可以科學合理地發揮引文索引在學術評價中的輔助作用。從實際情況看,由於大的社會環境沒有變化,以創新和質量爲導向的科研評價制度的建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科學的成果評價體系和成熟的學術規範、學風環境、學術共同體⑧建設也非一日之功,所以,即使現在一些單位意識到“核心期刊”的問題所在,力圖以代表作制度、同行評議取而代之,但在具體操作時仍然借用“核心期刊”表做參考。這種現象並非國內獨有,即使在西方一些發達國家也大量存在。 (二)“核心期刊”與學術期刊評價 “核心(引文索引來源)期刊”與學術期刊質量評價有共同的研究對象,在某些指標體系設置上有著共同的價值取向,即都是在某種評價目的支配下的學術期刊排序。前者主要是從期刊論文文本的相關信息中統計分析匯總結果,後者主要是從包括期刊的政治、學術、編輯、出版等內外質量整體評估後得出結果。因此,合理利用引文、轉載等數據,對全面評價一本學術期刊,有非常好的參考價值。 1.基本閾值的價值——可以爲學術期刊質量評價簡化程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如何對論文質量進行評價是最核心的爭議點。因爲大家都明白:整體不代表個體,一本總體質量水平高的期刊,不代表其每篇論文的質量水平都高,而且只要有部分高被引的論文,或有引文過度、引文造假情况,同樣可以拉升數值使其入列“核心(引文索引來源)期刊”表。同時,文獻的相互引用是一個複雜的思維過程,作爲其表現形式的引用文獻,只能反映某種影響力,而影響力不等於高質量。因此,評價期刊主要靠同行綜合評議,尤其是在對期刊內容質量進行評價時。但是,也應當承認,對每篇論文直至每本刊物進行全樣本同行評價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既不可能更無必要。“核心”就是相關聯事物的中心。無論是人文社科還是自然科學成果,根據大量文獻數據的統計分析,支撑“核心(引文索引來源)期刊”的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被引半衰期、基金論文比、二次文獻轉載等指標,是有其科學合理性的,凡是列入“核心(引文索引來源)期刊”表的,總體質量水平較高是顯而易見的。也就是說,當統計量達到一定閾值時,學者對論文或期刊學術影響力的共識性判斷(或學術聚焦效應)就顯示出來。這就是那些同行評審、編委會制度等審稿制度嚴格、學術質量高的期刊,進入“核心期刊”的概率高的原因,也是科研人員普遍認爲在“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門檻高、難度大的根本原因。名刊工程、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的評選等就利用了這個閾值。 2.引文索引的價值——可以在被引量(率)、影響因子、被摘量等客觀量化指標上提供學術期刊質量評價的正相關數據 比如,被引文量(率)指標從學科寬度、知識擴散程度反映該論文或期刊的質量、重要性和學術影響,與其內在質量存在著強正向的關聯。影響因子這個指標其實也是一種同行評議,其與論文質量的正相關關係主要是通過前期的專家審稿價值來實現的。大量的研究和實踐已經確認了這種一般規律性的有效性,尤其是對學術期刊的評價。再比如,被摘量也是典型的同行評議,也與論文質量正相關。像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編輯出版的報刊複印資料系列,共有100多種刊物,從全部公開發表的報刊文獻中,按一套完整的評選標準和流程,精選優質文獻。中國人民大學學術成果評價研究中心根據這個全樣本、全學科覆蓋的評選論文數據,研製並發佈了“複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期刊表,就是學術期刊評價有價值的參考工具。 爲了克服指標體系的缺陷,“核心期刊”評選指標一直在不斷完善中,如期刊歷史影響因子(考慮了辦刊時間、載文量)、對重要文獻或期刊的影響因子加權後再評價(考慮了引用源的權重)、學科篇均被引率(考慮了冷熱學科差異化)、引用集體偏好、期刊偏好、地域偏好(數據驗證)等等。像互引、自引、僞引、負引等人爲不端干擾因素也在不斷降低。美國、西班牙、澳大利亞的學者還借鑒Google搜索引擎的PageRank算法(通過網頁鏈接的複雜計算,衡量網頁重要性和質量的搜索結果排序,並取得了成功),對“文獻引用”具有類似“網頁鏈接”效應問題分析,提出了新的期刊評價理論。例如,2009年湯森路透科技集團選擇與華盛頓大學“文獻計量研究項目組”合作,宣佈了期刊引用報告(JCR)新增兩個評價指標:“特徵因子值”(這個指標兼顧了引文的數量與質量、剔除了自引,突破了學科限制,可以跨學科比較)和“論文影響分值”(對來自聲望高的期刊和作者的引用賦予更高的權重),⑨就大大豐富了“核心期刊”評價指標體系。 當然,對個體(單篇論文、單個期刊)而言,也會出現評價結果偏差,甚至低於“同類引用中位數”,而這恰恰是需要同行評議根據評價的目的予以彌補的地方。特別是人文社科領域,發揮同行評議的主體作用時,重點要對引證內容、引證價值、引證效用的審查,從而發揮相互補充、對比、印證的效果。 關於利用影響因子開展學術評價一直就存在著爭論。加菲爾德總結了對影響因子各種彼此對立觀點的看法後指出:“影響因子不是衡量文章質量的理想工具,但目前沒有比它更好的工具……經驗表明,在各個學科領域,最好的期刊是那些投稿最難被接受、發表的期刊,而這些期刊也是影響因子最高的期刊,這些最好的期刊在影響因子這個概念被提出來之前就存在了很長時間。作爲一種測度質量的方法,影響因子得到了廣泛的使用,因爲其測度的結果很好地符合我們對每個領域最好的專業期刊的看法。”⑩ 3.學科分類的價值——可以爲期刊同類比較、分類評價提供參考 如何開展分類評價是當前所有期刊評價體系中難以解决的問題。有比較才會有評價,只有同類比較、分類評價才有價值。我國學術期刊的專業化程度不高,綜合性或是跨學科類期刊很多,無論是自然科學期刊還是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在領域、門類、學科、專業側重等等方面,都有差異,即使是一些看似分類清楚的專業刊物,因其刊登文章的專業方向偏好,在同類期刊中也往往難以比較評價。因此,目前我國開展學術期刊評價只能大致分類。在期刊分類方面,國內幾乎所有的“核心(引文索引來源)期刊”表都在這方面做了努力,力求分類科學。當然,在目前的研製中,對一些分類模糊的期刊,往往根據期刊論文學科歸屬和引文集聚比例高低確定歸屬類別,那是不得己而爲之。總之,學術期刊評價借鑒“核心期刊”研製的分類經驗和數據,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4.歷史參考的價值——可以爲期刊評價提供歷史發展軌跡的數據參考 大數據時代,數據書寫著歷史、見證著歷史。一本學術期刊要成爲“核心(引文索引來源)期刊”,至少需要三年以上的文獻計量數據。這些數據的統計分析,是一本期刊的歷史發展和學術積澱的客觀反映,是歷史上引用者對該刊在同類文獻或期刊中的認同程度,這本身就是一種評價。一些期刊辦了多年,引用率、影響因子都很低,除非個案,常規性判斷其質量水平不會很高。而且,在“核心期刊”表研製過程中,大都有同行評議的環節,會對數據反映的結果偏差予以審查和糾正。因此,評價一本學術期刊,使用其引文、轉載數據應當是非常好的歷史佐證資料。 三、關於“核心期刊”與學術評價的未來發展 截至目前,還沒有發現一種普遍適用的、完美的學術評價的理論方法和指標體系,這是一個世界級的難題。因此弄清楚“核心期刊”與學術評價這兩者的複雜關係,有利於解決中國“核心期刊”之於學術評價的“囚徒困境”,而且會有力推動學術評價方法理論的創新。 理想的評價體系是根據不同的評價目的,運用同行評議(主體)+各種計量分析法(引文分析法、文摘法等)=複合多屬性評價法(如有學者提出的指標體系加權匯總法、層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灰色關聯評價法等等)。有學者推崇同行評議制度,在當前我認爲過於理想主義了。因爲,同行評議也存在著固有的不可控缺陷,人的問題有時比數據的問題更難把握。評議人的價值偏好、學術修養、學識水平、科學範式乃至人際關係和利害衝突等都會影響評議結果。而且,同行評議一樣可能阻礙科學創新,科學權威壓制新發現、貶低新成果、阻礙科學新人也不乏典型事例。在我國還沒有成熟的學術共同體和普遍認可的學術評價體系情况下,同行評議存在的諸多爭議不是短時期能解決的。同行評議制度的形成、發展、完善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 從應用角度看,在當前,學術評價尤其是從海量級數據中對學術成果、學術期刊進行評價,利用各種“核心期刊”評價體系是比較實際可行的選擇之一。加菲爾德說:“一個更好的評價系統實際上要涉及從質量上審讀每篇文章的問題,但是,這意味著又要進行一次同行評議式的判斷,這是非常困難的……即使可以這樣審讀,這些審讀者的判斷也還要依賴於同行的評論和分析引用情況,我們稱之爲‘引文上下文分析’。幸運的是,網上新的全文庫使這樣的分析具有了更多的實踐機會。”(11) 因此,對於“核心期刊”與學術評價關係的未來發展,筆者認爲: 1.學術成果評價的方法、手段會越來越豐富和多樣化,使用“核心期刊”等引文檢索數據工具進行科研成果評價的情況會越來越普遍。因爲伴隨著學術成果出版的網絡化、數字化、專業化,文獻計量學的精細化比較與類比數據挖掘,將爲學術成果評價提供無限可能的利用工具。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科學技術進步的日新月異,學術成果的數字化記錄,爲檢索、統計、分析、鑒定等創造了過去人力手段所不能及的條件。自然科學不少領域的研究成果,由於其可複製、可驗證、可視化等,廣泛應用技術化手段進行評價是可行的。社會科學領域研究,在一些史料梳理、空白發現、真僞比驗、資料累積等方面的評估,也有很大的應用空間。 2.學術期刊評價工作利用“核心期刊”等文獻計量學成果將越來越科學化。未來,期刊作爲學術成果的載體不管是紙介質還是數字形態,甚至其他任何形式的存在,只要不是唯一,就會有同類比較,就會有“文獻離散規律”,就會有“核心載體或平臺”。而“核心期刊”的研究也正在從粗放到精細、從量到質逐漸接近學術期刊評價的核心內容。“核心期刊”各種指標的聚合效應,各種要素的顯示度,都會爲同行評議提供更加可靠的參考數值。 3.文獻計量學意義上的“核心期刊”研究與學術成果評價研究不會分道揚鑣,而會相伴而生、共進共融,且在大數據時代會越來越緊密。這是由於科學研究在向專業深度和綜合交叉方向發展,對成果的評價難度在增加,除了依靠歷史發展、實踐驗證手段外,文獻計量學意義上的文獻分析,既能提供研究借鑒的歷史基礎,也能提供檢驗創新程度的比較手段。對同處於一個學術生態體而言,這是不可缺少的“咖啡伴侶”。 4.學術生態環境越來越良好,“核心期刊”之於學術成果評價的消極因素逐漸減少。科研評價是指揮棒,引導著學術規範、學風道德、學術創新等一系列學術生態環境的建設。這其中,學術期刊既是參與者也是評判者。這些年,我國正大力建設以創新和質量爲導向的科研評價體系,學術生態逐漸回歸理性,學術成果的規範性大大加強,學術道德監督也在網絡環境下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學術期刊的專業化定位也越來越明晰,這將爲“核心期刊”數據的科學性提供重要基礎。從一些發達國家的情況看,學術生態越是良好,“核心期刊”之於學術評價的作用越大。因此,我們有理由期待,在學界、學術期刊出版、科研考核管理、文獻計量研究、學術評價研究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核心期刊”研究將會對我國學術評價的理性和實踐發揮更大的作用。 ①參見錢榮貴:《核心期刊與學術評價》,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0頁。 ②爲便於論證,本文所涉“核心期刊”概念,在有關量化指標評價意羲上,遵從大多數人的認知,將其與各種“引文索引來源期刊”概念等同。有關這兩個概念的區別,請參見朱劍:《“來源期刊”、“核心期刊”不能誤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2月23日。 ③本文所涉科研考核指標的“量化”概念時,即指發文數量,也指論文被引用量。 ④參見高自龍:《原罪與救贖:我國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現象”評析》,武漢:《江漢論壇》,2009年第2期。 ⑤參見曹衛東:《量化崇拜“難產”學術大師》,北京:《人民論壇》,2006年第21期。 ⑥參見曹建文:《學術評價不能簡單量化》,北京:《光明日報》,2006年11月20日。 ⑦參見斯科特·埃德蒙茲等:《中國必須重新調整學術激勵機制以遏制科研欺詐》,香港:《南華早報》,2015年4月7日。 ⑧學術共同體這一概念是20世紀英國哲學家布朗提出來的,他在一篇題爲《科學的自治》的文章中,首次使用了“學術共同體”這個概念。他把全社會從事科學研究的科學家作爲一個具有共同信念、共同價值、共同規範的社會群體稱之爲學術共同體。這些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價值取向、文化生活、內在精神和具有特殊專業技能的人,爲了共同的價值理念或興趣目標,並且遵循一定的行爲規範而搆成了一個個不同領域的群體。中國的學術共同體建設之路還很漫長,不僅面對“去行政化”難題,更需要學人們自醒、自信、自覺。 ⑨參見趙丹群:《學術期刊評價理論的演變分析》,北京:《情報資料工作》,2013年第2期。 ⑩(11)Eugene Garfield,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http://garfield.library.upenn.edu/papers/jifchicago2005.pdf。标签:核心期刊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