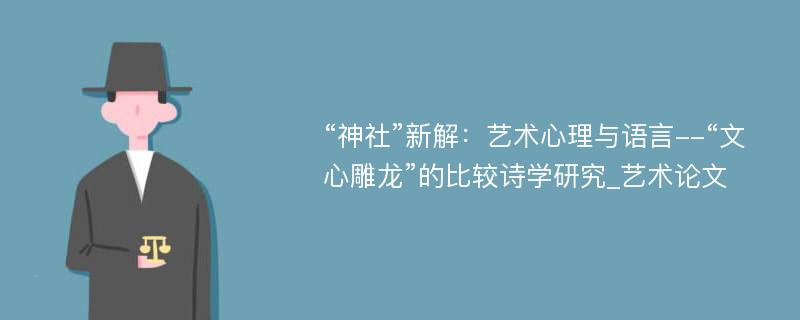
“神思”新释:艺术心理与语言——《文心雕龙》的比较诗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诗学论文,神思论文,语言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1—4403(2000)02—0071—08
《文心雕龙·神思》篇中的神思概念早已引起当代学者的广泛关注,一般认为《神思》篇是创作论的总纲,它所提出的神思概念也是刘勰艺术思维特征的概括。这种认识对于识别神思概念当然有一定意义。但是关于神思所昭示的艺术思维的内涵和基本特征是什么却很有商榷的余地。目前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这样的,认为“其为形象思维的特点,已成为比较普遍的认识。‘神与物游’四字,刘勰谓为‘思理’之妙,就十分简要地概括了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1](p43)。神思的基本特征是不是“神与物游”,笔者认为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这个问题的意义其实不仅是对一个概念的辨析,而且涉及到中国诗学中艺术思维本质的观念,甚至会涉及到其他一些文学理论和比较诗学的相关问题。因此有必要进行辨析。
笔者认为,《神思》篇虽然出现于千载之前,但它已经系统地将艺术构思过程与思维特征的阐释结合起来,说明了艺术形象性如何与语言符号结合并且在艺术作品中得以展现,这就使得它与当代西方的言辞美学形成一种超时空的对应。但它同时依然保持了自己从孔子诗学中得来的独特的、中国传统的言辞美学特点。
一、语言与神思:言为枢机
《神思》开头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话,它是刘勰神思论的第一层中心观念,开宗明义,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神思研究的基础。“神与物游”被认为是神思论的核心,也是出于此。因此我们从这里探索神思的奥秘是最合适的。这段话如下: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
首先值得讨论的这段话的中心是说什么,是以什么作为主要论点的。笔者认为这段话中有四个主要概念,分别是:神、物、志气和言辞。这四者其实是不同层次的排列,其中神是主体心理的统称,物是客体世界的合名,当然不是指客体本身,而只是客体对于主体所产生的感觉经验,也就是所谓“物象”。这可以说是明确的,没有争论的。但这两者只是处于心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实践活动的基本概念,它只说明主体以意识去把握客体映象。神与物游不是艺术创造的秘密,只是思维活动的一般规律即“思理之妙”。在刘勰之前,已有《乐记》中的物感说,“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而后心术形焉”[2](卷三十八)。这里所称的“心术”也是指的人类思维活动, 而乐即艺术只是“感物”之后的部分,即“形于声”的部分。刘勰所说的“思理”与“物感说”的“心术”相同,不是专指艺术思维本身,只是泛指艺术思维的基础,人类的思维与意识活动。而刘勰所说的艺术思维活动并不是指这种思维,他的艺术思维论是指第二个层次——志气和言辞——这是艺术思维而不是一般的思维和意识。志气和言辞的思维形式是在前者即思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性质又与前者不同的思维。所以刘勰更为重视艺术思维,把它与一般的思维形式区分开来:“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显然在艺术思维中,志气与言辞的作用就更为重要了,刘勰是用“关键”和“枢机”来形象地说明它们的。所以说把神思的主要特征看作是神与物游,恰恰是没有能把一般的思维活动与艺术思维活动区分开来,具体地说,就是错误地把“神思”与“思理”混同了。这种错误看法在当代比较文学理论和比较诗学研究中普遍存在,有的人就认为:
心理感应问题因而成为人们的想象心理活动基本的、核心的问题,也是艺术想象基本核心的问题。[3](P482)
不同的意识活动应当有不同的核心观念,艺术思维作为思维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必然有自己的对象和活动方式,也必然有独特的核心问题,从形式逻辑角度来看,这种认识的错误是明显的。“神与物游”说只能作为一般思维活动形式的特征,而《神思》篇的中心是说明艺术思维的特征,所以不能把“神与物游”作为它的中心。如果那样,等于把刘勰艺术思维理论的贡献抹煞了。
明确上面一层意思后,再进一步看以上几个概念之间的联系,问题将会更加清楚。刘勰把“神”与“志气”,“物”与“言辞”分别对举,从两对概念的转化过程说明了神思的发生和作用,其中发人深思的是后一对概念的搭配,刘勰在此为什么要把“物”的概念转化为言辞?原因就在于,刘勰认为,客体世界即所谓的“物”与人的主体意识——神——之间首先产生感应作用,作用的过程中,物的表现形式——“物貌”、“物色”这些物象通过人的感觉器官传达到人的高级意识,产生相应的心理经验和印象,此即所谓“物无貌隐”,“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等状况,这只是艺术思维的第一步,这时主体所具有的只是视觉和听觉等感觉器官接受外部事物刺激后所产生的“意象”。当然它并不只是客体的产物,而是主客体之间互相作用的产物,是心物同一或心物融合。但无可否认它与文学作品的性质是不同的,主要的不同在于,文学作品是语言的构成,而它尚未形成语言的表达。
所以刘勰在论述神思时指出,它的枢机在于辞令也就是语言,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说明物象,如果不借助于辞令,那么物象甚至不可能被“神”所接纳,因为“物沿耳目”,就是说物象只是人的感觉器官的反应和经验,如果要达到“物无貌隐”,使事物的全貌及其本质被认识,必须通过辞令——语言。以语言作为艺术思维活动的主导力量,借助于语言的介质,事物才能成为思维活动的具体因素。如果没有语言,将会枢机不通,事物的形象无法传达,也就是说艺术思维不能形成。这是刘勰神思论的精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神与物游”论的分歧是明显的。
二、艺术思维的发生:“规矩虚位,刻镂无形”
在阐明神思的主旨后,刘勰从思维的发生过程进一步阐明艺术思维的特性,他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或说是三个境界:第一个是神思方运,即艺术思维的开端,其表现为“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第二个阶段是写作过程,经历了“气倍辞前”,然后是篇成后的“半折心始”。第三才是经过写作实践后,总结规律,探讨艺术思维与人类语言实践的关系即言与意之间的联系,相当于当代理论中思维与符号的关系。总之,不论哪一阶段,刘勰都是以言辞为中心来进行考察的,把语言看作人的意识现实化,并且从语言艺术的角度来研究它。
艺术思维的发生被刘勰描述为“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前人多从虚构与想象的角度来理解它,比如牟世金先生早已肯定它是讲“凭虚构象”的,而且指出:“‘规矩’二句显然来自《文赋》的‘课虚无于责有,叩寂寞而求者’,也正是讲从无中求有(从无到有)的形象虚构”[4](P43)。这一观点的提出对于“龙学”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对此前人已多有评价,我们不多述。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与从黄侃以来的一些重要理论家的说法一样,仍有不足之处,就是没有能注意到《文心雕龙》的艺术思维理论与陆机《文赋》中的“从无到有”的说法虽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这种不同正是刘勰的发展所在。区别在于刘勰主张一种艺术思维的语言发生理论,他把语言的“规矩”与“刻镂”作为艺术思维的发生过程。我们首先要辨明的是此处的“规矩”与“刻镂”的本义是什么。前人对此的注意是不够的,周振甫《文心雕今译》等书中,都没有把这两个词另作注释,只是作了“孕育内容”与“刻镂形象”的一般译解。[5] 但我们注意到钱钟书曾经借陆机《文赋》来讨论“规矩”的含义。
“虽离方而遁员,期穷形而画相。”按李善注:“言文章在有方圆规矩也”;何焯评:“二句盖亦张融所谓‘文无定体,以有体为常’也。”……张融意谓文有惯体而无定体,何评尚膜隔一重。[6](P1193)
这里的“规矩”被理解为文体,笔者赞同这种见解并且认为它适用于《神思》篇中“规矩”一词。但仍要再加探讨才能明确其意义,《荀子·赋篇》中“圆者中规,方者中矩”,本义是指法度。《文赋》中借用于指文体,刘勰的“规矩”显然胎息于陆机《文赋》中“方圆”,用以指为文法度,具体就是文体。如《征圣》篇中“文成规矩”就是旁证。这个用法后世已经多次袭用,并且成为文体与语言相关联的用法,韩愈所说的“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等也就是类似用法[7](卷十二),明显把文体与言语合一。如果要说无中生有, 那么这种生有的过程是语言的发生过程,也就是钱钟书所说的“思之思之,无中生有。寂里出音。言语道穷而忽通,心行路绝而顿转”。这个“有”的产生是与语言思维相伴的,它正是语言本体的产物。我们再来看“刻镂”一词,《荀子·劝学》篇中“金石可镂”,这里的“镂”当然是指雕刻而言。中国古代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都是以雕刻为主,以后的竹简也离不开雕刻。正像阮元所说:“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之节策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之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8](卷二)。所以刻镂一词其实成了文字、 语言和文体的代名词。扬子《法言》中所说“童子雕虫篆刻”指的就是作赋,许慎《说文解字序》曰“秦书有八体……三曰刻符,四曰虫书”。用刻符和虫书来代替作赋说到底也是修辞的需要,是一种推类和隐喻的用法,相同的用法可以反用,《汉书·景帝纪》就云“雕文刻镂,伤农事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显然就是反其意而用的,用雕文刻镂专指为文之事了。
再看《文心雕龙》,其中多次用“刻镂”来泛指文字语言文体:
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原道》)
镂影离文,声理有烂。(《颂赞》)
虽纤意曲变,非可镂言语,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声律》)
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丽辞》)
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神思》)
从以上用法中可以看出,刻镂从规矩、文体的意义出发,向语言、言辞作多重意义转换,但它的所指是明确的。基于以上理解,我们可以对“规矩虚位,刻镂无形”作出新的解释。它的意思是说,在艺术构思之初,文体只是空的规则,言辞尚未完全形成。这样,刘勰的艺术构思理论与前人学说的不同之处就明显表现出来,它是以语言文体的形成作为自己的艺术想象或构思的标志的,在艺术思维活动中,语言起到中枢和机关的作用。那么,前人对于刘勰的“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所作的解释也就明显不符合刘勰本意了。刘勰并不主张“凭虚构象”式的无中生有虚构,他的艺术构思论与言辞美学密切相关。具体地说,它描绘了在艺术构思过程中,以语言为主导的思维发生的必然性。在构思之初,各种思维纷纷涌现,起到主导作用的文体和语言在这一过程中作用极为重要,是它们作为中枢,安排思绪,组织结构。从万途竞萌之中,转向以文学文体与语言来谋篇结构。
问题在于,刘勰艺术思维中的这一观念的提出有什么实际意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世界上最早地从文学言辞角度来研究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观念。它与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当代西方文化心理学中的语言思维关系讨论一样,是重要的理论学说。当代西方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讨论中,有两种不同的主要观念。一种是重视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同一性(IDENTIFICATION),认为有思维必有语言,两者是同一的。这种理论的代表大多是心理语言学家和部分反射学家,它是以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为依据的。 另一种则认为语言与思维之间是分离(DISJUNCTION)的,由于语言是外向的表达形式, 它与思维属于不同的构成体系,所以它们之间尽管可以紧密结合,但毕竟不能完全合一。由于两派之间长期争论没有结果,所以研究者们近年来把目光转向发生学领域——特别是儿童思维与语言、原始人类的思维与语特征的研究,以期有所发现。在这个领域里,第二种观念即语言思维分离论者们的发现对于人们启示较大,其中以皮亚杰和卡西列最为突出。皮亚杰提出儿童所特有的是自我中心思维,这是从无意识的我向思考向代表了社会意识的定向意识的过渡,它代表的是主客体之间的没有完全分化的状态。[8](P23)皮亚杰指出它的特点就在于:
定向思考是有意识的……而且它可以通过语言进行交流。我向思考则是下意识(SUBCONSCIOUS)的,也即它所追求的目标和它所解决的问题本身不存在于意识之中。它不适应外部现实,但却为其自身创造了一种想象或梦幻的现实。它并不倾向于去确立一些事实,而是意欲去满足愿望,保持严格的个体化,而且借助语言的手段无法进行交流,这是因为它主要采取意象(IMAGES)形式进行操作(OPERATION), 正因为这样, 为了进行交流, 它必须求助于兜圈子说话的方式, 通过象征(SYMBOLS)和虚构的手法,以激起我向思考的感情[9](P12)。
很明显皮亚杰所说的这种我向思考与通常的艺术思维十分相似,以形象和象征为手段是艺术思维的主要特征。卡西列则从另一角度研究了相关问题,他认为象征性行为是人类的基本特征,象征就是符号,语言只是象征的一种形式,在人类社会早期语言尚未形成之前,已经存在着神话的思维形式,这种思维形式也是以形象和象征为主要特征的。
皮亚杰与卡西列其实是相通的,他们强调思维与语言的非同一性,语言不是唯一的思维形式,他们分别从语言与思维的发生学角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他们还提出在先于语言的思维中,象征和形象的思维是主要形式之一。但是,笔者认为,他们在这里也有一个错误,就是把语言思维与非语言思维对立起来看待,他们在批判语言思维同一论时,也把这一分歧夸大为绝对性的了。笔者认为,在这一点上刘勰是比他们高明的,因为语言是人类最主要的符号象征系统,如果要说形象思维,那么也是先从语言开始的。而且从人类文明角度来看,语言作用最为重要,刘勰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正是一语道破其中奥秘。人类的高级意识必产生于语言,这也正是黑格尔一直不承认神话和艺术是思维意识的原因(注:可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2—65页,他认为神话和艺术属于“感觉、直观、表象的意识”形式,而不把它们作为思维的意识形式。)。因此如何说明从形象向语言的高级意识转化就成为研究非语言意识的关键,正像杰出的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所说:
思维与语言关系不是一件事情而是一个过程,是从思维到言语和从言语到思维的连续往复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经历了变化,这些变化本身在功能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发展。思维不仅用言语来表达;思维是通过言语才开始产生并存在的。[10](P126)
在他看来,思维(指初级的形象象征形式)在转化为语言时,并不像人加上一件外衣,思维在转化为语言时产生变化,并且有了自己的现实形式。
刘勰《神思》篇中语言思维发生论的意义正在于此,从艺术思维的开始,他便强调语言的作用,它表现为虚位的规矩和无形的镂刻,虽然不在形式上存在,但它已经作用于作者的思维,使思维从形象向语言的表达转化。在这种转化中思维自身也在丰富和发展,它从最初的物象形式“神与物游”提高到言辞形式,由隐而显,进入高级思维形式。这就是刘勰理论的特色,他认为思维与语言形式之间没有对立,思维从开始就与语言处于相互融合的关系,思维发生之际语言就已在暗中推动和制约它的发展,直到语言和思维反复往返,思维用语言获得存在的感性形式(马克思说语言是感性的也是精神的);语言由思维成为精神的形态。可以说,刘勰的神思论正是从艺术思维这个特殊的角度阐释了自己的语言思维观念,反过来,这种观念也说明了他的艺术思维观是有哲学基础的。
三、语言与意识——两点新解释
分析了艺术思维的发生原理之后,刘勰对于它的结果作出进一步的研究,他认为,艺术作品的构思与作品形式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即所谓“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作品永远不能与作者的初衷相合,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刘勰认为这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是个别作家的才能高低的原因。关键在于思维与语言的统一关系中同时也存在不同的因素。按照中国学术的传统,他把思维与语言具体化为三种因素:思—意—言,也就是再对意识进行划分,成为思维与意念两个成分,它们都与语言发生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其间的关联。
首先在于意念与语言之间有各自的特性,这是思维与语言之间产生有分有合关系的根本原因。刘勰把它们的各自特性描述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意念变幻多端,而语言受制于多种因素,所以不易随意念而变化。如果比较刘勰说法与传统的“言不尽意”之说,其间的区别已经十分明显。刘勰的“意”作为主体意识的目的是强调其自由活动状态,它的恣意想象。而语言的征实特性则是说明,语言并不是完全服从于个人的。从其本质来说,语言是有指向自我的一面,语言是个人的,它有自我意识在其中。但同时,语言符号系统是社会性的,是作为与个性主体相对的社会文化的产物,也是他人的。正如马克思所说:
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1](P34)
刘勰所说的“言征实”就含有对于语言符号的社会性的肯定,《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就已经肯定了言辞的社会作用,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刘勰用《易经》的名言来总括自己的观念:“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他这般推崇言的社会作用,思想根源在于孔子的德言说,孔子在春秋时期的思想变革中,把传统的道的观念进行改革,使它从精神的观念向实践的道德转化,反对那种道不可道,不可言传的思想。孔子说“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他使言成为道与德的实现,成为人间礼乐制度的代表。笔者已经多次指出,刘勰的言辞美学思想植根于孔子的文言说,原因即在于此[12](PP82—87)。无论如何,刘勰这里对于思维和语言之间关系的分析,为言意之辨,为“言不尽意”这个古老命题增添了一种新的解释,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其次,刘勰注意到思、意、言之间的授受关系,“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且由此也产生了彼此之间的互相契合与不合的两种关系。“密则无际,疏在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这种情况与《神思》篇开头所说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艺术想象其实完全不同,有人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是不妥的。更多的人则不明白刘勰为什么要提出这种授受疏离关系。
笔者认为,刘勰的这一观念与《神思》全篇的意义是相联系的。它仍然是对于艺术思维中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论述,只有从这一角度理解,才能解释刘勰为什么要提出这一观念。它的目的在于揭示人的意识不能完全控制写作过程中语言活动,从而展示思维与语言关系中另一侧面。虽然在写作中人的思想可以产生意象和意念,并且把它们外化为语言。但实际上这一过程中,并不总是“密则无际”的,相反,有时会产生主体思维不能掌握语言的状况,这是主体思维的无意识状态,它只能与前语言的零碎符号相通。 维果斯基曾经提出过“内部语言”(INNERSPEECH或ENDOPHASE),这是一种介于思维符号与社会语言之间的符号,它的词意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因素的作用,他说:
内部语言并不是外部语言的内在方面——它本身是一种功能。它仍然是一种言语,也就是说,与词语相联结的思维……它是一种变态的、不稳定的东西,在词和思维之间波动着,而词和思维或多或少是稳定的,或多或少描绘了言语思维的组成部分。[10](P163)
内部语言的不稳定性反映在思维与语言、意与言之间,可能使它们密合无间,也可能使它们疏远千里。内部语言的存在本身就说明,思维与语言之间毕竟是有间隙的,它们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同一。以维果斯基的说法,这种差别就是由于在我们的言语中,始终存在着隐蔽的思维,即“潜台词”。
另一位西方文艺理论家苏姗·朗格早就得出了相近的结论,她解释了潜台词产生的哲学与心理学原因。根据卡西列的符号哲学原理,她认为,语言与神话本质上没有区别而且有历史联系,语言把抽象和虚构结合在一起,在最初的感性激发和命名中,创造了符号,它结合了感知、记忆、思考,同时也为想象创造了符号的实体。这就是说,符号既有指称的功能,又有想象虚构的功能。也就是说梦和无意识都可以用符号的形式来表现。这便是符号的非理性表达。它有三种主要形式:一,可描述性的表现,即弗洛伊德所谓“可描述性”(DARSTELLBARKETTC)。这种作用是把经验的材料呈现为情感和性质,这是理性所办不到的,也是语言所无法完成的。它增加了语言的丰富性,也必然给了它使用中的歧义。二,逻辑上的“超限定性”(OVER DETERMINATION),也就是用同一种形式表达多种含义,可以使相反的、矛盾的情感用同一形式。最终可使艺术作品表达相矛盾的情感。例如钱钟书先生以《诗经·关雎》篇说明同一道理,同是一个“风”字,却可以表达多种意义。《关雎·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正义》曰:“……《尚书》之三风十愆,疾病也;诗人以四始六义,救药也。”所以风它可以有相反的意义,他认为“风字可以双关风谣与风教两义,《正义》所谓病与药,盖背出分训同时合训也”[13](P58)。 这种“背出分训同时合训”的语言,其实有其心理学的基础,无意识中的反逻辑的、非理性性质决定了这种符号的存在。当我们感到自己的语言与所表达的意义相去千里时,也可能正是这种符号的非理性内容起了作用。三,凝聚原则,这是弗洛伊德关于梦的运作原则之一,也是符号的非理性运作机制,它与移位一起,可以加强所创造的意象,使人感悟到情感的复杂性。
我们还可以从法国当代理论家拉康的学说中发现这一观念的存在,他进一步用后现代主义观念来说明符号与思维的不统一性。索绪尔把语言的本质规定为“差异”,拉康认为语言与符号是一样的。语言替代实物也就成为了一个替代品,这个替代的过程是与现实的分裂,分裂与差异是一样的。儿童出生以后,首先经历的是非语言的、非符号的世界,名为想象级(IMAGINARY ORDER),在这个世界中, 没有外界事物与符号。在进一步的心理发展中,儿童进入“符号级”(SYMBOLIC ORDER),这时儿童幻想中的世界被语言的世界分裂了。这种分裂表现为:一是自我的分裂,主体自身的意识被分裂;另一方面则是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分裂。符号与所指的现实之间永远得不到固定,不断从一个能指向另一个能指追求。由于拉康把符号与心理结合起来,心理的愿望和追求被他说成是语言符号特别是能指的追逐,人的思维活动从意识到无意识也永远不能与语言达到统一。
从维果斯基、苏珊·朗格直到拉康,他们的学说不同,对于思维与语言关系的看法也不同。但在思维与语言的疏离与结合问题,他们之间可以说是有密切关联的。刘勰的神思论虽然在时代上要早于他们,所涉及的问题却有相近的性质。我们通过对于神思论的思维特性、发生过程和主要内容方面的审视,可以得出简单的结论:刘勰的神思论建立在他系统的言辞美学基础上,艺术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是他探讨的核心问题。他认为象征与形象的发生恰是与语言密切相关的,艺术思维形成中,言辞居于枢机的地位。神思论并不是凭空虚构的想象论,在理论形态上,它发展了陆机以来的中国艺术思维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符号思维融合与疏离的辩证关系理论。这种理论形态与当代西方的语言心理和艺术思维理论是相同的。令人为之扼腕的是,西方学者的贡献早已被我们所熟知,而刘勰的语言与心理研究却埋没千载,现在确实到了让它与西方理论交相辉映的时候了。
收稿日期:1999—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