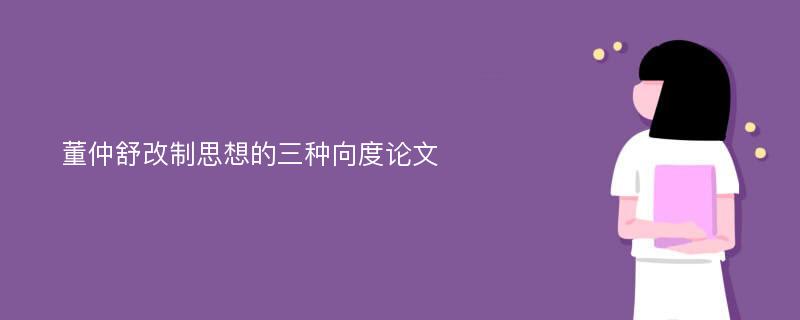
董仲舒改制思想的三种向度
黄 波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武汉430074)
摘要: 董仲舒讨论“改制”,既有理论层面的建构,又有经世角度的构想。具体说来,其改制思想具有三种向度:一是基于天人哲学中的王者受命观念而构建的新王改制说;二是对春秋经传展开创造性诠释所建立的孔子改制说;三是面对西汉早期的社会状况而提出的以更化为中心的汉代改制说。这三种向度具有紧密的关联。首先,新王改制说为孔子改制说建立了理论基础。其次,新王改制说和孔子改制说,一者以天的权威性,一者以孔子的权威性,在理论层面共同表明汉王朝革新更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关键词: 董仲舒;改制;素王;孔子;更化
改制是春秋公羊学的重要议题之一,清末经学家皮锡瑞称其为《春秋》经所蕴涵的精要“微言”①,近贤冯友兰以之为春秋公羊学的“基本精神”[1]。从公羊学史的角度讲,改制初由孔子“制义”②,后《公羊传》略有阐发,至董仲舒才使其显明,首次明确提出“改制”二字,并将“改制”之义旨应用于议政实践中,此后经《春秋纬》《白虎通》及何休《公羊解诂》等汉代著作之承继和解释,改制终成公羊经学的关键义理。
在公羊改制义的演进中,董仲舒的理论构建和经义抉发具有决定性的推进作用。目前,论者探讨董仲舒的改制思想,多将散见于《春秋繁露》各处的相关文字集中并笼统地加以解说,而没有注意到董仲舒在阐解改制思想时所具有的层次之分。概言之,董仲舒的改制理论具有三个向度:一是天人哲学层面的新王改制说;二是经典解释层面的孔子改制说;三是政治实践层面的汉代改制说。其中孔子改制说以新王改制说为义理前提,汉代改制说又以新王改制说及孔子改制说为理论基础,三者环环相扣,紧密关联。
一、新王改制说
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董仲舒论及“奉天法古”的公羊义理,其中涉及“法古”与“改制”的关系问题。
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为辞,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闻,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春秋繁露·楚庄王》,参照清苏舆义证本,下引仅注篇名)
《春秋》经义既强调“善复古”以“法先王”,又要求“王者必改制”,这在表面看来是相互抵牾的,故“自僻者”有质疑之语。针对问难,董仲舒对“王者必改制”详加解释,提出新王改制说。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已,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楚庄王》)
(一)“新王”之涵义
“改制”作为一项政治活动,其实践主体是“新王”。董仲舒对“新王”涵义之界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将玻璃纤维滤筒装入采样管内,采样管出口连接两个冲击式吸收瓶,将采样管由采样孔插入烟道中,使采样嘴置于测点上,正对气流,按颗粒物等速采样原理抽取一定量的气体。采样结束后将滤筒和吸收液进行处理并用离子色谱测出硫酸雾的量,除以抽取的气体量,计算出硫酸雾浓度。一般情况下吸收瓶内吸收液均检不出硫酸雾,滤筒对硫酸雾的阻留效率在99%以上[3]。
新王何以必改制?这涉及新王与天之关系问题。在董仲舒看来,新王一经受命,其与天之间便具有形同人间父子的关系。
首先是通过赢得他人信任和打造自身形象来建立自身的信誉;其次是从你和他人都看重的方面描述你的观点的好处;如果没有,那么就要用有说服力的数据、故事、观点来强化立场;最后就是要展现同理心,即了解说服对象并且与他们建立情感纽带。
其二,“新王”之正式建立需“受命于天”。“受命”是自殷周以降的传统政治观念,它强调“新王”惟有获得“天”的任命,其改朝换代的征伐行动以及新朝开创之后的统治才具备政治合法性③。
那么,“天”是如何择定并任命“新王”的呢?董仲舒指出: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将孔子以麟喻己之意加以引申,把获麟看作孔子的受命之符,这一创造性的解释使孔子的素王地位获得了来自天的确证⑪。孔子成为始受天命的素王,进而也具有了革旧立新和拨乱反正的权限,但这种权限之实践是通过制作《春秋》来达成的。
“天”对人间具有感知和主宰能力,它首先以民心之归服与否为依据来择定“新王”,再通过“受命之符”来表达任命。这一观念实则承继了《尚书》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的思想,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观。这也表明董仲舒的新王受命之说建基于天、君、民交互影响之上,并非仅涉及“天君关系”④。
(二)“新王必改制”之原因
其一,“新王”特指一个全新朝代的开创者,其形成来自“易姓更王”,而非子承父位式的“继前王而王”。
天子“事天以孝道”,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承天意及顺天志。天降祥瑞给新王,这一方面代表天对新王的认可和任命,另一方面则表明了天对旧王的否弃以及希望新王革除旧朝之政治弊端的意志。因此,新王当承顺天的这两方面意愿,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实行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等改革政策,一者以此告示天下新朝之政权受之于天,乃易姓而非继人,进而建立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二者借之展开救治旧朝之弊端的进程,恢复社会生活的活力,开创政权的新形象⑤。反之,如果新王“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能昭显天之授命以及除旧弊立新政的要求。
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为父,事天以孝道也。(《深察名号》)
简言之,改制在表面看乃是新王的“自显”行为,但其实质是在回应天的授命以及展现天的变革意志,故董仲舒称“制为应天改之”(《楚庄王》),又云:“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楚庄王》)。
就业关系到国计民生,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中国由于经济结构调整,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而旅游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缓解就业压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旅游就业中,由于旅游非正规就业对教育和技能水平的要求不高,因此在吸收城镇失业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在旅游非正规就业中,存在着一种规模较大但又经常被人们忽视的就业类型——自我就业。
对于单板受力病害,在桥面铺装厚度足够的情况下,铺设双层钢筋网片能够很好地解决横向联系不足的问题,但若受桥面铺装厚度限制,整体或部分桥面铺装只能设单层网片时,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增强梁板之间的横向联系。本方案是通过增加钢板来增强板梁之间的横向联系,在今后对类似病害维修处治时,需根据现场的具体条件确定合理、经济的方案。
(三)新王改制之进路
新王如何进行改制?这是涉及新王改制说之实践的另一重要问题。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董仲舒具体指明新王改制的实践进路。
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当十二色,历各法而正色,逆数三而复;绌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三代改制质文》)
除“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四项要求外,董仲舒指出新王改制另需遵循“逆数三而复”“顺数五而相复”“顺数四而相复”等三种历史运行规则。
根据苏舆校释⑥,“逆数三而复”,是指以改正朔为中心的黑、白、赤“三统”的循环往复;“顺数五而相复”是指按木、火、土、金、水的五行相生之序交替更始;“顺数四而相复”是指以救弊为主旨的“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三代改制质文》)的“四法”之终而复始。其中,“三统”和“四法”之内容皆指向新朝肇始之后历法、服色、刑罚以及各类礼制的变革,其目标在于立新和除弊,而基于五行学说的“顺数五而相复”则主要处理三王之前的五帝之黜进问题,其目的在于昭显天命的移变和强调历史的连续性。
董仲舒还以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变迁为实际例证进一步说明这套新王改制进路的运行状况,其云:
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名相官曰尹,作《濩》乐、制质礼以奉天。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作宫邑于丰,名相官曰宰,作《武》乐、制文礼以奉天。(《三代改制质文》)
商变夏,周代商,每一继起之新王,皆改旧朝之国号、造新宫邑、易官名、作新乐,并结合前朝的状况,按“三统”“四法”“五行”之运行次序制定新朝之“统”、规定新朝礼制之文质属性以及处理新朝之前的诸统治者的“亲”“故”“黜”“推”等历史定位问题。
2.2.3 不同体积流量对fs/i的影响 考察了不同体积流量(0.6、0.8、1.0、1.2 mL/min)对各fs/i的影响,结果(表4)朝藿定B、朝藿定A、朝藿定C、淫羊藿苷、木犀草素、槲皮素、川陈皮素、山柰酚、宝藿苷Ifs/i的RSD依次为0.86%、0.73%、0.72%、0.35%、3.68%、0.88%、1.38%、2.87%和1.14%,表明体积流量的波动对各成分fs/i无显著影响。
概言之,董仲舒认为新王之改制并非可任意进行,而是有其严格的内容规定和规则要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涉新朝礼制及政治秩序的“三统”和“四法”,这两种规则界定了历史变迁的往复运行特征,体现出董仲舒的循环史观⑦。
(四)改制与法古之关系
对于改制与法古之关系,董仲舒认为两者在实质内涵上并不矛盾。“自僻者”之所以提出疑问在于其仅“闻其名,而不知其实者”(《楚庄王》)。
对于改制,具体包括“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等内容,皆指向新王朝建立之后的革新政策,其目的在于展现天君之间的“授受之义”(《二端》)以及“天”之革旧立新的意志。
至于法古,其涵义是指效法先王之道。董仲舒云:
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楚庄王》)
先王之遗道来自“圣者法天”,主要包括“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内容,其功用在于“所由而适于治”(《汉书·董仲舒传》),其精义则是“仁义礼乐皆其具”(《汉书·董仲舒传》),这表明先王之道指向国家治理的根本价值原则,故其实践与否直接决定着政治的“治乱之分”。
从改制与法古的各自内涵看,改制之所改乃旧朝之陈制旧弊,并无“易道之实”,法古之所法乃先王之治道,而非先王之旧制,故两者并无绝然对立之处,反倒是它们皆系于天,改制之目的本为应天,法古之实质则在法天⑧,两者皆以天为最终之旨归。
综括而言,新王改制说以基于天人哲学的王者受命思想为立论根据,强调王者在新朝初创之后要按照“三统”“四法”等规则采取措施革新政治面貌,以昭显天的授命。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建构为孔子改制说和汉代改制说提供了哲学基础。
二、孔子改制说
晚清康有为曾著《孔子改制考》,以孔子“为神明,为圣王”[2],极力论证孔子据乱世而改制立法。从思想渊源讲,康氏之论实则深受董仲舒的孔子改制说之影响⑨。在春秋学史上,董仲舒首次明确提出孔子托《春秋》以改制的公羊学命题。
在对酒店管理专业进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采用角色扮演的形式,让学生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进行一定角色的扮演,在一定的场景之中来进行表演。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随天之终始,博得失之效,而考命象之为,极理以尽情性之宜,则天容遂矣。(《符瑞》)
(一)孔子为素王
孔子改制说的前提是孔子为素王。董仲舒云: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汉书·董仲舒传》)
孔子通本末之义,知晓“王者,人之始”(《王道》)的道理,故其作《春秋》,改一为元,大始而正本,欲正王以正天下。这种“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汉书·董仲舒传》)的制义思路,被董仲舒视作孔子为素王的写照和体现。
“素王”在公羊经学中是指“有德而无位”者⑩,故孔子之为素王,乃仅有王者之德而无王者之位,并不实际具有王者权力,但董仲舒指出,孔子的素王地位之获得仍来自天的授予,“西狩获麟”即为其受命之符。
“获麟”一事载于《春秋》之鲁哀公十四年: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心(公)⑫,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俞序》)
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从孔子之再言“孰为来哉”看,知其极为感惜麟出而无明王之应,而观孔子之言“吾道穷”,则知其将获麟与自己生平之运命相关联,以麟出无应且被获而死,来类比己之周游列国于七十余君而王道终不见用。
这座博物馆小巧精致,通过丰富的展品向人们展示了厕所的发展历史、厕所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及厕所技术的革新等内容。
(二)孔子托《春秋》以改制
按照“新王必改制”之要求,孔子作为新受天命的王者,必须启动革新政策以昭显天的授命。但孔子的王者身份是素王,并不能行使现实的政治权力,故董仲舒特别指明孔子是“托乎《春秋》正不正”来展现“改制之义”。
孔子怎样托《春秋》改制?这关涉孔子作《春秋》的问题。对于孔子作《春秋》之情形,董仲舒云: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餐饮企业依靠血缘、朋友等的招聘制度提拔核心岗位的做法已经不再适合,招贤纳士,任人唯贤才是重中之重,同样企业也要做好如何留住人才的功课!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西方彻底分权的划分模式中国目前不具备相应的先决条件,应在“中央决策、地方执行”的框架下推进,可考虑按照事权要素的划分,中央决策、地方执行,但是中央的决策权再进一步细分,决策可分为“做什么”和“做到什么程度”,在“做什么”权力保留在中央政府的前提下,“做到什么程度”是可给地方的自主权。同时强化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提升地方履行事权的效率和效果。
孔子“引史记、“理往事”,据鲁史旧闻作《春秋》,在行文笔削之际,加乎素王之心来评论二百四十二年之历史事件,以达成其“正是非”、“明得失”之经世目的。
从《春秋》形成过程看,孔子之改制是在历史空间中展开的,按蒋庆先生之言,孔子是“通过托鲁史作《经》的方式”[3]来展开改制的。具体来说,孔子是在编修鲁史旧闻中,通过对语词的调整来寄寓对史事的褒贬之义⑬,进而立新法,除旧制,以此展现素王的改制举措。
董仲舒还将孔子托《春秋》之改制置于朝代更替的真实历史背景中,进而提出《春秋》代周“当新王”的公羊学观点。其云:
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汉书·董仲舒传》)
又云:
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三代改制质文》)
“《春秋》当新王”,并非指董仲舒将《春秋》文本视作“新王”,而是指《春秋》乃代周而起的一代之治⑮,其本旨在于指明周德衰弊,天命转移,孔子受麟瑞之符,为继周之素王,并以作《春秋》的形式来行使王者治理天下的权限,故《春秋》即可被理解为是一个替代周朝的新朝代。从这一角度看,孔子托《春秋》之改制在实质上是“变周之制”。
(三)变周之制
考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董仲舒认为孔子改周朝之制,遵循着新王改制的“三统”和“四法”两种规则。照“三统”及“四法”之运行,周为“赤统”,且“主地法文而王”,则可推知《春秋》代周当为“黑统”,且“主天法商”⑯,以尚质为特征。《春秋》之“黑统”及“主天法商”中又各有诸多礼制规定和政策要求,据董仲舒之总结,其中可见于《春秋》经传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救文以质。礼之结构有文质之分,“文”乃外在仪式,“质”为内在心志,“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玉杯》)。至周之末期,周礼多文而少质,其实践流于形式,渐趋空泛,失礼之本。孔子忧惧周礼之衰弊,故作《春秋》力图“承周文反之质”(《十指》),如讥鲁文公以“丧取”、贤宋伯姬“凝礼而死于火”、大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善楚庄王“笃于礼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等,这类见于行事的褒或贬都体现出推重礼之质的义理倾向,皆被董仲舒看作孔子继周之弊而“救文以质”(《王道》)的举措,其要旨在于重建“贵志以反和,好诚以灭伪”(《玉杯》)的礼之精神,进而达成在周礼基础之上塑造文质本末皆备的《春秋》礼制之目的。
其二,绌夏、新周、故宋。“三统”说强调每一新统都要“具存二王之后”,以形成“通三统”的局面。如周朝新立之后,当在虞舜、夏禹、商汤之旧三统的基础上建立夏、商、周的新三统,故周之新王当“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三代改制质文》)。今《春秋》代周而立,则当新建商、周、《春秋》之新三统,故素王孔子首先应“绌夏”,再“亲周”、“故宋”,以存商、周二王之后,这在《春秋》经文中有具体表现,如杞本为夏禹之后,按周制当称杞公,但《春秋》经却书“杞伯来朝”,这即为孔子“绌夏”之辞,表明孔子将杞之爵号由公降至伯,不再视杞为王者之后;至于“亲周”,则由《春秋》宣公十六年载“夏,成周宣谢灾”来体现,按《公羊传》之解释,孔子作《春秋》,外灾不书,此处之所以记载,是为了表明孔子的“新周”之意⑰,其涵义照何休之解诂,是指“黜而新之,从为王者后记灾也”[4],即指周被孔子新黜为王者之后,故需按王者之后的标准记其灾异。对于“故宋”,则通过僖公十六年之“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文公三年之“雨螽于宋”、襄公九年之“宋火”等经文加以体现,《公羊传》认为,《春秋》之所以一再记载宋之灾异,原因在于孔子仍视宋为王者之后。董仲舒称“故宋”,旨在指明相对于新黜为王者之后的周而言,宋为旧的王者之后,因此以“故”称之,以示先后新旧之别。
其三,合伯子男为一等。按周制,爵位设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但孔子《春秋》改周之爵制,设为三等,公、侯存之,再合并伯子男为一等。《春秋》桓公十一年载“郑忽出奔卫”,《公羊传》解释云:“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忽乃郑庄公的嫡长子,为郑国的储君,桓公十一年夏五月郑庄公逝世,并于秋七月下葬。按照《春秋》的书法义例,对于因父丧而新继位的国君当贬爵称之,以示子不忍继父之位的孝道。郑国的爵位为伯爵,则贬爵一等当为子爵,故按例当称忽为“郑子”,但孔子作《春秋》却记其为“郑忽”。《公羊传》指出,《春秋》之所以称“郑忽”,原因是孔子革新周之爵制,变五等为三等,合伯、子、男为一等,因此,若仍依例称忽为“郑子”,则与称“郑伯”无别,并不能体现贬爵一等以见孝道的意旨,故孔子加以变通转而直接称名以达成贬爵的目的。在《公羊传》这一解释的基础上,董仲舒更进一步指出,《春秋》爵制为三等之原因在于孔子之改制遵循了“四法”的终而复始规则,按照“四法”的循环,《春秋》为“主天法商而王”,其礼制要求“制爵三等”(《三代改制质文》),故《春秋》为三等爵制。
总括言之,孔子改制说,是董仲舒在新王改制说的理论前提下,对《春秋》经传展开创造性诠释的结果,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将“西狩获麟”解释为孔子的受命之符,使孔子成为素王,进而具有改制的权力;其二,将《春秋》文本视作由素王孔子所立的代周而起的新朝代,从而为孔子改制提供实践依托;其三,通过对《春秋》记事书法的分析,抉发出孔子变周之制的具体状况,进而为孔子改制提供了直接例证。这三个部分相互联结共同构成孔子改制说的义理总体。
三、汉代改制说
新王改制说和孔子改制说,是董仲舒在义理层面对改制思想的建构,其现实目的在于为汉代革新建立理论依据,以推进汉代改制的历史进程。
汉代肇兴之初,朝廷政制,多沿袭秦旧,未加兴革,如萧何采摭秦法作九章律令;叔孙通定朝礼颇采秦仪而损益之,但司马迁仍称其“大抵皆袭秦故”(《史记·礼书》);张苍定历法章程,沿用秦之水德,并袭秦正十月为岁首,服色尚黑如故;在社会治理方面,实行宽简无为之治,崇尚“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史记·曹相国世家》)的原则,这造成在汉初基层社会的管理中仍大体因袭秦朝任刑令的治理方式,其间仅有政令施行的疏密缓急之别⑱,这直接导致诸多地方官员仅依照律令刑法治民,而缺失仁义礼乐的教化措施。
1.3 统计分析 应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计算NIPT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
因此,汉初士人素有呼吁改制的主张,其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者在礼制方面,如贾谊、公孙臣以及武帝继位初期的赵绾、王臧等人积极筹划汉代推德改制之事,其中贾谊、公孙臣按照邹衍五德终始说指出汉代秦当土德,宜数用五、色尚黄等;二者在治理政策方面,如陆贾、贾谊等人在分析秦政之失的基础上,提出以仁义德教取代秦之任刑罚作为革除秦政之弊进而“顺守”天下的根本措施,其中贾谊深刻揭示了“礼”“法”之关系,指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强调“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衰”(《汉书·贾谊传》),认为仁义礼乐之德教相较于法令刑罚之于民众道德的培养以及淳朴民风的养成更具根本作用。
董仲舒对汉代改制的思考,并未提及服色、正朔等礼制层面的变革⑲,而是集中在革除秦政任刑之弊以重建汉代治理模式的政策方面,这主要体现在《天人三策》中的“更化”思想上。具体言之,董仲舒从分析秦政之弊及其对汉初治理之影响入手,阐明汉代实行更化的必要性,再指出汉代更化的目标是兴德教以代替任刑罚,最后提出兴德教的具体辅助政策。
全城免费打的先锋——驿城金丰公社,土地托管1.6万亩,拥有社长36名、社员超过7200户,组建160支打药队,免费打药4.6万亩,让年迈的老农人从繁重的农活中解脱出来。
(一)汉代更化之必要性
以秦为鉴,反思秦政之失,以立救弊之策,是汉初儒者典型的议政方式。董仲舒承继其绪,其言秦政之弊云:
殷汤之后称邑,示天之变反命,故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新(亲)周⑭、故宋,乐宜亲招武,故以虞录亲,乐制宜商,合伯子男为一等。(《三代改制质文》)
从各站各月的平均风速情况看(图5),各个站点都存在同样的季节变化。平均风速最大的站点为国家气象站(58449),其各月的平均风速基本都高于其它3个站点。
“自恣苟简之治”是指任刑罚的治理政策,其主要表现及后果是:
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汉书·董仲舒传》)
不兴德教而专任刑罚之治理,造成官员“造伪饰诈,趣利无耻”,使百姓困苦,流为盗寇,终致刑杀甚众,但作奸之事不息。这种社会乱象影响深远,波及汉初之治,甚至及于武帝一朝。
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汉书·董仲舒传》)
汉继秦之后,与民休养生息,欲行善政,但终未致太平之治。董仲舒认为原因在于秦朝任刑之政的“遗毒余烈,至今未灭”,民风习俗之薄恶嚚顽既成积重难返之势,则仅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是不可根治的。
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汉书·董仲舒传》)
面对秦政之弊端,只有解而更张、变而更化才可革除其“遗毒”,进而达成善治。因此,“更化”之于西汉初期政治具有重大的必要性。
(二)汉代更化之目标
西汉政治只有变而更化才可形成善治,那么,更化具体指向何种目标呢?董仲舒在对策中分析武帝何以未获天之祥瑞时指出:
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汉书·董仲舒传》)
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认为,武帝乃至汉初诸帝尽管励精图治,但仍不成善治,未获天地之美祥,根本原因在于仅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而不兴教化,使民间基层之治理,仍因循秦制,“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故造成秦政之弊未除而“万民不正”。因此,汉代更化之具体指向是变更秦之专任刑罚的“自恣苟简之治”而归于仁义礼乐之德教。
在董仲舒看来,汉代当采取德教之治进行更化,并非凭空选择,而是具有来自天人哲学和历史经验的双重根据。
其一,在天人哲学的层面上,董仲舒以阴阳比拟刑德,再以阴阳的运行特征指出“任德不任刑”乃是天意的选择。
管理会计是指对企业当前以及未来的经济活动为考察对象,以提高企业经济管理能力为目的,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提供管理决策的科学依据。管理会计是在传统会计中分离出来的,其目的就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汉书·董仲舒传》)
天道运行,阳德阴刑,阳出以生育养长万物,阴伏于空虚之处,仅时出佐阳,这充分表明天之“任德不任刑”的意志。人间的君主是受天命而王,因此王者需“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汉书·董仲舒传》)。
需加说明的是,董仲舒也提及“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这表明阴阳之于岁功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有主次之分,阳为主而阴为次。因此,“任德教”并非指独任德教,“不任刑”也非指废弃刑罚,在这一前提下,“任德不任刑”之真义应是指一种以德教为主而以刑治为辅的治理原则。
概言之,董仲舒以天的权威性,强调“任德不任刑”的治理取向,这为汉代实行德教更化提供了来自天意的形上根据。
其二,在历史的角度上,董仲舒举出周代商的例证来表明德教之于“继乱世”的新王朝的重要意义。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汉书·董仲舒传》)
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汉书·董仲舒传》)
商代末期,纣王为政昏聩,社会紊乱,民不聊生,可称乱世。周取而代之,文、武二王以及周公戮力根除其弊,并制作礼乐以兴修教化,终致成康之隆治,且此教化之成果延及后世子孙,使周朝之国祚长及八百余年。这体现出新王在继乱世之后以德教治国之功效显著且长远,进而也表明汉继秦乱如果以德教之治替代刑令之治将符合成功的历史经验,因而具备现实合理性。
(三)汉代更化的辅助政策
董仲舒对汉代改制的思考,还包括提出推进汉代更化的辅助政策,其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兴太学以养士。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武帝虽夙寐晨兴,忧劳万民,但“未云获者”,直接原因在于“士素不厉也”⑳,进而没有形成养士求贤的制度,这导致地方官吏的素质状况不佳。
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汉书·董仲舒传》)
在董仲舒看来,地方基层的郡守县令乃“民之师帅”,若“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因此,推进汉代更化之当务之急在于养士以培养优秀的官员,而“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汉书·董仲舒传》)故董仲舒提出兴太学的建议:
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书·董仲舒传》)
简言之,兴太学之目的在于养成德才兼备的德教之官,使其在基层社会有效地实行教化,进而推进汉代更化。
其二,改革选官制度。
董仲舒不仅指出武帝朝的官员素质问题,还认为朝廷的选官制度也需加改革。
一是地方官吏的选拨问题。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认为地方长吏出自郎中、中郎,而郎中、中郎又从二千石官吏的子弟中选出,其中部分官员子弟仅以钱财鬻官,并不一定是贤者,因此,这种选官方式不能确保选贤与能,故需要改进。
二是官员的晋升问题。
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指出官员晋升之标准应在于是否称职有功,但现今则仅按“积日累久”之年资排辈晋升,这容易造成不肖者有其位,而贤能者则不得擢升的状况。
针对这两个问题,董仲舒提出两种对策,一是:“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汉书·董仲舒传》)二是:“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建议由列侯、郡守等高级官员从吏民中择其贤者,岁贡朝廷以甄优劣,并提出考察官员要以贤能为上,量材授官,录德定位。这些建议在实质上是主张选拨官员要打破“世卿世禄”的世袭体制㉑,而归之于不论门第、财富之高低多寡仅唯德才是举的考选制度,其目的在于拣选出优秀的官员以推行汉代的更化。
其三,禁止官员与民争利。
汉代初期实行无为之治,与民休息,至文景时代,经济呈繁荣态势,但社会风气却渐显败坏之状,其表现之一是出现官员“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的现象,其所造成的危害是:
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汉书·董仲舒传》)
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指出官员与民争利将使民众生计困苦,进而铤而走险、违法犯禁,终使民风薄恶,教化陵夷。因此,他主张“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并认为这不仅体现了上天之“受大者不得取小”的意志,还符合“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的太古之道,故他进一步劝谏武帝“所宜法以为制”,并呼吁王公大夫“所当循以为行”。
其四,宗孔子之术
秦朝焚书之后,强调以吏为师,民间不得挟书,自此,学术之发展遂呈凋零之势。汉兴,至惠帝四年初除挟书律,思想学术始得复兴。儒、墨、道、法、阴阳、名等学派逐渐活跃于汉代初期的学术与政治舞台。
汉初朝廷虽宗奉黄老道家思想,但并未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故文景之时,朝廷所置博士类别广泛,其中包括治儒家六经者、习刑名、术数及言五德终始者等。由此可推知,当时朝廷各级官吏之知识背景是多元且芜杂的,对于某一社会问题,他们都从自己的为学立场提出不同的对策,并互相辩论一争高下,进而形成思想竞争的氛围,这使朝廷的施政决策充满变数和不稳定性。董仲舒云: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汉书·董仲舒传》)
针对这种状况,董仲舒提出专宗孔子之术的对策。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这一被班固称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赞》)的建议,在近代以来,被诸多学者视作继秦焚书坑儒之后中国历史上主张限制思想自由而行专制政治的典型案例。但考之董仲舒的本意,他仅是从构建汉代统治的指导思想或意识形态之立场出发,主张以儒家思想为政府之“统纪”,使其成为朝廷制定各类政策的理论依据,进而顺利推进汉代的德教更化,而其所云的“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并非是指在整个社会场域内禁止其他学派之发展,而仅是指杜绝其他学派成为朝廷之指导思想的进路。[5]
四、结语
综括而言,董仲舒首先从天人哲学的学理层面构建新王改制的根据和进路,再从经典解释的层面将孔子树立为新王改制的典范,最后在议政建言的层面提出汉代改制的目标和政策。这三个方面紧密关联。首先,新王改制说为孔子改制说建立了义理基础,其后,新王改制说和孔子改制说,一者以天的权威,一者以孔子的权威,在理论层面共同说明汉王朝革新更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董仲舒所建构的改制思想,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还具有实践意义。考之汉代史实,其一,历法、服色层面的改制实现于太初元年,史称“太初改制”,《汉书·武帝纪》云:“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据钱穆先生研究,太初改制乃“误混三统五德之说于一而不能辨”[6],其具体所指乃“以正月为岁首”是以董仲舒的三统说为依据,而“色上黄,数用五”则以邹衍之五德终始说为前提。其二,救弊层面的改制则呈现为长期演变的历史过程。建元元年,罢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准奏公孙弘之为博士置弟子员并择其优秀者以补官缺的上疏。其中,公孙弘的上疏实则承续了董仲舒提出的兴太学以养士以及改革选官制度的建议,但更明确地主张官吏应自习儒学的士人中择取。“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儒林列传》)司马迁的描述表明公孙弘之上疏在长时段的实践中造就了大批儒学出身的官吏,其中包括被史书特别记载的“循吏”,他们在地方基层的行政中积极推行儒家的德教理想,“利用‘吏’的职权来推行‘师’的‘教化’”[7],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董仲舒所拟定的更化汉代政治的目标。
注释:
① 皮锡瑞云:“《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臣贼子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制立法以致太平是也。”参见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页。
② 《春秋》经中蕴涵有孔子所制之义,《孟子·离娄下》载:“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云:“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
③ 《尚书》中的天命观是中国古代早期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经典理论,具体的解释可参见张端穗:《天与人归:中国思想中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的观念》,载黄俊杰主编:《中国人的理想国》,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66—102页。
④ 萧公权先生云:“董子天人关系之理论实为天君关系之理论。”这并不符合董仲舒天人思想的真实状况。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3页。
⑤ 这实则表明新王改制具有两重目的,一者在立新,一者在除弊,此正如段熙仲先生所云:“改制盖有二义,其一以新民之耳目,以明受命,所谓‘所以神其事’也;其一则承前代之弊而不可不有以救之,此则文质之说也。”参见段熙仲:《春秋公羊传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61页。
⑥ 晚清学者苏舆对“逆数三而复”、“顺数五而相复”、“顺数四而相复”释之甚详,参见【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5—186页。
⑦ 关于董仲舒的循环史观的具体阐释,可参看陈俊华:《论董仲舒的循环史观》,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4期,1996年6月。
⑧ 邓红先生根据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所云之“道之大原出于天”,指出:“‘法古’如是法‘道’的话,也可能等于法‘天之道’,‘法古’即‘法天’了。”参见邓红编著:《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⑨ 黄开国先生指出,康有为早前并无公羊学的知识背景,其在撰写《孔子改制考》期间,存在一段研习公羊学理论的时间,《春秋董氏学》即是康有为学习春秋公羊学以及研读董子《春秋繁露》的成果。参见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78—679页。考之《春秋董氏学》,其中第五卷即专言“春秋改制”,且康有为解之甚详,故可见康氏论孔子改制实建基于董仲舒的经义抉发上。参见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0—122页。
⑩ “素王”最早见于《庄子·天道》,至汉初,贾谊《新书·过秦下》以及《淮南子·主术训》都提及“素王”,其中《淮南子·主术训》提及孔子为素王,黄开国先生认为其乃当时淮南王刘安门下的“一位治《春秋》的学者所写”,参见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王光松认为《淮南子·主术训》的提法不如董仲舒孔子素王论丰富,如没有提及孔子为素王的受命之符和改制活动。参见王光松:《汉初“孔子素王论“考》,载《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 期。
⑪ 据刘尚慈先生汇集,在公羊学史中,关于获麟还存在多种解释,如将获麟视作周亡之徵或汉兴之瑞,乃至孔子将殁之征等,参见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53页。但将获麟看作孔子受命之符,则属董仲舒所首创,其后为《春秋纬》承继,可参见徐栋梁:《论〈春秋纬〉对〈春秋繁露〉受命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载《衡水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15—19页。
⑫ 苏舆云:“王公,疑缘上而误,当作‘见王心’。”参见【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9页。
⑬ 在春秋学史中,对于孔子如何借“修辞”以“立义”这一问题,元儒赵汸的《春秋属辞》究之甚详,他认为孔子本鲁史作《春秋》,故《春秋》经中兼存“史法”与“圣人书法”,“史法”被称之为“存策书之大体”,而“圣人书法”则主要包括书与不书、变文以及特笔等三项,参见【元】赵汸:《春秋属辞》,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关于赵汸春秋学内容的具体阐释,可参见黄开国:《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成都:巴蜀书社,第1—54页。
⑭ 此处苏舆本作“亲周”,但据钟肇鹏先生考证,在《春秋繁露》的宋本、明钞本、周本、华本等中,此处为“新”字,而在王本、殿本、卢本、凌本、苏本等中则为“亲”字,相较而言,宋本、明钞本、周本、华本乃早出,故从之改为“新周”。参见钟肇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3页。
⑮ 蒋庆先生认为“《春秋》当新王”之“新王”是指《春秋》文本,并将其视作“公羊家所谓非常可怪之论”。参见蒋庆:《公羊学引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91页。这实质是泥于表面文字的解释,没有按照文本将其置于孔子改制的背景中加以理解。在孔子改制的理论脉络中,新王只能是孔子,而《春秋》则为孔子寄寓改制思想之书,董仲舒仅是将其类比为一个由孔子开创的新朝代,故称其为“新王”。正如苏舆所云:“不以秦为受命王,斯不得不归之《春秋》以当一代”,其义即是指《春秋》乃继周的一个新朝代。参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8页。
⑯ 需加说明的是,此处言《春秋》为“主天法商”,是按“四法”之运行规则推导所得。在宋本以至苏舆本的《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皆载有“春秋者主人”这一说法,其原文为:“春秋何三等?曰:故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如何理解此处所载的“春秋者主人”?有如下几种看法:一是据钟肇鹏记载,清代学者张惠言校改“人”为“天”,认为当作“春秋者主天”,这便符合“四法”的循环规则,参见钟肇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第461页。二是苏舆认为董仲舒所言之“春秋者主人”乃是一种异说,参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205页。三是钟肇鹏认为“春秋者主人”是指《春秋》兼统文质,是文质之统一,参见钟肇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第461页。四是曾振宇认为“春秋者主人”是指《春秋》遵从人道,参见曾振宇:《春秋繁露新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5页。按:董仲舒所列的“四法”及其对应朝代分别是指主天法商(舜)、主地法夏(禹)、主天法质(汤)、主地法文(文王),照此,《春秋》代周,为“主天法商”是可确定的,此处言“春秋者主人”便略嫌突兀,也无相关文字加以佐证,再加上“天”和“人”字形相近,不无出现抄录笔误的可能,故笔者认为清代学者张惠言的校正符合《三代改制质文》的整体意旨,可予采信。至于其他三种解释,是在确认“春秋者主人”无误后所作出的,不合乎《三代改制质文》的整体语境。
⑰ 《公羊传·宣公十六年》云:“成周者何?东周也。宣谢者何?宣宫之谢也。何言乎成周宣谢灾?乐器藏焉尔。成周宣谢灾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
⑱ 钱穆先生指出:“汉初之规模法度,虽全袭秦制,而政令施行之疏密缓急,则适若处于相反之两极焉。”参见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4页。
⑲ 董仲舒尽管未具体指明汉朝当定何种服色及正朔,但他在天人哲学的普遍层面上已提出新王改制当遵行的“三统”及“四法”理论,因此,在他看来,汉代若需进行礼制层面的改制,也应当按这套理论来定服色以及正朔。
⑳ “士素不厉也”是指“平日对于士人没有鼓励劝勉”,参见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两汉之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4页。
㉑ 反对官员任职的世袭体制是春秋公羊学的大义之一。《公羊传·隐公三年》提出“讥世卿”的观点,其云:“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诸侯之主也。”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00.
[2]康有为.孔子改制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2:1.
[3]蒋庆.公羊学引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145.
[4]春秋公羊传注疏[M].何休,注.徐彦,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63.
[5]余治平.独尊儒术:并不因为董仲舒——纠正一种流传广泛而久远的误解[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6]钱穆.秦汉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32.
[7]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M]//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81.
Three Aspects of Dong Zhongshu’s Thought of Reform
HUANG B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
Abstract: Dong Zhongshu’s reform thought includes both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conception.Specifically,its content has three aspects:first,the new ruler’s reform thought based on the idea that the emperor must accept the guidance of the heaven;second,Confucius’reform theory that is established through a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unqiu Scripture;and third,the Han Dynasty’s conception of reform that revolves around change in face of the social reality of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These three aspects are closely related.The new ruler’s reform thought has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fucius’reform theory;the two theories,one with the authority of the heaven and the other with the authority of Confucius,jointly illustrate the necess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reform of the Han Dynasty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Key words: Dong Zhongshu;reform;Confucius;change
中图分类号: B234.5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152(2019)02-0119-10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2.015
收稿日期: 2018-11-18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作者简介: 黄 波,男,湖北广水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汪频高
(E-mail:luckywpg@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