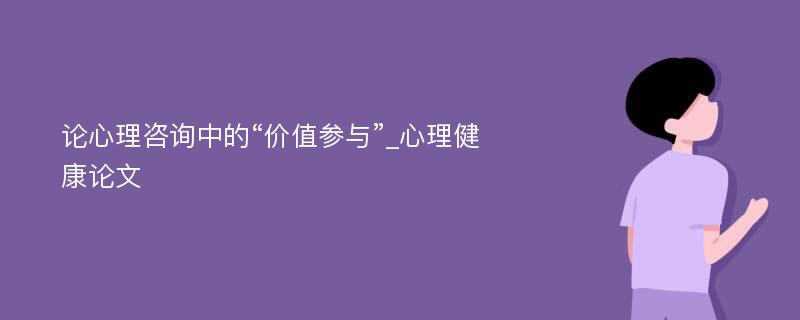
论心理辅导与咨询中的“价值参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辅导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1)04-0025-06
在心理辅导与心理咨询中,价值问题的处理始终是一个敏感而又棘手的问题。众所周知,“价值中立”原则是以人为中心学派特别是罗杰斯(Rogers)的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核心思想,在我国心理辅导与咨询专业化的过程中,曾经被许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所推崇、接受并加以应用。然而,随着实践的深入,不少辅导员(咨询员)发现,价值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完全的“价值中立”是不切实际的,也是难以真正做到的。于是,心理辅导与咨询的理论和实践都不得不重新面对这样的问题:是“价值中立”还是“价值参与”?如果我们能证明“价值参与”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那么价值又应如何参与辅导(咨询)呢?我们又如何保证价值参与的正确性呢?事实上,我国心理辅导与咨询界很少研究的这一“价值参与”问题,恰恰是心理辅导与咨询的核心问题,它关涉心理辅导与咨询的哲学基础、目标取向乃至其理论与技术的“本土化”,所以必须予以澄清并给予明确的解答。
一
显然,要讨论心理辅导与咨询中的“价值参与”问题,就得首先回答这样两个相互关联的先决问题:其一,“价值参与”是必需(必要)的吗?其二,“价值参与”是必然的吗?
“价值参与”是必需的。何以必需呢?这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第一,在理论层面上,心理辅导与咨询存在的哲学基础之一是相信人(受辅者、来访者)是可以改变的,而“受辅者的改变首先是价值观念的转变”(注:樊富珉,王宏宇:《论心理辅导的哲学基础》,《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89页。)。因为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无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还是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价值追求都是人的本质的独有的重要特征,也是人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依据。人类如果没有价值追求,其精神向上提升和向外拓展无疑都将成为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个体成长的历程实际上就是个体不断实践其生活目标并将其生活经验内化为其价值系统的过程,而“一旦价值观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被内化,它就成为指引行为、对客体和情境所抱态度、对自己与他人以及比较自己与他人进行判断的标准与尺度。”(注:Rokeach,M.Beliefs,attitudes,and values,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68,P.16.)因此,心理辅导与咨询的核心就是帮助受辅者(来访者)建立适当的价值系统,促其心理健康发展并不断求达“自我实现”。虽然价值改造不是心理辅导与咨询的目的,但它无疑是达成辅导与咨询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既然心理辅导与咨询能促进人的改变、而这种改变通常包含着受辅者(来访者)价值观的转变,那么,作为辅导(咨询)关系中的“帮助者”的辅导员(咨询员),其价值参与辅导(咨询)就是必需的,否则受辅者(来访者)的价值观念的转变便可能缺乏转变的载体。因为人在现实生活中虽不是象行为主义学派所说的完全受决定,但也绝非像以人为中心学派所主张的完全的自主。第二,在文化层面上,心理辅导与咨询作为一种改变人的特殊的教育历程,它与其他教育活动的历程一样,必然要考虑“向什么方向改变”的问题,而这种考虑的可能选择便是让辅导与咨询中的价值取向符合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显然,这种价值取向的方向性是需要辅导员(咨询员)的“价值参与”来支持的。诚外,我们理应倡导并支持受辅者(来访者)在价值追求上的自主选择,但这种自主的“创造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背离社会公认的“一致”。试问:当我们面对的辅导(咨询)对象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接班人而他们的抉择能力又遇到困难,抑或他们的价值追求存在明显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完全地“不干预”(注:[美]马斯洛等著、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267、92、266、127页。)、完全地“任其自然”(注:[美]马斯洛等著、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267、92、266、127页。)吗?显然,以自由主义哲学为基础的“价值中立”原则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如果说这种基础与取向在信奉个人至上的美国尚有人批评的话(如舒尔兹对罗杰斯体系的批评),那么在重社会价值、重个人的社会责任的中国文化中,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完全的“价值中立”是可行的。一句话,在价值追求的指向性上,为了避免辅导员(咨询员)显得过于消极或完全受受辅者(来访者)的操纵,辅导员(咨询员)合理的“价值参与”是必要的。第三,在现实层面上,虽然理论家们对价值问题如何造成心理问题(即价值观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的认识或许有所不同,但对于价值取向模糊、价值评价偏差、价值认同失衡以及价值观念错位等价值观问题是许多心理问题的诱因这一看法是相当一致的。在学校和家庭中,我们所发现的一些被称为“问题儿童”的孩子,实际上更应该被看成是由价值观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许多辅导员(咨询员)在心理辅导与咨询实践中也发觉到,不少受辅者(来访者)的心理问题源于某些价值观的混乱或价值观的丧失,这甚至成为其心理困难的基本原因。譬如,辅导员(咨询员)都有体会,许多受辅者(来访者)的心理困难往往起源于某种“鱼和熊掌”的二难选择,而这种选择矛盾实质上便是受辅者(来访者)深层的价值冲突的表现。事实上,一些学者对价值观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既然如此,从心理辅导(咨询)改变的要求来说,辅导员(咨询员)的“价值参与”就是完全必要的了。
其实,心理辅导与咨询中的“价值参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然的。首先,完全的“价值中立”是不切实际的,也是难以真正做到的。价值中立是辅导员(咨询员)的价值中立,是辅导员(咨询员)在辅导与咨询过程中不做任何价值参与、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正如马斯洛(Maslow)所说的:“理想的情况是,医师的那一相当抽象的参照系统,他曾读过的教科书,他曾上过的学校,他对世界的信念——这些都绝不要让患者觉察到。”(注:[美]马斯洛等著、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267、92、266、127页。)实际上,这种“价值中立”正是也只能是一种“理想”。如果说我们把这种“理想”当作一种辅导(咨询)观念或态度尚且可行也有某种积极意义的话,那么,从实践操作和技术的角度看则是很难行提通的。试想一下,在辅导(咨询)过程中,辅导员(咨询员)在进行诸如“解释”(interpretation)、“指导”(directive)、“忠告”(advice)、“反馈”(feedback)“逻辑推理”(logical conseguences)以及“影响性总结”这一系列影响来访者的操作流程时,他(她)能始终严守完全的“价值中立”立场吗?没有辅导员(咨询员)必要的价值参与的这些技术操作,又如何使特定的受辅者(来访者)发生改变呢?显然,结论只有一个:除非从事的是非常刻板而机械的辅导(咨询),否则无法将辅导员(咨询员)的价值和信念排除在一切辅导(咨询)关系之外。其次,完全的“价值中立”是不太符合多数中国受辅者(来访者)的文化特质的。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有学者让来访者在心理咨询告一段落后填写一份调查问卷,对问卷中这样一个选择题——“你希望心理咨询员在心理咨询中,直接给出权威指导,还是利用药物和仪器治疗,或是经过自身的努力在咨询员的配合下改善?”结果是,绝大多数来访者希望在心理咨询时得到“直接的权威指导”,而不是“药物和仪器治疗”或“经过自身的努力在咨询员的配合下改善。”(注:叶斌:《掌握大学生现状,探索本土化道路》,《大众心理学》1999年第3期,第12-13页。)知名学者江光荣从自己的咨询经验中也体会到,我国的来访者比较易于接受咨询员的权威,有时甚至期待着咨询员的权威态度(注:江光荣:《心理咨询与治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显然,这一事实虽不能也不应该就因此让我们得出辅导员(咨询员)必须持权威态度或给受辅者(来访者)以权威指导,但这种特质的文化相对性至少说明一点,完全的当事人中心疗法不太符合中国来访者的要求,完全的“价值中立”在辅导(咨询)实践中不具有普适性。第三,“价值中立”即便在西方也只是部分咨询流派的理论立场和原则,并非所有流派的一致主张。例如,行为主义学派就认为咨询者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近三十年来极为受重视的理性——情绪疗法也有明显的价值干预倾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在价值问题的处理上,尽管西方心理咨询界在理论立场方面存在分歧,但在实践中却维持着一些为多数治疗者公认的原则,其中不乏与“价值参与”有关的要求,如咨询员应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承认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但共同认可的是那些社会公认的、有生命力的价值体系),遵循一批共同的价值准则(其中包含有“尊重真理”、“关心不让他人遭到损害等”),等等(注:江光荣:《心理咨询与治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这种奇特局面本身也证明了心理辅导与咨询中的“价值参与”的事实上的必然。
二
既然价值参与辅导(咨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接着就需要探讨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价值究竟该怎样参与辅导(咨询)呢?
从目前心理辅导与咨询的实践来看,“价值参与”的方式不外乎三类:“价值评断”、“价值澄清”与“价值导向”。所谓“价值评断”是指辅导员(咨询员)对受辅者(来访者)的价值观作好坏、正误判断,通过灌输或操纵的方式做价值的裁判,甚至替受辅者(来访者)做决定;“价值澄清”是辅导员(咨询员)在辅导(咨询)历程中帮助受辅者(来访者)澄清其价值追求,帮助受辅者(来访者)了解与体察自身价值观之间存在的矛盾及其行为的代价与后果;“价值导向”则是指辅导员(咨询员)在必要的时候引导(而不是代替)受辅者(来访者)作出价值选择,有时甚至引导(同样不是代替)受辅者(来访者)作出相应的改变选择。事实上,在这三种方式中,“价值澄清”与“价值导向”是难以分割的:“价值导向”是在“价值澄清”的基础上进行的,“价值澄清”既是“价值导向”的铺垫,也是“价值导向”的必经之路,而“价值澄清”的结果有时也就具有“价值导向”的意义。因此,辅导员(咨询员)的“价值参与”实际上就是在“价值评断”和“价值导向”这二者中作出选择。
那么在心理辅导与咨询的历程中,辅导员(咨询员)应持“价值评断”与“价值导向”哪种立场呢?显然,“价值评断”与完全的“价值中立”一样是不可取的。因为第一,人类具有理性、情感和自由意志,人之主体性和选择性的存在决定了受辅者(来访者)在通常情况下有自由选择和自我决定的权力。虽然完全的“价值中立”是不可行的,但简单而直接的“价值评断”势必扼杀受辅者(来访者)的价值追求,导致其自主权的丧失,因此有可能违背辅导员(咨询员)的伦理,也不符合心理辅导与咨询的本质。一句话,在价值问题的处理方式上,“价值评断”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价值中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第二,“价值评断”主要涉及价值的内容,这种重在对受辅者(来访者)价值内容的干预似乎超越了心理学的传统限定,因为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及其正确性通常属于伦理学的研究范畴。换言之,如果心理辅导与咨询人员不安“本份”,就很可能也很容易将辅导(咨询)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化。虽然要在辅导与咨询中完全杜绝价值内容的干预也是困难的,但我们依然要持有这样的理念(信念):在辅导与咨询中应给予受辅者(来访者)以最大的主动权和最大限度的自由,不应存在有直接地或暗示性地迫其接受某种价值的企图。既然辅导员(咨询员)不能替受辅者(来访者)做决定,也不能逃避价值判断,在心理辅导(咨询)中他(她)必然要扮演一种价值角色,那么“价值导向”就应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价值参与”的提法或许要比“价值干预”的提法更符合辅导与咨询的精神实质。
如果说“价值导向”是一种最佳的选择,那么又应该如何进行“价值导向”呢?它有可供参考的“模式”或操作“程序”吗?我认为,在已有的价值咨询的若干具体模式中,郝来(Hawley)的六因素模式是一种具代表性也具借鉴价值的模式。郝来将价值选择过程分为6种因素,前4种涉及选择过程,后2种涉及如何行动。具体序列是:(1)倾向: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2)影响:是什么影响我作出这一决定的?我是如何自由选择的?(3)可能:对于这一选择的可能替换方案是什么?我是否已对替换方案作了充分考虑?(4)后果:我的选择可能带来什么后果?我愿意为后果承担风险吗?这些后果对社会是有利还是有害的?(5)行为:我能够根据选择行事吗?我的行动确实与我作出的选择一致吗?(6)模式:这一选择能够持续地体现在行动中吗?我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以便让这一选择持续反映在我的行动中呢(注:转引自郑维廉主编:《青少年心理咨询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5页。)?郝来还进一步给出在课堂和团体咨询中帮助受辅者作出使其在感情上容易接受,并能导向成功的价值决策的三个步骤。可以看出,郝来的六因素模式重视受辅者(来访者)的自我分析、自我抉择,给受辅者(来访者)以充分的尊重,这有助于培育受辅者(来访者)良好的情感,也能适应各种类型的价值问题。但这一模式的有效性似乎仍过于依赖受辅者(来访者)的自主能力,其完全程序化所导致的机械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价值导向”的角度来看辅导与咨询中的价值问题的处理,我们可以把辅导员(咨询员)的“价值导向”归纳为以下几种方式:(1)价值澄清。帮助受辅者(来访者)澄清自己的价值取向,明确自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帮助受辅者(来访者)认识其价值观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冲突之所在。价值澄清的过程就是帮助受辅者(来访者)弄清楚他(她)自身价值体系的真正内容(真正向往的东西)并帮助澄清受辅者(来访者)在需求、价值和目标这三者间的冲突的过程。价值澄清的目的就是帮助受辅者(来访者)对内心冲突作理智的检查,自我分析“是什么,属于什么样的问题”。(2)价值归因。受辅者(来访者)在对动机冲突作出价值判断之后,辅导员(咨询员)进一步引导其运用理性推理的方式对自己的内心冲突进行归因,让受辅者(来访者)认识其价值观与行为和情感(乃至症状)的联系,并充分领悟到当前心理问题的起因、表现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她)的价值观念系统出了问题,从而产生通过处理自身价值问题来解决自身心理问题的愿望和决心。(3)价值选择。在价值澄清、价值归因的基础上,帮助受辅者(来访者)作出充分理智的价值选择(决策)。价值选择是“价值导向”过程中最具实质性的步骤,因为受辅者(来访者)的心理困扰往往表现为价值选择的困难。为此,辅导员(咨询员)在引导受辅者(来访者)作价值选择时可使用如下几种策略:其一,“价值优势”策略,即尊重在价值澄清中所确定的受辅者(来访者)感到最有价值的东西,帮助其实现自己的主要价值需求,并通过发掘其优势价值中的积极因素,领悟多种需求间的密切联系,从而尽可能兼顾其他需求。其二,“价值拓宽”策略,即帮助受辅者(来访者)充分发挥想象力,拓宽其价值选择,或每一种价值选择所具有的多种可能的具体选择,尽量探讨各种可行的方案。其三,“价值权衡”策略,即根据受辅者(来访者)的主客观条件,根据其意愿,帮助其权衡各种选择的利弊(后果),引导其选择更为有利于身心健康和发展也更加切合实际的价值观或目标。其四,“价值引入”策略,即辅导员(咨询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谈及自己的价值观或对某些价值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在某些时候有必要也被允许引入外在的价值观。但这种引入的目的只在于扩展受辅者(来访者)的视野,以帮助其获得更大的价值选择余地,而不是将“引入”的价值观强加给受辅者(来访者)。(4)价值干预。在心理辅导与咨询中,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在帮助受辅者(来访者)进行价值选择时,需要更大的宽松度。只要无损于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价值选择,都应被视为合理的,都在可以考虑之列。然而,事实表明,个人价值取向与社会价值取向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甚至会形成极大的反差。沙莲香对大陆中国人所作的“人生价值选择”的调查研究结果就说明了这一点(注: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页。)。因此,在辅导(咨询)中,对于受辅者(来访者)的那些明显与社会公德相抵触或损害集体利益的价值选择,辅导员(咨询员)有责任给予“干预”,加以引导,因为“正常的个性必须在个体的成长和社会亲合之间实现一种有益的平衡。”(注:[美]马斯洛等著、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267、92、266、127页。)对于青少年受辅者(来访者)来说,由于他们仍然处在成长阶段,辅导与咨询也有必要在道德方面给予引导。在这一领域,辅导与咨询过程事实上不可能是价值观充分自由的选择过程。当然,即便如此,辅导员(咨询员)仍然必须避免将价值观强加给受辅者(来访者),而是应该深入研究道德发展论和价值澄清过程,以便能够为受辅者(来访者)提供新的道德取向和道德思维。(5)价值认同。在价值澄清或作出相应的改变选择之后,辅导员(咨询员)应进一步引导受辅者(来访者)对确定的价值取向的自我认同,考虑并加强或引导改变受辅者(来访者)的生活模式,以便让其作出的价值选择能持续反映在他(她)的行动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心理辅导与咨询中的“价值导向”也是一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过程。一方面,“模式”及其“序列”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实际辅导(咨询)过程也并非就是上述“方式”的完整的“连续体”。不同的辅导(咨询)活动(如团体辅导与个别辅导),其“价值参与”的方式更是不尽相同的。此外,辅导(咨询)中牵涉到价值问题时,辅导员(咨询员)有时无法完全逃避价值评判(当然应尽量在自我内部隐蔽地进行),有时要杜绝价值内容的干预也是困难的。在辅导(咨询)的历程中,辅导员(咨询员)和受辅者(来访者)谁有多大程度的选择或决定改变的权力也应视具体的辅导(咨询)情况而定。因此,“个别性”、“灵活性”是辅导员(咨询员)应当乃至必须持有的辅导(咨询)观念。然而另一方面,对于处理价值决策问题,无论采取哪种“模式”或方式进行“价值参与”,辅导员(咨询员)都必须抱有以下四种价值信念:非简单评断、非价值说教、自我抉择和尊重。一句话,辅导员(咨询员)的职责在于帮助和引导而不是做决定。这就是辅导(咨询)过程中辅导员(咨询员)的“价值参与”的基本准则。为此,我们至少在观念上仍然可以重温并记取马斯洛说过的话:“作为这一过程的一种模型,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位医师,如果他是一位不错的医师并且也是一个不错的人,他决不会梦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患者或以任何方式进行宣传,或试图使一位患者模仿医师自己。”(注:[美]马斯洛等著、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267、92、266、127页。)
三
在心理辅导与咨询中,一旦“价值参与”、“价值导向”的角色、原则、立场和方法确立起来,如何保证这种“参与”、“导向”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就是我们最终要考虑的问题。那么,要想使辅导员(咨询员)的价值导向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和最终达成,我们还需要考虑并依赖什么样的条件呢?
心理辅导(咨询)的历程实际上就是辅导员(咨询员)与受辅者(来访者)的价值参与、交流和沟通的历程,也即是“价值导向”的历程。在这种历程中,即使辅导员(咨询员)没有直接向受辅者(来访者)宣传或灌输某些特殊的价值观,但他(她)一定在使用一套有关辅导(咨询)的哲学,即生活的哲学,而辅导员(咨询员)的生活哲学中自然涉及价值和道德伦理。因此,要使辅导(咨询)中的“价值参与”有效且不违背道德,辅导员(咨询员)自身必须具有坚定、明确、统一、协调且符合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体系。这就是说,辅导员(咨询员)一是应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有自己的价值观点,并对自己的价值取向有自觉意识;二是必须建立起一套积极的、与主流文化价值相适应的价值与伦理哲学,从而在辅导(咨询)实践中遵循自己所属文化中绝大数人公认的价值准则。由于辅导员(咨询员)有各自的价值观和生活哲学,这一方面就需要辅导员(咨询员)了解并明确主流价值观的内容,另一方面也需要全国的专业学会抓紧制定从业者的道德准则,以便规范辅导、咨询和治疗行为。事实上在这一领域,西方咨询界已经形成一批咨询员须共同遵循的价值准则。一些西方国家的全国性专业协会(如美国心理学会、美国咨询和发展协会等)也制定了成文的规范,其中规定了咨询家处理价值问题的原则和程序。当然,由于价值具有文化相对性,西方的“准则”只能参照,但对于我国的辅导(咨询)界来说,这一工作是必须要做的,而且越快越好。
辅导(咨询)关系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众所周知,辅导(咨询)过程是建立在辅导员(咨询员)与受辅者(来访者)良好的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的,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帮助受辅者(来访者)改变和成长的前提条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帕特森(Petterson)甚至认为咨询或治疗关系“就是一种人际关系”(注:转引自钱铭怡:《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因此,作为辅导(咨询)的基本要素之一,辅导(咨询)关系无疑是“价值导向”过程中受辅者(来访者)的一种重要的“心理背景”,它直接关系到辅导员(咨询员)与受辅者(来访者)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和价值互动能否顺利进行,直接影响到双方在价值问题上的感受、沟通、传达和接收,从而直接关涉到“价值导向”的成败。正如罗杰斯所总结的:“我从自身的经验中发现,如果我能设法造成一种真诚、尊重和理解的气氛的话,就会出现一些鼓舞人心的情形。”(注:[美]马斯洛等著、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267、92、266、127页。)因此,为了减少“价值导向”过程中受辅者(来访者)的心理阻抗,辅导员(咨询员)应着力于现实的辅导(咨询)关系的不断调整和优化。在这方面,辅导员(咨询员)应起主导作用,负主要责任。简单地说,在辅导(咨询)过程中,辅导员(咨询员)只有坚持承诺与责任、关怀与尊重、接纳与期望、权威与权力、真诚和同感等立场和信念,才能建立起良好的辅导(咨询)关系,而只有良好的辅导(咨询)关系,方能承载并预期“价值参与”过程中的“价值导向”的成功。
辅导与咨询中价值问题的处理也应结合认知与情感的因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有时需要将价值和认知结合起来,以认知为先导,通过论理、辨析、质疑、启发、说服、驳斥、剖析、合理化等方式,帮助受辅者(来访者)在理性层面上把握住最有价值的东西,并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有效而积极的人生哲学。实践证明,辅导员(咨询员)若能通过自己的工作将价值和认知自然融为一体,必有助于受辅者(来访者)应用更高水平的道德推理,从而不仅能帮助受辅者(来访者)恰当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也能帮助其更好地解决其他的价值问题。情感对价值咨询来说,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价值导向”中,价值的交流、沟通、传达、接收往往需要以情感为中介,没有良好的感情基础,理性就会显得苍白,认知也会失去依托。因此,在“价值导向”过程中,辅导员(咨询员)既要善于营造融洽的情感氛围,激发受辅者(来访者)对其价值追求的热爱,也要努力发展受辅者(来访者)积极的情感。正如心理学家开(Williamkay)所指出的,有必要使人类的文化进化朝向充满同情的思维,要教会儿童懂得互爱,因为这是积极的道德行为的基础(注:转引自郑维廉主编:《青少年心理咨询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页。)。
价值冲突往往还涉及到道德冲突。青少年受辅者(来访者)遇到的很多问题,实际上都与道德推理和价值澄清过程中的缺陷有关。怀特曼(Whiteman)等人发现,达到较高道德发展和道德推理水平的人,对他人的看法一般更为积极,对人类的看法也更为乐观(注:转引自郑维廉主编:《青少年心理咨询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页。)。因此,辅导员(咨询员)还有必要对社会学习理论、心理动力学理论、皮亚杰(Piaget)的道德发展理论和考尔伯格(Kohlberg)的道德发展理论等有深入的了解,也有必要对青少年的道德冲突的特点和道德教育加以细致研究。这方面的修养有助于辅导员(咨询员)了解受辅者(来访者)的道德冲突、道德决策和道德内化的过程,从而能帮助辅导员(咨询员)处理好受辅者(来访者)的这一类与道德冲突有关的价值问题。
标签:心理健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