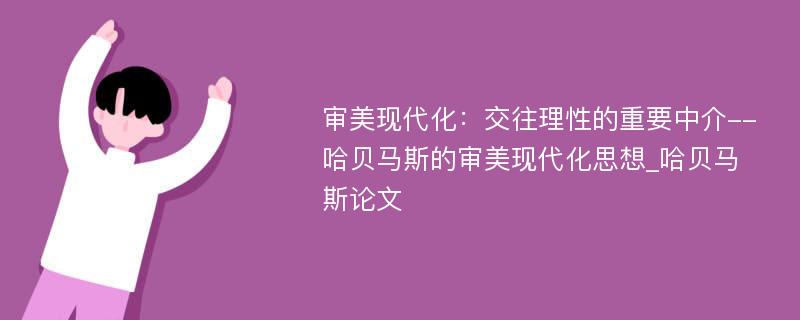
审美现代性:交往理性的一个重要中介——哈贝马斯的审美现代性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马斯论文,一个重要论文,理性论文,中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1-0031-05
从严格意义上讲,哈贝马斯并非一个纯粹的文艺理论家,他更多地关注的是哲学、社会学和语言学,而非文学或艺术,但是他在诊断现代性的危机时,还是非常客观地评价了审美现代性的作用。他认为审美现代性曾经是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先锋,它的创新品格和果敢精神很大程度上引领了现代性的发展趋势,但后来,由于它满足于对自身的模仿和重复,而陷入一种自闭和孤独的境地。不过,作为文化现代性的一部分,审美现代性仍旧担负着提升读者审美能力的重任,但是现实中大量无深度的作品并没有完成这样的使命,审美现代性被置于一种无足轻重的处境之中,它真正的身份应该如何?哈贝马斯认为,审美现代性应该作为交往理性的一个重要中介,促进主体间性、增强社会的整体性建构以及加强传统与现代联结,从而使得它们都能和谐、健康发展。
一、曾经的辉煌: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先锋
关于审美现代性的重要性,哈贝马斯认为它在现代性自我确证过程中扮演着先锋角色,因为“现代”一词首先是在审美批判领域中确定自己的。“十八世纪初,著名的古代与现代之争(‘古今之争’)导致要求摆脱古代艺术的范本。主张现代的一派反对法国古典派的自我理解,为此,他们把亚里士多德的‘至善’(Perfektion)概念和处于现代自然科学影响之下的进步概念等同起来。他们从历史批判论的角度对模仿古代范本的意义加以质疑,从而突出一种有时代局限的相对美的标准,用以反对那种超越时代的绝对美的规范,并因此把法国启蒙运动的自我理解说成是一个划时代的新开端。……因而,‘Moderne’、‘Modernitaet’、‘modernite’和‘modernity’等词至今仍然具有审美的本质涵义,并集中表现在先锋派艺术的自我理解中。”[1] 这表明在现代性的确定过程中,一些嗅觉灵敏的艺术家较早地从艺术上洞察到“现代”带来的变化,并试图界定这种变化,希望从这种变化中揭示社会现状。在他们看来,艺术上的这种新变化不应再被看做是对古代范本的模仿,它应是一种独属于这个新时代的私有品,或者说这种艺术上的变化在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由此可见,审美现代性率先扛起现代性自我认同这面大旗,并向传统宣告现代性的确立,现代性这个新生力量所拥有的冲击力和创造力是巨大的,它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整个世界也为之动容了,全球开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地球村”(麦克卢汉语)逐步形成了。
其后,波德莱尔深刻地揭示出现代的艺术作品身上所凝聚着的现代性“时间”特性:“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2] 他也揭示出美同时包含着绝对美与相对美,“构成美的一种成分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加以确定,另一种成分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一种,或是兼容并蓄,它像是神糕有趣的、引人的、开胃的表皮,没有它,第一种成分将是不能消化和不能品评的,将不能为人性所接受和吸收。”[2](475) 这说明,审美现代性可以从当代生活的“瞬间”中挖掘出现实性和永恒性的辩证关系,从“瞬间美”中凸现绝对美和相对美的依存关系,这些都是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重要前奏。而对于独立的、先锋性的艺术作品而言,波德莱尔认为它们必须不断地浸入到现实性之中,永不停歇地追逐和透析“瞬间美”,这样它们才会富有创新性,才会丰富现代性的内容。因此,“审美现代性的特征体现为在变化了的时间意识中探寻共同焦点的态度。这种时间意识通过前卫派或先锋派这类隐喻得以表现出来。先锋派就把自己看做一种对未知领域的闯入,并使自己处于突发的危险之中,处于令人震惊的遭遇之中,进而征服尚未为人涉足的未来。先锋派必须在那些看来还无人问津的领地中寻找方向。”[3] 由此可见,对于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现代性而言,谁来探究和涉足那些未知领域呢?在哈贝马斯看来,是那些富有创新和果敢精神的先锋派,他们敢于冒险、勇于创新、不计个人得失,他们虽经常受人讥讽和耻笑,被人误解,视作异类,但不可否认,现代性的许多问题被这些艺术家们深刻地揭示出来,让人们增进了对现代性的了解和对人类处境的认识。
但是今天,审美现代性的这种创新和果敢精神开始衰落了,如奥克塔维奥·帕兹(Octavia Paz)揭示的:1967年的先锋派没有给人振聋发聩的全新感觉,而是不断重复着1917年的先锋派的行动和姿态。此时的先锋派虽然号称先锋,但它早已没有早期先锋派的那种勇往直前、勇于探索的气质,他们变得功利和现实起来,希望凭借着“先锋”头衔为自己赢得利益和声誉,甚至有些人堕落为商品的俘虏和商家的宠儿。为此,他们只是模仿着早期先锋派的行为来制造轰动效应,来博得关注,但这种行为只是具有早期先锋派的创新之名,而没有他们的创新之实。这样的先锋派既不能解放人们的思想,开拓人们的视野,也不能引领人们去创造新的生活,也无助于现代性的建构。相反,“如果一种文学的主要目的是将一种特殊的消费行为强加给读者,它其实就是实践的,尽管这与先锋主义者所想要的那种实践性不同。在这里,文学不再是解放的工具,而成了压迫的工具。对于商品美学,我们也可以作出同样的评论,这种商品美学用来诱使购买者买下他们所不需要的东西。在这里,艺术成了实践性的,它是一种具有迷惑力的艺术。”[4]因此,当高举“急先锋”大旗的先锋派仅仅靠重复和模仿来聊以为生的话,那么从此层面上讲,审美现代性就不能再胜任确证现代性的重任了,这也是后来现代性要求助于哲学来确认自己的原因所在吧。
二、现实的困惑:对抗还是合作
当审美现代性不再具有创新精神的时候,那么它就不会再为现代性带来冲击力了,这样,审美现代性曾扮演的先锋角色也就不再有意义了,因此哈贝马斯说:任何认为自己是先锋派的人都会读到自己的死亡宣判书。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审美现代性就毫无存在价值了,哈贝马斯认为不是,因为虽然现代性的观念与欧洲艺术的发展有着直接关系,但现代性并不等同于审美现代性本身,它包含着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两大方面,而文化现代性又分成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分别具有认知—工具理性结构、道德—实践理性结构和审美—表现结构,它们分别关涉着知识问题、公正性问题和道德问题或趣味问题,因此审美现代性并没有失去价值,它已经成为了文化现代性的一部分,担负起了培养和提升人们的审美能力这个艰巨而漫长的任务。那么,化为了文化现代性的一部分之后,审美现代性的作用和身份该是怎样的呢?
其一,审美现代性曾尝试做现代性的“对抗者”,但它自恋的缺点使自己画地为牢,没有了现实性。哈贝马斯指出,当现代主义作品陷入模仿和重复早期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时候,它的那种现代性的“引导者”身份便被消解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寻找出路,现代主义换上了现代性的对抗者的服装,转而成为了现代性的批判者和否定者,希望以此为契机来推动艺术的发展。但是现代主义采取的不是直接的对抗,不是对现实的具体问题进行揭示和批判,而是以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来拒绝和排斥现实问题,以一种隐喻方式来讽刺和批判社会现状。可是,这种深奥、艰涩的现代主义作品不容易被大众阅读和接受,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虽然它深刻地、细致地描绘出都市的现代人的生活状况——失望和寂寞,灵魂空虚和失落,虽然它“以显微镜般的准确度来反映现代西方文明的矛盾和缺陷”,但是许多人对它的评价是难以读懂的“天书”,因此这样的反抗和斗争就成为了少数人的拼搏,而很难产生较大的社会解放作用。因此,“对抗者”身份这种转变并没有为审美现代性赢得更多生机,相反,这种“不合作”态度致使艺术更加自恋,愈加相信自给自足的重要性。“艺术成为一面批判之镜,它映射出审美与社会世界之间的不和谐特性。这种现代主义转变越是痛苦地加以实现,艺术越是与生活世界疏离,越是遁入完全自足而又无法企及的境况。”[3](144)在哈贝马斯看来,此时的审美现代性陷入了一种二律背反之中,它本来想以批判之矛来刺穿现代性华丽之盾,但它没有以“介入”(萨特语)方式进入现实之中来冲锋陷阵,而是以一种超然姿态来拒绝和排斥现实,从而构成一种所谓的批判。由于这种艺术作品是“曲高和寡”的,因此这种批判其实只是几个人的抗争,这样的艺术作品非但没有担负起解放大众的重任,反而使得大众对艺术的批判性产生了质疑,审美现代性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
其二,转变为现代性的“合作者”之后,审美现代性却陷入一种无足轻重的处境之中。在现代主义以超然姿态与现代性相对抗失败之后,超现实主义试图突破艺术自给自足的困境,尝试着改变艺术作为现代性的“对抗者”身份,转而扮演起现代性的“合作者”,希望促进艺术和生活和谐相处。为此,它所作尝试有:“把艺术与生活、虚构与实践、表象与现实削平到同一个平面,取消艺术物品与实用物品、刻意上演与自发实验的差异,宣称任何东西都是艺术、人人都是艺术家,取消各种标准并把审美判断等同于主观体验的表现”[3](144)。这种实验性的艺术行为虽然试图消解艺术作品的自足性,使艺术回归生活,希望改善艺术与生活、审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对立关系,使它们和谐统一起来,但结果却是差强人意。哈贝马斯指出,超现实主义的初衷是要显示出自己的叛逆性——改变此前艺术与生活的紧张关系,使两者和谐统一起来,但是它的两个失误滞缓了它的反叛计划。其一,当超现实主义消解了艺术的自足性的时候,艺术就无法依据自己的规则来塑造崇高形象,就无法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否定,那么,它在此方面上曾有的解放效果便不复存在了。其二,超现实主义的这种为协调艺术和社会关系而削平两者对立关系的方式,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艺术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但大量的无深度的艺术作品既没有为艺术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也不会使人更清楚认识社会现实,相反,它会降低艺术的批判能力和解放效果。也就是说,当审美现代性仅仅为了达成与现代性合作这样的简单目的,而放弃自己应有的自律性的时候,结果,这样的牺牲和诚意非但不能赢得人们的认可,反而会将它自身置于一种类似鸡肋的尴尬处境之中——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样,经历了现代性的“引领者”——“对抗者”——“合作者”三种身份变化之后,不尽如意的审美现代性将何去何从呢?哈贝马斯认为,审美现代性的最恰当身份是作为交往理性的一个重要中介,协调着主体间性,弥补着社会的分裂,连接起传统与现代。
三、恰当身份:交往理性的一个重要中介
作为交往理性的一个重要中介,审美现代性在促进主体间性、完善整体社会以及尊重传统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通过文学这个媒介,主体间性得以丰富和细致化。在论述文学公共领域时,哈贝马斯指出:文学虽是私人领域,充斥着私人话语,但它可以公布于众,接受公众阅读和批评,那么围绕着作品,作家与读者、读者与读者等可以进行交流,增进交往。例如,和读者一样,理查逊也会因他小说中人物的处境而替他们伤心落泪;为了消除现实与表象之间的差异,斯特恩把小说放在与公众相关的场景之中;斯达尔夫人经常在家中举办社交活动,饭后让所有在场者回家互相通信,以便把彼此当作作品中的写作对象。另外,通过作品,公众可以就公共问题展开讨论,这样既增进了交往和团结,同时也培养了公共意识,加深了对自身和社会的认识和理解。“通过阅读小说,也培养了公众;而公众在早期咖啡馆、沙龙、宴会等机制中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报刊杂志及其职业批评等中介机制使公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他们组成了以文学讨论为主的公共领域,通过文学讨论,源自私人领域的主体性对自身有了清楚的认识。”[5]从这个角度看,文学领域的交往除了提升了公众的审美能力和认识能力之外,也加强了公众之间的交往和对话,使他们因一些文学话题、现实问题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增进认识,增强团结。
其次,审美现代性有助于消除隔阂和仇视,有助于建构社会的完整性。在分析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时,哈贝马斯指出这些书简是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为什么他要赋予这些书简如此高的荣誉呢?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席勒强调了艺术的“公共特征”和“交往特性”,凸现了艺术具有弥合人际疏离和社会分裂的特效。席勒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物化特征和官僚政治,“不仅物化的经济过程像一架精巧的钟表,使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彼此脱节;独立的国家机器也是像钟表一样机械地运转,它使公民成为异己,并通过‘划分等级’把公民视为统治对象而纳入冷漠的法则”[1](53)。另外,他还揭露了科学日益专业化和抽象化的不良趋向,席勒斥责抽象的思想家常常有一颗冷漠的心,他们往往为了真理而分解一个整体的事物;指责那些务实的人具有一个狭隘的心,他们为了效率和成就而把自己禁锢在单调小圈子中,从不考虑与他人交往。资本主义带来了异化、分裂和隔阂,靠什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席勒认为不能靠物质至上的国家和道德至上的国家,而应依赖审美的创造冲动建立的“游戏和假象的快乐王国”。美既可以解决两性的永恒对立,也可以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整体中的冲突。“这时弱成了神圣的,而不可遏制的强反而成为耻辱,自然的不公正通过骑士风尚的宽宏大度得到改正。任何暴力都吓不倒的人,却被羞怯的迷人红晕解除了武装;任何鲜血都不能扑灭的复仇之火,却被泪水窒息了。甚至仇恨也要倾听荣誉的柔和的声音,征服者的剑也要宽恕已经解除武装的敌人;在恐怖的海边,好客的炉灶为陌生人冒起炊烟,要是从前,在这里接待他的只有杀戮。”[6]通过审美现代性的中介作用,社会中的仇恨、暴力、分裂等不良现象一定程度上被解决了,人际关系得到了改善,社会分裂现状得到了缓解,社会的整体性得到了增强。
最后,作为交往理性的一个中介[7],审美现代性还起到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纽带作用。哈贝马斯在分析本雅明的现代性思想时候,指出本雅明既反对一种空洞的时代观——它们固执地信仰进步,也反对把一切都相对化的历史主义——它们像捻念珠一样按次序来排列历史。对于本雅明而言,现代性并非完全值得称赞和认可的,因为“进步与野蛮”往往是如影随形的。另外,传统并非应该完全有用或完全无用,因此要批判地看待现代性,要辩证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本雅明认为,历史存在着连续性,但现代性对传统的继承不是单调的重复和模仿,而是通过大众的期待视野,借助“回忆”来选择传统中感受的碎片,从而实现对传统的拯救,把传统与现代紧密地连接起来。这与哈贝马斯所分析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再生产相似,文化交往可以促进传统的连续性与日常实践所需知识一致起来。当然,对于本雅明而言,拯救传统并不仅仅使人尊重传统,而在于借回忆传统来激发集体意识,促进主体交往和团结。“本雅明看到,他称之为世俗启示的幸福感全系于对传统的拯救。只有当我们在自己需要的眼光里用来解释世界的那种语义学潜能没有枯竭时,幸福的要求才能兑现。”[8]从此处看,哈贝马斯认为,本雅明拯救传统的终结目的是为了大众的幸福,是为了使大众真正地生活在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之中,这也是为什么本雅明矛盾地看待机械复制技术的原因所在。虽然复制技术消解了传统艺术的灵韵(Aura),但它使艺术走进了大众视野,使更多人参与到艺术创作、欣赏和再创造之中,使大众解放了思想,提升了审美能力和认识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本雅明无疑是肯定机械复制的。
总之,哈贝马斯梳理了审美现代性在现代性发展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从“引领者”、“对抗者”到“合作者”,最后到“交往理性的中介”,审美现代性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开阔,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它不再眷恋个人奋斗,也不满意于敌我之间的争斗和虚假的合作,而是从现代性的健康发展出发来关注主体间性、社会关系、传统的连续性以及大众的幸福,从而有效地发挥着艺术的解放作用。当然,在哈贝马斯看来,审美现代性自身还不足以解决现代性诸多问题,要想避免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错误和提高交往理性的作用,就不能把这种重任仅仅放在文化现代性的一部分——审美现代性身上,而必须挖掘文化现代性的全部潜能——科学、道德和艺术三者整体发展,这样才能既促进现代性的进一步发展,也能减少现代性许多不必要的危机。
